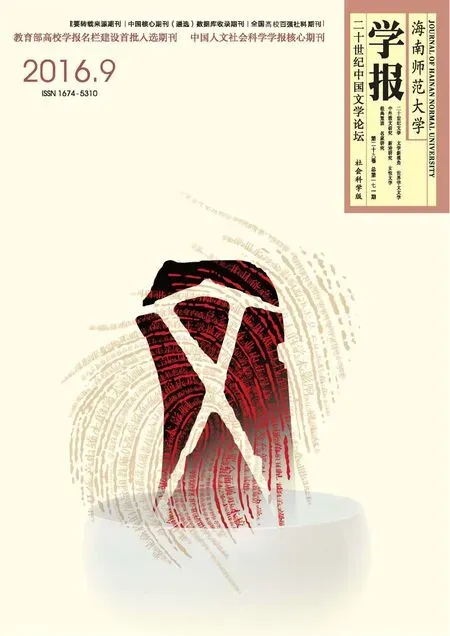场域转换与《朝花夕拾》的情感裂隙
2016-03-16李彦姝
李彦姝
(教育部 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0)
场域转换与《朝花夕拾》的情感裂隙
李彦姝
(教育部 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0)
《朝花夕拾》创作于1926至1927年间,发轫于北京、续写于厦门、修订于广州,诞生于鲁迅辗转漂泊的人生旅途中。其间鲁迅经历了被北洋政府通缉、与许广平相知相恋、南下任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历史事件或个人遭遇。地域环境的转换、个人经历的更迭、社会时局的变迁等,使散文中暗藏着相当程度的情感裂隙:在北京的创作反映出对于社会境况的不满和讥讽,在厦门的创作流露出温情与落寞相杂糅的回忆之美,在广州的创作体现出虎落平阳、壮志未酬的理想幻灭。视角在回忆与现实的两端游移,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鲁迅思想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鲁迅;《朝花夕拾》;场域转换;情感裂隙
鲁迅的创作一向与悲凉、幽暗、战斗这类词扭结在一起,把笔触伸向个人“回忆”是少有的事情。如此说来,散文集《朝花夕拾》①本论文所引《朝花夕拾》文字均出自《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可算作一次偏离轨道的创作旅程,其流露的审美风格、折射的生命意识与鲁迅其他文章迥然不同。读《朝花夕拾》不难发现,鲁迅不仅擅于以笔为剑,凭借悲愤犀利的语词刺穿社会的黑暗,也擅于以温润的心灵去感受沐浴生命之光,以平和的姿态缅念往昔岁月的静好,以质朴的情感眷恋既杳渺又真切的故土与亲人,以细腻的心思捕捉日常生活的灵光等等。
《朝花夕拾》所射出的不是刺眼的烈日强光,而是含情脉脉的一抹夕阳。为何《朝花夕拾》会在1926至1927这短短一年多颠沛流离的经历中破土而出呢? 厘清《朝花夕拾》创作的时代背景与地域环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卓尔不群的价值和内涵。《朝花夕拾》的创作起始于北京、延续至厦门、封笔于广州,诞生于鲁迅辗转漂泊的人生旅途中,其间经历了被北洋政府通缉、与许广平相知相恋、南下任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或个人遭遇。《狗猫鼠》、《阿长和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五篇作于北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 》五篇作于厦门;最后于广州修订成册,并写小引与后记。因为创作场域的转换,所以这部散文集看似浑然一体,实则文本内部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情感裂隙。鲁迅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久。环境也不一样。”
一
分析作于北京的数篇散文,绝对绕不开当时的政治语境。卷入北京女师大风潮(1924年至1925年)、“三一八”惨案(1926年)以后,鲁迅在北京失去了公职,并与周作人、许寿裳等文教界人士一起被北洋政府通缉,这期间他为了避难,先后辗转于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朝花夕拾》里在北京期间所写就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体风格——有细腻的记叙,有犀利的议论,也有引经据典的考证。写作视角时而流连于过去,时而又回到现在,将对现实的讽刺批判夹杂在复杂的回忆之情中。此时,鲁迅在现实与回忆的天平上周旋游移,“在回忆往事中不忘社会启蒙的追求,仍旧进行着文化批判,并且视野异常开阔”*庄汉新:《中国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狗·猫·鼠》作于鲁迅寓居北京的后期,正是他因“女师大风波”与“现代评论派”笔战之时。这篇散文可以被看做鲁迅“闲话风”散文的代表作。“‘闲话’也称‘漫笔’,不仅是题材上漫无边际,而且是行文结构上的兴之所至的任意性。”*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这种“任意性”深切表达了鲁迅深陷政治风波时心境的杂芜和凌乱,欲远离世俗尘嚣而不得的矛盾心理。谈到仇猫的理由,鲁迅主要列出两条: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和讨好苟且的一幅媚态。猫缺乏虎狮一般的刚烈和强硬,猫软弱、世俗、叫嚣……而这些均指涉了鲁迅眼中“现代评论派”浮滑、不彻底的伪君子文风。最初,现代评论派倾向于北洋政府,拒斥国民革命,后来看到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又转身投奔革命。鲁迅从这类人的骑墙心态中看到了革命的危机,现代评论派的投机举动恰恰与鲁迅所倡导人生的严肃性、纯粹性、彻底性背道而驰。《狗·猫·鼠》的前半段都是在以畜喻人,夹叙夹议,具有浓厚的隐喻性和讽刺性,继承了鲁迅一贯的“嬉笑怒骂”的杂文风格。但是鲁迅没有将这种文风延续到底,而是突然笔锋一转,从现实转入到回忆:“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把现实的不快抛到一边,充分沉浸在回忆的情境中,这之后,便尽是些幽默、诙谐、充满童趣的文字了。原来,儿时仇猫的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讲述童年时对于宠物隐鼠的喜爱。描写了对于“老鼠成亲”这一传说的神往,记录了蛇与鼠这对天敌间的周旋与博弈,讲述了了长妈妈误伤隐鼠而嫁祸于猫的经过……童年的幸福正隐藏于此类看似无甚意义却摩挲心灵的奇闻轶事中。作者饶有兴味地追忆幼时听祖母讲故事的情景:“那是一个我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边,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人与动物、植物、自然浑然一体,构成一幅温馨和谐、令人沉醉的夏夜图景。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又从时光机器中跳脱出来,从现实中来,又回到现实中去,首尾呼应,再一次表达了对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讥讽和不满:“我大概也总可望成为所谓‘指导青年’的‘前辈’的罢,但现下也还未决心实践,正在研究而且推敲。”人届不惑之年,现实与回忆展开交锋是自然之事。同一个命题之下,鲁迅对于世态炎凉的认识日渐深刻,既以现实的姿态与论敌针锋相对;又以温暖的笔致与儿时的趣味欣然重逢,使得已悄然远去的童年记忆重新发酵。
在《二十四孝图》中,作者批判了“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故事中所折射出的伪善的传统“忠孝观”。这套忠孝观念随着时代推移,已经很少有人真心去实行,却被当作经典来教育一代又一代国人。作者谈到“郭巨埋儿”给幼小心灵留下的阴影:“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一个原本用来教育后辈行孝的故事,反倒造成了亲人间的隔阂,这是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巨大讽刺。《无常》一文,作者明则写鬼,暗则喻人;明则写古,暗则喻今。鲁迅评价无常:“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无常虽在阴间,属摄魂之鬼,但它对人间、对将死之人竟怀着那样的怜悯和恩赐。鲁迅凭借“无常”之名,一方面回忆了幼时参加迎神赛会的生动景象,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于现实生活中“人生无常”的慨叹,由“生的苦趣”,联想到人世间的“公理”不存,于是生发了对于阴间的向往。鲁迅本人的经历似乎也印证了“公理之不存”的说法:“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庄钟庆、庄明萱:《两地书·集注(厦门-广州)》,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8页。动荡的时局以及浇薄的人心,使鲁迅不便于直抒胸臆,然而又不甘于放弃战斗。作者的思绪游离于回忆和现实之间,现实的幽暗、世事的缠绕,让他不能彻底地沉浸于妙趣横生的儿时记忆。虽将一系列文章归入“旧事重提”的行列,但是陈酿中掺杂了新酒,回忆之门时开时合、有所遮蔽。回忆带有几分伪饰的色彩,更像是一个幌子,为的是衬托出借古喻今之义。北京生活希望之不存,使鲁迅必须另辟蹊径,继续生活。
1926年8月22日,鲁迅于离京前夕在女师大演讲时说:“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未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鲁迅:《记谈话》,阎晶明选编:《鲁迅演讲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年,第45页。“存在”可以理解为还原并皈依朴素的生命和生活本身,鲁迅正是带着所谓“存在之希望”远赴厦门的,南下之行既暗含着收敛锋芒、韬光养晦的企图,也可视为返璞归真、回归日常生活的选择。
二
1926年9月,鲁迅从上海登船,次日来到厦门,就职于厦门大学。许广平也启程奔赴广州工作。此时,鲁迅已经远离了北京的是非,虽然在厦大也为人事而烦心,但是鲁迅毕竟算是逃离了政治风波的漩涡,开始了一段较为安逸闲适的学者生活。另一种慰藉源自爱情,在厦门的135天时间内,84封“两地书”成为了他和许广平友谊、恋情的见证。这种书信交往的方式,也使鲁迅适时宣泄了内心的苦闷,使他的内心变得柔软平和,冲淡了他对于外部现实的敏感和关注。
鲁迅在厦门度过的是一段宁静欣喜与落寞无聊相互交杂的时光。文风较为平和,思绪辽远,对于日常生活、自然世界、亲人朋友的回忆星星点点,落笔成文。“以眷恋、珍惜、伤感、感伤、了悟来替代那空洞而不可解决的‘畏’和‘烦’。”*李泽厚、刘绪源:《“情本体”是一种世界性视角》,《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3期。即使偶尔向着现实投去一瞥,也代替不了对于往昔回忆的深情和专注。鲁迅在厦门,一直未间断地与许广平通信,这些信件从侧面折射出他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态。厦门是一个潜心作文的好地方,鲁迅谈到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时说:“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时,才坐下来做文章。”*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与北京相比,鲁迅的厦门生活大致是舒心的,既远离了穷苦,“薪水不可谓不多”*庄钟庆、庄明萱:《两地书·集注(厦门-广州)》,第21页。,又远离了繁忙:“我的能睡,是出于自然的,此地虽然不乏琐事,但究竟没有北京的忙,即如校对等事,在这里就没有。……和在北京的天天提心吊胆,要防危险的时候一比,平安得多,只要自己的心静一静,也未尝不可以,暂时安住。”*庄钟庆、庄明萱:《两北书·集注(厦门-广州)》,第60-61页。
爱情的力量,使鲁迅的童心被唤醒,让鲁迅重新发现了自己身上那种温柔细腻的情感,使得鲁迅重新对朴素的日常生活投入热情,并将笔触重新伸向已逝的童年时光。与许广平的通信中,鲁迅常提及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展现出其亲近于世俗生活的一面:“饭量照旧,这几天而且更能睡,每晚总可以睡九至十小时;但还有点懒,未曾理发,只在前晚用安全剃刀刮了一回髭须而已。……此地的点心很好;鲜龙眼已吃过了,并不见佳,还是香蕉好。”*庄钟庆、庄明萱:《两地书·集注(厦门-广州)》,第22页。
但是,这种生活状态对于一位精神斗士而言不免太过寂寥,鲁迅多次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提及其心无定所的游子心态:“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至极。”*庄钟庆、庄明萱:《两地书·集注(厦门-广州)》,第17页。“其实此地对于我的身体,仿佛到好,能吃能睡,便是证据,也许肥胖一点罢了。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高兴,好像不能安居乐业似的。”*庄钟庆、庄明萱:《两地书·集注(厦门-广州)》,第17页
与此同时,由安闲而滋生的寂寞正是通向文学创作(尤其是回忆体文章)的一条正当路径。回忆所需要的温情由纷至沓来的信笺滋养,回忆所需要的宁静与寂寞由厦门的地理环境孕育,由此,鲁迅借助温情和宁静,打开尘封的记忆之门。如果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温情、深邃的宁静和深切的寂寞,单为现实嚣扰所累,很难说他能够那样彻底地进入到回忆的隧道中去。《朝花夕拾》中作于厦门的五篇散文,可以看作是鲁迅远离中心,寄身孤岛的“闭关”之作。
人沉浸在具体而细微的生命体验和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品味、珍惜和回首的方式,找寻情感之依、生命之根。它是“散步的时候偶尔在路旁折到的一枝鲜花,是路边拾起的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9页。。日常生活是现实的存在,童年回忆是沉淀的存在。两者相结合,便体现出鲁迅欲从童真中搜寻意趣、从“存在”中寻找希望的真义。在《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对孩童日常玩耍情景的细致描写:“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在我们十分熟悉的这段文字中,充斥着饱满丰富的意象和蓬勃的生命气息,作者以童年的视角,用简洁明快的文字,对于百草园中的花鸟树虫等大大小小的生命,从视觉、听觉、味觉上加以描摹,正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些卑微、少为人们所关注的意象在鲁迅笔下复活,与童年快乐时光相得益彰。
“人”是回忆中最生动也最深刻的因素,鲁迅此时的散文中出现了人物群像:父亲、长妈妈、衍太太、藤野先生、范爱农……父亲早逝,在鲁迅心中父亲形象是模糊的,而《父亲的病》中病痛缠身的父亲形象复活,鲁迅回首父亲临终前的一幕,流露出深挚的思恋之情和悔疚之意。少年无知般的喊叫打破了父亲临终时的平静安详,这成了鲁迅永远的隐痛。《父亲的病》和《琐记》中都出现了衍太太这个人物。作者以极简的笔墨勾勒出邻家中年妇女衍太太身上的戏剧性。她圆滑世故、口是心非,对自家孩子严加管教,却怂恿邻家的孩子们去“吃冰”、“打旋子”、“偷东西”……但是她的所作所为在小孩子眼里看来却是莫大的善良和宽容。作者虽然被衍太太的流言所伤害,但是时过境迁,回忆衍太太的时候,怨恨已经渐渐消散,作者可以超然地一笑而过。剩下的只是对这个戏剧性人物善意的嘲笑,丑行蜕化为笑谈,正如萨义德在谈到自己回忆录时所说:“写这本回忆录的主要理由,当然还是我今日生活的时空与我昔日生活的时空相距太远,需要连结的桥梁,这距离的结果之一,是在我重建一个遥远时空与经验时,态度和语调带着某种超脱和反讽。”*[美]萨义德:《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彭淮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页。
回归童年记忆,回归日常生活,鲁迅的记忆之门和细腻情感完全敞开,在厦门的日子里,鲁迅固然流露出被寂寞包裹的游子心态,但这种心态亦可成为温情回忆的催化剂。走异路,逃异地,于他乡,念故土,鲁迅在南国写就了一段柔软而鲜活的童年诗篇。
三
1927年3月,鲁迅南下广州去中山大学执教,与许广平及好友许寿裳同住广州白云楼,将“旧事重提”这十篇散文集结成《朝花夕拾》,并在此完成了小引和后记。
鲁迅来到广州有与许广平相聚的用意,但就鲁迅的本心而言,厦门的生活太过消磨意志,适合于短暂休憩,不适于人生长久之计:“这里的惰气,是积四五年之久而弥漫的,现在有些学生们想借我的四个月的魔力来打破它,我看不过是一个幻想。”*庄钟庆、庄明萱:《两地书·集注(厦门-广州)》,第208页。安逸生活太容易磨损人的锐气:“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不料有些人遽以为我被夺掉了笔墨了。……我先前对于青年的唯唯听命,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庄钟庆、庄明萱:《两地书·集注(厦门-广州)》,第194页。去广州,是为了爱情,是为了摆脱涣散的惰气,更是为了在短暂停顿之后继续在精神之路上前行。鲁迅用了“野心”一词形容他赴广州的目的:“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但是,现实难遂人愿,鲁迅来到中山大学不久,国民党就策动了“四·一二”政变,毕磊等30多名中山大学学生被捕,鲁迅多方营救无果。年过不惑的鲁迅对于生命无常、世态炎凉早已深有感触。“五四”时期发出“呐喊”声的鲁迅,此时无助地落入到无所归依的“彷徨”情绪之中。
《朝花夕拾》小引中的文字写于1927年5月,分别对于创作背景、命名原由、回忆的真实性等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此时,离“四·一二”事件距离很近,鲁迅颇有虎落平阳、壮志未酬的“百无聊赖”之感:“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
带着积极的入世心态来到广州,结果却还是要返回到记忆洞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现实距离太近,是难于被归纳描述的,记忆须经过时间的发酵沉淀,经过空间的辗转漂泊,才能彰显出它的珍贵和魅力。记忆是一处避风港,以对逝去韶光的怀念,来对抗现实的死寂与灰暗,徘徊犹疑的生命脚步可以暂歇于此,以励再行。
那么,记忆与昔日的现实又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呢?鲁迅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幻想的美妙总是悄然屹立于现实的庸常之上,当幻想唾手可得之际,人们才恍然大悟,觉得不过如此、意兴阑珊。记忆也是想象的一种,是人对于过往生活有所选择的想象。回忆的内容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在所难免,“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回忆被过滤、被沉淀进而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了的、“理想性”的想象。
至于后记,作者写后记的目的本来“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却不料又写成了一篇颇有点“掉书袋”意味的长文,“或作或辍地几乎作了两个月”。对正文中《二十四孝图》的引用错误进行勘误,对于《百孝图》不同绘制者、编纂者的态度进行比较,赞赏胡文炳删除“郭巨埋儿”一章的“勇决”,隐约批评了“纪常郑绩”先生“模棱两可”态度——这自然与鲁迅所一贯反感的“不彻底性、不纯粹性”相呼应。后记还罗列了曹娥投江、老莱娱亲、活无常等不同版本的插图,对其来历和典故娓娓道来,对不同作者的画风一一点评,批评了世道的浇漓轻浮、以“肉麻”为“有趣”的低俗趣味,以及以“史料”冒充“学问”的不良风气。
这篇后记“漫谈式”的写作风格,更像是一篇精心考据、精彩论证的杂文——是文体上的天马星空,亦是情感上的疏离杂芜。恐怕其原因仍是作者的寂寞:在史料上用力,是“很新颖的,也极占便宜”。这让人联想到当初辛亥革命落潮之后,鲁迅对于佛经、碑拓的收藏和研究兴趣。正是对于当下失去了兴趣,才会对古迹萌发出兴趣,主观情感被客观史料所淹没。此一点,乃正是鲁迅作此后记时的心境——如果说写于北京的文章中还带着点对现实的恨意,写于厦门的文章中满怀着天真雍容之爱,那么作于广州的小引和后记,则流露出作者看尽沧桑、宠辱不惊的平静和落寞。广州见证了鲁迅雄心之重燃至希望之幻灭的起落过程。希望之幻灭并不是终点,在情绪的低位上固然有令人沮丧的现实,也有痛定思痛后选择新路的权利。
《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历程中的一个异数,但又是鲁迅整体思想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当他对当下的现实感到消沉无助、对未来的选择感到迷茫恐慌时,他将思绪从社会转入到自身,从现实转入到回忆,却又从未真正地远离社会现实。《朝花夕拾》更像是鲁迅思想进程中的一条“缝隙”,缓解了彼时鲁迅的思想困境,它既是彷徨失落中的回望,也是重振雄风前的砥砺,没有情感的波动和沉潜,也就没有日后勇士的复出。
(责任编辑:王学振)
Field Transformation and Emotional Fissure inLifeisaMoment
LI Yan-shu
(CenterforSocialSciencesDevelopmentandResearchinInstitutionsofHigherLearning,MinistryofEducation,Beijing100080,China)
Written between 1926 and 1927,LifeisaMoment, initiated in Beijing, continued in Xiamen and revised in Guangzhou, was produced in the course of Lu Xun’s vagrant life journey, during which he had undergone historical events or personal encounters such as his being wanted by the Beiyang government, his acquaintance and love with Xu Guangping, his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he south,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coup on April 12, etc. The changes i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social events have replenished his prose with some emotional fissure, namely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and satire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embodied in his prose written in Beijing, the beauty of reminiscence mixing warmth with loneliness demonstrated in his writings in Xiamen, and his disillusionment of ambitions mirrored in his works written in Guangzhou. The switch of the perspective between reminiscence and reality is indicative of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Lu Xun’s thought during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Lu Xun;LifeisaMoment; field transformation; emotional fissure
2016-09-03
李彦姝(1983-),女,辽宁大连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和电影批评等研究。
I206.6
A
1674-5310(2016)-09-0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