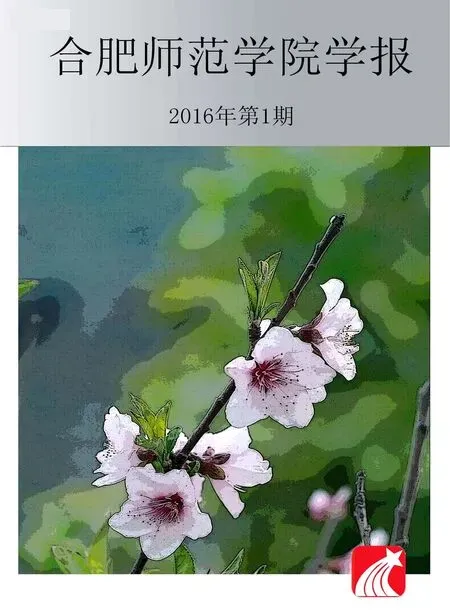《无主之家》中的战争创伤“记忆”
2016-03-16钱全
钱 全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无主之家》中的战争创伤“记忆”
钱全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海因里希·伯尔的《无主之家》从战后德国儿童和妇女视角,描写了孩子们破碎的家庭记忆,在父亲形象的缺失、母亲形象的背离中揭示了战后儿童的心理创伤。战争寡妇的精神窘境和无奈选择让主人公感到切肤之痛。小说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和它所带来的心理的创伤的难以愈合,提醒人们不能忘记战争,更要直面历史。
[关键词]战争;心理创伤;历史记忆;道德反思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8)是当代德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4 年,伯尔发表了他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主之家》,在这部小说中,伯尔将他的写作方向由从直接描写战争残酷性转向描写联邦德国战后小人物日常生活的主题。作品对两位阵亡战士家庭中缺失丈夫和缺失父亲的孤儿寡母生存状况作了详细描述,这样的家庭在战后的德国绝不是特殊的个例,而是构成战后西德社会的主体,是一种真实的常态。丈夫缺失和父亲缺失的“无主之家”是战后德国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伯尔适时地反映这个问题,不仅对人的社会生存和心理状况给予关注,而且要求读者对战争历史和当前的社会现状进行深入的反思。其用意,就是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提醒读者万万不可忘记战争,更不可忘记历史。
一、破碎的家庭记忆
《无主之家》中,伯尔通过两个少年主人公的角度,以两条线索展开,运用回忆与现实生活情景不断交叉出现的叙事方法,为读者呈现出两个由于战争而不再完整、支离破碎的家庭的生存境况。小说中的两个少年主人公,小马丁和小布里拉赫,都在战争中失去了各自的父亲,从而使得他们无法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对家庭的记忆充满了心酸与苦涩。
(一)父亲形象的缺失
伯尔在小说的最初两章通过对二人父亲照片的描写,向读者描绘出了两个父亲在生前的大概形象:小马丁的父亲是一个爱笑并稍显腼腆的年轻人,而小布里拉赫的父亲在照片中则是一个佩戴着铁十字勋章的面带微笑的小伙子。他们给自己孩子所留下的真实的记忆几近于无,伯尔在小说中直接交代了布里拉赫的母亲是在她分娩后两个月就收到了丈夫在战场上去世的噩耗,也就是说,小布利拉赫几乎是一个遗腹子;而小马丁的父亲伯尔在小说中虽然并没有直接说明去世的,然而通过一些侧面描写也不难推知小马丁应该也没见过父亲的面。因此,两个孩子对父爱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时常在梦中幻想自己父亲是什么样的,但往往求之而不得, 在梦中他们看不清父亲的脸,父亲就“像个突然闯入梦中的陌生人”。而现实中,他们对父亲的概念也是畸形的,小马丁天真地认为父亲的标准就是“早餐有鸡蛋”、“生活有规律”[1]6,因此他总是觉得照片上的父亲并不想一个真正的父亲,太年轻、太无忧无虑了。事实上,小马丁对父亲的理解来自于一个和他的亲人住在一起的一个男人——他父亲的战友——阿尔贝特,在生活中,阿尔贝特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像父亲一样照顾着小马丁,但在小马丁的内心深处,阿尔贝特与“父亲”这个概念终究还是不能完全划上等号的。相比较小马丁,小布里拉赫对父亲的理解则更加模糊,或者说他对“叔叔”的认识更加深刻。“在他的意识中,做母亲的都得有个叔叔”[1]12,而因为家境窘迫,世道艰难,他的母亲不得不经常给他换“叔叔”, 一个个“叔叔”像幻灯片一样更替,使得他虽然对“父亲”的概念缺乏理解,却能将“叔叔”分出类别。但是不论怎么说,自小失去父亲的残酷现实所给两个孩子所带来的创伤是无比沉痛的,他们对父爱的渴望永远不会停止。
(二)“母亲”形象的背离
父亲和母亲是孩子家庭生活的两根支柱,当其中一根折断时,另一根就在孩子今后生活中显得尤其重要。小说中的两个小主人公在从小失去父亲、缺乏父爱的情况下,他们对来自母亲关怀的渴望就愈发强烈。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母亲应该给予他们双倍甚至更多的关怀和全方位的保护,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至少满足他们成长过程中基本的需求,而在精神领域,更是应该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心灵的慰藉。然而不幸的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在失去丈夫后,因为各种各样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或者对生活感到无趣、空虚,或者为生计而委曲求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己孩子的需求,尤其是与孩子在情感上的沟通。不可否认的是,她们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她们留给孩子的记忆与观感却不尽如人意,从而直接导致了两个孩子对母亲的感情态度上充满了矛盾与困惑。
以布里拉赫家为例。布里拉赫家的经济状况已经不能简单的用拮据来形容,因为战争的原因,在布里拉赫太太生小布里拉赫时,她的全部财产不过就是一个装着少量钱、粮票、一条别人给的脏毛巾和几张丈夫的照片的手提包,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于是他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那个战争年代生存下去。布里拉赫太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依附于一个又一个男人以维持生计;而小布里拉赫更是在五岁半时就为了养家而游走于黑市,通过帮助邻居在黑市买东西赚取佣金以贴补家用。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布里拉赫每天面对的就是金钱带来的压力和母亲身边时常更换的“叔叔”,每天当他从黑市回到家时,他多么想要得到母亲的陪伴和宽慰,然而母亲为了维系那个临时的、畸形的“家庭”,不得不将本该用于照顾小布里拉赫的精力,放在了应付小布里拉赫的“叔叔”身上。当母亲和卡尔叔叔坐在沙发上耳语,发出吃吃的笑声时,小布里拉赫憎恨她;当母亲向面包师讲出那个描述男女结为一体的粗俗的词语时,小布里拉赫开始觉得她变得冷酷;当莱奥叔叔指责小布里拉赫“贪污”,母亲对他产生怀疑、哪怕只是片刻时,小布里拉赫的心如刀绞一般,甚至用罢工的手段报复了母亲。这些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中不该出现的状况,在一般正常的母子关系中不该产生的矛盾,都给小布里拉赫幼小的心灵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小布里拉赫在内心深处依然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但是这些矛盾所带来的心灵之间的缝隙却永远无法弥合。
而小马丁的家庭虽然富足,不像布里拉赫家那样需要为生计挣扎,然而母亲内拉因为丧夫带来的创伤而流连于各种社交活动,也同样忽视了小马丁的感受。每当小马丁一个人躺在床上,隔壁母亲和她所谓“朋友”开party的噪声传到他耳中时,他就忍不住诅咒他们;当小马丁听到楼道里传来的那些拜访的陌生人的笑声时,他就恨他们的脸,恨他们带来的礼物,恨他们的一切。他渴望能和母亲待在一起,哪怕不说话,可是母亲却总是离开他,不陪在他身边,他对母亲的态度和小布里拉赫一样,都充满了矛盾,爱恨交织。小说中,两个母亲现实中的形象与孩子心目中母亲应有形象的背离,是伯尔着力刻画的一点,正是对战争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的控诉。
(三)儿童心理的异化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在幼年时所受到的不恰当的照料方式,尤其是情感上的疏忽和早期的分离,都会导致发育过程中思维以及行为的异常,并在心灵上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2]413马丁和布里拉赫二人自幼丧父,母亲对他们的关爱又不够,加之生活中来自或经济上或社会舆论等方面的压力,使得两个孩子的心理逐渐开始异化,脱离了他们那个年纪的儿童所应当拥有的正常心理。
两个孩子的母亲,内拉出没于各种舞会、party或是研讨会,常常晚归或是彻夜不归,一连许多天都是如此,各种各样的男人无论是为了她的金钱还是姿色,都不时地拜访她、邀请她,向她献殷情,甚至直接的追求她,于是内拉的母亲就常常责备她“你又到哪儿鬼混去了?”,外面也有人称她为“半个交际花”;而布里拉赫太太更是因生活所迫,不断地跟不同的男人同居,搬家时被邻居说闲话,学校的老师和教会的牧师也称她“不洁德”。这些外界对两个孩子各自母亲的流言蜚语,并不会因为他们还是孩子就远离他们,他们开始可能是不经意得听到一些,后来慢慢地就变成有意的去打听到底自己的母亲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关心的话题不再是正常十一二岁的孩子所关心的玩具、游戏,而是道德的标准。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自己的母亲在道德上是不是高尚的,在贞操上是不是完美的,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不结婚,不结婚和“叔叔”住在一起是不是符合道德标准这一类普通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根本不会考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的问题,布里拉赫甚至还跟马丁聊起过母亲与面包师之间关于“男女结合”的事情,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们,使得他们的心理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扭曲,变得畸形乃至异化,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不洁德的,因此许多人不知羞耻”,而布里拉赫因为五岁半时就为了养家而游走于黑市,整日寻摸着如何才能省钱,更是产生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以“金钱”为标准的道德观。
总而言之,父爱母爱双重的缺失、残酷现实的压迫,加上从小在由于战争而不再完整家庭中长大,他们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心酸,他们对家庭的记忆也变得支离破碎,由这带来的心灵创伤,久久无法弥合。
二、“寡妇工厂”的斑驳阴影
在“二战”中,德国法西斯政府通过狂热的民族主义宣传,以“爱国”的名义,通过政府征召的方式从无数原本完整幸福的家庭中,将一个又一个丈夫从他们的妻子身边带走,送上残酷的战场,当战争结束时,能够安然回家的丈夫少之又少。战争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寡妇工厂”,源源不断地制造着数不清的破碎的家庭和失魂落魄甚至绝望的寡妇。
伯尔在《无主之家》中塑造了两个因为战争而失去丈夫的寡妇形象——内拉和布里拉赫太太,然而两人又因为家境的不同,所以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
(一)战争寡妇的精神窘境
内拉是一个富家小姐,他的父亲的果酱工厂在一战期间得到了飞速发展的机会,因为饥饿岁月对果酱厂总是好的。良好的家境,加上和丈夫赖的两情相悦,她的生活本该如童话般美好。可惜的是,战争从来都不会因为你是富家千金就对你网开一面,丈夫赖在战争中因为上司格泽勒的刁难而殉难,失去丈夫的打击让内拉一蹶不振,在她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从此内拉的精神世界因为创伤而与现实的世界割裂,充斥着空虚和白日梦,她逐渐对一切事物都不感兴趣,打不起精神。正如拉卡普拉(LaCapra)在《书写历史,书写创伤》中所说:“创伤是一种破坏性的经历,这个经历与自我发生里分离,造成了生存困境;它造成的影响是延后的,但影响的控制是很艰难的,或许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的。”[3]41内拉就处在这种创伤的阴影下。她并非甘愿一直消沉下去,但失去丈夫的巨大伤痛在她心里所留下的阴霾绝非朝夕就能消散的,过去与赖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和现实中失去赖的苦痛时刻折磨着内拉的心灵,最后只能借助流连于各种舞会、研讨会或是邀请客人来家里开party来打发时光。“她总是做她本不愿做的事,不是虚荣心的驱使……只是一种想漂游的感觉刺激着她去随波逐流,上下沉浮,其实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思。”[1]22,这么做并不代表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反而“这种献殷勤的人她结识得越多,她就越加爱自己的丈夫”[1]23。直到有一天,格泽勒这个将她的丈夫送到死神手中的始作俑者,竟然在神父的推荐下登门拜访,还恬不知耻的请求她参加关于赖的诗歌的研讨会,甚至还想追求她时,内拉竟然发现自己对这个“切断了自己生活”并将剩余的四分之三人生扔进了废物间的投机分子连恨也不值得,只觉得无聊,而自己只是“寡妇工厂的产品”。 在面对新的感情、婚姻和生活时,她心里充满矛盾,一方面她渴望得到幸福的生活、炽烈的爱情;一方面她又害怕再一次失去。她开始抵触婚姻,恐惧结婚,以致后来她明明爱着阿尔伯特,可当阿尔伯特提出想和她结婚,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时,她却总是坚定的拒绝着,她对阿尔伯特说:“只要你愿意,我马上做你的情人……比妻子更忠心,但我不会再结婚。……根本不结婚也许还更好些……三百万、四百万这样隆重热烈的婚姻协定被一场战争毁灭,只剩寡妇们。”[1]97究其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原因,是因为在她经历过那些痛苦的体验后,她明白战争的残酷是不会因为纳粹宣传中高呼的几个口号——“领袖”、“人民”、“祖国”就减轻的,所以她最终选择拒绝婚姻,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可能再一次成为寡妇的伤害,或者说,过去的创伤记忆使得她无法再次开始进入一段正常的婚姻。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宁可做个风流寡妇也不做微笑的妻子”[1]177。
(二)战争寡妇的无奈选择
布里拉赫太太与内拉有着不同的处境。她没有内拉富足的家境,本就贫寒的她在失去丈夫,生下小布里拉赫之后,生活变得更加的拮据。作为一个年轻的寡妇,毫无疑问的,她也渴望能够再有一段美好的爱情、美满的婚姻。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得无奈的她只能通过出卖肉体,一次又一次的给自己的儿子换“叔叔”,因为在当时战后的德国,如果她想要和她的儿子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军人烈士“寡妇”的身份所带来的补贴是她无法拒绝的。她与“新生活卡尔”有过一个孩子,却被她自己去医院打掉了;后来与莱奥又有了个女儿,莱奥却让她去做流产,即使最后生了下来,莱奥也完全不准备尽到父亲的义务。终于,当她因为无法支付高昂的牙医费用,她又一次要给小布里拉赫换一个叔叔了,她要搬到有妇之夫面包师家里去住免费的房子。虽然如此,可是从小说中描写的细节不难看出,布里拉赫太太真爱的人始终是小布里拉赫的父亲,她的丈夫。她总是将丈夫送给她的一个“当时是灰色,现在已经磨得黑不溜秋的麂皮钱包”随身带着,而且每次搬家,无论“叔叔”换了多少,“父亲”的相片总是摆在正中的位置。
无论是内拉出于害怕再次成为寡妇而拒绝婚姻的自卫行为,还是布里拉赫太太更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已出卖肉体和尊严,都不过是身处战后德国那样艰难环境下的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在经历创伤事件后正常的进行自我保护的应激反应。凯西·卡鲁斯说:创伤事件可以造成创伤受创者在“时间、自我和外部世界”经历的断裂[4]4,受创者同时存在于“两个现实,两个时间点上”[4]92,这种创伤记忆与正常记忆的无法融合,最终导致了受创者身体、精神与灵魂处于各自分离的状态。而究其根源,实际上她们都不过是战争的受害者,政治的牺牲品,是“寡妇工厂”的产物而已,而像她们这样被“寡妇工厂”的斑驳阴影遮盖的妇女与家庭,在那战后的德国,又有谁能够统计的清楚呢?
三、对历史记忆的不同态度
告诫人们不能忘却战争,要正视历史,这是伯尔终生为之奋斗的大事。在小说《无主之家》中,伯尔塑造了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物形象,他们对过去的历史记忆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一)对战争记忆的有意回避
格泽勒是马丁父亲生前所在部队的上司,是直接将赖送向死亡的凶手。在俄国战场上,格泽勒仅仅为了验证普通士兵是否绝对服从上尉的命令,就强迫赖去执行一项明知不能成功危险性很大的侦查任务,赖果然就被俄国人击毙了。格泽勒在小说中只是一个配角,但是这个配角被多次提到,他是一个滑稽的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他是一个玩弄权术把士兵的生命视如草芥的罪人,然而当战争结束时,他摇身一变,竟然厚颜无耻的成为了诗人战士赖——那个被他直接“谋杀”的可怜人的热心研究者。他对纳粹和战争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每当提到战争,提到纳粹将军的名字时,他的脸色就会熠熠发光;但是对于赖曾经是他下属的事情,他却假装忘记,他总是说:“我要向前看,我现在的任务是享受生活。”当内拉告诉他自己的丈夫牺牲了,他轻率地说:“我知道,别人已经告诉我了,我早就知道了,谁不知道这个啊?”他说,他并不记得曾经认识过赖,尽管在战后他非常热衷于对赖诗歌的研究。他想将过去战争中的罪行通通忘记,正如他自己说的,“已经把我的记忆一点一点斩尽杀绝了。该把这场战争忘却了。”[1]225-226伯尔在刻画格泽勒这个人物时,绝不仅仅是把他当做一个孤立的文学形象塑造的。在战后的德国,像格泽勒这样在战时犯有罪行,战后却选择回避的人多不胜数,他们有的是因深受战争的创伤而不愿回首,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却仍然选择闭口不言;有的则是如格泽勒一般,故意将自己在过去的罪行选择性遗忘,甚至美化自己不堪的历史,他们并不为曾经的错误忏悔,反而用拥抱明天的借口去开始所谓的新生活,他们在战后的社会中竭力伪装自己,使自己看上去如天使般纯洁,而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是伯尔最害怕也最不能容忍的。
(二)对战争记忆的直面反思
与格泽勒相反的阿尔伯特是马丁父亲赖的幸存战友,在马丁父亲去世后,阿尔伯特和马丁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小马丁和内拉。在内拉不在家时,他会关心小马丁的一切日常生活;在内拉夜里从外面归来时,他会为她准备食物与咖啡。他数次向内拉提出要与她结婚,但都被拒绝,他的出发点是帮助内拉走出赖死去带来的阴影,给她和小马丁一个完整的家。在事实上,他扮演了“继父”和“丈夫”的双重角色。同时,他对纳粹和战争的态度与格泽勒是完全不同的。他因为曾经在敖德萨的军事监狱里夜间老鼠从他脸上爬过而害怕老鼠;他告诉小马丁,格鲁姆没有牙齿和头发是因为他在集中营带过;为了教育小马丁不要忘记战争的罪恶,阿尔伯特曾经带着小马丁去参观一处纳粹暗设的小小集中营,向小马丁讲诉他的父亲和自己是如何在纳粹分子的严刑拷打下度过三个昼夜的。当小马丁告诉他校方对于纳粹罪行的宣传一直是轻描淡写甚至忽略不计的,因为另外一个“可怕”的事情掩盖了纳粹的可怕性,那就是“俄国人”时,他严肃的告诫小马丁,永远要记住历史。在马丁眼里,阿尔伯特叔叔是孤独的,因为“他必须面对那么多认为纳粹没有多么可怕的人们”。
格泽勒与阿尔贝特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物,实际上表现了战后德国民众对于过去那段历史的两种态度。通过格泽勒人物形象的塑造,伯尔意在告诫读者,某些军国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在战后披着无辜的外衣混迹在普通百姓之中,他们妄图将战争留在历史之页上的创伤淡忘,甚至抹去。而阿尔贝特形象的塑造,实际上代表了伯尔自身对于历史的态度,那就是只有直面历史,敢于揭开历史上留下的伤痕,才能真正弥合留在人们心中的创伤。伯尔在小说中对格泽勒之流的冷嘲热讽,正是他对那些受到法西斯主义毒害却既不为回首往事、也不为良心折磨所苦的人的严厉追索,是对于弥散在生活之中的法西斯细菌的无情荡涤。[5]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对德国人要“摧毁记忆”感到忧心忡忡,他说:“法西斯主义还活在人们心中;人们常说的清理过去至今没有成功,而扭曲、蜕变成为空泛冷漠的忘却。”伯尔清楚的知道,战争摧毁的不仅仅是有形的建筑,随着纳粹编制的神话一个个的破灭,人的信仰、信念、价值观也受到致命的打击,他曾借他的小说人物之口说过:“只要战争造成的创伤还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流血,战争就永远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6]4德国战后给百姓带来的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创伤,而是长期的深刻的伤痛,这种创伤,更多的是作用于心灵的创伤,而心灵的创伤远不像肉体的创伤那么容易愈合。如格泽勒之流,一味的对过去采取回避态度,或许可保一时的光鲜亮丽,可在其掩盖之下的,是伤口不断的恶化,以致重蹈覆辙、无可救药;而阿尔贝特,或者说伯尔对待战争、历史记忆的态度,则是直面历史,记住历史,这并不是不断地刺激已经溃烂的伤口,相反地,是为了最终的痊愈而剜去伤口周围的腐肉。《无主之家》中小马丁和小布里拉赫这样的失去丈夫、失去父亲的家庭,在战后的德国不计其数,伯尔通过主人公的切肤之痛,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和它所带来的心理创伤的难以愈合,提醒人们不能忘记战争,更要直面历史。
[参考文献]
[1]海因里希·伯尔.无主之家[M].倪诚恩,徐静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丁玫.为了灵魂的纯洁而含辛茹苦——艾·巴·辛格与创伤书写.[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3]Lacapra D. Writing History , Writing Trauma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4]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Baltimore and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5]张志忠. 废墟上崛起的自由斗士——论海因里希·伯尔 [J]. 山西大学学报,1992,(3).
[6]倪诚恩.无主之家·译者序[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何旺生)
The Memories of War Trauma in the “NoMan’sHouse”
QIAN Quan
(SchoolofHumanities,JiangnanUniversity,Wuxi214122,China)
Abstract:Heinrich Boll's “No Man’s Ho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and women in post-war Germany, which described the broken family memories of children, revealed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of those children in post-war, by characterizing the image of the father in absence, of the mother in departure from the normal. The spiritual dilemma and helpless choices of war widows had the protagonist to feel painful experiences. The novel showed people the cruelty of war and it was so difficult to heal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reminding people never to forget the war, but to face the history.
Key words:war; psychological trauma; historical memory; moral reflections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6)01-0098-05
[作者简介]钱全,男,安徽芜湖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