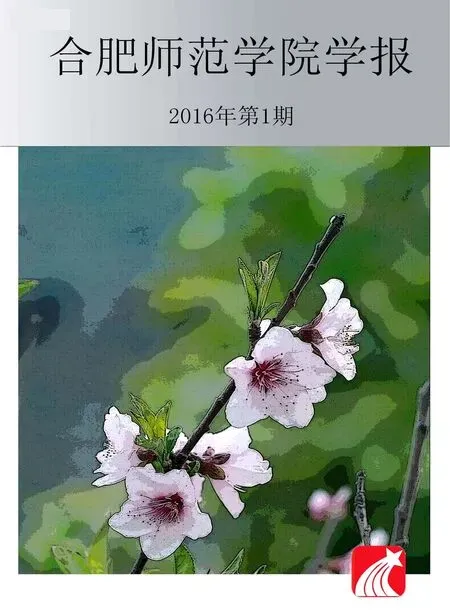从“地方性知识”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2016-03-16龚光明
龚光明
(阜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从“地方性知识”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龚光明
(阜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地方性知识”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的知识,产生后会借助现有条件或创造条件,发展成为“普遍性知识”。为使“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普遍性知识,董仲舒一方面通过神化皇权获得汉武帝的支持,另一方面使儒家借助阐释灾异得以参与政事,从而获得儒儒者的支持。并吸纳时人普遍了解的科技成果,使“天人感应”理论获得更多社会大众的认可与接受。因此,“天人感应”理论不仅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征,而且从地方性知识发展成为了普遍性知识。
[关键词]“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情境;地方性知识
每一种思想观念或知识体系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带有特定的“地方性”特征。汉代“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是当时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是董仲舒等人对这些条件认识与把握的结果。董仲舒认识到大一统的政治需要统一的社会思想,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在此基础上,利用汉武帝笃信鬼神上帝的思想,通过阐述儒家经典《春秋》所载灾异使其与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构筑了天人互感的理论体系。
一、从“地方性知识”看“天人感应”论产生的条件
吉尔兹认为,“事物的发展趋异而非趋同”[1]127。因此,他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为了“回应普遍主义、一致性规则与观念。”人们生活在各自差别的多样性环境中,不可能以同样的象征符号体系来认识、传达和解释社会。因此,“地方性”并非仅指特定地域性与特殊性,还包括特定的属性,涉及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立场、观念及价值观等[2]。可见,“地方性知识”并非“地方性”一词所直接反映的表面意思,更强调知识产生和发展所需的特有情境,即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具体的社会环境或自然条件,抑或两者的共同作用。特定社会或自然情境使知识带有“地方性”特征,成为“地方性知识”。既然“地方性知识”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并得到辩护的,因此对知识的考察应着眼于其形成所需的具体情境[3]。
汉代独特的社会条件为“天人感应”理论的创立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其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乃至自然因素都产生了作用,它们共同组成“天人感应”理论“地方性”的独特情境,使其成为具有汉代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把“天人感应”理论看成是“地方性知识”,必须从其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认识。
1.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是“天人感应”理论创立的首要前提。长期战争造成社会凋敝,百业待兴,汉初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经过几代努力,景帝时经济逐步恢复,国力强盛,国家政权得以巩固,“无为而治”已不适应社会需要。除黄老之学外,儒、墨等学派都很活跃,对封建专制制度构成一定威胁,因此大一统的政治迫切需要思想上的统一。到好大喜功、希图大有作为的汉武帝时,他更需要一种理论体系从天道的角度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及维护封建专制制度[4]47。董仲舒在回答武帝的策问时,认为:“今师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维护与巩固。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如果禁绝六艺以外不属于孔子学说的思想,则“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随下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
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得借《春秋》所载灾异阐发其灾异观,表明“地方性知识“先是批判的,然后才是建设的,即具有矫枉和“颠覆”的意义[3]。批判意味着某种已有知识已失去其赖以形成和得到辩护的特定情境,新的情境需要建设新的知识。因此,首先要认识与把握情境要素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已有知识出现何种不相宜的内容,然后对其中不适应新情境的内容进行修正、批判直至抛弃,从而为新知识建设创造条件。董仲舒从政治与思想相统一的角度,提出思想统一对于封建国家专制统治的重要性,实现了儒学独尊的局面。因此,大一统思想对当时历史的发展有积极作用[4]42。
2.汉武帝笃信鬼神和先秦以来“天人感应”观念成为董仲舒学说又一前提。中国整个封建时期,统治者都在为自己的政权寻求“君权神授”的依据。儒家的“天道”观恰好满足了统治者的这种需求,这也正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立其为正统的主要原因。所以,汉代社会鬼神崇拜、巫术迷信等风靡一时。汉武帝的策问说“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汉书·董仲舒传》)?“符”即“符命”,即封建帝王受命之符兆,目的是为鼓吹“君权神授”、神化皇权提供依据。汉武帝为使社会认可其皇权受命于天,需要贤良们为其寻找依据。而关于灾异缘起之问,则使仲舒有了把《春秋》所载灾异与人事相关联的借口。
先秦人格神的“上帝”、“天”等观念为“天人感应”理论的创立准备了基础,“天道无亲”等都是此观念的表现。《诗经·邶风》中已包含“天人感应”观念,面对大自然灾异的警示人们仍我行我素,因而引起诗人的忧患[5]41。说明殷周时天命观已存在,天、人已被关联起来。《吕氏春秋·应同》论证了五行相生相克,并提出“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观点。战国后期,邹衍提出五行相生、五德终始观念,但还没被用于解释灾异现象,先秦时期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还没结合在一起。
3.“天人感应”理论。以上述内容为基础,董仲舒创立了“天人感应”理论,而天人感应首先“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出现”[6]138。他利用《春秋》所载灾异,大肆宣扬灾异与人事之联系。认为“异”之害大于“灾”,是后者的发展。因人事过失,天对人事的反应由“灾”转换为“异”,“甚可畏也”。体现了天、人之间稳定的联系,天总能及时根据人事作出反应,“人事”成为其后每个环节的原因(《汉书·董仲舒传》)。并根据“人事”对“天象”的影响程度,论证了“天”的感应等级:灾害总发生在过失初现之时,随着过失的继续而逐步升级,显示灾害―怪异―伤败之序(二端)[7]345-346。体现了上天对人君的关爱。
董仲舒通过论证天人同类、同类相感,再加上“气”的中介作用,阐释了天、人相感的必然性。他把人之头、发、五官、四肢、骨骼乃至性情等,都和天作了对应,得出“天人同类”的结论(人副天数)[7]800,805。冯友兰认为:“‘天人同类’的观念是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论的一个理论基础。”[8]64既然天人同类,同类相应则理所当然。阴阳变化与宇宙万物、人类社会之间都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可以互相感应,“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同类相动)[7]814。同样,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与天也是同类,两者之间也存在感应(官制象天)[7]492,钟肇鹏先生认为,《官制象天》论述官制取象于天,“官制、人形、天数都是相通的。此亦仲舒天人相类、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之一端”(官制象天)[7]483。天有五行,五行相生相胜,人类社会应设置五种官制与之对应,顺应阴阳、四时、五行规律,社会就安定,反之则有祸乱[7]845。既然各方面都“相类”,天人感应就顺理成章了。通过引入阴阳五行概念,董仲舒为建构“天人感应”学说的广厦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吉尔兹认为,文化之本质既非物质性亦非观念性,或为二者简单混合。人类行为皆是符号活动——一种受其本身观念及其所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所支配的有意义的活动。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作为表象的人类行为符号实则蕴含着丰富的、交织重叠的、深层次的社会内涵[9]5,11-12。“天人感应”理论“表象”的背后,是那个时代“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这种文化背景是政治、经济、思想等多种因素共同编织的网络,共同对知识的产生起作用,这也就注定了“天人感应”理论的“地方性”特征,使其成为“地方性知识”。
二、从“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的转化看“天人感应”论的兴盛与传承
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那种认为“主张地方性知识就是否定普遍性的科学知识”的观点是一种误解[3]。相反,普遍性知识是由地方性知识发展而来,知识都要经历由地方性到普遍性的过程。即便万有引力定理,不仅生成于当时英格兰特定的情境,而且其被看成普遍有效,也是因为辉格党的政治胜利或殖民化的顺利进展等社会文化因素所致[3]。可见,万有引力定律成为世人认可的普遍性知识之前,需先成为地方性知识,而其成为普遍性知识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可以说,普遍性知识都由地方性知识发展而来,起源于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但其产生后能否得到有效辩护,在辩护过程中受众范围有多大,决定于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如果地方性得到众多社会成员的认同与接纳,就获得了转变为普遍性知识的可能,这种可能还包括将来世代的认可与接纳。同样,普遍性知识在一段时间后会随着其赖以产生或存在的情境条件的变化或消失,认可与接纳的范围会不断缩小,普遍性最终将会消失。体现了由普遍性向地方性,再到消失的转化过程。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也是先从地方性知识开始,然后得到汉代社会乃至以后历代的认可与接纳而成为普遍性知识的。可以说,董仲舒在初创“天人感应”理论时,为使其发展为普遍性知识开辟了道路。
1.把“帝”与“天”关联起来,赢得汉武帝的支持。在博取汉武帝对儒学的支持后,董仲舒极力神话封建统治。他对先秦“人道”本于“天道”的观念作了系统发展,认为“天道”是“人道”变化的依据(《汉书·董仲舒传》),人之“道”必须依据天之“道”而变,天之“道”不变,人之“道”就没有变化的根据。他认为天的地位最为尊崇,“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7]940。
接着,通过分析古代造字法把皇权与天的尊崇地位关联起来,把“王”神话,王是天、地、人之间的贯通者,理应代天治理万民(王道通三)[7]732。在“天人相类”的基础上,对“天子”做了进一步发挥,“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为人者天)[7]702,705把人君纳入“天”的神权系统中,人君代天而统治万民,使君权与天命紧密相关,神化皇权。君是“天”之使者,万民必须服从。“‘君权神授’从提高至上神的地位和权威而提高帝王的地位和权威。”[10]177-178董仲舒通过“人道”本于“天道”、王乃“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天子受命于天”三个层次,神话了人君,凸显了其万民之主的地位。这自然符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胃口,满足了其权力欲望,从而得到其支持。
2.借灾异参与政事,得到儒者支持。董仲舒在神话皇权的同时,也限制了王权,儒者得以借阐发“天意”实现治世目的。因此,“天人感应”说对于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一面。
董子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7]48托言《春秋》,首先阐发了君乃万民之主的观念,万民应顺“天意”,甘心受制于“天子”。但君权的至高无上,人间已无可抗衡的力量,遏制了儒家参与政事的愿望。鉴于此,董仲舒借助“天人感应”理论,最终限制了君权,满足了儒者“入世”的愿望,故要“屈君而申天”。所以,董仲舒把天人感应思想建立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真正目的是“为监控君主提供一个通达天人的渠道”[11]。
武帝信奉鬼神,不怕人但怕天。董仲舒根据儒家伦理道德要求指出,万民之主的人君应为万民做出表率首先“正心”,如此万民才能顺从,社会才会安宁(汉书·董仲舒传)。“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现,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现。”(王道)[7]193为君者只有正己,方可顺天意,绝灾异。
又说,天生民不是为王,立王却是为民(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7]498。王为民而设,理当为民服务。民受制于君,君听命于天,而天之视听来自民,民处于统治秩序的最底层,而天却是民意的反映,“民”是起点也是终点。因此,天人感应的真正作用在于限君权、申民意,“伤败乃至”的实现者正是民众,民是“天意”的最终实现者。现实社会中,朝代更替多由人民来完成。从此意义上说,是人民在行“天道”,是人民给不遵“天道”的统治者以最终惩罚,使有丧国之痛。
“天意”是什么?“天”给不出答案,这就给人提供了“联系”天、人的空间。既然儒术已独尊,那么“天意”只能由儒者来表达。但是否真是“天意”,只有解释者自己清楚。董仲舒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地阴阳)[7]1089“天意”通过阴阳五行之气显现,观察气的变化可知天意。“气”是天、人“感应”的中介,“灾异以见天意”(二端)[7]347。上天的警告是对人君的仁爱,给他改过之机。只要他愿意改正,就可继续其统治;否则,就会灭亡。“由此,天压制了专制人君的权利,使之不敢胡作非为”。[12]169既然“天之立君为民”,能使民安乐,天就立其为王;残害人民,天就使其覆灭。“君”的德行决定其能否长久统治。但不会过错始现就覆灭其政权,在灾异警示不知悔改时,才会亡国灭种。“这就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当作天意劝皇帝采纳,又以亡国相威胁,带有几分强迫性。谁又能强迫皇帝呢?天,只有天,董仲舒找到天。”[13]158
这是儒家企图参与政治决策而采取的手段。膨胀的皇权遏制了儒家治世欲望,正常的途径被堵塞了。董仲舒巧妙地借用神化之“天”限制皇权,顺利实现儒家的参政愿望。徐复观也说,“屈民而伸君”为虚,“屈君而伸天”是实[14]344。汉代帝王常因灾异而自责,有时还采取免租、减刑等措施,正是“天人感应”说产生积极作用的体现。“臣下则通过‘灾变’取得了与皇权协商与整合的可能,‘谏诤’也由此获得了某些相对的合理性”。[15]191-192古代几乎年年有灾,臣子们利用灾异进谏或指责皇帝,及时提醒其省事节欲,纳贤安民,有利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
3.以汉人认可的科技成就美化“天人感应”,以获得人们的支持。董仲舒吸收当时的科技成果以增添“天人感应”的“科学”色彩,“天人感应”理论也反映了时人对天、人关系新的思考。“天人感应”中两者的感应是互相的,“天地之阴气起”,“人之阴气”随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同类相动)[7]814,肯定了人事引起“天”的感应与天象引起人事的感应具有同样效果,不再是先秦单方面的“人道”本于“天道”的被动状态。
董仲舒的气之说,“正是从当时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中吸取了适合于自己需要的思想资料”[8]54-55。董子认为阴阳五行皆气,为天地万物共有,人、天“相类”,阴阳五行之气也充斥人体。秦汉时的《内经》说:“地为人之下,大虚之中者也……大气举之也”。即是说,“地处于广大虚空之中,而虚空又充满了气”。[8]54
《周易·乾卦》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吕氏春秋·应同》中的“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都阐述了同类相感的道理,并分别以火就燥、水流湿等以及音律学中的“鼓宫而宫应,鼓角而角动”的道理,为同类相应提供事实依据。《吕氏春秋·精通》还有“慈石召铁”。都是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最新科学成果,被用于证明天人感应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同类相感”被用于推测未知领域,使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具有了某种真实性。董仲舒列举了当时尚无法解答的十大难题作为其神秘主义见解的论据,并总结说:“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既已有之矣,或者吉凶祸福,利不利之所从生,无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郊语)[7]903。这些未知现象引起时人好奇,激发其探索自然的兴趣。当时的动植物、天文、气象等方面的知识,尤其动植物生长发育的季节韵律,成为宣扬天人感应论的科学论据。董仲舒充分利用人们认同的知识,作为自己学说的理论依据,使其理论获得认可、接受。
三、结语
“天人感应”理论也反映了汉人在对天地人统一体认识的基础上,向大自然寻求解决途径的尝试。董仲舒的天包括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三方面意义,他力图把三者加以统一,构成一个体系[6]122。人类改造、利用自然,难免破坏其间的和谐。一旦超出自然能够承受和修复的程度,就会发生灾害,危及人类安全。董仲舒们虽未认识到这种关系,但觉察到灾害与人类活动有关,是人类活动感应“上天”的结果。他们有自己的认识路径,视天人为同类,同类就能相互感应,相信一切无法认识的自然奥秘都操纵于神灵,“天”则是众神之“神”。灾异的发生正是“人之曾祖父”──“天”对人君的警示、谴告。因此,“天人感应”并非完全迷信,其中有合理的成分,是人类探索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尝试。
“地方性知识”产生于特定的地域环境或社会环境,都打上深刻的地方性或时代性特征。同时,某种地方性知识在特定情境中产生后,便会寻求发扬光大的途径,即升级为普遍性知识。为此,需要适应大众社会的普遍需求,亦即使地方性知识成为更多或者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知识,实现其由地方性向普遍性的转换。“天人感应”理论形成于汉初特定的社会情境,是董仲舒对当时社会环境现实认识与把握的结果,并通过神化皇权、吸纳人们认可的科技成果等,使其受到更多社会成员的认可与接受,从而由地方性知识发展成为普遍性知识。
[参考文献]
[1][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M].北京:三联书社,1994.
[2]黄丽萍.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与本土化民主发展取向[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5).
[3]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
[4]魏文华.儒学大师董仲舒[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5]公木,赵雨.名家讲解《诗经》[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6]金青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9][美]吉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0]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1]李耀南.尊君与屈君--董仲舒之天的二重功能[J].孔子研究,2004,(4).
[12]刘国民.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3]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M].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85.
[1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陶有浩)
On Dong Zhongshu’s “Telepathy between Heaven and Mankind” from Perspective of “Local Knowledge”
GONG Guangming
(School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FyyangNormalUniversity,Fuyang236037,China)
Abstract:“Local knowledge” is the knowledge produced in special context, and then it will develop into “universal knowledge”. In order to make the theory become universal knowledge, on the one hand, DONG Zhong-shu got Emperor Han’s support by deifying imperial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he got Confucian’s support by making them take part in political affairs by interpreting disasters and freaks. And what’s more, in order to get the people’s approval and acceptance, he absorbed th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understandable to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So, the theory of “telepathy between heaven and mankind” not only had the characteristic of “local knowledge”, but also developed into universal knowledge from local knowledge.
Key words:the theory of “telepathy between heaven and mankind”; DONG Zhongshu; context; local knowledge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6)01-0063-05
[作者简介]龚光明(1968-),男,安徽滁州人,博士,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委托项目“名宦为治与地域文明的构建——以宋明清时期的颍州为例”(2015WBZX01ZD)
[收稿日期]2015-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