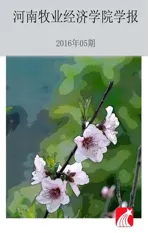《剪灯馀话》的诗词艺术
2016-03-15霍龚云
霍龚云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哲学与文史
《剪灯馀话》的诗词艺术
霍龚云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融合诗词曲赋等韵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的现象。《剪灯馀话》全书60827字,羼入的诗词有17424字,约占30%,其中三篇小说中的诗词比例超过50%。李昌祺用连篇累牍的诗词介入小说,几乎有喧宾夺主的迹象,作品中的某些诗词缺乏灵气,略显拖沓累赘,表现力不强。大量的诗词写入小说也说明作者意识到诗词与小说之间审美的差异性,试图调和小说与诗词间不同审美风格的冲突,使小说华艳与典雅并存,且可以借诗词来提升小说地位。
《剪灯馀话》;李昌祺;艺术特色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融合诗词曲赋等韵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的突出现象。如在最早的杂传小说《穆天子传》中就有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互赠答的三首歌谣,李剑国先生《诗与唐人小说序》评论道:“从《穆天子传》中的四言诗、《燕丹子》中的骚体诗,到六朝小说中的五言诗,小说中的诗体也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1]当诗歌迎来它的鼎盛时期时,小说的发展亦步入了自觉的时代,唐代小说家就恰如其分地借用诗歌在小说中抒发感情,渲染气氛。因此诗文融合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且成为“文体众备”的唐传奇的重要创作表达范式。《剪灯馀话》融入了大量诗词歌赋,继承并发展了唐传奇的这一特点。
一、《剪灯馀话》其书
《剪灯馀话》的作者李昌祺(1376~1452)为明代小说家,名祯,字昌祺,一字维卿,以字行世,号侨庵、白衣山人、运甓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为官清厉刚正,廉洁宽厚,疏滞举废,救灾恤贫,官声甚好。同时他又是一位多才多产的文人,学识渊博,著述繁富,诗集有《运甓漫稿》,又仿瞿佑《剪灯新话》作《剪灯馀话》。明代徐伯龄《蟫精隽》评价说:“庐陵李昌祺先生,名祯,永乐甲申进士,历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工诗文,尤精画,所著有《运甓漫录》《剪灯馀话》等集,学博而才富,识高而指远。”但长期以来,李昌祺的官声掩盖了其文名,其文名又以小说更卓绝,因此学界忽略了对其诗词的研究。加之文艺创作在当时为文人雅士所不屑为,李昌祺亦因此颇受讥议。他死后“议祭于社,乡人以此短之。”都穆《都公谈纂》也说:“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昌祺独以作《馀话》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欤!”
《剪灯馀话》(以下简称《馀话》)乃李昌祺仿瞿佑《剪灯新话》而作,“是明初极有影响力的续书,羼入了大量诗文,全书共60827字,插入的诗文却有17424字,约占30%,书中诗词共206首,集中起来倒可以成一部诗集。”[2]它们不仅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诗词本身亦具有闪亮的艺术价值。
二、《剪灯馀话》的诗词艺术
1.自作诗
《馀话》中诗词多是以小说人物的口吻,吟咏佳人闺怨、羁旅之愁、人生感慨等,这类诗作是小说中比例最大的部分,作用也最为明显。诗词的合理介入,成为小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抒情叙事,渲染环境气氛,而且有利于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长安夜行录》中男主人公诗云:“少年十五十六时,隐身下混屠贩儿。乍可无营坐晦亦,不说有学行求知。四时活计看垆螯,八节欢情对酒厄。紫糖旋泻光滴乳,白面新和软截脂。大堪纳吉团遮筐,小可充盘圆叠棋。火中幻出不亏缺,素手纤纤擎日月。汉贤逃难亲曾卖,今我和光还自匿。室中莱妇知同调,窗下儒仲敦高节。自从结发共糟糠,长能举案供薇蕨。怡怡伉俪真难保,布服荆钗有人悦。乐昌明镜一朝分,奉倩寸肠中夜绝。内家非是少明眸,外舍寒微岂好逑?宝位鸿图既云让,柳姿蒲质底须留?贫贱只知操井臼,凡庸未解事王侯。去剑俄然得再合,覆流信矣可重收。愿挥董笔祛疑惑,聊为陈人洗愧羞。”[3]127其妻诗曰:“妾家阀阈本寻常,茆屋衡门环堵墙。辛勤未暇事妆饰,婉婉惟知佩礼章。前年嫁得东邻子,博学多才贯经史。致身不愿取功名,鬻饼宁甘溷闾里。朝朝日出肆门开,童子高僧杂拌来。得钱即已随闭户,促席相看同举杯。何期忽作韩凭别,赴水坠楼心已决。红莲到处洁难污,白璧归来完不缺。当代豪华久已亡,贞魂万古抱悲伤。烦公一扫荒唐论,为传梁鸿与孟光。”“《长安夜行录》的故事是杂取唐孟集《本事诗》中卖饼者妻事和唐人笔记小说中记录岐王、申王、薛王事缀成,别无新意。”这两首叙事诗的插入,使得小说内容进一步完善,小说的主题随之明朗化,借诗歌陈述了乱世中平凡人家对和平安稳生活的向往,赞美了尊重历史的求实态度。这种以诗歌独有的方式给予小说主题特别的观照方式,把诗的意境和小说的内容糅合为一体,弥补了小说太过直观的不足。诗词介入小说,使读者在品味故事的同时,也能欣赏诗词,松弛有度,产生诗文共赏的独特美感,颇适合文人口味。孙楷第先生极度赞成这种写法,他说:“此等作法,为前此所无。其精神面目,既异于唐人之传奇;而以文缀诗,形式上反与宋金诸宫调及小令之以词为主,附以说白者有相似之处;然彼以歌唱为主,故说白不占重要地位,此则只供阅览,则性质亦不相侔。余尝考此等格范,盖由瞿佑、李昌祺启之。”[4]
翰林侍讲临川王英在《馀话》序中写道:“昌祺所作之诗词甚多,此特其游戏耳。”小说题材的限制性和创作的游戏目的,决定了其中诗词“香艳”的风格,李昌祺也未能越出这一规范。首先表现为对女性之美的细腻刻画,从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写到娇美姿态的形容,都体现了欣赏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品味,同时带有秾丽的脂粉气。如《鸾鸾传》对女性纤指的描写:“纤纤软玉削春葱,长在香罗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满甲染猩红。”又如《右酥乳》:“粉香汗湿瑶琴轸,春逗酥融白凤膏。浴罢檀郎扪弄处,露华凉沁紫葡萄。”有学者认为:“她们善于招徕,故意讨人喜欢,向观者表现出柔顺和娇弱的样子。她们的姿态、动作,乃至身上的某一个部位,全都是按照某种趣味精心培养起来的;表情微微受到控制,那不再是心情的自然流露,而是趋向优美的作态;为了抓住观者的心,她们既要表演得自然,又要精益求精,远离自然。于是,一种高雅的色情在她们身上被畸形地培养出来。”[5]这一正确的批评用在《馀话》描摹女性的艳诗上也是恰如其分的。其次表现为诗词有引向床帏之间昵狎的男女欢爱上。如《凤尾草记》龙生代答诗曰:“深谢韶光染色浓,吹开准拟倩东风。生愁夕露凝珠泪,最怕春寒损玉容。嫩蕊折时飘蝶粉,芳心破处点猩红。金盘华屋如堪荐,早入雕栏十二重。”诗中香艳露骨的色情描写,是对世俗人生情欲肯定的反映,但语言色彩皆秾艳靡滥,有太过猥亵之嫌。又如“胭脂晓破湘桃萼,露重荼蘼香雪落”“香肩半嚲金钗卸,寂寂重门锁深夜”等类诗句用俗艳的脂粉等具有暗示性的词语描写,极尽妍态,透露着赤裸裸的肉欲色彩,且格调欠雅。
2.集句诗
《馀话》中集句诗共计31首,《月夜弹琴记》30首,《洞天花烛记》1首。前人曾对这些诗歌作出了高度评价。安磐曰:“《馀话》记事可观,集句如:‘不将脂粉涴颜色,惟恨缁尘染素衣。’‘汉朝冠盖皆陵墓,魏国山河半夕阳。’对偶天然,可取也。”[3]116虽然不是自己的诗句,但李昌祺集得极好,诗句都是他精挑细选所得,组合技巧高超,不露痕迹,宛若天成。更妙的是诗风不趋于流俗,哀婉深致,如:“形容变尽语音存(《诗统》苏东坡),地迥难招自古魂(《鼓吹》李商隐)。闲结柳条思远道(《诗统》范镇),欲书花叶寄朝云(《鼓吹》李商隐)。窗残夜月人何在(《鼓吹》胡曾)?树蘸芜香鹤共闻(《鼓吹》陆龟蒙)。今日独经歌舞地(《三体》赵嘏),娟娟霜月冷侵门(《草堂》康伯可)。”诗歌流露出“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伤,不见人形瘦,但闻人语声,隔着不可超越的时空,思念就像摇摆的柳条晃晃悠悠,绵绵不断,如果可以把思念镌刻在花叶上,也只能把它寄给空中不可触碰的白云,想要寄给的人已不在月下窗前,这种心伤的痛楚感令人灼灼不安,悲伤的情绪在诗的尾声中达到极致,美好的月色下却让人感到沁人心骨的寒冷。全诗诗意连贯,自然流畅。又如:“残妆满面泪阑干(《鼓吹》),鬓乱钗横特地寒(王安石)。不见玉颜空死处(白居易),故园东望路漫漫(《三体》)。”诗中没有愁情绪语,佳人泪湿妆容,鬓发凌乱,姣好的面貌上笼罩着死寂的悲哀,迷惘的眼神延展到看不到尽头的远方,诗句把女子彻骨的悲伤巧妙地连接起来,显得哀婉凄楚,感人至深。
《至正妓人行》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叙事诗,也是《馀话》中仅有的一篇独立诗作。钱习礼认为:“观其运巧思于雕锼,出奇语于豪纵,落笔之际,必有谓元、白复生,未知其孰先孰后,诚佳作也!”周述也认为:“始既欣羡其以容貌供奉于当时,晚又感叹其衰老沦落于民间,设使元、白赋之,亦岂能逾于是作也。”刘子钦评价道:“见而知之者,咸以为元、白遗音。”我们以为这些评价誉之过甚,李昌祺在创作动机、形式及内容上竭力模仿《琵琶行》,然而格调却差之甚远。如《琵琶行》描述琵琶女技艺高超的诗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读来如闻其声,音韵绵绵,不绝如缕,且波澜起伏,经久不息,反复吟咏,荡人胸怀,“急雨”、“私语”、“珠落玉盘”、“莺语花底”等形象的设喻令人如临其境。反观《至正妓人行》对大都遗妓弹奏效果的诗句:“参差角羽杂宫商,微韵纡徐巧抑扬。坠絮游丝争绕乱,哀蛩怨蚓互低昂。呦呦瑞鹿剔灵囿,哕哕和鸾集建章。楚弄数声谐洗簇,氐州一曲换伊凉。伊凉浏亮益闲暇,埙篪笛笙皆在下。琚瑀铿锵韵碧霄,机梭淅沥鸣玄夜。”仿佛只是诗人在用乐器名称和音乐知识堆砌诗句,索然无味,“坠絮游丝”的设喻俗不可耐,“哀蛩怨蚓”的设喻毫无美感可言,简直不能与《琵琶行》相提并论。又如对人物年华最盛时期的描述,《琵琶行》道:“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寥寥数语就道出了琵琶女早年的盛极一时,与后来天涯沦落形成巨大落差,令人扼腕叹息。《至正妓人行》则写道:“记得先朝至正初,奴家才学上头颅。银环约臂联条脱,彩线挼绒缀罛罟。……羽林英俊驰轻毂,惯向奴家通夕宿。凤枕鸳衾肯暂辜,蜂媒蝶使交相属。……齐姜宋女总寻常,惟诧奴家压教坊。”诗人对大都遗妓鼎盛时期的描述冗长拖沓,诗句也多是对专有名词的过于频繁的运用,而想要表达的实质内容则略显单薄无力,且尚未脱离低级趣味。
《馀话》中还有为数不多而具有预言性质的谶诗,这类诗歌多出现在《听经猿记》、《何思明游鄷都录》等神怪小说中,谶诗对未来境况的预料,玄机暗藏,使得小说更加神秘含蓄。如《武平灵怪录》关于笔的诗作:“早拜中书事祖龙,江淹亲向梦中逢。运夸秦代蒙恬巧,近说吴兴陆颖工。鸡距蘸来香雾湿,狸毫点处腻朱红。于今赢得留空馆,老向禅龛作秃翁。”作者巧妙地利用诗歌揭示故事的谜底,令读者倍感新奇的同时,一切迷雾亦消散不见。
三、结语
《馀话》全书60827字,羼入的诗词有17424字,约占30%,其中三篇小说中的诗词比例超过50%。毛宗岗认为小说叙事中插入诗词“本是文章极妙处”,但反对其中的“俚鄙可笑”之作。李昌祺用连篇累牍的诗词介入小说,几乎有喧宾夺主的迹象,而作品中的某些诗词缺乏灵气,反而使小说略显拖沓累赘,表现力不强。大量的诗词羼入小说,说明李昌祺意识到诗词与小说之间审美的差异性,试图调和小说与诗词间这种不同审美风格的冲突,使小说华艳与典雅并存,借诗词来提升小说的地位。《馀话》面世后,友人的褒奖确实与诗词大有关系。曾啓说:“故其所著,秾丽丰蔚,文采烂然。”当时的刑部主事刘敬也评论说:“此特以泄其暂尔之愤懑,一吐其胸中之新奇,而游戏翰墨云尔。”“游戏翰墨”也突出了作者以诗词来炫耀才华的目的,而这样的创作心理使得诗词更趋近于华丽丰赡,总而言之,“漱艺苑之芳润,畅词林之风月,锦心绣口,绘句饰章”是对其小说中诗词最妥帖的评价。
[1] 崔际银.诗与唐人小说[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2.
[2]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一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0.
[3] 周楞伽.剪灯新话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6.
[5]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83.
(责任编辑:张明海)
2016-08-19
霍龚云(1987-),女,河南平舆人,郑州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
10.3969/j.issn.2096-2452.2016.05.017
I
A
2096-2452(2016)05-006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