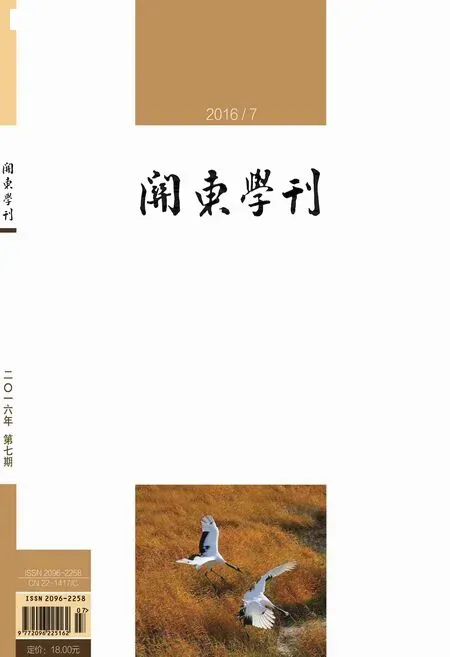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及省思
2016-03-15陈岸峰
陈岸峰
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及省思
陈岸峰
新文学运动期间,胡适所书写的《白话文学史》掀起了百年文学史的高潮,此书开白话文学史书写之潮流,更引来无穷的思索。其后,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虽姿态互异,各具心思,均先后对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及其文学史观作出挑战与修订。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文学史之书写成为政权确立之政治论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不为官方所接纳,招来无尽批判,遂有唐弢等人奉命集体编写之《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海外的夏志清却早以《中国现代小说史》,独自树起抗衡大陆以官方意识形态书写现代文学史之流弊。以上数种重要的文学史以至于八十年代所掀起的重写文学史以及其中种种细节的问题,均乃此文的论述重心,期藉此对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及文学史思潮作出批判性的省思。
现代文学史;胡适;王瑶;唐弢;重写文学史
一、前言
二十世纪肇始,中国已有文学史的书写。1904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授课的林传甲(归云,1877-1922)编写了第一本中国文学史。同年,在苏州东吴大学,黄人(摩西,1866-1913)也正编撰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史》。*相关论述可参阅戴燕:《文学史的力量——读黄人〈中国文学史〉》,载《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1-210页。1917年,适值五四运动爆发,由胡适(适之,1891-1962)与陈独秀(仲甫,1879-1942)所领导的新文学运动亦燃起燎原之火,胡适所书写的《白话文学史》更掀起了百年文学史的高潮,此书揭既开白话文学史书写之潮流,更引来无穷的思索。其后,周作人(星杓,1885-1967)的《新文学的源流》与钱基博(子泉,1887-1957)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虽姿态互异,各具心思,均先后对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及其文学史观作出挑战与修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风云色变,现代文学史之书写成为政权确立之政治论述,民国时期文学史书写之思想激荡,渺难再期。王瑶(昭琛,1914-1989)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不为官方所接纳,招来无尽批判,遂有唐弢(越臣,1913-1992)等人奉命集体编写之《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海外的夏志清(1921-)却早以《中国现代小说史》,独自树起抗衡大陆以官方意识形态书写现代文学史之流弊。百年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可谓曲折而坎坷。
二、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一)性质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历来“文”“史”不分家,从《战国策》到《史记》,既是历史,亦是文学。关于文学与“文学史”之别以及两者之功能,钱基博有如下阐述:
夫史以传信。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的主观的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学之范畴也。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5页。
钱先生提出两点值得注意:1.文学史之为“史”者,贵在客观的记载,而文学则贵在抒写情志之主观;2.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而文学则重抒情达意。重要的是,他认为前者“不如”后者,因为前者乃科学,而后者乃创作。依其判价,文学创作乃高于文学史的书写。基于以上的定义,他认为司马迁(子长,约公元前145或135-公元前87)的《史记》与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史》并非文学史,原因在于前者乃“发愤之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即是说司马迁在记事上仍具“史”的特性,可是整体上偏向于抒情;至于胡适该文,则因为“褒弹古今”“好为议论”“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故亦被划为非文学史之列。*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5页。
谢无量(1884-1964)则认为文学史“属于历史之一部”。*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第43页。其后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如顾实(1878-1956)、穆济波(1892-1978)、胡怀琛(季仁,1886-1938)、郑振铎(西谛,1898-1958)、胡云翼(南翔,1906-1965)、游国恩(泽承,1899-1978)等都作如是说。及至张希之(1909-)撰写《中国文学流变史论》时,文学史就明确地被规定为“特殊的历史科学”。*张希之:《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北平:文化学社,1935年。而在历史学者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中,俗文学史之研究则更是以小说及戏曲为主。*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由此可见,文学与历史以及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泾渭难分。
文学史之编写,一方面是为记录文学的发展脉络,如此一来,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否不再存世,或为政治干扰而禁毁,其作品与文学观点均可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文学史之编写也可为后来者所资鉴,惟有如此,文学创作方有发展与突破的可能。同时,文学史因为有了历史叙述的性质,因此它是一种追忆与编撰,是在历史想象中进行,正如戴燕所说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完成,都曾经过叙述上的虚构与情节化的操作。*戴燕著:《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8-49页。戴燕甚至由此而推论说:
如果要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式是靠着历史学的滋养形成的,是历史主义的一个神话,也许并不算夸张。*戴燕著:《文学史的权力》,第49页。
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唐弢等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皆证其言非虚。虚构与情节化的文学史书写,如同造假,而遗憾地却出现在1949年之后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中。
(二)功能
一个国家、民族可以借着文学史之编写,“维持一个社群与身份的共同感觉”。*Perkins,David.“TheFunctionsofLiteraryhistory,”IsLiteraryHistoryPossible.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P,1992,p.180.正如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指出,假若英国人不再对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与米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有任何反应,那么他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IsLiteraryHistoryPossible,p.180.维持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学想象,正是文学史的主要功能之一。
此外,文学史作为对过去文学遗产的呈现、评价及总结,其所凸显或压抑的对象,实与主导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纵使文学史并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反映文学的过去,*IsLiteraryHistoryPossible,p.182.它虽永远受制于现在(present),但是文学史家却往往将传统视为重塑现在的资源,*IsLiteraryHistoryPossible,p.181.更将当下的意识投射于过去,令过去反映他们的关心与意向。*IsLiteraryHistoryPossible,p.182.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建构,正是致力于国民启蒙与文化复兴。然而,1949年之后,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唐弢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均沦为党同伐异、建构神话,既是确立政权的合法性,亦是凝塑共产阵营的集体革命意识。文学史遂往往沦为政治工具,其书写则为达至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任意挪用。
文学史虽诚如陈思和所言:“不能不是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渗入和再创造”,*陈思和:《笔走龙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然而他也指出:它更需要证明,必须从材料出发,尊重客观存在的科学性;它更需要批评,文学史家面对的是人类精神符号——语言艺术的成品,只有在审美层次上对他们作出把握,方能真正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陈思和:《笔走龙蛇》,第107页。
“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渗入与再创造实属必然,故而“研究者”本身的道德、文化水平以及文学品味、鉴赏能力以至于文字表达,均必须达到相当的水平,否则势必祸枣灾梨。大陆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所犯的错误便是没有“从材料出发”、没有“尊重客观存在的科学性”,遑论审美层次上的欣赏,基本均沦为政治机器的螺丝钉,从而丧失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与尊严。
(三)史家意识
文学史既是历史的一部份,文学史家自然也必须具备史家意识。在此书的所有文学史家当中,唐弢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虽屈从于中央指令的“以论带史”*所谓的“以论带史”,指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学术界,主要是史学界,有过一场编写史书应该“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的论争,前者是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后者希望在尊重历史事实及材料之下得出结论。论争的最后结果,当然是左倾的“以论带史”占据优势。详见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编写后记》,载《唐弢文集》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50页。一切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归,排列座次,分清敌我,然而他自己却有非常强烈的史家意识。唐弢主张“论从史出”、“实事求是”。*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载《唐弢文集》第9卷,第377页。更重要的是他更提出作为文学史家贵在有“史识”与“自己的见解”;*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载《唐弢文集》第9卷,第385页。而且必具备学问,先有一专门学问;*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载《唐弢文集》第9卷,第384页。有了学问又能以“敏锐公正”的眼光以筛选作家,则为“史识”。他同时强调:
文学史家衡量作家作品总有一条杠。主编的责任就要掌握好这个杠。*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载《唐弢文集》第9卷,第384页。
因为“写文学史的人操着生杀之权”,“得慎重处理”。*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载《唐弢文集》第9卷,第375頁。唐弢的史家意识,迥然不同于严苛的官方意识形态,而荒谬的是,他竟在十九位现代文学史专家中,被委任为主编,其它更左的专家竟没被看上。*唐弢早在1929年便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并有一定的贡献,其党性不容质疑,此为其一。其二便是他与鲁迅有私交,其模仿鲁迅的杂文,几可乱真。他甚至以一己之力搜集鲁迅佚作,编为《鲁迅全集补遗》,于1946年冬,即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前夕出版;又于1951年出版《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由以上的事迹可见,唐弢的党性及其文学功底以及在文坛上的地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可谓不二人选。详见丁华整理:《唐弢在邮局》;卢豫冬:《唐弢杂文与鲁迅杂文之间》;方行:《鲁迅佚作及其未刊稿的编印——追怀唐弢同志所作出的贡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1-526、533-546、527-532页。“历史是多么无情”,一心为新中国建立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王瑶备受批判,历尽磨难;有志于独立撰写现代文学史的唐弢,屈从于政治,编写了不惬己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同样,作为抗衡大陆文学史而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1921-2013),也很清楚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身份与使命:
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小说史》初版原序)*夏志清:《作者中译本序》,载《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社版,1979年,第17页。
以审美意识作为文学判价的唯一标准,只是悬于理想的美好愿望,而事实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却是以“反共”著称。*夏志清:《作者中译本序》,载《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5页。夏志清的以文学美学标准编写文学史的理想一如王瑶所曾指出:
文学史只能根据作品在客观上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来评价,而不能根据作者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来评价。*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载《王瑶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很可惜,1949年之后,无论是现在大陆的王瑶、唐弢,还是海外的夏志清均无法实现心中的美好愿望。政治既是事实的存在,而却又有如梦魇般纠缠着现代文学史的书写。
三、独立成科与政治干预
王瑶则这样厘析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
……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虽然这三者都是以文学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其一致性,但也有各不同的特点。……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这不符合文学史的要求。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载《王瑶全集》第5卷,第4页。
文学史必须有别于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然而这却是大陆现代文学史的通病,哪一本不是标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依据以分析作家与作品的?哪一本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为依归的?就连王瑶自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不也一直高举毛泽东(润之,1893-1976)的《新民主主义论》与“鲁迅的方向”?至于作家作品汇编的问题,则几乎可以说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特征,该书基本缺乏“史”的特征,对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文学现象,缺乏详细的介绍,而在该书现有的历史脉络中,也缺乏“上下左右”的联系,故各章分开独立成为作家作品论,也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即如王瑶本身有这样的文学史意识,却也碍于“党性”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左右,从而没办法对作家作品以至于文学历史现象作出客观的书写,空悬理想,也是枉然。
1949年之后,现代文学史虽在各大专院校独立成科,然而基本上却沦为中共论述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史,且看1951年5月30日由老舍(舒庆春,1899-1966)、蔡仪(1906-1992)、林何林(1904-1988)以及王瑶所草拟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王瑶:《王瑶全集》第7卷,第252-262页。仅从其“绪论”架构,则可见政治如何对新文学作出扭曲:
第一章、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
第一节、目的:
一、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二、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
第二节、方法: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第二章、新文学的特征
第一节、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
第一节、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
第三章、新文学发展的特点
第一节、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发展
第二节、新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三节、大众化(为工农兵)方向的发展
第四节、新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第四章、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一、五四前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1917-1921)
二、新文学的扩展时期(1921-1927)
三、“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
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1937-1942)
五、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大会”(1942-1949)
从“不是”什么,到“是”什么,完全颠覆了历史事实,从一开始就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共产党革命)与新文学运动挂钩,从辩证论、唯物史观到马列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这一切是“教育”,亦是“洗脑”。戴燕便指出:
文学史先是在中学、大学纷纷登台,在学科建制当中立足,然后在职业化的大学里成为必修课,逐步实现其制度化的过程。经由这种制度化的过程,中国文学史终于变成了一种共识和集体的记忆。*戴燕:《前言》,《文学史的权力》,第8页。
所谓的“集体记忆”,无非便是那些为配合革命需要而虚构出来的所谓英雄人物及英勇事迹,如白毛女、刘胡兰等等,虽满纸血泪,却多为虚构。
王瑶,作为第一位负责在北京大学系统教授现代文学史并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者,虽以“党性”与“左翼理论家”著称,*关于“党性”,除了体现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其它文章之外,王瑶确实也接受了官方对文学的“党性”的要求。可参阅王瑶编著:《中国新文学史稿(增订本)》附录,香港:香港波文书局,1972年,第130页;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载《王瑶全集》第7卷,第263页。此外,王瑶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中便说过因为他是左联领导的《新地》的编辑,便“自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左翼理论家。”见王瑶:《王瑶全集》第7卷,第264页。樊骏说:“他的时评政论,数量比文论多,内容也更有价值。他因此被称为‘左翼理论家’。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和实践的。”见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兼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硏究会、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114页。可惜该书仍未能符合中央的要求而备受批判,饱受屈辱。及至在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个年会的报告中,在阐述文学史作为“文艺学科”的性质时,他却又指出:
现代文学史由于所研究的作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此常常不免有超越学术范围的干扰;但科学地研究问题必须有勇气排除这些干扰。*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王瑶全集》第5卷,第16页。
这就是身受其害者对1949以后的以政治干扰文学史书写的否定。夏志清亦曾指出大陆方面以政治主宰文学史书写之荒谬:
……对于共产文学史家来说,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政治的正统性成正比。一位作者的声望,终须视他在文坛与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他能否保持对党忠贞不二的清白记录而定。丁玲与冯雪峰的失势,致使一九五七年之前写成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一夕之间过了时,因为那些文学史家无法预知这两个显要作家反党的本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426页。
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政治运动不断,也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唐弢自然亦是有见及此,方才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原因在于“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载《唐弢文集》第9卷,第494页。“当前”与“史”是矛盾的,而“历史要求稳定”。*唐弢:《一个想法》,载《唐弢文集》第9卷,第492页。唐弢又指出:
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一律写成了政治鉴定书。*唐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载《唐弢文集》第9卷,第49页。
也因为在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特别严苛,为了党同伐异,不惜扭曲事实,如对待非左派的胡适、徐志摩(槱森,896-1931)、沈从文(1902-1988)、林语堂(1895-1976)等作家,刻意抹煞彼等的文学贡献,甚至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作出攻击。至于党内的胡风(1902-1985)、冯雪峰(1903-1976)、丁玲(1904-1986)、王实味(1906-1947)以及路翎(1923-1994)等等,均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而一再备受批判。一部现代文学史,竟是如此血泪斑斑。
夏志清所提及的冯雪峰与丁玲的政治问题,确是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备受猛烈批判的原因,但也只是众多错误中的两点而已,王瑶对此必然深知个中三昧。故此,王瑶晚年面对“重写文学史”的思潮时,他也同意并支持,*王瑶:《文学史著作应该后来居上》,载《王瑶全集》第8卷,第12-14页。甚至说:“研究文学史当然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载《王瑶全集》第5卷,第62页。然而,王瑶晚年却依然大力拥护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初版、修订版以及五十年代、一九八二年的版本中,均大力拥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甚至在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王瑶依然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意义》作为发言。见王瑶:《王瑶全集》第5卷,第243-279页。若是如此,文学史又怎有可能成为他所期待的“文艺科学”?
四、“重写文学史”的省思
1978年,邓小平(1904-1997)复出并实行改革开放后,思想开始解放,官方的意识形态亦逐渐放宽,遂有“重写文学史”的呼声的出现。“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思潮是在1988年7月《上海文论》第4期上,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他们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中所提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专栏发表了一批具有强烈的“重写文学史”色彩的论文。“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并成为思潮,是在1988年,可是王晓明却明确地把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与在会上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王晓明:《专“重写文学史”栏主持人的对话》,载陈思和:《笔走龙蛇》,第113、126页。至于陈思和则这样理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产生原因: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载《笔走龙蛇》,第110页。
“重写文学史”的政治实践意义,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陈思和指出“重写文学史”的三重要旨:1.以文学演变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综合了实证、批评、规律探讨等各种研究方法;2.从材料出发,尊重事实,亦即强调“史识”的重要性;3.在审美层次上对作品作出批评,体现批评者的主体性。*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载《笔走龙蛇》,第107页。同时,“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释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载《笔走龙蛇》,第109页。王晓明则认为,“重写”即是将当下对现代文学史的新的理解写下来。*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对话》,见陈思和:《笔走龙蛇》,第139页。
此外,陈思和与王晓明亦就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流派、各种文类以至于作家等,在“专栏”中作出详细的对话,每期的“专栏”中均有关于现代文学的重新评价的文章刊登。虽然以这样的形式作为在1985年在北京万寿宫的“序幕”后的具体化,规模不大,理论性亦不强,而由此序幕的揭开,正如陈思和所比喻为胡适与陈独秀之揭开新文学运动一样,*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载《笔走龙蛇》,第134页。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以及彷如雨后春笋般的不同类型的“重写”,从不同文类的具体篇章、作家、流派、社团以至于文学史的出版。陈思和这样回忆当时“重写文学史”的盛况:
前几年王晓明先生和我在上海的一家理论刊物上主持一个“重写文学史”专栏,所发表的文章并不怎样的好,但这个命题却引起了许多前辈学者和年轻同行的反响。一些老作家,老学者——像德高望重的前辈王瑶先生、贾植芳先生、钱谷融先生、施蛰存先生、唐湜先生、汪曾祺先生,都纷纷着文,无论看法怎样不一致,都反映了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和重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无非是这个命题说出了学术界对原有的以定于一尊面目出现的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不满足。*陈思和:《一本文学史的构思——〈插图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国球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第51页。
正是文学史家对于“定于一尊”的文学史书写模式的不满,从而形成两辈学人的共同诉求,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高潮。
其实,早于1983年,由中央指定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唐弢便说过:“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不拘一格”,*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交流》,《唐弢文集》第9卷,第415-416页。“现代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唐弢:《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谈到我的一点看法》,《唐弢文集》第9卷,第358页。关键是:
文学史首先应当是文学史,它既不是作家作品论,也不是文学运动史或思想斗争史。*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编写后记》,《唐弢文集》第5卷,第150页。
简而言之,就是“去政治化”,还文学与文学史以独立的地位。唐弢在1989年10月写的《关于重写文学史》中更为直接地宣称:
我赞成重写文学史,首先认为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不应当也不必要定于一尊。不过文学史就得是文学史,它谈的是文学,是从思想上艺术上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与叙述,而不是思想斗争史,更不是政治运动史。*唐弢:《唐弢文集》第5卷,第631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报上已有人将“重写文学史”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他的学生汪晖曾劝他别参予撰写相关文章,但他还是写了,原因在于:
一是因为他早就对现有的文学史——包括他自己主编的两种文学史不满了,他“新时期”写下的关于艺术风格和文学流派、关于钱锺书、废名、师陀、张爱玲的文字也都是为重写文学史作准备。二是因为从鲁迅那里他学到的还有对青年的爱惜与保护;对于研究过文网史的先生,他是深知中国的有些文人的深文周纳的卑劣的。在他看来,文学史总是要重写的,重写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是非,但那是学术的是非,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绝不应冠以“自由化”的帽子。*汪晖:《“火湖”在前》,《唐弢纪念集》,第441-442页。
在深文周纳的文网时空,在阿谀当政以干进的社会,唐弢的治学精神与学术追求,值得敬仰。*黎湘萍在《晚景照人梦依稀》中便认为唐弢晚年撰写《关于重写文学史》,明确地大力支持“重写文学史”,便是他“开阔的学术胸襟的一个典型表现”。见《唐弢纪念集》,第445页。王瑶也赞成“重写文学史”,认为过去“钦定”文学史的书写是“不可取的”,“重写”就要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王瑶:《文学史著作应该后来居上》,载《王瑶全集》第8卷,第14页。
每次新的文学史的出版,都可称之为“重写文学史”,此口号风靡一时。最关键的也就在摆脱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宰制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典范在前,就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唐弢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陈思和犀利地批判说:
……教科书总是最集中地体现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以一种思想文化的霸权面目出现,使舆论一律,进而达到思想的箝制。*陈思和:《一本文学史的构思——〈插图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国球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第51页。
锋芒直指当政,其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这场轰轰烈烈的“重写文学史”终于在政治的干预下而告终。因为,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是为“新政权的合法性、正统地位提供历史依据”。*见钱理群:《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王瑶先生和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命运》,《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5页。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现代文学史便与国家论述与神话建构密不可分,其党性不容置喙。
五、非偶然的擦身而过
1985年5月在北京万寿宫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陈平原宣读了他与钱理群及黄子平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设想,即陈思和与王晓明所视为“重写文学史”的思潮的开端。*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对话》,分别见陈思和:《笔走龙蛇》,第114,126页。在1993年至1996年间,由陈平原等主编,由北京大学出版共三辑的《文学史》,似乎意在作为“重写文学史”的实践。第一辑《编后记》中有以下的目标:
“文学史”是我们的研究课题,可这种“学术对话”的意义当不限于此。
以文学史为研究对象,并非排斥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而是强调将文学现象放在“史”的位置上考察。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而不是取个别文本的独立分析。至于文学史理论以及对已往文学史著作的反思,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陈平原等主编:《文学史》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0页。
由此可见,虽没有“重写文学史”的宣言与锋芒,而却有其实践的目的。可以说,由陈平原等主编、由北大出版的《文学史》称得上是与上海的陈思和与王晓明掀起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南、北呼应。第二辑的《编后记》中亦有以下关于“试写文学史”专栏的说明:
设立“试写文学史”专栏,目的是将理论探讨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文学史撰述远非“史识与史料的结合”一句话所能涵盖,涉及不少棘手的问题。不同文学史著述,有不同的学术思路、理论设计、叙述策略以至操作程序,是非功过需要仔细辨析。不作惊世骇俗的翻案文章,只想选取同人中正在撰写的文学史片断,加以认真的批评。*陈平原等主编:《文学史》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347页。
由此可见,《文学史》的“重写文学史”的目标很明确。可惜的是,三辑的《文学史》中,真正称得上与文学史有关的,寥寥无几。1993年第一辑中的十九篇论文中,只有以下几篇与文学史有关:陈平原《小说类型与小说史研究》、陈国球《文学结构与文学演化过程: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理论》、李小良《影响·文互指涉·中国戏曲史》;王宏志《文学史里的〈新月派〉》、葛兆光《陈列与叙述:读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夏晓虹《考据与图表的现代功用:读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吴方《一个过渡性的文本:读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95年第二辑《文学史》中的十七篇论文,与文学史有关的计有:龚鹏程《南北曲争霸记》、夏晓虹《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王宏志《文学上演变的解释:唯历史背景主义》、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朱晓进《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学史研究思路:读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月亮《辑录与案语: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1996年第三辑《文学史》中的十六篇论文,与文学史有关的计有:陈平原《现代中国散文之转型》、陈炳良《从文学史看台港文学》、陈国球《关于文学史写作问题:以柳存仁〈中国文学史〉为例》、王宏志《一部最初的中国新文学史?论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由此可见,三辑合共五十二篇的论文中,与文学史相关的大约只有二十篇,还不到一半。而且,目录中有不同分类,“栏目”繁多,参差不一,第一期有“文学史理论”“思潮·流派”“作品与接受”“文化与文学”“文学史着检讨”“旧籍新评”“翻译·评介”;第二辑有“中国古代文学史论”“试写文学史”“女性文学批评”“翻译·译介”“旧籍新评”;第三辑则有“文化与文学”“诗学研究”“小说研究”“台港文学研究”“文学与艺术”“文学史着检讨”“翻译·评介”。由此可见,范围极大,几乎可以说是“学术史”也不为过,例如:第一辑:周英雄《必读经典·主体性·比较文学》、陈清侨《美感形式与小说的文类特性;从卢卡契到巴赫金》、廖炳惠《里柯的三度模仿论及其问题》、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第二辑王德威《世纪末的华丽:台湾·女作家·世纪末·边缘诗学》、余君伟《历史论述与解构批评的局限》;第三辑葛兆光《从出世间到入世间:中国宗教与文学中理想世界主题的转变》、张鸣《即物即理即境即心:略论两宋理学家诗歌对物与理的观照把握》、夏晓虹《发乎情,止乎礼义:林纾的妇女观》、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戴燕《“用思困人”及其它》、文洁华《艺术史的现代挑战:从人文主义观点到多元诠释》、奚密《从现代到当代:从米罗的〈吠月的犬〉谈起》。简而言之,三辑《文学史》中绝大部分论文所关注的与“文学史”可谓风牛马不相及,虽不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但却没对当时“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起到更积极的推波助澜作用,殊堪可惜。故编者在第三辑的《编后记》中便有以下的慨叹:“没能坚持当初的理想,毕竟是一种失败”。*陈平原等主编:《文学史》第3辑,第398页。由此慨叹,再结合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宣扬“重写文学史”所受到的政治干预,可见《文学史》之落幕,亦是一次非偶然的擦身而过。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却彼等尽力推进“重写文学史”的良好初衷。当然,值得反省的是,事过境迁,又有多少具体而富有新意的关于文学史的省思的学术著作面世?又有多少迥然不同的文学史的书写具体落实?
六、分期的问题
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而又莫衷一是。目前所见,我们似乎已习惯于将1949年10月1日作为划分“现代”与“当代”文学的时间界限。然而,1985年在北京万寿宫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中,钱理群与陈平原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重要观念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二十世纪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29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提出,在于打通大陆学界的文学史时期区分的局限:“近代文学”(由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现代文学”(由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代文学”(由1949年10月1日到现在)三段分期。然而,严家炎则认为这三分法,一者“分割过碎,造成视野窄小褊狭,限制了学科本身的实际发展”;再者“以政治事件为界碑,与文学本身的实际未必吻合”。*严家炎、钱理群主编:《前言》,《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陈平原指出,他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光是一个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他们甚至是要把“二十世纪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来把握”,而且宣称“这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31页。当然,我们至今还没见到“新的理论模式”的建立。陈平原又将“二十世纪文学”的小说进程细分为五期:1897-1916、1917-1927、1928-1949、1950-1978、1979以后。而曾与陈平原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钱理群却在与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前言》中将现代文学史作七个分期:1897-1916、1917-1927、1928-1937、1937-1949、1949-1976、1977-1984、1985以后。*严家炎、钱理群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页。何以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陈平原与钱理群又有不同的分期呢?陈思和认同“二十世纪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而其划分的文学史时期却又有所不同:由五四开端的启蒙文化时期,由抗战为开端的战争文化时期,以及由八十年代为开端的现代文化时期。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都折射出这三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艰辛过程”。*陈思和:《一本文学史的构思——〈插图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国球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第66页。值得一提的是,唐弢提出的文学史分期,甚至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开放:
现在大家都从“五四”讲到建国。我们是不是将来要改,我看很可能改。因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一码事;现在国外就看作一码子事。但起点不同,一般欧洲人从一九0一年开始,就是从二十世纪开始。后来有些专家到中国来,他们慢慢地也接受了我们的看法,觉得从“五四”开始有道理。但下限还是到现在为止,无所谓当代。我们现在下限到开国为止,就有些问题。建国以后新起来的作家好办,但从“五四”开始的一些老作家,比如巴金、老舍、冰心等人,就把他们腰斩了,他们建国以后有很大发展……。*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第9卷,第378-379页。
王瑶也撰写了《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王瑶全集》第5卷,第46-65页。对种种的可能性都作了考察,但并没有任何的具体建议。综观以上种种设想,可谓百家争鸣,却难有定论。
实际上,巴金(李尧棠,芾甘,1904-2005)、老舍(舒庆春,舍予1899-1966)、冰心(谢婉莹,1900-1999),以及从五四过渡到新中国的所有作家,包括郭沫若(鼎堂,1892-1978)与茅盾(沈德鸿,1896-1981),他们的精神与肉体已然分离,五四精神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五四精神只是任由当政者挪用、蹂躏的对象而已。当然,这批作家,在五四时代曾经是民族之魂,摇旗吶喊,及至新时代,已沦为违心的清客、侍读,噤若寒蝉。简而言之,以上种种建议,看似超然,却无视现实。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五四”的主流文学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主流文学可以相提并论吗?假如我们都承认并接受一九四九之后,占重要位置的很多作家的思想及其作品的内容已与五四时期有很大的分野,甚至已从党的立场来书写而完全失去独立思考的事实,我们又怎能泯灭1949年10月1日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划分?现、当代文学的划分,既是政治在文学上的影响的事实,而这划分也不无好处,甚至可以说是大家在当时公认的事实,正如陈思和便说过: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本来就不是在纯文学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窗口,借助这个窗口可以了解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诸种因素,所以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陈思和:《一本文学史的构思——〈插图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国球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第62页。
故此,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下,变是必然,变得太多,甚至在节枝上各施各法,只是舍本逐未。以1949年10月1日作为划分现、当代的时间坐标,可以说是绝对的客观事实,是从政治而文学的,从国家机器而下及教育以至于个体,一以贯之,从以完成国家论述。任何企图改动者,虽颇有愚公之精神,却难以一锤定音。
七、总结
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掀起轰轰烈烈的新文学革命开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对胡适《白话文学史》则以逆向论述以呈现新文学运动中新、旧两阵营以至于在新文学阵营内部的颉顽书写。1949年之后,文学史的书写基本沦为政权确立之论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他带来无尽的批判与屈辱,唐弢等人历时二十多年所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塑造了官方主宰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样板,而身处海外的夏志清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立意抗衡,并企图勾勒出不受时代影响的文学“大传统”。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书写,既可见文学的发展,而文学史家的姿态,思维之所向,更是百年中国风雨飘摇之缩影。
陈岸峰(1975-),男,文学博士,香港大学教授(香港 999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