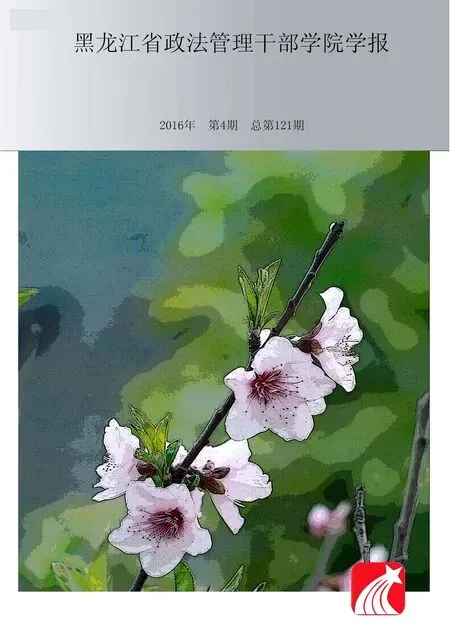裁判思维下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解读
2016-03-15钱瑾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钱瑾(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裁判思维下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解读
钱瑾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性质尚无定论,应当认为其具有程序法的性质,各个条款相互独立,因此对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执行性的解读,需要按照不同条款进行。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之间的效力冲突应当交由仲裁庭裁量,法院应当拒绝管辖。在当事人一方提请调解时,仲裁庭可以中止仲裁程序,以便当事人调解,如果调解失败,仲裁庭有权继续审理。我国应当从条款的起草、法律制度的设计以及示范条款的提供上促进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适用和发展。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可执行性;条款独立
一、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概述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或Escalation Clauses)是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复合型条款。在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中,双方合意将和解(conciliation)、调解(mediation)、专家决定(expert decision)等作为仲裁或者诉讼的前置性层次,只有在完成前一层次,才能进入后一层次,仲裁或者诉讼就成为了救济的最后路径。
这种将ADR作为仲裁或者诉讼前置程序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顺应了国际商事合同的发展需要。首先,相对于直接仲裁或者诉讼,它有利于节约时间成本和费用。其次,它也有利于维系双方当事人的商事合作关系,特别是当双方签订了长期合同时,直接诉讼或者仲裁更显得有些粗暴。再次,它可以为复杂的合同提供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方案,突破传统单一制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性,通过不同层次的纠纷解决程序解决具体的问题。因此,作为一种温和性的纠纷解决条款,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在国际商事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出于便利需要,国际商会(ICC)、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仲裁协会(AAA)等少数机构制定了多层次争议解决的示范文本以供当事人参考。
然而,在实践中,不少当事人往往没有履行磋商或者调解义务就提请仲裁或者诉讼,让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形同虚设。而且,仲裁被申请人几乎从不质疑仲裁申请人不经磋商就提请仲裁的程序性权利。不遵守协商条款的后果,究竟是关闭仲裁的大门,还是阻却获得实体裁决的道路?
因此,研究协商条款与仲裁条款的效力冲突,有利于厘清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性质,对于探究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中诸条款的可执行力以及违反协商条款对仲裁庭管辖权的影响等也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我国裁判思维下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
(一)四川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2005)
百事可乐公司请求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的裁决进行执行。当事人双方的合同中含有以下仲裁条款:“如本合同的解决(解释)或执行(履行)产生争议,双方应尝试首先通过协商解决此项争议。如展开协商后45天仍不能以上述方式解决争议,任何一方皆可将争议呈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仲裁院根据该委员会或仲裁院的仲裁程序进行仲裁。”成都市中院认为,百事公司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提起仲裁前与四川百事进行了45天的协商,因此不予承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的复函①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四他字第41号复函,第42号复函。中确认了成都市中院的裁决有效。
该案对仲裁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无论有无协商期,对于协商程序,长期的中国仲裁实践,尤其是涉外及国际商事仲裁实践,都未将其作为一个必须强制进行的前置程序,而仅仅是一个依据当事人自愿原则选择进行的任意性程序,不影响当事人即时提起仲裁的权利。除非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表明协商及/或调解程序是进行仲裁的前提或者前置程序,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作随意的扩大解释,不能剥夺另一方依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的权利。这种裁判思维,承认了协商和仲裁是相互独立的条款,一方未履行协商条款,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而且如果没有明确表明协商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则该协商条款仅具有任意性。实践证明,这种裁判思维有利于避免一方恶性拖延协商时间,快速进入仲裁程序解决争议。
因此,2005年百事可乐案以协商期未满足为由拒绝承认执行的裁决,对这种长期仲裁实践思维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也增加了实践中对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的困扰,协商条款与仲裁条款效力上发生冲突时,如何加以权衡?
(二)润和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2008)
2008 年润和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中,润和公司基于合同中“凡应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申请仲裁……”的规定,要求仲裁庭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都认为,“由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规定提交仲裁争议,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时再提交争议。而受理仲裁申请时,本案申请人并未提交有关双方协商的依据,也未提供已经通知润和公司要求协商解决的依据,因此不予受理仲裁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润和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的审查报告的复函中认为:当事人虽然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发生纠纷应当协商解决,但其未明确约定协商的期限,约定的内容比较原则,对这一条款应当如何履行和界定在理解上会产生歧义,而结合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的目的来判断该协议的真实意思,当事人约定的“友好协商”和“协商不成”这两项条件,前项属于程序上要求一个协商的形式,后一项可理解为必须有协商不成的结果,妈湾公司申请仲裁的行为,应视为已经出现了协商不成的结果,因此,在前一项条件难以界定履行标准,而后一项条件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仲裁庭有权依据该仲裁协议受理案件。
最高法的复函与05年百事可乐案之前的裁判思维趋于一致,将协商条款和仲裁条款区分开来,并且厘清了05年百事可乐案造成的协商条款扩大化和模糊化的概念。协商条款如果要具有执行力,则应当具备明确的要件,双方对这一条款的履行和界定在理解上不会产生歧义。“友好协商”的形式难以界定履行标准,因此只要出现了结果(提请仲裁视为协商不成),就不必要求证明行为(友好协商),从而从结论上否定了“友好协商”条款的可执行性。
事实上,最高法的裁决与国际商事仲裁庭的裁决也趋于一致。ICC 11490案中就认定“友好协商不能构成仲裁前置条款(‘be settled in an amicable way’constituted no condition precedent to referral to arbitration),这只表明双方不愿意进行仲裁的意图”[1]。
综合两则最高法复函的典型性案例看,最高法在解读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时,区分协商(或调解)条款和仲裁条款的效力,如果协商(或调解)条款只做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约定协商的期限等具体内容,则将认定该协商(或调解)条款不具有可执行性,对仲裁庭、法院的管辖权不产生阻碍作用。
三、国际商事实践中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判例解读
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存在丰富的判例涉及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而条款是否具有可执行性与该条款的性质密不可分。对这些判例作分析,可以大致看出,目前国际上对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性质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就是仲裁条款
苏黎世州最高上诉法院认为,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是仲裁条款,其中的协商、调解等条款是实体法性质。因此,违反协商、调解条款不能产生排除法院或者仲裁庭管辖权的效力,只能产生实体上的违约救济[2]。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在于,如果将协商、调解条款视为具有程序法性质,则会出现双方当事人的提起仲裁或诉讼的权利由于未满足该条款而被排除在外。ICC第8445号案件也采取了这种观点,认为“对仲裁庭而言,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上陷入徒劳无益(futility)的境地,则仍然要求双方当事人调解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拖延争议的解决”[3]。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违背双方当事人的订立初衷,也不能凸显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对维系商事合作关系的优越性。如果只将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视为仲裁条款,否认协商、调解条款的程序法性质,那么违反协商、调解条款只能赋予一方当事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违反协商、调解这种程序性事项带来的经济损失极难界定,很可能无法起到救济的效果。另外,调解作为一种ADR方式,在国际商事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适用,应当认可其程序法性质。事实上,苏黎世州最高上诉法院的实体说判决,在瑞士也遭到了不少批评[4]。
(二)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是由数个程序构成的整体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性质实质涉及的是“程序上的可裁性(procedural arbitrability)”问题,即裁量仲裁开始的条件等,而不是“实体上的可裁性”,包括裁量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争议事项是否属于仲裁条款范围等[5]。
美国法院倾向于认为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构成一个新的争议解决方式,整体上产生程序法的效力,调解是仲裁的前置程序,部分履行的情况影响整个条款的效力。如2002年美国第11巡回法院在Kemiron Atlantic v Aguakem International,Inc[6]案中裁定,当事人不履行调解条款,仲裁条款未被触发(triggered),当事人没有提起仲裁的义务,因此法院对于当事人是否履行前置程序有管辖权。该判决也在2003年的Portland LLC v DeVito Builders.[7]中得到了援引。
ICC第12739号、第6276号案件以及第6277号案件中仲裁庭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协商是仲裁的前置程序,但是双方当事人没有履行该前置程序,因此仲裁管辖的条件尚不成熟,仲裁庭被解散(而非仲裁程序中止)[8]。
学界对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中的诸多条款结合起来构成新的争议解决方式的观点,尚没有一致意见。笔者认为该观点仍存在不足:第一,将诸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可能会导致对该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僵化解读,特别是认为其中一个条款未满足整个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都无效。第二,诸条款的结合也影响了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没有履行协商或者调解条款,并不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因此放弃了提起仲裁的权利而交由法院处理,从这个角度上看,将整个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视为无效的观点是非常激进的。
(三)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是数个独立条款的衔接
第三种观点认为,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是数个争议解决方式的结合,每个条款彼此独立,违反调解条款不会导致仲裁条款无效。在调解程序作为仲裁前置程序可执行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要求调解,而另一方当事人要求仲裁,那么仲裁庭应当拒绝管辖,促使当事人进行调解[9]。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更符合当事人订立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时的期待,也更凸显多层次争议条款的优点。当事人选择在仲裁前设置协调、调解的条款,只是为了用更灵活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将仲裁“一裁终局”的影响降到最低,因此从当事人设置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初衷上看,并不是为了将协调、调解和仲裁捆绑成一个整体的条款,协商、调解条款甚至影响仲裁的提起效力。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中的协商或者调解条款,与仲裁条款一起,不过是多个条款的组合,各自应当有独立的执行力。这些条款各自独立,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这些条款只存在衔接的关系,而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当事人未满足协商或者调解条款而提起仲裁,体现的是条款执行力上的冲突,应当由仲裁庭裁量。如果仲裁庭认为,当事人应当履行协商或者调解,则可以中止仲裁程序,协商或者调解失败,则继续仲裁程序。这样既不会浪费仲裁庭的组成,增加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费用,也不会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真正使该条款发挥其优势。
综上,对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的考虑,应当区别分析各个条款的可执行性。仲裁条款的可执行性无须赘述,国际上也达成了一致,因此实际上需要考量的即协商或者调解条款的可执行性。
对于调解条款的可执行性,各国法院和仲裁庭一般都认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条款上足够明确,二是条款要明确规定调解程序对双方当事人的执行力。因此主要看条款使用的语言以及法院或者仲裁庭的解读。比如使用“可以”这样的字眼,那就意味着双方的调解义务仅具有选择性,不产生对双方当事人的强制性约束力[10]。对调解义务的解读,各国法院认为,如果包括回合数[11]、特定参与成员[12]、或者主持机构[13]等,可以认为这个条款足够明确,双方应当首先履行调解条款规定义务。
不过国际上尚未对协商条款的效力达成统一意见。大多数法院都认为协商条款不具有强制性,没有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的义务,不具有可执行性。唯一的例外是澳大利亚法院在United Group Rail Services Ltd v Rail Corp.案中首次承认,“进行善意的协商”也具有执行力,其在判决书中写道,“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如果双方订立了清晰且具有约束力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并首先约定协商,则应当得到尊重。协商和调解的唯一区别是调解中有第三人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而协商只是双方自己达成协议。由于调解中双方也可以自行达成协议,因此把协商和调解作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协商条款也应该具有执行力”[14]。但是只有“友好协商”这样模糊性的词汇,国际上一般都认为,不能使得协商条款明确而具有执行性。除非具有更明确的程序性事项[15]。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上普遍认为,协商或者调解条款如果足够明确并规定了程序性事宜,可以认为其具有可执行性。协商或者调解条款具有独立程序法性质的观点,也被《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所采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2002年颁布的《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旨在供成员国直接援引或依据该法制定本国法。该法的第13条规定:“当事人同意调解并明确承诺在一段特定时期或在某一特定事件发生之前,不就现在或未来的纠纷提起仲裁程序或者司法程序的,仲裁庭或法院应当承认这种承诺的效力,直至所承诺的条件实现为止,但一方当事人认为是维护其权利而需要提起的除外。提起这种程序本身并不被视为对调解协议的放弃或调解程序的终止。”由此也可以看出,协商或者调解条款不会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
四、提高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可执行性的路径
(一)从条款起草注意防范风险
判断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执行力的关键还是在于条款是怎么起草的,而判断的标准以及违反条款约定的后果等更多地由各国国内法来决定。为了使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中协商、调解条款更具有可执行性,避免沦为原则性的规定,实践中应当对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起草事宜加以注意。
首先,在起草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时,应当采取强制性的语言如“必须”、“应当”、“有义务”等,而非任意性的词语如“可以”等。避免影响当事人事后协商或者调解程序的开展,也能明确表明双方为了维护商事合作关系而在争议发生后进行协商或者调解的强烈意愿。
其次,层次衔接上应当明确。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可以首先进行协商”,则当事人可以约定随时可以提起仲裁。如果双方采取了强制性的语句如“必须先调解”,则应当在条款中明确“调解是协商的前置程序”。
最后,应当明确具体的程序性规则,比如协商的回合数或者期限,协商的参与人员,调解的主持机构等,避免使用“双方应友好协商”“双方应尽最大的努力协商”这样概括而原则性的语句。
长远看,从起草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时就注意使用强制、明确性的语句,能督促双方履行义务,减少未来争议发生时的不确定性,也对条款的可执行性认定大有裨益。而司法实践中对条款效力冲突时采取中止仲裁程序的做法,顺应国际商事实践的主流,也符合我国一贯的裁判思维,将对我国司法实践有所借鉴。
(二)条款独立下仲裁庭的管辖程序设置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管辖权争议,实际上是协商或者调解条款与仲裁条款在效力上产生了冲突,这应当交由仲裁庭裁量。仲裁庭应当判断,该条款中的协商或者调解条款是否具有强制性和明确性。如果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双方应当在提起仲裁前履行协商或者调解义务,并对如何协商或者调解有详细而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则可以认为该协商或者调解条款具有可执行性。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三种情形:第一种,如果当事人未尽初始层次中的协商、调解义务,直接跳过仲裁程序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一方当事人提起仲裁,一方诉至法院,那么法院应当拒绝管辖,交由仲裁庭审议。第二种,如果当事人合意放弃协商或者调解条款,提起仲裁,则仲裁庭对此有管辖权,法院应当拒绝管辖。第三种,如果一方当事人要求调解,一方当事人要求仲裁。则仲裁庭应当拒绝管辖,中止仲裁程序,让当事人进行充分协商或者调解。协商或者调解不成,仲裁庭仍然可以继续仲裁程序。这样既不会浪费仲裁庭的组成,增加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费用,也不会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真正使该条款发挥其优势。
(三)对于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将会暴露出来,漫长的诉讼与沉重的司法成本可能仍然无法解决纠纷,在这样的环境中,应当更加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仅让诉讼成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应当让当事人在每个纠纷解决阶段都能合理表达自己的需求,弱化诉讼或者仲裁的终局作用。
然而我国并没有详细条款规定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只有仲裁协议具有执行力,调解或者协商条款并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的提高,除了从微观上需要对条款的起草和适用进行风险的防范,还需要从程序和整个法律制度上,推动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适用和发展。
具体而言,应当从法律制度和示范规范上推进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适用:首先,应当在《仲裁法》的修订中规定“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承认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效力,给予协调、调解条款的法律适用空间。这种条款的设置,可以在归纳国内相关判例的基础上,对于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认定设定一定的标准,比如各个条款的明确性判断,还有仲裁机构应当如何进行管辖程序等。其次,我国仲裁机构可以像国际商会等一样,制定多层次争议解决机制的示范条款,为当事人提供指引。示范条款在国际上已经屡见不鲜。在我国多层次争议解决机制仍然没有获得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界足够重视的情况下,示范条款能够为不少当事人制定有执行力的条款具有足够的参考性,减少诸如“友好协商”等模糊性措辞的出现,规避法律风险,从而促进我国国际商事实践的发展。
[1]Final Award of ICC Case No.11490(2012).
[2]Cassation Court of the Canton of Zurich on March 15,1999,published in ZR 99(2000)No.29.
[3]Final Award of ICC Case No.8845(2001).
[4]Decision of April 23,2001 by Court of Appeals,Canton of Thurgau;reported in ASA Bulletin 2003:418-420.
[5]John Wiley&Sons,Inc.,Petitioner v.David Livingston,etc.376 U.S.543(1964);Howsamv.Dean Witter Reynolds,Inc.,537 U.S.79(2002).
[6]Kemiron Atlantic v Aguakem International,Inc.290 F.3d 1287(2002).
[7][13]HIM Portland LLC v DeVito Builders.317 F.3d 41 (2003).
[8]ICC Case No.12739(2005);Partial Award of ICC Case NO.6276(1990);ICC Case No.6277(1991).
[9]Rachel Jacobs,Should Mediation Trigger Arbitration in Multi -step Arbitr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15 Am.Rev Int’l Arb.161(2004).
[10]Final Award of ICC Cases No.10256(2003).
[11]White v.Kampner,641 A.2d 1381,1387(1994).
[12]Fluor Enters.Inc.v.Solutia Inc.,147 F.Supp.2d 648,653 (2001).
[14]United Group Rail Services Ltd v Rail Corp.New South Wales.2009N.S.W.C.A,177,Australia.
[15]Final Award of ICC Case No.11490(2012).
[责任编辑:郑 男]
钱瑾(1992-),女,浙江宁波人,2015级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D997.3
A
1008-7966(2016)04-0107-04
2016-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