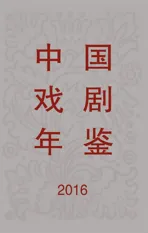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交织而成的史诗
2016-03-14冉常建
冉常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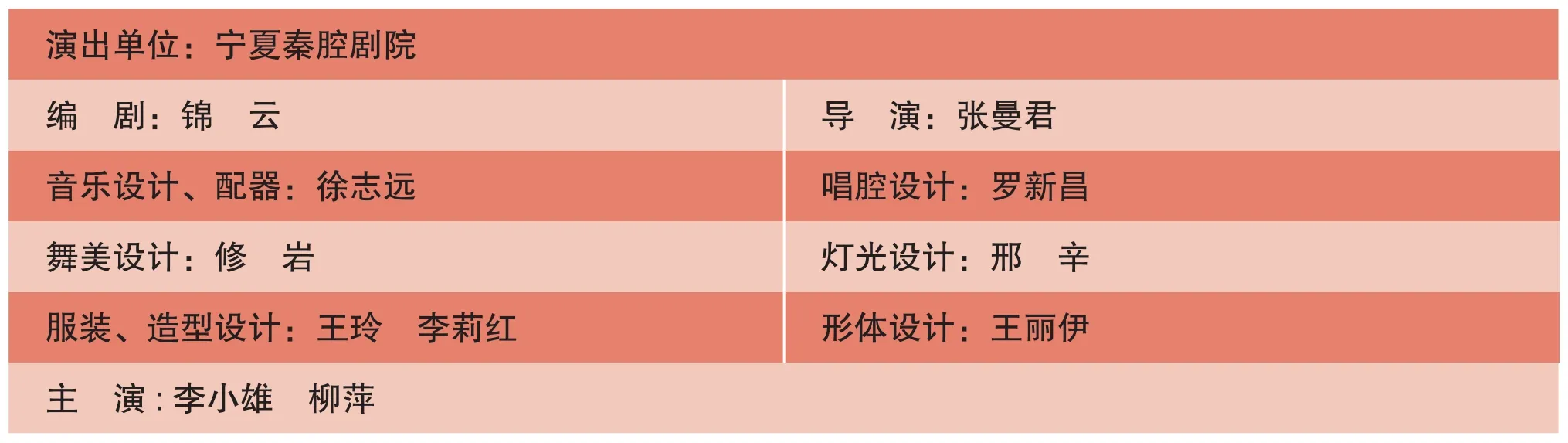
演出单位:宁夏秦腔剧院编 剧:锦 云 导 演:张曼君音乐设计、配器:徐志远 唱腔设计:罗新昌舞美设计:修 岩 灯光设计:邢 辛服装、造型设计:王玲 李莉红 形体设计:王丽伊主 演:李小雄 柳萍
宁夏秦腔剧院演出的大型戏曲《狗儿爷涅槃》,以深刻的哲理内涵、浓烈的诗化情感、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演出样式给首都的戏曲观众带来了多样化的审美享受。在这里,我从以下三个方面简单谈谈观赏此剧的感受。
1、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民族命运的史诗
秦腔《狗儿爷涅槃》不是按照一人一事的传统戏曲结构来组织戏剧情节的,将跨越半个世纪的祖孙三代的发家梦整合在一个舞台演出之中,深刻体现了中国农民精神基因的传承与变异。本剧选取了解放前、解放后和改革开放这三个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波澜起伏的时代背景中重点描写了狗儿爷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轨迹。本剧编剧锦云和导演张曼君不满足于仅仅从道德层面上来评判生活、评判历史、评判人自身,他们从社会、文化、历史、哲学、道德等多种角度去透视生活、透视历史、透视人自身,对农民的国民性、民族性进行深入反思。剧中,狗儿爷的父亲为还债吃活狗崽;狗儿爷抢收地主的芝麻、相亲、分土地、听洞房、被割尾巴、烧门楼;狗儿爷的儿子用推土机开山、修路、拆门楼。这大大小小的事件被融入千百万中国人共同经历的时代背景中,将个人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相结合,从而使本剧成为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民族命运的史诗。
《狗儿爷涅槃》对国民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沉思主要集中在对农民意识的挖掘和展示上。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经济形态,小农文化中封闭、落后、保守、愚昧的传统观念是束缚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枷锁。编导努力站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叙述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揭示历史、人生的本质。创作者从新的角度审视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把眼光投射到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的集体意识、无意识层次,去追寻形成民族性格的深层原因。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天灾人祸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无从补偿的贫困与苦难,狗儿爷也像千百万中国农民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浮沉。他们一家三代有着传承不变的精神基因和发家梦,然而时代的巨变也为他们三代的发家梦注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小农经济的主要物质形态和生产工具是土地与车马。因此,对土地和车马的追求是中国农民发家梦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农民的集体意识和代代因袭的集体无意识。本剧中,当已经拥有的土地车马被强行剥夺后,狗儿爷的发家梦被彻底击碎了,他的精神支柱也被摧毁了。
《狗儿爷涅槃》不仅表现了民族精神基因的世代传承,而且展示了改革开放导致的中国民族精神的裂变。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的陈大虎等年轻人挥别历史的因袭,满怀现实的希冀,重塑自我,奔向未来。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思想观念被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思想观念所取代。通过狗儿爷及其儿子陈大虎两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编导暗示了小农文化及其精神的衰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局。
2、具有多重美学价值的时空形态
如何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和众多事件组合在两个小时的戏剧演出中,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本剧编导打破了传统戏曲顺向的时空进程,通过交叉时空、逆向时空、阴阳时空的结构方法,来组织戏剧情节,使演出充满了时空上的跳跃性、多变性。为了集中精力表现主要事件和主要情节,编导淡化了剧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在抽象而多变的时空中演绎了狗儿爷一家三代的人生命运。

本剧舞台时空的转换主要是依靠祁永年鬼魂的叙述完成的。千百年来,地主与贫农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两极。地主祁永年与贫农狗儿爷祖孙三代具有扯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因此,利用祁永年的鬼魂介绍故事背景,交代人物关系,表现灵魂对话,不仅使本剧舞台时空的转换流动超越了物理时空,构成了主观时空与客观时空随意转换的时空形态,而且还有助于揭示地主与贫农的矛盾冲突,深化演出的思想内涵。本剧以祁永年鬼魂与老年狗儿爷的对话开场,介绍了狗儿爷要放火烧掉高门楼的行动。紧接着,祁永年鬼魂当场更换服装,时空闪回到解放前他逼迫狗儿爷父亲陈老汉活吃一只小狗崽的场面。当陈老汉抱恨身亡和发家梦碎后,舞台上的死尸一个鲤鱼打挺又复活过来,变成了老年的狗儿爷,时空又回到了现在。这个死尸变活人的手法形象地揭示了农民发家梦的世代传承与延续。在祁永年鬼魂的引导下,舞台时空快速穿插了青年狗儿爷抢收地主家的芝麻、相亲、得失土地车马等情节。最后,祁永年的鬼魂介绍了自己的女儿与狗儿爷的儿子陈大虎结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山、筑路、发家、致富等情节。在此,演出的叙事时空由虚入实,地主与贫农作为对立的两极也彻底融为一体,它们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彼此依存又相互转化。狗儿爷和他父亲奋斗了一生的发家梦在后代身上展露出了曙光。
本剧编导善于利用时空的并置来加强历史事件内在的悲剧性,诗情与意蕴就在舞台时空的交叉并置中回荡、透射出来。当李万江与狗儿爷的前妻冯金华入洞房时,疯疯癫癫、不明真相的狗儿爷抱着板凳,躲在洞房的窗下偷听、找乐。此时,屋里屋外两个空间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它们彼此衬托,从而加强了狗儿爷人生命运的悲剧色彩。在洞房内外的两个空间中,同时出现了背媳妇的场面。舞台前区,狗儿爷喜悦地背着一条板凳,把它当作拟人化的媳妇冯金花,回想到了当年与她成亲的情景。舞台后区,李万江背着狗儿爷的媳妇入了洞房。编导把虚实两个背媳妇的场景同时呈现在舞台上,使观众更深切地彻悟到人生的悲凉和历史的残酷。
3、新颖独特的演出样式
本剧导演在挖掘文学剧本的思想立意和设计叙事结构的基础上,还与音乐设计、舞美设计、主要演员共同研究整体舞台形象和人物形象的独特呈现方式,使演出样式新颖而独特,并富有强烈的视听冲击力。除了具有多重美学价值的时空形态外,导演还充分发挥戏曲舞台的假定性、抒情性、歌舞性等艺术特长,运用歌舞队、舞美道具和肢体语言等创造鲜明、独特的演出样式。歌舞队既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串场者,也是舞台道具的检场人、舞台画面的造型因素。在剧中,歌舞队忽而作为群众参与戏剧行动之中,忽而跳出剧情来介绍时代背景,忽而又作为一种旁观者倾听主人公的心声。例如,当火烧高门楼时,狗儿爷在用多条板凳搭起的高架子上,唱出了回忆梦想发家的精神历程和人生往事。这时,导演安排众多歌舞队员爬在前区的板凳上倾听狗儿爷的心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舞台景观。

此外,导演还利用歌舞队与主题歌的结合,反复渲染本剧的主题思想。如“惊蛰化一犁,春分地气通。旱天打响雷,圆我一个梦。” 每当舞台上响起粗犷豪放的主题歌时,就会出现歌舞队风格别致的群体舞蹈。本剧留给人们的另外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导演对舞美道具板凳的多样化运用。在剧中,板凳既是空间样式,又是视觉造型;既是演员表演的支点,还是主人公情感投射的对象。例如,本剧一开场,舞台上就呈现出七零八落的长板凳。在灯光的明灭中,场上的板凳和群众越来越多。他们以样式新颖的群体定格造型,营造了一幅农民众生态群像图。随着全剧事件的流动,板凳不断被拆卸组合,成为物化的芝麻、逃难的行李、表演的高台、想象中的新娘等。导演用极端化的舞台样式,盘活了舞台空间,外化了人物心灵。表情达意的肢体语言是塑造人物和抒发情感的利器。在本剧中,导演从人物的精神状态、生理状态、性格状态、戏曲工架的造型感、戏曲动作的韵律感等方面创造人物的形体造型,从而也用美化的、歌舞性的肢体语言外化了人物的精神特点、生理特点和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又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涵。例如,老年狗儿爷与青年狗儿爷在面部化妆和形体造型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反差。老年狗儿爷的形体造型是罗圈腿、弓背腰、架肘、揣手,着重表现历史岁月印在这个人物形象上的沧桑痕迹。此外,狗儿爷的形体动作在身体造型的工架化、生活动作的舞蹈化、手眼身步的韵律化、动作节奏的音乐化等方面也力求向戏曲的美学特性靠拢,体现出对现实生活提炼和美化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