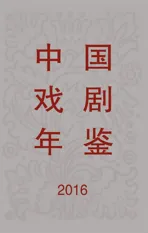脱胎与蜕变
——川剧《草民宋世杰》剧本移植试析
2016-03-14邓添天
邓添天
2015年2月,四川省川剧院新创川剧《草民宋世杰》在成都首演,3月晋京展演,引起了业界的关注。早在该剧排演前,我就在四川省剧协的剧本研讨会上看到了剧本,是著名剧作家隆学义自京剧《四进士》移植而来。
相对于京剧《四进士》,川剧《草民宋世杰》在剧本上完成了脱胎与蜕变。剧作家隆学义在移植过程中提取了京剧的情节内瓤,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斫伐扬弃,形成了川剧《草民宋世杰》区别于京剧《四进士》的四大特色。
一是戏剧叙事代替了时间叙事。京剧《四进士》文本冗长,完全按照故事发生先后顺序叙事,缺乏人物塑造,缺乏情节取舍,缺乏轻重缓急的戏剧节奏,是一本典型的流水账。比如,“宋世杰替杨素春告状”的起因,也就是姚廷春、田氏加害杨素春的原委,就占全剧三分之一的笔墨。其后的毛朋、顾读、刘湜、田伦四进士的背景情况又轮番上演,一个信息多处交待。可以看出,京剧剧本相当于是演员表演身段、技巧的场记。京剧《四进士》如果从戏剧结构、人物塑造等角度来审视,实在乏善可陈。但川剧《草民宋世杰》在这方面采用了西欧话剧那种节奏感更强的戏剧叙事,撕烂了京剧原有的流水账本,加强了正反矛盾交锋。我们依次来看每一场的铺排。第一场“暗遇馆遇”。正所谓“不破不立”。剧本开门见“锋”,开场就为“宋世杰替杨素春告状”立下了态度的军令状——他对官不屑、爱民如子、善打抱不平,期待对峙当年海瑞大人四位门生为官清正誓言的愿望,为宋世杰铺垫了揭竿而起的动机。这“立”的过程,全从算命解命泡茶吃茶的对话行动中来。第二场“救女收女”。呈上“破”的起因:异乡人杨素春有苦有冤。与“立”的态度相抵触,旋即进入行动状态。第三场“改状递状”。艰难险阻越是强大,那么战胜它的行动就越是掷地有声。宋世杰“改状递状”也在层层阻挠下发生——阻挠先是宋世杰内心纠结:幕幕回顾打抱不平却不太平的身世、幸遇万氏垂爱、又怕牵累万氏的顾虑;接着是顾读门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拦截;再后来终于见着顾读,顾读却在“包揽词讼”的措辞下语言套;劝说宋世杰收敛血气方刚的年少性情;在杨素春住处上找宋世杰徇私的证据;拿词状“一字入公衙、九牛拔不出;湿笔点干纸,画字要人头”严苛律例吓唬;等等。阻碍就像磨砂膏,能让皮肤更嫩白,宋世杰游刃有余的一一应对,其行动也饱满起来。就这样,以反激正,以正推反,刚出炉的正面行动肯定要等待绝不示弱的反面行动继续磨砺,于是,顾读产生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隐忧,暗示门差干掉宋世杰。剧情顺理成章进入短兵相接的下一场。紧接着田伦的“雅贿行贿”行动,属于放大矛盾的一个背景交待,因为就算不贿赂,顾读对宋世杰替民告状也反感非常,贿赂只是顺水推舟;所以隆学义以楔子形式几笔带过,精干洗练;接着迎来宋世杰“取证抄证”第四场。田家官差与替田卖命的街娃,他们一前一后,一明一暗,一个送信,官官相护,强强联手,从事件本身投下障碍;一个杀宋,釜底抽薪,从根源上绝后患。可有意思的是,他们看似杀气腾腾,来势汹汹,实则纸糊老虎。这是隆学义有意而为之,他想写人,外强中干的弱态更能展现世间百态的真实面貌。为何?无地位的官差和街娃只是奉命行事者,可以说,他们也是被官府熟视无睹的弱者,所以弱智们做事不太在意做事效果。再加上他们都带着抱怨主子的情绪上场,那就更是如此。所以宋世杰才那么容易偷信取证,稍微嘘寒问暖,街娃就缴械投降。表面上,这场虽如溪水徐徐流动,但它徐中带急,因为宋世杰知道假老虎背后的真老虎了,告状的对象变了,溪水呈积蓄状,慢慢回旋成深潭,正待决堤。铺垫到此,终于顺利进入“抗贪揭贪”正面战场。因田伦、顾读的行贿受贿,毛朋写刁状踢乌龙球的证据在手,宋世杰义薄云天,最终赢了官司。


二是鲜活的人物、积极的行动、跌宕的剧情。俯瞰全剧,宋世杰告状一事仿佛所向披靡,他的性格也有棱有角;但隆学义没有顾此失彼,非常注重次要角色的塑造。就说让宋世杰告状有机可乘的几个人物:比如赖词的毛朋、疏忽的官差、感动的街娃,他们的做法是合理的,展现了炎凉的世态。我们依次开看。先是毛朋为什么要写赖词?作为巡按大人的毛朋,当然知道何时写赖词是引火烧身,何时写赖词是备年终总结用。可见目前属于后者。此时原告被告都是无利益关系的平民,所以毛朋代写状子就为官司能赢,法宝就是“无赖不成词”,其他人等的清白和惩罚也就麻麻扎扎,小事一碟。而后,官差为什么会把信和银子交给素未谋面的宋世杰保管?因为京剧也这样,这是住店的规矩,防火防盗。只不过京剧里交了银子,信件犹豫再三后自己保管。乍看,京剧官差似乎更有防范意识,实际上他们就是宋世杰偷信、拆信、看信、装信,展示表演绝活的两个支点,他们更像傀儡。而川剧里,银子和信件按住店规矩一并交出,绝无犹豫。为什么?难道官差不知道信件是秘密,不能随便给人吗?官差当然知道,只是官差只管把事办到,至于办得好不好,不重要。再者,隆学义给官差交信交银子的行动给了充分的解释“双脚双手八只腿飞跑,差钱都不给”,而且还带着“贱差瘦差”的抱怨情绪,办事质量可想而知。再后来是街娃为什么没把宋世杰办掉?街娃是田伦买来的临时性命,亡命天涯的人是最容易动摇的可怜虫。他们几乎只有两个诉求:一是保命;二是求财。他们只顾眼前利益,只想守好眼前利益,走一步算一步,谁满足了他,谁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所以宋世杰用慷慨买走了他们的杀气。因为和官府相比,宋世杰的钱财还要稳当些。正反几个回合交锋,宋世杰都能稳操胜券,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壁垒深严、高不可攀的官府实则危机四伏。利益集合体不比人心集合体,真正遇事时,利益的集合体更像散兵游勇,利益稍有分配不公,一溃千里的懈怠如家常便饭发生,人心集合体其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只会让利益集合体望其项背。正所谓,哀兵必败,官府派出的刽子手个个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只在乎生存利益,那么当这些利益被官府居高临下的忽视时,那么饥肠又怎么能够完美地代表肥肠呢?于是,拔苗助长式的临时委派,有如空心萝卜,满嘴酸水,错漏百出也是自然之事。
三是浓郁的川味。实际上,《草民宋世杰》剧只借了京剧的骨架,而包裹骨架的全是不折不扣的川剧表达。这里不仅有川剧的硬件。比如昆高胡弹灯,甚至川北灯戏的吹吹腔,都完美融于叙事;还有“一人吃饱全家饱,单嚼;两对街娃到处敲,干操”,这样“一句一词式”体现着川人幽默风趣、乐观豁达的特有的表述节奏,让人一听就联想到川人。而且还有川剧的软件。字里行间、语序排列,剧中人怎么说话,说什么话,也是泡在四川味里。更有一些封存已久的老话、旮旯的土话、极富喜感的俏皮话也俯拾皆是,比如“抹不脱”、“歪瓜裂枣”、“疯都疯了”、“抽我底火”、“死砍脑壳”、“车身”、“脆蹦脆蹦”、“花儿马踏”、“笼起”等,已经超越了现如今流行的“巴适”、“啥子”、“要得”等通俗川话。今天某些新创川剧,做得好一点的,可以从理论上称它为川剧,做得不好的,就是话剧加唱。这种状况正是季国平博士在《强调中国戏曲美学必要性》里指出的痛点,也就是,其符合川剧美学原则、化为川剧表现手段的“唱做念打”写作功夫还下得不深,其戏曲化、剧种化、程式化、个性化的属于川剧的识别度还不高,犹如画龙不点睛,画虎去掉骨,总觉得缺点什么。一方文化的传承,如若流于皮毛的继承,甚至流于理性的继承,而缺乏感性的继承,那都还得警惕。在普通话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一概要求标准化、一体化的今天,重新拾掇原汁原味的川剧,对于所有川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四川年轻一代作者,非常迫切。年轻人最不应丢失的就是流淌于身心间的、有底蕴的民族民间性。今天展示地方文化,多用物品代表;少以人物性情示之。模模糊糊、无棱无角、生活在地方但不具备提炼地方人物性情精髓能力的作者们,于地方文化发展来说,不是益事。而隆学义的川剧创作,正具备了这样的品质, 不仅理性上继承了川剧技艺,而且感性上张扬了川剧的个性。
四是提供了充分的表演空间,是读演两相宜的场上曲。读《草民宋世杰》剧,你能顷刻察觉到,隆学义确实是一位深谙舞台、对川剧表演艺术了如反掌的剧作家,他是比着川剧表演艺术充实内容。比如字里行间的地道热辣的川话表达,仅此一点,便帮了演员塑造川人性情一个大忙。因为无语言无依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今天走在路上的川人,也未必具有川人的辨识度。舞台,于现代人而言,可能便是川人找寻姓氏的唯一地点。隆学义算是比川人更懂川人,演员有了这些依托,就由不得他不姓川。其他的,如唱功戏(昆高胡弹灯吹)、技艺戏(变髯口,耍口条、异地同台)、讲口功(名词排列的大段绕口令),也是多多益善地倾囊相授。最重要的是,这些内容不是为表演而表演、经不起推敲的文字记录,而是统一于戏剧叙事之下的表演述说,且人物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思想。这些都是为戏剧献身的表演,而不是为表演献身的戏剧。
然而,除了上述优长,我一直觉得《草民宋世杰》剧好像还缺少点什么?
首先,《草民宋世杰》剧做了两件事,一是移植剧种,二是改编传统戏。这两件事要做好,一要剧种配适度高;二要在人物、情节、主题的构思上不再传统,焕发新意。那么《草民宋世杰》剧的这两件事做好了吗?当然与川剧配适肯定很高, 这第一件事做得很成功。那么,第二件事,《草民宋世杰》剧的新意在哪里?《草民宋世杰》剧属公案戏。从古至今,公案戏几乎秉承着一种情节和两种结果,一种情节是为民请命式的告状,两种结果是要么告赢(遇到包公或赢得侥幸);要么告输(输得彻底);情节和结果反映了人们的两个心迹:一是期盼主宰对错生死的官都是好官,这是浪漫主义写法;二是直面过去官场告状难的现状,这是现实主义写法。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呼唤公平公正是一致的愿望,这个愿望永不过时。所以公案戏要写得好,关键看“告状”故事讲得是否精彩。而从改编层面上说,《草民宋世杰》剧的故事是讲精彩了的,但属于侥幸赢类型,那么还应在“侥幸”上找缺失。
“侥幸”赢类型的写法会让人产生“顺着写”的错觉,觉得没有矛盾,宋世杰太强了,所有事都难不倒他。即便这是正反矛盾交战的写法,但“侥幸”意味着反面力量是藏着的,或者是不易察觉的,虽然隆学义也都有交待,但在观演过程中,寥寥几笔的交待很容易被快节奏的戏剧叙事轻轻抹杀掉。康式昭先生也说过,“顺着写”的路子,缺乏矛盾的可视性和尖锐性,虽然它的情节可能是合理的,但就写戏而言,并非上选。所以既然已经如此了,只有在导排上捕捉一些台词之外的动作与情态,用特写的方式,强调出次要人物那份坚定的孱弱,让观众体察到这份炎凉百态的意味深长,从而更深刻地看待宋世杰,虽是处处逢迎,却是如履薄冰;虽是合乐喜庆,却是布满杀机;虽是油嘴滑舌,却是腹背受敌,虽是暂时地胜利了,却是永远地失败了。有了悲情色彩,观众才会同情宋世杰,观演距离才会拉近,主题的警示意义才会更加流畅地传递出来。观众心理学说,观众进剧场,总有一种潜在的高高在上的心态,就像杜兰朵站在高台,挑衅求婚者把她骗下来一样,是对持与高傲的。而促使人与人之间最快靠拢的方式,就是示弱。当然,我们相信,经过打磨,主创人员有求婚者的本事,不仅能把观众“骗”下高台,而且还能“骗”出杜兰朵式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