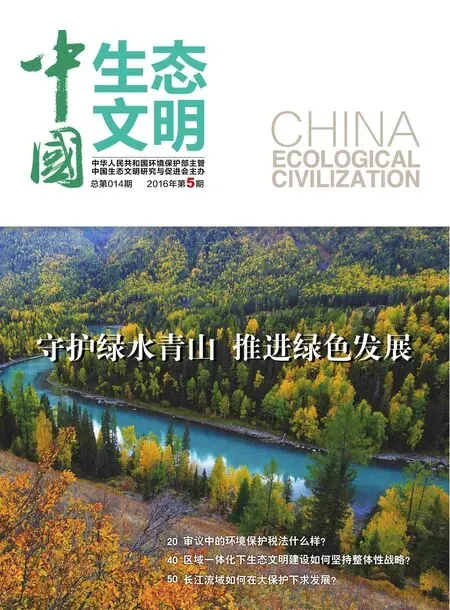丁香
2016-03-14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阿 来
丁香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 阿 来

阿来,男,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获奖者,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协主席,巴金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诗集《棱磨河》,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等。
来自四川阿坝高原的阿来在文学上的造诣和影响力享誉国内外,而他多年致力于呼吁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却鲜为人知。阿来曾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生态环保议案,2013年呼吁维护生态安全“底线”,2014年提出应针对自然保护区立法,2016年的议案涉及野生动物、珍稀植物的保护。多年来阿来一直都在关注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化,呼吁保护生态脆弱的高原环境,以及雪莲、红景天等珍稀野生植物,新书《蘑菇圈》的灵感就来源于人们对松茸、虫草的过度开采。
《丁香》与《桐》选自阿来的哲思散文集《语自在》第二辑“草木之名之美”。阿来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逊的姿态去了解它,城市里的花草,跟城市的历史有关,它们是把自然界事物和城市连接起来的媒介,同时也把我们带到一个美的、文化意味悠长深厚的世界。
打开电脑新建文件时就想,关于丁香有什么好说的?其实不止是丁香,很多中国的植物,特别在诗词歌赋中被写过——也就是被赋予了特别意义的植物,都不大好说。中国人未必都认识丁香,却可能都知道一两句丁香诗。远的,有唐代李商隐的名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就这么两句十四个字,丁香在中文中的形象就被定格了,后人再写丁香,便如写梅兰竹菊之类,就不必再去格物,再去观察了,就沿着这个意义一路往下生发或者有所扩展就是了。
于是近的,就有现代诗人戴望舒的名诗《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一个女人,如果有了诗中一路传承下来的某种气质,就是一个惹人爱怜的美人了——这种气质就是丁香。虽然,我们如果在仲春时节路过了一树或一丛丁香,那么浓重热烈的芬芳气味四合而来,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联想,却是深长悠远的哀愁与缠绵。或者怀着诗中那种薄薄的哀愁在某个园子中经过了一树丁香,可能会想起丁香诗,却未必会认识丁香;也许认识,但也不会驻足下来,好生看看那树丁香。我甚至想,如果有很多人这么做过的话,这样的丁香诗就不会如此流传了。
抛开眼前的丁香花暂且不谈,还是说丁香的诗,这种象征性意义的固定与流传,在李商隐和戴望舒之间还有一个连接与转换。那就是五代十国时南唐皇帝李璟多愁善感的名句:“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但是,丁香花却并不是真的这么愁怨的,花期一到,就一点都不收敛,那细密的花朵攒集成一个个圆锥花序,同时绽开,简直就是怒放。我在植物园拍一株盛花的火棘时,突然就被一阵浓烈的花香所淹没了,但我知道,火棘是没有这样的香气的。抬头,就见到一株纷披着满树白花的丁香!说纷披,确实是指那些缀满了顶生与侧生的密集花序的枝子都沉沉地弯曲,向着地面披垂下坠。那么繁盛的花树,是怎么引起了古人愁烦的?待我走到那树繁花的跟前,那么多蜜蜂穿梭其间,嗡嗡声不绝于耳,我只在蜂房旁边才听到过这么频密的蜜蜂的歌唱——同时振翅时的声响。这么样子的热闹,这么强烈的生命信息,怎么和一个“愁”字联结起来?
但是,诗人们不管这个,只管按照某种意思一路写下去,“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这么按照某种意思一路写下去。

所以,李璟写下“丁香空结雨中愁”时,不仅接续了李商隐的愁绪,而且请来了雨,让丁香泛着暗暗的水光,在长江边的霏霏细雨中了。这位皇帝还把这种写愁的本事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李煜,他写愁的诗句甚至比乃父更加有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李姓父子身逢乱世,却不是曹操父子,文有长才,更富政治韬略与军事禀赋,所以强敌环伺时,身在龙廷却只好空赋闲愁,只好亡国,只好“流水落花春去也”,只好“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就说到成都这座城市了,李璟李煜写出那些闲愁诗也是亡国诗的时代,也是我们身居的这座城市产生“花间派”的时代。是那些为成都这座城市的历史打上文化底色的词人们用“诉衷情”、“更漏子”、“菩萨蛮”和“杨柳枝”这样轻软调子的词牌铺陈爱情与闲愁的时代。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偏怨别,是芳节,庭下丁香千结。”
看看,那时候长江南北战云密布,偏安一隅的成都就很休闲,那时他们还赋予了丁香后来在中国人文化观念中固定流行的爱情的意义:“豆蔻花繁烟艳深,丁香软结同心。”什么意思?一来是诗人格了一下物,看到丁香打开花蕾(所谓丁香结),花瓣展开,这种两性花露出的花蕊,也就是雄蕊与雌蕊的组合都是那么相像——同心,并从此出发联想到了爱情(也是同心)。但是,这么一种地方性流派审美生发出的意义,却在后来浩大的诗歌洪流中不甚显著,因为这个地方的文化从来不能顺利进入或上升为全国性的主流,当然,李白们,苏东坡们是例外,因为他们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视野上都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所以,后人评花间词说:“嗟夫!虽文之糜,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
再后来,好多很好描写了成都的诗文都是外来人的杜甫们所写下的了,成都太休闲,不要说修都江堰这等大事,连写诗这样不太劳力费神的事,都要外地人代劳了。
以上,是我说丁香顺便想到的,对成都努力让自己符合休闲城市这个定位时,关于文化方面一点借古喻今的意见。
既然说了意见,索性顺便再说一点,这是有关这座城市的园林设计与道路街巷的植物布局。
人们常说,一座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城市最大的记忆承载体当然是一座城市的建筑。成都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要靠老的街道与建筑来负载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味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一座城市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一代人相伴,却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树。对成都来说,就是那些这座城市出现时就有了的树:芙蓉、柳、海棠、梅、槐……这座城市出现的时候,它们就在这座城里,与曾经的皇城,曾经的勾栏瓦舍,曾经的草屋竹篱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基本风貌,或被写进诗文而赋予意义,或在院中,在某一街口,一株老树给几代人共同的荫庇与深长而具体的记忆。但是,在今天的城市布局中,这些土著植物的地盘日渐缩小,而从外地,从外国引进的植物越来越多。我个人不反对这些植物的引进,比如立交桥下那些健旺的八角金盘就很美观,而且因其生长健旺也很省事。池塘中和芦苇和菖蒲站在一起的风车草也很美观。街道上一排排的刺桐与庭园中的洋紫荆也不可谓不漂亮,只是它们突然一下子来得太多太猛了,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意思。在我看来,其实没必要一条一条的街道尽是在这座非热带城市连气根都扎不下来的小叶榕,须知它们是挤占了原来属于芙蓉的空间,属于女贞和夹竹桃的空间,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属于丁香树的空间。这几日,正是丁香盛开的时节,但城中却几乎看不到成气候的丁香的分布了。一种漂亮的芬芳四溢的土著植物差不多已经从街道上消失了,退缩到小区庭园与公园,聊作点缀了。前天,被请到什邡去为建立地震遗址公园出点主意,回来路上,三星堆博物馆主人留饭,在博物馆园子里,看到几丛很自在,很宽舒地生长着开放着的丁香。但那里虽然在地理上还属于成都平原,毕竟行政上是在别的行政区划的地盘上。
还是今天,5月2日,到城北的植物园才看到几株漂亮的丁香。
出城进城,正在扩建的108国道都拥挤不堪,但让人安慰或者愿意忍受这般拥挤的是,改造过后就好了,而且道路两边的挡土墙上,就彩绘着扩建完成后大道的美景,我就想,那时大路的两旁,会有很多的丁香吗?
真的,让这座城市多一点土著植物,因为这些植物不只美化环境,更是许多城市居民一份特别的记忆,尤其是当这座城市没有很多古老建筑让我们的情感来依止,多一些与这座城市相伴始终的植物也是一个可靠的途径。植物也可以给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增加一些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