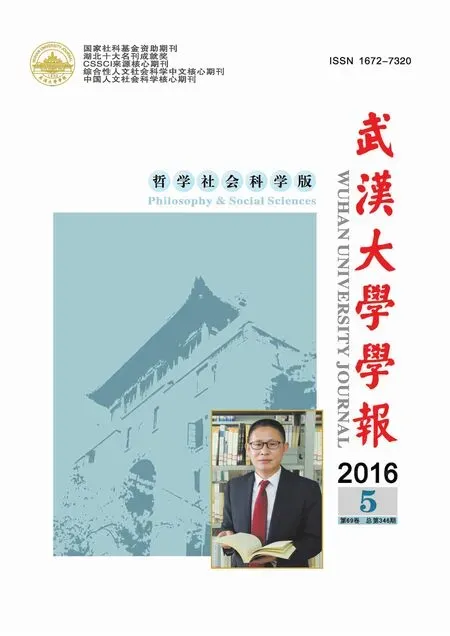论婚姻缔结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及其效力
2016-03-13冉克平
冉克平

论婚姻缔结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及其效力
冉克平
从合同法、继承法、婚姻家庭法等抽象出意思表示及其瑕疵,作为共同的“公因式”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婚姻缔结之中可能存在意思表示瑕疵,例如心中保留、通谋虚伪表示、错误(重大误解)、欺诈以及胁迫等类型。在效力上,缔结婚姻一方心中保留不影响婚姻的效力,但是因双方通谋虚伪表示、错误、欺诈以及胁迫而缔结的婚姻,属于可撤销之婚姻。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的维护以及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的原则,缔结婚姻时瑕疵意思表示效力例外应予以变通。
婚姻缔结; 意思表示瑕疵; 通谋虚伪表示; 心中保留; 重大误解; 欺诈胁迫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婚姻自由作为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在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得以广泛确立。通常认为,结婚是男女双方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互为配偶的结合(不考虑同性婚姻),是否缔结婚姻以及与何人缔结婚姻,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他人不得强迫或者干涉(《婚姻法》第5条)。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男女双方完全真实自愿,各自的内在意思与外在表示完全一致固然理想。然而,现实世界中,婚姻缔结的双方当事人虽表面上达成结婚的合意,但一方或双方因为受各种主观或者客观因素的影响,致使当事人的内在意思与外在表示之间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亦非鲜见。例如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男女一方或者双方是为了获得户籍、房屋等而“假结婚”*参见郑吉喆(2014):《卖房避税假结婚,假戏真做一场空》,载北京法院网,http://bjg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7/id/1349877.shtml。;或者一方对另一方的品行等发生错误;一方受到他人的欺骗、胁迫等。
在民法典总则编制定的背景之下,意思表示及其瑕疵如单方虚伪表示、通谋虚伪表示、错误、欺诈与胁迫等,以及相应的效力规则,无疑是民法典总则立法的重心。从201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民法典总则草案》来看,第三节规定的即是法律行为的效力(第121条至136条)。我国《婚姻法》第11条仅规定了胁迫婚姻属于可撤销的婚姻。然而,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因男女一方心中保留、双方通谋虚伪表示,或者一方因错误(重大误解)、欺诈等而缔结的婚姻,有必要探讨的是:(1)民法典总则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规范,能否在婚姻缔结行为之中得到运用,以发挥总则之于分则的体系效应?(2)如果民法典总则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可以一并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基于婚姻关系的自身特性,在具体适用上是否应有所差别?笔者拟以婚姻家庭法为视角,结合我国的司法实务,分析婚姻缔结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及其效力,以期为我国相关立法及其适用略尽绵薄之力。
二、 意思表示瑕疵适用于结婚等身份行为之考察
(一) 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本质的学说分歧
通常认为,法律行为是德国式总则得以构建的基石(王泽鉴,2009a:20)。这是因为,总则中的自然人、法人、物、代理等制度均属于民法的具体制度,很难说有足够的统领性,只有法律行为完全是“提取公因式”的产物,当之无愧地成为括号前的制度(马俊驹、梅夏英,2004:25)。19世纪德国法学所获得的全球性声誉,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法律行为学说基础之上。
然而,由于财产法与身份法存在异质性,“债法与物法的分配原则是两者在法律后果层面上的相似性,而亲属法与继承法则是因为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的、类似的生活事实”(梅迪库斯,2000:20-21)。亲属身份关系如夫妻、亲子、亲属的内容与效力,均与伦理及社会习俗密切关联,因此,总则中的法律行为规范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亲属法,大大苦恼了民法学者(陈棋炎,1984:10)。虽有学者认为,采取“提取公因式”抽象出来的民法总则所规定的是各种法律关系的共同事项,因而法律行为被认为可以适用于民法各编,包括财产法与身份法*Dernburg,Burgerliches 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Bd.1§7.1.一般认为,物权法、债权法、知识产权法属于财产法,婚姻家庭法(或称亲属法)属于身份法,继承法则是与身份法相联系的财产法。。但是,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与财产法律行为不同,仅具有法律行为的形式而不具有其实质。德国式总则实为财产法的总则,尤其是作为民法总则灵魂的法律行为制度仅能适用财产法,原则上不能适用亲属身份法(陈棋炎,1980:15;大木雅夫,1999:206)。对此,我国许多学者也认为,由于民法典总则中的法律行为、代理等制度在家庭关系中几乎都无法适用,婚姻家庭法被纳入民法典,主要是因为后者是市场经济与家庭生活的共同法,并非因为前者与财产法具有同样的体系逻辑(谢鸿飞,2013:98;薛军,2006:40;茅少伟,2013:1137)。
学说上认为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原则不能适用法律行为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1)身份行为具有事实先在性的特征。如王泽鉴教授(2009b)认为,身份关系具有事实先在性,即先有身份生活事实,法律再为评价而加以规范。陈棋炎教授(2005)亦认为,有亲属的身份行为未必就可以发生亲属的身份效果,必须有人伦秩序上亲属的身份共同生活关系事实时,才有发生亲属的身份法上效果之可能。亲属的身份行为并非由亲属之意思表示所构成,更不能依据亲属的效果意思创设亲属的身份法关系。(2)身份行为的意思表示具有特殊性。日本著名的身份法学者中川善之助教授(1961)认为,财产行为中的意思是行为人经过合理计算之后选择的意思,而身份行为中的意思则是非合理计算而决定的意思;身份行为的效果意思与该身份生活的事实不可分割:有身份生活的事实必有相应的意思,反之,有该意思必有相应的身份生活事实。美国学者麦克尼尔(2004)亦持类似观点,认为身份契约与财产契约不同,前者是典型的初级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s),具有长期性、非计算性、全面合作、互相依赖和难以转让的特征;后者是典型的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ships),具有短期性、计算性、可度量的互惠性交换和鼓励转让的特征。 “行为人所实施的身份行为如结婚、收养等,除具有成立亲属身份法律关系的意思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而且行为人之间的效果意思对设立、变更或者消灭亲属身份关系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余延满,2007:46)。
(二) 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的本质分析
近代西方资产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个人自由与权利观念迅速觉醒,代表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被废除,“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使主体平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原则成为市民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在家庭关系领域,因经济活动日益个别化,个体对家族血缘的依附关系逐渐减弱。财产法上平等、自由的思潮开始影响婚姻家庭法。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从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出发,对家庭法进行了全面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家庭法的精神面貌,使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薛军,2010:78)。传统的以父权为主导的家庭结构日趋瓦解,家长制的家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平等伴侣型为核心的家庭结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夏吟兰,2011:5)。一方面,从家庭法的发展来看,法律对家庭关系的干预日益扩大,家庭法在整体上趋向于债法,趋向于长期债之关系(克尼佩尔,2003:182)。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伦理趋于开放,财产法开始渗透到家庭内部,家庭法上的“伦理人”与财产法中的“经济人”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现代民法中的家庭伦理性不断降低。即使是伦常的互动关系,也已经被契约性的互惠关系所侵蚀、所取代(熊秉元,2014:36)。有学者总结道,现代家庭法解读起来不再像描绘一个虚构的、自然伦理的生活关系,而是如同一个社团章程,在该章程中涉及名称、登记、婚姻实务执行权、家庭内部的收入平衡与清算程序(克尼佩尔,2003:114)。总之,在私人自治成为财产法的支配原则的数百年之后,现代家庭法终于向其敞开了大门。
笔者认为婚姻缔结行为是最典型的身份行为,相对于合同、遗嘱等财产行为,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具有特殊性。但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一样,均蕴含意思表示,属于法律行为的实质范畴。
首先,所谓的“事实先在性”仅适用于非婚生子女的自愿认领与否认这两类身份行为*自愿认领与否认必须以亲子血缘关系这一事实存在或不存在为前提,就此意义而言,自愿认领与否认作为身份行为具有“事实先在性”的特征。中川善之助教授在阐释“事实先在性”的涵义时,即以非婚生子女的任意认领作为例,认为认领者与被认领者之间,必须有自然之亲子关系的事实先行存在,其后才可由任意认领为媒介,使法律加以追认而为法律上之亲子关系。参见[日]中川善之助:《身份法总则的课题》,岩波书店1961年,第195~197页。,而对于结婚、离婚、收养等行为而言,由于事先并不存在与当事人身份相牵连的客观事实或纽结,此类法律关系的创设源自当事人个人的意愿。虽然身份、身份关系作为人伦秩序的范式已经“定型化”,但是,完全抛弃法律行为的因素,当事人之不可能产生法律关系。因此,欲获得法律上所规定的权利,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构成某种门槛(Zweigert & KoetzAn,1998:235)。虽然伦理先于法律秩序确定了某些亲属身份关系的内容,但是这也不足以成为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的本质差异。因为各种财产行为类型大多非为法律有意识的创造,它们在获得法律秩序的认可之前业已存在于人们的交易活动之中,这些行为因法律秩序将其作为形成法律关系的行为类型予以认可而成为法律行为(弗卢梅,2013:27)。
其次,相对于无伦理成分的交易关系,亲属身份行为具有较多的“法定主义”,具有较高的强制性。因而亲属身份关系上必然存在较多的公法规范,比如有关家事法官和家事程序的相关规定在婚姻家庭法之中出现得特别频繁,正是反映了这一特殊性(苏永钦,2005:46)。身份行为的类型及内容的法定主义,类似于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原则。差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基础在于伦理秩序与社会习俗,而后者是物权的支配性及保护交易安全的必然要求(孙宪忠,2014:262)。但是,不应据此将合同法与物权法、婚姻家庭法相对立,因为即使在物权法、婚姻家庭法之中,涉及法律秩序所认可的权利和法律关系时,也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内容上的形成自由(弗卢梅,1013:16)。
再次,法律行为的要旨在于,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根据行为人的意愿实现相应的法律效果。法律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因为法律行为的术语指向意思表示与其法律效果之间的关联(Pawlowski,2003)。虽然财产行为的法律效果与身份行为的法律效果存在差异,但是作为私人自治的工具,两者均表现了行为自由与效果自主的本质特征。在婚姻家庭法上,虽然自然人只能在法律及普遍承认的伦理原则的架构内通过身份行为来确定人的法律地位,因而身份行为的法律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律及伦理的规定,但不能认为法律后果只要来源于法律规范就违反了私人自治,毕竟身份法律关系的创设与消灭均取决于行为人的意志。
最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婚姻中的行为与市场行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近些年来,经济学家运用经济理论很有魄力地解释货币和市场领域以外的人类行为如种族歧视、政治、犯罪、教育,也包括婚姻。美国学者贝克尔认为,一方面,鉴于婚姻几乎总是出自意愿,或者由婚姻当事人决策,或者由他们的父母决定,因此,经济学上的“偏好理论”完全可以适用*经济的核心控制者是偏好和技术,它们是市场的两大君主。一个基本的决定性因素是消费者偏好,消费者根据自己先天或后天的偏好(并以其货币选票加以表达)解决社会资源的最终目途,也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各个点之间进行选择。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8页。。于此,可以假定婚姻当事人(或者他们的家长)试图提高他府的效用水平;使结婚的效用高于独身时的效用;另一方面,鉴于男性于女性在寻找配偶的过程中存在竞争,所以,可以假定婚姻市场的存在。在环境的限制下,每个人都试图寻找最佳的配偶(贝克尔,2015:209)。运用上述两个原理,可以对亲属身份行为进行如同财产行为相类似的分析。这也表明,亲属身份行为与市场财产行为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
然而,与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利己之心不同,在家庭内部人们作出行为时的利他之心十分重要。前者是经济学界所有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总是自私的,其利用利己之心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看不见的手”最终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效用(亚当·斯密语);后者是亲属身份行为相异于财产行为的本质差别。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父母、配偶、孩子等都是他们最为钟爱的对象,也就自然地经常成为对他们的幸福或者痛苦有着最大影响的人(贝克尔,1998:325)。因此,在缔结婚姻时,人们所具有的利他之心通常构成该身份行为的特殊情境。
综合而言,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同样是自然人自主安排或设计私人生活、依其意愿塑造法律关系的法律工具。对于婚姻缔结之中发生的虚假婚姻、重大误解、欺诈、胁迫等现象,民法总则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规范仍然可以适用。只是考虑到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具有伦理色彩,而且不存在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因此针对不同的情景,对于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的适用应当进行必要的变通。
三、 通谋虚伪表示缔结的婚姻及其效力
(一) 比较法上通谋虚伪婚姻的效力
通谋虚伪表示(scheingeschäft),又称“虚假行为”,意指表意人和相对人虽就表示内容达成了一致,而实际上双方并不想使该表示产生法律效果,亦即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的是形成某项法律行为的假象(拉伦茨,2003:497)。就婚姻而言,男女双方当事人结婚的主要效果在于建立法律上的婚姻共同生活,这属于婚姻的本质意义(史尚宽,2000:97)。若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并非为了建立夫妻共同生活,而是利用法律规定的次要效果(如税法上的优惠税率、姓名法上的效果以及外国人法上的便利等),此种情形称为“虚假婚姻(Scheinehe) ”(施瓦布,2010:50)。
从比较法看,男女双方通谋形成的虚假婚姻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并不相同,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规定虚假婚姻为可撤销婚姻,以德国、意大利民法以及美国法为典型。德国法力图阻止这种对婚姻自由的滥用,规定当事人缔结婚姻时约定不建立婚姻共同生活的,可以废止该婚姻(《德国婚姻法》第1314条第2款第5项)。意大利民法与之类似*《意大利民法典》第 123 条第1款规定:“在配偶双方商定不履行婚姻义务也不行使婚姻权利的情况下缔结的婚姻,任何一方配偶都可以提起撤销之诉。”。在美国,虚假婚姻被许多外国人所利用,这些外国人为获得移民美国的资格,通过与美国公民结婚从而符合美国移民法的规定达到目的,这类婚姻被称之为“绿卡婚姻”。这类婚姻往往具有婚姻的合法形式,但无婚姻的实质内容。对此情形,多数州的法院认为这种以移民为目的的绿卡婚姻是可撤销婚姻;但是也有此类婚姻是无效婚姻,另一些法院则认为绿卡婚姻与婚姻有效还是无效并不相干,无论法律规定还是法院都无法要求当事人履行婚姻之实(夏吟兰,1999:34、36)。
第二,规定虚假婚姻为无效婚姻,以日本、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日本的学说认为,关于身份上的行为虚伪表示应当无效(我妻荣,2008:276)。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27条规定,对于虚假的婚姻,即双方或其中一方无意建立家庭而登记结婚的,检察长和不了解虚假婚姻的一方得请求宣布其无效。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说与判例认为,纯粹身份行为因涉及公共秩序,且身份行为注重当事人之意思,若无真正结婚之意思,此婚姻根本无效(林诚二,2008:368)。台湾地区“民法”第87条第1项关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之规定,对身份行为亦有适用余地,夫妻双方通谋而为假离婚之意思表示,依照第87条第1项规定,其意思表示无效(王泽鉴,2009a:285)。
由于婚姻具有特殊性,一些国家法律允许因通谋虚伪缔结的婚姻在特定情形下可以从无效、可撤销婚姻转为有效的婚姻。具体而言:(1)考虑子女利益的原则。例如法国判例认为,如果夫妇双方完全是为了达到与婚姻毫无关系的其他结果而准备举行结婚,由于这种联姻缺乏“同意婚姻的意思”,该婚姻无效;但是,为了赋予他们共同的子女以婚生子女的地位,于此而言他们的婚姻仍然有效(最高法院第一民事庭1963年11月20日)(罗结珍,2005:165-166)。在美国,若男人与怀孕的女人结婚是为了使其子女合法化,但并不打算履行婚姻的义务,则许多法院视婚姻有效,而不问当事人结婚的动机(夏吟兰,1999:34、36)。(2)结婚已达一定的期限或者存在夫妻共同生活。《意大利民法典》第123条第2款规定,对于虚伪婚姻,法律规定任何一方配偶都可以提起撤销之诉,但自婚礼举行之日起一年以后,或者在婚礼举行之后当事人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就不得再提起撤销之诉。我国台湾地区学说亦认为,通谋的虚伪婚姻如无婚姻共同生活之事实,应为无效,然于举行婚姻仪式时,纵为虚伪表示,而于其后实行婚姻共活,则其无效已被治愈,应成为有效(史尚宽,2000:392)。
(二) 我国相关学说上的分歧与评析
我国《民法典总则草案》第124条规定了通谋虚伪表示。但是,现行立法如《婚姻法》等并未对通谋虚假婚姻的效力作出规定。学说对此认识不一,大体可以分为以下观点:(1)无效婚姻。有学者认为,当事人缔结的虚假婚姻应为无效婚姻(夏吟兰,2012:76)。(2)可撤销婚姻。有学者认为,当事人缔结的虚假婚姻应为可撤销婚姻(王洪,2003:94)。(3)有效婚姻。还有学者认为,对于通谋的虚伪婚姻,除规避法律者认定其无效外,只要其构成了法律婚或事实婚,就应肯定其效力(余延满,2007:184)。(4)原则可撤销,例外为有效。有学者认为,婚姻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私人关系,虚假婚姻并未给社会和他人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法律规定虚假婚姻为可撤销婚姻,将撤销的权利赋予当事人比一律将其归之无效更具有制度的弹性,也更符合私法自治的精神。但是,若是结婚时属于通谋的虚伪结婚,但后来存在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或者在双方生育有子女的情形下,应当强制通谋的虚伪结婚有效(金眉,2015:183)。
笔者认为,从立法论的角度看,通谋虚伪婚姻原则上应为可撤销。虚伪婚姻虽具有表面上的婚姻合意,但是夫妻双方均无建立夫妻共同生活关系的效果意思。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虚伪婚姻与之类似,均属于意思表示有瑕疵。加之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藏之于内心,难于为外界所探知,因此赋予夫妻双方以撤销权更为合适。但是,考虑到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在下列情形下,应当认定虚伪婚姻可以从可撤销转为有效:(1)夫妻双方在虚伪结婚之后建立了夫妻共同生活关系;(2)具有共同子女的情形;(3)夫妻一方在1年内未行使撤销权。对于通过假结婚避税或者购买学区房等情形,由于其均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52条第7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因此都属于无效婚姻。
(三) 虚伪婚姻对第三人的效力
对于虚伪婚姻对第三人的效力,比较法上认识不一:(1)无效的后果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日本学说与判例认为,如果依据《日本民法典》第94条第2项的规定,虚伪婚姻针对善意第三人的关系时有效,这对于身份关系的本质是不妥当的。因此,虚伪表示形成的身份关系,应当在所有的关系上无效,即可以对抗所有人(我妻荣,2008:276)。(2)无效的后果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有学者认为,虚假婚姻的无效,其结果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王泽鉴,2009a:285)。这显然是将虚伪婚姻与财产行为适用于相同的规则。(3)区分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而适用。有学者认为,无效的虚伪婚姻,不独当事人相互间,即对于第三人亦不得主张其为有效。然善意第三人是否得主张其有效,即是否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此时“民法”第87条第1项但书,应变通适用,即就人的利益关系,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例如甲男已与第三人乙女订婚,而与丙女通谋为虚伪的婚姻举行婚礼,则对于信其为真实之乙女,足以构成婚约终了或解除婚约之重大事由,如乙女因而另与丁男订婚或结婚,不但自己不负违约责任,反而得向甲男请求损害赔偿。但第三人仅就财产上利益,不得主张其为有效,惟得请求因信其为有效所受损害之赔偿(史尚宽,2000:192-193)。
就我国现行法而言,由于婚姻关系的成立与废止以登记为要件,且婚姻登记信息已实现全国联网(2012年6月),因此对于该行为对第三人的效力包括:(1)双方虚假结婚,第三人理应知晓结婚登记信息,而且第三人亦不能与夫妻一方再行缔结婚姻,因此不存在善意的情形;(2)双方虚假离婚,由于婚姻登记已被撤销,如果一方又已与第三人缔结婚姻的,在该虚假离婚被撤销前,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 因心中保留、重大误解缔结的婚姻及其效力
(一) 心中保留缔结的婚姻
所谓心中保留(Mentalreservation,Geheimer Vorbehalt),又称真意保留,是指表意人将意欲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保留于内心,其所表示的内容并非其意思的意思表示。表意人内心的意思(真意)与其表示出来的内容相反,其不想使表示的内容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属于单方虚伪表示。《德国民法典》对此有明文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16条规定:“意思表示不因表意人在心里做出对所为的表示并不意欲的保留而无效。该表示须以他人为相对人而做出,且相对人知道该项保留的,该表示无效。”。如果男女当事人一方并无缔结婚姻的真实意图,而是为达到其他目的而向对方作出结婚的意思表示时,由此形成的婚姻即属于心中保留的婚姻。
对于因心中保留形成婚姻的效力,依《德国婚姻法》第16条、《瑞士民法典》第120条,不问相对人知之与否,均为有效。《奥地利民法典》亦然,并引用土耳其人语“婚姻无戏言,一切皆真实” (史尚宽,2000:191);在日本,第94条规定的心中保留不适用于以当事人的真意为必要的身份行为。心中保留并非当事人主张婚姻无效的理由,即使相对人知道当事人的内心意思与表示内容不一致,也不例外(栗生武夫,2003:57-59)。美国一些法院认为,即使是所谓的“玩笑婚姻”,只要当事人双方在表示上一致而且经过了必备的程序,就可以推定有效。提出宣告该婚姻无效的一方必须出示其视为玩笑的证据。在相关的少数案件中,如果这类婚姻存在问题,并且当事人婚后并未同居,考虑到当事人的同意有瑕疵,并非完全自愿以及当事人还不够成熟,法院通常会宣布该婚姻无效。然而,有些法院认为,如果当事人缔结婚姻时并无关欺诈、胁迫或者精神衰弱的充分证据时,不得宣布该婚姻无效(夏吟兰,1999:46-47)。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未做规定,学说认为,在结婚之时,当事人一方在作出的结婚要约时,即使明知另一方为心中保留(表示与意思不一致)仍为有效,相对人对其所作的结婚承诺,仍可以成立有效的婚姻,以保障家庭与婚姻(黄立,2002:283)。
我国现行法对于心中保留并未规定,《民法典总则草案》仍然对此未作规定。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缔结婚姻(《婚姻法》第8条)的当事人必须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婚姻才得以成立。因此对于所谓的心里保留身份行为的效力可采取大陆法系的通常做法,即无论相对人是否知道另一方为不欲结婚的真意,表意人均不得以心里保留为由主张缔结的婚姻无效,以保障婚姻与家庭。
(二) 因错误缔结的婚姻
错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因误会或不知而发生主观认识与现实不符的情形。从比较法看,在缔结婚姻时发生错误的,该婚姻可撤销。在立法技术上,因错误缔结的婚姻有两类:
一是抽象概括模式。《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第2款第2项规定:“若配偶一方在结婚时不知道事情关系到结婚的,婚姻可以废止。”例如配偶一方以为自己在举行订婚仪式或是在参加演出。对此,学说认为,法律未对其他一些重要的错误没有做出规定令人不解。例如对于伴侣身份(例如女子和未婚夫的孪生兄弟)结婚的认识错误,或者对于伴侣个人品质(例如对方患有精神病或者阳痿)的认识错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者认为此种情形受害人完全可以通过离婚制度获得足够的救济(施瓦布,2010:48)。《瑞士民法典》第124条(因误解而结婚)规定:“下述情形,配偶一方可诉请法官撤销其婚姻:(1)因误解而同意举行仪式的,即其本人或无意举行仪式或无意与婚约另一方举行婚礼;(2)对配偶他方的性质产生误解而结婚,且缺少该性质无法要求其维持婚姻共同生活的。” 《西班牙民法典》第73条第1款第4项:“在缔结之时婚姻缔结者一方误认另一方身份,或其他对于是否同意具有至关重要的个人信息的,婚姻归于无效。”我国澳门地区“民法”第1508条第1款b项规定:“在结婚时,结婚人对另一结婚人之个人身份存有错误;可因欠缺结婚意思而将婚姻撤销。”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97条虽然关于错误的效力未作规定,但理论上认为,当事人本身错误,例如注重当事人之身份者,误甲为乙而与之结婚,应为可撤销(林诚二,2008:370)。在美国家庭法上,如果错误是对于一方对另一方身份的认识,而非其自身品德,或者是关于结婚仪式性质的认识,婚姻可诉请无效(斯丹德利,2004:43)。
二是具体列举式。《意大利民法典》第122条对因错误缔结婚姻的情形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该条第2款规定,在缔结婚姻之时,一方因对对方的人身发生辨认错误,或对其基本情况产生重大误解而同意结婚,该方配偶可以提起婚姻无效之诉。对个人基本情况产生的重大误解,系指鉴于配偶他方的情况,如果真正了解对方就不会做出结婚允诺,包括对以下方面的误解:(1)对夫妻共同生活产生障碍的身体或精神疾病、性变态;(2)因故意犯罪而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除非婚礼举行前恢复自由;判决生效之前不得提起撤销之诉;(3)惯犯或职业罪犯;(4)因卖淫被判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判决生效之前不得提起撤销之诉;(5)对于非配偶导致的妊娠,如果发生在第233条规定的期间以致可能发生丈夫否认亲子关系的情况。《巴西民法典》第1556条规定:“如待婚双方中的一方在作出同意时对他方的身份发生重大错误,婚姻可因为此种意思瑕疵撤销。”第1557条:“如对他方的身份存在以下错误,视为重大错误:(1)所有涉及其身份、荣誉和名誉,一方知道此种错误后,变得无法忍受与被误认的他方共同生活的;(2)不知道他在结婚前所犯的罪行,而此种罪行基于其性质使得夫妻生活变得无法忍受的;(3)一方不知道他方在结婚前的不可治愈的身体缺陷,或严重的可传染或遗传的疾病,它们可能给他方配偶或其后代的健康带来危险的;(4)一方不知道他方在结婚前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而基于其性质,变得无法忍受与被误认的配偶共同生活的。”
此外,《法国民法典》第180条规定:“未经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自由同意而缔结的婚姻,只能由夫妻双方或其中并未自由同意的一方提出攻击(1975年7月11日第75-617号法律,如对人或者对人的根本资格发生错误,另一方配偶得提出婚姻无效之诉)。”虽然立法上规定得比较抽象,但是依据法国的判例,一方对另一方的民事身份、国籍、姓名乃至所属家庭发生错误,在这种错误对其同意结婚起了决定性作用时,可以构成(对结婚表示的)同意瑕疵。法院认定以下情况属于一方对另一方的根本资格发生错误:(1)一方根本无意中断(某一)情人关系,并且仍然保持着这种关系,而另一方对此一无所知,在此情况下与其结婚;(2)无法确定原先的婚姻关系是否仍在继续,或者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离过婚,或者不知道另一方是妓女,或者不知道另一方受到普通法上的有罪判决,或者一方搞错了对方的国籍;(3)不知道另一方没有正常的性关系能力;或者不知道未婚夫精神不健全,或者不知道对方是财产受到监护管理的成年人,或者一方完全没有结成持久婚姻关系的实际意愿(罗结珍,2005:177)。
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与《合同法》(第54条)采用的是重大误解而非意思表示错误术语*通常认为,重大误解既不能包括表示错误(例如写错了或者说错了,不可能构成重大误解),也不能涵盖传达错误,而且其只限于有相对人的错误,不可能包括无相对人的错误情形(如遗嘱等),因此使用“意思表示错误”术语更为妥当。。《民法典总则草案》第125条仍然使用的仍然是“重大误解”一语。《婚姻法》所规定的婚姻可撤销的原因并不包括重大误解或者错误。对于因错误导致的婚姻是否应当作为可撤销婚姻。理论上认识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因同一性认识错误、人身性质认识错误而结婚,均属于可撤销婚姻(王洪,2003:94)。还有学者认为,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发生重大误解主要是指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在相关基本情况上发生认识错误,如结婚对象的认识错误、对方婚姻状况的认识错误、对方精神或身体健康状况的认识错误等。与此情形,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和《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发生认识错误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但是在当事人未撤销以前,其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有效(吴国平,2010:18)。
笔者认为,既然我国《婚姻法》第5条规定,婚姻的缔结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或者干涉,那么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有瑕疵或欠缺的原因就应均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从借鉴比较法上的立法来看,若在缔结婚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身份属性或基本情况产生错误,以至于其真正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就不会达成结婚合意,则该婚姻可撤销。身份属性或基本情况的错误具体包括主体认识错误、身体健康状况认识错误、婚姻状况认识错误及名誉认识错误(如另一方有犯罪、卖淫等经历)等。但对于经济条件、收入状况等发生错误,本质上属于动机错误,基于保护家庭的目的,不允许撤销。
五、 因欺诈、胁迫缔结的婚姻及其效力
(一) 因欺诈而缔结的婚姻
所谓欺诈,是指表意人在意思表示的形成过程中,因相对人或者在相对人知情的情形由第三人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致使表意人的表示行为与真实意思不一致。对于财产行为,法律允许表意人撤销该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立法理由在于:在此种情形,表意人的意思决定自由已经不复存在(拉伦茨,2003:542-543)。但是,对于因欺诈缔结的婚姻是否可以撤销,比较法上规定不一:
第一,肯定立法例。《德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第1314条第2款第3项规定:“配偶一方因受恶意欺诈致使缔结婚姻,而牵涉到配偶该方在知悉实情和正确评价婚姻的性质时就不会缔结婚姻的情事的;欺诈涉及财产关系或系在配偶另一方不知道的情况下由第三人实施的,不适用本项的规定。”在判断恶意欺诈时,适用对第123条发展出来的原则。其中特别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欺诈及其导致的错误必须与婚姻共同生活之间具有关联性。法律中规定的“正确评价婚姻的性质”即为此意。若欺诈的内容和婚姻没有关联,就不会导致婚姻的废止;二是欺诈在另一方配偶知晓的情况下通过第三人完成的,婚姻也可以废止,这里不适用第123条第2款第1句规定的“应当知晓”;三是一方当事人违反义务的隐瞒重要事项也构成恶意欺诈。当事人一方故意向另一方隐瞒有关婚姻的重要情况进而令对方陷于错误的认识,即属于此种性质的欺诈。前者属于消极欺诈,该告知义务限于通常情况下对另一方的结婚决定有重要意义的事项,后者则属于积极欺诈(施瓦布,2010:49)。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因被诈欺或被胁迫而结婚者,可以在发现诈欺或胁迫的事由终止之后六个月内向法院请求撤销(第997条)。结婚撤销之效力,不溯及既往(第998条)。学说认为,婚姻受第三人为诈欺时,应以对方配偶为恶意时,其婚姻始得撤销。在离婚,第三人为诈欺时,以相对人明知其诈欺之事实时,始得撤销,但因诈欺之离婚亦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史尚宽,2000:431)。
第二,否定立法例。法国法系的婚姻立法,规定婚姻仅系错误或胁迫的事由才可以撤销,不特别保护被欺诈的婚姻当事人。法国法谚有云:“在婚姻,任人欺之。”对此,《意大利民法典》(第122条)、《西班牙民法典》(第73条)、《巴西民法典》(第1557-1559条)以及《葡萄牙民法典》(1634-1638条)均不许以欺诈为婚姻撤销的原因。澳门地区“民法”第1508条亦未规定。
但是,仔细考察法国法系的立法例就可以发现:虽然上述国家民法并未规定欺诈属于婚姻可撤销的原因,但由于其规定错误是婚姻可撤销的原因,而且错误的情形比较广泛,欺诈与错误的相同之处又在于,被欺骗的人是基于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因此可以把欺诈视为“引起错误”(caused mistake)的特殊情形。相比欺诈,错误并不要求欺骗的意图,更容易实现。由此导致相同的结果:在德国法上属于因欺诈缔结的可撤销婚姻,例如一方故意隐瞒身体重大疾病,在法国法上因构成错误亦属于可撤销婚姻。
我国《婚姻法》仅规定胁迫为可撤销的原因(第11条),依据反面解释,欺诈不被认为属于婚姻可撤销的事由。*2003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民政部 《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 46 条规定:“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2000年左右,我国学者在讨论修改1980年《婚姻法》时,绝大多数人均主张扩大可撤销婚姻的原因。有学者主张,应当与《民法通则》关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内容相一致(王利明,2001:45);还有学者主张应将胁迫、欺诈、暴力、未达法定婚龄、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规定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夏吟兰等,2001:226)。但是,这些意见最终没有被立法机关所采纳。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婚姻法》第5条强调“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步”,因此,在完善我国现行立法时,应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将欺诈增列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
从我国司法审判实践来看,骗婚的情形比较常见,具体而言:(1)一方当事人欺骗另一方当事人例如一方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身份或姓名、疾病、生理缺陷、恶劣品质(例如犯罪前科或犯罪身份等)、实际年龄、婚史等,并在婚姻登记机关缔结婚姻;(2)一方不仅欺骗另一方当事人,而且欺骗婚姻登记机关并办理登记。例如甲假冒他人或者虚构身份,以骗取乙的财物为目的与乙办理结婚登记,甲随即下落不明(陈文,2012:26);(3)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仅欺骗婚姻登记机构,并未欺骗对方当事人。例如甲(如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的身份证办理结婚登记,其后在一起共同生活(冯砚农,2012:22)。
就上述情形而言,第(1)种情形属于意思表示瑕疵,构成欺诈婚姻,受害人可以请求撤销;第(3)种情形属于结婚登记程序瑕疵。对于其效力,有学者认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应以事实和行为为考察的依据。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否认婚姻关系的存在,形成了婚姻共同生活的事实,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就没有对其进行干预的必要(孙若军,2004:17)。司法实践也有判决肯定的判决。*司法实践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和子女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关系有效。参见王礼仁:《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选择——以诉讼时效法律规范的性质为主线》,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第20页。第(3)种情形不仅属于意思表示瑕疵,而且属于结婚登记程序瑕疵。对于这类婚姻的效力,有学者认为,在缔结婚姻时一方以欺诈的手段(如以张三冒充李四)导致“当事人同一性”错误的,因双方无结婚的合意,受害人可以请求主张婚姻不成立(王礼仁,2010:30)。笔者认为,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的冒名登记婚姻,双方仅形成“名义夫妻”,因缺乏结婚实质要件而应认定婚姻关系不存在。相反,若是仅存在婚姻登记瑕疵,当事人之间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并且建立夫妻共同生活的,应对确认婚姻有效;或者虽未达结婚年龄,但是其后达到结婚年龄的,婚姻由无效转为有效。
(二) 因胁迫而缔结的婚姻
在比较法上,胁迫均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80条以及最高法院第一民事庭(1968年12月17日)判例、《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第2款第4项等。我国《婚姻法》第11条第1句亦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对于胁迫,有学者认为,胁迫包括威胁与强迫,前者是精神胁迫,是指行为人(当事人或者第三人)以未来可能发生的不法损害相恐吓,致使相对人陷入恐惧而作出与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后者是身体胁迫,意指行为人(当事人或者第三人)一方以现时的身体强制,致使相对人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而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王利明,2011:650-651;马俊驹、余延满,2010:196)。还有学者认为,胁迫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胁迫者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威胁的对象通常涉及人格权与财产权;二是胁迫者以直接面临的损害相威胁。如胁迫者针对对方当事人及其亲友施行暴力行为(王利明,2012:611;刘守豹,1994:101-102;胡康生,2009:90-91;杨立新,2013:472)。由此可见,我国学者通常所言的胁迫不仅包括精神胁迫而且包括身体胁迫。
笔者认为,胁迫仅限于精神胁迫,而不包括身体的胁迫。因为在身体受到直接强制而使表意人陷入无法反抗境地的情形,表意人实际上已经成为相对人意志表达的工具(朱庆育,2013:279)。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第1款的规定,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所谓“以……损害为要挟”,足以表明胁迫是使他人陷入恐惧而作出意思表示,并不包括直接的身体强制。
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为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婚姻法司法解释》第10条第2款)。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婚姻法》第11条)。对此,有学者认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只是一种因胁迫而产生的受胁迫者不可能主张其权利的原因,但绝非其全部。从比较法视角出发,应规定其起算点为胁迫终止之日或可免胁迫之日(余延满,2007:206)。
六、 结 论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发现,缔结婚姻时的意思表示瑕疵,例如心中保留、通谋虚伪表示、错误(重大误解)、欺诈以及胁迫等类型,与设立合同、订立遗嘱时的意思表示瑕疵类型相比,并无本质的差异。由于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工具与核心,因此在体系上,从合同法、继承法、婚姻家庭法等等抽象出意思表示及其瑕疵作为共同的“公因式”足以支撑总则编的构建,从而使民法典总则名副其实。而非如学者所言,作为总则编灵魂的法律行为制度仅能适用财产法,我国未来民法典在体系上不宜设置总则,而应如同法国、瑞士、意大利、荷兰等民法典那样设置序编(陈小君,2004:36;余延满,2007:47)。概言之,对于亲属身份行为,民法总则原则可以适用。不过,考虑结婚等亲属身份行为的伦理基础与交易安全的阙如,应当在《民法典总则草案》第三节规定:“结婚、离婚、收养等身份行为适用本法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依据身份行为的性质不予适用的除外。”
由于缔结婚姻时的心中保留、通谋虚伪表示、错误、欺诈、胁迫等通常仅与当事人之间私人利益相关,而与社会公共利益无涉。为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及体现法律婚姻家庭的保护,有瑕疵意思表示通常并不完全否定婚姻的效力,而是使婚姻的效力取决于当事人,即产生有效或可撤销的法律效果。但是,鉴于保护未成年子女与维护夫妻共同生活的原则,缔结婚姻时瑕疵意思表示的效力呈现以下特点:(1)可撤销的自被宣告撤销之日起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就未成年子女而言,应适用离婚的有关规定;(2)在建立夫妻共同生活的特定时间之后(如1年),意思表示瑕疵即得到弥补,则可撤销婚姻转变为有效婚姻。
[1][美]加里·S.贝克尔(1998).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美]加里·S.贝克尔(2015).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3]陈棋炎(1980).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北:台湾三民书局.
[4]陈棋炎(1984).亲属、继承法与民法总则间之疑难问题.载郑玉波主编.民法亲属·继承论文选辑.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5]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2005).亲属法新论.台北:台湾三民书局.
[6]陈文(2012).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的结婚登记应予撤销.人民法院报,2012-07-26.
[7]陈小君(2004).我国民法典:序编还是总则.法学研究,6.
[8][日]大木雅夫(1999).比较法.范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9]冯砚农(2012).山东乳山法院:用姐姐身份证登记,离婚犯了难.齐鲁晚报,2012-02-22.
[10] [德]维尔纳·弗卢梅(2013).法律行为论.迟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1] 胡康生(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
[12] 黄立(2002).民法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 金眉(2015).论通谋虚伪结婚的法律效力.政法论坛,3.
[14] [德]罗尔夫·克尼佩尔(2003).法律与历史.朱岩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5] [德]卡尔·拉伦茨(2003).德国民法通论(下).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6] [日]栗生武夫(2003).婚姻法之近代化.胡长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7] 林诚二(2008).民法总则(下).北京:法律出版社.
[18] 刘守豹(1994).意思表示瑕疵的比较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1).北京:法律出版社.
[19] 罗结珍译(2005).法国民法典(上).北京:法律出版社.
[20] 马俊驹、梅夏英(2004).我国未来民法典中设置财产权总则编的理由和基本构想——兼论对民法总则的检讨.中国法学,4.
[21] 马俊驹、余延满(2010).民法原论.北京:法律出版社.
[22] [美]麦克尼尔(2004).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3] 茅少伟(2013).寻找新民法典:“三思”而后行.中外法学,6.
[24]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2000).德国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
[25]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2014).经济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
[26] 史尚宽(2000).亲属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7] [德]迪特尔·施瓦布(2010).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8] [美]凯特·斯丹德利(2004).家庭法.屈广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9] 苏永钦(2005).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0] 苏永钦(2009).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编纂若干问题探讨.比较法研究,4.
[31] 孙若军(2004).论欺骗登记婚的法律后果.法律适用,10.
[32] 孙宪忠(2014).物权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
[33] 王洪(2003).婚姻家庭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34] 王利明(2001).婚姻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法学,3.
[35] 王利明(2011).合同法研究(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6] 王利明(2012).民法总则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7] 王礼仁(2010).“婚姻登记瑕疵”中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人民司法·应用,11.
[38] 王礼仁(2011).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选择——以诉讼时效法律规范的性质为主线.政治与法律,4.
[39] 王泽鉴(2009a).民法总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0] 王泽鉴(2009b).民法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1] [日]我妻荣(2008).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42] 吴国平(2010).论无效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立法完善.政法学刊,1.
[43] 夏吟兰(1999).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4] 夏吟兰(2001).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新婚姻法解说与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45] 夏吟兰、何俊萍(2011).现代大陆法系亲属法之发展变革.法学论坛,2.
[46] 夏吟兰(2012).婚姻家庭继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7] 谢鸿飞(2013).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
[48] 熊秉元(2014).正义的成本.北京:东方出版社.
[49] 薛军(2006).法律行为理论:影响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重要因素.法商研究,3.
[50] 薛军(2010).“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中国法学,1.
[51] 杨立新(2013).民法总则.北京:法律出版社.
[52] 余延满(2007).亲属法原论.北京:法律出版社.
[53] [日]中川善之助(1961).身份法总则的课题.东京:岩波书店.
[54] 朱庆育(2013).民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5] Hans-Martin Pawlowski(2003).AllgemeinerTeildesBGB.7.Aufl.,358a.
[56] Konrad Zweigert & Hein KoetzAn(1998).IntroductiontoCompa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3.
■作者地址:冉克平,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Email:rankeping@sina.com。
■责任编辑:李媛
◆
On the Defects of Declaration of Intention in Marriage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RanKeping(Hua 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claration of intentions and their defects abstracted from contract law,inheritance law,and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can be applied as the “common factor” for behaviors of entering into a marriage.Some defects could lay in marriage establishment,such as intentional reservation, collusive simulated act, error(gross misunderstanding) and other types of fraud and duress.In a marriage,one party's intentional reservation has no impact on the marriage's legal effect,but the bilateral misrepresentation,error,fraud and duress can make the marriage revocable.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the conjugal relations and protecting minor children,the effectiveness of defective intention in marriage establishment may have slight modifications.
marriage; intention defects; collusive simulated act;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fraud; duress
10.14086/j.cnki.wujss.2016.05.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X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