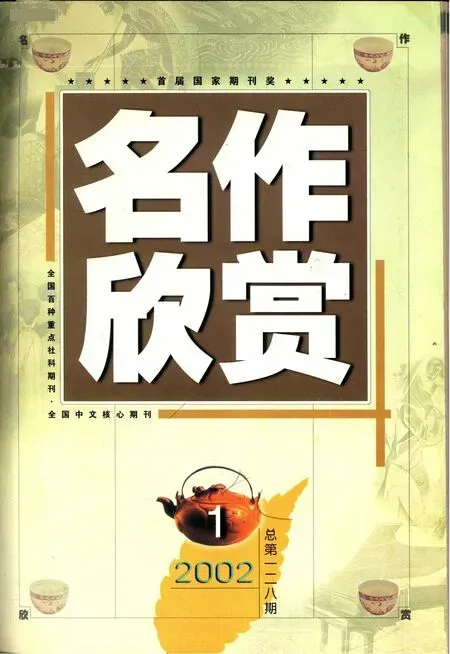鲁迅杂文与师爷笔法——现代散文探胜之一
2016-03-12北京黄开发
北京 黄开发
鲁迅杂文与师爷笔法——现代散文探胜之一
北京 黄开发
摘要:《灯下漫笔》《“京派”和“海派”》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鲁迅杂文。三篇文章都似乎不大“讲理”,换言之,很有些“师爷笔法”。鲁迅成功地把师爷笔法融入现代杂文之中,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汲取师爷文化中有益、有力的优良成分,使之转化为适合自己的匕首和投枪;但毋庸讳言,他也不免受到师爷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
关键词:鲁迅杂文师爷笔法《灯下漫笔》匕首投枪
如今,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对鲁迅杂文越来越陌生了。他们学过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没有鲁迅杂文,大学一二年级上“中国现代文学史”基础课,老师也很少讲到。我给大三学生开“中国现代散文研究”选修课,是要讲的。我选择了鲁迅杂文的三个文本,与学生一起研读,力图让他们突破由众多言说和成见所造成的重围,从而贴近鲁迅杂文。这三个文本分别是《坟·灯下漫笔》《且介亭杂文二集·“京派”和“海派”》《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我得老实承认,这几篇不是精挑细选的结果,它们都曾经引起过我的注意和困惑。高一语文课本里选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我感到好奇而又茫然;本科现代文学选本里有《灯下漫笔》,我对其中关于“两个时代”的概括迷惑不解;以后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小品文论争,重读《“京派”和“海派”》,发现作者的指责与对象的实际情况差别甚大。几篇作品写于不同时期,所攻击对象的类型有别,并且可见鲁迅杂文的主要枪法,还是颇有代表性的。
几篇文章的论证方式很另类,似乎有些不“讲理”,与一般重实证和逻辑的论文迥乎不同,我曾经的困惑也因此而起。
如果说《热风》等集子中的杂文像匕首和投枪的话,收在《坟》里的长篇杂文《灯下漫笔》和《春末闲谈》则如同重磅炸弹。教科书上都说鲁迅的杂文具有高度的形象性、逻辑性等,可我最初试图找出这两篇全面控诉中国历史和文明的篇章的逻辑线索时遇到了困难,它们在论证关键环节上出现了中断或者说跳跃,不像逻辑严密的论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借助于联想和象征来完成的。这种现象在鲁迅杂文中,甚至在整个中国现代杂文中比比皆是。
《灯下漫笔》写于1925年4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论争的产物。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后期,社会动乱,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学衡派”和“甲寅派”向新文化阵营发难。文章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批评,揭露和批判所谓中国历史的本质,提出著名的关于“两个时代”的论断;第二部分由历史批评转向文明批评,进一步找寻造成中国人苟安心理的文化原因。两部分的旨趣最后都指向社会革命。
两部分均从具体的生活现象出发。第一部分写了作者由于国内乱局造成手中的货币贬值,后来终于打折把纸币折扣兑换成现银,于是从恐慌转为欣喜。由此联想到:“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再简要勾连评点历史上的几次治乱,得出一个重大的结论——中国历史的循环不外乎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第二部分开头引用了日本评论家鹤见佑辅《北京的魅力》中的一段话,其中讲述了这个日本人与一个久居北京的白人的晚餐,及他对中国“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的赞美。这本来是一次具体的筵席,而鲁迅把它虚拟为“人肉的筵宴”,把中国比喻为“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指斥中国人对外“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对内根据尊卑秩序“吃人”或“被吃”。文章对“人肉的筵宴”进行了高度的形象化概括:“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最后发出“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厨房”的呼声。这不仅是一个象征,而且是全文基本的构思方式。文章不是逻辑严密的论证,这给结论带来了不确定性。其长处是对于作者来说,可以更自由、更直接地概括社会和文明的现象,对读者来说,可以诉诸人们的情感体验,给读者包含着理性的具象化认识,还可以引起读者开放式的联想;短处则是影响了结论的可信性。当然文中列有作为论据的材料,然而这些材料相对于宏大的思想命题来说是单薄的、较为随意的,难以弥补象征形成的思维跳跃所留下的空隙,难以支撑起结论。
象征性构思源于作者的体验结构。“人肉的筵宴”与关于“两个时代”的论断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理论概括,而是反映出一个启蒙主义者面对本民族长期受奴役的历史而积淀下来的心理体验,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相同的心理体验,引起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警惕,激发青年们进行反抗。
再来看看《“京派”和“海派”》。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创作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其中首先举了上海作家的例子。12月,居住在上海的作家苏汶在《现代》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予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刊出《论“海派”》等文章,由此导致了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论争的高潮到1934年3月底已经告一段落,而在一年之后的1935年5月,鲁迅旧事重提,并借题发挥。1932年,周作人弟子沈启无所编晚明小品选集《近代散文抄》出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上海的出版商纷纷重印晚明小品集,出版文集最多的是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上海杂志公司版)和平襟亚主编的“国学珍本丛书”。左翼作家与言志派作家争夺对晚明小品的阐释权,提出各自的小品文观,双方分别以鲁迅和周作人为代表。鲁迅文章关注了其中的两件小事情:“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而且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二是有些新出刊物,真正的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前者指1935年出版的由施蛰存编选、周作人题签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一书;后者指同年2月创刊的《文饭小品》(康嗣群编辑,施蛰存发行)月刊第三期,首篇是周作人的文章,末篇为施蛰存的文章。鲁迅指出了所谓“京海杂烩”的趋向,其实是向言志派精神导师周作人过招,大有“擒贼擒王”之势。
写于1930年4月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与前两篇不同,直接针对的是个人。革命文学兴起时,梁实秋发表文章,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左翼作家冯乃超指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写《“资本家的走狗”》反问:“《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哪)个资本家,还是所有资本家?”鲁迅发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道:“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不过,梁实秋又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鲁迅说,为了准确起见,还得在“资本家的走狗”前添几个字——“丧家的”。这还不够。梁实秋暗示革命文学作家“到××党去领卢布”(《“资本家的走狗”》),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的句子(《答鲁迅先生》),而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的。鲁迅指其“不过想借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这里的是非姑且不论,单就文章来说,其中论证逻辑是不严密的,因为忽略了别的可能性,而他紧紧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要把论敌死死地钉在一根柱子上。
在白色恐怖当中,梁实秋的说法很容易激起政治高压下左翼作家的敏感和愤怒。鲁迅咬住不放:“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这里把梁实秋“莫须有”式的或然判断变成了全称的肯定判断,然后做出评价:“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按照通常的眼光来说,三篇文章都不大“讲理”,换言之,很有些“师爷笔法”。早在1926年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时,陈源就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称鲁迅是个“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说他“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不仅陈西滢,同时代人中钱杏邨、郁达夫、苏雪林、林语堂、曹聚仁等都指出过鲁迅文章里的师爷气。他们之中有的是鲁迅的论敌,有的是他的朋友。
绍兴在明清之际盛产师爷。师爷是地方州县官署中主官所聘请的幕友——私人顾问,协助主官处理专门的事务。师爷并非由一地专供,只是因为出任此职的绍兴人最多,名气又最大,所以常见把“师爷”与“绍兴”联系起来称呼。师爷的工作专业性很强,如有刑名、钱谷、朱墨等,分管司法、财政、书记诸方面的工作。主理刑事判牍的刑名师爷地位最高,平常所谓绍兴师爷,是以刑名师爷为代表的。绍兴师爷造就了相应的师爷文化。有研究者列出师爷文化的表现:“具体来说,如冷静、清晰、周密、灵活的思维方式,多谋善断、稳重干练、严密苛刻、易怒多疑、睚眦必报的性格,‘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苦嘴,深刻、缜密、犀利、扼要、简括、圆滑、老辣的师爷文风(‘师爷笔法’),翻雨覆雨、深文周纳、歪曲事理、颠倒黑白、锻炼人罪的师爷手腕(‘师爷笔法’之恶劣的一面),自感愧疚、怕遭报应的负罪心态,等等。这当中,既有优良的成分,也有恶劣的成分,是一种优良善恶因素杂糅的文化形态。”①师爷文化表现在文章里就是师爷笔法。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1949)和《师爷笔法》(1950)二文中,都借一篇笔记小说里老幕友讲刀笔秘诀的故事,可见师爷笔法的一斑:诉讼要叫原告胜,就说他如不是真的吃了亏,不会来打官司的;要叫被告胜,便说原告率先告状,可见“健讼”。又如长幼相讼,指责年老的欺侮弱者,则年幼的胜;反过来,指责年幼的不敬老,则年老的胜。周作人还举了自己小时候在书房里学作翻案文章的例子。有一回论汉高祖,他写道:“史称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天资刻薄人也”,后面举出汉高祖杀害功臣的事。先生看后大悦,给了许多圆圈。作者说:“这就是师爷笔法的一例,虽然天下文章究竟并不是在绍兴,总之文风原是一致的,不妨就以此为一派的代表名称。”周作人1923年在《地方与文艺》里点出师爷与浙江文化的关系:“近来三百年的文艺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辞的犀利。”这第二种潮流的特色就与师爷笔法紧密相连。事实上,周氏所举“深刻”派里的章学诚、李慈铭、章太炎等都从事过幕业。从地域文化传统上来说,鲁迅、周作人可以分别视为浙江深刻、飘逸二派的现代传人。其实,兄弟俩文章里都有师爷笔法,其中鲁迅杂文里的师爷气更为突出。
刑名师爷善于根据需要剪裁证据,删改字句,该虚处则虚,该实处则实。师爷的目的是要替主官把事情办好,是有私心的,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是非曲直之分。而鲁迅却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是非显然,爱憎分明。他从师爷笔法中提取合适的武器,加以改进,为我所用。如《灯下漫笔》没有正面攻击,而是采取了曲折的方式。中国历史是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往复,中国文明是不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这都是宏大命题,恐怕无法证伪,也难以证实。所以鲁迅避实就虚,迂回袭击,通过象征形象的想象空间,极大地渲染了对象的惨无人道。本体和象征体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表露出文本强烈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在启蒙主义话语中,“吃人”是对中国文化最大、最严重的控诉。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社会革命的激烈的鼓吹者,鲁迅必须斩钉截铁地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把一些被文化保守主义者用来证明中国文化魅力的证据置换成中国社会和文明必须改革的反证。在《“京派”和“海派”》中,鲁迅执滞于两件小事情,攻击对象的人格。施蛰存在文学观上与周作人相近,与左翼作家对立,这才是鲁迅予以讽刺和打击的真正原因。周作人虽是晚明小品热的始作俑者,但当这个热潮兴起之后,他并没有很热心地参与,而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则是抓住梁实秋论争文章中片言只语的“裂隙”,对证据进行某种改造,并予以扩大。两篇文章也都不是正面进攻,而是侧面袭击,从小事情或文字上打开缺口,力图使对象的人格破产,从而否定他们所代表的某种价值。
绍兴师爷素有“刀笔吏”之称。“刀笔”本来指古代书吏写竹简,写错后用刀削改,所以秦汉时的书吏被称为刀笔吏,后来转义成绍兴师爷书写诉状舞文弄法的专称。绍兴师爷长于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他们可以根据需要润饰或修改判词,“出重出轻”,有时仅仅置换一两个字,或者稍稍颠倒一下语序,就能置人于死地,或者使有罪之人免于刑罚。《“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拈出一个“乏”字,陷对手于“死地”,如老吏断狱,一语定谳,这个精心提炼出来的形容词显示出师爷笔法寸铁杀人的绝技。师爷笔法的刀笔功夫与文学的形象表现相结合,产生了鲁迅笔下生动、深刻、辛辣的杂文形象。杂文形象是师爷笔法的一个突出表现,通过漫画式的三笔两笔,勾勒出打击对象的典型特征,并通过具体的论证将其定格。形象化的功能是污名化,污名化用俗语来说就是骂人,喜骂正是师爷笔法的突出特点。“人肉的筵宴”是象征型的杂文形象,辛辣而又犀利,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很容易激起对中国传统文明强烈的憎恶。《“京派”和“海派”》讲述了法国作家法郎士长篇小说《泰绮思》里的故事。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立志要把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感化出家。他虽然成功了,却为这个女人神魂颠倒,内心失去了平静。他最终跑到了泰绮思那里去表白,但此时泰绮思已经快死了,说自己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紧接着这个故事之后,鲁迅写道:“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于是——团圆了。”这等于是为所谓“京海合流”画了一幅漫画。鲁迅这样写“资本家的走狗”:“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鲁迅笔下的杂文形象丰富多样,充分体现了“深刻、缜密、犀利、扼要、简括、圆滑、老辣的师爷文风”。
周作人自称文章里有师爷笔法,然而后来他对自己文章里流布的师爷笔法进行了反思。他没有把1925、1926年前后攻击个人的杂文收入文集,广告过的《真谈虎集》最终有目无书。又在《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中,说其“写的最不行的是那些打架的文章”,“都容易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他在《关于绍兴师爷》中指出刑名师爷的文化传统,说刑名师爷既是不第秀才改业的司法佐治员,这便规定了他的性格,“可以说是申韩业的儒生”,“主要的特质是受过国学的熏陶,会得做八股的……申韩的法家成分实在只是附加的一点……这所谓八股,当然不是正式的时文,乃是指自唐宋,以至清朝千余年来养成的应制的本领,不论律师经义以及策论,都能依照题目,说得圆到,那一套舞文弄墨的手段”。结尾处又说:“绍兴师爷现已不复开馆授徒,可是他的作风还是一时不会断绝,则是由于国粹之流泽孔长也。”这里对师爷笔法进行了文化批判,其观点是深刻的。说这话不久,时代发生巨变,他在一年以后发表《师爷笔法》中有些改口:“师爷笔法在中国文章里存在着,难以尽去,只要转而为人民服务,成为匕首似的文章,也是很有用的一种东西吧。”这是一段很纠结的文字,语含讥讽,但似乎也不是完全言不由衷。
鲁迅成功地把师爷笔法融入现代杂文之中,并使其成为灵魂式的东西。他能够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汲取师爷文化中有益、有力的优良成分,使之转化为适合自己的匕首和投枪;毋庸讳言,他也不免受到师爷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鲁迅在《坟》的后记里自剖,说自己背负着摆脱不开的“古老的鬼魂”,中过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韩非子是法家代表人物,法家所体现出的峻急、苛刻自然会表露在其杂文的字句、体格上。这消极影响不仅体现在鲁迅一人身上,也同样潜藏在陈源、梁实秋、周作人等人那里。
由上述的例证可见,杂文是一种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文体,不是四平八稳的学术论文,亦非和颜悦色的小品文。从接受的角度来看,与鲁迅杂文产生共鸣更多靠的是在相同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下相同或相近的社会体验和现实态度。只有尖锐地体验到现实之痛,不满并且试图反抗,才更有可能深刻认识鲁迅杂文的价值。而社会体验和现实态度不同的读者,抑或不同时代和文化环境中的读者很容易产生隔膜感,甚至可能会对鲁迅杂文做出否定的评价。时过境迁,今天读者不再与杂文所论对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则会根据当下的文化批评标准要求文章“讲理”,有可能对师爷笔法中的一些表现不满。鲁迅以后的杂文家多流于政治争斗,一味叫嚣,好勇斗狠,内容空疏,惹人生厌。在多元文化和思想并存的今天,要重振杂文,就需要稳健的文化心态和“费厄泼赖”精神,祛除现代杂文传统里的不良成分,树立杂文良好的社会声誉。
周作人晚年在致鲍耀明的信中谈及他的散文理想:“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我自己却不会做),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②杂文,小品文(随笔),再加上记叙抒情散文,这三者可谓现代汉语散文的三大正规军。杂文是文学对现实最敏感的神经,是战斗文学的代表,而鲁迅杂文将永远是中国杂文的武库。
①李乔:《烈日秋霜——鲁迅与绍兴师爷》,收入朱志勇、李永鑫编:《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页。
②黄开发编:《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作者: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周作人、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文学思潮等。
编辑:赵斌mzxszb@126.com
古典丛谈Class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