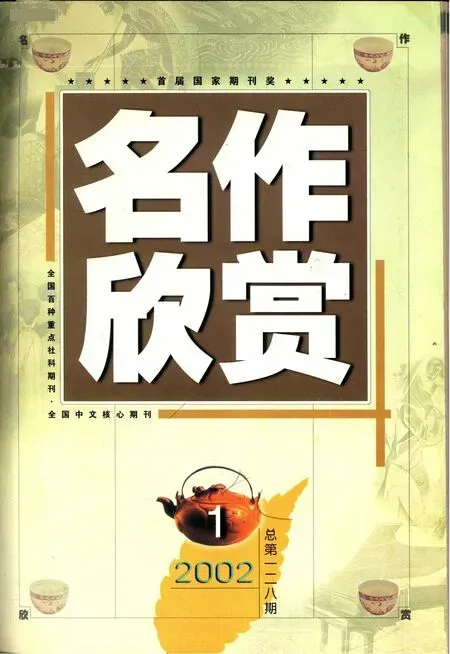永远的心灵的朋友
2016-03-12北京杨匡汉
北京 杨匡汉
永远的心灵的朋友
北京 杨匡汉
摘要:月亮是宇宙天体的物象,是地球上的人们视通万里的心象,更是诗人作家笔端常见的文化母题和审美创构的意象。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从“古月”到“今月”,月始终都是艺术家们灵魂的提灯,不仅在创造性转换中做出努力,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鉴赏和想象的空间。
关键词:月亮心灵提灯审美创构
站在我们地球上,对那个地球一侧的月球,不知多少人有过梦幻般的向往和猜想。
美国第一位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其实只在月球上留下过大大的脚印,所拍摄的月球表面,也是坑坑洼洼,似无多少佳景可言。
据2012年10月31日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称,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研究小组分析推测,大约三十九亿年前,有一颗直径超过三百公里的小行星撞击月球,形成了巨型撞击痕迹。这次撞击产生的能量造成了月球表面大范围熔解,此后又由于其他体积较小的小行星撞击等因素,月形变得更为复杂,加大了准确判断撞击痕迹的难度。报道还称,面向地球一侧的月球表面称为“海”,月球表面平坦且黑暗区域较多;另一侧海拔较高且月壳较厚。日本国立天文台教授渡部润一就此次调查结果表示:“(这次的研究)解释了月球下面和背面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们也正一步步地走近月球历史谜团的真相。”
美国人在探究月球谜团上似乎有更多的妙想。由美国航空航天局前工程师迈克尔·莱创办的电梯港集团公司2012年宣称,该公司不但可建一座地球太空电梯,而且可以建一座月球太空电梯。由于月球引力更小,在月球上建太空电梯比在地球上建更容易。太空电梯虽然造价昂贵,但不需要动用大量燃料,因此建成之后的运行费用比运载火箭低两个量级,且可像高速公路一样二十四小时运转,将航天器、有关货物和旅游者等带到太空去。建成后的月球太空电梯还可以与地球太空电梯连成一体,将来有一天,人类只须经过几次换乘,就可以乘坐太空电梯从地球抵达月球。
望月、登月、探月,魂牵梦萦着那么多天文学家、科学家、航天员,标志着人类科技的发展与进步。这一切都属于工具理性的思维、物象性的科学想象。然而,这个世界上既有哥白尼和爱因斯坦的天空,也有梵高和毕加索的天空;既有阿姆斯特朗接触到的月亮,也有从古到今文人们仰望着的月亮。可以说,前者是物理的,后者是审美的;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感性的。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往往在或新月或明月或皓月或残月当空的时分,灵魂深处那些情思会自然涌动,化作诗,形成文,留下了许多美妙的篇章,从古典到当代,不断地在传承中流转。古今中外,不少作家诗人都以“月亮”为中心,对这一经典性的母题,做出了回响。
不妨先看外国诗歌。在传世之作中,那些专以月亮命名的篇什并不多见。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1798—1837)因自身长期患病,思想上充满矛盾与痛苦,所以仰望上苍时,只是吟出:“哦,我可爱的月亮/不过对痛苦的往事/一一追忆,细细思量/对我也能帮不少忙。”(《致月亮》)那位著有《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英国小说家劳伦斯(1885—1930),曾以一首《新升的月亮》爆得诗名,他看到的是“金色的月亮在和黑暗面对面地密谈”,诗人突然“闯进月亮和夜晚的秘密小天地/原来他俩正在相爱/她仰望着夜晚/他甜蜜地亲吻着她/于是世界容光焕发”。是真情还是偷情?我们无法考证,但把月亮和情欲联寓起来,不失为人化自然景象的奇妙构想。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雷尼埃(1864—1936)的作品,大多吟咏美的风物、梦的人生和爱的情趣,那首《金黄的月亮》,则有一种明净、典雅、细腻的纯美:“漫长的一天以金黄月亮结束/月儿款款地升在白杨树中央/这时它薰香的空气中弥漫着/濡湿的灯心草间沉睡的水香。”在炎炎烈日下艰苦劳作了一天,结束的帷幕,是在白杨树梢升起并变圆的金黄月亮!那温柔,那委婉,那朦胧的意境,跃然于纸上。至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以“新月”命名的《新月集》,也并非都写月亮,而是潜入内心,以霏霏飘洒的爱的甘霖,浸透凡尘、天国和生灵,希望生活充满琼浆。
相对而言,中国诗歌可以说是对“月亮”情有独钟。那“想象的月亮”、那“审美的月亮”,从古到今,汗牛充栋。诗中的“中国月亮”,比“外国月亮”不仅出现得早,而且更圆更多。
“嫦娥奔月”的神话,“月宫桂树”的传说,寄托了中国人对月亮的奇思妙想和脉脉深情。从《诗经》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月出》),到《楚辞》的“印明月而不熟息兮,步列星而极昭”(《九辩》);从唐诗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到宋词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林林总总,涉月之诗不计其数,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国人亘古未变的对美的期待。即以李白为例,《李太白全集》中,据有人统计,仅以“月”为题或涉及月亮的诗就达二百五十余首(外国诗人中找不出来这么多)。这位“诗仙”,赋予月亮以自己的生命。他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他是盼望“月光长照金樽里”,竟然一蹾手中酒杯放言:“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问”本身是一种对话的姿态,到了李白这里,成了“把酒问”,主动出击之“问”,尽情浪漫之“问”。古典诗词中由“望月”到“问月”,之后又有“咏月”“拜月”“步月”“玩月”等大胆之举。而李白的那个“问”,更被三百年后的苏轼接手过来,转化为具体的、中秋的、情理交融的月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水调歌头》)这首词是苏轼在山东高密的“超然台”上望月思弟,饮酒达旦,飘然若仙,一挥而就的。这个“天上宫阙”,这个可望不可即的月亮,尽管令人“高处不胜寒”,却照亮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悲欢离合和所有的年华。
今人不见古时月,然而,今月曾经照古人。“古月”“今月”或许有别,但月亮运行如常,并且始终成为作家诗人们心中的诗意之灯,时时刻刻让天心回到当下。且不说当下那些诸如《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流行歌曲,即便是当代小说家,也把“月亮”视为灵魂的提灯而倾心,而饱满,而敏感,而有情有义,而有了在苦难中仍然热爱生活的信念和梦想。以《暗算》等小说鸣世的作家麦家就有如此感悟:
文学不是太阳光,可以让万物生长,给万物带来实际的利益,文学有点像月光。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月光,对我们现实世界的万物生长,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是没有损害的。世间大部分东西是不需要月光的,无月光照样可以生长。但是如果没有月亮,我们的情感世界,我们的心灵可能至今都还是一片黑暗。月亮是照亮我们心灵的阳光。人间很多美好的情感、梦都是在月光之下产生的。对我们来说,对一个诗人来说,对一个正在谈情说爱的人来说,月光就是他的亲人,见了月光,他的感情会莫名地变得丰满,情绪会特别饱满。我们在太阳光下劳作,可能汗流浃背,可能站得高看得远,但有一些很内心的东西因为被太阳一照就失去了,或者躲起来了。月亮升起来时,我们很多美好的梦想、情感、思念都苏醒了。①
心灵有了月光的浸淫,一切美好的东西就会一一激活起来,在当代人这里,也就有了对这一“古典”的“月光”的投影。不过,回到“古典”不是机械地复归“原点”。大凡聪敏的当代作家和诗人,选择“返本”而求“开新”,护持古典而又创造性地重建,注重传统的“月亮”又注重新鲜的“月亮”。我国台湾诗人洛夫,就以“解构”的方式,改写了李白的《月下独酌》。
李白原作 :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洛夫解构新作:
独酌是对酒的一种傲慢
可是,除了不解饮的月亮
我到哪里去找酒友?
天上也月,地上也月
花间也月,窗前也月
壶里也月,杯中也月
我穿上月光的袍子
月亮借去了我全身的清凉
举杯一仰而下
一个孤寒的饮者月下起舞
下酒物是壁上零乱的影子
他喘息,他冒汗,他脚步踉跄
他把酒壶摇啊摇
摇出了一个寂寞的长安
摇啊摇,摇出了一个醉汉
一卷熠熠生辉的盛唐②
在这一古典的回响中,作为当代人,洛夫此作的意义在于:解构了“独酌”的字义,指明“是对酒的一种傲慢”;阐释了“月徘徊”,并丰富到天上、花间、窗前、壶里、杯中统统有月,为“相期邈云汉”立体地作证;改造了“举杯”,变成了“摇”,摇出了一个寂寞的长安,摇出了一卷生辉的盛唐。于是,洛夫实现了古典情结与当代生活的自由切换。也就是说,既切合了复古心绪,又彰显了自然理念;既诗化了文化价值,又增添了今人襟怀。
从古典延伸而来的感动,到了当代作家莫言的笔下,既延续了传统的平朴优雅的情愫,又加入了更多现代的激荡表达,亦实亦虚、亦真亦幻地绽放着奇异的光彩。他有一篇题为《会唱歌的墙》的散文,写的是故乡高密的风物。苏东坡望明月、问青天的《水调歌头》写于高密,那“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生命浩叹,也发乎高密。作为高密之子的莫言,自然会像苏轼那样望明月,但更多的是看月光下的乡土:
看不到一点点水面,只能看到层层叠叠地在月亮中蠕动鸣叫的青蛙和青蛙们腮边那些白色的气囊。月亮和青蛙们混在一起,声音原本就是一体——自然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天安门集会,青蛙在池塘里开会。
莫言接着写道:“月亮明晃晃地高挂在天中,池塘中水平如镜。”但就在这“仿佛梦呓”的情景中,苏轼词里“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意境,酿成又一则发生在高密月光下神奇的故事:
(99岁高寿的)门老头儿到处收集酒瓶子……他用废旧的酒瓶子垒了一道把高密东北乡和外界分割开来的墙……这道墙是由几十万只酒瓶子砌成,瓶口一律向着北。只要是刮起北风,几十万只酒瓶子就会发出声音各异的呼啸,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成了亘古未有的音乐。在北风呼啸的夜晚,我们躺在被窝里,听着来自东南方向变幻莫测、五彩缤纷、五味杂陈的声音,眼睛里往往饱含着泪水,心中常怀着对祖先的崇拜、对大自然的敬畏、对未来的憧憬、对神的感谢。
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但不要忘记这道墙发出的声音。因为它是大自然的声音,是鬼与神的合唱。③
当然,这道会唱歌的墙,如今在突飞猛进的经济建设中倒下了。但那千万只破碎的玻璃瓶子,在月光下,在雨水中,依然闪烁清冷的光芒,依然会继续歌唱,如同古典诗句“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谢灵运:《夜宿石门》)一样。月光、蛙声、酒瓶和人、物、自然交汇在一起,真真切切地在人世间起舞,无论高唱或低吟,都会渗透到乡民的灵魂里,并且世代相传。
如果说莫言写月光是从叙事中见出一种境界,那么,北京大学教授、富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谢冕,则把月亮视为一种意象。他认为:“就月亮这一意象而言,它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是充满诗意的,是永远鲜活而有灵性的。”④
2003年,谢冕和一帮学界朋友相聚温州。时值阴历十六,月儿分外姣好,诗界同好欢聚于堪称“诗之岛”、中国山水诗发源地的江心屿,望月色与灯火辉映,闻吟声共涛声唱和,对月抒怀,人天共乐。谢冕参与了雅调共弹,效当年兰亭胜会,洵足媲美,发动同行者都来写一组《温州的月光》,还特意撰有《同题散文〈温州的月光〉前记》,以明心志。
温州月光,因得人文融合之妙趣,融入了谢冕襟怀。他情思荡漾,竟对这个题目一写再写,先后写出四篇《温州的月光》。不过,谢冕没有那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而是以意象和具象相结合的方式,于细微处落笔月色,眉英英而露爽。在《温州的月光》之三中写的是:
月正中天。那光华寂无声地掠过谢家池塘,照着池塘上的春草,春草上的流萤。那春草和流萤也都在月色的迷蒙中发出幽幽的光。
这分明是从古典山水诗大家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引发出来的。而在“之四”一文中他又写道:
疏星如萤,月色如银,那山野的草香和虫鸣与明澈的月色融成一片,此夜温州的月光里充盈着芳香的气息和金属的颤音。次日拂晓起来,发 现昨夜的月明竟缤纷成了草尖的晶莹,还有楠溪江上星星点点的波粼。
此一工笔画的描写,如银月色,缤纷成了草尖的晶莹露珠,流转成了江上的波光粼粼,具象的巧妙变换,事实上也和谢灵运当年“浥露馥芳荪”“空水共澄鲜”的咏怀遥相呼应,只是更细腻、更具体、更灵动罢了,使月光与当代人的生活、情感联系起来。
通过对上述以“月亮”为母题的诗文的观察,我们不难看到,其一,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月亮”是人类,更是中国人永远的心灵朋友,是自由和爱的诺亚方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二,古典的“月亮”高高在上,迢迢却又不遥远,我们一直仰望,怀有敬畏之心;当代文学中的“月亮”就在身边,可以有一种亲近的感受,两者之间有一种高下、远近的传承关系。其三,作为对古典的回响,一方面要使“月亮”所隐含的情思暗流永续下去,另一方面要不断有新鲜的元素加入进来,鼓励原创、激活原创,从古典美走向现代美,真正达至“月涌大江流”的繁胜之地。
①麦家:《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文艺报》2012年7月13日。
②洛夫:《唐诗解构》,《香港文学》2012年7月号。
③莫言:《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④谢冕:《那些遥远的星星——在伊斯坦布尔的发言》,《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6日。
作者:杨匡汉,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编辑:张勇耀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