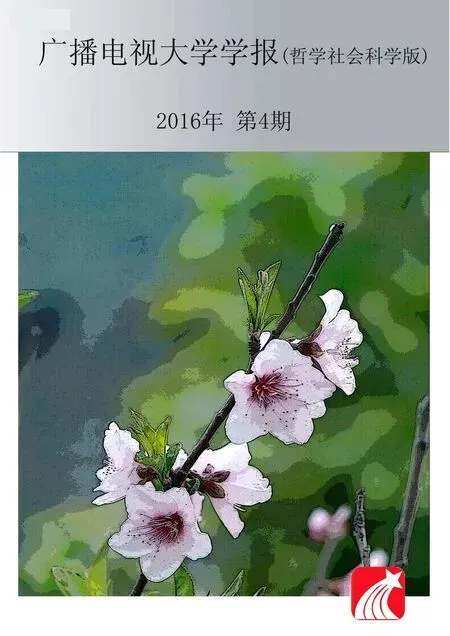政治真理与农民心态的联想
——兼论《末代紧皮手》的土改书写
2016-03-10赵怡
赵 怡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政治真理与农民心态的联想
——兼论《末代紧皮手》的土改书写
赵 怡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中,《末代紧皮手》是第一部集中专门以土地为线索,更直接以“活人土地爷”(余土地)为主人公的小说。作者李学辉以巴子营独有的“紧皮”这一传奇而原始的农事活动为点睛线索,将人物命脉、社会变迁、国家政策走向等一系列重要元素全都挂在深沉的“土地信仰”这根线上探究巴子营乡民的历史命运。“土地改革”是无法绕开且最值得着眼的历史性和政治性话题,小说以土地改革切入展开对政治真理与农民心态的联想,书写了西北边塞乡民在适应国家大激荡时所产生的阵痛与坎坷。小说中土改现象背后涵盖的深远历史意义与影响,值得研究与反思。
《末代紧皮手》;土地改革;政治心理;农民心态
人多地少,土地问题如何解决一直是考验中国历朝历代执政者的攸关性问题。长久以来,不断积累的人地矛盾常常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都曾试图将权力触角伸到基层乡村社会,然而,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到来,之前那些种种全力尝试均未到达预期的结果。此前,国家权力的扩张破坏了传统文化系统,造成基层精英流失、基层组织恶化的“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现象。而二十世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从地主所有向小农所有的重要土地所有制度的转变,重构了国家与底层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晚清民国以降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历程获得实质性进展。1950年代后中国农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1]也是如此。李学辉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对此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描述,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巴子营及其土地信仰
土地是人类生存、延续、发展的根基。蒙昧状态时,人类对土地就寄望了深沉的感情,怀着敬畏感与神圣感对土地顶礼膜拜。《白虎通·社稷》中“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这明确表明了我国的土地崇拜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膜拜上升为国家礼典,开始从上到下系统地祭祀和信仰,由此土地神应运而生。这些一个个形形色色的掌握着万物生死的神灵,受到国家的祭拜与万众的崇奉,相关的灵验传说和故事也大量衍生。古往今来的笔记小说等各类文献中,关于民间土地神及其演变的记载卷帙浩繁。现当代乡土小说里触及土地信仰、土地崇拜、土地神的篇章众多,但是专门以“土地神”为主人公的小说始于《末代紧皮手》。2010年,西部乡土小说作家李学辉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以诡谲奇特的视角描写了一个真人化身的“土地神”——余土地其人一生的命运沉浮,在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紧皮”是一种巴子营传承千年的独有农业保墒措施,“保墒”就是“保水”。在古代文献中也称为“务泽”,即“经营水分”,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来满足作物蒸腾。在西北特有的气候环境中,冬季寒冷,降水稀少,如何保持水分以维系农作物的生长,是西北人生存的头等大事。古人在《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齐民要术》也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辍”;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这些都是对松土保墒功能的生动总结。
小说《末代紧皮手》中的“紧皮手”就通过“紧皮”这一极具地域性的传统保墒法来完成巴子营土地的保墒大事。“紧皮手”被看成巴子营当地的“活人土地爷”,全因他紧皮的完成好坏直接关系到乡民一年的收成,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技术下,“紧皮手”的地位之高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对历代“紧皮手”的选拔也是极其苛刻和残酷的,可一旦被选中,就成为活人神,享有巴子营最尊贵的地位。尊贵和价值是成正比的,紧皮手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所不可想象的,一生不能近女色、不能洗澡(只能在雨天和雪天,洗天澡)。
《末代紧皮手》是一部浸染着深刻历史悲剧意识的作品,“末代”一词阐述了贯穿小说始终的明确悲剧性。人性与宗法的交锋、道德与欲望的纠葛在作家笔下都化为一个个真善美的毁灭却依旧延续而无解。小说典型地体现了李学辉的个人气质——苍凉、孤寂、凝重、幽默。这部孕育于西部荒漠的重量级乡土小说以巴子营独有的“紧皮”这一传奇而原始的农事活动为点睛线索,以独有的“活人土地爷”(余土地)为主人公,叙述了解放前后凉州巴子营里乡民的命运沉浮,反映了西北边塞在适应国家大激荡时期中自身命运走向所产生的阵痛与坎坷。
“土地改革”是无法绕开且最值得着眼的历史性和政治性话题。本文试图从《末代紧皮手》这一具体的文本中探讨以下问题:西北巴子营大地上的土地改革的首要目的到底是经济层面上生产关系的变革,还是政治目的上国家政权与农村关系的重建?当极具传统规训思想的巴子营乡民出现使人惊骇的过激行为时,到底是因为仇视地主何三还是盲目愚昧,为什么巴子营的乡民会轻易被鼓动去毁坏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传统民俗,从而带来对巴子营历来最受尊敬的紧皮手这一神圣化身的亵渎和侮辱,以致消失?小说中描写的种种悖论和悲剧,对当今社会有着怎样的启示?
二、巴子营的“土改”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时,同样也指出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所有问题当作革命的谋略。美国学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在中国,土地改革是一项无可比拟的革命的和军事的策略”。他高度赞叹了中国当时的土地改革政策。日本学者田中恭子在论文《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中写道,中共土地政策激进化的直接因素是军事性的。胡素珊(Suzanne Pepper)在《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写道,“土改究其实质也是一项共产党为其夺取政权这一直接利益而服务的政策。这也是共产党人自己的看法。土地革命摧毁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垄断,这是创建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必要步骤”。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这一小说文本中土改现象背后涵盖的深远历史意义与影响,非常值得我们研究与反思。
1.土改的第一步:划阶级
土地改革政策的基本核心是阶级矛盾,“划阶级”则是第一步。土改重新塑造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关系,阶级关系顶替血缘、地缘关系,化作全新的农村品级秩序。然而,涉及敌我阵营对立这样性命攸关的问题,在李学辉小说《末代紧皮手》的书写中,又是如此荒唐而肆意。在烈士遗孀王秋艳这里,即使正常按照田亩、家产、财富的标准,理应划分成“贫农”的王秋艳,却要依靠姿色的撩拨得到认可。在袁皮鞋的政权和男权的畸形社会面前,勉强得到这个被承认的“贫农”成分。书中这样写到:
“还是个当过兵的男人。”王秋艳抢过针,拉过袁主任的手,轻轻在扎刺的部位揉了揉,细细的针尖泥鳅般扭着身子,那根刺便笑着顺针尖跑了出来。
袁主任感觉舒服了很多。……袁主任不再发表意见,众人听到肚子里叽里咕噜的叫声,就一致响应:“就贫农,就贫农!”[2]P80
王秋艳是小说《末代紧皮手》里出了名的勤劳能干的女子,是巴子营一道靓丽的景象。况且,按道理说,她自身的美貌和干练,加上拥有革命烈士遗孀的身份,她的丈夫何立民因为革命壮烈牺牲,这些本应理所当然使她更加受到乡民的保护和尊敬。可是,当大时代的潮流席卷到巴子营时,女性在政治层面上的失语和性别意识上的屈从,导致她不得不放弃自身正当存在的权利和话语,在巴子营艰难地探索属于她的生活可能。
如果说王秋艳依靠姿色换取了本应属于自己的“贫农”身份,那么,何菊花因为原生家庭,天经地义被归为“地主”。这样本质上极为荒唐又表面上看似合理的思维模式,让人万般愤慨和无奈:
“地主,有啥审核的。”
“她家不是地主,巴子营就没地主了。”
“可何三已死了,她家的房子、地、牲畜都分完了,定地主合适吗?”“什么觉悟?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下的娃娃会打洞。地主的姑娘不是地主,难道你家是地主。”[2]P8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下的娃娃会打洞” 这样丝毫没有理智分析的儿戏判断,轻而易举地将何菊花划入被打倒的敌人阵营。在中国庞大的国土范围内,土地改革政令发布后,各个地区的情况和具体划分情况极其复杂和困难。可是,面对身份复杂难辨的何菊花时,巴子营的底层当权者不由分说地一刀切。我们暂且不谈她的父亲何三是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资助红军的,是如何在平时的生活中厚待巴子营乡民的,是一个怎样睿智和慈爱的老人,我们就只单单谈何菊花本人。她和王秋艳两个人一道是巴子营乡民心中最美好的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温柔内敛,一个干练灵巧。何菊花从小在父亲的培养下,几乎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代表,可命运却从不优待她。革命时期,那时父亲何三还在世,她就悲惨地遭到国民党军官的凌辱,后来在新政权中又一次次遭到鞭挞。最终,为了保护龙鞭保护余土地,何菊花寒冬腊月赤裸着身子,抱着龙鞭狂逃,躲避那些喊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口号试图抢夺龙鞭的民兵,最终跌入地道,悲壮死去。
接下来,看看紧皮手余土地的情况。按照李学辉大悲剧的创作倾向,毫不例外地,主人公余土地同样被打入“地主”阵营。由于乡民内心仍然遗留的对土地和土地神的莫名敬畏感,使得余土地(活人土地神)被划为“地主”的过程略显艰难和曲折,小说中分为两部分:
乱扯了半天,实在没法给余土地定成分,袁主任倒没了主意。
“抓阄。”……袁主任挥挥手:“回家去,给你们一个晚上考虑,明天再不表态,每家罚一斗麦子。”
出了门,有人嘀咕:“地的皮紧不好,就不是一斗麦子的事了。”[2]P83
“抓阄”这一情节的出现,完全显露出作者高超的想象力和作品的反讽意味,不同于王秋艳和何菊花,读者或许会在小说中袁皮鞋推出阶级成分划分概念时,不免好奇对于“土地神”要如何处理?谁敢定“土地神”的成分?作者巧妙地让反派袁皮鞋想出“抓阄”这个方法,看上去随意但完全不用任何人负责的方式,企图将巴子营的乡民从害怕得罪神灵的强大负罪感中解脱出来。作为底层政权代表,袁皮鞋提议是多么狡诈阴险又精妙绝伦!不过,出于对土地千百年来的敬畏感,巴子营乡民心中对土地的深沉信仰,紧皮手信仰仍未完全消失。“罚一斗麦子是小事,惹了活土地爷是大事”。第一次动员群众失败后,袁皮鞋再次召集群众给余土地划分成分:
“找五个碗来,要一模一样的,再给我提来半袋黄豆。”……“记住,这五个碗底里分别标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既然你们定不下余土地的成分,今天就让你们投豆子表决。”
这也新鲜。人们把豆子捏在手心里,掂量一番,将豆子朝各自想丢的碗里丢去。豆子在碗里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们的心一揪一揪。投完豆子后,袁主任一个碗一个碗数完豆子,然后扣过碗来,谁也认为绝对不是“地主”的那个碗底,赫然贴着“地主”二字。袁主任笑笑:“你们跟我玩什么心眼?这余土地受何三和大户人家供养几年,他不是地主谁是地主。”……
“巴子营复查成分的工作已圆满结束。”而后,骑了他的那辆破自行车,返回凉州城。[2]P84
第一次“抓阄”动员未果后,袁皮鞋改变了方式,绞尽脑汁计划出另一个更加阴险、逼人就范的招数——“投豆子”。五个碗底里分别标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投豆子的时候,乡民们谁也看不见到底投的碗底写了什么字,“他们的心一揪一揪”。当谁都认为绝对不可能是“地主”的那个碗扣过来后,赫然“地主”二字,猛烈地敲击着每个人的心。可是袁皮鞋却显得早已洞察,他一句“你们跟我玩什么心眼?这余土地受何三和大户人家供养几年,他不是地主谁是地主”早已显示了阴谋得逞的快意。在袁皮鞋的心中,余土地早已被划为地主,他只是在费尽脑力地想如何实施、如何让乡民们服气。“余土地被定为地主,使巴子营人的心里有了不舒服,好像一根绳子挽了疙瘩又被铁丝箍住”,千百年来百姓对土地无法割舍的复杂情愫,在巴子营来说就是对紧皮手余土地的情愫,他们依赖、小心、敬畏余土地,最重要的是即使抛开“紧皮手”这个特殊的身份,余土地作为一个“人”来说,德行也是巴子营里数一数二的。对于他的屡次受难,善良的村民们都是不舍与不解的。
当完成“划阶级”这第一步后,小说中巴子营的乡民则彻底被分为敌我两个截然对抗的阵营。从此,阶级身份和阶级冲突替代了巴子营传统的各种身份和冲突,先前纷繁的社会关系被整合为唯一的阶级意识。土改造成了二元对立的尖锐模式,没有模糊地带,没有缓冲力量代表,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后来,这样的划分将传统巴子营中各色人物的命运的走向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分裂与对立,产生了难以估量和改变的悲惨结果。
2.土改的第二步:着魔的“群众心态”
在《末代紧皮手》中,余土地用来紧皮的工具就是龙鞭——“不到紧皮之日,龙鞭在上土地庙供着,非等到请鞭之日不可”挪用,这个象征着保佑巴子营百姓生存大计的龙鞭,一直是这个民间小村子的传统神物。它是巴子营百姓祈祷土地收成的命根子,热爱生命和土地的善良地主何三在沉塘自尽之前吩咐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保护龙鞭:
“跪下。”他喝令余土地。
余土地虔恭地将龙鞭放到了供桌上,跪了下来。陈二打开了箱子,抱起鞭子想放到里面。
何三拍住了箱盖,接过了龙鞭,返身来到龙窝前。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油布,将鞭子包起来,沉入了龙窝。
“你们记住,谁若泄露了秘密,会遭天雷惩罚的。余土地,只要你在世一天,就要看护好这条鞭子,不管地是谁的,只要属于巴子营的,你每年都必须紧皮。”
余土地深深地点了点头。[2]P59-60
但是,当后来轰轰烈烈的文革来临之时,传统的祭祀土地的仪式就首当其冲地成了破除四旧的靶子,从而,仪式里最大的帮凶——“龙鞭”顺理成章地成了首先要消灭的对象。何菊花为了完成父亲临死也一再嘱咐的遗愿,那奋不顾身的赴死场景,极其震撼,让人捶胸顿足!
“枕头里是什么?”
“不知道,我们一抖枕头,她就发了疯。”
“袁书记,何菊花脱了衣服。”
“袁书记,何菊花脱了裤子。”
“她就是脱了皮,也要追。”
偌大的田野上,一个精赤赤的女人抱着一个枕头在飞奔,后面跟着一大群男人,边追边叫。……她转身跳下了地道……一切都凝固了。一道白光消失后,追赶的男人们的气一下歇了,他们都木木地站立着,回味着刚才看到的情形。……余土地到洞底,见何菊花躺在一边,几只老鼠忙着啃食何菊花的脑浆和血液。[2]P148-149
当何菊花为保护象征紧皮手生命的龙鞭而壮烈赴死后,袁书记跺跺脚,“何菊花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这是咎由自取。”大队书记抹了把眼泪,那句“她也是人哎”不禁让人潸然泪下。党和政府站在真理的位置上,以革命真理和革命权威自居,不容置疑地将异者归为假丑恶,民众丝毫无法撼动这种政治真理的化身和权威话语权的地位。小说里,一段经典描绘了袁主任的出场方式,将他洋洋得意的自大形象跃然呈现给读者:
一辆德国造的自行车咿咿呀呀地在巴子营响起时,吸引了不少人来观望。当看到袁主任笑嘻嘻地停了车子,用手在车把上拍了几下时,巴子营人察觉出了他的兴奋。[2]P80
袁主任在《末代紧皮手》中就是革命真理的微缩化身。百姓的生命在革命真理面前弱小而无力。革命真理、政治真理对于百姓来说,显得凶恶野蛮。土地信仰,被当作封建迷信、牛鬼蛇神,被无一丝人情味地强行消灭。而对于寄托在紧皮手身上的、保护余土地保护龙鞭的何菊花来说,革命真理直接将灾难引来,生命就此陨落。
3.土改的第三步:诉苦运动
当破除四旧运动来临时,民间的传统信仰都变成了戕害人心的封建迷信。《末代紧皮手》中,巴子营独有的代表土地爷的“紧皮手”也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中一次次受到凌辱和折磨。这都是对诉苦运动形成鲜活的呼应与写照,小说第九章《将斗争进行到底》中,“活人展览”一节让人哑口,无力感倍增:
“巴子营再带次头,这次阶级教育展览不再用图片和文字,要用活人来代替,要活学活用。”……“主题定为:‘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把余土地打扮成地主,把何菊花打扮成地主婆,表演不就行了。”……为编这场戏,正接受监督改造的农民诗人被叫进了大队部。他让民兵连长去找一个破筐,一只破碗,一顶破草帽和一根棍子,做道具用。他扮演一个还债的贫农。他把两把椅子装扮得像模像样,一把准备让余土地坐,一把让何菊花坐。
“要把他的祖宗三代都骂个狗血喷头。”农民诗人满怀豪情。
农民诗人说:“这是政治任务。”[2]P128-129
“可是穿上龙袍的余土地端坐在椅子上,巴子营人怎么看他都和土地爷像,竟肃然起敬起来”。村民心目中对土地的敬畏之心是渗入内心的潜流,随时都能不自觉的涌出,在盲目攻击谩骂看热闹的同时,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得到解脱,反而更加惴惴不安!
“农民”背的那袋粮食货真价实,本来一上场说几句话就会放下,谁知农民诗人很刁,始终没有将让他把口袋放下的那句台词说出来,他也不便放下。见农民诗人又随意加戏,他的火气窜了上来,扔了筐子,把口袋一撂,一个嘴巴打过去,“日你妈,让你狂,让你耍人。”“地主婆”陀螺般转起来。
民兵连长见火候已到,马上呼起了口号:“打倒地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巴子营知道口号一呼,戏就快结束了,便可嗓子吼起来。袁主任因何菊花没扮演地主婆有点不快,但“农民”货真价实的一个嘴巴和冲天的口号,使他的不快很快烟消云散。[2]P130
诉苦运动进行中,农民与地主的对比,使农民认识到地主是其贫穷的罪魁祸首,发现两个阶级究竟是谁养活谁的道理。利用道德倾向浓重的经济层面的推进,阶级划分给巴子营乡村刻下了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印记。土地改革的初衷诚然是想将农村社会的土地财富分配更加平均,但对新政权来说,更深层的动因其实是发动底层群众的政治热情,刺激广大农民对地主、对富农的仇恨,从而反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统治,转过来拥护和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使乡村社会治理和资源逐渐归属到共产党的手中,完成政权的最终构建。从这看,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其经济功能与政治目标相辅相成。在小说的《地道》一章中,对蒋介石的反动意识植入就明显体现了这种强行又粗暴的灌输:
“一个石头要砸死一个蒋光头,要形成人民的汪洋大海。”人武部部长每天都在巴子营蹲点督阵,他看着码叠得整整齐齐的石头,对挖地道的人说。
“谁是蒋光头?”有人问。
人武部部长的脸一黑:“你连蒋光头都不知道,蒋介石呗。”
问的人摸摸头:“蒋介石只是一个人,一个石头要砸死一个蒋介石,这成千上万个石头,哪有那么多蒋介石要砸。”
“什么逻辑?什么立场?”人武部部长拔出了腰中的枪:“要不是特殊时期,我枪毙了你。”他一枪朝一块石头击去,子弹在石头上拐个弯,飞进了一颗树中。[2]P132
小说里乡民们不知蒋介石为何人,更不知为何要砸死他。他们一面整天挖着地道,一面陷入“一个石头可能会砸死一个蒋介石”的自我想象。但是,“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3]尤其最后一章《胡麻开花蓝茵茵》,“剜毒根”一节是这部小说中,余土地被残害的高潮片段,令人震惊:
“把鞭子全捆在余土地身上,他不是爱紧皮吗?我们就紧一紧他的皮。”袁书记抓起一条牛鞭看了看。
“先从脖子上绕,然后从腿上绕,剩下的全绕他身上。”
一条牛鞭绕在了余土地的脖子上,余土地的呼吸有点困难,他的两条腿上也被密密地裹绕了牛鞭,牛鞭的鞭杆旁逸斜出,在大太阳下,余土地挺立在原野上,百来条小鞭子像百十条蛇爬在他身上。牛鞭在太阳光的直射下,有了热意,余土地艰难地站着,站了一阵,他轰然倒地,胸前的几根鞭杆撑住了他,他的身上仿佛中了许多杆箭,刺猬般滑稽。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拿几根木棍,顶住他,让他尝尝人民专政的威力。”[2]P184-185
“紧皮手”余土地因为紧了土地的皮,袁皮鞋就要紧他的皮。从脖子到腿到全身密密麻麻地缠上牛鞭,在太阳直射下紧皮手轰然倒地的样子,让袁皮鞋拍手称赞“这就是人民的力量”,他要让不服管的巴子营乡民知道,你们爱戴敬畏的土地爷必须尝尝“人民专政的威力”。当余土地轰然倒地,也意味着袁皮鞋权威的树立、传统乡村权威的倒塌。
伴随着“划阶级”的诉苦运动,利用农民自然状态下的苦难和苦难意识,使其与国家的政治框架建立起联系。李里峰在《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一文中对诉苦的动员技术作了更具体的概括,指出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诉苦的种种顾虑;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账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的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借助种种动员技术和策略,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
三、巴子营的“土改”启示
从解放初到文革结束,巴子营这块偏僻之地上出现了太多的荒唐与悲哀,同时赋予了太多的荒谬性悖论。作家李学辉对那段敏感的历史从来都不回避,反而用一个个悲剧提醒着人们对那段历史予以反思。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人类文明如何进步,人性的关怀依然是我们追求理想社会构建的精神依据。
巴子营的历史和人的一生一样,都是一种经历,一种悲喜交织、荣辱并存的生命拓印。李学辉是西部大漠的凉州人,生于斯长于斯,一生情系于此。凉州是河西走廊之门户,东邻宁夏,西邻青海,南邻省会兰州,北通敦煌。古时素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重地之称,曾经是中国第三大城市,一度是西北的军政中心、经济文化中心。李学辉的每一部作品都自觉充当起了凉州文化的代言人,持续向世人描绘着凉州古城里纷至沓来的鲜活的小人物、小景象和大情怀、大悲剧。“补丁”这一笔名,意为凉州文化的补丁,缝合凉州文化和精神。这座古城历经了四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像一颗遥远的夜明珠,在历史长河中的骤起骤灭,也闻听杀伐声也嗅到血腥气。只要随着作家李学辉描绘的图景,就会发现凉州城往日的荣光依旧瑰丽绚烂,它的文化血脉依旧汩汩流淌。
《末代紧皮手》书写的这块厚重土地上,土地改革粉碎了传统等级结构,随着阶级斗争这样的革命新政治话语的涌进,巴子营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价值观被重新书写,过去底层的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做起了巴子营的主人,这种政治地位和乡民心理的巨大变化,正是袁皮鞋代表的以政治真理推行土地改革的真正意义所在。袁皮鞋把阶级话语刻进巴子营中, 完成了对巴子营底层群众的政治动员。背后的政治逻辑则是完成巴子营重新分配资源和整合群众的合法性。
当然,今后的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必须要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根基。以史为鉴,在乡村城市化的浪潮中,总结历史制度的变革、乡村的治理、农民权利的保护及其主体性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但一个永恒的怪圈一直存在:在诉苦、翻身、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对农民而言,土地、房屋、财产,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给的,亦即国家给的,国家圆了一个普通农民最朴素的梦。同时这种感激又是和敬畏联系在一起的,能够将农民敬畏的对象打翻在地的力量,农民对其不能不产生一种或明或暗的敬畏。[4]社会在实践中不断成熟与前进,但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庞大的农民群体的思想似乎永远慢一步,他们天经地义地接受着一切政策的来临与政策的改变,似乎从无异议与想法,正如《末代紧皮手》中将巴子营的百姓比如河滩里的野草一样,他们的愚昧与善良都一直那么让人心痛:
偌大的河滩里冷黄的野草安逸地蜷伏着,等待来年,它们对生命的轮回没有太多的抱怨。什么时候绿,什么时候黄,那是老天爷的事情,与它们相干不大,它们只管该绿的时候绿,该黄的时候黄。[2]P9
在小说《末代紧皮手》中,随手可以拾到这些荒谬性的悖论描写。这些与制定政策初衷相悖的实际结果,在巴子营人身上总能找到最佳的诠释与嘲讽。地主何三曾经为家业付出过辛苦;即使王秋艳的丈夫何立民生前扬言要革他的命,他都忍了;民国政府抓壮丁时,他还因为替巴子营的乡民说情被抓进县衙,差点挨枪子,交了银元才勉强了事;国共斗争时期,他还资助和收留过红军,红军大官因为太感激打了收条给他,因为这事,还被国民党马家军诈去了几件宝贝。
可这样淳朴仁义的地主得到的下场,也仍旧是和那些恶霸土豪一样。当革命革到何三头上时,他苦思冥想也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自觉“这辈子没做过太过分的事”。对地主一刀切的做法,在何三这样的地主身上,显失公允。
旧有农村权力格局被推翻,地主何三、紧皮手余土地不仅在土改中被夺去了土地和财产,同时也被夺去了政治上的权力、社会上的地位甚至是人身上的自由,一步步退让出原先享有的历史舞台中心。就像亨廷顿(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说,土地改革“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也就是说,土改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那么,就真的没有人在当时混乱疯狂的革命中,保留一点人情味吗?“大队书记”是巴子营土生土长的农民,所以打小他就深知“紧皮手”这一身份在巴子营具有的神圣象征意义,加之善何三、菊花都是他打小的邻里街坊,这些都构成他本来生命熟悉的元素。当他作为巴子营的基层政治干部时,他从骨子里就不愿将他们如此非人地耍弄和亵渎。与袁皮鞋相比,大队书记对于巴子营的实际情况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有时还会因此对党的阶级政策和土地政策提出质疑。比如当何菊花为保护龙鞭跳入地道摔死,精赤赤的身子旁,几只老鼠正忙着啃食她的脑浆和血液。大队书记抹了把眼泪,那句“她也是人哎”不禁让人潸然泪下。而袁书记跺跺脚,“何菊花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这是咎由自取。”但在上级袁皮鞋看来,这正是大队书记思想不通、觉悟不高的表现。
大队书记的思想意识和个人素质本身就和国家政权的上层意志的要求差之千里,加上袁书记发布的政策常常脱离巴子营实际、且反复不定,他会频繁陷入对袁皮鞋负责和对巴子营乡民负责的矛盾中。这种夹缝处境让巴子营的基层干部动辄就会担上思想落后、革命不彻底等罪名,这必然使他的行为选择发生改变,促成他以不得罪人为基本追求,而不能更好地完成自身政治权力职能,从而形成了大队书记在巴子营的基本政治职能逐渐让位给袁皮鞋的最终状态。土地改革历程中,全国基层政治精英因为权责分离而产生的“躺倒不干”“敷衍塞责”“好人主义”等心态和行为,是像巴子营这样千千万万小村庄最终完成土改任务的推动力。像大队书记这样的基层政治精英,在土改期间,在自身情感与上级政令的矛盾摸索中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暗暗维护当地村民利益或攫取个人私利。
要进行这样一场覆盖极广、变革极大的彻底的历史性的运动,难免会染上极端化和局限性。有学者把它叫做历史运动的惯性。势之所至,无可挡也!直至其极端的偏颇化悲剧彻底爆发出来,完全暴露其势能,才会最终停止。《末代紧皮手》中巴子营里任务命运的坎坷与阵痛,是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悲剧。我们后人要正视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巴子营的历史无法改变,紧皮手的悲剧已经上演,唯一能改变的是坚决不让巴子营当今的后人重演种种悲剧。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这一小说文本中土改现象背后涵盖的深远历史意义与影响,永远值得研究与反思。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182.
[2]李学辉.末代紧皮手[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132.
[3]陈志让.1927- 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A].[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16- 217.
[4]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A].刘 东.中国学术[J]. 2002,(12): 133.
[责任编辑:王雪炎]
Association between Political Truth and Peasants’ Psychology, Together with Land-reform Reviews inTheLastJiPiShou
ZHAO Yi
(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China200240)
2016-09-20
赵 怡,女,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I
A
1008-0597(2016)04-0042-08
10.16161/j.issn.1008-0597.2016.0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