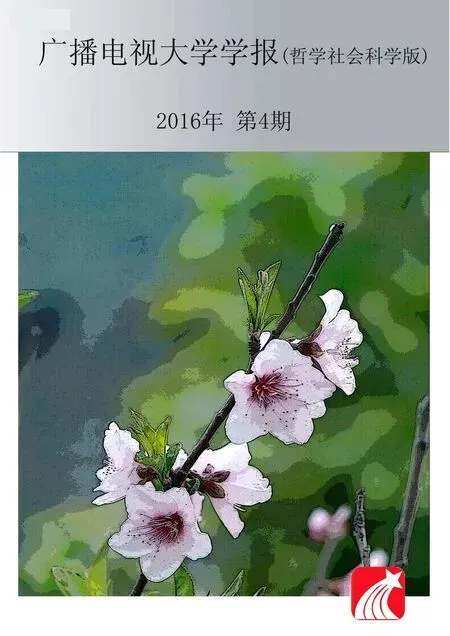从病迹学视角解读李兰妮的《旷野无人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2016-03-10徐晓红
徐晓红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从病迹学视角解读李兰妮的《旷野无人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徐晓红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深圳作协主席李兰妮是癌症和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中,详细记录了她对“躯体化”的认知及通过认知日记抗病的过程,本文聚焦她所言及的家族史及与母亲的关系,尝试做出笔者的解读。在并不善于自我解剖、公开个人精神疾病的中国,李兰妮的创作与抗病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病迹学研究的可能。
李兰妮;病迹学;创伤;自我心理治疗
李兰妮长达40多万字的《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由多种文体连缀而成,在82篇“认知日记”中,李兰妮从抑郁症患者的角度记录了她从2003年6月到2004年8月间求医、服药、写作等方面的内容。“认知日记”后附的“随笔”记下了李兰妮在《旷野无人》写作及同步接受治疗过程中的生活感受,夹杂着她对幼年生活的回忆、对梦境的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笔”部分可视为抑郁病患者李兰妮对病历的自我书写。在参阅国内外精神病学方面的书籍后,李兰妮对抑郁症患病根源进行了探究,通过追溯家族史、回想幼年记忆等研究探索,她将疾病诱因归于遗传基因、家族史及母亲。
“随笔”与“认知日记”虽无时间上的连续性,但可以对照阅读进一步了解她的患病历程。后附“链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作为作家李兰妮的文学创作的节选,大多是已发表的散文、中篇小说的片段,内容也是围绕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很多篇幅聚焦到她的母亲兰兰。二是作为读者的李兰妮对国外精神病学著作的引用,包括精神病专家的著作、抑郁症患者的手记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抑郁症患者用于自愈的阅读疗法图书目录。链接之后是“补白”部分,结合“认知日记”“散文”“链接”的内容,李兰妮从各个角度有感而发,或是补充或是注脚或是评论,让前三个部分的衔接更为完整自然。
这样四种不同文体的组合虽然新颖,但有些部分不太容易阅读,时间轴有些混乱,尤其在她对母亲的回忆性叙述中,多次出现内容的重复,突冗地将时间轴推前又拉回,可看出她对这部分叙述所流露出的内心不安和动摇。
伴随着李兰妮对抑郁症的日渐了解,她也找到了适合调试自身情绪的方法,比如阅读名人患病的书籍及信仰疗法,让她找到了情绪抒发、痛苦宣泄的契机,心态得以重新调整,并找到了活下去的动力。这种自我心理治疗的方法其实与“文学治疗”有相通之处,在精神医学临床治疗中也会使用阅读疗法,借助文字、艺术的力量让人的神经得以放松。可以说李兰妮的这部著作也为临床精神医学尤其抑郁症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读者进行精神病学启蒙的角度而言,我们能够借助此书了解抑郁症的基本知识,借助作者的体验我们可以更真切地了解抑郁症的发病诱因、症状、治疗状况。如其说该书为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不如说是一个抑郁症患者通过阅读、认知日记疗法的抗病史。
一
在《旷野无人》与电视节目《鲁豫有约》中,李兰妮提及自己从小身材瘦长,体弱多病。十四岁之后开始经历血管瘤、甲状腺癌、淋巴癌、胃下垂、内分泌紊乱等躯体疾病,小小年纪就动过几次大手术,成年后更是频频上手术台,她在未被告知患了癌症时,坚强又乐观地挨过一次次刀子。身体的柔弱让她精神所受的负荷加深,但她并不自觉,认为偶尔的失眠、多虑不过是正常的身体反应,服用药店买来的安眠药了事,她仍在乐呵呵地工作、写作、生活,甚至在1986年被精神科医生推测可能患有“抑郁症”时,仍不以为然,完全认为是一次误诊。一直到2003年4月她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遏制不住的自杀冲动让她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这才开始对自己的精神疾患有所认知。
其实躯体上的不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致使她患上精神疾病的诱因。李兰妮最初对就诊精神科的抗拒是因为对抑郁症、精神卫生知识的匮乏,这也是国人的通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中,心病与身病是无法分开的,但国人习惯将自己内心的压抑、无从排解的不适情感化作躯体化的不适加以表达,比如头疼、胃疼。不仅限于患病者当事人,甚至整个家族都会对精神病的公开存有抵触心理,精神或心理疾病如果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曝光会让家族感到不光彩,也是一贯的“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在作祟。这也源于很长时间以来精神病在中国带有严重的污名化,加上患者本人的病耻感很强,不习惯在公共场合透露病情。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凯博文1980年代在湖南进行精神病学跨学科调查,发现大多门诊病人中的神经衰弱、头疼失眠等症状与社会环境因素有直接的关系。①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偏向将人的精力重心放在对人际关系方面,而忽略对个人内在精神的关注,他通过分析由文化形塑的精神疾病个案,证实了社会变迁转化成的个人苦难及个体绝望。
另一方面,出生于1956年的李兰妮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大变革事件,在每个转变的关节点期往往比其他时期更容易形成集体社会焦虑与时代病症。这在与李兰妮为同一时代人的伤痕文学作家群中也有所体现,他们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不太习惯直接表达个人情感需求,作品中也能够窥见其倾向于内省的特质。于此而言,小说中关于文革前后的部分会引起这一代人的共鸣,也有助于我们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深入了解上一辈人的生活和情感状态,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伤痕文学与作家创伤的新视角,更能够真切地窥见社会、环境、家庭等外因对作家的创伤。
李兰妮从小缺乏父母足够的关爱,有着与“弃子”心境相仿的经历,这其实与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哈姆生等作家的童年生活非常相似,这些作家在创作中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并将童年创伤与疾病体验化为小说的素材,从中能够窥见疾病与创作的双重作用机制。
现有的科学证据和传记资料表明,躁狂抑郁症及其相关性情与艺术想象和艺术表现之间有所关联,处于躁狂状态下的作家亢奋且思维活跃,而处于抑郁状态下的作家虽然思维和行动会出现滞缓情况但沉静则可能带来专注[1]P224。李兰妮《旷野无人》的结构及“认知日记”的部分内容,出现了明显的思维混乱,让读者难以共情,其实这也可理解为作家抗病过程中思维不稳定的真实表现。这与芥川龙之介在精神疾病严重发作时创作的《河童》《齿轮》等有共通之处,作家眼中光怪陆离的世界与文学创作的刺激机制也成为文学病迹学研究的切入点。②《旷野无人》中《十二岁的小院》的插叙部分正是李兰妮所处的家庭小环境在癫狂的社会大环境中的微观写照,李兰妮对抑郁症发作及治疗过程的描述,也为我们了解疾病与创作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李兰妮具有职业作家敏锐的感受力,这让抗病过程在她的笔下得以更真实的再现,让对病痛、孤独和死亡等形而上的思考更为深刻。可以说李兰妮对精神疾病这一题材的感性书写,我们出现可以从病迹学研究的视角窥见作家患病过程与创作的相互影响。作家将精神疾病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并在笔下将之赋予新的意义,在她进行自我分析、克服负面情绪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出她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无疑,李兰妮是非常勇敢的抑郁症患者,她能够克服内心恐惧,公开病史,这也会激发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理解和关爱,促使更多的患者鼓起勇气去接受诊疗。
凯博文在《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中揭示了以“躯体化”为名的身体疾病与心理问题之间的隐秘关系,这对于我们认识自身的身体疾病和心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凯博文看来,“中国人并不缺乏表达情感的词语,而是受到文化塑形的心理过程导致他们在压制自己的情感症状”[2]P152,李兰妮在治疗抑郁症的过程中尝试记录日记,不失为一个正视内心情感的绝好途径。写日记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表达的过程,会尽最大可能运用最贴切的词语描摹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在私密的日记书写过程中,无需顾忌所谓的文化禁忌,不用考虑潜在的读者的感受,可以尽情表达内心最私密的情感,让人的情绪得以抒发和宣泄,这本身其实也是心理治疗,即认知疗法、叙事心理治疗技术③的一个环节。
二
关于李兰妮对抑郁症患病史的自我探究及围绕个人家族史的分析,的确让人折服,但其独断性的笔触也有让人难以苟同之处。
李兰妮在童年时代未得到充分的家庭关爱,这不完全是她父母的错,当时社会背景下,她父母专注于工作,疏于关心孩子的内心,何尝不是为了给她与弟弟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而不得已的选择呢。时间上没有充分的陪伴,并不代表不爱孩子。社会上一些贫困家庭物质上非常匮乏,父母整日守着儿女也不能说在精神方面对子女做到了充分的关爱。李兰妮在这一方面似乎对她父母太过于苛刻了,至少不是十分宽容。
《旷野无人》中围绕母女间纠葛的部分也是李兰妮小说创作的重要母题,笔者有不少同感,对她不甘屈服母亲的压力,大胆解构母爱的做法表示钦佩。在她与母亲间不太和谐的互动中,体现出女性的成长过程中对自我、命运和社会的认识,揭示出女性成长的困境。其实,在现代文学中对母亲形象的越轨性书写、对“母亲神话”进行解构的女作家不在少数。最先让人想起的是未享受过母爱的作家萧红,她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幼年的情感缺失让她在情感上时刻处于饥渴状态,与男人交往中处处失控,一段感情总是盲目地开始、草率地结束,这不能否认这与她幼年的生活阴影有很大关系。完全对慈爱的母亲没有概念的萧红之笔下的母亲,残忍、变态、暴虐甚至失去人性。庐隐在她出生后外祖母马上病逝,母亲从此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交由奶妈喂养。还有梅娘,她起的笔名就意味“没娘”,她对母爱也是陌生的,在作品中将母爱与人道主义同时融入创作中,对母爱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这些女作家对缺失的母爱各有不同的表现,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也都流露出潜在的对母爱强烈的渴求。正是这种无法满足的感情使他们的作品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让她们写活了作品中的母亲,对心理剖析入微,描写母女间的情感纠葛冷血又真切,之中不难窥见人性的阴影。另一方面,童年相对幸福,感受到母爱温暖包容的女作家,如冰心,在母爱的呵护和关爱下成长,她笔下抒写的母爱的赞歌堪称时代的经典。冯沅君的母亲是通晓诗书、思想开朗的知识分子,疼爱幼女,又不忘加以严格管教,冯沅君在作品中对男女婚恋的情感纠葛处理得更加理性,很少描写心理扭曲的母亲形象。当然考察女作家与母亲的关系只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家作品,而不能用之去做囊括性的解读。
李兰妮有意与母亲保持距离,认为与母亲的谈话绝大多数是消极、忧虑、负面的,容易破坏她的治疗效果。在她看来母亲无疑是极度抑郁的,早年在军队发展颇为不顺,加上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让母亲对社会产生抱怨和抵触情绪,并将此时不时地发泄在孩子身上。这种歇斯底里的母亲形象,让人想起德裔美国精神分析师罗姆·瑞茨曼(Fromm Reichmann)于1948年提出的“制造分裂症的母亲”(Schizophrenogenic mother)的概念。在美国工业急速发达的社会背景中,传统家庭解体,人与人的情感渐渐淡漠,家族关系变得扭曲,并直接影响了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瑞茨曼的学说提出后马上受到了社会的追捧。瑞茨曼非常重视母亲在孩子养育环境中发挥的机能,指出精神分裂症源自幼年所受到的精神创伤,与其说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疾病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人格状态。母亲如果长期对年幼的孩子进行指使、干涉,对孩子教育中的言语表现及非言语表现出现不一致或矛盾的话,会让孩子在成长中无法形成正常的情感交流模式。母亲的性格、思考方式、消极不安的情感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容易让孩子形成分裂型人格。基于此观点后期又发展为双重拘束交流障碍、三代假说、伪相互性等学说。在《旷野无人》中李兰妮引用了十多本精神医学经典著作,自诩半个精神病研究专家,虽然她并未直接言及瑞茨曼的学说,但也不排除她直接或间接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类似的观点,在此触发下对她们母女关系进行了解构。
李兰妮从小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常常被托付他人照顾的经历使她从小就养成了很强的自立、自律性,学会了察言观色的本领,见识了人心的冷暖。这也让她过早地失去了小孩子原本具有的天真好动的天性,她举手投足间模仿大人,吞声忍气,敏感又倔强。父母为军人,服从国家的安排,一切以集体利益为重,家庭氛围也不太和谐。当她母亲在怀她的时候,曾极度矛盾,恨自己怀孕怀的不是时候,耽误了在部队的发展,她的出世加深了母亲的抑郁,抑郁远大于初为人母的喜悦。这样的孕育过程无疑非常不利于胎儿健康,甚至比单纯的营养缺失造成的伤害更大。李兰妮从小无缘无故滋生的与母亲的生分,也可能缘由母亲生理上对这个生育的抗拒情绪。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很多家庭多少都有些重男轻女,她在成长中也对弟弟有些妒忌,她是长女,自尊心强,不愿给别人造成负担。频繁的搬家转学,她总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甚至交不到一个稳定的要好的朋友,好不容易在不安中适应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了变动,又是新的一轮的不安和适应的过程。这虽然增强了她对环境的顺适能力,但也让她的神经变得紧张敏感,与人交往形成障碍,长时间沉迷于一个人的世界。甚至她连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够信任,更无从谈起信任他人了,这样就让她无法与外界有一个较为健康的认知,与人的交流也抹上一层阴影。久而久之她养成了一个习惯,对死亡、灾难、恶性事件、威胁等灰色、黑色影像的记忆非常精准,对这些负面信息的接受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另外,军队大院中生活的不顺、磨难扛过后,还要时刻留意下一次磨难的到来,这让她的神经变得异常敏感,对幸福快乐的感受能力急速下降,感受不了生的乐趣,涌起强烈的自残、自杀冲动。
正如她自己分析的那样,她从孩提时就很善于隐藏、压抑自己的情感,她会藏起自己的失落,表面上阳光,成为别人倾诉、给予别人关爱的对象,久而久之变成了自闭。这种自闭是别人不容易察觉的,她本身从事的就是自由职业,需要长时间的独处才能够安心进入写作状态,长久不与外界接触也会让她的自闭更加严重。我们知道文学创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患病作家的症状,让他们得到情感释放的机会,从而可以减缓病痛。但李兰妮在《旷野无人》创作时,对幼年创伤回顾视角的处理致使她的抑郁症更加严重,反复咀嚼幼年的不快记忆对她而言是非常难熬的事情,让她会陷入不良情绪的循环中,甚至可以说通过会对她造成负面的影响,从此角度而言,这种回顾性写作并不完全具有“治愈性”,某种程度上会让她的抑郁症状更加恶化,乃至将她推向危险的悬崖。
李兰妮对宏观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影响对人格形成的分析非常精彩,但自认为遗传了母系的抑郁,提出“精神基因”“遗传和突变”,将自己的患病诱因归结于遗传和基因,其实也是一种自我隐瞒。她认为是母亲的负面情绪不当的处理方式给她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的确母亲的精神状态的好坏会影响到孩子的性格,但李兰妮的发病诱因也不能全归因于母亲。李兰妮的父母虽然健在,但长年不在她身边,让年幼的她产生了茫茫大地无所依归的感觉,时间一长更加变得惶惶不安,这样造成了她容易精神紧张、猜疑、妒忌、神经过敏等不健康的性格特征,并构成了精神病爆发的远因。中国第一代精神病防治工作者黄嘉音指出,精神病家世即家族史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某些精神特点和人格倾向的遗传,另一方面是有精神病的父母或祖父母的生活环境,对于儿童的教养是不利的,影响是不良的。除此以外,教养不当、父母人格缺陷、缺少父母之爱、精神病家族史等均会对孩子心理健康产生很大的危害性。[3]
除了原生家庭的因素以外,关于中国社会环境与中国人性格形成、精神疾患问题的表象,早在上个世纪由有名的传教士、中国通亚瑟·斯密斯在行走中国的大江南北,对中国人进行细密观察后,撰写了《支那人气质》,他指出中国人的神经粗,对数字时间概念缺乏精确的认识,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都能安然入睡。同样,在1871年,约翰·达震博士在《医学报告》中指出神经和精神疾病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缺乏那种西方式生活的压力,他们无忧无虑。与这一看法完全相反的也是一位美国的学者,麦卡特尼在《东方神经》一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的精神疾病的心理社会病因,很多都是曾经在西方医学文献中作为致病因素列出过的,比如家庭矛盾、社会动乱、文化变迁等带来的问题,并且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中国人对自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东方神经”,因而中国人是一群“神经紧张的人”[2]P15。在此特意列举这两种相反的意见,为了指出精神疾病诱因的复杂性及多样性,精神疾病的病症本身千差万别,着重症状的某一个侧面得出结论存在以偏概全的风险。像“遗传基因”“分裂症的母亲”类似的归因会让作家得到一些心理慰藉,但这并未触及到问题的症结,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加以警惕。
三
最后,从日本“当事人研究”(基于日本森田疗法的理念,正视自身症状)所提倡的“自我倡导”的角度来看,李兰妮的著作堪称一部“自我倡导者”著作,作为抑郁症患者兼职业作家的身份,她或许是出版披露病史专著的第一人,此点无疑对“自我倡导者”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李兰妮也曾在深圳地方举办公开讲座,在央视“开讲了”、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鲁豫有约”等口碑颇好的节目中讲述自己的抗病史,也有人将之视为与病共生的励志型典范,甚至淡化了她的职业作家的身份。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突破了她通过写作这一“自我传播”途径的疆域,扩增了她的潜在读者群,也源于当今社会对心理健康的广泛关注,她在媒体上的讲演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更多的人了解精神疾病,减少对精神障碍认识的误区,加深人们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与病理之间的刺激和交互作用的了解。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比如抑郁症的背后所隐藏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个病人身上均有差异,对不同症状的个体感受也是千差万别。《旷野无人》是抑郁症当事人的自我言说,较为详尽的患病体验记会有助于国人了解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目前,出版界虽然出现了不少精神疾病方面的文学作品,但大多属于非当事人视角下的疾病叙事,这与李兰妮著作带给我们的抑郁症当事人患病、抗病体验的阅读感受显然不同。
在公开讲座中李兰妮曾被问起在她频频言说自己的不幸,一次次咀嚼内心的创伤中,是否会让她的伤口一次次被揭开,反而妨碍了她平常心态的形成。我们知道病痛的叙说也是一种叙事方式,这种病痛的叙事语言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尤其作为职业作家,在她的描述中不自觉地会存在一些夸大或虚构的成分,频繁的 “倾诉”“告白”会让她习惯这种心理创伤体验,并将之视为日常化。习惯了与自己的疾病和创伤独处的她,正如她自己所言在“恨怨自怜中陷得太久”,现在成为了倾诉者,用她作家的才华过滤了的语言,反复叙述自己的成长史、家族史、创伤史、抗病史、治疗史,这难免从一个极端滑入另一个极端。从文学与阅读具有的治疗作用而言,创作是作家对情感的抒发手段,文字倾诉能够减缓内心的负荷。但李兰妮在《旷野无人》的创作过程中,对疾病体验的反复咀嚼、回顾直接导致了她抑郁症的爆发。由此可见,疾病对作家的创作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有时疾病下的心理状态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帮助其获得新的领悟,发现新的写作素材,但也会因疾病影响到作家心态,带来一系列负性作用,这些负性因子一旦在创作过程中呈现,很有可能会让作家产生恶劣的情绪,撕裂甚至扩大作家的创伤,一不小心还会将他们推向精神疾病爆发的悬崖。
弗兰克尔认为:“可怕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和态度”[4]。但社会固有的观念将“病人”与“正常人”进行隔离,通过冰冷的精神医学术语将他们置于健康者的对立面,造成了病人的双重痛苦。作家在多种病症的缠绕下让文学创作过程也带上了一层朦胧色彩,作家带病创作中的疾病叙事也反映了其心态微妙的变化,也可以说在创作中作家所体味的心态变化远比作品展现的疾病更为真实、深刻。李兰妮对抑郁症患病的自我解释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无疑很多是正面的,但她将大量精力耗在疾病的言说这种行为很难评价是幸亦或不幸。在阅读李兰妮的作品时,笔者总有作家在其他题材的发展空间被遏制之感。实际上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感知到原生家庭的一些不完美,对于作家而言,重要的是这种心态对于她创作和生活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李兰妮的文学功底,若将母女间的情感纠葛、一家四代女性的命运为题材,或对《十二岁的小院》加以扩充,创作一部长篇纪实小说或许并不比“精神档案”的可读性差。她多次在公开场合声讨“我没有一个很好的母亲原型可学习”,这何尝不是女性作家的自怜自艾。天底下本无有完美的母亲,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努力让自己成为较为理想的母亲,这真的无需太悲观。
文学本身是人学,透过病迹学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梳理作家的生平经历,通过作家的创伤和疾病体验更好地了解社会和文化对人的形塑,更有效地梳理时代的特征。如李兰妮所言,《旷野无人》的写作一是为了帮助自己治疗抑郁症,二是希望通过此书能帮助更多患抑郁症却不敢正视病症的人们——特别是孩子。在如今社会精神与心理疾病的患者日益增多,通过此作品能够让人们引起对身心健康的重视,在遭遇心理不适或精神状态不佳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自我梳理,慢慢找到问题的诱因并进行自我情绪管理。通过文学病迹学的视角进行的作家创作与疾病交互作用的研究成果,同样也能成为临床医学很好的参照。临床病理学能够进行确切的诊断,有助于作家对自我情绪和创伤的控制和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会扩宽文学与精神医学的跨学科研究及医学人文学研究的深度。
[注 释]
①参见张敦福著《哈佛大学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一份旁听报告》载自:《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
②病迹学是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以精神医学为基础的一门边缘性学科,以杰出人物特别是艺术家为对象,从精神医学传记的角度探究他们成长经历中的异常性格、内心纠葛等与艺术创作间的交互作用。1990年代初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前院长王祖承介绍了日本病迹学的发展状况,并引入中国,与临床病理学研究相互促进。目前仅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几篇运用病迹学研究方法的成果。
③叙事心理治疗是20世纪80年代从家庭治疗领域中派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取向,即通过故事讲述让问题外在化,注重考虑现实环境中的人际关系,主张经验现象的一元论,并进行自我解释,避开医生治病的隐喻,引导人们通过新的视野看待心理健康问题。参阅杨广学,李 明所著《叙事心理治疗的生存本体论含义》,《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刊载。
[1]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疯狂天才——狂躁抑郁症与艺术气质(刘建周,诸逢佳,付 慧译)[M].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凯博文.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郭金华译)[M].上海:三联书店,2008.
[3]黄嘉音.幼年环境缺陷对健康的影响[J].家,1952,(6).
[4]刘翔平.寻找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说[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57.
[5]近藤裕子.臨床文学論——川端康成から吉本ばななまで[M].彩流社,2003.
[6]兼本浩祐.人というソフトはどこまで使えるのか——徴候的可能性の実現としての病跡学[J].日本病跡学雑誌.2013,(12).
[责任编辑:王雪炎]
A Pathography-persp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Li Lanni’sNoneintheWild:ASpiritualDocumentoftheDepression
XU Xiao-hong
(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ShandongChina266100)
2016-10-19
徐晓红, 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日本研究中心,讲师,东京大学文学博士。
I
A
1008-0597(2016)04-0028-06
10.16161/j.issn.1008-0597.2016.0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