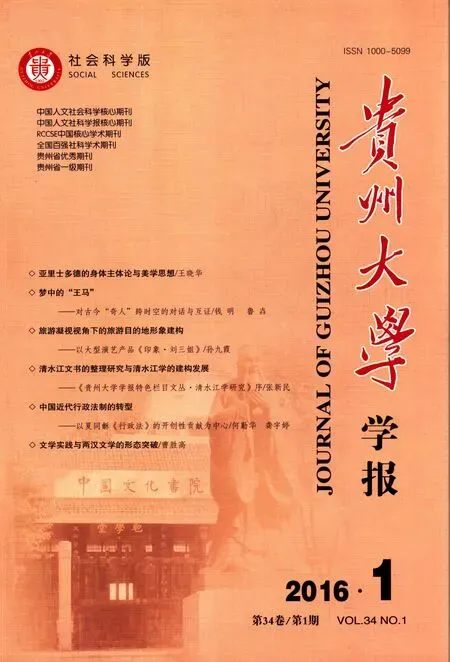论苗族椎牛神辞中的季节性节律
2016-03-09陆群
陆 群
(吉首大学 哲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论苗族椎牛神辞中的季节性节律
陆群
(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苗族椎牛仪式神辞中透露出来的诸多信息暗示了该仪式与季节之间的关联性。神辞中冬去春来的季节表征非常明显,先民的生活就依托于这种季节交替循环所产生的大自然物象的深刻变化。自然的季节性节律与人的动物性节律在春天这个季节里达到了高度统一。日常生活的节奏根据季节的节律组织起来,以春季为主题的节庆活动由此带上了仪式性的神圣义务和庄严意味,并使苗族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得以周期性延续。
关键词:苗族;椎牛神辞;季节性节律
人类生活在自然之中,必须遵循季节的某些时序,在恰当的时间里做恰当的事情。由此,人类社会就必然会建立起某些规则,来提示自然的季节性节律,使其行为符合自然的时序。上古的节庆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提示”功能,其“季节性节律”的标识非常明显。法国人类学家葛兰言(M.Granet)认为:“从本质上说,上古的节庆是季节性的,这些节庆是和谐(concorde)的节庆,人们通过它们在社会中同时也在自然界中确立良好的秩序。”本文拟以苗族椎牛祭祀仪式及其吟诵神辞为例,探究古代苗族如何通过仪式和神圣观念来表达自然的“季节性节律”,以及如何依托季节性仪式而使苗族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得以周期性延续。剥离出这些信息来对其古代的信仰进行溯源,可透视从这些信仰中如何产生出古代苗族的季节仪式,并包含相应的季节规则。
本文所用椎牛祭祀仪式中的吟诵神辞主要依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石启贵在湘西所做田野调查有关椎牛祭祀的仪式文本。该文本由麻树兰、石建中整理译注,民族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1]之所以选择苗族“巴岱雄”椎牛祭祀仪式神辞是有道理的:首先,该仪式是由苗族巫师“巴岱雄”(bax deib xiong亦称作苗老司)主持的苗族传统宗教仪式之一①湘西苗族民间宗教有两种:一为巴代雄(bax deibxongb),俗称苗教;二为巴代扎(bax deib zhal),俗称客教。苗教和客教各设各的教坛,各有各的巴代祭司。。椎牛,苗语称“弄业”(Nogx Niex),意为吃牛,主要由祭雷神(习肱松Xid Chunb Sob)、敬谷神(习滚农Xid Ghunb Nongt)、祭日月神(布冲Bul Qod)、巡察酒《耍酒Shab如ud》、祭家祖(喜香Ⅺd Xangb)、剪纸(铺头Pud Ndeud)、迎舅酒(培酒己 Nbeud Joud Gil)、迎宾饭(培利己 Nbeud Hliet Cil) 等九堂构成。其椎牛神辞,全是用湘西苗族古辞“都”体表述。即以两句偶联为主,排比、并列构成长篇的古老文体,其咏诵神辞因此而被称为“都肱”( dut ghunb)。[1]2文本所记录的神辞均由“巴岱雄”在仪式过程中念诵或唱诵。考虑到宗教仪式的相对稳定性,尤其是椎牛仪式的“苗教”性质,我们可认为,这一根源于苗族古代社会的仪式神辞未曾经历大的变动,其中依然保留了大量苗族古代社会的信息;其次,依据石启贵当年所收集的资料情况,可知其调查地主要在湘西花垣、凤凰一带,集中在腊尔山台地上,即传统观念中的“深苗区”,其苗族传统文化较其他地方保留得相对完整*元代建立后,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土司制度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主要政治制度。明代和清初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政权主要有永顺、保靖、桑植三宣慰司。当时在以腊尔山为中心的湘黔边,还有一块既未设置土司又未派流官治理的所谓“生苗”区。其地域范围,据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二》引清人方显《办苗纪略》载:“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
一、冬春之交:自然万物生长的起点
仪式的神辞,在民间是口耳相传,其文本是石启贵在整理过程中用汉字记音记录下来的。原文虽然不是古代的东西,但它却可能成为反映古代社会事物的一面镜子。如果能正确地理解原文,我们可能了解到古代的事物。作为一种传统的、集体的创作,仪式神辞是根据某些已经规定的主题在仪式歌舞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们(指仪式神辞)因此也成为一份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产生这些定期集会的情感。”[2]116那么,在椎牛仪式神辞中沉淀着怎样的“定期集会的情感”呢?
仪式神辞描述了这样一种状态:大地从寒冬里苏醒过来,太阳暖暖地照着,人们走出户外,一切都欣欣向荣:“如内比冬(Rut hneb bleid dongd),如囊比住(Rut nangs bleid jut)。门母投内皆柔各斗(Mongb mongl ndout hneb gieat roub ghaob deul),投囊皆根比丙(Ndout nangs gieat gid bloud nbil.)。”[1]2大意是:“年头好天气,年初好太阳,房屋主人到石板上沐浴阳光,往岩板坪去晒太阳。”[1]17一阵风袭来,冬寒还在,但人们开始到四面八方去种阳春,干农活了:“出三便排斗补(Chud sanb blab npand deut bul),出茶召告然丁(Chud nzat zhaot ghaot rans denb),补牙己宰己三(Bub ral git zanl git ncant),补牙己豆己受(Bub ral git dout git sheub)。”[1]18大意是:“主人到四面去种阳春,往八方去干农活。三阵寒风袭来,三次怪风刮到。”[1]18在椎牛仪式的第四堂法事“布冲”(Bul Qod)即祭日月神的神辞中,亦展示了同样大自然从冬到春季节转换的物象表征:“如内比懂(Ruthneb bleid dongd),如囊比住(Rutnangs bleibjut),亚比略小(Ad bloud liaox xub),亚主果攘(Ad zhux ghot rangt),出三把排斗补(Chud sanb blab npand doub bul),召告然丁(Zhaot ghaot ranx denb)。不牙及宰及才(Bub ral git nzanl git ncant),不牙及豆及受(Bub ral git deut git sheub)。”[1]745-746大意是:“开年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一家大小,一屋老幼,来到山坡干农活,做阳春。(这时),一阵阵冷风从身上吹过。”[1]745-746
神辞中,季节的表征非常明显:阳光、温暖的石板、沐浴阳光的人们,还有山坡上种阳春干农活的农民,而残冬的寒风犹在,一阵阵,从人们的身上吹过……这是冬春之交的大自然物象:万物从冬季里苏醒过来,大地潜伏着生机,等待着生长。冬春之交,是大自然生发的起点。
“椎牛”仪式的举行从时间上看多选择在秋冬,农历十月到次年的二、三月期间。这段时间,放大一点说,也正是大自然休眠调整孕育生机和等待生长的时节。即使在人的认识水平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也知道大自然之于人的生存之重要:大自然是孕育万物的生命之源,大自然作为丰饶与富足的象征,是有生命力的,大自然也会“死”,冬天的万木萧条就是大自然“死”;大自然也会“生”,春天的万木初长就是大自然“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特别重视大自然的“生”,因为这种“生”关系着人类的“生”。[3]《凤凰厅志》载:“苗人于农毕十月,或饶裕之家,或通寨醵钱,购牯牛之肥壮而纯白者,先其约会亲邻,戚党、男女、少长毕集,结棚于寨外,主客皆盛服从事,宾至,声铳,以祓不详。”[4]在清代统治者的眼中,“椎牛”仪式中大规模的“集众欢歌”是非常危险的:一是“群饮以糜财”[5],二是挟枪矛(椎牛)易使苗众“寻睚眦醸衅”[5],以至于一度规定“严禁椎牛祭鬼”。[6]
“椎牛”仪式中大规模“集众欢歌”的时间性正暗示了它与季节之间的关联性。仪式中的诸多细节依然为我们提供了透视古代苗族社会的窗口。从椎杀的过程来看,为什么不是一刀使牛致死而要以数次的椎杀使牛慢慢致死?椎杀的时间为什么往往要选在岁末初春季节交替之时?为什么仪式中所用的牛定要健壮的公水牛,不能阉割,椎牛时需要法力很强的“巴岱”来主持,参加祭祀的“巴岱”和椎牛手在椎牛前的一段时间里必须吃素食和净身,他们还必须是没有私心的人?依据泰勒的灵魂观和弗雷泽的“巫术”思维原理,我们可得到解释:苗族椎牛,其内在的思维逻辑是使承载着牺牲的灵魂的血液注入大地之中,大地由于得到新的灵魂而获得生机。[7]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椎牛仪式的第四堂法事“布冲”为什么重点做的是“琶内料农,琶糯料查”(汉意为赎稻赎粟,赎糯赎粘)。这是人们对大自然之“生”的重要期待。神辞用了较大篇幅描述了稻谷的起源,原是狗、猪、牛等从山坡野外把野生稻粟种粒带回家,掸落在狗窝、牛栏边而发芽生长出稻谷之后,被人类发现可食而栽培至今。谷粟是大自然之“生”的重要赠与,是人类生存的养命之源,故椎牛仪式中“布冲”虽名义上祭的是日月神但神辞中的重点却是讲述稻谷的起源的原因之一。仪式第三堂“敬滚农”(chud ghunb nongt)则专事敬五谷神。五谷神一直是苗家视为珍贵的神。在过去苗人的观念中,村寨上若是哪家粮食富足,就认为是其家谷神粟神坐堂居库。椎牛仪式中冗长的神辞沉淀着苗家人对五谷神的重视:“太阳还没出山,月亮还没出岭。找来一张桌子祭稻神,得了一张桌子祭粟神。凉水洗净,雨水擦亮。桌子洗得干干净净,光光亮亮。抬一张祭稻神的桌子,扛一张祭粟神的桌案。放在堂屋边,搁在中柱旁。敬送拿得八个银碗,取得八个金碗。洗得干干净净,刷得亮亮光光。拿来覆在祭稻神桌四面,拿来覆在祭粟神桌四方。又做成八碗肉,做成八碗饭。敬送女稻神,敬给男粟神。……”[1]734-737大自然的“生”“死”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原始先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远古时期,原始先民的生活就依托于这种季节循环所导致的大自然物象的深刻变化。
二、从原始采集和狩猎到农耕社会
“椎牛”神辞中大量出现的“后辈舅爷为最尊”的表述以及溯源椎牛古根时讲述“神母犬父”神话透露的知母不知父的情节,可以断定苗族“椎牛”仪式是一项非常古老的祭祀仪式,它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产生于远古的原始采集和原始狩猎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并在农耕社会中得到稳定和持续发展。
苗族在整堂贺客中,以主家的后辈舅爷为最尊者。苗乡称舅辈为“根蔸亲”,传说他们是代表椎牛所祭的大祖神前来受供的。椎牛必要请舅爷,舅辈受到尊敬,仪式神辞中就有“椎牛报客到舅屋”:“娘业保歹埋哑告(Nongx niex baod dand mex ad ghaot),哑苟缸求埋囊拜(Ad goul gangs njout mex nangd banx),各来费生他己道(Ghaob lanl huib sends nteat jid daot),眉途眉九会心难(Mis ndut mis joud huib xend nanx)。”[8]25这段神辞的意思是:“椎牛报客到舅边,一腿送往舅家园,诸位舅舅费心了,全力以赴帮操办。”在舅爷前来时的拦门歌中,还有专门的迎舅曲《原是舅辈大驾临》:“破头及化流柳抓(Paot ndeud jix hat lieul lieul zheax),枷坡禾没禾门想(Ghad paot aob mex ghaob mis xangd),冬宜贵子农长沙(Dongx nis guib zit zhaos zhangl sax),宜初出卡哑丕攘(Nis qut chud kheat gheat boub rangd)。”[8]19这段神辞的意思是:“爆竹震天晌不停,炮渣掉下好几升。以为长沙贵客到,原是舅辈大驾临。”
椎牛时舅辈还必须做“头椎”。当巴岱把一切安排就绪后*巴岱叫人于场坪中立根五花柱,主家刀师在水牛心脏部位画个碗口大的红圆圈,在由巴画出椎牛场地范围。,就可以开始椎杀牛了,这时主家向舅爷下跪,并献红布一段,叩请舅爷入场椎牛,即由舅爷手执梭镖入场(称为“头椎手”)。若舅爷年迈,则可将梭镖转交母族青年子侄接矛来椎。[9]471充当“椎手”的人至今还被呼为“大舅爷”“二舅爷”“三舅爷”……仪式结束后还有“吃忌肉”的规则和禁忌。后腿,也是送给舅家的兄妹的。牛腿按血亲分配,腿序为:父亲之舅辈为“恃打”(jongx dat,直译为椎牛舅),理抬头腿(后腿带尾巴);儿子之舅辈为“仲且”(jongx qed),地位次之,抬二腿(后腿不带尾巴)。倘若吃双牛,父舅椎白牛,抬白牛头腿;子舅椎黑牛,抬黑牛头腿;余下三四腿送姑,姑又以大小排列。无姑则须送给直系亲,无直系亲者给堂舅或堂姑姐妹。相沿成俗,不可更动。违者犯祭,社会舆论就会对此加以谴责。[9]472至今,苗族中仍认为“娘亲舅大”,解放前在苗族中留有姑舅表婚的习俗,说是“姑妈女,隔河取,舅舅要,隔河叫”,意为姑家女儿嫁给舅家里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亦反映了舅权遗风在苗族中的盛行。这是母系氏族的遗风,说明“椎牛”是一项诞生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古老的宗教习俗。
仪式第十二堂“岔公业”(Chat Ghot Niex)“讲述椎牛古根”,是椎牛祭祀重要仪式之一。按其内容属于“史辞”。史辞,苗语称“都果”( dut ghot)。“果”,汉意为古、老、史。顾名思义,史辞是叙史的辞。《椎牛古根》苗语称“果聂”(ghot niex),是一部融神话、传说、故事于一体的较为完整的创世史辞。它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是关于创世神话,记叙天地形成、万物起源等,以神话为基本內容,充满奇幻,神话色彩很浓;后半部是创世传说,这部分多以写实记事为主,包括苗族鼓社根源,即椎牛和鼓舞的根源。[1]1276其中就有《神母犬父神话》,主要叙述神母犬父结合、犬父之死、神母追究犬父死因及其苗族子女椎牛赔罪等。
《神母犬父神话》(又名“奶葵爸苟”)在湘西民间被演绎成多个版本流传。神话传说不可能等同于历史,但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早期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尤其是关于本民族起源、民族迁徙之类的神话,会刻录这个民族的某些历史印迹。盘瓠传说就是这样,它隐含着图腾时代苗族社会生活的诸多信息。这个时代虽已远去,但留下的时代烙印却是难以抹去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今天透视苗族社会“历史的真实”的重要窗口。
盘瓠传说体现了苗族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信息。传说中盘瓠是由妇人耳中产出,可以看出此时人类还认为生育是女人单方面的事情,而且女人地位很高,是公主,是神母,受到尊敬,盘瓠子女也只知道母亲是谁却不知道父亲是谁,这些都说明盘瓠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笔者曾从生育观念演变的角度,认为人兽婚类神话是人类生育观念的折射,人兽婚类神话应是人类生育神话中的一环,在远古的人类社会,原始先民对人类由来及妇女何以生育的认识十分不解,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把生育与男女之间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认为人是女人自己生出来的,如同田野、平原、大地生长出草木一般。[10]因为不知道父亲是谁而到处询问,说明当时产生了对父性的需求,男性的地位有了提高。这个信息反映了盘瓠神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时期。至于盘瓠和辛女生下了孩子,他们“六男六女,自相夫妻”,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原始群时代对杂交婚姻关系并不精准的记忆的残留。
盘瓠盗取谷种的神话母题则是南方生产环境与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即稻作文化与盘瓠信仰的结合。在偷盗型神话母题中,被偷的物往往与先民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在远古时期,当一些氏族的人开始懂得栽培稻种,原始农业开始出现时,但另一些氏族还不知道稻种的栽培,而这时候犬已经驯化,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帮手,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狗帮助人盗取稻种的情节。“盗取”在这里并无任何贬义,而是一种获取生存技能的表现。稻作经济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社会从单纯地依赖自然索取生存资源到主动向自然生产和谋取生存资源的转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定居生活的出现。传说后半部讲,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石室中”,他和辛女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开疆拓土,生儿育女。按照唐代李贤注,南山为今武陵境内。盘瓠在武陵山区隐居,表明盘瓠已经告别了先前的狩猎生活而进入农耕时代。传说显示出农业生产的开始和农耕社会的到来。湘西苗族直至解放初期,在遭遇天旱时,还会通过“抬狗”的方式来求雨。只有在农耕时代,雨水对田地才如此重要,苗族选择用“抬狗”的方式来求雨表达了苗族人民对盘瓠祖先的尊崇,认为只有请来了盘瓠祖先才能顺利地降下雨水。盘瓠神话产生于狩猎时代向农耕文明的过渡。在狩猎时代,盘瓠神犬是狩猎保护神;在农耕时代,它成了农业神,神话的内容注入了时代的信息。
“椎牛”仪式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祭祀仪式,在产生之初并不为苗族所独有。《曾子名言》记载:“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11]农耕文明出现后,牛作为参与农业活动的重要助手而被保护起来,很多民族尤其是汉民族中,逐渐用“土牛”“纸牛”“面粉牛”来替代“牲牛”。自宋以降,各地方志开始有了详尽的记载,如《齐河县志》曰:“立春前一日……芒神并泥牛设于县大门内。至立春时,各职官拜芒神毕,各执春仗打牛三次,随令众役将牛打碎,各国本衙,又作小泥牛、芒神送诸缙绅家,谓之‘送春’。”*参见《齐河县志》民国二十二年本。在苗族,由于特定的自然历史等原因及根深蒂固的“巫”文化传统,祭祀仪式中椎杀真牛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
三、自然的季节性节律与人的动物性节律
苗族在举行椎牛祭祖大典的时候,所有的亲戚六眷、朋友乡邻都来祝贺,这被称为“贺客”。仪式过程往往呈现出“集众欢腾”的特征:“众各挝鼓鸣金,吹角号,烧柴以祭,祭毕,以一肩遗先刺者,余皆分而食。又别割一牲。火燎去毛,烹之,名曰火炭肉,置牛首于棚前,刳长木,空其中,冒皮其端,以为鼓,使妇女之美者,跳而击之,择男子善歌者,毕衣优伶金蟒衣,戴折角巾,剪五色纸两条垂于背,男左女右,旋绕而歌,迭相唱和,举手顿足,疾徐应节,名曰跳鼓或有以能歌角胜者,男女各出财物,为角具,男子以绸绢,女子簪环,各级队对歌,彻夜不休,……”[12]葛兰言在研究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时认为:“任何一种标志着农事开始或终结的事物——田园主题就与这些事物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种事实使得在漫长的冬季休耕期的开始或终末举行野间集会成为正当之举。”[2]117郑康成在笺注《诗经》时几次提到了这种节庆,认为这是青年男女感春气而相互吸引、相携出行而成古礼。从神祠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集会要在一定的时间(“辰”)进行。
动物性节律是指动物在情欲方面,有明显的“发情期”,大多一年一次,且时间短暂。一些家养的动物则一年两次,如我国的农村有这样的谚语:“二八月里狗走窝”。动物性节律的本质是动物肌体的自我保护。当动物无法支付高昂的生殖成本时,它们必然自我节制。人类由动物进化而来,在以原始采集和狩猎生活为生时,人类在身体上与动物没有两样,也会必然处于性活动的节律机制之下。但人类是幸运的,自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后,人类开始了定居的农耕和畜牧生活,有了相对稳定而丰富的食物来源。食物来源的稳定和丰富加强了人类的营养,大大增强了人类的体质。同时,定居的生活大大减少了旅途奔跑的劳累和痛苦,这样带来了人类在生理上的重大变化,其中显著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逐渐摆脱了原始“性节律”的控制,一年四季都可能交配和生殖。这也许是一种“解放”,“情欲的解放”。这种解放,既能保证人类种系繁衍的实际需要,又能有效促进人类男女关系的密切。
这种转变也是自然选择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人的生育现象中仍然还保留了一部分动物性特征的原因,春秋两季受孕的孩子比率更高。据霭理士的研究发现:“在文明的国家,得胎成孕的频数也有它的时期性,一年中的曲线,大抵春季要高一些,有时候秋季也比较的高,看来就是这种节气的一些痕迹了。”“大部分的高等动物有它们的繁育的季候,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即在春季、秋季,或春秋两季。有的未开化的民族也有这种季候,世界上有许多分散得很远而很不相干的这种民族,在春季、秋季,或春秋两季,都有盛大的欢乐的节气,让青年男女有性交合与结婚的机会。”“所有的证据都只在一年之中,性冲动自然而然的特别活跃的时期确有两个,一在初春,一在秋季,并且往往秋季比初春还要见得活跃。”[13]这里,他讲了人的生育概率也有春秋季节的某种痕迹,但总的情况是一年四季并没有明确划分,而且随着物质条件的提高,更是消除了这种界限。
自然的季节性节律与人的动物性节律在春天这个季节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为了感谢春天带来的万物勃发,也为了顺应人类自身的动物性节律的律动,以春季为主题的节庆活动便出现了,这类活动,既是对大自然带来的春天万物勃发的感恩,也是顺应人类自身的生理规律的支配。所以,在这类节庆活动中,往往会伴随人类自然的性活动,这是一种在大自然的春天里不可遏止的人类自身的春情,是自然而然的性活动。既然人的生殖是两性交合的结果,那么自然的生殖也应当是两性交合即天地化生的结果,并且,只要通过有意识地刺激大自然的“性欲”,就可以激发大自然的交合,从而促进大自然的生殖力。反过来,大自然的生殖力也可以让置身其间的人受到感染,从而增强人自身的生殖力,于是以春季为主题的节庆活动中的两性交合便带上了仪式性的神圣义务和庄严意味。[3]
人们通过仪式在社会中同时也在自然界中确立良好的秩序,因为正是在这些季节里,大自然季节的变化才是那样地顺理成章。“季节庆典标志着农村生活中每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竞赛也将相邻村落的青年男女以相互冲突的方式汇集到一起,在这其中,爱情就从乡村集会和歌舞中产生了。”[2]123凌纯声、芮逸夫考察湘西苗族许多春日节庆活动时这样描述道:“苗中有跳年、跳月、调秋之俗,青年男女,结队对歌,通宵达旦,歌毕杂座,欢饮谑浪,甚至乘夜相悦,而为桑间濮上之行。”[14]清人严如煜亦这样记录苗人的赛歌:“或有以能歌斗胜者,男子出铀绢,女子出簪环,以为彩结队。对歌彻夜不休,以争胜负,胜者取其彩。不善歌者不入队。所歌皆个其土风或淫亵语,歌巳,杂坐牛饮,双饱谑浪,甚至乘夜相悦,而为桑中濮上之行,虽知亦不禁,名曰‘放野’。”[15]这里的“桑中濮上之行”一语是古代形容野合行为的常用之语。
日常生活的节奏是根据季节的节律组织起来的,那些在春天举行的节庆是非常重要的,是建立在冬去春来、寒暑交替等气候变化的基础之上的,诚如葛兰言指出的那样:“古老的中国节庆是季节性质的和乡村性质的。”[2]以农耕生活为生计的中国人,无论是生产活动、社会生活还是精神观念,都会受到季节韵律的支配。它们与植物生长周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农业周期之间亦同样。只有认为它们依赖于农耕生活的季节节律,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石启贵.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椎牛卷[M].麻树兰,石建中,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陆群.神话中的死亡与习俗中的“化生”——湘西苗族春日节庆习俗及其神话的人类学解读[J].民族论坛,2008(8).
[4]凤凰厅志·赛祀[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61.
[5]〔清〕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一百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清〕佚名氏.苗疆屯防实录(卷八)[M].伍新福,注.长沙:岳麓出版社,2012.
[7]陆群.腊尔山苗族“巴岱”原始宗教“中心表现形态”的分径与混融[J].宗教学研究,2011(1).
[8]石启贵.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文学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9]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湘湘文库(精)[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0]陆群.苗族生育神话的建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4).
[11]高昌礼.曾子名言历代名人赞曾子[M].扬州:广陵书社,2007:38.
[12]凤凰厅志·赛祀[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61.
[13]〔英〕霭理士.性心理学[M].潘光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32-34.
[14]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42:155.
[15]〔清〕严如煜.苗疆风俗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责任编辑钟昭会)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1-0081-06
作者简介:陆群(1969—),女,湖南古丈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宗教与文化。
收稿日期:2015-11-2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