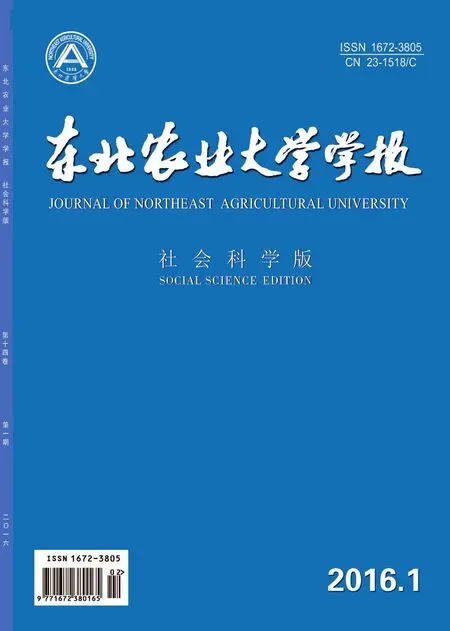徐訏心理小说之特异:心理医生视角弥漫
2016-03-08冯芳
冯 芳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58)
徐訏心理小说之特异:心理医生视角弥漫
冯芳
(浙江大学,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徐訏部分小说弥漫心理医生视角,此类作品的客观心理分析超出弗洛伊德学说范畴,具有心理学说内涵,部分小说甚至提出心理问题解决或心理疾病诊治方案,这是徐訏与20世纪中国长于心理描写作家的首要区别。文章运用心理学方法具体论述徐訏小说中变态心理分析、犯罪心理分析及正常心理分析,认为20世纪中国文坛“类心理医生写作”作家中,徐訏堪称翘楚。徐訏早期心理治疗小说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可谓中国心理治疗小说创作的先行者。
关键词:变态心理分析;犯罪心理;正常心理;心理医生;心理治疗小说
心理小说写作区别的讨论利于徐訏心理小说文学史地位评定,如祝复兴[1]、刘沁怡[2]比较施蛰存、徐訏、叶灵凤三位超验写作者,认为他们均是精神漫游者,施蛰存的作品偏于心理而徐訏偏于哲理,施蛰存笔下人物行为更断裂,思维更跳跃;田建民从文化类型、欲理崇抑角度指出施蛰存与徐訏心理小说区别,认为前者具有后现代解构主义意味,而后者表达知识分子理想,施蛰存心理小说崇欲抑理,而徐訏心理小说崇理抑欲[3];李卫东[4]、蒋传红[5]强调施蛰存更注重分析内心世界或表现色欲冲突,而徐訏更理性,认为二者小说分析均源自弗洛伊德学说。但笔者看法略有不同,徐訏、施蛰存心理小说主要区别在于:徐訏心理小说弥漫心理医生视角,客观审视与分析人的心理或心理病症,且远超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甚至提出心理问题解决方案或心理疾病治疗方法。施蛰存心理小说中——不否定其艺术成就——心理医生思维并不发达,心理分析与反思不足,未见心理疾病治疗方法,小说心理视角未超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徐訏与20世纪中国长于心理表现的作家不同,由其曾接受哲学及心理学专业教育决定。因篇辐有限,本文拟重点讨论学界研究较少的科学思维,即徐訏心理小说弥漫的心理医生视角。
一、变态心理剖析
徐訏小说《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的“我”说:“我对于变态心理学有特浓的爱好”,徐訏正是如此。
小说《失眠》中,故事意欲说明如何对症治疗失眠症:“我”和富商张证龙结识于治疗失眠的电疗室,“我”对电疗室的先进设备颇为注意。治疗一段时间后,因失业而失眠的“我”投入工作后恢复正常睡眠,但张证龙的失眠症未愈。他因爱情理想受挫放浪形骸而失眠,寻求纯洁高贵情史为零并与他有爱情的女子,但碰到的女子在他看来均很庸俗。“我”帮张证龙分析,其实他已比许多人幸福,只因欲求过多、理想太完美,才导致痛苦失眠,若人人像他,自杀将难以计数。张证龙听从劝告,降低标准结了婚。小说探讨失眠症治疗对策——物理治疗与心理疏导,徐訏这一趣味与许多心理作家殊异,其他作品中亦有表现。小说《秘密》中具有心理医生思维的“我”是美丽且富有的偷窃癖患者家禾的好友,“我”曾听妻子怀疑家禾偷窃但并未相信,后来“我”与家禾同去百货公司亲见售货员指责家禾偷东西,当即顿悟,“我”斡旋其中对经理解释家禾身份高贵,偶尔恍惚犹如精神病,最终赔钱息事。事后,家禾向“我”和盘托出发病起因,她说童年时父亲娶了妾,此事对她刺激很大,她对妾有而母亲没有的物品感到非常嫉妒,于是偷来送给母亲并获夸赞,就此患病。“我”知道后,边保密边替她消除后果。但家禾的偷窃癖不易禁绝,一次宴会上当着“我”的面她仍在偷窃,在“我”引导下才物归原处。于是“我”送给她刻着“不要遗失,不要遗失你的自己”字样的金指环。家禾在“我”的帮助下终于降服偷窃癖的魔障。小说对偷窃癖的描写符合病征,矫治方法较合理,可见徐訏对变态心理诊治的浓厚兴趣。
小说《期待曲》中,徐訏塑造并分析具有强迫型人格障碍的音乐天才许行霓。许行霓对人对己要求苛严,属完美主义强迫型人格障碍,最后发展成精神病。小说重点剖析许行霓“爱情宗教化”情结及具有心理医生般洞察力的“我”与许行霓之妹素霓的揭示。许行霓视女友高贵如神,女友成长于基督徒家庭,从小信仰基督教,为女友信仰许行霓在国外四年守身如玉。但看过她照片的“我”分析:这女子很平常,嘴唇坚毅,怀春而无圣洁气质,许行霓那样深沉高超的人有神圣爱情信仰正常,他女友未必如此,“这个音乐天分很高的人,一定有过人的想象,他在这些年把想象都罩在爱人身上,所以她就成神一般的存在了”。许行霓死后,素霓分析证实“我”的观点并获得新发现,素霓说:“我发觉我哥哥似乎永远是一个相信抽象东西的人,他后来所爱的,从他所说的话来看,似乎只是他们两个人所总合的爱情,这爱情变成了抽象的奇怪的神秘的存在,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来侍奉,来服从这个爱情。”许行霓会疯,因爱人不如想像般神圣,竟会在未分手时就同另一男子相好,后来又发现女友不守信用随便处置他的物品,更感到情感被玷污,信仰与精神就此被彻底摧毁,“失去心理上的信赖,他失去了一切自然与自尊,神经就开始变态起来”。素霓与“我”虽未明确提及“情结”概念,但实际分析揭示了许行霓“爱情宗教化”情结。荣格说:“情结这东西……是一种经常隐匿的,以特定情调或痛苦情调为特征的心理内容的聚集物”“情结是联想的聚结——一幅多少有些复杂的关于心理本质的图景——有时是创伤性人格的,有时只是一种痛苦或者被高度渲染了的人格。”[6]情结形成于先验原型,且通过外在因素提供典型情境。许行霓“爱情宗教化”情结原型是圣女与基督教,且将几年的想象贯注于情结,情结能量极大。“受控于原型的人绝不会不成为精神错乱的牺牲者”[6],许行霓不幸被言中。小说中“我”屡次奉劝许行霓要更理智,恋爱双方会变,故喜欢她、需要她便好,不要产生爱情,教他将生命寄托于事业。“我”的劝说不完全正确,却对症下药,可惜许行霓已被浓重情结吞噬,酗酒行为加重心理扭曲,使他在迷狂中自毁。结合徐訏经历不难发现,“我”与许行霓正是徐訏矛盾人格的外化,徐訏将驾驭情结的挣扎写成小说,既是自勉亦是救人。
《旧神》中,刘推事的变态情结由具有心理医生眼光的“我”揭示。“我”说“刘推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恨女子者”“说到刘推事恨女子心理来源,我是完全知道的”,因许多年前微珠辜负刘推事赤诚的爱,导致刘推事人格改变,由乐观变得消极。后来刘推事处理案件中深化片面认识,认为“女人只是一种罪恶。她们只是以男子为工具,破坏一切,摧毁一切。”刘推事不仅“恨女子”,而且“怕女子”,他说“我不能结婚。我一结婚,一定会天天担心我太太会谋杀我。甚至我怕极了,会先动手杀死我的太太。”“我”和旁人看到刘推事的表现,明确谏诤这是“变态心理”,常劝导他。但他的变态心理已根深蒂固,直到与微珠重逢,才略有反省(下文将谈到“变态”并犯罪的微珠)。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以精神病治疗为中心。富有爱心的“我”应聘成为著名心理医生奢拉美的助理,起初“我”在疗养院实习,每天与精神病人接触,希望救助病人。“我”发现奢拉美与护士给予病人无限安慰与允诺,但允诺从未兑现。“我”猜想他们或许认为病人并无记忆,果然,奢拉美表示病人无系统思维,昨日欲念已忘却,今日不安源自其他。“我”对此不认同,细心探究病人躁动原因并安抚。后因工作需要,“我”隐瞒身份进入患者白蒂家中救助。白蒂因家庭不合自我放逐于酒肆舞榭,后来失手杀人,从此变得行为诡异、厌倦生活、情绪低落。奢拉美给“我”的任务是:第一步要白蒂休息、精神安定,第二步要白蒂搬到僻静环境,然后用针药在生理上帮助她。“我”观察白蒂发现:“在她的表情之中,常常有凝视在空虚的浅笑,这一种凝视,是神经衰弱的一个特征,但并不是十分变态。她变态的地方,我寻不出,但在她突然一哄闹,一沉静之中,我看出她整个心境在两极端间摆动。我推想她的人格一定是矛盾的结晶。”“我”不断用爱心感化白蒂,告诉她“你知道有多少爱你的人看重你的青春健康与美”;看出家庭环境对她的身心健康有害,“这样沉闷的空气,这样的生活,从早晨到夜里,大家忙碌,忙碌到夜,没有一句大声的说笑,没有一种游戏与娱乐”。“我”认为白蒂“有青春之火在她胸中燃烧,但是环境是一个冰桶”,白蒂不可能脱离家族。“我”和海兰①海兰为《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另一主人公。的关爱使白蒂逐渐好转,又得到奢拉美诊治,“白蒂易怒、易感、易哭、易笑的脾气逐渐减少”。“但她的兴趣终是不长易变,而且终需要别人鼓励。一到厌倦一件事时,又抽起烟而微喟起来”“奢拉美医师对于她容易厌倦的脾气非常担忧,认为这是将来复发的病根”。果然,白蒂以“变态”而强大的意志主宰“我”和海兰,奇异的三角恋爱使“我”忘记医生本分,痛苦的海兰自杀。面对海兰之死,白蒂痊愈,恐因海兰“以死相鉴”的爱使她醒悟,“我”自省之余立志“终身献给可怜的病人”。读者常被小说的三角恋情吸引,并未注意治疗描写的用心良苦。
小说《婚事》亦是精神病题材,发病程度更严重,寻找病因颇难,治疗方法亦不同。洁癖、高神经质的杨秀常因压力患神经症,最后掐死爱妻爱琳发展为精神病。杨秀常掐死爱妻的原因由心理医生俞医生揭示。俞医生回忆:“我那时刚刚从医学院毕业,对于神经病②小说中患者为精神病人,但书中有时表达为“神经病”。大概是因为徐訏师从汪敬熙先生,将生理学与心理学结合过于紧密,喜欢将心理学问题以生理学角度考虑。后文中亦有类似情况。处处感到特别的兴趣,我请一位教我们神经病理学的苏教授为我介绍一个可以供我研究的实习的地方,他就介绍我到西郊一个天主教的疯人医院里。”俞医生在那里看到了杨秀常。俞医生注意到秀常过分整洁,便向其家人求证秀常是否洁癖,小说并未详作解释,其实有所隐喻,从心理学上看,过分整洁意味着这类型人性格优柔寡断、谨小慎微、对自己要求过分严苛,严重者可发展为强迫症。从故事发展看,这与最终悲剧的发生有密切关系。俞医生还向秀常家人询问家族遗传史,发现“没有神经病的遗传”,也了解到秀常婚恋正常,这使俞医生大感困惑。俞医生用许多物品试探秀常,发现他对其中一首歌有较大反应,俞医生便以该歌曲询问其家人从而洞知秀常内心世界之一隅,即他与爱琳的往事。小说无暇揭示俞医生举动的心理学渊源,其实,从荣格的情结研究中可以找到根据。荣格说,语词联想测验中,当刺激词与病人心中一些不愉快的事物联系时,病人的反应时间会延长,这些刺激词往往潜藏情结[6]。但杀妻及患病谜团尚未解开,因此俞医生通过催眠术深入探求,在催眠术施行中,俞医生与秀常对话,还让秀常之妹冒充爱琳套秀常的话,终于解开秀常杀妻及患病之谜,一切皆因秀常嫉妒爱琳与秀纲的亲密关系。心理学认为,精神病患者在分裂状态下对致病原因无意识,但在深度催眠下却可回忆和述出,在意识到和述出后,病人自知力会恢复或部分恢复[7]。鉴于秀常强迫性地认为其脑中的某条神经是杀妻凶手,俞医生便在院方配合下假装对秀常施以手术将那条神经切除(俞医生平时也在做鳗鱼神经移植试验),同时施以安慰剂,秀常逐渐痊愈。多年后,秀常向“我”吐露当年患病杀妻之因,他因忙于工作而未能陪伴爱琳,于是爱琳与秀纲走近,这使他感到嫉妒,连做梦都在为此困扰,但为大家庭和睦长期忍耐,没想到竟在梦中实施杀妻暴行。为远离危机,秀常离开大家庭环境,降低事业追求陪伴新人。《婚事》全方位探讨精神病诊治,体现了徐訏对相关领域的谙熟及对人类精神健康的关怀。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950年,当时沉寂半世纪的催眠术在国际上“复活”不久[8],可见徐訏对心理医学进展十分关注。
此外,小说《过客》《自杀》《炉火》等逼肖地描写了变态心理。徐訏绘写变态心理时,并不从旁观察而是富有理性,在《炉火》《彼岸》中,他探入病人内心,绘写迷狂精神状态,呈现出爱德华·蒙克画作般风貌。
二、犯罪心理剖析
徐訏小说中通常用弗洛伊德学说解释犯罪心理,“人的个体是一个随时可以发疯犯罪的动物”“杀人强奸一类事情往往只在自我与本我冲突之中,由毫厘之差因本我不被约束而爆发”[9]。如小说《父仇》中,“我”自称是一位“研究犯罪心理与变态心理”的学者,从事“访问囚犯的工作”,仿佛是徐訏的自述。
小说《杀机》中“我”与遥敏均是文质彬彬的人,却因三角恋产生杀机。作为丈夫,“我”对妻子晓印与好友遥敏的私情感到愤恨嫉妒、尊严受损,但尚未发作。一日火灾,晓印慌乱中披上“我”的大衣不顾儿子和“我”去救遥敏,一念之恨使“我”将长梯抵在遥敏窗上:“我”要堵住出路让晓印与遥敏同赴黄泉。与此同时,遥敏误将披着“我”的大衣晕倒在烟雾中的晓印认作“我”,也在一念之恶中将门关上:他要让“我”在外面葬身火海。最后晓印葬身火海。事后“我”与遥敏一同为罪行追悔,我们均是一时本我吞噬自我,因此遥敏反思应张扬超我,他说:“我们人性的成分只是神性与兽性,有的神性多,有的兽性多。但是是人,就不会完全是神性,也不会完全是兽性的,不过如果我们不知道崇扬神性,兽性随时会伸出来的……如果一直听凭兽性发扬,神性也就会逐渐隐没的。”
徐訏还注重犯罪人格分析。小说《杀妻者》中,通过“我”对杀妻者“他”外形的观察,将“他的脸有无情的冷酷”表达出来。他说算命者对他的命运有所预见,小说正以此暗示其人格及先验性与犯罪间的某种联系。随后他向“我”讲述的杀妻故事印证:他因富有而被妻子蓓华的女友笙英算计,笙英骗他说蓓华有外遇,他从此冷酷对待美丽善良的蓓华致使其自杀身亡。笙英顺利骗取他的感情,又和情人一起鲸吞他的钱财。当他了解实情后,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在精神功能轻微损伤的情况下杀死笙英及情人。小说《投海》的中心事件是余灵非杀死出轨妻子,但小说并不就事论事,而是花费大量笔墨表现余灵非看似无关的心理世界,体现徐訏对犯罪心理的理解。从看似无关的心理世界中,了解到余灵非曾在内地坐牢,到香港后一切皆幻成空,他对现实不满,心境苦闷,在麻木中变得极端个人主义。通过心理描写,可看出余灵非杀人并非完全出于冲动,很多时候他极其冷静,杀人后不后悔、不难过、不害怕,对人生无甚留恋。如此刻画是徐訏有意而为,意在暗示,余灵非的人格已在过往经历中变成反社会人格,“灵非”二字即含此隐喻。
徐訏说“一个人的犯罪,往往与他的某种严重情结有关”。犯罪心理学认为,当情结磁性充分作用时,情结便具备与自我抗衡的能力,甚至“吞噬”自我,刺激个体情结将导致个体情绪、情感急剧变化,从而对犯罪动机的动力产生影响[1]。小说《旧神》中,微珠第二次杀人因“怨恨被弃”“恐惧被弃”的情结受到刺激。微珠的犯罪心理被颇有心理医生潜质的自己剖析出来。她分析:被前男友程先生抛弃后,心里就埋下怨恨的种子。此后遇到崇拜她、尊敬她、爱慕她的刘推事,刘推事的态度使她人格尊严觉醒,亦将原本“怨恨被弃”的种子浇灌成蓊郁大树,尊严觉醒使她更强烈地感到当初被程先生抛弃是莫大耻辱。从此,微珠处心积虑地准备报仇,并如愿杀死程先生。出狱后,出于“恐惧被弃”心理同时与多名男子交往。后来她与人结婚,再度面临被弃危机,在“怨恨被弃”“恐惧被弃”情结支配之下,将丈夫杀害。微珠虽然对自己的犯罪心理洞若观火,但完全无超越性视角。徐訏为此设置角色“我”,“我”作为微珠老友,曾在她失恋时劝说:“恋爱不是神圣的,谁都可以变;谁的变都是有她自然的理由。这决不是有什么好与不好的道德成份在里面。当然不变的坚贞的爱情比较美丽。但美丽是自然的,不能勉强。”但固执自私的微珠未能发展出合理的防御机制。小说《炉火》中,叶卧佛杀死爱子美儿的行为动机更复杂,“恨女子”“望子成龙”情结在犯罪中的作用也更复杂。小说中具有心理医生眼光者是叙述人,绝大部分篇幅均在回溯叶卧佛“恨女子”情结的形成。当叶卧佛遇到父子二人均爱恋的女子韵丁时,因“恨女子”“望子成龙”情结而实施虐待。当然,也因韵丁爱美儿让他深深嫉妒,这份阴暗被他用现实因素文饰。最后,当美儿将他文饰的面具拆穿,说要背弃他、抛弃寄望的事业与韵丁在一起时,叶卧佛受到强烈刺激拔枪将儿子射杀。究其因,叶卧佛心中交织“爱美儿”“望子成龙”“恨女子”“爱韵丁”等复杂情结,这些情结受到美儿强烈且全面的刺激,以致叶卧佛瞬时崩溃。
三、正常人格心理剖析
美国心理学家赫根汉说:“人格的最正确解释来自于全部理论的合成而不是某个单一理论或范型”[10],因每种范型各有侧重,范型间可形成互补。徐訏小说中运用了多种范型的人格理论。
小说《英伦的雾》与《笔名》侧重剖析人格的理性、情感、直觉、感觉维度。《英伦的雾》中“我”是位具有心理医生思维的学者,认为人格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亦是个体特质,对此观察贯穿始末,“我”以己度人,指出:“冷眼观察对方的情感与人格,是萨芝的专长”——萨芝是小说中另一角色。“我”将人格置于社会文化环境中考查,在英伦的雾中思考“有人说伦敦的雾使英国民族有冷静远见的特性……”,“我”认为西班牙人“带着西班牙的情热”。“我”持续观察其他三人(包括萨芝)的人格。小说伊始,“我”体会妻子的感性冲动并因此疏离,观察新结识的西班牙青年与妻子一样的感性冲动,譬如通过青年的画作分析人格“布局取材以及大胆色彩地运用,表示他是一个热情爱新奇的人,但是线条方面有许多地方太取巧一点,不够工夫”,也将西班牙青年追求妻子的浪漫举动看在眼里。后来,西班牙青年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我”将此归因为人格需要,“致死原因是他工作的热忱与勇气”。“我”对已成为西班牙青年妻子的前妻说:“他太富热情,他要刺激,他要震动,他要在晴天白日之下,听一声霹雳,他每天期待,寻觅,这是他爱你的缘故,也是他致死的原因。假如他不去找战争的刺激,他也会厌倦你的爱情。”“我”分析英国女子萨芝的人格,说:“英伦的雾把英国的女子熏陶成冷静,沉着,涵蓄,敏见,远识,不失足,不莽撞,不后悔,无热情的动物。她是这个典型的代表。”总之,小说通过“我”揭示人格迥异,可归结为:西班牙青年与“我”前妻是情感型人物,“我”与萨芝是思维型人物,并暗示相反人格组合或是相同人格组合皆非理想婚姻。
小说《笔名》中,同样具有心理医生组合的文学编辑“我”关注新朋友金鑫夫妇的人格。接触中,“我”发现金鑫故意戴着精致而文质彬彬的人格面具面对妻子与社会,妻子映秀亦如此。二人对婚姻生活均感不满。“我”从金鑫偷偷写的小说中发现其人格在极端理性之外有着极端野性与极端感性的一面;“我”在阅读映秀秘密诗集时发现她灵魂的疯狂与自制,“我”从她匿名的文艺评论中又发现她人格中理性而渊博深湛的一面。在“我”看来,他们人格相配,只是某些部分被压抑,因此“我”想帮助他们卸除人格面具,但因金鑫逃离而失败。总之,这两篇小说旨在人格分析,体现荣格人格类型理论,还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影响,与一般作者的性格刻画迥异。《婚事》中除俞医生外,“我”也具有心理分析能力,“我”认为风趣活泼的秀桢与占有欲极强的事业狂人俞医生绝非佳偶,“俞医师的爱与这个风致是一种不能调和的矛盾”。后来“我”又设想:假若秀常——同样是占有欲极强的事业狂人——是女人,那么与俞医生倒般配。心理学家认为,同中有异的人格搭配最佳。如凯尔西认为“同中有异”是:“同”指“以相似交流方式为基础”,即双方同以抽象或具象作为交流方式特征;“异”指“不同的工具使用原则”,即一方倾向于合作的做事方式而另一方倾向于独立实用的做事方式[11]。荣格认为,想获得“互补”效果,须具备一个前提,即对对方差异无排斥感[12]。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在徐訏小说中亦被大量运用,试举几篇为例。小说《巫兰的噩梦》中,“我”是位文化学者,始终在剖析自己与他人人格心理。看到儿子女友帼音很像亡妻时,便思考儿子是否有恋母情结。随着故事情节展开,“我”逐渐反思自己具有“红痣情结”:起初“我”因变种巫兰花的两点红联想亡妻的两颗红痣,因此尤其钟爱巫兰,后来发现理性的“我”看到帼音的红痣竟情难自禁,于是作精神分析“我也读过一点关于心理学的书,难道我下意识中,竟有这种奇怪的错综(错综即情结)”。最后,在能量发泄与反发泄的相互作用下与具有亡妻影子的帼音拥抱在一起,酿成儿子自杀惨剧,事后他反思“好像自始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步步逼我走进这可怕的综错”。总之,“我”对人格本我层面中情结对人的操控有清醒认识,这是对欲望的精细反思。小说《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里,“我”是心理医生助理,对自我或旁人展开人格分析已成习惯。比如“我”从白蒂超乎常人的感召力觉察她人格中特有的权力意志,“我”还为白蒂祖母——一位振兴大家族的强悍女性展开人格遗传学分析,“是她祖母的遗传,她祖母有丰富的生命力。在她的画像之中就显着这种无比的魔力”。比如有次“我”心境失衡写了一封不够替人着想的信,当“我”醒来重读信件时感到十分羞惭,这一体验使“我”反思:“好像这封信是别人在揭发我心底的私藏。这些私藏,如果不是经心理分析专家的揭发,连我自己都无法反省出来。”这正是“我”反省人格中超我与自我的冲突。小说《灯》中,“我”是位作家。抗战期间被带到日军司令部刑讯,仍不断叩问自身人格心理。“我”被投入牢房时看到有人衣裳单薄,便将大衣盖在他身上,孰料此人拥着大衣长眠不醒,其间“我”饥寒交迫期盼他速速死去,这一体验使“我”反思自己并非出于高尚人格帮助人,只是出于“道德的本能”,即人格中的超我。敌人为逼供施加重刑,“我”多次想供出情报,但每当要供认,脑中或眼前就闪现两盏强烈的灯,使“我”当即昏厥。“我”自由后,便去考查昏倒是否因过强灯光或超大压迫刺激,发现并非如此。最后得出结论:“这实在是我心理上对自己保护的一种机能”“在我心里正是有一种传统的力量在控制我的供认,所以即使在我意愿供认的时候,或在我无法支持肉体的刑痛而想供认的时候,我心理的自卫机构就使我突然晕过去了。”这正是前述“道德的本能”即人格中的超我控制自我,产生道德焦虑,使自我无法畅行,自我发展出防御机制,造成“我”的昏厥。总之,小说中的“我”具备弗洛伊德学说知识并据此分析心理。
徐訏观察人格心理时还运用阿德勒“自卑感”与“补偿作用”理论。阿德勒说,成为人就具有自卑心理,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因为人初始生存均要完全依赖于成年人,儿童会感到与依赖的成人相比极其无能,人就是带着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长大,自卑感在有的人那里起到激励作用,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成为障碍。小说《父亲》中,莉莲不敢与来自内地的“我”结婚,因母亲是“根植香港的葡萄牙人的小圈子里的香港人”。母亲与一个内地人姘居生下莉莲,因身份殊异二人最终没有结合。“我”认为莉莲有自卑情结,“她的心理,一定受她幼年时父母不正常爱情与生活对她的影响”。显然,自卑感在莉莲身上产生了障碍作用。阿德勒说,人在生活或心理上难免有某些缺陷,致使某一目标无法实现,但人有欲念采取各种方法补偿这一缺陷,以另一目标代替失败的目标,以求减轻、消除心理困扰,这便是“补偿作用”——一种普遍心理现象。小说《江湖行》中,周也壮在如云舒卷的体验中反思人生与人格,其自我剖析颇具阿德勒眼光:“第一我要考验我的组织能力,这好像是补偿我在青年运动中做别人的政治傀儡的损失,第二我要恢复我贫穷中流浪的能力,第三不用说,在我下意识中,我要在江湖中寻找失去了的葛衣情”“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只是对于过去自己行为的补偿与报复,上面的三种,第一种是对我学校生活的补偿,第二种是对于舵伯对我经济支持的一种反抗,第三种则是对于我过去葛衣情的一种情感的报复。”[13]另外,徐訏小说中人格演进常由敏锐的“我”揭示。小说《英伦的雾》《不曾修饰的故事》《结局》《过客》中均有类似表现。
四、结语
徐訏的心理学探索及心理写作与其哲学体系息息相关,为徐訏“多元谐和共生”的哲学体系打下人性论基础——徐訏因此对人性的同一性、相异性看得透彻,在强调阶级性反对共同人性、领袖崇拜的年代,他自觉疏离主流,倡导人人均是具有心理与生理限度的平等凡人而不是神。若读者因徐訏心理小说获得心理治疗及“人人平等、谐和共生”体悟,则响应了他创作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就心理医生写作而言,徐訏以其作品在20世纪中国文坛堪称翘楚。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冰心、余华、冯唐等虽有学医或从医经历身但未研究心理学,故有人将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称为“国内首部心理治疗小说”[14]。发表于1943年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便是心理治疗小说,徐訏可谓中国心理治疗小说创作的先行者。今日,人们对人格心理认知程度大幅提高,但精神危机日益严重,毕淑敏曾言“中国是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地方”[15],因心理医生写作匮缺,徐訏心理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先锋性依然颇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祝复兴.都市漫游者的超验叙事——论海派小说的超验性审美方式[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
[2]刘沁怡.超验:都市里的狂想曲——论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超验叙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3]田建民.欲望的阐释与理性的想象——施蛰存、徐訏心理分析小说比较论[J].文学评论,2007(1).
[4]李卫东.施蛰存与徐訏的小说——人性的书写[J].语文学刊,2013(21).
[5]蒋传红.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双重人格[J].名作欣赏,2012(20).
[6]陈凡龙,关鹏.荣格的情结理论与犯罪动机[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5).
[7]王志超,林举达,刘庆荣.催眠恢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知力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6(2).
[8]徐静.浅析催眠术与催眠疗法[J].法制与社会,2008(34).
[9]徐訏.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10]赫根汉.人格心理学导论[M].何瑾,冯增伟,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
[11]大卫·凯尔西.请理解我[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1.
[12]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荣格心理学纲要[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
[13]徐訏.江湖行[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14]王恒.毕淑敏创作的心理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15]罗敏,毕淑敏.中国是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地方[N].第一财经日报,2007-04-23.
作者简介:冯芳(1976-),女,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思潮与哲理作家。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805(2016)01-0074-07
收稿日期:2016-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