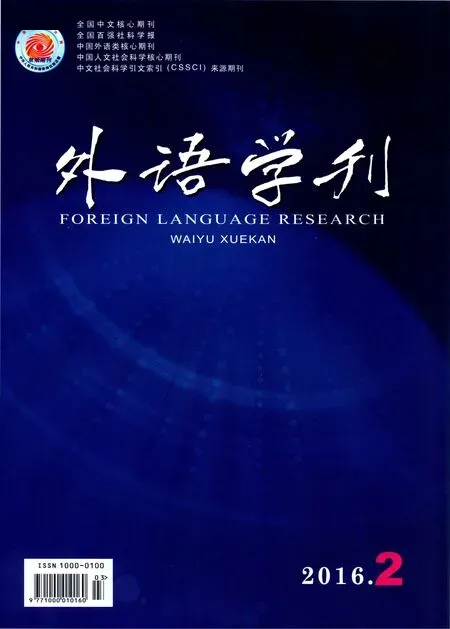后现代美国南方文学的审美特征*
2016-03-06李媛媛
李媛媛 陈 夺
(哈尔滨学院,哈尔滨 150086)
后现代美国南方文学的审美特征*
李媛媛 陈 夺
(哈尔滨学院,哈尔滨 150086)
后现代美国南方文学颠覆“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传统。本文借用后现代主义理论解读后现代美国南方文学的审美特征,认为其特征主要体现在消解的“元叙述”、与历史的“断裂”和追求“无深度感”倾向3个方面。
元叙述;断裂;“无深度感”倾向
美国南方文学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30年代的“南方文艺复兴”早已为这一地域性文学流派烙上鲜明的标签,“南方文艺复兴”取得的杰出成就奠定南方文学的巅峰时刻。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南方文学第二代的卡森·麦卡勒斯、尤多拉·韦尔蒂、威廉·斯泰伦等代表作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这丝毫未减弱南方文学杰出成就赢得的崇高荣誉。时过境迁,“南方文艺复兴”的光环和南方文学的传统尽管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区域文学的发展,但已日渐式微。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时期,60年代之后美国南方文学更多受到西方世界后工业社会的影响,进入美国南方文学的后现代时期。自由市场的高度完善,福利制度的高度发达和社会制度的完备化已然消解之前社会中一些主要矛盾冲突形式,与社会发展对应的是在文化领域中出现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深具后现代特征的文化、艺术和社会现象开始以否定者的身份向传统发难。反叛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这是一种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这种对传统审美模式的颠覆在后现代主义美国南方文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后现代美国南方文学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消解的“元叙述”、与历史的“断裂”状态和追求“无深度感”的倾向3个方面。
1 消解的“元叙述”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把追求人类自由解放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追求真理的叙事称为元叙述,这些元叙述在一切的话语当中占据优先地位,是占据主导权、拥有权威性的话语,是支撑西方世界的客观或普遍真理。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在知识领域进行着革命性的变革,现代性的“元叙述”即“宏大叙述”已经失败,现代性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已经消失。学者或知识分子不再是“元叙述”的掌握者,而只是有限的专家。利奥塔把后现代表述为一种精神和价值:解构“元叙述”(或宏大叙事),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冲破旧范式,藐视限制,追求不断变化。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破坏性的,当代文化世界里的每一个元素都受到它的影响,文学、美学、建筑、哲学、音乐、舞蹈、电影和摄影,没有哪一种文化形式能够逃离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当代美国南方文学显然接受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理查德·福特、安妮·泰勒等当代南方作家的作品中无不体现这样一种解构“元叙述”的倾向。这种对元叙述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南方文学消解“地域观念”或称为“地方观”的艺术创作本源。
后现代之前的南方文学离不开深深植根于南方人内心的“地方观”。美国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南方往往被历史学家认为区别于其它地区。南方作为种植园经济的产物具有农业理想主义、白人贵族统治等鲜明的特征。南方人引以为傲的除了主流社会中专属于贵族阶层的优雅礼仪和人才辈出的南方文学恐怕再无他物。由于农业经济的落后性,人口的流动性不明显,人们世代生息的南方这片沃土成为南方作家忠于自身血统、审视自己内心、抒发自己情怀的有效手段。对于大多数“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来说,南方的意义远远大于地方本身。“地方的意义对南方文学的影响当然远远超出空间的范围——它是一个特殊的场景。”(丹尼尔·贝尔 1992:98-99)随着农业占主要地位的经济形式的瓦解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南方”已经丧失原有的精神指涉、情感认同和归属功能。一体化进程使得南方被改造、被同化,当代的南方文学也顺应潮流地解构其曾经辉煌的“地方观念”,不仅作品的场景和题材疏离“地方观念”,一些作家也离开南方,寻找新的写作沃土。
后现代时期的美国南方小说家理查德·福特著作颇丰,以《体育记者》和其姊妹篇《独立日》为读者熟知。福特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居无定所,漂泊在浮华的现实当中。福特的作品颠覆后现代之前的南方文学传统,浓郁的“地方观念”已然消逝,南方不再是作家及其作品精神和知识的源泉,消解“地方观念”才是指引其航向的明灯,忠实于“地方”的信念并不能给南方文学带来新的生机,“我当时是想离开南方……我得离开这里以拯救自己,重塑自我”(Brooks 1983:6)。福特甚至声称宁愿做一个失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愿做一个成功的南方作家。
安妮·泰勒自认为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人,并且被归类为南方作家。这样的归类源于一个事实:泰勒成长于南方并且在南方接受教育。但是安妮·泰勒本人质疑南方这一地域性标签的实际意义,她认为将美国划分为不同区域的想法本身就是主观的、片面的、不合理的;南方人不应固守过去不放,期待美国还有可以辨认的区域。对于大多数后现代时期的南方作家来说,南方不外乎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已失去其情感的牵挂和文化的内涵,作家们呈现的是南方意识的崩溃而非“地方观”的延续。
后现代时期的南方文学消解区域意蕴的同时,也消解南方文学的“元叙述”,即传统南方文学中具有权威性的“宏大叙述”模式。现在的南方作家显然更主张跳出区域界限去寻求更广阔的艺术表现力,这与他们的前辈们的想法背道而驰。福克纳的18部长篇小说都以南方为背景,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离开过那个“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消解“地方观”的后现代南方文学似乎将整个世界都纳入其创作的范畴,但其艺术创作的维度不免有些狭隘,深度不免有些肤浅,失去风格鲜明的地域特色的南方文学是否还能存在也正是评论界关注的问题之一。
2 “断裂”的历史
南方文学拥有浓郁的历史色彩,传统的南方文学作品尤其是南方文艺复兴一代的作品都具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尽管“南方文艺复兴”的作家缺乏一定的组织和共同的艺术创作主张,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并将历史投射到文学创作中。他们相信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进程,对南方历史尤其是美国内战历史的反思能够帮助人们恢复或重构记忆和历史,以抵御现代化过程的步步进逼。
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在更为根本的方面抛弃历史意识,把自己置身于与传统、连续性等的告别之中,从而使自身处于与历史的“断裂”状态。与历史的“断裂”状态在后现代南方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证明。后现代时期,南方文学的历史观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的审视历史、珍视历史的态度转变成一种与历史“断裂”的状态。历史叙述过去并作为一个连续且连贯的体系的功能被后现代时期南方作家无情地解构。“笼罩在历史上的神圣、权威的光环被驱散,其曾经拥有的指导和象征价值在被抽去……历史的客观性以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真实反映过去的可能性被质疑。”(Lyons 1996:59)
理查德·福特的作品体现出当代人们认为过去已经消亡,过去根本不存在的观念。美国南方评论家奎因曾指出,“福特的小说在拒绝基督教和历史的后现代场景里展开,基督教和历史对于它的南方前辈曾是那么重要”(李杨 2006:30)。《体育记者》是福特的代表作品,也是他成功把握时代脉搏、把握读者阅读心理和审美需求的佳作。该作品的主人公巴斯克姆拥有和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昆丁相似的经历,他们都离开南方,前往北方,但巴斯克姆却没有像昆丁那样站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审视历史、重塑自我,而是选择以一个无根的形象存在于与历史的“断裂”状态之中。巴斯克姆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可以传承的东西,曾经有过的家庭业已解体。形影相吊的巴斯克姆在福特的笔下斩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历史的连续性在他的人生中彻底断裂,他陷入无根、孤立的现在瞬间。“谁的历史能揭示很多真谛?在我看来,美国人过于强调过去是定义自我的方式,这样做会是死路一条……多数人的过去并非很精彩,你一旦准备好,他就应该变得索然无诶,解除对你的控制。”(Guinn 2000:119) 传统价值观的削弱和认知方式的变革是后现代思潮涌入南方的必然结果。巴斯克姆对于过去的看法真实地反映出以福特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南方作家的历史观:探寻现在生活瞬间的意义和价值,不须追寻过去,只须拥抱现实。
以短篇小说见长的梅森承认在一定的方面自己是一位南方作家,但同时也阐明自己是“南方文艺复兴”的反叛。她善于描写快餐店、高速路、购物中心等当代消费文化的场景,她的笔下多是当下南方的生活状况和为了追赶现代化的步伐而隐退历史感的普通人。梅森曾说,“我不能肯定旧南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不怀念过去……时代在变化,我的兴趣是书写现在的故事”(Mason 1988:37)。人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南方,现实赋予人们的意义远远超越传统南方文学中怀旧的情绪所能赋予的意义。后现代南方文学对于历史的重新定位、思考和颠覆正是后现代主义孜孜以求的,唯有质疑并解构以往的历史才能紧紧抓住现在,“断裂”的历史或许正是后现代时期南方文学唯一的出路。
3 追求“无深度感”的倾向
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的逻辑填平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转而追求无深度感或平淡感”(牛宏宝 2002:753)。平淡、浅薄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这种平淡摒弃现代性文化为了追求深度而形成的独特的探索性手法和技巧,阻碍艺术创作的有机统一原则,以便使其失去深度。
在哈瑞·克鲁斯的作品中关爱变得荡然无存,满眼皆是怪诞和狂野。这种怪诞不同于奥康纳时期的怪诞,奥康纳的怪诞意在用冷漠的叙述风格造就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借以重塑人们的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和价值观。克鲁斯小说里的人物完全失去道德意识,社会行为规范被无情的践踏,人物只依靠欲望和本能支配着行动。巴瑞·汉纳的作品也使用哥特式的艺术创作技巧,但较之福克纳的哥特式创作方式不免显得无深度感。汉纳本人也承认其中的差别,他认为福克纳是以哥特式的创作方式处理悲剧,而他本人只是希望将故事处理得荒诞不经,以这种后现代式的“嬉戏”元素达到滑稽可笑的效果。失去道德严肃性和庄重性的人物带给读者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汉纳的怪诞和幽默缺少具有统一性的价值体系的支撑,也就失去南方文学黄金时期的磅礴气势和伟大的人文关怀。福特的作品多以第一人称叙述,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居无定所或被家族抛弃。福特描写离婚、情感变化往往几笔带过,甚至用轻松的语气描述本该大悲大喜的事情,具有一种与我无关的疏离感和无深度感。南方文艺复兴时期和后现代时期的南方文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制造、突化情节冲突,后者淡化情节,试图从平常琐事中发现文本的意味。
与“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相比,后现代时期南方文学摒弃广泛深刻反映南方重大社会变革的创作理念,避免对其先辈们为之奋斗并极力维护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颂扬。后现代时期南方文学叙述的是生活的一个微小的侧面或日常生活的表层,呈现的是肤浅的人物甚至是颠覆道德的人物,也很少对人生、伦理道德进行深入思考。老一代南方作家关注道德意识的建构和重塑,而后现代时期的南方作家更倾向于书写这种意识的崩溃。
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文学流派,而是一种文化状态。后现代时期的美国南方文学在文学主题和写作风格上的转变不仅仅关乎文学领域内的变革,在后现代的审美模式中,读者体验到不同于阅读南方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审美感受。后现代时期的南方作家在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解构“南方观念”这种宏大叙事模式,使南方文学鲜明的地域特色一去不返;历史的本质和功能在后现代南方文学领域受到质疑;“无深度感”的主题、情节的选择和文风的处理方式更是从本质上印证后现代南方文学的巨变。在读者和评论家看来,具备如此后现代审美特征的南方文学似乎难以再次书写南方文艺复兴的辉煌,不免令人感伤,然而 “非同一”、“消解”、“断裂”和“多元”这些关乎后现代审美的词藻带给南方文学的或许又是它的新生。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三联书店, 1992.
李 杨. 美国南方文学后现代时期的嬗变[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牛宏宝. 西方现代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Brooks, C. Southern Literature: The Past, History, and the Timeless[A]. In: Castille, P., Osborne, W.(Eds.),SouthernLiteratureinTransition[C]. Memphis: 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Guinn, M.AfterSouthernModernism[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ppi, 2000.
Lyons, B. Richard Ford: The Art of Fiction[J].ParisReview, 1996(140).
Mason, B.A. An Interview with Bobbie Ann Mason[J].SouthernQuarterly, 1988(2).
【责任编辑孙 颖】
OntheAestheticFeaturesinPostmodernAmericanSouthernLiterature
Li Yuan-yuan Chen Duo
(Harbin University, Harbin 150086, China)
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postmodern period has subverted the great tradition in the Southern Renascence. With the help of postmodern theo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stmodern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the reversal of metanarrative, disruption to history and pursuit of depthless tendency.
metanarrative; disruption; depthless tendency
I106.4
A
1000-0100(2016)02-0147-3
*本文系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后现代美学视阈下的‘美国南方文学’研究”(2014B068)的阶段性成果。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2.028
定稿日期:2015-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