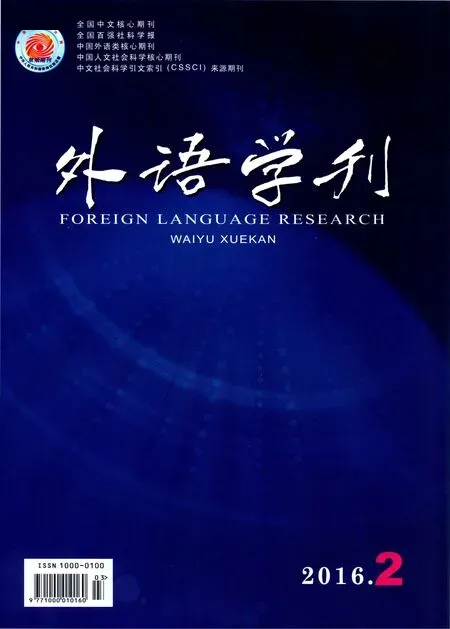和合翻译理论的哲学之思*
2016-03-06戴玉霞刘建树
戴玉霞 刘建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 710071)
和合翻译理论的哲学之思*
戴玉霞 刘建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 710071)
本文从哲学基本原理出发,重点以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切入点,探讨和合翻译的本质,旨在深化对和合翻译的理解,为翻译研究增加新的思考路径。
翻译哲学;和合翻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1 引言
综观国内翻译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引进大量西方翻译理论,包括奈达、纽马克、雅各布逊、巴尔胡达罗夫、巴斯内特和勒菲维尔等一大批学者的译学论著。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译论的消费者(吴志杰 2011:5)。西方译论发展到今天,与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是一种在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能动的革命反映,是一个不断由发展中的无数相对真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江治刚 李军花 2006:62) “哲学问题是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Newmark 2001:132) 可见,将翻译的认知上升到哲学高度是揭示翻译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于是,本文以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为进路,追问究竟何为和合翻译之本体,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翻译以及何为科学的和合翻译研究方法等问题,从而证明和合翻译理论的理据性。
2 和合翻译理论阐析
和合翻译理论以张立文创立的“和合哲学论”为理论依据,“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文明中多元素、多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变异过程中各种要素、元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合(张立文 2006:32)。目前,钱纪芳(2010)、吴志杰(2011)和张从益(2009)等已经从某些层面论述从和合学途径进行翻译研究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力图将翻译涉及的多种要素有机地融合起来:纵向上,从翻译的审美主体入手;横向上,从翻译的审美客体入手,提出“和合翻译”的新构建思想,认为和合翻译是融合“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的人文价值时空态、生生不息的创作过程。那么,首先要弄清楚翻译主体和翻译客体这两个要素的范畴与特征。对于翻译而言,它是一项错综复杂的活动,涉及很多因素,主要包括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等。从美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的审美主体首先是译者,其次也包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承担者,要了解并理解原文作者、分析认识原文文本、了解原文读者的审美体验、考虑译文读者的审美心理和接受程度,并最终生产出一个自己较为满意的译语文本,因此译者可谓翻译的绝对主体。作为创作主体的原作者和译文读者则是翻译的相对主体,因为他们既是认识理解活动的主体,又是被认识和理解的对象。文学翻译的审美客体首先是文本(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其次是文本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等要素,其中文本是整个客体系统的核心,是直接客体,其余方面是翻译审美活动的间接客体。了解这一点,下面来看和合翻译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来重新进行理论定位的方式。
“和合学”提出“人文价值时间”的概念,认为人文精神及其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时间,是“自强不息”的人文时间,是“革故鼎新”的价值学时间,其中“往古”、“现今”和“将来”三维序态互动互补,既冲突、又融合,构成“纵向维度”的时间链(张立文 2006:6)。针对这一概念,那么在翻译这种人文精神创造过程中,同样涉及译者启用三维序态的生生过程:有冻结的既往过去的“往古”序态的在场,也就是译者与原文作者进行对话的过程;有“现今”序态的在场,也就是译者与文本人物的对话,通过参赞化育的方法将其思想表达出来;同时还有等待美好词语将其表达出来的“将来”序态的在场,也就是译者与译文读者对话的过程,译者通过想象构建一个虚拟的生生道体的过程。因此翻译是审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呈现出的三维序态的互动互补的既冲突又融合的“纵向维度”创造过程。纵向地看,翻译是在时间维度上的和合过程,即译文要符合时间的3个序态的要求。在这3个序态中,译文实际上分别是3场对话的结果,这3场对话是不断冲突、不断融合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和合过程。新的译文就创生于这个不断和合的过程中。
而后,“和合学”又给出“人文价值空间”的概念,认为生存活动空间的中西文化互动互补,融合冲突,大体可命名为“横向维度”的空态,这便是中西之所以能平等交往参赞化育的原因。正如我们所知,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人类通过长期的交际活动又形成文化,由此可见翻译活动是一种涉及语言转换、文化传播的交际活动(戴玉霞 樊凡 2013:111)。除语言与文化维度外,更进一步地说,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就是艺术维度的转生。如刘宓庆指出,“在文学翻译中,审美再现所要表现的,是原文的内容情志美,语言形式美,句子修辞美,篇章结构美。由此可见,一切翻译的审美再现都集中于3个问题:第一,就语言层面而言,原文中的各种形式美如何模仿?第二,就文化层面而言,原文中民族化的语言表达如何保留?第三,就艺术层面而言,原文中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关系如何再造?”(刘宓庆 2001:53)。因此,翻译是在一个“语言维”、“文化维”和“艺术维”3个“横向维度”之间互动互补、融突和合的创生过程。翻译在“横向维度”要满足3个层面的对话需求。这3个层面涉及到“语言层面”、“文化层面”和“艺术层面”。要满足3个层面的对话需求,审美主体(译者)要与审美客体(文本)之间进行3场对话:汉英语言层面的对话、汉英文化层面的对话和汉英艺术层面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平等交往、相互融合、相互触发,进而产生新的译文。
可以看出,和合翻译是融合“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的人文价值时空态的生生不息的创作过程(戴玉霞 樊凡 2013:110)。
3 和合翻译理论的哲学理据
3.1 和合翻译本体论
(1)和合翻译本体论:考察20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研究,本体论在翻译领域里已经从阙失走向错位。例如,语言学译论认为“翻译是双语的语义转换”,文艺学译论认为“翻译是原文的艺术再现”,文化学译论把翻译定义为“再现原著文化的语言表现”,多元系统译论把翻译定义为“文学、社会多元系统的互联互动”,交际学译论则认为“翻译即交际”(胡庚申 2004:33)。其实这些理论研究的都是翻译的本质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究其原因,这些论者对存在的把握局限于经验领域,把自己所感知的翻译对象破格晋升为“本体”, 其实质是仅仅把译学系统中的某一研究对象当作整个系统的本体论存在。质言之,这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开拓多维翻译研究的方向,产生多元性研究局面,是把本体论放到一个非本体论的道路上去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这时本体论的错位就不可避免。
那么,究竟什么是翻译的本体,首先要考虑“存在”这个因素,因为只有存在才会有本质。而“存在”不属于经验范畴,是思辨范畴里的内容, 经验之中的东西不是“存在”而是“在者”。这一点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观点不谋而合。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追问将“存在”与“在者”混为一体。他认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只能通过“在者”才能显露出来。可见,这个“在者”并不是一般的“在者”,而是特殊的“在者”,即“此在”(人的存在,或人在面对“眼前的世界”中“上手”事物中的存在),因为只有“此在”才会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以及具体物象的意义(冯文坤 2009:2)。毫无疑间,海德格尔诠释学的核心概念是“此在”,并以“此在”为基础。同时,“此在”又包罗万象,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此在”自己的存在,意义正是在理解过程展示出来的(海德格尔 1996:47)。他认为,“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本体论;它从此在的诠释学出发,而此在的诠释学作为生存的分析工作则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向之归的地方上去”(同上)。所以,现象学反思对一切存在的追问,这种追问隐藏不露,然而却渗入一切存在者之中,意思是说,“此在”总是我的存在,但又不是一个被实在化的有限形体或被仪式化的先验主观之我(冯文坤 2009:导论4)。据此,冯文坤提出,“根据存在论来看待翻译,我们发现翻译具有生存本体论的意义”。所谓“翻译的生存本体论”,就是从研究译者的现实生存活动和生产方式出发,来领会和揭示翻译存在的意义(冯文坤 2009:11)。那么,对于和合翻译而言,不仅具有“生存本体论”的种种特点,还具有“和合本体论” 的特征,具有双重本体论的意义。
(2)和合翻译本体论的生存本体论特征:海德格尔的“此在”之于翻译的意义在于:在翻译过程中,源语世界要经过译者的摆渡使之从可能世界通过主体的认识实现自己的“客体化”,因此,源语世界只有触碰译语世界时才能找到其出场的可能性。在触碰过程中,即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个人生存的“此在性”得以再现与表现。通过翻译,译者立足于自己的“此在”,向源语世界敞开,使译语世界与源语世界发生聚合与变异性诠释。换言之,源语世界与译语世界彼此是被撕裂的时间性存在,被撕裂的时间性存在构成它们各自远游的出发点,构成彼此欲求对方和向对方运动的始基,由此出发踏上一条走向对方的浪漫历史之旅(冯文坤 2009:17)。
对于和合翻译而言,从“人文时间态”的角度来看,也就是纵向维度上来看,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按照人文时间的序态依次出场。首先是原文作者通过对生活的感受、个人的生活经历或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与理解,用自己的笔触以文字形式形成原文,然后则处于“隐身”状态;紧接着译者出场,译者则以“有”和“在场”的状态与原文作者对话,将原文作者的固有历史性存在变成超历史性存在,与“此在”的译者变成一种“共在”;紧接着,译者与译文的读者对话,将读者含纳在一个“此在”的新时间概念地域,再现读者的“此在性”。也可以说,从“人文空间态”来说,也就是横向维度上来看,包括主体(译者)对客体(源语世界)从语言、文化和艺术维上的一个认知过程。译者犹如一个摆渡者,将原文世界摆渡到“此在”——译者之“此在”,译者从“此在”出发,结合各种因素(包括译者的认知理解力、经验和双语表达能力等),创造出原文的来世生命,即译文。也就是说,译者赋予原文以生命本质,把它的非在场性转化为在场性,从而进入译语世界的此在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弗洛伊德所讲的“被欲望的对象”,彼此欲望,彼此唤醒,彼此移入对象之中(冯文坤 2009:40)。
由此可见,和合翻译认为,在时间维度上,译者通过对话与交流实现原作者与读者的此在性的再现;在空间维度上,主体与客体通过对话使原文出离于自身,通过译文使其生命得以延续。因此可以说,和合翻译具有生存本体论的特点,通过对话的方式,使源语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间与空间相互作用中的地域,而这一地域是超历史的,因此也是崭新的、不再保持原貌的文化创造与积累。总而言之,源语世界的意义必须借助译者的“在场性”才能得以显现,译者负责对原文进行理解、阐释与选择,演绎出源语世界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从而生发出读者的文学生存空间。就是说,只有在生存论的视域里,过去才能孕育着现在并繁衍着未来,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实现根基的回归与还原(冯文坤 2009:40)。
(3)和合翻译本体论的和合本体论特征:“事实是,任何一个存在物之出场或显示,都是以不可穷尽的不在场的东西为根底,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就是以‘隐蔽’(‘遮蔽’)为根底。”(张世英 1999:91) 意思是说,任何事物的构成都是由在场的与不在场的构成,前者是有,是对后者的遮蔽,而后者是无,是前者的根基(刘华文 2008:53)。对和合翻译而言,源语世界遁隐于“无”,译文彰显于“有”。译文始终在原文“无”的撑托下,在暗中与原文有着密不可分的融汇契合。然而,在此融合的过程中,译者的“此在”与“他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那么如何化解种种冲突,就出现和合的要求。这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说:“芸芸众生,皆因差分而有分殊,又分殊而有冲突,冲突而有融合,融突而有价值创造”(张立文 2006:63)。在翻译这种人文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就是主体对其生存的译文世界进行思考的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活动。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每个译者超越自我进入他者的世界,为源语世界筹划出未来生命的可能前景。换言之,创作主体超越主体和客体因为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与分离,达到主客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正如张世英认为,“哲学乃是教人超越(不是抛弃)主客关系,在更高的基础上恢复到主客融合的整体,亦即从宇宙整体的内部体验到物我(包括人和己)两忘的境界,这就是最高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存在”(张世英 1999:49)。因此,对于和合翻译这种主客相融合、创造和合生生道体的过程,其和合本体的特点不言而喻。
3.2 和合翻译认识论
翻译要解决最基本的问题,除了本体论的问题,即翻译是什么;另一个涉及翻译的认识论问题,即翻译如何运作。关于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与创造,认识活动的目的,是获得对客体本质和规律性的知识,即真理。在这里,主体指具有思维能力的进行着实践的人,客体指主体通过实践所作用的对象(黄勤 2006:5)。那么,从哲学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一种认识活动和认知过程。在这种活动中,译者是这个活动中的认识主体,其作用对象是源语世界,因此,源语文本就是认识的客体。主体在反映客体时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因为译者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背景知识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融合,最后综合成每一个译者独特的认知结构和认知方式,从而对主体的认识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译者自身的结构、能力与状态将直接或间接制约认识(翻译)的发生、发展及其成果(孙伟平 1995:46)。然而,客体对主体反过来同样有着制约作用。即主体在认识和改造客体时,总是要受到来自客体方面的种种限制,主要表现为:主体的认识和实践必须从客体的实际出发,不附加任何主观成分,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主体活动必须遵循客体本身固有的规律性,否则归于失败;主体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必然受到客体内在矛盾程度的制约,客体内在矛盾暴露到什么程度,主体的认识和实践就达到什么程度(黄勤 2006:6)。可以看出,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译者在面对原文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认识客体进行筛选、加工和整合,从特殊中发现普遍,从现象中揭示本质,从有限中把握无限,表现出一种能动性与创造性。而创造性活动是人所特有的活动,只有通过创造性的活动,人才能化隐性意义为显性意义,并且化事物的形态、结构和属性为意义和价值。这种说法可谓与“和合学”中关于创新的说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张立文认为和合的根基与源泉不在于形相的差分,也不在于冲突融合,而在于人类文化的智能创生或价值创新,这是和合学的根基与灵魂。因为有所创新,才能有所超越;有所超越,人类文化才能得以前仆后继地向前发展。因而人类的生命智慧和自然智能的道德觉醒,是和合生生的“动因”,主体的价值创造是和合生生的“动力”(张立文 2006:120)。然而,译者所具备的创造性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无限度地任意发挥,它应该建立在原文语言、译文语言和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受到原文本的基本内容即客体和原作者这一主体因素的制约,在遵循一定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不断逼近对于对象的客观真实的认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也就是说,译者对原文的认识应该是基于心灵的应和,译文应该是物我之间的和谐统一。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融入原文,才会有所触动而感发,在激发中,达到主客相融、物我相和、物与神游的境界。
3.3 和合翻译方法论
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有力保障。我们认为“和合方法论”可用于和合翻译这种人文精神的创造活动,成为其实现和合生生道体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法。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种指导方法。
其一,“和合生生法”。所谓“生生”,指新事物、新生命的不断化生。“生生”是一个动-动结构,前一个“生”作为动词,指“使……生”或“让……生”;后一个“生”字是状态动词的名物化用法,指生态系统的天然生机或天地万物的生长化育(张立文 2006:2)。那么,对于翻译而言,海德格尔说道,“源语世界是非在场性的,是寂静之言,寂静之言必向人(译者)运作,必由寂静之音向有声之音的译语世界生成”(海德格尔 1996:143 )。刘华文说,“翻译不是把原文中的存在之物,原文中的‘有’被强行拉进译入语中成为译文中的‘有’。翻译是一个生成过程,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化生转化过程。这种转化符合所有生成转化规律”(刘华文 2008:56)。这种生成的本质在于其超越性,即超越现实的、在场的东西,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融合生生为一个整体。即过去的在现在中潜在出现,未来的是现在的展开和预设。这种化生与转化改变翻译中时间上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分裂,其实质是为原文抵达译文铺平道路,使两者的“有”与“无”在转化生成中达到圆融洞澈,互补互济。那么,原文从“无”到“有”,来到译文的生存世界中,必定与译文在语言和文化很多方面发生一定的碰撞,这就须要译者启动智能创造性的活动,通过在场的与不在场之间的融通,实现新生命的化生。如此说来,在和合“生生”方法论的观照下,对于所谓原始文本就不再只是所谓的历史或传统,或一堆完成的、过去的材料,它们以某种方式独立存在,适遇而生,蓄势待发地等待译者的领会和实践而获得来世的生命。那些“历史”的文本保存作者对他生存过的世界的感悟与经历,具有一种生成可能性。和合译学的研究应该把重新演绎译本的这种曾经实际存在的生成可能性作为中心任务。其实质是要求译者要以开放的、不断生成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曾在的文学资源,而不仅仅把它们看作已经完成的、封闭的文学体系。换言之,“和合生生”的翻译观要求译者要努力挖掘蕴涵在原文中的生机,敞开自己,以开放、动态的积极心态,在顺应翻译本质规律的前提下,综合处理好与原文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走向翻译的“和合生生”之途。
其二,“和合意境法”。王国维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王国维 1986:23)。可见,在文学创作中,意境是作品的灵魂,没有意境的作品,是无灵魂的躯壳。意境缘于情,是人类情欲的喧哗和升华的表现,是文学作品的最高成就。张立文认为,和合艺术审美境界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融突中,“无我之境”超越“有我之境”而化生;所谓“有我之境”是以艺术审美主体生命情感、智慧投入其中,“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物便是艺术审美主体心灵情感的呈现;所谓“无我之境”是艺术审美主体超越自我生命情感、智慧,解脱了我执、物执,达到无我无物的艺术审美自由之境(张立文 2006:284)。对于和合翻译而言,审美主体在翻译过程中追求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最高层次之“无象之象”,是中国哲学所说的“道”、“无”,是一种最接近宇宙本体和形上意味的最高境界,即“思与境偕”、“物我两忘”、“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是超越有限时空并获得物我同一、心灵无限自由的审美境界。译者的感情寄托和精神世界同宇宙万物节律同一,我之“思”消融于物之境,达到“了”的艺术境界,也就是所谓的“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境界(戴玉霞 2011:108)。
4 结束语
本文以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线索,阐发和合译学理论的构建意义。和合翻译具有生存与和合本体的双重属性,翻译由于其双重本体论而获得一种揭示翻译存在的价值。没有翻译,原文的生命就会被阻隔或消失,只有通过翻译这种创造过程,才能维持不断更新,源语世界的生命才能得以延续。而和合是原文内部生命力的活力,每一次运动都蕴藏着“生生”的动力,是原文出离于自身,是自身的不断涌现,是生命的外化。其中,“生生”是源语生命力的活力,构成源语走向译语的内在的生发机制。“生生”是一个动态、开放和宽容的理念,创生是多样的、变异的,是一种生生不息之途。
人在翻译过程中,既是认识主体又是实践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同时又有一定的限度。和合翻译是以和合为其终极目标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的“是者”依次出现,包括翻译主体因素(原文作者、译者和读者)和翻译客体因素(原文与译文),通过主体间的对话以及主客间的对话,创造出新的译文,也就是新的和合体(即译文)过程。
“和合生生法”与“和合意境法”是和合翻译致力追求的方法与目标。“和合生生”所追求一个非惟一的、非绝对、非一元的多样、多元要素的和谐通融的和合本真状态,从而实现各要素间“并育并行、不害不悖”的圆融无碍。也就是说,在主体与客体的和合过程中,做到心物交融,物我合一,从而产生和合境界的艺术作品。这种创作必然是意与境浑、人与天通、铢两悉称,在不即不离,似与不似之间,让读者感受到极具神韵的和合生生道体。
戴玉霞. 飞鸿踏雪泥 诗风慕禅意——从接受美学视角看苏轼诗词翻译中禅境的再现[J]. 外语教学, 2011(5).
戴玉霞 樊 凡. 和合理论关照下的苏轼禅诗英译研究[J]. 外语教学, 2013(3).
冯文坤. 翻译与翻译之存在[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冯文坤 万江松. 由实践哲学转向理论哲学的翻译研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胡庚申. 翻译选择适应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黄 勤. 蔡元培翻译观的认识论诠释[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江治刚 李军花. 翻译本体研究的哲学思考[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2).
刘华文. 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钱纪芳. 和合翻译思想初探[J]. 上海翻译, 2010(3).
孙伟平. 主体认知结构及其对认识活动的影响[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1995(12).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吴志杰. 和合翻译研究刍议[J]. 中国翻译, 2011(4).
俞宣孟. 本体论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张从益. 和合学途径的翻译研究[J]. 外语学刊, 2009(3).
张立文. 和合哲学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张世英. 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Newmark, P.Approachesto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Snell-Hornby, M.TurnsofTranslationStudies[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责任编辑谢 群】
APhilosophicPerspectiveonHarmoniousIntegrationTranslationTheory
Dai Yu-xia Liu Jian-shu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This paper intends to be reflective of the theory of Harmonious Integration Translation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ttempts to clarify what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Translation is, and aimis to probe a new wa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philosophy; Harmonious Integration Translation;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H059
A
1000-0100(2016)02-0098-5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和合学关照下的苏轼诗词英译研究”(13K132)的阶段性成果。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2.019
定稿日期:2015-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