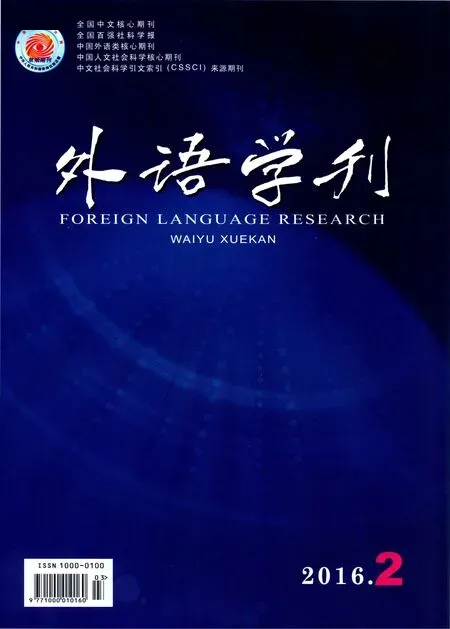委婉语的意向性解析*
2016-03-06李凯
李 凯
(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 150040)
委婉语的意向性解析*
李 凯
(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 150040)
委婉语的认知操作是主观意向性制约下的意象选择和意义同一化的活动。委婉语的操作特点是间接意象指向并可替代直接意象,意向性通过属性连通的程序引领意象的解读和表征。属性连通和同一是将间接表达解读为直接表征的关键,使两个意象在意向性控制下具有同等意义。委婉语的实现程序通过意象的择取、属性的连通和意向性的指导3个步骤完成。
意向性;意象;属性连通;委婉语
1 引言
根据《中华现代汉语词典》,委婉语解释为:话语态度温和,不使用尖刻词语,不直接表达意思,但又能传达本意的一种语言现象。这里关键有两处:(1)委婉语是替代语,语用特征是以此代彼,是间接言语行为;(2)委婉间接之意可被解读,可作出直接表征,如何做到委婉语间接表达能传递且可解读出直接话语意义应该是委婉语得以全面解析的认知明确。
委婉语(euphemism)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研究走向与语言学中诸多学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委婉语的构成机制和语用规律方面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说明委婉语依然羁绊在修辞、语义和语用的阐释,且各项探索都主要针对委婉语组构和交际效用角度展开,未能从认知和心智理论深度作出机理阐明和操作明晰,研究精细度和宽泛度都有待深入提高。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结合心智哲学的相关理论,换尺度换角度地对委婉语从意识、意象(image)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等解释层面做出较为详实的机制分析和步骤说明。由于委婉语的基本特点是以间接表达替代直接表征,厘清二者之间同一性的实现手段和连通性(alignment)的发展路径是大势所趋。间接“替代”直接的说法蕴含转喻的基本理念,是认知转喻思维操作的前提和根基,说明委婉语中存在转喻性因素作为连通途径;间接与直接在意义上“同一”(assimilation)的结果说明间接和直接之间存在主观和必然的互通操作程序。这势必将委婉语的实现视为主观意向性制约之下的“间接=直接”。关键要解读二者如何等同的认知理念和认知操作。主观意向性如何随附给间接表达,且又如何激活相同意义的直接表征,其内在机理和操作步骤势必给予澄清。
委婉语从认知语用角度可以诠释为以“表达”(expression)含蓄指向、暗示“表征”(representation)的间接言语行为。间接表达是意向性控制下意图表述的内容,它涉及这样的过程:对于某事物、事件、形态等先入为主地形成种种知觉意象,再经由转喻性质的连通路径或经由格式塔认知原则的转换,提炼成为精准的与表述内容相关的意象及意向性,即表征;连通过程所形成的意象和意向性内容,通过意向性态度的转圜突显成语言表达式。我们有理由认为,委婉语“间接=直接”的实现方式是:在意向性调控下的意象连通,基础和手段为转喻性质的类-属联结。委婉语的意义天生固有某种不确定性,须要依据认知主体生成的意象和意向性对间接表达映射的内容给予主观解析。委婉语间接和直接的认知和心智机制是意向性对意象连通的制约作用,连通步骤则是以属性为核心的意义同一过程。
2 委婉语操作的特征——间接意象指向直接意象
委婉语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使人感到痛苦即敬畏、恐惧、羞耻、不适等各种消极心理反应的事物,信息组织者(说写者)有意地运用语音、语义、语法等手段对这些事物非直接的语言或言语表达,从而避免使信息组织者本人、信息理解者(听读者)、话语涉及的第三方即信息的潜在理解者感到痛苦(邵军航 2007:120)。委婉其实未必都是为了抵御消极心理而故作善言的表达方式,更应理解为在特定语境中说话人针对可能引起的各种心理属性及意象而有意运用与这些事物不相关联乃至截然相反的非直接语言表达,属于语用学研究范围。但是委婉语与语用学合作原则却背道而驰,是曲折迂回地避开某种表达,采用和借助婉转方式以取得更符合礼貌原则的交际效果。委婉语的操作结果是间接的表达指向直接的表征,作为后者解读的依据,形成意义和表征上的“间接=直接”。根据对修辞性言语的认知研究,委婉语的基本语用意图是对外界的认知(Sperber, Wilson 1986/1995:233-234)。直接和间接如何等同以及如何同一的全新认知是委婉语解读的根本所在。
委婉语并非是对客观真实事物的写照,而是大脑中对特定事物融入主观成分而形成的意象,直接和间接意象之间达成意义的同一是委婉语的实现和操作方式。所谓委婉语中的“意象”指客观事物的物象在心智中的构念(construct)。“构念”作为科学哲学概念,是只存在于主体大脑里的一个理想物象,不是真实存在的对象(MacCorquodale, Meehl 1948:55)。“理想物象”只能依据主观化调控以间接的表达方式传输出来,理想和真实物象的差异是委婉语得以委婉间接表达的本源。意象在大脑不断留存、提取和记忆与之相关的外界物象的属性过程中生成,意象能够操作的精髓实质是事物属性的连通,从而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改写和加工。物质被人类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和反映(列宁 1984:128)。
委婉语的直接表征和间接表达都是意象的主观性映射,也可以说委婉语中存在直接意象和间接意象两种意象。对外界事物纷繁的物理属性进行思维改写形成前者,对个体突生性心理属性进行暂且组构构成后者,物理和心理属性之间必然存在意义等同的契合点。间接意象指向直接意象来自于认知主体对二者具有相同属性的主观认定,是反思的活动。委婉语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特征,也无法体现语言本身的意义,委婉语是语言使用的特征,或者说是语言使用者根据需求将主观意向赋予语言使用的特征。语言的具体载体可以根据交际过程中提出的目的和任务赋予词与公认词以不同的内容(李洪儒 2013:13)。语言使用的前因后果皆源于认知主体对外界客观事物形成的以属性为中心的各类感觉,继而将感觉改造为意识,升华为意象,提炼为意向性,意义的意向性实际上是认知主体将自身的感觉和感受随附给物象的主观用意。
有关意象的“图画理论”(picture theory) 认为,“感受”在大脑里以意象的形式呈现(Mitchell 1995:9),而“意象”是对感官所感觉、感受和意识到的事物、事件及物象等进行反思的结果。反思的心智活动表现为神经活动,意象是靠神经细胞映射而成,映射的结果是在心智产生意象(Bergen 2005:255-260)。人类在认知外界过程中,首先产生知觉和视觉,继而日积月累逐步生成意象。例如看到鸟在飞,产生视觉方面的拓扑感觉和感受,再依据知识储存探搜相关意象的记忆,将鸟的视觉感觉与其他事物的感觉进行映射,再经由格式塔转换,实施联想行为,呈现出风筝也可以像鸟那样翱翔的意象。对两种不同意象进行留存、比较、提炼和加工之后得出二者共同具备的属性“飞”,与这个属性相关的所有客观意象和理想意象也会根深蒂固地留存于大脑,必要时自然产生连通,使得鸟和风筝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同一属性下的同一意象功能。这也就是委婉语中间接可以指向直接的成因。
感受的形成和属性的得出在操作路径上具有相同的程序,但是对物象所形成的具体感受不尽相同,如鸟可以翱翔,也易受伤。除了主观的认知因素不同,即使对同一个事物实施表达时,意向性的语用意图也会因物象属性庞杂而生成的临时感受和表达需要的不同而不同。鸟作为“公认词”在主观性调控下完全可根据其不同时空的感受和语用意向性作出不同的表达。语言使用中鸟的意象势必与相关意象,如风筝,产生大脑天然连通,且可将风筝意象的常规和非常规属性特点强加给鸟,作出借此说彼、似是而非的委婉表达。尽管如此,认知主体依旧可以顺着某属性联想到某意象,在语境调控下,再由此意象连通到其他意象,这是委婉语可借一个意象表征另外一个意象的基本动因。意象和意向性是委婉语操作的关键,意象具有连通性,而意向性具有专属性。意象可解释为对外界物象的心理表征,且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虽异却同。对表征的支撑理据是认知主体对外界不同事物生成的有关信仰、欲望和期待的心理属性(attribute)和思维阐明(predicates)(Ramos 1998:305-345)。鉴于此,心理表征是心理属性作用的多维结果,心理属性可作为委婉语意象操作的根据地。
“思维阐明”解释为认知主体在感觉和感受过程中生成的种种意象。同一感受的意象可不同;同一意象的感受可相异。感觉和感受随机生成原始意识(primary consciousness),这是意图借语言进行主观语用意图表达时的自然倾向和必经之路(Edelman 2003:5520-5524)。例如古代将“着火”称作“走水”,着火的感觉使个体产生需要用水的原初意识,着火在思维阐明过程中逐步形成比感觉更进一步的感受,且选择一个相关的意象将感觉和感受传递出来,并受控于灭火的意向性,即“走水”。意象在认知主体意向性主导下进行的反思意识(reflective consciousness)是心智对原初意识经过大脑加工之后的演算(Revonsuo 2010:81)。意象在观察外界事物过程中经由感觉和感受而生成,并在意向性和语用需要等条件引领下完成主观突显(highlight)。人们通过五官获得感觉,或者通过某些感官的互通获得移觉,经过大脑具有映射能力的神经物质将感觉或移觉得来的视觉、听觉等的物象映射为感受,其结果在心智产生意象(徐盛桓 廖巧云 2013:5)。“非词语性的意象是在心智上呈现与词语的概念可以对应的那些意象”(Damasio 2010:60),非词语性的意象是语言表达的先验性载体,在语言原初意识的干预下,以属性为依据对意象发挥持续留存、连通和转化,形成表面约定俗成却又触类旁通的特定语言表达手段,委婉语就是一例。由此委婉语意象可分为两大类——逻辑上的直接意象和非逻辑的间接意象,例如:
① “巴图鲁教的是箭术,皇阿玛给的是舐犊之情。皇阿玛还是偏心你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恰恰是皇阿玛的这一偏爱,到使臣弟成了无用之人了”。(流潋紫《甄嬛传》)
“无用之人”是间接意象,原本是一无是处之意。但是果郡王才华横溢,直接意象并不在此,根据当时的语境和君臣双方的意向性,所表征的是无弑君夺权、争夺江山之意。不争夺江山是无用之人的属性之一,是无用的下位类意象之一,二者具备产生连通的条件,在需要时由后者激发,可互通使用。直接表征是不争夺江山之人,这是直接意象;在属性同一的条件下,意象连通之后形成间接意象“无用之人”。间接意象与直接意象之间语义上有所偏离但却依然息息相通。委婉语中无用之人往往会触发认知主体脑海中两个意象,一是有关一无是处之人的规约性意义,是经验积累形成的一种感知,是根据知识组构集合而固化成的意象。而委婉表达的直接意象却是不争夺江山,扩充、细化无用的间接意象意义,在认知语境中完全跨越认知主体对无用的逻辑性理解,由此激活对委婉语直接意象意义的非逻辑性心理属性的探寻。委婉语的间接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语言用于解读现实的逻辑规约,展现委婉语中主观意象构建态势和程序,是主观意象搭建的另外一层心智经验。这种逻辑和非逻辑的差异性如果没有语境和意向性等因素的控制,则无法领会直接表征的用意所在。对外界物象的性、状等产生的逻辑概念是直接意象,通过属性留存、连通和转换过程而生成的相关意象则为间接意象,委婉语通常是属性基础上的相关、相似意象的双重表达。
3 委婉语操作的中介——意向性
意象是委婉语直接和间接的连通因子,而意向性是指引意象取向的激活因素。认知主体以自身主观意向性为指导,选择相关的意象而形成委婉语的间接表达。意向性是意识的主观高阶,是对意象属性提炼的语用,也是意象构造时的指路明灯。例如:
② 不是本宫不喜欢香料,只是嘱咐你,有些香料用的不当只会伤身,你懂得用香料,便应知道其中的厉害,春天了,连猫也要叫春,其他猫就会叫,可是本宫的松子却喜欢扑东西。(流潋紫《甄嬛传》)
对于“扑东西”的理解不完全取决于人类意识对它进行的综合或改造,更多的是凭借主观感觉和感受,形成与“扑东西”相关的种种意象,经过对“扑”意象的功能属性进行提炼和加工,意向性和表达适用度也随之明确。所谓意向性表现为意识活动中对对象的注意、过滤、选择、表征时的心理状态,并呈现判断、评价、表征的功能(徐盛桓 廖巧云 2013:5)。意象是意向性作用的对象,意向性直接引发意象的产生、注意、过滤、选择和表征,意象得以彰显的根本原因是意向性对话语表达时的意象选择所起到的导引和构建作用。委婉语意向性的研究除了涉及意向性的主观化参与因素以外,还要考虑意向性的对象、内容和实施。委婉语在表达中会调动恰当语境下能够配合表达用途的各种相关意象,形成必要的语言形式和内容,意象的调用受控于主观意向性运作。意向性的内容是选择何种属性作为直接和间接意象的关联点,完成二者的联想和连通。意向性的实施是在属性匹配基础上的直接和间接意象的同一化过程。
意识活动使认知主体产生千变万化的感觉和感受,这种感觉和感受在属性作用下形成不同的意象,因为人类的思维推理运作始终以属性为核心考量。类-属思维模式(category-property alignment)是人类的默认性、根本性的惯性思维,是天生固有的且不断发展进化。两岁半的儿童就完全自然而然且自发性地、恰当地形成并凝练指类思维。(Gelman,Goetz,Sarnecka, Flukes 2008:156)属性成为链接两个意象之间的纽带,也是意向性运作的直接诱因,由于某属性对于某些意象的适用性和连通可能性,才使意向性能够指引意象的择取。意象可以有不同的属性,但是两个具有相似属性的意象会产生必然的联想和连通。委婉语的成因就是凭借属性的异同而形成既相关且不同的意象感受和意向性内容,从而生成语言表达。例如:
③ 李燕: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刘震云《手机》)
女人出门产生的意象和感受很多,传统守规矩的女人意象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通常不出门。“出门”的心理属性是破坏三纲五常,做出水性杨花的行为。委婉语中“水性杨花”当然不便直接表达,于是借助与其具有同样属性的另外一个意象“出门”作为间接的意象表达。属性是意向性的直接导火索,牵制意象的择取。主观化控制下的委婉表达是委婉语的主要意向性之一,从而话语表达方式选择意象不同而属性相同的语言符号。所谓主观意向性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对我们理解语言语义添加一个十分必要的维度(Kemmer 2005:80)。
委婉语在意向性中的概念为:认知主体在认知参数和特定语境的调控下对所处内、外环境做出利己的映射,这决定委婉表达的遣词造句。在委婉这个意向性指引下,对意象构念实施属性归纳、提取和选择的操作过程,这就是委婉语的操作。如“出门”也只是“离开家”的行为、过程和结果等不同部分的转喻性、突显性属性之一,并在此属性基础上以委婉为意向性构筑不便明说的其他意象。“出门”的意象是对其心理属性进行心理估量之后产生的朴素意义上的感受和意象,是认知主体对水性杨花持有的委婉性心理态势。水性杨花心理属性不便明言,因此选择与之同一属性基础上的另一意象进行言说,间接和直接具有意象不同而属性相同的意向性。同一句委婉语中,意向性内容体现意象的千差万别,而意向性态度则体现属性的不谋而合。在意象、意向性的共同作用下,外界物象中各个成分在主体意向性的选择下产生直接和间接之分,且以委婉语的形式登堂入室。
委婉语之所以避开直接表达而选择间接表达,目的是要对委婉语的意象定位进行意向性的主观反应和表征。外界物象经由意识筛选,通过连通和联想形成主观化意象,意象的生成须要对感受进行重建和改造,以及对属性的提炼和明晰。意向性指引意象的生成,且限制对语言符号的选择和表达。人类的感受意识镜像外界物体的影像图画,经由反思的圈限和属性的突显而升级为意象,意象必然涉及与其相关的属性,而该属性也可能是其他意象的属性之一,成为对其他意象进行连通的要点,意向性内容则显现某特定属性基础上的意象选择。例如:
④ 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张爱玲《我看苏青》)
同行之间的妒忌是属性,以此属性为基础生成两个不同的意象,一个是同行,一个是女人。在委婉意向性的制约下,借助相同属性将两类不同的意象进行连通和连接,形成委婉语的间接表达。因此属性是委婉语意向性活动中的主要依据对象,也是意向性引领意象解读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委婉语中不同意象的同一性的属性始终以其恒常存在态势贯穿在意象的产生和意向性的提炼当中。那么意向性的活动应该指在语用意图的制约下,持续提炼不同意象的属性涵义集合,且从中择取其一,作为意象连通的基本点和委婉语间接表达构建的根据地。意向性在委婉语中的使用是针对意象的异同而实施的属性提炼的程序运作。如上文“水性杨花”、“相妒”等皆为意象和意向性活动中的一系列行为、性状的共相属性。由此委婉语的构成是“间接”+“属性”的语言结构,在意义上等同于“直接”+“属性”。属性推理是从听、说双方视角出发的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认知解读,这是以非字面的另一概念(属性)作为话语终极含意,含意和言语行为之间存在默认和非默认的功能关系,但最终以非默认达成默认的形式体现(邹春玲 2014:56)。
委婉语中的意向性运作过程通常要对意象中有关性状、行为和过程等种种不同成分进行属性提炼和加工,再与委婉语中的不同意象进行连通从而构建思维表征和语言形式。“概念和意义尽管经常和图像伴随,但意义和概念的普遍性是对图像个体性暂时性的超越。对意义图像论的超越事实上也就是对感性个体化经验的超越,它揭示出意识中的语言逻辑层面的共相真实性。”(高秉江 2013:82-87) 委婉语的操作要根据主观意向性对外界物象和意象的多重属性进行笼统归纳和有效抉择。委婉语通过其间接表达的运用对外界物象进行主观化的属性披露,对委婉语中涉及的意象进行意向性重造。委婉语具有“间接”+“属性”的认知语用特征,应该纳入认知和语用的研究范畴,需要扩充和修缮的是委婉语如何借助意向性达成属性识别的根据和路径。例如:
⑤ “你怎么那么有出息呀?我还不够你看啊?”“得允许我有审美疲劳吧?”(高璇 任宝茹《我的青春谁做主》)
委婉语间接替代直接的意义和内容本具有不同认知参数和特定语境下的多维意象特征,个体在对委婉语实施意向性认知过程中难免存在歧解。上例“审美疲劳”的意象牵涉到其包含的不同属性意义。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可以把意义结构必需的常体要素界定为词汇意义的核心或基础,它们区分为由种属关系联系起来的两个部分(李洪儒 2011:18)。“疲劳”为一切活动过度的基本属性,是词汇意义的核心也是常体要素,属性是意向性的根基,以此属性连通“不好看”等主观意象形成意向性调控下的委婉语操作。委婉语的意向性使用是属性提炼把握下的认知操作结果。
4 结束语
本文首先说明委婉语存在间接意象指向和替代直接意象的特点,借此论证、确定委婉是存在转喻关系的间接言语行为模式。委婉语采取间接表达的做法是基于意向性对意象牵引和规划的影响,意象性在主观化感受基础上形成,以属性为核心操作而触类旁通,联结其他相关意象,完成委婉语的“直接=间接”的认知操作。委婉语的间接表达是对主观意向性选择的意象进行“间接意象+属性”的生成过程,直接表征则是“直接意象+同一属性”的解读过程。委婉语的操作基本是:首先形成感觉感受基础上的意象,对意象进行加工提炼得出属性,属性连通给其他具有相同属性的意象,根据属性决定意向性走向,再挑选合适的意象进行委婉语的表达。
高秉江. 图像、表象与范畴——论胡塞尔的直观对象[J].哲学研究, 2013(5).
李洪儒. 说话人意义及其结构的研究维度[J].外语教学, 2011(5).
李洪儒. 论词层级上说话人意义的形成因素[J].外语教学, 2013(6).
列 宁. 列宁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邵军航. 委婉语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徐盛桓 廖巧云. 意向性解释视域下的隐喻[J].外语教学, 2013(1).
邹春玲. 言外转喻属性模式的微观操作层面分析[J].外语学刊, 2014(1).
Bergen, B. Mental Simulation in Literal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Understanding[A]. In: Coulson, S., Lewandowska-Tomaszczyk, B.(Eds.),TheLiteralandNonliteralinLanguageandThought[C]. Frankfurt: Peter Lang Publisher, 2005.
Damasio, A.SelfComestoMind:ConstructingtheConsciousBrain[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0.
Edelman, G.M. Naturalizing Consciousnes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Z]. 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3.
Gelman, S.A., Goetz, P.J., Sarnecka, B.W., Flukes, J. Generic Language i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J].LanguageLearningandDevelopment, 2008(2).
Kemmer, S. Emphatic and Reflexive-self: Expectations, Viewpoint, and Subjectivity[A]. In: Stein, D.(Ed.),SubjectivityandSubjectivisation:LinguisticPerspectives[C]. Cambridge: CUP, 2005.
MacCorquodale, K., Meehl, P.E. On a Distinction between Hypothetical Constructs and Intervening Variables[J].PsychologicalReview, 1948.
Mitchell, W.J.T.PictureTheory:EssaysonVerbalandVisualRepresenta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Ramos, F.Y. A Decade of Relevance Theory[J].JournalofPragmatics, 1998(3).
Revonsuo, A.Consciousness:TheScienceofSubjectivity[M]. Hove &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0.
Sperber, D., 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1995.
【责任编辑孙 颖】
TheIntentionalityStudyofEuphemism
Li Kai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40, China)
The cognitive operation of euphemism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image selection and meaning assimilation in control of subjective intentionality. The feature of such operation is that indirect image could be used to point to and substitute direct image, in which intentionality guides the construal and representation of images by way of attribute alignment. The so-called attribute alignment and assimilation is the key to explaining the indirect expression as the direct representation, making the two images having identical meaning in control of intentionality. The realization of euphemism is carried out by three procedures: the selection of images, the alignment of attributes and the guide of intentionality.
intentionality; image; attribute alignment; euphemism
H030
A
1000-0100(2016)02-0083-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言外转喻的加强联想模式构建研究”(11YJC740166)、黑龙江省教育厅教改项目“英语专业阅读课程策略主导-生成认知教学模型构建研究实践” (JG2014010777)和哈尔滨理工大学实践教学环节项目“英语专业语言技能认知教学模型操作实践”(ZHJG52015042026)的阶段性成果。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2.016
定稿日期:2015-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