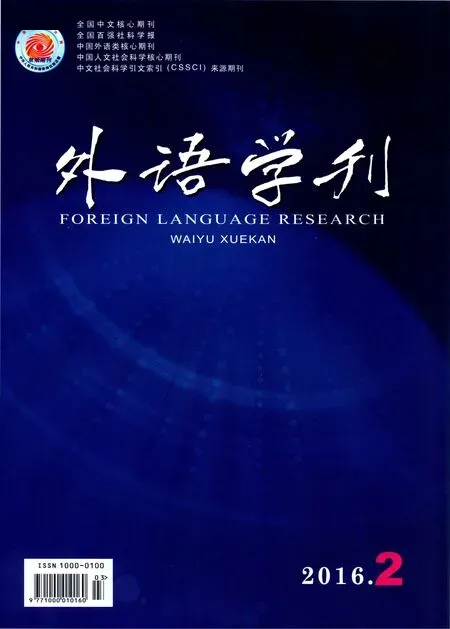语气、功能与句类*
2016-03-06吴剑锋
吴剑锋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30)
语气、功能与句类*
吴剑锋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30)
汉语语法分析中的句类概念来源复杂、内涵模糊,导致汉语句类观在语气、功能、用途和目的等概念间游移不定。本文梳理句类、语气和句子功能3个概念的演变过程、内涵外延以及相互关系,得出结论:语气是基于词汇、句法等多种手段的句法范畴,句子功能是基于作用或用途的功能范畴,句类是基于句子交际功能的语用范畴。而句子的交际功能就是句子标示的言语行为,不同的句类实际上是代表不同言语行为的句子集合。因此,必须打破汉语句类和语气一一对应并循环论证的传统,将句类和语气区别对待,坚持言语行为句类观。
句类观;语气;功能;言语行为
1 引言
汉语句类研究虽起步较早,但汉语语法分析中的句类概念来源复杂、内涵模糊。汉语句类观在语气、功能、用途和目的等概念间游移不定、莫衷一是。由于对句类的性质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从而导致汉语的句类划分陷入陈述句(declarative sentence)、疑问句(interrogative sentence)、祈使句(imperative sentence)和感叹句(excla-matory sentence)的4分模式制约至今仍难有突破,许多与句类相关的语言现象也因此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解释。本文梳理句类、语气和句子功能3个概念的演变过程、内涵外延以及相互关系,重新审视和反思传统句类观的局限性,指出言语行为句类观的科学性。
2 汉语句类概念的演进
汉语的句类概念直接借鉴自英语的sentence type(句类),早期被直译为“句子种类”或“句子类型”,如章士钊(1907/1990:1,14,12,261)、刘复(1919/1990:87-89)、金兆梓(1922/1983:78-81)和黎锦熙(1924/1992:228)等。这个时期句类概念的名称并不固定,而且没有明确的定义,大多只是一些解释性或举例性的说明。直到1942年何容(1942/1985:153)出版《中国文法论》才第一次明确使用“句类”这一专名,并将“句类”直接和英语的sentence type(句类)等同,用来指“依助词所表的语气”区分出来的“语句的类别”。至此,“句类”作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和固定范畴正式确立。
20世纪50年代,综合自《马氏文通》以来各家研究成果的《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简称《暂拟系统》)问世,将句子按语气分为直陈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4类。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大学现代汉语教材均把句类定义为句子的语气分类,把句类的外延确定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
由于作为中学教学语法的《暂拟系统》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的一批大学语法教材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得汉语语法研究中关于句类的主流观点是:句类是句子的语气分类,句类的外延一共包括4种: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
在句类语气说普遍为汉语学界接受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提出句类功能说,主张从功能角度划分句类,如黄伯荣(1958)、朱德熙(1982)和范晓(1996,1998,2009)等。黄伯荣指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主要是根据说话的目的或句子的作用分出来的”(黄伯荣 1958:3)。这里的“说话的目的”和“句子的作用”其实就是句子的某种功能。朱德熙是最早明确提出句类功能说的学者:“从句子的功能来看,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称呼句和感叹句五类”(朱德熙 1982:23-24)。朱德熙句类概念的外延则多出一个“称呼句”类型。80年代中期,3个平面理论主张语法研究要区分句法、语义和语用,并直接将句类定义为“句子的表达功能或语用价值的类别”(范晓 1996:383)。3个平面理论的提出对汉语语法研究影响很大,句类功能说逐渐为人们熟知和接受。
从句类概念的产生和演进可以看出,汉语的句类概念先后与语气、句子功能等概念相关联。由于这些概念的形成路径和理论依据不同,由此也导致汉语句类概念的内涵模糊不清,在语气、用途、目的和功能等概念间游移不定。值得注意的是,与内涵模糊不定、莫衷一是相对照的是,句类概念的外延则相对固定,除极少数学者增加“称呼句”这一类型外,汉语语法学界普遍认同句类的外延包括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4种类型。
3 句类与语气、句子功能的关联
汉语的句类概念和语气概念分别直接借鉴和参照英语的句类和语气(mood)。在分析汉语的句类和语气关系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英语语法研究中句类和语气的关系。
3.1 英语的句类和语气的关联及差异
在英语语法研究中,句类和语气的关联主要表现在部分类别名称的重叠上。由于句类和语气中都有祈使(imperative)类别,因此容易产生混淆。除都有祈使外,句类中的陈述(declarative)与语气中的直陈(indicative)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和误用(Lyons 1995:176)。作为一个形态句法范畴,语气可以在鉴别句类时发挥作用,比如:陈述句中的主要动词典型地带有直陈语气(indicative mood)的形态;祈使句中的动词常带有祈使语气(imperative mood)的形态。但无论如何,句类和语气在类型上都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Asher, Simpson 1994:2519)。英语语法研究通常把句子分为陈述(declarative)、祈使(imperative)、疑问(interrogative)和感叹(exclamatory)4类。前两类和动词的语气相对应:陈述句中的动词是直陈语气,祈使句中的动词是祈使语气;后两类则与动词的语气并无对照关系。(何容 1942:151) 总之,语气是基于动词形态变化和语法意义相结合的句法范畴,主要有直陈(indicative)、祈使(imperative)和虚拟(subjunctive)3种类别;句类是基于句子功能和句法形式相结合的功能范畴,主要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4种类别。
3.2 句类与语气的关联
汉语的句类概念是对英语语气概念的借鉴和参照,并伴随着汉语的语气研究而产生,其从产生之初就与语气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语气研究的副产品,是先有语气研究,再有句类研究。汉语句类与语气的纠缠主要体现为类别和名称的完全一致: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究其原因,既与英文句类与语气在类别名称上的重叠有关(两者都包括祈使类),也与早期汉语语法学界对英语语气和汉语的“语气”的不同解读有关。
刘复认为说话时语气有种种不同,据此可以将句子分为直示句(declarative sentences or sentences of statement)、感叹句(exclamative sentences or sentences of exclamation)、询问句(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r sentences of question)和命令句(imperative sentences or sentences of hortation)(刘复1919/1990:87-89)。刘复首次把句子分类的依据归结为“语气”,从而在句子类型与语气之间构建某种关联。
金兆梓直接把英文的sentence type翻译为“句的种类”,认为句子的分类依据是主词与表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但某个句子的最终归类依据却是句子的语气,并将句子区分为直陈句(declarative sentence)、传感句(exclamative sentence)、布臆句(imperative sentence)和询问句(interrogative sentence)(金兆梓 1922/1983:78-81)。
黎锦熙根据助词所表的语气来区分句类。他把语气分为5类,同时把句子也分为5类:“现只就思想表达方面归纳一切句子的语气为5类: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惊叹句和祈使句”(黎锦熙1924/1992:228)。如果说以前的学者只是建立句类与语气的联系,那么自黎锦熙开始则把句类与语气类型混在一起。这种把句类与语气类型相对应的分析模式对汉语句类及其与语气关系的研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目前,汉语语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大体上秉承将句类与语气联系起来的分析思路,参照英语语法对sentence type的4分法,将declarative sentenc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imperative sentence和exclamatory sentence直接套用过来译成汉语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同时也相应地称为4种语气:陈述语气、疑问语气、祈使语气和感叹语气。(黄伯荣 廖序东 1991:6,胡裕树 1995:314,钱乃荣 1995:192,邢福义 1997:121,邵敬敏 2007:213)
3.3 句类与句子功能的关联
人们从一开始便注意到句类不同于句型,这是因为句型是从句子结构出发分出的句子类型,是纯粹语言内部的事,不涉及语言的使用者,而句类则和语言的使用者密切相关。早期语法研究者认为句类就是句子的语气分类,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句类是句子的功能分类,和句子的作用或用途有关。
早在1958年,黄伯荣指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主要是根据说话的目的或句子的作用分出来的”(黄伯荣 1958:3)。这里的“说话的目的”、“句子的作用”其实就是句子的某种功能。
朱德熙明确主张从句子功能角度划分句类,把句子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称呼句和感叹句(朱德熙 1982:23-24)。
80年代中期3个平面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主张语法研究要区分句法、语义和语用3个平面,认为句类是“根据句子的语用平面上语用价值或表达用途分出来的句子类型”(范晓 1998:2)。从“语用价值或表达用途”角度考察句类,其实也是从句子功能角度考察句类。
4 句类与语气、句子功能的差异
尽管句类与语气、句子功能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和纠缠,但句类、语气和句子功能3个概念的形成路径和理论依据各不相同,由此也决定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语法性质,分属于不同的语法范畴。
4.1 语气是基于词汇和句法等多种手段的句法范畴
在英语语法研究中,语气的内涵可描述为:语气是以句子中动词形态的屈折变化为语法形式来反映说话者对句子判断的心理态度这一语法意义的形态句法范畴(Jespersen 1924:313,何容 1942/1985:150)。在性质上,语气是一个句法范畴(syntactic category)或形态句法范畴(morphosyntactic category)(Jespersen 1924:313; Asher, Simpson 1994:2516),这是因为英语传统语法提取语气的途径是先形式后意义,即从已有的语法形式追寻所表现的语法意义,采用形式决定意义的思路(何容 1942/1985:150)。根据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的严格对应关系,只有通过动词形态变化反映出的心理态度才能称为语气(Booth 1837:124),而通过短语、词汇和语调等手段反映的心理态度则不属于语气。反之,不反映心理态度的动词形态变化也不是语气。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汉语的语气概念甚至可以说比英语的语气还要复杂。既借鉴英语语气、情态(modality)的内涵,又融入传统汉语研究中口气、口吻的概念成分,因而与助词功能、情态类型以及口气等概念纠缠不清,从而导致汉语语气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很模糊。
汉语语法研究中语气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清代的袁仁林,他在解释虚字功能时使用“语气”这一概念:“凡其句中所用虚字,皆以讬精神而传语气者”(袁仁林 1710/1989:11),从而将语气和助词功能联系到一起。马建忠在语法意义上将英汉语语气两个概念的内涵相等同,将其外延区别开来,认为汉语的语气“有二:曰信,曰疑”(马建忠 1898/2000:323)。刘复借鉴英文句类概念,把汉语语气归结为与句子功能相对应的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刘复 1919/1990:87-89)。黎锦熙进而将助词、语气类型和句类3者联系起来,认为语气“各用相当的助词来帮助,或竟由助词表示出来”(黎锦熙 1924/1992:228)。贺阳(1992:59)和齐沪扬(2002)等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情态概念融入语气阐释。
尽管汉语语气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模糊不清,但其属于句法范畴的性质界定却基本为语法学界所认同和接受,只是汉语语气的实现手段不同于英语等动词形态丰富的语言,汉语的语气是通过词汇(如语气词、助词和部分关联词“如果、要是”等)和句法等多种手段表示英语语气的语法意义(赵春利 石定栩 2011:497)。
综上所述,汉语语气是基于词汇和句法等多种手段的句法范畴。
4.2 句子功能是基于作用或用途的功能范畴
句子是言语交际的最基本单位,“句子功能”无疑是语法学中一个最基本的重要概念。顾名思义,句子功能指句子的作用或用途。然而,如果再具体点的话,句子功能到底是句子哪方面的作用或用途?对于这个问题恐怕我们却无法找到一个统一或一致的答案。这是因为,根据不同的依据和标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从国内外现有的一些相关研究文献中便可以体现出来。
国内现有文献中体现出来的句子功能观主要有:(1)句子功能语用说:这类观点着眼于句子语用层面的作用,认为句子的功能指“说话的目的或句子的作用”或“语用价值或表达用途”。持这类观点的主要代表学者有黄伯荣(1958:2)、朱德熙(1982:23-24)、张斌(1998:171-172)、范晓(1998:17)、吕明臣(1999:11-13)和吕冀平(2000:351)等。(2)句子功能语篇说:这类观点从单个句子在一群句子或者一个篇章中的语法地位来讨论句子功能,认为句子的功能指句子在语篇里的地位和作用。吕叔湘首先提出这一观点:“要是按一个句子在一串句子里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按功能来分类,可以分为始发句和后续句”(吕叔湘1990:522)。吴为章(1994:25-48)接受并进而发展这一观点。(3)句子功能综合说:这类观点从句子在话语中的作用或用途角度来讨论句子的功能,认为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子主要有表意功能、交际功能和组篇功能3大功能。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范晓(2009:3-15)。
国外文献关于句子功能较有影响的观点有:(1)布拉格学派马泰休斯的句子功能观,认为句子的功能指信息传递的表述功能。(2)韩礼德的小句功能观,认为小句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可以看出,句子功能是基于作用或用途的功能范畴,而且句子功能分不同方面,句子具有不同层面、不同种类的功能。
4.3 句类是基于句子交际功能的语用范畴
在讨论汉语句类的属性之前,先看看汉语“句子”和英语sentence是否等同,汉语的“句子”是否有不同于英语sentence的特点。
4.31 汉语的句子是语用单位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主张对语言学界影响深远。西方语言学界一般都认为句子(sentence)是句法单位,话语(utterance)是语用单位,句子和话语是对立的一组概念:句子是一个抽象实体,是抽象语言系统的一部分,而话语是实际使用的话语,是说话人用语言系统(如词和句)按一定规则说出来的话语,它们分别属于语言和言语的范畴。
汉语言学界通常将汉语里的“句子”和英语sentence对应。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汉语的句子是言语或语用单位,这些学者主要有吕叔湘(1990)、朱德熙(1982)、姜望琪(2005:10-15)、沈家煊(2007:1-15)和范晓(2009:3-15)等。
朱德熙(1982)的结论是:“确定汉语句子的最终根据只能是停顿和句调”,其这样定义的句子恰恰等于英语的话语(沈家煊 2007:1-15)。
姜望琪详细论述汉语句子不是抽象单位,更像英语的话语,从篇章语法的角度看,也可以说它像语篇(discourse)(姜望琪 2005:10-15)。这是因为,在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研究中,句子已逐渐与话语分离,演变成一个抽象单位,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词的界限并不清晰。而汉语研究特别是对相当于句子这一级单位的研究开始较晚,以至于汉语的句子至今仍是一个具体单位和使用单位,或称动态单位。因此,汉语的句子并不等同于英语的句子,它更像英语的话语。跟句子相当的汉语单位应该是词组,而不是句子。
沈家煊从语法化角度观察句子和话段的关系,认为英语语用单位话语经过语法化已经变为句法单位句子,而汉语的句子还没有完全语法化为句法单位(沈家煊2007:1-15)。换用实现关系和构成关系来说,英语里抽象的句子在话语中实现为具体的话语,而汉语里句子的构成就是话段。
综上所述,汉语“句子”相当于“话语”,和“言语行为”一样都是语用单位,相对于英语等语言来说,汉语的句子和语用的关系更为直接。
4.32 句类是基于交际功能的语用范畴
人们运用语言都是为影响别人的思想、感情或行动,以达到一定的目的。由于说话的目的不同,就会使用不同类型的句子。例如,使用陈述句的目的是用来告诉人们事情是怎样的;使用疑问句的目的是用来向人家提问;使用祈使句的目的是让听话人去做某事。上述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这些句子类型,是根据句子在交际中(说话中)所承担的作用划分出来。由此可知,句类实际上是句子的交际功能类型,即按照句子在交际中的作用所分出的句子类别。
上面我们分析得出句类是基于句子交际功能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而按照言语行为理论者的主张,句子实现或承担的交际功能是说话人通过说出句子所做出的言语行为。塞尔明确指出,“一般说来,通过说出一个句子所做出的言语行为就是这个句子意义的功能”(Searle 1969:1)。按照塞尔的观点,说话者通过说出一个或数个语句来完成一种或数种言语行为,如进行陈述、发出命令、提出问题和做出承诺等(同上:16)。例如:
① 我告诉你,她也一直爱着你。(王朔《空中小姐》)
② 你给我到县里去买馒头!(梁晓声《钳工王》)
③ 我问你,这些日子,城外是不是打仗呢?(老舍《火葬》)
④ 我保证不再出一点声音。(王朔《无人喝彩》)
例①是一个“陈述”,告诉听话者“她”也一直爱着听话者这件事;例②是“命令”:到县里去买馒头;例③是“询问”,询问城外是否在打仗;例④是“承诺”,保证不再出声。
上述这些句子都是说话人言说活动的结果,同时它们又都分别代表一个以言行事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言语行为是这些句子所实现或承担的交际功能。言语行为理论强调,人们说话时就是在实施一个行为。更加精确地说,言语行为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构造出或者说出一个语句标记,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同上:16) 上文我们分析过汉语的“句子”其实相当于“话语”,因此,汉语的“句子”和“言语行为”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从语言角度看,是一个个话语单位(句子);从行为的角度看,是一个个言语行为。这从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这些句类的名称也可以看出来,“陈述、疑问、祈使、感叹”这些术语本身就是言语行为的概念,就代表一种言语行为。
既然句类是句子的交际功能类别,而句子的交际功能就是句子做出的言语行为。那么,句类本质上就是句子所标示的言语行为的类别,不同句类实际上就是不同言语交际行为的句子集合。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句类是基于句子交际功能的语用范畴。
5 言语行为句类观的科学性
人们从一开始便注意到句类不同于句型,后者是从句子的结构出发分出的句子类型,是纯粹语言内部的事,不涉及语言的使用者。而句类则是和语言的使用者即人密切相关,早期语法研究者认为句类是句子的语气分类,因为语气涉及到语言的使用者。
然而,传统句类观存在严重缺陷。这是因为传统句类观以语气为纲划分句类。一方面对句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缺乏科学认识,另一方面,囿于从语气角度考虑问题,把语气和句类混为一谈,将句子的语气等同于句子的交际功能。
从马建忠和黎锦熙以助字(语气词)为纲到章士钊和何容等以句子的语气为纲再到3个平面理论以句子的交际目的或用途为纲,句类划分经历从词法平面到句法平面再到语用平面的过程,可以说,在对句类性质的认识上经历过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然而却一直没能摆脱“语气”的束缚,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目前学界对语气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语气是通过语法形式表达的说话人针对句中命题的主观意识,是对句中命题的再表述,或是表述说话人表达命题的目的,或是表述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和评价等,或是表述与命题有关的情感。句子要实现其交际功能,当然具有一定的语气。然而,尽管语气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句子的交际功能,但是语气并不就等于句子的交际功能。句类和语气不是一回事,因为不是所有语气都反映句子的语用目的,如对命题的态度、评价和命题有关的情感未必和句子语用目的有直接关系,它是一种“内指”的功能,因为它指向句子命题本身,并不针对听话者。例如:
⑤ 他去北京了。
⑥ 他一定去北京了。
⑦ 他可能去北京了。
⑧ 他去北京了吗?
前3个句子都是告诉别人“他去北京了”这个消息,都是陈述句。例⑧和前3个句子的不同在于它不是告诉别人消息而是向人家提问,因此例⑧是疑问句。我们再看例⑤-⑦,它们虽然功能相同,但是表达的说话人的态度和情感却不一样。例⑤是一般的肯定,例⑥表示说话人对命题“他去北京了”持非常肯定的“必然”态度,例⑨则表示说话人对命题“他去北京了”持一种不太肯定的“或然”态度。也就是说这3个句子的语气不一样:例⑤表示肯定语气,例⑥表示必然语气,例⑦表示或然语气。虽然例⑤-⑦的语气不同,但是它们的交际功能相同,都是告诉听话者事情是怎样的,因此都是陈述句。
语气句类观因囿于从语气角度来考察句类问题,要么干脆认为语气只有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4种,要么虽承认语气的类别多达十多种,但认为只有功能语气才是划分句类的依据和标准,功能语气也只严格局限在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4种范围,这样处理的结果自然是削足适履,难有突破。语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句子的交际功能,但是由于语气只是部分地反映句子的交际功能,因此,句子的语气在句类表现上并不充分,以语气划分句类只是找到体现句子功能的片面的而非全面的标记,这种片面的概括不可能穷尽所有句子,因此也不可能得出一个完整全面的、科学的句类系统来。
20世纪80年代,句类功能说开始和句类语气说分庭抗礼,人们开始认识到句类是句子的功能分类,和句子的用途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家分类的依据和标准不同,但所分出来的结果却基本一样,均把句子主要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4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划分句类时无论如何标榜,都无法回避句子的用途,即句子的功能。问题是,句子的功能分不同的方面和层面,句子具有不同层面不同种类的功能。比如,系统功能语法就认为,语言(小句)具有3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篇章功能,语言的这3大功能分别说明语言使用者作为现实世界的“观察者”与“闯入者”的功能以及语言自身“相关者”的功能:概念功能针对客观现实世界、人际功能针对人(话语使用者)、篇章功能针对语言自身。句类和句子的功能相关联,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如果再具体一点的话,句类到底和句子的哪方面功能相关联呢?持句类“功能说”的学者要么不作说明;要么语焉不详,使用“表达用途”或“句子的作用”等比较空泛的概念。这就难免造成理论认识上的盲区和实际操作上的无所适从。其实,人们所说的句子功能,在这里就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或者说人际功能,因为它针对语言使用者运用句子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即如何使用语言去做事(以言行事)。句类名称中的“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这些术语本身就是言语行为的概念,代表一种言语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句类本质上是言语行为的类别。
从语气说到功能说再到言语行为说,人们对句类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进一步接近问题的本质。既然句类是句子的交际功能类别,句类本质上是句子代表的言语行为类型,那么,只有走出传统句类划分的误区,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思考句类划分问题,坚持言语行为句类观,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反映句类的本质。
6 结束语
汉语语法分析中的句类概念来源复杂、内涵模糊,从而导致汉语句类观在语气、功能、用途和目的等概念间游移不定、众说纷纭。本文对句类、语气和句子功能这3个概念的演变过程、内涵外延以及相互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进而得出:语气是基于词汇和句法等多种手段的句法范畴,句子功能是基于作用或用途的功能,句类是基于句子的交际功能的语用范畴。而句子的交际功能就是句子所标示的言语行为,不同的句类实际上是代表不同言语行为的句子的集合。因此,必须打破汉语句类和语气一一对应并循环论证的传统,将句类和语气区别对待,坚持言语行为句类观。
范 晓. 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范 晓. 汉语的句子类型 [M].太原:书海出版社, 1998.
范 晓. 关于句子的功能[J].汉语学习, 2009(5).
何 容. 中国文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42/1985.
贺 阳. 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2(5).
胡裕树. 现代汉语[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黄伯荣.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8.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下册)[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
姜望琪. 汉语的“句子”与英语的sentence[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1).
金兆梓. 国文法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2/1983.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4/1992.
刘 复. 中国文法通论[M].上海:上海书店, 1919/1990.
吕冀平. 汉语语法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吕明臣. 走出“句类”的误区[J]. 吉林师范学院学报, 1999(2).
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第二卷)[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马建忠. 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 1898/2000.
彭利贞.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齐沪扬. 语气词与语气系统[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钱乃荣. 汉语语言学[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邵敬敏. 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沈家煊. 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J].汉藏语学报, 2007(1).
孙汝建. 语气和口气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吴为章. 关于句子的功能分类[J].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4(1).
邢福义. 汉语语法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袁仁林. 虚字说[M].北京:中华书局, 1710/1989.
张 斌. 汉语语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张志公. 现代汉语[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章士钊. 中等国文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07/1990.
赵春利 石定栩. 语气、情态与句子功能类型[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4).
朱德熙. 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1997.
Asher, R., Simpson, J.TheEncyclopediaofLanguageandLinguistics[Z]. Oxford: Pergamon, 1994.
Booth, D.ThePrinciplesofEnglishGrammar[M]. London: Charles Knight and Co., 1837.
Halliday, M.A.K. 功能语法导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Jespersen,O.ThePhilosophyofGrammar[M]. London: Geogre Allen & Unwin, 1924.
Lyons, J.LinguisticSemantics:AnIntrodu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earle, J.R.SpeechActs:AnEssay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责任编辑谢 群】
Mood,FunctionandSentenceTypes
Wu Jian-fe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Owing to the complex origin and obscure connotation, there are divergent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sentence type, which shif-ting among concepts, such as mood, function, usage and goal.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hree concepts: sentences type, mood and sentence function in their conceptional evolution proces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as well as interrelationships.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sentence type is a pragmatic concept in terms of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sentences, which is the speech act indicated in the sentence. Each sentence type is a representative set of different speech a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o beyond the tradition(which leads to a vicious circle) of strictly corresponding moods to Chinese sentence types and to firmly differentiate the two concepts from the speech act perspective of sentence type.
perspective of sentence type; mood; function; speech act
H043
A
1000-0100(2016)02-0071-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言说动词研究”(09CYY032)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2.014
定稿日期:2015-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