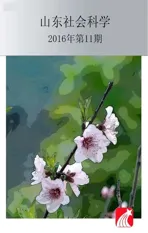论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中的记忆、历史与生存焦虑
2016-03-06许文茹申富英
许文茹 申富英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山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论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中的记忆、历史与生存焦虑
许文茹 申富英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山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其布克奖获奖小说《终结的感觉》中通过追忆往昔表达了对个人记忆与历史的质疑。小说通过对记忆与历史不确定性的探寻,对人类生存现实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道德责任模糊感根源的解构,对生存的对立面死亡的表述,传达出现代社会人类犬儒主义生存状态下无法抑制的生存焦虑。
《终结的感觉》;记忆;历史;生存焦虑;犬儒主义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凭借长篇小说《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Parrot,1984)、《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England,1998)和《亚瑟与乔治》(Arthur&George,2005)曾三次入围布克奖*2002年,曼财团(Man Group)成为布克奖的赞助商,布克奖名称由“Booker Prize”变成了“Man Booker Prize”。因此,有时也翻译成曼布克奖。提名,2011年,作家终于如愿以偿,小说《终结的感觉》(TheSenseofanEnding,2011)获布克文学奖。小说共分为两章,第一章主要叙述托尼和他的几个朋友青年时代的生活,这也是托尼自认为真实的记忆;在第二章中,前女友维罗妮卡的母亲的一封遗嘱使得托尼对其记忆产生了怀疑,这份遗嘱迫使托尼去探寻一些过往事件的真相,他发现了记忆的不可靠性,曾经的生活与自我变得面目全非。这部小说通过托尼的叙述将一个人物从青年到老年的生活与心境表现出来,故事细节的真实性在主人公单方面的叙述之下变得扑朔迷离,故事的情节和结局也是托尼推理的产物,这体现了巴恩斯一贯的对记忆与历史的不信任和对真实的解构。
然而,这部小说在延续前几部小说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之余,还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生存关怀,这一点无论小说细节的真实与否都是无可置疑的。小说通过对记忆与历史不确定性的探寻,对人类生存现实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道德责任模糊感根源的解构,对生存的对立面死亡的表述,传达出现代社会人类普遍的生存焦虑,正如小说题名“终结的感觉”,这种终结的感觉或是结局的意义究竟是何物,人类无法触及,却时时刻刻生活在其阴影之中。另外,从小说的开放式结尾我们得出:人类已不再是最初的被欺骗而昏昏度日,而是洞悉了一切,却听之任之,这是一种犬儒式生存状态,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说:“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是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再是遮蔽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成为建构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 幻象。”*张一兵:《肯定的犬儒主义与意识形态幻觉——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4期。当代作为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与古希腊传统的犬儒主义不同,早期的犬儒主义者愤世嫉俗,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而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犬儒主义者虽然持有嘲讽式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实际却认可官方意识形态,服从于社会权威。事实上,齐泽克并不赞成这种犬儒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竭力维持着事物的表象,而这种表象又是本质性的,就像《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中描述的一样,这种表象一旦被拆穿,整个体系就会崩溃。当代犬儒主义的本质是‘知’与‘行’的分裂”*此观点来源于网络上季广茂教授发表的文章《犬儒主义: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这是现代社会人类精神分裂症的体现,并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无法遏制的生存焦虑。《终结的感觉》中的人们总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屈从于表象而回避真相,因为只有掩饰真相,才能抚平创伤。
一、记忆的不确定性与道德责任的模糊感
巴恩斯在《终结的感觉》中用小叙事的手段解构了记忆这个“个人历史”或是“小历史”的真实性。然而,记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记忆的不确定性与记忆主体及记忆主体的道德责任意识等内在性有什么关系?这种联系与现代社会人们犬儒式的生存意识是否有关联?这些问题在这看似琐碎的小说情节中便能见出端倪,这本小书只有一百多页,却似乎是生活巨大洪流中的一颗水珠,折射出的是广袤无垠的宇宙。
记忆的本质是不确定的,记忆常常被虚构。“这最后一幕我没有真正见过,但是,你最后所记得的,并不总是与你曾经目睹的完全一样。”*[英]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郭国良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小说中处处表现出作者对记忆真实性的无从把握,“这是我最主要的真实记忆……因此这些回忆可能有些个人偏见吧。”(p.35)巴恩斯对记忆和历史的态度,很明显是受到著名学者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的影响,《终结的感觉》可以理解为巴恩斯对弗兰克·克默德的追忆。(序言p.15)克默德在1967年出版的批评著作《终结的意义:小说理论研究》*弗兰克·克默德和朱利安·巴恩斯的这两部作品的书名均为The Sense of an Ending。陆建德教授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终结的感觉》的序言中将克默德的这部作品的书名翻译成《终结的意义:小说理论研究》,刘建华在其中译本中将克默德这部作品的书名翻译为《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TheSenseofanEnding:StudiesintheTheoryofFiction, 1967)中谈道:“在这‘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只会碰见自己’的时代里……我们的和谐的范式、我们的开头与结尾、我们的根据人类的愿望而描绘的井然有序的世界还怎么能满足我们呢?”*[英]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刘建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根据克默德的虚构理论,虚构是理解人类世界的一种方法,然而虚构也常常会无法满足人类真实的欲望。在这里,克默德道出了记忆与记忆主体及记忆主体的道德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即记忆与其他虚构物一样,它们是能指所构成的幻象,其功能是为了掩盖可怖的不可能性的“实在界”,然而这样的幻象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我们,我们总是想穿越幻象、寻找真实,殊不知幻象背后却是一无所有,人们只能将幻象编入现实。
《终结的感觉》中的小说情节与人物在充满模糊感的记忆中展开,情节处处自相矛盾,人物支离破碎。然而小说破碎的情节和模糊的记忆中的人物却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生存焦虑。维罗妮卡到底爱不爱托尼?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维罗妮卡的母亲为什么要把艾德里安的日记留给托尼?艾德里安为什么要自杀?最后的那个傻瓜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些疑问全都留给了读者去思考,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中揭示真相。然而,无论答案如何,巴恩斯邀请读者参与思考的目的并不是要赋予这部貌似是侦探小说的作品一个最终的结尾,而是要使得读者在思考的过程中体会人生的变化带给我们的启示,设定自己站在未来的一点来回望过去,从记忆中体会时间与生存的意义,在人生即将终结的时刻来体会那种终结的感觉。作者在小说中这样描述记忆:“我们认为记忆就等于事件加时间。但是事实远非如此:事实更加怪异。是谁曾说过来着?记忆是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忘记的事情。而且我们理应明白,时间并非显影液,而是溶剂。但是这样理解并不讨好——也对我们无益;对我们过日子并没有什么帮助;于是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p.82)“我有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我早就把维罗妮卡抛在脑后。”(p.83)年老的托尼为了克服自身的生存焦虑,他认为自己与妻子玛格丽特的生活是美满的,而与维罗妮卡的恋爱经历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因此在记忆中删除了关于维罗妮卡的事件,这是为了克服生存焦虑而采取的一种犬儒式自我保护的生存手段。在小说中,维罗妮卡似乎代表了生活的隐秘性、不可知性的一面,而玛格丽特却代表了生活秩序、理性和可知性。然而,托尼在意识中或许认为自己喜欢的是玛格丽特的坦率、真诚与热情,却在潜意识中仍然无法摆脱对维罗妮卡所代表的神秘生活的向往。托尼对于意识形态幻象包裹下的不可能性心向往之,也促使他在维罗妮卡母亲留下遗嘱之后,数次主动与维罗妮卡联系。
在这一情节发展过程中,托尼代表的人类的道德责任意识被展露无遗。托尼最初在潜意识中对有关维罗妮卡的记忆采取的是犬儒式的视而不见策略,也自认为自己是这一恋爱经历的受害者,直到维罗妮卡在寄给托尼的一封信中揭示了:托尼当初在得知维罗妮卡与自己分手并与自己的好朋友艾德里安相恋之后,给他们写了一封无比恶毒的信。这段被托尼删除的记忆让他面对自己的卑劣行径时产生了极度悔恨之情,让他感觉自己也许并不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对待爱情、生活也许并没有什么责任感而言。同时也隐隐感觉自己那一次去维罗妮卡家的“那个令人难堪的周末”似乎另有隐情,维罗妮卡似乎并不是那种和他分手后又上床的对爱情随随便便的人。托尼对维罗妮卡及她的家人抱有偏见,从他对待维罗妮卡的哥哥杰克的态度可以看出:托尼对于艾德里安与杰克的优秀学业十分嫉妒,直到后来向杰克询问维罗妮卡的联系方式时,托尼还是无法放下偏见,海阔天空地想象杰克如今是如何的困窘,因为“用这种方式回忆他,一点儿没让我觉得不舒服”(p.104)。这种嫉妒感来源于“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国家,比起年龄差异,阶级差异更是历史悠久”(p.95)。阶级地位的差异使得托尼在维罗妮卡家人面前十分不自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控制已经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是蕴含在民族文化之中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已经渗透于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中。”*卜建华:《当前社会思潮的传播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托尼在体会到这种阶级差异和意识形态幻象的虚幻性的同时,却视而不见,依然虚构着自己受到不良款待的那个周末的情景,幻想着杰克在现实中遭遇的挫折与失败,这通通源自于人类犬儒式的生存意识和无法挣脱的生存焦虑。在看似平静的生活表象之下是由人们犬儒主义生存法则包裹的无法遏制的生存焦虑,当记忆、现实和历史被完全颠覆,剩下的就是无尽的混沌和混沌状态下人性的扭曲。
记忆的虚幻性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人类道德责任意识的途径,然而就像齐泽克探讨意识形态幻象的悖论性一样,一方面幻象是必需的,在遮蔽不可能性的同时,要接近实在界;另一方面幻象要与不可能性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持现实感。记忆的虚幻性一方面鼓励人们去深入接触人类生活的本质,然而这种本质却又是无法最终触及的,人们永远无法获得那种“终结的感觉”或“终结的意义”;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要让这种虚幻性记忆远离这种本质以维系人类的现实感,因为,一旦遭遇实在界,现实将随之崩溃。人类的这一生存悖论让人类永远无法摆脱在夹缝中挣扎的生存焦虑与恐惧。
二、历史的不确定性与人类的生存焦虑
巴恩斯的小说一贯秉承对历史不确定性的表述,《终结的感觉》也不例外。虽然小说并没有像《福楼拜的鹦鹉》和《十又二分之一历史》等巴恩斯其他作品那样对某些具体的历史的宏大叙事或历史人物进行解构与建构,但是小说在行文之中,无不从细节处透露出作家的历史观。巴恩斯的大多数小说都可归于琳达·哈琴式的“历史编纂元小说”。《终结的感觉》虽然不能称作典型的历史编纂元小说,但是小说通过罗布森自杀事件对于历史编纂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戏仿却体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他死了,我们都知道他有个女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孩子怀孕了——或者说曾经怀孕过。但此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呢?只有一份可被称作史实的文字记录,就是那张写着‘对不起,妈妈’的自杀遗言……那等到五十年之后……怎么可能还会有任何人有能力来记录罗布森的故事?(p.21)
历史编纂元小说游戏于历史记录的真实与谎言之间,质疑已被接受的历史信息。历史学家或是小说家如何检验历史陈述的真实性?问题的答案涉及“事件”与“事实”的区别。历史事件确实存在,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够明确无误地了解历史事件呢?历史编纂和小说写作决定了哪些事件将变成事实,正是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将事件变为事实,如哈琴所言“后现代主义念念不忘突出的正是事件(本身没有意义)和事实(被赋予了意义)之间的区别”*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122.。紧接着,巴恩斯又对新历史主义者热衷于历史细节的考据进行了滑稽模仿,
别忘了在此事例中定会涉及验尸,因此一定会有验尸报告。罗布森很可能写过日记,或是写过信,还打过电话,这些内容都可以被人记起。他的父母也会答复他们收到的那些吊唁信。而五十年后,考虑到现在人们的平均寿命,他的同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可以接受访问。”(p.22)
不管是历史编纂元小说还是新历史主义都关注历史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然而在巴恩斯强烈质疑历史的确定性的背后是作家对人类深切的生存关怀。巴恩斯对历史的表述并不局限于再现具体的历史形态,而是从对历史的不信任中流露出对人类生存的焦虑之感。“存在先于本质”,首先是自我的存在,“自我”是先于本质的,人的“自我”决定了人的本质。巴恩斯对历史的解构消解了自我存在的场域,使得自我的存在变得飘忽不定,自我感觉不到任何的存在之感,人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种对生存的焦虑感油然而生。青年时代的托尼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在历史课上讨论什么是历史,托尼认为,“历史就是胜利者的谎言”,老乔·亨特认为“它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科林说历史“一个劲地重复……一直都在专制与反抗、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贫穷之中徘徊”(p.20)。巴恩斯在这里把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表露无遗。历史如今已经成为披着合理外衣的最大的意识形态幻象之一。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成为对中国历史的经典概括,然而这样一句话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历史真的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有规律可循吗?历史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力量使得历史总是在“专制与反抗、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贫穷之中徘徊”呢?事实上,在宏大叙事消解的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已经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虚构性或文本性,历史意识形态的这种幻象性已经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的那样用于简单地掩盖事物的真实状态,这种幻象性已经写进历史这一存在的本质之中,“历史的虚构性成了我们生活现实的一部分”*申富英:《论现代小说中历史虚构性的嬗变——从〈格列佛游记〉到〈尤利西斯〉再到〈洼地〉》,《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然而,今天的人们在洞察历史意识形态幻象性的同时,却对历史的虚构性视而不见,在权力编织的意识形态幻象之网中昏昏度日,“一切政治体系和社会制度都是腐朽的,可是,除了追求混沌的享乐,我们一概拒绝考虑别的选项”(p.11)。这是一种现代犬儒式生存状态,“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只有像艾德里安这样对生活本质敏感的体察者,才会有穿越意识形态幻象来一看究竟的勇气和斗志,“艾德里安敦促我们笃信原则应指导行动,将纸上谈兵的想法运用于人生。”(p.11)然而,这样的勇者最终还是失败,甚至割腕自杀。作家似乎想说:只有像主人公托尼那样,远离历史、现实与记忆的复杂性,通过删除和整理自己的记忆来创造适宜个体生存的个人历史与集体历史或是个人现实和社会现实,才能从不堪忍受的生存焦虑中幸存下来。历史不仅仅是胜利者的谎言,更是那些在生活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的记忆,这些人称不上是胜者还是败寇。然而,幸存下来的犬儒主义者或是狂躁的抑郁者依旧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幻象的缠绕,因为这种幻象性已经写进了社会现实的本质之中,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有关人类生存的“历史变成一本‘有关人类焦虑的永远也翻不完的日历’”*[英]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刘建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三、生存焦虑下对终结的恐惧
小说题名为《终结的感觉》,对于“终结”(ending)一词的理解至为关键,“终结”可被理解为“确定性”。记忆、历史和现实等在巴恩斯看来都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一个终结的意义,或是一个无法终结的概念。对记忆、历史和现实的建构与解构是想无限接近那无法最终达到而又无法摆脱的创伤性内核,然而,实在界无法以真实面目示人,人类抵达真实的历程永远无法终结,这也是西方学者给巴恩斯冠以怀疑主义者的原因。正是这种渴望终结而又无法终结的循环往复的生存现实,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生存焦虑或是生存恐惧。巴恩斯要表达的终结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无助、绝望的感觉,无法改变的事实。这种感觉可从小说突兀的结尾见出端倪,小说结尾似乎揭示:那个智障的孩子是艾德里安和维罗妮卡的母亲生育的,托尼早前对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的诅咒居然变成了现实,这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一个极大的反讽。自此便可以解释维罗妮卡为何一直对托尼反复说“你还是不明白。你从来就没明白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所以干脆就别试了吧。”(p.186)人类永远无法洞悉生存的本质,巴恩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终结”在小说中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死亡。小说包括两场死亡事件,一个是罗布森同学的死亡事件,另一个是艾德里安在浴缸里割腕自杀。巧妙的是两场表面似乎不相关的死亡事件居然可能是出于同一个缘由,这不禁让读者联想到艾德里安的自杀是否是受到了罗布森的启发。无论是罗布森还是艾德里安,他们的死亡原因都是无法解开的迷。相较于艾德里安,罗布森只“是一棵平凡无奇的蔬菜”(p.15),年少的同学们在得知罗布森死亡之后,不但没有给予同情,反而极尽调侃之能事,妒忌罗布森能把女朋友的肚子搞大,还猜测其女友是处女还是婊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冷漠的境地。若干年后,当托尼回想起这段往事,在为自己的恶毒感到自责的同时,也惊觉自己并不是自我所认知的高尚个体,巴恩斯通过主人公托尼的自省,表达出一种对人类道德责任感的拷问。与此同时,小说还传达出在人生将尽之时,通过整理过往的记忆和历史,我们获得的不仅仅是惊奇,还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焦虑和恐惧。
从小说中的另一起死亡事件即艾德里安自杀事件,读者可以解读出巴恩斯的死亡观。小说以艾德里安的自杀场景开篇,以令托尼震惊的故事结尾,在此过程中,艾德里安死亡的原因始终无法得知。艾德里安可以被看作作者的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洞悉了世界本质的不确定性,沉溺于虚无之中,由于看不到走出虚无的途径,在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之时(与女友的母亲生下一个智障儿),只能一死了之。“他名叫艾德里安·芬恩,一个高挑而羞涩的男孩,起先总低着头朝下看,什么都放在自己心里。”(p.4)“他除了偶尔开玩笑,基本上都很严肃。”(p.8)艾德里安处处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博学而敏感。“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p.8)他是剑桥的高才生。然而这么一个优秀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小说没有给出答案,这或许源于他对生活的不信任感,他引用加缪的话说,“自杀才是唯一真正的哲学问题”(p.16)。从艾德里安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影子,对生活有着无法摆脱的焦虑感,钟情于对年老与死亡的描述,例如《柠檬桌子》就是关于变老和死亡的小说集,书中的大多数人物就像托尼一样已经迈入老年,然而,他们一方面明白不应该再留恋年轻时代的激情和欲望,但另一方面又将这些美好小心翼翼地保留在记忆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感到越来越无力追求过往生命之乐时,才能从经过删除与处理的记忆处体味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从而克服无法抑制的生存焦虑或是一种对于终结的恐惧。弗兰克·克默德认为:“即使当我们获得了现代文人们的那种怀疑态度,我们似乎仍有必要对虚幻的模式做某种程度的屈服……我们不愿看到代表出生的滴和代表死亡的答之间的间隔悬而未决。”*[英]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刘建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而当这一切虚构被某个外来物攻破之时,“你的大脑——你的记忆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它仿佛在说:千万别指望你可以这样顺顺利利、舒舒服服、慢慢腾腾地衰亡——生活可比这复杂多了。”(p.144)自此,我们发现世界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我们甚至都不能拥有我们自己。然而,在震惊之余,我们发现如果人生缺少了这些精巧万分的虚构,那么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就会变得无比残酷。在这种境况下,我们虽然在意识或是潜意识中对虚构和由虚构杜撰的人生境况了然于心,却常常有意识地视而不见,在不知何处开始、何处终结的中间地带编织着我们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幻象。
四、结语
相较于巴恩斯其他的几部作品对于宏大愿景的痴迷,例如,《福楼拜的鹦鹉》将历史人物传记与小说融为一体,《英格兰,英格兰》将“英国性”与国家民族记忆作为小说主体,《十又二分之一历史》(AHistoryoftheWorldin10 1/2Chapters,1989)解构了“诺亚方舟”神话,若干小故事呈现出作者对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质疑。一些读者认为《终结的感觉》只是纠缠于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并且其中的爱情故事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然而正是这样一部以片段方式呈现的有关日常生活记忆的碎片式小说最终让巴恩斯斩获大奖。
在朱利安·巴恩斯看来,无论记忆、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虚构性,这种虚构性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人类存在于“滴”与“答”的中间过程,处于“生”与“死”之间,随着逐渐年老,过往的记忆被各个击破,剩下的就是那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创伤性内核。我们在祈求结局到来的同时又惧怕终结的感觉,在频频回望过去的同时又在不断渴望未来,人类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生存悖论之中。然而,不管是悲观主义还是怀疑主义,这种感情必须服从和被抑制,因为真实是我们无法最终达到的,为了维系一种生存的现实感,我们“不得不制止滴和答之间的间隔所具有的那种要掏空自己的倾向,以便在滴之后的间隔里保持一种对于答的强烈的期待和这样一种感觉,即无论答有多么遥远,一切都会照常发生,就好像答肯定会随之而来似的”*[英]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刘建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终结的感觉》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犬儒式的生存隐喻,作者和读者并不在乎故事的结尾有没有解答小说中人物与情节的所有疑问,因为一方面真实无迹可寻,另一方面揭露真实根本无济于事,在当代社会,重要的不是真和假,而是内心真实的“欲望”。因此,巴恩斯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呈现其一贯对于历史与记忆不信任的态度之外,将人类犬儒主义生存状态之下的那种对于生存的焦虑用一个看似平淡的故事表现出来,让我们认识到记忆和历史的欺骗性,但却丝毫无法阻挡其发挥作用。小说讲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个绝望的故事开启了我们对于过去的那扇记忆之门,触碰到记忆中那些可能永远无法以真实面目示人的欲望与创痛。
(责任编辑:陆晓芳)
2016-09-11
许文茹(1981—),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方向博士生,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申富英(1967—),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詹姆斯·乔伊斯作品幽灵叙事形式研究”(项目编号:13BWW043)和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青年项目“拉康—齐泽克理论视阈下的文学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2CWXZ01)的阶段性成果。
I106
A
1003-4145[2016]11-01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