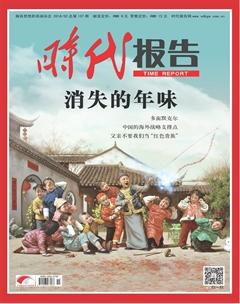祖国高于一切
2016-03-02陈祖芬

编者:作品写于一九八〇年,作为陈祖芬的成名作,这篇作品选取了一个从海外归国的老科学家,数十年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迎合了当时全国开展富国强民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作品表现了炎黄儿女对祖国的爱,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渴望的时代主题。本期奉上《祖国高于一切》,邀您一同再次领略老一辈科学家留给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柏林妻子
三十年前。德国柏林。
俗话说: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即使像王运丰这样豁达的人,现在也屡屡跌进感情的深渊。他陷在厚实的沙发里,望着正在地毯上嬉戏的三个儿女:孩子们和她长得太像了!那凹陷的棕色眼睛,那举手投足之间,无一不渗透着她的音容笑貌。说来也怪,只有在她出走之后,他这做丈夫和父亲的人,才充分地领略了这一切遗传上的惟妙惟肖之处。于是孩子们那欢快的笑声,只能引起他悲凉的情思。人对于失去了的东西,总是感到分外的宝贵。她出走了,却较之她在家的时候,愈发地使他感觉着她的存在和他视之比生命更宝贵的她的爱情。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像旋转木马似的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一切都是从那个邮件开始的。那是一张祖国寄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简直不是看报,而是吞!他一口气把那条喜讯吞了下去,然后才久久地品味着、陶醉着……当然喽,回国去!一九三三年他出国留学时,坐的是德国海轮。这样先进的海轮,这样超乎他想象的内燃机!世界上一见钟情的故事不少,他和内燃机的姻缘就由此产生了。海轮途经新加坡,几个洋人向海里扔下几枚钱币,对中国人说:谁下海捞着,钱就归谁。洋人笑着,笑得白脸变成血红;下海的中国人也笑着,笑得黄脸变成惨白。这种愚昧痴呆的笑,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一架燃烧起自豪和力量的内燃机!
柏林到了。啊,这么多的汽车!一辆、两辆,三、四、五、六……唉,数不过来!来自人力车和马车的国土的王运丰啊,这些飞驶的汽车无疑是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你们中国造不了汽车,你们连一个内燃机厂都没有!
唉唉,中国在德国的四百多留学生,几乎谁都不学内燃机专业--回国没饭碗啊!可是难道中国就永远没有内燃机、永远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轮船了?!不!……
现在王运丰是西德内燃机专业的国授(国家授予)工程师,拥有一吨多重的书。正是这些书,浓缩成他生命的精髓;而他的生命,也分解在这些书里了。书本是他生命的影子,当然要跟随他回国的。影子是不会和他自身分开的。妻子再好,也可能分开……前几天国民党在西德的便衣跟踪他、审问他。昨天半夜又有人打电话来威吓:“小心点,否则我们要用手枪来对付你。”妻子吓得睡不着了。她痴愣愣地瞪着他,那棕色的大眼睛更加凹陷了。一夜之间,她变得像一朵萎缩了的花。他的心也萎缩了起来:他干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他召集了留德同学和侨民开会,呼吁响应周总理对海外知识分子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立刻给周总理发了电报:“留德同学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表示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并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回国参加建设的号召,请速派遣外交代表和安排留德学生回国事宜。”祖国解放前几年,国民党驻西德的机构先后三次动员他回国。他拒绝了。可这次,他偏要回!“你别走吧……”棕色眼睛的妻子哭了,泪水莹莹地望着那六间一套的家。每间房里都有大幅的地毯和贵重的家具。于是,他看见爱情在讲究的咖啡壶上闪耀,在雕花木上微笑,在地毯上伸展,在她的泪水里流淌……只有他和她才知道,他的事业加上她的爱情,才能经营起这个美妙的家庭。他们是一体的。他和她之不能分开,犹如他们那三个孩子不可能再分解成他和她的细胞一样。.
但是,当她知道他回国的决心已不可动摇时,她赌气回到东柏林的娘家去了。这位柏林妻子和他竟是同样地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唉,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一个共性如何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人们可知道,往往同一个共性,又能使眷属终成无情人?
无情?当法官宣读了离婚的判决后,她在法庭上当众就哭了起来。他真想一把搂住她说:别哭了,和我一道去中国吧,就像结婚时他拥着她走向他们的家……
家被无理查封了。家具、地毯、车库,一切都贴上了封条。根据当地法律,私自撕毁封条的,要加倍从严地法办。但是封条可封不了王运丰那急于回国建设的心,那颗像内燃机一样产生巨大能量的心。一切可能发生的凶险,都在“祖国”这个古今中外最有魅力的名词面前,变得不值一顾了。王运丰撕下了汽车上的封条。在德国司机的帮助下,他带走了三个孩子和跟随他的影子——一吨书。而财产,全丢下了。“生活中最没有用的东西是财产,最有用的东西是才智。”这话是谁说的?对了,莱辛!是啊,只要有书,有才,就可以为祖国服务。他怀着赤子之心奔向理想的境地。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天真的。第一个从西德回国的工程师王运丰,和他那三个七岁、五岁、二岁的孩子一起稚气地笑着……
“德国特务”
有人靠回忆度日,有人靠想象生活。有人因独具精神而力量过人,有人因敏于思想而陷于痛苦。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有了思想。王运丰被作为专政对象,独个儿在河北蔚县的崎岖山路上担煤。他的思想却因抵抗专政而变得毫无规则。如果他能未卜先知地预料他这个留德的内燃机专业工程师在六十年代中期将以担煤为生(虽然煤也是燃料),真不知当初他还能不能拼命攻读了!不过他当然还是要攻读的,否则他就不叫王运丰了!“王运丰,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德国特务?”特务?他在德国倒是有特殊的任务。他在内燃机专业毕业后,本来满可以每两年准备一篇博士论文,到一九四五年,两个博士学位也到手了。但他不去考。他给自己规定的特殊的学习任务,是尽可能多学会几门技术--祖国什么都欠缺啊!于是他又去学焊接、电工、管理、铸造。铸造是冶金不可缺少的部门,但在旧中国被看成下贱活:打铁翻砂么!西德教授惊讶地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王运丰:“我没见过中国留学生学我这个铸造系的。”王运丰在铸造厂实习,每隔三四分钟就得把一只七十斤的砂箱搬上机台。搬几下还凑合,一会儿就对这七十斤的宝贝儿望而生畏了。那也得搬!默默地喊个号子吧:“一、二——为了祖国!”“一、二——为了祖国!”十个月后,他的臂力使他在留德侨民中成了划船冠军。二十多年后,他的臂力使他还能在蔚县山区担煤、运煤……
黑煤上闪烁着白雪。漫天又飞扬起雪片。一九四五年,炮弹皮和断砖碎瓦像雪片似的飞着。苏军进攻柏林了。柏林当局规定,居民听到空袭警报,全下防空洞。“王先生,整个楼的人都下防空洞了,你快走吧!”邻居劝他。“我就不信炸弹正好掉到我的头上。”炸弹尖叫着,偏偏来到了他的头上。他万念俱灭,只等着人生最后的刹那。一声巨响,楼晃悠着,土直往他头上掉。还有知觉?那就是说还没死?他活脱脱地蹦了起来,跑出去一看,五十米远的一幢楼成了瓦砾堆。他又回到楼里攻读。他不是不怕死。天生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每次轰炸几小时,他要是往防空洞一钻,这几小时岂不是浪费了?对于一个学习癖,最痛苦的莫过于时间的浪费了:几个小时又可以吸收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顾不上危险不危险了。一个人只有忘却自我,才能真正地发现自我。正是在忘却的时刻,他会焕发出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他将惊讶地看到他拥有着什么样的才能!
“王先生是我们的安慰,王先生不怕轰炸我们也不怕了。”德国邻居们信任地望着他,差点没把他当成了上帝。但是炸弹像下最后通牒似的把他的门、窗都震落了。搬家。又震落了门、窗。再搬。他终于把一叠十几张设计图交给了德国老师考核。“王先生真不是一般的学生!”他快活地在弹坑间疾步走着,好像在生与死的边界线上穿行。“王先生来了!?”书店老板亲热地招呼他:“我给你留出了一捆书,准是你需要的。”他和书店老板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的默契:不用他挑书,老板知道该给他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书了。他又把一份咖啡送给了好心的老板。咖啡在战时因缺货配给而变得身价百倍。但是咖啡再贵重也就是咖啡。而书籍却能变出内燃机,变出坦克,变出祖国所需要的无穷尽的宝物。
天安门前的阅兵行列里,开来了一辆辆中国制造的轻坦克、水陆两用坦克和装甲车。王运丰坐在观礼台上,像父亲欣赏儿子那样,向坦克倾注着全部的情和爱。真不知是坦克因他的注视而变得威武雄壮,还是他因坦克的出现而变得这样不能自已。他回国后就担任了坦克专业局的技术领导职务。可是厂呢?只有农机修理厂,机车修理厂。衣衫褴褛的祖国母亲啊,让我们来装扮你吧!先把这几个修理厂改建成发动机厂和坦克制造厂。唉唉,师傅们还是在山沟里制造步枪的半手工业做法,没有工艺规程,做出的零件一会儿一个样。必须把坦克几千个零件的每一个工艺规程都写下来,一切纳入现代化生产的轨道!规程写了三年,以后进程就快了。原先坦克的大部件都得向苏联订货,以后订货单上开的项目一年比一年少了,最后终于全部取消了订货单,而代之以中国制造的坦克。
不过他跟坦克的缘分并不长,反而跟卡车很有缘。一辆卡车载着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这个全国先进生产者的相片,抄走了好几箱书。书是他的影子。人一旦连影子都给剥夺了,将是怎样的凄苦!另一辆卡车拉他游街、批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特务!他的柏林老婆还到中国来串连过!”唉,柏林妻子!他离开柏林时,把本想留给她的小女儿也带走了——愿思念女儿的心情使她回到他的身边来吧。他给她邮去了路费,一年年地等着,终于把她等来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期待中的会见又这样地激动着他。.
在匆匆的一瞥中,他就把对于他是那么熟悉的她的身影、她的一切都看清楚了。“亲爱的,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她笑了。她又伤心了:孩子们的德语说不利落了。因为前不久他出差了七个月,孩子们没人管了,就把德语忘了一半。可是他总得下去开展工作啊。他吻别了妻子,又走了。妻子回来一年多,他走了倒有八个月。他怎不想想,这个数字对一个不懂中国话、又对德国有着深深眷恋的妻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何况当时又正逢困难时期。“你看人家全家去德国了,我们一起走吧!”妻子痴愣愣地瞪着棕色眼睛,作着最后的努力。火车门关上了。妻子的泪水一行行挂在车厢玻璃上。他追着启动的车厢想说,想说什么?唉唉,全忘了,忘了。他只是用内疚的、失神的眼睛看着她,眼睁睁地看着火车载走了他的爱、他的心。他的胸膛一下空虚了,只有火车的隆隆声在他那空荡荡的胸膛里撞击着、回响着……
卡车的隆隆声在野地里显得孤单单的——又是一辆卡车把他送往蔚县监督劳动。押送“德国特务”的人戒备森严地拿着枪。其实,为确保安全起见,他们不妨先枪决他领导下设计的坦克。卡车途经八达岭。雪把他的胡子、眉毛都染白了。黑夜里他只见野狼闪着碧绿的眼睛。他柏林家的地毯就是这种绿色。现在要是能把这地毯裹在身上就好了。在这大冬天里坐卡车,身上冷得就像穿了皇帝的新装——什么也没穿!也许今晚就冻死,连同他的知识一起消亡。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碰到暴力,毫无招架之功;知识分子碰到秦始皇,也只有束手待坑……
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漫天大雪使天地之间成了个大雪坑。王运丰在蔚县的山路上挑着一担煤,一步一停地向山上爬着。爬了半天好像还只是停留在雪坑的坑底。好大的坑啊……
中国母亲
一个人在平静的时代生活、工作,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懂得什么叫解放。当王运丰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时,他的感觉犹如一个刚走出监狱的人,来到充满阳光的天地里,感到了令人目眩的光明、自由和解放。他的知识和才能,原先就像是一群拥挤着给关进笼子的小鸟,现在要把它们统统放出来,让它们冲天而起,展翅飞翔了。唉唉,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六十多岁的人啦,他是恨不得把每一分钟的时间拉长。有些人受了委屈,或是疯狂地对社会挥着拳头,或是颓废地失掉了自信。一个人要是对自己都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呢?--王运丰摇着头。他自信他的才能,他的价值,所以他这个“德国特务”偏要给周总理写信--给我工作!可惜总理已病了。他又给邓副总理写信,不料“批邓”开始了。一九七七年他再给党中央写信,于是应邀出席了国宴,获得了工作的权利。
是啊,只要能为祖国工作,他什么都可以不计较——贫困、委屈、凶险、一切。一九六〇年苏联撤退专家,某柴油机厂陷于困难境地。“领导同志,让我去支援这个厂吧。”“老王啊,那是重灾区,你知道吗?”“怎么不知道?我刚从那儿出差回京么。那儿,已经有人吃树叶了。”“你能受得了?”“那儿的上万职工都受得了,我为什么受不了?我还要把三个孩子都带去。整个家迁去!”
“厂长同志,你们厂哪个部门最吃紧?”王运丰问。“铸造。不过铸造车间最脏、最累--”“我来主管铸造车间。”王运丰毫不怀疑当年他在德国铸造厂搬那七十斤重的砂箱时,就预感到有一天会在中国的铸造车间里大显身手了。他和职工们改善了车间管理,稳定了产品质量。
人们往往以为,一场战斗胜利结束了,就可以痛快一下。但是王运丰是这样疲乏,以至没有精神来享受曾经那么期望着的胜利的日子。是的,只是在任务完成了之后,他才一下感到精力衰竭,难以支付生命的需要。生活是苦啊。“李师傅,你怎么没吃饭去?”“王总,是,是这样,我粮票没了。”“李师傅,拿着,快买饭去!”“三斤?”“快去!”他回家了。孩子们饿得用自来水把生高粱面冲得稀稀的,当饭吃呢。可怜的孩子啊,爸爸怎么忍心看着你们挨饿啊!他晕倒了。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脊椎硬化,等等,他近乎瘫痪地卧床了。一般的人,谁不愿意生活得好一些,活得长一些,留给子女的钱多一些。老年得病难免会想这想那。但是他最揪心的,是他的才能没有得到预期的、真正的发挥。就说在柴油机厂吧,书记很好,带头吃苦。可工厂是多头领导,总工程师制又没建立。他这个党外人士又只能担任副职。他的职权范围就相当有限。想作一些重大的改革,无职无权,无法推广,才能施展不出来啊!医治这种制度上的弊病,比医治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要难多了。
当他干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把他的手脚束缚起来。但是难啊,总有一些绳索从他的前后左右伸将过来……一九七五年,他靠边站时,有一位老上级请他到南京帮助筹建电子计算机站。他是个给剥夺了工作权利的“德国特务”,到南京去当临时工,政治上可是担风险的事。但他说去就去了,就像当年走向重灾区。他从大量的技术资料中,发现外国某公司提供的电子计算机,和合同中规定的型号不一样。这是一套拼凑的旧设备,连正规的出厂合格证都没有。可我们的干部说,“我们已经验收了,而且支付了货款的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听任外商欺骗!”“客人是我们请来的,别谈电子计算机的问题。”王运丰震惊了:这么奴颜婢膝!是啊,往往愈是真心实意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人,愈是有自力和奋发的精神;而排外的人,往往走向媚外。科学使人格高尚,而无知使人格萎缩。
“我要上国际法庭控告你们!”外商想先发制人。
真闹出事儿来,王运丰当然是罪加一等。那么又会有一辆卡车把他带走。也许是囚车。不过他这时倒冷静了:其实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一部分。当初轰炸柏林时,年轻轻的都不怕死,何况现在?人要是能死在他所爱的事业上,那也就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可是孩子们怎么办?这些年他们插队、掏粪,而且因为那显而易见的外国血统而给人围观!活着,还能送去一片父爱……唉,人老了,更重感情了。这三个孩子从小离开了妈……当初在柏林法庭上离婚的劲头哪去了?我是个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母亲的科学家。母亲可以一时错怪她的孩子,但我不能不爱母亲。让我们感谢祖先传给我们的这种默默的献身精神吧!我已经和计算机站的领导和同志们研究了一切材料和数据,我们决不能花钱买一架废物,更不能让外国人把中国人当作废物。“科学是使人的精神变得勇敢的最好途径。”布鲁诺又在给我以启示了……
勇敢战胜了欺骗。外商同意交一套新产品:“你们中国还是有人才的。”
还是有人才的?仅仅“还是”?不,我们有的是人才!但是在我们这块充满着人才的土地上,还延续着一种扼杀人才的习惯:有些掌握科学而不掌权的,得服从本单位掌权而不掌握科学的;有些想干且知道怎么干的,得服从不想干且不知道怎么干的。在两种对立的精神品质的阴错阳差、东拉西扯中,人才还在给消耗着,但是人们往往不震惊,不愤怒,因为这一切都已习惯了。而习惯是一种何等不可思议的力量!它能把一切可笑的和可泣的、可怜的和可叹的、可鄙的和可赞的、可恶的和可爱的统一起来,维系着一个伟大而落后的国家。
“王院长,您来了!”是的,在五机部党组、国防工办和王震副总理的一次次关心下,王运丰副院长沐浴着党的政策的春雨,来到了五机部科学研究院。“王院长,您来了!”是的,他又来到了以人相待的社会里,重新感到在人和动物的千差万别中,还有礼貌这一说。而礼貌,正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回国三十年,实际工作时间只十五年。其他时间除了挨斗、靠边,还有让他干坐办公室。他本来可以创造多少价值?他自己无法估计,更无暇估计。他又忙于筹建电子计算中心。“如果说,机械化是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一个象征,那么,电子计算机科学将是从本世纪过渡到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标志。”——他什么时候成了电子计算机的义务宣传员了!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交游广阔!他几次去西德寻找三十年前的同学、老师。在国际合作中,有时私人友谊比官方谈判更起作用。他联系派遣了一批中国实习生去西德学机械制造业,又几次请来西德的专家、教授来我国讲学,进行造船、建工等方面的合作。“王先生”,柏林大学的老校长望着他三十多年前的学生:“在我有生之年,能为中德教育合作建立关系,是最大的愉快。”而王运丰也感受到一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的愉快。可是我们的行政效率……直到他第三次赴德找老校长时,教育合作才刚有所进展,而这时,老校长已过世了……
我们有些当领导的,往往把精力花在如何转动官僚主义的机器上,而不去转动生产机器,去提高生产力。当我们很多人恨不得把每一分钟拉长的时候,偏有一些人在把每一分钟掏空。制造冤案的时代过去了,但是那种因循的习惯,却像幽灵似的戏弄着勤勤恳恳的人才。母亲老了,往往有些怪癖。好在祖国母亲现在是又古老又年轻:既有老人的涵养和怪癖,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冲动。我们作子女的,应该关心的不是母亲给我们什么或给了多少,而是我们是否帮助了母亲!说起来,王运丰被抄走的书至今没退还。他在“牛棚”被迫写的材料,也没退还。“造反派”为了给他强加罪名,硬把他这中农出身改成“富农”,也至今不更正。他的住房还是那么紧,他那些没被抄走的书,也只能继续封存在板箱里——没有地方摆出来。一位西德专家来他家做客时,他很怕有伤国体:“我这间房又是卧室,又是书房,又是饭厅,又是会客室。”“不,王先生,这已经不错了。你记得吗——战后我那间屋连窗玻璃都没有,只好用X光胶片贴在窗框上。”
好了,伤感使人衰老,牢骚使人不思进取。王运丰毕竟找到了他的幸福。他从一九三八年出国留学时就希冀着的幸福:为祖国奉献才能。人是要有信念的。在古今中外人类发展史上,信念始终是动力。王运丰在科学的道路上探索了一辈子,他确认的最伟大而又最平凡的真理,则始终只有一条:祖国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