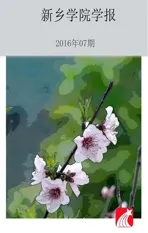多重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解读
2016-03-02吴秀群
吴秀群
(铜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多重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解读
吴秀群
(铜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摘要:“创造性叛逆”自提出之日起,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肯定它,有人否定它。肯定它是因为它正好迎合了自身需求,否定它是因为它与自己的“忠实”信仰相背离,由此也引发了“叛逆派”与“忠实派”之争。文章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对“创造性叛逆”进行解读,以厘清“创造性叛逆”在不同视角下的真实内涵,从而避免对“创造性叛逆”的误读。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译介学;解构主义;顺应论;接受理论
“创造性叛逆”来自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专著《文学社会学》。埃斯卡皮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1]在他看来,“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提出之后,一直颇受争议。有的学者对其大加宣扬,有的学者却对其嗤之以鼻,其原因在于对“创造性叛逆”的解读不一。有学者用“创造性叛逆”来描述译者的翻译实践,有学者用“创造性叛逆”来揭示翻译的规律,分析翻译成品,并由此产生了“忠实派”与“叛逆派”之争。本文将从不同的视角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一一解读,力图厘清“创造性叛逆”在不同视角下的真实内涵。
一、译介学观照下的“创造性叛逆”解读
谢天振先生以文学翻译中的 “创造性叛逆”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创建了译介学,并认为由于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绝不可等同,并提出要将翻译文学编入译入语文学,由此还提出编写翻译文学史的构想。
在翻译“忠实派”看来,“创造性叛逆”大逆不道,在翻译中唯恐避之不及。而谢天振先生则为其正名,指出“创造性叛逆”一语只是英文术语creative treason的迻译,是个中性词,是对一种客观现象的描述[2]。谢天振先生在其著作《译介学》中再三强调,“创造性叛逆不是一个用来指导如何进行翻译的方法和手段”[3]134。也就是说,“创造性叛逆”并不是用来指导翻译实践的,而是用来描述翻译成品的,而且这里的翻译特指“文学翻译”。谢天振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没有创造性叛逆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正如埃斯卡皮所说,翻译“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英国翻译学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等同于原文。然而,理想的翻译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是归化,也是在迎合译入语读者的情况下,对原文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处理,有的甚至将原文文化“化掉”了。
谢天振先生还归纳了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他将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又可分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其中争议较大的是“个性化翻译”和“误译”。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在变相地鼓励胡译和乱译。谢天振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严肃的翻译家应该避免误译,但误译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而且误译有时还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同时,谢天振先生也指出,有部分青年学者由衷地赞叹“创造性叛逆”,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未真正领会其实质,只是热衷于探讨“什么样的创造性叛逆是好的创造性叛逆”“什么样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好的创造性叛逆”,以及“该如何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度”,实际上,这些都是关于“怎样翻译”的问题,是对“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误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译介学观照下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是鼓励译者可以任意发挥,而是描述文学翻译成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创造性叛逆”这一事实,它是“对跨语言、跨文化传播和接受中一个规律的揭示”[3]134,它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翻译的实质。正如王向远[4]先生所说,“忠实派”和“叛逆派”都过于将自己的主张绝对化,“忠实派”理论可以用来指导文学翻译实践,而“叛逆派”理论可以用来描述文学翻译成品,二者并不矛盾。一方面,对于“创造性叛逆”是对文学翻译成品的描述的观点,笔者也十分认同。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创造性叛逆”进行明确定义,不能将任何“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都称为“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不是机械的字对字的翻译,而是需要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挣脱原文的枷锁,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创造性叛逆”应该是对译者劳动成果的肯定,若将一切不负责任的译文统统称为“创造性叛逆”,无疑是对辛勤付出汗水的译者的一种贬斥。因此,笔者认为谢天振先生提出的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有待商榷。
二、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创造性叛逆”解读
解构主义翻译观打破了结构主义范式的封闭性,并将被结构主义排斥在外的许多因素都纳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形成了多元的理论体系,以功能理论为依据的目的论派、阐释学派、操纵学派都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目的论派的翻译理论是由其代表人物威密尔(Hans J.Vermeer)在“行为理论”基础上创立的,是从译文视角来研究翻译的一种解构主义翻译观,它以译文功能为取向,注重翻译的实用性。目的论派从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的环境三个方面来考察翻译活动,指出翻译活动是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根据翻译文本的功能做出的选择。因此目的论下的翻译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译文的功能和目的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显然,目的论派强调了译者行为的主动性,将译者身份提升至和原作者同等的高度。翻译从对原文内容的选择到对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在一定目的指导下进行的,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忠实”摹本。在目的论观照下,翻译就成了有目的性的改写。威密尔在其目的论中提出“颠覆原文”的观点,即“原文的语言特征和文体特征不再是衡量译文的唯一标准”,打破了“原文中心论”。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原作意图可以被随意歪曲甚至剥夺,原文信息可以任意篡改,译者的个人意志可以无限度地放纵或张扬,目的论的翻译被认为是阐释或改写的“重写式翻译”,译者被称为原文的“背叛者”。因此,目的论派虽反拨了传统“文本中心论”,但同时又削弱了文本意识,使“创造性叛逆”变得无章可循。后来德国功能派的主要倡导者诺德(Nord)将忠诚原则引入功能主义模式,针对文学文本翻译提出“功能加忠诚”原则,其中“忠诚”指译者的伦理道德观,对译者的翻译行为有了一定的规范,也减少了目的论派的功能主义倾向,这与目前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不谋而合。
阐释学派的翻译理论以解释学为哲学基础,主要聚焦在伽达默尔(Gademer)的三原则之上,即“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其中“理解的历史性”使原文意义的确定性开始动摇;“效果历史”肯定了“误读”在翻译中的合理性,进而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视域融合”又使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得到合理解释。在阐释学派看来,任何翻译都只能是一种“创造性的重新阐释”,不是原文本的“忠实再现”。伽达默尔指出:“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再创造。”[5]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带有自己的“偏见”,肯定了译者主体性。阐释学派认为意义不是由语言规则设定的,而是在视域融合过程中通过对话生成的,不同视域的融合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否定了意义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刘小刚在伽达默尔释义学的观照下,指出“创造性叛逆就是视域融合中的意义生发。视域融合使我们具有了一个既不同于原来的自我视域,也不同于他者视域的新的视域”[6]。他还进一步厘清了“创造性叛逆”的四个规定性特征——普遍性、原文规定性、双重性和描写性,认为“创造性叛逆”“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了视域融合中的意义运动”[6]。因此,在阐释学派视域下,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改写。斯坦纳(George Steiner)以阐释学为基础,提出翻译的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经验和价值观带入译文,因此翻译必定是对原文的改写。但这种改写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结果,即译者并非有意识地去改变原文,其显意识中仍然是如何尽量“忠实”地去翻译它。但有人却把这种“潜意识”当作“显意识”,并大做文章,于是有了“翻译即改写”“翻译即叛逆”等提法,实际上这已经背离了其宗旨,创造性叛逆并非鼓励在翻译实践中去背离原文,也不会造成原文意义的无限撒播。
操纵学派以目标文本为取向,认为翻译是一种被操纵的行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列费维尔(Andre Lefevere)在其专著《翻译、改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在他看来,翻译是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改写类型”。改写有诗学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另一位代表人物赫曼斯(Hermans)也认为,“所有翻译都会出于某种目的对源文本实施某种程度的操纵”。译者价值不是中立的,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受很多制约因素的操控,如意识形态、道德观、价值观、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翻译是受双重权力话语操纵下的产物。但这些操控因素也处于潜意识层,并非处于显意识层。吕俊先生在《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中指出,在学习解构主义中应避免以下几个倾向:不应把在解构过程中发现的潜意识变成显意识,也不应把解构当成目的,不应把非理性当成理性[7]。
除了以上翻译学派,还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试图通过翻译重写殖民地翻译史,重新建构殖民地文化体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推崇“创造性叛逆”,但它主要是为了凸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对文本作政治改写,其目的就是为了使语言替女人说话;新历史主义透过翻译史结构,根据研究者和译者的历史观重写翻译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解构主义翻译观颠覆了原作权威性,打破了原作中心论,解开了束缚在译者身上的“镣铐”,赋予了译者更多自主权。在解构主义反中心、反理性思潮的影响下,涌现了不少翻译研究学派,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局面,也产生了“翻译即改写”“翻译即叛逆”“翻译即操控”等激进思想,充分挖掘了人的潜意识。但另一方面,它却走向了极端,导致了对解构主义的误读,使翻译陷入混乱的局面。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再三申明,解构决不是拆毁或破坏。德里达认为,一个系统的解构意味着另一个系统的建立。因此,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的“创造性叛逆”实际上是“借解构之名行破坏之实”,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三、顺应论下的“创造性叛逆”
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1987年发表的题为《作为顺应论的语用学》一文中首次提出“顺应论”。1999年,耶夫·维索尔伦在其专著《语用学新解》中系统地阐述了该理论,标志着该理论的成熟。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也就是顺应的过程,并认为人类语言主要具有三个特征: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对于语言顺应性来说,还需考察顺应的语境因素、顺应的结构对象、顺应的动态过程和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理应考虑语境因素,对结构对象进行调整,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语言和结构不断进行调整的动态过程。江中杰认为,“创造性叛逆就是在难以进行直接的语码转换和文化传递的情形下所作出的成功顺应”[8]。可见,“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权衡利弊之下对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作出的一种顺应选择。
首先,语言的“变异性”为译者传达原文的精髓、实现等效、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语言的“商讨性”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灵活地选择翻译策略,达到翻译目的。谢天振先生提出的“个性化创造性叛逆”,正是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再创造的结果。文学性越强的文本,译者进行再创造的空间就越大。诗歌翻译普遍被认为是再创造程度最高的文学翻译。最后,语言的“顺应性”能“确保使用者从一系列具有变异性的可能性中作出可以商讨的语言选择,从而尽量满足交际需要”[9]。如外国著名的香水“poison”在引进中国时,并没有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毒药”,而是音译为“百爱神”,正是顺应了译入语语境的需要,一下子也勾起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再如,电影片名Lost in Translation意味深长,译者并没有简单处理为《迷失在翻译中》。实际上这部影片也并不是真正讲翻译,因此,译者灵活借用了故事发生的地点,翻译为《迷失在东京》。
语言的三个特性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依据。“顺应语境因素”和“顺应结构对象”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提供了准则,“顺应的动态性”则告诉我们翻译是一个为了满足译入语语言和文化语境的需要不断作出调整的过程,译者意识越凸显,反映其主体性越强,译文的创造性也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创造并非为了背叛原文,而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原文的精髓,是为了更深层次的忠实。
因此,顺应论下的“创造性叛逆”实际上是指译者依据语言的“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特征,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整语言结构,对文化作相应处理,以适应译入语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过程,它是对翻译过程的描述。
四、接受理论下的“创造性叛逆”
接受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达到高潮,其代表人物是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其核心理论是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和伊瑟尔的意义不确定理论。实际上,姚斯的“期待视野”脱胎于西方现代哲学阐释学中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和伽达默尔的“视野”,认为每个读者在阅读作品之前都已经具备一种“先在理解结构和先在知识框架”。译者首先是读者,只有译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结合,形成视野融合,译者才能充分理解原作。但由于译者个人的文化素养的限制,其对原作的理解不可能与原作者完全契合。又由于译文的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改变,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也就成为必然。这正如谢天振先生将“创造性叛逆”还归纳为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伊赛尔在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的文学作品中的“未定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意义空白与意义未定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本的召唤结构的概念。接受理论给翻译带来的启示就是:译作要想获得成功,一方面要尽量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另一方面要留下一定的空白让读者去填充。译者既要帮助译作读者去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鸿沟,又要使译作和原作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译者既要迎合读者,又要提升读者。有时译者为了迎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从而造成有意误译。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和《贝姨》,从形式上拉近了译入语读者和译作的距离,让人倍感亲切,也加大了译作在译入语中的接受率。这正是译者为迎合读者“创造性叛逆”的体现。但这样做的弊端是不利于译文读者了解异域文化,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中西文化交流。
接受理论颠覆了传统的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将读者推向前台,因此有人认为接受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读者美学,它大大提高了读者的地位,毕竟翻译是为读者服务的。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如果不考虑读者的接受,即使译者呕心沥血,译作也很有可能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许多在国内获得一致好评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外后的遭遇便是如此。因此,译者的一厢情愿不一定能成就一部文学翻译作品。而莫言的作品能在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掀起一阵热潮,其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正如葛浩文本人所说,翻译“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10]。正是他的这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才使他的译作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
综上所述,接受理论下的“创造性叛逆”实际上是译者以读者为中心,为了迎合译入语读者,满足他们的期待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当然,为了迎合译入语读者而不惜对原作大加删减,甚至歪曲作者的原意,并不是翻译的常态。
五、结语
20世纪末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问世后,“创造性叛逆”成了翻译界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赞之,有人鄙之。本文以译介学、解构主义翻译观、顺应论和接受理论为框架,探讨了不同视域下对“创造性叛逆”的不同解读,力图厘清不同理论框架下“创造性叛逆”的真实内涵,从而减少对“创造性叛逆”的误读。每个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暴露出一定的弊端。随着翻译研究的转向,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翻译伦理视域下来研究“创造性叛逆”,并期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2]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12(2): 33-40.
[3]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4]王向远.“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J].广东社会科学,2014(3): 141-148.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45.
[6]刘小刚.释义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J].中国比较文学,2006(1):129-140.
[7]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78.
[8]江忠杰.从顺应性理论看创造性叛逆[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83-87.
[9]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London:Arnold,1999:61.
[10]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45-56.
【责任编辑郭庆林】
收稿日期:2016-02-23
作者简介:吴秀群(1979—),女,湖北钟祥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7-004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