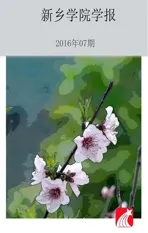《狂人日记》与《地下室手记》的解构主义倾向分析
2016-03-02张艺
张 艺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狂人日记》与《地下室手记》的解构主义倾向分析
张艺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将《狂人日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结构法则的相似性,两者都有解构主义倾向。解构主义文本分析法是一种揭示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而上学本质之间差异的方法。它否认文本仅限于传达作者单一观点的信息,而认为文本解读应该是在文化层面上对不同世界观的多元化、多角度的解读。通过对《狂人日记》和《地下室手记》两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两位作者的解构思维都是积极进取的, 他们通过对两个痴狂人物的塑造,来替整个社会发声,并用“支离破碎”的语言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最后用类似意识流的手法推动情节发展,从而将作品带入更深刻、渺远的境界。
关键词:狂人日记;地下室手记;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法国。解构,或译为“结构分解”,是解构主义论的先驱德里达提出的术语。它最早出现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原意为分解、消解、拆解、揭示等。德里达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了“消除”“反积淀”“问题化”等意义。具有解构主义倾向的文本多是“问题化”的、反传统的,这包括思想内涵的反积淀化,语言艺术的反传统化、陌生化,结构形式的消解化。解构主义论者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中心化 、结构化倾向体现在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就是在对单面性格主人公的塑造和解读中来发现作品的解构主义倾向。德里达不认可西方千年流传的哲学思想与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因而对旧有的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与文本分析加以责难。在文本的思想内涵方面,他认为西方的哲学思想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受海德格尔理念的启发,德里达将哲学中的深刻内涵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在文本的分析中,“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鲁迅特别关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 并深受其影响。笔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思想表达与表现形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有人认为《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解构主义倾向的小说。而在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后,我们不难发现,从单面性格人物形象,到思想内涵的基本特点,再到语言、结构,《地下室手记》与《狂人日记》有着相同的解构主义倾向。本文试从两部作品的基本结构出发,分析两者的解构主义倾向。
一、《狂人日记》与《地下室手记》思想内涵的解构主义倾向
鲁迅先生曾指出自己创作《狂人日记》的意图是“暴露封建家族制度与礼教的迫害”。作品塑造了一个与黑暗社会格格不入的“狂人形象”,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种种弊端和其“吃人”的本质。当“吃人”的事实与民族历史相伴发生之时,鲁迅先生塑造的“狂人”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强烈地抨击黑暗的社会,反叛封建礼教。这一点与解构主义的本质与纲领相类。“解构主义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眼光看待世界,它要的就是离经叛道,要的就是对传统的批判,只要传统存在,解构主义就会用其无孔不入的眼光解构传统,发现新的方向”[1]27。鲁迅先生塑造的“狂人”似一株夹缝中生存的劲草,在恶劣的环境中生长。在小说结尾,“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揭示了整篇文章的基调,实质是作者借“狂人”之口发声,向世间呐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这世上!”尽管解构论者常忽略解构主义中的积极一面,但解构主义仍存在一种永恒的主题——“发现希望”。“解构是对于存在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而这样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否定性的破坏,它是一个关于根基的问题、关于根基与构成根基的事物之间关系的问题”[1]122。在《狂人日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鲁迅先生对传统礼教的批判与解构,更是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提出的希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塑造的“地下室人”与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一样,也是处于时代前沿、社会底层的呐喊者。地下室人受19世纪40年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胸怀大志、期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青年。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文明如“碾压”般的入侵,地下室人理想破灭。他在追梦的旅途中受到种种打击,于是他以被西方文明扭曲了的心灵对西方文明做出“非理性”的判断。通过塑造这一形象,陀氏在俄罗斯大地上树起了“俄罗斯人民真理”的大旗。
地下室人身世坎坷。他是个孤儿,长大后到了政府机关工作。由于对公务毫无兴趣,他在得到一笔巨额遗产后便辞去公职,蜷缩在自己的地下室中,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他以一种“隐形人”“多余人”的身份窥探这个世界,发表着痴狂的“奇谈怪论”。他说:“我什么事也不能干,不论是恶的还是善的,不论是恶棍还是诚实的人,不论是英雄还是爬虫,什么都干不成。现在我生活在自己的角落里,用对谁都没有用的怨恨来刺激自己,我认为聪明人是不能干什么的,只有傻子才干些事。”他称自己是“懒汉”,并以此得意[2]。解构主义论者认为《地下室手记》整篇都以地下室人的“胡谈”推动文章的发展,用这种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来解构受西方文明冲击的俄国社会,揭露其弊端。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也有着双重人格。“狂人”一方面以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病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另一方面以新时代斗士的思想与封建“吃人”的社会作斗争。而在陀氏笔下,《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也有着双重人格,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另一面他是神经错乱的“疯子”。但无论是狂人的“病态”也好,还是地下室人的“精神错乱”也好,他们无不是在借着“疯狂”的外表追求光明与自由。在传统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是固定的, 其价值取向是可把握的。而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形象是非理性的,是难以把握的,是从人物性格的多元化方面对单面性格人物形象的解构。
二、《狂人日记》与《地下室手记》语言艺术的解构主义特点
解构主义论者始终认为,文本的语言应是“延异”的,是向外“扩散”的。也就是说,任何文本的语言都是无法确定的,文本的意义只能是一个不断向外扩散的过程。意义的随意性、零乱性、不完整性不断地拆解形而上学的中心和本源,并且拒绝成为新的中心和本源。意义总是因为语言的限制不断地生成、转换,继而又不断地消失,最终消解了意义本身。中心的消解就意味着取消意义,意义的延异就否定了世界上存在着终极不变的意义。
在任何作品中,由于语言的流动性与无意识性,语言都会成为文学理论家研究的对象。在解构主义的探索中也是如此。德里达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是从语言开始的。从一个角度来说,作家意识的流动性与语言的不确定性使文字有种引人入胜的魅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字的模糊性、晦涩性能把小说引向更细微更深刻的境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意蕴就是在文字的书写中呈现的。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狮子似的凶心, 兔子的怯弱, 狐狸的狡猾。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这里没有情节的推演,甚至没有指涉的对象,但我们能捕捉到彻骨的凉意和恐惧; 而于凉意和恐惧之中,渗透着一种决绝的反抗情怀。近乎陌生化的语言使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于传统文学有缜密逻辑的语言的解构。这种诡异的氛围与黑暗化的表现手法,使我们能感受到环境描写带给我们的无尽想象。又如: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狂人日记》不是一般的白话,它用了欧化的手法,将叙事变得陌生,给人带来奇异的感觉。
再看陀氏的《地下室手记》。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以至于迷信到敬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很迷信。不,您哪,我不想去看病是出于恶意。
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现在,我就在自己的这个栖身之地了此残生,愤恨而又枉然地自我解嘲:聪明人绝不会一本正经地成为什么东西,只有傻瓜才会成为这个那个的。
小说以模糊不清、没有逻辑的语句表现了人物的心理。主人公时常感觉社会上的人都在质疑他,甚至连他自己都在质疑自己。他东拉西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语,而这种不断变换的语言,正是人物内心的表白。
《狂人日记》与《地下室手记》都采用了欧化的语法,读起来很拗口:其语体特征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含混的,而这正是解构主义对语言的要求。这两部小说以向前延伸、向读者内心延伸的手法,通过不确定的表达,得到了确切的含义。
三、《狂人日记》与《地下室手记》结构形式的解构主义倾向
按照“解构”理论泛化后的理解,我们认为解构主义分析法是从整体中分解出部分的方法,把看似统一的文本拆散,侧重于研究文本中的边缘性结构与材料,从而达到否定传统、否定中心内核的效果,使文本的意义变得或隐或现、若即若离,在无限的延伸中不断发现被隐藏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结构主义像是一个核桃,敲开了坚硬褶皱的外壳后人们会惊喜地发现当中的核心;而解构主义更像是洋葱,在被一层一层剖开后,最后只剩下辣眼的虚无。
《狂人日记》在剥开街坊邻居、路人、赵贵翁、古久先生、佃户、医生、大哥这些“外皮”后,“内核”里面呈现一句“救救孩子”的呼声。然而正文前的小序却解构了文章的内核:“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作者在这里似乎没有交代当狂人痊愈后,谁替他发声,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地下室人”也是如此,他有过“美好而崇高”的理想,有过爱,而现在,心里充满着绝望、颓废和痛苦。他返回自身,仿佛只靠头脑生活,只能思考、议论,是一个“以进行意识活动为主的人物,其全部生活内容集中于一种纯粹的功能——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当我们剥开“地下室人”经历过的荒诞可笑的事件,剥开他荒诞的言语之后,也只剩下作者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恰恰又是没有答案、没有尽头的。
四、结语
总的来说,解构主义分析文本的方法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而上学本质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解构主义否认文本仅限于传达作者单一观点的信息,而应该被解读为在文化层面上对不同世界观的多元化、多角度的解读。两个相似的文本在被解构的过程中通常会显示出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彼此冲突。如果我们将一个文本用解构阅读的分析法与传统阅读的分析法作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许多被隐藏与被忽视的观点。当我们感受到鲁迅和陀氏之间的联系时,也应该能感受到《狂人日记》和《地下室手记》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它们的解构思维都是积极进取的。两位作者通过对两个痴狂人物的塑造,来替整个社会发声,并通过解构传统的语言,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用类似意识流推动情节的形式来发展小说结构,达到了一种深刻、渺远的境界。通过对《狂人日记》与《地下室手记》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解构主义倾向与解构的手法使两部小说已经达到一个既清醒地看透现实, 又不懈地追求理想的高远境界,奠定了两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德里达.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M].何佩群,译;包亚明,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M].施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1-43.
[3]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9.
【责任编辑郭庆林】
收稿日期:2016-02-19
作者简介:张艺(1996—),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对外汉语。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7-00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