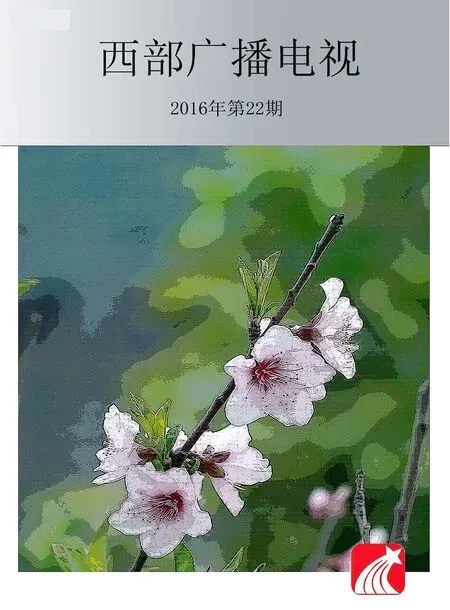遇见众生 看见真实 行随万物
——试论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美学对东方电影的影响
2016-03-01郭哲启
郭哲启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遇见众生 看见真实 行随万物
——试论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美学对东方电影的影响
郭哲启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电影和日本电影作为东方世界电影中的两个代表,以其充满符号化独立鲜活的意蕴和内涵受到世界影坛广泛的特别关注。这是两个被深深烙上民族符号印记的国家。在传统的东方文化熏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充分体现着东方影像美学的叙事特征,但却有着各自也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各个时代的特征。而中国的美学中的常用手法“留白”“象征隐喻”“诗意意境”对这两个民族电影的影响尤为深刻。
中国美学;东方电影;儒道禅;隐喻;留白;
1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
“留白”是中国传统美学最为绝妙和恰合时宜的创作手法,而导演们将其运用到电影中也有诸多耐人寻味的优点。电影其实无处不留白。其一,“留白”可以制造悬念,营造意外,增加电影的可看性,通俗来讲就是抓人眼球。其二,“留白”可以烘托气氛,起到反衬的作用,以此衬彼,言他物以引起所陈之辞。其三,把“留白”这一美学艺术运用到电影中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观影者的主观能动性,给人以充分想象和思索的空间,让观众通过对生活的体验去联想、分析,填补留白中各种各样的情节与心情。有时,构成要素可能才是用来反衬巨大空白的配角。例如,日本导演新海诚的动画电影《秒速五厘米》,唯美的画风和大量的恰如其分的在叙事中穿插着“留白”艺术,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影片共分为三个部分,三个部分都未曾详尽介绍主人公经历的生活变化,也没有明确阐明结局,但是三部分的串联插叙,镜头叙事独特的组接,让观者心中不禁产生了莫名的悲伤。这种感受的获得就是得益于影片“留白”。
2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象征和隐喻”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还有一种为人所常用的手法,即为“象征和隐喻”。在电影中这种方法也被常常运用,譬如“鱼”这一动物的运用,鱼是艺术电影中一种较为典型的意象存在,而鱼在不同的电影中所表现的象征符号却各有不同之处。鱼活跃于隐喻与超现实主义的符号群之中,江河湖海丰茂的中国、日本艺术表达上,时常把鱼当作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鱼在文化通常表现为:轮回、繁衍与性欲等,这些元素既能统一,但在不同的条件下也可以衍化引申成其他的象征符号。以鱼为图腾的文化群落在各地的考古发现之中多有反应,而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之中,鱼更是极其重要的一种符号,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鲲鹏之变。而一直传承至今中国太极图中的双鱼追尾,体现的也便是一种阴阳相合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种从生殖崇拜延伸出来的性文化,也让鱼成了性的一种载体。我们还可以在中国和日本电影中找到很多隐喻和象征,日本电影非常频繁的使用烟花和樱花,如北野武导演的《花火》,岩井俊二的《烟花》《情书》《燕尾蝶》等。这是日本民族“极哀观”的极致美学在镜头中的表达方式。日本人认为,生命在最佳绚烂的巅峰迅速凋零极具美学特性。中国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一个红灯笼和一层一层堆砌的厚厚的墙象征隐喻着封建的压迫。
3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诗意和禅意”
“意境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理论成果,它发源于道家老子的“道-气-象”范畴,并在发展同时贯穿于中国美学史的各个分期,直至唐代美学家提出“境”这个范畴标志着意境说的真正诞生。
而中国“意境”美学对电影的影响,反映出来可以产生一个新名词——“诗意电影”。“诗意电影”非常擅长营造诗歌一般的意境和从儒释道中结合汲取“禅意”。中国早期“诗意电影”的代表作品即有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这是中国早期“诗意电影”的代表作。看这部电影会随着情节流动、情境转移,营造作者心目中的诗情图景。再比如说稍晚一点的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不过是寻常的故事,是常被表现的父子之情。但电影美好的意境一出现,那浓浓的诗意美感,充满中国特色的影调使人流连忘返。同样“诗意电影”的代表人物有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侯孝贤擅长运用不露情绪的长镜头,将机位久久定住不动,或者缓慢的平摇,空镜头转场,使本来平淡的画面产生令人动容的情愫。
4 结语
在这类电影中,故事讲什么已经不再重要,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状态,风格是散淡的,观看时,你就像再品一壶茶,虽不浓烈,但别有味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我们的情感才变得那么细腻,因为他们纪录的才真是我们精神的渴求。
[1]何耀东.古诗词象征手法赏析例谈[J].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2009(7).
[2]刘小梅.中国古典诗歌“意境”与“视域”[J].青年科学,2010(3).
郭哲启(1995-),女,山东济南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