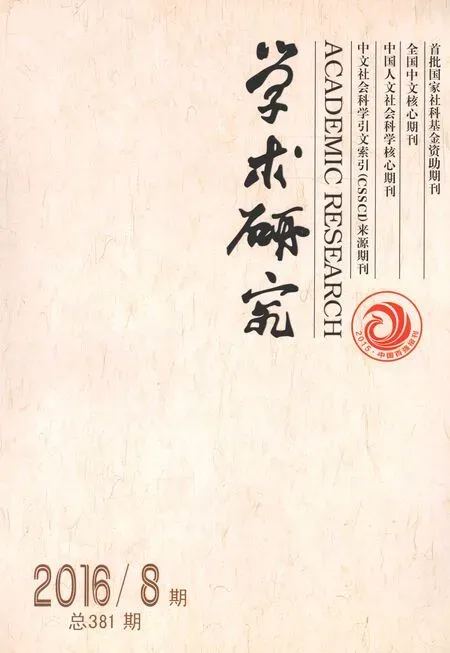强制阐释与过度诠释
2016-02-28毕素珍
毕素珍
强制阐释与过度诠释
毕素珍
强制阐释和过度诠释虽然都是对文学作品的不当解读,然而表面的相似背后实则隐藏着本质的差异。从其所涉及的阐释与文学实践的关系、与文本话语的关系,强制阐释是否具有文学指征与文学价值,以及阐释的动机、性质和目的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过度诠释是对文学作品合法而不合理的解读,而强制阐释则是对文学作品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解读;过度诠释远离了文学作品,强制阐释背离了文学作品;过度诠释尚在文学场内言说,尚有一定的意义可言,而强制阐释根本抹煞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
文学阐释 强制阐释 过度诠释 差异
“强制阐释”是张江基于多年潜心研究,重新审视当代西方文论,概括和提炼其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于2014年6月16日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访谈时首次正式提出的概念。“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其基本特征有四: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强制阐释从根本上抹煞了文学阐释的本体特征,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强行阐释或重构文本,做出符合论者目的的结论,背离了文本的原意,导致文学理论和批评对文学自身的偏离。强制阐释理论的提出,旨在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正当性提出有力质疑,展开有效的辨识和批判,为当代文论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过度诠释”是意大利著名学者昂贝多·艾柯1990年在剑桥大学主持丹纳讲座的演讲中,针对文本解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解读中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造成的过分越界及读者诠释权力的过分夸大提出的一个概念。对于何为过度诠释,艾柯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而是提出“我们可以借用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没有什么规则可以帮助我们断定哪些诠释是‘好’的诠释,至少还有某个规则可以帮助我们断定什么诠释是‘不好’的诠释”。[2]艾柯尝试着在理论上把某些诠释界定为过度的诠释,探求对诠释的范围进行必要限制的路径。
在文学阐释活动中,表面看来,强制阐释和过度诠释都是对文学作品的不当解读,二者似乎大同小异,相差无几,然而事实上,通过分析即可发现二者存在本质差异。本文拟就强制阐释的定义及四个基本特征所涉及的阐释与实践的关系、与文本话语的关系,强制阐释是否具有文学指征与文学价值,以及阐释的动机、性质和目的对二者进行比较,旨在厘清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
一、阐释与实践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存在与意识相互关系的理论,文学活动是一种人的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和反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4]文学归根结底来源于生活,是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理论是从文学活动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由此造就了文学理论应当具有的实践性品格。此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还在于它必须经得起文学活动的实践的检验。
“西方文论的生成和展开,不是从实践到理论,而是从理论到实践,不是通过实践总结概括理论,而是用理论阉割、碎化实践,这是‘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5]强制阐释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的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直接从文学以外其他学科截取和征用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为了能够达到主观目的,论者不惜违背作品解读的基本原则,从作品的片言只语里、边边角角中,通过精挑细选,拼接剪裁,甚至无中生有,对文学作品做出符合主观意图的阐释,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理论的来源不是文学实践,在许多情况下,文学文本只是这些理论阐述自身的例证,研究对象也偏离了文学本身。“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主观预设的批评,是从现成理论出发的批评,前定模式,前定结论,文本以至文学的实践沦为证明理论的材料,批评变成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理论目的的注脚。”[6]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甚至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批评方法,脱离文学实践与经验,违反文学理论生成的本来过程,无法做出有文学效能的解读,提出科学的审美标准,无益于文学理论生成和丰富的方向,更无法指导文学的创作和生产。不同的文学批评,都会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褒贬是非、抑扬臧否的分析和评价,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倾向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红学家会在一部《红楼梦》中看到不同内容的原因。文学阐释有倾向、有立场是正常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立场、路径、结论等只有产生于无立场的合理解读之中和之后才是合理的,文本与结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绝不可倒置。只有这样,文本经过阅读、鉴赏、批评,才能变成有血有肉的活的生命体,才能变成审美对象。与强制阐释从理论到实践的反序认识路径不同,过度诠释是从文本出发,从文学活动实践出发,不预设批评的立场、模式、路径,在与文本的对话中逐渐得出结论,从认识路径上说,遵循的是一种由实践到理论的正序认识路径。
简而言之,强制阐释脱离文学实践,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做符合阐释者主观意图的阐释,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是一种反序认识路径。过度诠释以文学实践为基础,从对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不预设立场,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尽管在分析之路走得过远,遵循的依然是一种正序认识路径。
二、阐释与文本话语的关系
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有两极,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和审美极。艺术极是作者写出来的文本,而审美极则是读者对文本的实现。”[7]在文学创造和接受过程中,文本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文学作品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文学丰富内涵和感染力的存在,使得文学阐释可以各式各样,因人而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本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解读,“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8]阐释的界限——文本——就在那里,对作品的阐述和引申可以走到任何地方,但文本最终会将其拉回来。在文学解读过程中,我们应该尊重作品的先在制约性。面对同一文本,见仁见智的解读之所以可以被认识和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是在阅读同一文本的基础上进行阐述交流。无论是对前人发现的深化、推进和修正,还是提出全新的见解,有一点必须遵守的,就是不能离开文本话语。在尊重文本的基础上,阐释者把对作品的感受、体验、理解、判断一并结合起来对作品进行解析,力图达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程度,才有可能实现对文本的正确阐释,千古一理,概莫能外。
文学创造是一种个体性很强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是一种非常具体的个别存在,因此文学批评的对象也常常是具体的作品和作家的个体性创造。艾柯“文本意图”的提出,使我们仿佛听到了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一种回响,文本意图要求回到文学文本自身,考察其语义策略和文本意图。因此无论是高屋建瓴还是微观注视,文学阐释都要求对作品进行梳理、选择、集中以及概括。文学阐释与文学作品密切相关,决不能疏离作品,任何诠释必须是立足于文本及文本意图,文本意义产生于作者、文本和读者的互动过程中。而强制阐释听从最不受节制的主观意图的唆使,将一部文学作品任意玩弄于股掌之间,随意摆布,是一种主观预设的批评,具体表现为前置立场、前置模式和前置结论。阐释者在批评之前就已经预设明确的立场,根据立场选定标准和批评文本,其目的不在阐述文本,而是为表达和证明立场。阐释者在介入文本之前,就已选好批评理论的模板和式样,并用它来强制框定文本,根本无视文本自在含义的表达。阐释者的批评结论同样产生于文本解读之前,批评的目的也是为了证明其前置结论的正确性。这种阐释看似和文本相关,但在实质上已无关联了。强制阐释这种从现成理论出发,远离、无视甚至背离文本含义,依据主观需要解读文本,剪裁文本,选择文本的做法,必然会使论者不把注意力放在文本上,在阐释过程中缺乏诚意,把主观意志凌驾于作品与作者之上,背离了文本话语,使文本沦为主观需要的奴隶。这种强制性在实践上彻底违背文学阐释的基本原则,丧失了阐释的合法性。
过度诠释是阐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文学作品进行穿凿附会的认知和评价,曲解了文本话语,违背了文本的连贯性及原初意义生成系统,阐释者在文本中所发现的东西不是文本所要表达的东西。阐释者由于过度好奇,过度自负、自信,将一些偶然的东西视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呈现一种过度倾向。这同读者反应理论和解构理论过分推崇读者的能动作用、任意诠释和游戏文本的主张相关。以罗塞蒂对但丁的解读为例,罗塞蒂试图在但丁的文本和共济会—罗塞克卢的象征符号之间寻找某种相似性,结果没有发现多少相似性,把某种相似当做本质的相似,从而在过度诠释的路上越走越远。过度诠释研究作品的构成因素、运行机制及其相互关系,其研究焦点放在文化、道德和心理等方面,而非重点关注文本的审美和结构等因素,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基于文本题材、形象、语言、结构、风格等作品构成中问题的解读,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文学文本,它曲解了文本,却未背离文本,其阐释虽不合理,却也合法,虽与作者的创作本意有所抵牾,但不排除作品本身客观上显示了其阐释的内涵的可能性,正如我国古代文论所言,“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9]“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10]历史对各种文学解读的大浪淘沙,终将证实某些过度诠释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意义。
三、强制阐释是否具有文学指征与文学价值
各个学科都有不同的特定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可以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但其研究理论和方法并不具有普适性,跨学科的运用需要依据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相应的变通和调适。而强制阐释通过对概念的堆砌搬弄、理论的生吞活剥,直接从其他学科截取和征用现成理论,脱离文本和文学本身,消解文学指征,对文本做非文学的阐释,无法给出具有文学价值的理论探讨。红学大师俞平伯逝世前对自己毕生研究的红楼梦只说了一句,“《红楼梦》说到天边还不是一部小说”,其中所包含的就是对《红楼梦》研究中某些消解文学指征缺乏文学价值的强制阐释行为的拒绝。
强制阐释挪用、转用或借用种种文学场外的理论如传统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理论、政治、社会、文化理论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生搬硬套,盲目移植,使阐释背离了文学的特质。强制阐释运用话语置换、硬性镶嵌、词语贴附以及溯及既往这四种策略,把非文学的理论转化成文学的理论对文本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或将文本的原生话语锁定于场外理论的话语框架之内,或打碎分割文本,镶嵌到场外理论的模式之中,或将场外术语注入文本,使作品获取疏离文本的意义,或以后生场外理论来检视前生的历史文本,并不能恰当地解释文本,对文学、对理论,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具备任何文学意义或价值。
文本可能存在多种诠释的可能,过度诠释问题产生的关键在于它越过了合理诠释的连贯性标准、简洁经济标准、互文性标准、相似性标准等内部标准和外部标准,导致文本的意义发生增殖,造成过度诠释。虽然对文本的诠释超出了文本意图的界限和范围,但过度诠释是对文本内容进行诠释,就文本所未曾说出的东西提出问题,依然是对文本做文学场内的阐释,因而还是可能有文学价值的。例如,从严谨规范的学术立场来看,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多有断章取义和过度诠释之嫌,但并不对其解释的有效性构成障碍,这是因为她的解读是基于文本的解读,具备明显的文学指征与文学价值。卡勒认为,过度诠释“将其思维的触角伸向尽可能远的地方”,“有可能揭示出那些温和而稳健的诠释所无法注意到或无法揭示出来的意义内容”。[11]一些过度诠释的目的是力图将作品文本与叙事、修辞、意识形态等一般机制联系起来,目的不是去重建文本意义,而更多地想去探讨作品文本赖以起作用的机制或者结构以及文学、叙事、修辞语言、主题等更一般性的问题。这种试图去理解文学文本运行机制的努力是一种合理的学术追求。有些诠释走得太远,诠释得太多,在解读中实现意义的增殖,是不正常、不合适的。而有些则可能产生新的发现,发现新的意义,或更为有趣的见解,至少对文本阅读和诠释现象产生某种惊醒和导引的作用。对文本的合理阐释只能根据一个读者群或一个文化体系约定俗成的整体回应来判断,而群体共识的形成是一个需要不断得到修正的长期过程。借助文化达尔文主义,在历史选择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排除有些文学解读的新内涵、文本意义的新发掘产生于这种“偏激的深刻”。在文学解释活动中,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实现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古今中外,一些文学作品正是通过这种解读方式,实现了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
四、阐释的动机、性质和目的
文学作品鼓励诠释上的自由,阐释者的积极作用就是对文本意图进行推测和寻觅。这种推测和诠释,不是一个无奇不有自由联想的过程,而是必须服从文本自身的指导,文本的存在使诠释有所归依和限制。“你可以从文本中推出它没有明确写出来的东西……但你不能让文本说出与它本来说的相反的东西。”[12]“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培养忠实和尊敬的练习历程,我们心中必须受到某种深刻敬意的感动,被我以前说过的‘文本意图’所生出的敬意所感动。”[13]文本的开放性和意义的无限性绝非毫无限制的无限性,它针对的仅仅是文本语境中的无限性。无论是强制阐释还是过度诠释,阐释者都没有处理好阐释者的权利和文本语境要求之间的辩证关系,都过分强调阐释者的权利,阐释行为都发生了越界,不过,同是越界,同为非正当阐释,二者的动机、性质和目的却大相径庭。
文学作品一旦完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作为社会文本有了属于自己的命运和意义。文本的结构方式本身就包含了两种解读的可能性:“批评思维能够与它的处理的模糊现实建立一种令人赞叹的默契关系;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中,它会导致最全面的分裂。”[14]强制阐释显然属于后者,阐释与文本、与文学在本质上彻底分裂。强制阐释是对理论做符合主观目的的滥用,征用文学领域以外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生拉硬扯解释文本,“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批评者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把文本捶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15]是对文学作品的损伤和粗暴践踏。文学阐释活动本应是一个阐释者与文本互动的双向回流过程,其目的是阐述、挖掘、探索文本含义。文学阐释的要素如立场、路径、结论等只有产生于无立场的合理解读之中和之后才是合理的,而强制阐释有既定的理论标准,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选择、剪裁文本,是脱离文本内容和含义而存在的主观意向的表达。诠释者无视由文本的连贯性、上下文语境及结构的稳固性所决定的文本的自主性、持久性和整体性,意欲把从作品局部得到印证的结论上升为对整个文本的阐释以及对理论的论证,甚至力图将其他阐释主体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也包括在他的阐释和理论之中,其阐释实质上已与文本丧失关联。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这样的阐释没有任何有效性,只会带来阐释的混乱,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本,而是论证主观结论,进而证实其所持理论的正确性和普适性。
过度诠释是对文本的误读,诠释者以对一些偶然巧合重要性的过高估计或倒果为因的思维方式,以过于丰富的想象与联想对文本的诠释理解过了度,其诠释不符合文本的连贯性整体原则,对文本某一部分的诠释不能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所证实。过度诠释问题的产生与西方神秘主义密切相关,神秘主义者认为诠释的使命就是去搜寻作品一字一句后面隐藏的神秘意义和未曾言说的内涵,以及或许并不存在的终极答案。此外,代码理论的系统结构使人们对文本的各种预设和推论成为可能,而有效的文本理解一般来自于对相关系统结构的有效控制和运用,不好的诠释或过度诠释则往往是错误地运用系统结构所致。过度诠释问题也与误读理论的倡导有关。过度诠释行为的动力表明,其出发点是源于阐释者解析作品本身的善良愿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对文学作品更加完整深入细致的多元理解。比如鲁迅塑造阿Q形象的本意是画出麻木沉默的国民灵魂,让世人清醒头脑,但也曾有人怀疑作者在泄私愤,是在借阿Q影射自己或另外的某个人,以至于鲁迅如此慨叹:“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16]诸如此类的解读,是脱离作品实际的,是对作品的误读,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阐释者对作品含义挖掘的努力和愿望。
总之,过度诠释与强制阐释二者之间巨大的本质差异在于,过度诠释是对文学作品合法而不合理的解读,而强制阐释则是对文学作品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解读。过度诠释远离了文学作品,强制阐释背离了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文学鉴赏的接受层次,对于批评家来说,文学阐释是对作品的理性检测和衡定,它要求阐释者在感受、理解作品的基础上作出尽可能恰当的客观评价,更具科学研究意味,更着眼于实现包括作品审美价值、文学自身发展价值等在内的广泛的社会价值。就此而言,强制阐释和过度诠释皆非对文学作品的正当阐释。作为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文学阐释既推动文学创造,影响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又推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具有深刻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度诠释尚在文学场内言说,尚有一定的意义可言,而强制阐释根本抹煞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除了带来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混乱,对文学活动不会产生丝毫贡献与意义。
[1][6][15]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8][11][意]昂贝多·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4、42、1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5]张江、毛莉:《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第4版。
[7]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29页。
[9]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顾学颉校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4页。
[10]谭献:《复堂词录序》,顾学颉校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9页。
[12][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俞冰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7页。
[13][意]安伯托·艾可:《艾可谈文学》,翁得明译,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1页。
[14][比利时]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16]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I02
A
1000-7326(2016)08-0008-05
毕素珍,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