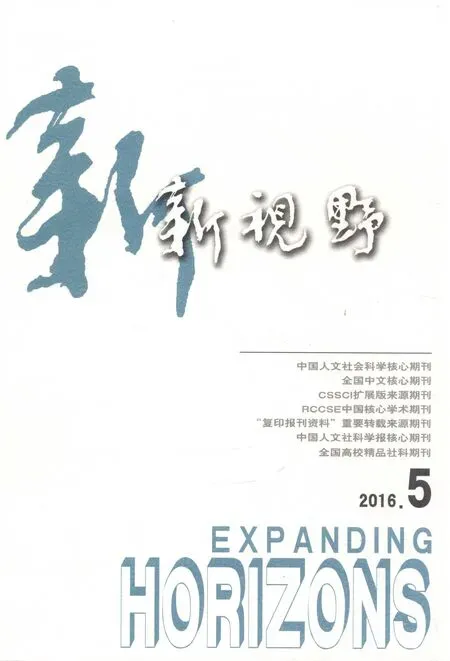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
2016-02-28杨生平
文/杨生平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
文/杨生平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世界关系上彰显人文精神,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奉行道德至上,在人与自身关系上弘扬精神人格。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着中国人的中国梦,也影响着近代欧洲发展及启蒙思想形成。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经历了曲折,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人精神充盈、人际和谐和文明行为养成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基本特征
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既要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组成的不同内容与元素,又要考虑到这些文化内容与元素的作用过程及其效果;既要看到这些文化正面倡导的东西,又要看到这些文化自身无法涉及到的盲点及其相应的负面影响;既要看到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包括国外影响),又要看到它在当前的意义。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是积极进取的文化,它能在保持基本价值取向与风格的基础之上,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吐故纳新。这里,我们只能从主流文化入手,对其基本特征进行简单分析,并作简要历史梳理说明其意义与价值。尽管不同时代主流文化不完全一样,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形成儒释道互补的主流格局几乎是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达成的共识。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看,它彰显人文精神。与西方文化强调“人类中心”不同,中国文化主张顺应自然,适应自然,重视“天人合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当然主张道法自然,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面前只能被动顺受,中国文化主张积极面对自然,发挥人的主动性。它认为虽然成事在天,但谋事却在人。孔子甚至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想事成,不努力肯定不行,但光靠人的努力也同样不够,必须做到“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更是表现在如何处理人的精神家园上。与其它文化将人的精神家园重心设置在彼岸世界不同,中国文化则是把人的精神家园放在此岸世界,认为只要努力,在现实世界中就可以实现精神圆满。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2]这种“重人生轻鬼神”的修养方式自然更是一种充满现实精神的人文关怀。儒家强调“人皆可成尧舜”,主张只要认真修行,人人皆可达到“圣人”境界。不但如此,既使本源于印度的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也被改造得更有人文情怀。禅宗是在印度佛教影响下中国自产的佛教,它主张人性即佛性,认为修炼不必居于庙寺,在家亦可修炼(即居士),提倡顿悟成佛。中国文化这些特点自然构成了其它文化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其难以逾越的屏障。虽然中国文化尊重自然,但它却没有形成一套如何尊重自然特别是在尊重自然的同时改造自然的办法(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注重实践,但缺乏一套系统的认识论体系)。
其次,从人与社会关系看,它奉行道德至上。儒家本是一套道德思想,它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提倡以“仁义礼智信”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自汉武帝以后,它便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政治学说(即政治道德化)。与此同时,儒家的“礼”“序”观念也被本体论化,成为一种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世界秩序(从董仲舒的宇宙论化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本体论化)。从一般意义上说,将以“德”为核心的思想落实于全社会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充满温情与人情,因而最终也会使它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人情社会自然让人们能体会到社会温暖,但同时也会导致找关系、走后门现象)。但由于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之中维护的是封建等级秩序,这也就导致其不可否定的局限。另外,将道德秩序用于管理社会似乎还有一定道理,但把它用于管理社会经济与政治就不得不说有明显弊端了,它必然会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政治建设。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导引出资本主义的。
再次,从人与自身关系看,它弘扬精神人格。中国文化十分注重人的精神,儒家强调通过“养浩然之气”充实人的精神,佛教强调通过修行达到成佛境界,道家强调通过顺任自然达到自由逍遥境界。而它们之间又有互补作用,不同人都可从中找到精神修炼与充实方式。所以,有人用“拿得起”(儒家的“有为”)、“放得下”(佛教的“空”)和“想得开”(道家的“无为”)来比喻中国文化儒释道互补状况,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仅如此,中国文化更注重精神修养的社会关怀。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4]并把人格区分为“信善美大圣神”六种境界。道家强调清静寡欲,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5]佛教在讲修炼成佛时,也主张用爱心、慈心、同情心去关爱众生,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些无疑都是中国文化弥足珍贵的遗产。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梦
就中国梦而言,一般人只知道它的直接含义——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却不一定想到其引申含义。既然是复兴之梦,那它自然还应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说明目前中华民族并不强大,二是说明中华民族曾经强大过。如果没有强大过,又谈何复兴?若果真如此,人们自然又要反思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中华民族曾经靠什么强大,二是中华民族为何又是怎样走向衰落。只有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急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我们又该怎样实现复兴。
谈到中国民族曾经的强大,自然不能不从《礼记·礼运》的“大同”谈起。《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正是这个“大同”理想引领着不少中国封建帝王和贤人圣士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使中国民族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从汉武盛世到开元盛世,从永乐盛世到康乾盛世,无不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离“大同梦”的实现还有一段距离,一方面缘于历史的间断性(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间都不很长,之后都会有一段长时间的滑坡以及频繁的改朝换代斗争),另一方面缘于其等级森严,制度严酷。马克思就曾这样评价过康乾盛世:“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6]正当清政府仍以天朝大国自居,津津乐道于八方朝贺之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大门。
“大同梦”破灭了,但大同思想却没有终结。自鸦片战争以后,不少志士仁人都用它去建构自己的思想并试图以此再次圆梦。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莫不如此。洪秀全把大同思想与基督教结合起来,试图建立他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就曾专门写过一部脍炙人口的著作——《大同书》,希望通过它拯救中国亦拯救世界,并对大同进行了解读。他说:“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分等殊异,此狭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此广大之大道也。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一内外为一,无所防虞,故外户不闭,不知兵革,此太平之道、大同之世。”[7]孙中山更是直言不讳他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与大同的关系,并以“天下为公”为其响亮的政治口号。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说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8]
谈到大同,自然要涉及到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它们自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前者虽然也有比较明确的理念与具体的方法,但它毕竟只能算是一种抽象的理想,没有坚实可靠的现实与理论基础;后者则是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分析得出共产主义结论的)。因此,不能把两者混同,但这又不排除它们之间存有联系。从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它的最早中文译名就叫“大同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太平天国时,曾转述西方在中国传教士的话说:“欧洲近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中国很久以前就有了。”有资料证明,康有为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但他却以这种学说“主张暴力,为中国人所不取”为由而放弃。所以,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9]康有为没有找到,洪秀全、孙中山等同样也没有找到。因此,中国近代中上一次又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都以相继失败而告终。最终,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这条路,这才拯救中国人于水火并建设了新中国,把中国人民进一步带上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如果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现代中国梦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实现大同梦想就是传统中国梦。这两者虽有质的区别,但也不可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其中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既包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民情相结合,也包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若用这个思路去分析两种中国梦,那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圆了近代中国人的伟大梦想,也是圆了整个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伟大梦想。与历史上几大盛世相比,这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在实现人民自由民主平等基础之上的综合振兴。因此,它的意义更明显,更重大。反过来,将传统中国梦的意义充实到现代中国梦之中,又会使它更具人文关怀。与美国梦的个人主义和欧洲梦的整体协同不同,中国梦是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结合、群体与个人的有机结合。它既注重社会与自然多方面协调发展,又注重群体与个人的协调发展;它既注重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又注重人际和谐与人间温情。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人的中国梦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也曾影响着西方社会发展。由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统治,13世纪的欧洲明显落后于中国。此时的欧洲经济十分萧条,思想禁锢异常严厉,急需一场经济腾飞与思想解放运动以实现社会变革。一般认为,文艺复兴起到了思想解放的目的,其口号是回到古希腊和古罗马,而文艺复兴思想又直接影响着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这里的关系自然存在,但有一点也同样不能忽视:即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从13世纪到18世纪欧洲人做了近五百年的中国梦。
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深深被中国富裕吸引,一呆就是近20年。1295年回国后,他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财富的丰盈,宫殿的华丽,生活的奢华和都市的发达。由于这本书的出版正赶上欧洲印刷术革命,因此,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中国的富裕深深吸引着众多西方政客和商人把贸易目光转向中国。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也正是受这本游记的影响,本想前往中国,却无意中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随着“富裕中国”在欧洲的盛行,许多西方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传教士与商人不同,他们带来和带走的是文化。随着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富裕中国”又增添了“美丽”成分,中国对欧洲的吸引力又增强了。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描述中国:“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10]物质上的富裕与精神上的充实,让“中国”渐渐进入急待破旧立新的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视野。德国著名哲学家、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茨通过传教士了解中国后,十分感叹地说:“我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中国人为了使自己内部尽量少产生摩擦,把公共的祥和、人类共同生活的秩序考虑得何等周到,较之其他民族的法律不知要优越多少”,[11]“特别令我们欧洲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农民和仆人之间也相互问候,如果多时不见,彼此十分客气,相敬如宾,这完全可以同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举止相媲美”。[12]法国著名哲学家、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伏尔泰更是把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上升到建设欧洲人文思想的高度。伏尔泰十分崇拜孔子,甚至自称是孔子的弟子,认为“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徒弟”。[13]他大声疾呼法国要以中国文化为标杆“全盘华化”。为了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独特的情感,他刻意改编了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取名《中国孤儿》,并把背景从春秋时期移到宋末元初。显然,伏尔泰想借吸收中国文化元素抨击当时欧洲的世袭贵族制度,重塑欧洲人文精神。
其实,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在赞叹中国时并没有盲目赞美中国,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弊端。莱布尼茨就曾明确指出中国人在思辨与科学方面明显不如欧洲,伏尔泰则指责中国人对传统过于推崇,以至丧失了进步能力,他甚至惊叹这样聪明的民族为何在科学与音乐方面表现得如此幼稚。当然,欧洲人热衷中国,醉翁之意不在中国梦,而在构筑他们的欧洲梦。事实看来,那时的中国也的确为之提供了基础。试想一个长期受宗教神学统治、急需人性解放的民族,一旦发现有这样一个既如此富裕又似乎充满人情味的国家(莱布尼茨曾把中国儒学称为自然宗教),又怎能不欣喜若狂。但欧洲人建筑他们的欧洲梦,明显在立足自己基础上借鉴他人。如果说中国文化对启蒙思想“主体”(即人文精神)建构起了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启蒙思想的另一关键词——理性(即科学精神)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可是,当欧洲人完成他们的欧洲梦后,他们眼中的中国梦就开始变味,此时他们便从对中国的赞美和迎合转向抨击和豪夺。孟德斯鸠就这样无情抨击中国:“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14]“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这就使中国人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淳朴同时也是最奸诈的国家”。[15]现代经济学鼻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则从贸易不自由与贫富分化严重等方面,宣判中国经济衰落的必然。面对思想家的批判与引导,面对中国财富的巨大诱惑,西方政客与商人在中欧贸易的巨大逆差中终于发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鸦片。渐渐地,他们感到用鸦片解决问题已经不能满足他们胃口,于是就发动了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随着大英帝国的建立与衰落,欧洲梦也逐渐从顶峰降到低谷。20世纪随着美国的强大,美国梦又成为世界强音。可21世纪伊始,美国又渐露衰落势头,此时人们又开始寻找和议论起别的梦想。2004年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写了一本畅销书——《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此书出版不久,他又把目光转向了中国,进一步认为中国梦才是人类未来的新希望。历史经验表明:别人的说法我们需要兼听,但关键得有自己的判断,走好自己的路。
四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经历了曲折,但它在当前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时代价值。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随着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引起了国际人士的关注。人们一般认为这些国家经济奇迹的创造,跟他们推行或信奉儒家文化有关。上个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久违的以儒家为核心的国学再次进入国人视野并受到热捧。近些年来,国学热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时间,不少人以吟诗诵词,甚至恢复传统礼仪为时尚。客观地讲,国学热在国内的升温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合理性。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渐感精神生活空虚、人际关系淡漠与社会文明行为缺失。对此,仅就儒家思想简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首先,儒家思想有利于精神充盈。与人有物质需求因而要通过劳动创新物质财富来满足一样,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同样需要付出辛勤的劳作,只不过这种劳作是需要通过修炼或修养的方式来完成。在儒家看来,人最重要的价值以及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精神,但因人常受利益的诱惑与环境的影响,这种精神需求常常被忽视或淹没。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16]要想获得人的至高价值,做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人,就既要有对人之为人的正确认识,更要有艰难的践行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从“格物穷理”开始。“格物穷理”既要格物、致知,也要诚意、正心与修身。光有前者,没有后者,是知而不行;光有后者,没有前者,是行而无知。只有两者结合,做到知行合一,才算真正完成了人之为人的修养过程。在一般儒家看来,修养是一个不断提升与演进的过程,做“真正的人”是起码标准,而达到“圣人”则是至高标准。孟子更是把人的修为分成“信、善、美、大、圣、神”六种人格。在儒家思想中,人的修养虽然注重的是道德境界,但它却不只有“至善”的效果,更有“真”“善”“美”统一的意蕴。
其次,儒家思想有利于人际和谐。由于儒家的精神修养说是以“仁”为基础的,因而它自然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与社会风气的好转。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不但如此,孔子还指出了“仁”的由近到远的实施方法。他说,“仁者爱人”,“爱必由亲始”。所以,“孝悌”是“仁之本”。孟子更是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17]儒家不仅重视一般人际关系,也十分重视君民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并把“仁爱”思想贯彻到底。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8]这种有着既爱他人又爱万物的“民胞物与”思想,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充满温情与感情。历史事实也证明,儒家思想滋养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创造,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封建明君与志士仁人,激发了众多后贤创作了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名言佳句,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梦想而奋斗。
再次,儒家思想有利于文明养成。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儒家不仅提出“仁爱”思想,更是通过“礼”和“仪”把它落实于人的行为之中。儒家文化的“礼”,既是一种修养,又是一种规范与秩序。作为修养,它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至诚至敬;作为规范,它要求人们对不同人与物要有不同礼数;作为秩序,它要求人们在不同领域遵守不同规则。所以,“礼之用,和为贵”。作为礼的外在形式,“仪”对礼的实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仪”既可以强化礼的内容,亦可以强化礼的效果。中国古代有各种礼仪,有祭天、祭地之礼仪,也有生活用膳和婚丧嫁娶等礼仪。不过,儒家更重视丧礼和祭礼,特别是父母的丧礼(即慎终)和追念祖先的祭礼(即追远)。孔子的学生曾子就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19]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0]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既要注意自己内心修养(即“质”),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与衣着修饰(即“文”)。由此可见,儒家不仅提出了“仁爱”思想,更是通过“礼仪”由近及远、由内到外将它落实落细落小,处处规范并影响着人的言行。经过多年的盛行与发展,后继者更是把这些思想总结为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行为规范文本,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女儿经》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思想非常重视幼儿教育。这些文本往往成为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经典范本。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幼儿时期的教育,对一个人一生文明举止的养成与健康心理的形成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历史事实也证明,儒家这些思想也确实对社会成员文明言行的养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十分复杂,作用也有时间区隔,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总体阐述。仅就儒家思想而言,它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明显的重义轻利、重精神人格轻社会人格、重私德轻公德等弊端。我们不能因今天精神匮乏就盲目推崇儒家思想,毕竟我们要在解决精神文明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强大的物质文明。可这些单靠儒家思想是无法根本实现的。试想在目前竞争异常激烈的全球化浪潮中,一个没有完整人格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又如何能赢得足够发展的空间?因此,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显不合当下时宜,但经颜元改造后的“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则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
注释:
[1]《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
[2]《论语·先进》。
[3]《论语·雍也》。
[4]《孟子·离娄下》第十九章。
[5]《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
[7]康有为:《礼运注》,《康有为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5页。
[8]《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94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0]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11]莱布尼兹:《中国新事萃编》,孙小礼:《莱布尼兹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12]莱布尼兹:《中国新事萃编》,第111页。
[13]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4年,第253页。
[1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61年,第129页。
[15]周宁:《永远的乌托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16]《孟子·公孙丑上》。
[17]《孟子·梁惠王上》。
[18]《孟子·尽心上》。
[19]《论语·阳货》。
[20]《论语·雍也》。
责任编辑顾伟伟
G122
A
1006-0138(2016)05-0104-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全球化基本矛盾、特征和意义研究”(11BZX020)
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北京市,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