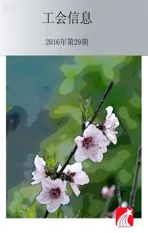释“乡”
2016-02-27水天
文/水天
释“乡”
文/水天

“乡”字在中国,是重要的表述符号,使用频率很高。
“乡”字与人的出生地、初居地和祖籍地密切相关。人的出生地、初居地与祖籍地,按区域分,大到国,中到省、市、县,小到乡、村。可是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地、初居地和祖籍地,经常使用的名词,则大多与“乡”字相关联,而不使用“省”、“市”、“县”、“村”。这比如,表述自己的出生地、初居地和祖籍地,叫家乡、乡梓、吾乡;客居他方,称自己的出生地、初居地为故乡、乡关,称客居的地方为异乡、他乡;人在他方,怀念出生地、初居地,叫怀乡、乡愁;人在他方即使遇到同省、同市、同县但不同乡的人,也互称同乡、老乡;同一个地方的人形成的友谊,叫乡谊、乡情;同一个出生地、初居地共同的口音,叫乡音;明清以来,在北京等大城市出现的同乡会,其实是某省、某市或某个地区的人结成的组织,却不用“省”、“市”等命名,而是用“乡”字。
从字源上解释,“乡”同“飨”,其最初含义,是两个人相向而坐,一个人招待另一个人饮食。后来才假借为它意。“乡”后来与人的出生地、初居地、祖籍地密切相关,是在“乡”成为一级行政区的称谓之后。
自唐朝开始直至当今,乡一直作为县以下、村以上的行政区域。以“乡”标注的行政区域,延续至今已经有1000余年的历史。其间,乡的规模有大有小。但无论如何,乡的规模总在县以下、村落以上。笔者认为,这种特有的行政区划,隐含着为什么“乡”成为故园、老家代名词的密码。
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在传统社会时期,人出生在某一个具体的村落里。及至渐渐长大,人的活动范围则不可能局限在这个村落。私塾就读、田野劳作、亲族联谊以及简单的商业往来,必然会与邻村、邻村的邻村建立某种关联。换句话说,人之出生与最初的生活区域,是以所在村落为中心,辐射到周边若干个村落。没有特殊的需要,活动区域不会大到整个县域甚至更广阔的范围。而这片经常活动的区域,大致超不过一两个乡的范围。因此,在人的生活中,以至于在人的记忆、意识乃至情感深处,乡,而不是村,也不是县,更不是省,成为除家庭院舍以外关联度最高的地域。村过于狭小,不足以代表生活区域;县、省太大,对于尚处于垂髫、年少和青年阶段的人来说,又显得遥远与陌生。在人们居家生活、学习、劳作的时候,乡是伴随着他们生活的最真切的外在环境;在他们离家迁徙、漂泊他方之后,乡则成为记忆中和心灵深处最难以忘怀的地方。
正是因为乡与人的这种特殊关联,“乡”这个字,就成为人们表述出生地、初居地和祖籍地的代名词,于是,在表述时就有了家乡、故乡、乡土、乡里、乡梓、乡关;就有了乡音、乡情、乡谊。也正因为如此,身在他方的人才有了怀乡与乡愁。乡作为故土、故园、老家的代名词,后来又进一步被“扩大化”地使用,演化出他乡、异乡、老乡、同乡、同乡会、同乡会馆等超越“乡”范畴的称谓。重感情的人,还将曾经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甚至人们将帝王驻跸的地方叫帝乡,将梦里的情境叫梦乡。千百年来,尤其是在交通与通信十分不便的传统社会里,“乡”字与人生际遇息息相关。它关涉到人的居住与迁徙、生活与记忆、人际交往方式等方方面面。它甚至超越了单纯的地域概念,成为颇具感情色彩的字。如“乡愁”,一个“乡”字加上一个“愁”字,涵盖了客居之人思念家乡故土的全部情绪在里面。唐代诗人崔颢曾做《黄鹤楼》一诗,其中那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不愧为表达乡愁的“千古擅名之作”;而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以其结尾那句“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从更加宽广的视野,表达出对乡国的一种绵绵思念的愁绪。
“乡”字还泛指农村。兴许是因为“县”这个词,不仅包括了农村的范畴,还包含着城市的因素,而乡以及乡以下的村,则构成完全意义上的农村。所以,“乡”字,就成为农村社会的代名词,这如:乡村、乡土、乡下、乡野、乡间;地处偏远的农村叫穷乡僻壤。农村人则被称为乡民、乡人、乡党、乡亲、乡下人,甚至还出现带有贬义的称谓:“乡巴佬”;在传统农村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叫乡绅;农村中的医生叫乡医;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规矩约定,则被称为乡俗和乡规民约。也正因为“乡”字泛指农村,我国的学者在从事农村研究和教育实践活动时,也广泛使用“乡”字。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研究我国农村社会,其结集就叫《乡土中国》;1926年,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搞的农村教育实验活动,就叫乡村平民教育实验。

由此看来,“乡”字与国人密切关联,它关涉到人们的心灵世界和内在情感,关涉到人们的日常语言表达。在网络热词日益走红的当今,“乡”字的地位,对于我辈来说,是永远不会落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