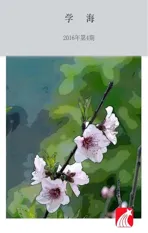有别于“心本体”的“意本体”*
——对作为宋明新儒学归宿的刘蕺山哲学的重新定位
2016-02-27张再林
张再林
作者简介: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特聘教授。西安,710048
有别于“心本体”的“意本体”*
——对作为宋明新儒学归宿的刘蕺山哲学的重新定位
张再林
内容提要蕺山学与其说如牟宗三所认为的那样,仅为阳明心学的补充和完善,不如说以其以“意”易“心”,代表了一种迥异于“心本体”的全新的“意本体”的哲学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崛起和形成。而“意”的合内外、一天人的性质又决定了,一种真正的“意本主义”实际上也即一种“身本主义”。这种身本主义不仅使蕺山的本体论与工夫论彻底地打并归一,而且使其学说最终实现了从宋明新儒学哲学的“意识知觉”范式向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行为”范式的理论皈依。也正是在这里,为我们豁显出了牟宗三中国哲学解读中的那种流于“康德主义”的理论误区,并使“超越牟宗三”成为今日中国哲学思想之真正光大弘扬的必然的趋势。
蕺山的“意本体”阳明的“心本体”身本主义牟宗三的“三系说”
随着牟宗三所谓宋明新儒学“三系说”的推出,随着其将刘蕺山学说视为宋明新儒学的最终归宿的“结穴”,几近被世人所冷落、所遗忘的蕺山学开始一跃为今日宋明新儒学研究中的显学。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尽管议论蜂拥、见解纷呈,包括宗三先生在内的蕺山学的研究却以其业已登堂而尚未入室,使其哲学的真正而准确的定位始终悬而未决。有鉴于此,笔者将重辟蹊径地再次步入这位明代巨人的思想之旅,以期对蕺山的理论深蕴给予挖井汲泉的更为深入的勘探和开掘,并从中进而实现对宋明新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真正的理论自觉。
蕺山“意”的本体论内涵
一如众人所指出的那样,蕺山学乃阴阳学的进一步深化。在笔者看来,这一深化至为关键的是,蕺山以《大学》的“意”释阴阳之“心”,最终以“意”易“心”,从而更端别起,实现了宋明新儒学从“心本体”向“意本体”的战略性和革命性的转移。
关于这种以“意”释“心”,蕺山指出:
心只是个浑然之体,就中指出端倪来,曰意。(《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41页)①
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同上,第390页)
而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同上,第341页)
在心为意。(同上,第137页)
那么,何为这种“心之端倪”、“心之本”、“心之所以为心”、“心之所在”的“意”呢?蕺山给出的答案极其简洁明确,他称“心所向曰意”(同上,第343页)。在这里,“意”被解释为心的“朝向”、“趋向”,由此就有了他所谓“意”如“定盘针”、“意”如“舟之舵”、“意”如“指南车”如此等等之说,而与中国古代词源学上的作为“心之所之”的“意”字解释不谋而合。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正如阴阳心学的“心”实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心”而非知识论意义上的“心”一样,蕺山的作为“心”的根本所在的“意”亦如此。故在蕺山那里,其“意”的“朝向”、“趋向”与其说是观念上的取向,不如说是价值上的取向。这意味着,正如其“意者,至善之所止也”一语所示,蕺山的“意”实际上是和“好善恶恶”的好恶之情而非“知是知非”的是非之心联系在一起的。而蕺山所谓的“好恶意之情,生而有此好恶之谓意之性”(同上,第344页),所谓“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即四者之所自来,所谓意也”(同上,第389页),所谓“好恶从主意而决”(同上,第457页)恰恰是对此的明示。
一旦蕺山把“意”与价值性的“好恶”联系在一起,一旦他同时把该“好恶”视为“此心最初之机”,这不仅导致了一种中国式的“爱感优先论”在蕺山哲学中的推出,也使一种康德式的之于至善“趋向”而非“趋就”的“内在目的”成为蕺山哲学的应有之义。这样,与当代哲学家梅洛-庞蒂以“我能”训“意”的思想一致,一种有别于既定性、既成性的“可能性”,就被视为蕺山的“意”之所以为“意”的真正旨趣。在蕺山哲学里,这种“可能性”或借《中庸》的表述被称之为“微”,或借《易传》的表述被称之为“几”。故蕺山谓“动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同上,第279页),谓“人心之有意也,即虞延所谓‘道心惟微’也”(同上,第337页),谓“未有是心,先有是意,曰‘心几’”(同上,第434页)。如果说“几”为我们指向了“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话,那么“微”亦与“几”同义,即所谓“惟微云者,有而未始滞于有,无而未始沦于无。蓋妙于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也”(同上,第337页)。因此,无论是“几”还是“微”,其都以“妙于有无之间”为归。于是,正如黑格尔的《逻辑学》以“生”(Werden)训亦有亦无之物一样,在蕺山那里,“生”亦成为其“妙于有无之间”的“几”、“微”的真实涵义,进而成为以“几”、以“微”为旨的“意”的真实涵义。
这一切,使蕺山之“意”最终成为“生意”之“意”,并使“生意”作为“意”的点睛之笔,成为其主意说所力揭所高标的一大主题。故蕺山提出“生意之意,即是心之意,意本生生,非外烁我也”(同上,第468页),提出“人心如谷种,满腔都是生意,物欲锢之而滞矣。然而生意未尝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同上,第429页),提出“当其未感之先,一团生意原是活泼泼地也”(同上,第341页)。同时,对于蕺山来说,也正是在这种“生意”之“生”中,使心宗的人道与性宗的天道之间的坚壁涣然冰释,二者之宗旨从根本上完全打通了。因为无论是力主“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易传》,还是高标“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的《中庸》,其都为我们表明了中国传统的天道同样是以“生”为宗的。故随着“意”之“生”的内核的彰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看似主观的“意”得以客观化的贞定,而且也意味着,一种宇宙本体论化的“意”亦随之在理论上被正式地奠定。
这样,正如在心学那里,其讲“心即理”、讲“吾心即宇宙”、讲“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心”成为本体论化的“心”那样,在蕺山那里,通过“心”向“意”的还原,“意”随之亦成为本体论化的“意”。故蕺山指出“满腔子生意流行,自有火燃泉达不容已者,又何患天地万物不归吾一体乎?此古人务本之说”(同上,第488页),指出“心浑然无体,而心体所谓四端万善,参天地而赞化育,尽在意中见”(同上,第443页),指出“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同上,第390页),并且还指出“观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无间也。观喜怒哀乐,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无间也”(同上,第518页)。而这种“周流无间”的“一元生意”不仅使人成为气化流行的有机整体,使蕺山从未脱身心二分的“心本论”进而走向身心一体的“气本论”,而且也使我们突破了人与宇宙的形骸的间隔、限囿,并最终导致蕺山的超越形下形上之分的“大身子”的概念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应运而生:
自圣学不明,学者每从形器起见,看得一身生死事极大,将天地万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机蚤已断灭种子了。故其工夫专究到无生一路,只留个觉性不坏。再做后来人,依旧只是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学,宜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终终始始,无有穷尽,只此是死生之说。原来死生只是常事,程伯子曰:“人将此身放在天地间,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于此有知,方是穷理尽性至命之学。(同上,第579页)
万物非万物,我非我,浑然一体,此身在天地间,无少欠缺,何乐如之!(同上,第522页)
此处的“大身子”不正是梅洛-庞蒂的“走向世界之身”在人类哲学史上最早的先声之鸣吗?同样无独有偶的是,如果说蕺山的“大身子”是以“一元生意”为其原始根基的话,那么,梅洛-庞蒂的“走向世界之身”亦是以一元化的“生命意向”为其深刻的依据。然而,虽然同为“意本主义”,如果说,梅洛-庞蒂对“意本”的揭橥是对西方传统哲学“万物唯识”的唯心主义的反戈一击的话,那么,蕺山对“意本”的发明则是对其先师阳明学说不无佛学化的“以觉言性”的唯心主义的彻底力辟。
也就是说,阳明心学尽管以其天才的眼光,对《大学》的“诚意”之旨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和提升,如其提出“意之所在便是物”,提出“只好恶便尽了是非”,但囿于宋明新儒学中的“知识论转向”这一大的思想背景,实际上却“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同上,第318页)。换言之,对于蕺山来说,阳明心学之所以诉诸于良知并最终诉诸于心,乃在于其“将意字认坏”,也即在于对“意”的误读。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其“四句教”中“有善有恶意之动”这一命题的推出。该命题表明,阳明将“意”视为现象层面的已发的起念、动念,而流于了以“念”训“意”的理论误区。实际上,“意”与“念”看似相似,归根结底却是迥然异趣的:“意之好恶,与起念之好恶不同。意之好恶,一机而互见;起念之好恶,两在而异情。以念为意,何啻千里?”(同上,第412页)也即在蕺山看来,“意”以其好善恶恶的价值取向是属于本体的“一机”(一几)的,与之相反,“念”则以其有善有恶则停留在现象的“两在”之处,而与那种“无意之意”的本体的一元化的“意”乃自有轩轾、格格不入。故蕺山最后一针见血地批评指出,“今云‘有善有恶意之动’,善恶杂糅,向何处讨归宿?抑岂大学知本之谓乎?”(同上,第445页)
这种“意本”的错失使阳明从“意”转而经由良知“求精于心”,以期以“心本”置换、偷换“意本”。但是蕺山认为,由于“四教句”又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由于阳明的“心”背离了心之所以为心的好善恶恶的价值取向,而流于了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这使他的“心”依然远离了意本之物所寓的“至善栖真之地”,依然与哲学本体之旨失之交臂。在蕺山那里,这种与哲学本体之旨失之交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即与“性天”之旨失之交臂。而“(心)离性而言,则曰觉”(《明儒学案·蕺山学案·语录》),这里的“觉”也即佛学之“觉”。故蕺山最后一言以蔽之地总结曰:
后儒喜以觉言性,谓一觉无余事,……。噫!是率天下而禅也。(同上)
此处的“喜以觉言性”的后儒解者多指阳明后学。其实,其所指对阳明本人亦同样成立。以至于可以说,阳明后学之所以一方面如王龙溪那样“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以其“玄虚”的极力高扬而流于“夷良于贼”的道德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如泰州学派那样“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以其“情识”的高度彰显而踏上了“一是皆良”的道德相对主义的不归之路,恰恰源于阳明心学本身之于“意”的好善恶恶价值取向的付之阙如,从而也恰恰表明阳明心学本身乃是所有这一切流弊的始作俑者。故牟宗三将这些流弊视为“人病”而非“法病”的观点亦可以休矣。
因此,蕺山“意本”学说的推出,与其说如牟宗三所说是对阳明后学乘弊而起的产物,不如说是对阳明心学本身乘弊而起的结果。正由于阳明不无佛觉化的“心”在道德上的游浮无归、进退失据,才使蕺山推重的所谓的“至善之所止”的“意根”得以从中崛起。故尽管蕺山宣称“先生(阳明)所谓心,即愚之所谓意也”(《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48页),尽管蕺山在论述中心意二者往往互为指代而难以分离,然而二者的实质却毫厘千里。一为人心,一为道心,而蕺山所谓“人心之有意也,即虞廷所谓‘道心惟微’也”(见前引)适可为证;一为心体,一为独体,由此就有了蕺山所谓“端倪即意,即独”(同上,第517页)之论;一为无极,一为无极而太极,从而才使蕺山提出“好善恶恶之意,即是无善无恶之体,此之谓‘无极而太极’”(同上,第411页),而这种“无极而太极”也即蕺山所谓的“天下极”:“始于几微,究于广大。出入无垠,超然独存,不与众缘伍,为凡圣统宗。以建天地,天地是仪,以类万物,万物是宥。其斯以为天下极”(同上,第136页)。
这样,在蕺山的学说里,一种从“意”出发的对濂溪《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的再造就成为其顺理成章之举。其结果,就是蕺山的“从深根宁极中证人”的《人极图》与《人极图说》的推出。人们看到,一方面,这种《人极图》与《人极图说》是不同于濂溪的《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的,如果说后者更多地是从天道的性宗上逐渐切入的话,那么,前者则更多地是从人道的心宗上次第展开的,或更确切地说,是从心之所以为心的“意”之独体上次第展开的。而《人极图说》所谓“无善而至善”的“心之体”、作为《人极图》的进一步解说的《人谱续篇》的“体独”、“独知”均为此“意”之独体的明证。随之,就有了“意”→“动念”·“静容”→“五伦”→“百行”这一徐而推出的图式。显而易见,它既一如蕺山所说,“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同上,第1页),乃是对阳明后学的“远人之道”的迷失的纠拔,又同时是对濂溪“太极图”的倚重天道的倾向的纠正。另一方面,由于在蕺山那里,“意”也即“生意”之“意”,这意味着其“人极图”又不失为是对濂溪那种“以生为道”、那种“太极→阳动·阴静→五行→万物”的“太极图”的重申和继承,并且是一种经由心学发明的“人道”的历史否定之否定的重申和继承,一种“天人合一”式的和作为理论合题的重申和继承。
其实,它岂止是宋明新儒学奠基者濂溪“太极图”的本体论思想的发展中的重申和继承,它还更为远绍地乃儒学创始者孔孟的“践仁知天”、“尽心知性知天”这一本体论思想的发展中的重申和继承。至此,正如西方的绝对理念运动的“圆圈”在黑格尔哲学这一终结者处回到了其原点那样,中国的道的运动的“圆圈”亦在蕺山哲学这一结穴者处重返其发轫之地。二者的差异在于,一种“言意之辨”在这里同样成立:如果说前者为我们指向了理论上的《圣经》的“泰初有言”的言论之“言”,那么,后者则为我们指向了更为泰初、更为始源的《大易》的“言不尽意”的“生意”之“意”。
既然“言不尽意”,那么,这意味着为了把握本体的“意”,仅仅求助于言的概念、言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意味着为了完全彻底地把握本体的“意”,除了求助于言的概念、言的理论之外,我们还必须即语即默地诉诸无言的“反躬体贴”的“生命体验”。而“体验在践履上做工夫”(同上,第517页),故一如蕺山所指,一种与有别于认知的实践相关的意之功夫论的开出,就成为意的本体论真正实现的必经之途、必由之路。
蕺山的工夫论——“意”的本体论的真正实现
蕺山的这种亦人亦天的本体的“意”,以其主体与客体的互为一体、密切交织,按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之说,就是其所谓的“走向世界的身体”之身。故如前所述,与他的大写的本体的“意”一致,蕺山有所谓的“大身子”之说。一旦“身”在哲学视域上的凸显和挺立,对于蕺山来说,对心思的理论上的“是什么”的本体论的关注,就不能不涉及到对身体的行为上的“如何作”的工夫论的提撕和标举。而这种对工夫论的提撕和标举,不仅体现了蕺山之于远绍礼教的和《论》、《孟》、《学》、《庸》所推重的古老儒家的“修身”传统再度的忠实皈依,也与一路高歌“良知良能”而轻工夫的阳明心学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也就是说,在阳明心学那里,固然其不仅提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且反对不能精察明觉的“冥行”,固然其不仅强调“在事上磨炼”、“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且推出了“四句教”这一眉目朗然、有章可循的修身工夫。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他坚持“良知即道”,认为良知本自具足,人人现成,随机显现,乃至可以使我们“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传习录上》),并由此得出了“个个人心有仲尼”、“满街都是圣人”的宏阔之论,这使对人为道德实践的工夫论的轻忽成为阳明心学一难掩的弊病。而龙溪与泰州学派身上所体现出了那种如此鲜明而不无极端的道德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则将其师说中的这种工夫论的轻忽倾向推向了极致。
也正是针对阳明心学的这种倾向,蕺山不依不饶地提出了自己的针针见血的批评:
阳明只说致良知,而以意为麤根,故于慎独二字,亦全不讲起,于《中庸》说戒慎恐惧处亦松,所以念庵有收摄保任之说。(《刘宗周全集》二册,第451页)
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从《中庸》看得;其言良知,亦从生知看得。然《大学》只是言学而知之者……起一善念,吾从而知之,知之之后,如何顿放?此念若顿放不妥,吾虑其剜肉成疮。起一恶念,吾从而知之,知之之后,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养虎遗患。总为多此一起,才有起处,虽善亦恶;转为多此一念,才属念缘,无灭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同上,第458页)
自古无现成的圣人,即尧、舜不废兢业。(同上,第9页)
同时,也正是针对阳明心学的这种倾向,蕺山有的放矢地为我们推出了他的对治之方。而这种对治之方一言以蔽之,即对古人的“慎独”工夫的彰显。故蕺山宣称“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同上,第300页),宣称“《大学》言心到极致处,便是尽性之功,故其要归之慎独。《中庸》言性到极致处,只是尽心之功,故其要亦归之慎独”(同上,第389-390页),并且他还提出“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同上,第565页),“慎与不慎,人禽之关,不可不畏”(同上,第566页)。而这种“慎独”既与于慎独二字“全不讲起”的阳明心学全然无涉,又与对慎独不无发明的朱子理学判若霄壤。朱子解“慎独”时曰“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按朱子此解,与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旨一致,“慎独”之“独”不过是那种幽暗细微且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的将萌的人欲而已。
与这种朱子的不无形而下的解读不同,蕺山则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其宣称“‘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258页),宣称“独便是太极”(同上,第481页)。而这种以“天命之性所藏精处”释“独”、以“太极”释“独”,也即从哲学本体上释“独”。故对于蕺山来说,一如其本体是“意本体”那样,“独”即“意”,“意”即“独”,二者乃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由此才使蕺山明确断言:“古人慎独之学,固向意根上讨分晓”(同上,第264页),也才使牟宗三先生一语中的地指出,在蕺山那里,“依其用语之习惯,独即慎独之独,独体之体,即‘意根最微’之意也”。②既然“独”与“意”完全打并归一,这不仅意味着蕺山的“慎独”也即其“诚意”,进而亦使蕺山学主旨是“慎独说”抑或“诚意说”这一古今学案之争随之冰释,业已成为地地道道的“伪问题”。
因而,在蕺山那里,“意”与“独”二者虽有一多从“心宗”上言一多从“性宗”上言之差异,然归根结底,二者却有着异名同谓的涵义。“好恶从主意而决”,同样,好恶亦与“独”须臾不可离,故蕺山谓“心无善恶,而一点独知,知善知恶。知善知恶之知,即是好善恶恶之意(《明儒学案·蕺山学案·语录》),谓“故谓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此时浑然天体用事,不著人力丝毫,于此寻个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还他本体,曰独”(同上)。再如,“意”即“隐微”,同样,“隐微”亦是“独”的固有之义,故蕺山直宗《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的思想,视“独”为“本心呈露”之时,“性光呈露”之地,并发出“至哉独乎!隐乎!微乎!”(《刘宗周全集》二册,第138页)这一叹为观止的赞语。又如,“意”为“生意”之意,同样,“独”亦以生生不息为归依,故蕺山不仅以天道的“穆穆乎不已者”训“独”,而且提出“独体不息之中,而一元常运,喜怒哀乐四气周流,存此之谓中,发此之谓和,阴阳之象也。四气,一阴阳也。阴阳,一独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也不测”(同上,第138页),在他的《易衍》里,“独”成为大易的生生不息之主旨的别注。
除此之外,二者的别无二致之处还表现为,虽然蕺山宣称“慎独之外,别无工夫”,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功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功夫”(同上,第390页),认为如同“慎独”,“诚意”亦同样具有工夫论的属性和功能。这与其说是为我们表明了蕺山学说中的工夫上的二元论的推出,不如说,由于其“诚意”之“意”也即“慎独”之“独”,故蕺山“诚意”之工夫与“慎独”之工夫最终间不容发地融为一体、打并归一了。于是,蕺山有如下之论:
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乃见真止;定、静、安、虑,次第俱到,以归之得,得无所得,乃为真得。此处圆满,无处不圆满;此处亏欠,无处不亏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为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处一动,便有夹杂;因无夹杂,故无亏欠。而端倪在好恶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恶必恶,彼此两关,乃呈至善。故谓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此时浑然天体用事,不着人力丝毫。于此寻个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还他本位,曰独。(同上,第453-453页)
在这里,蕺山告诉我们,“天非人不尽,性非心不体”,“浑然天体用事”的“诚意”离不开和有赖于“于此寻个下手工夫”的“慎独”。于是,这不仅意味着真正的“诚意”乃是“天生人成”之举,还意味着“意根”这一“独体”的发明,既取决于“好善恶恶”这一“意”的天赋之性,又取决于“为善去恶”这一“意”的人为的道德践履。无独有偶的是,人们看到,后者的这种“为善去恶”也恰恰是蕺山《太极图》与《人极图说》所特有的一大主题。一方面,在为善上,蕺山有(无极太极)凛闲居以体独→(动而无动)卜动念以知几→(静而无静)谨威仪以定命→(五行攸叙)敦大伦以凝道→(物物太极)被百行以考旋→(其要无咎)迁善改过以作圣这些步骤的推出,另一方面,在去恶上,蕺山又有(物先兆)微过,独知主之→(动而有动)隐过,七情主之→(静而有静)显过,九容主之→(五行不叙)大过,五伦主之→(物物不极)丛过,百行主之→(迷复)成过,为众恶门,以克念终焉这些步骤的推出。
诚如牟宗三所分析的那样,这些道德践履步骤“根本处是独体”,并且“此一正反两面所成之实践历程为从来所未有,而蕺山独发之。……此足见蕺山诚意慎独工夫之深也”。③也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为蕺山独发的“工夫之深”,才使蕺山始终与轻视工夫的心学敬而远之地保持距离。一如其子刘汋在《蕺山刘子年谱》中所写道的那样,“先生蚤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曰:‘象山、阳明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治边事,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功矣。其旨痛险绝人。苟其说而一再传,终心弊矣。观于慈湖、龙溪可见,况后之人乎’”(《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62页)。对于阳明心学,他虽“中信之”,却“终而辨难不遗余力”,乃至即使在他临终之际,亦为我们留下了“若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之断语(同上,第37页),乃至危难当头,其言“吾平生自谓于生死关打得过,今利害当前,此中怦怦欲动,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当也。”(同上,第7页),以一种现身说法的方式,痛贬心学的袖手空谈心性而于事无补之弊。同时,也正是这种前所未有而为蕺山独发的“工夫之深”,才使蕺山从时儒莫不翕然而宗之的“心”的觉悟之“理”,回归于古人时时而习之的“身”之践履之“礼”。故蕺山每曰:“古人生禀朴茂,又有三千三百之礼以为节文,故检身如不及,而成才也易。后世礼教荡然,士多习为猖狂之行,于凡威仪之节、言动之准,废而不修,骄惰已成,驯至决裂。子弟而悖其父兄,卑幼而陵其师长,往往有之。今欲学为人,请自学礼始。凡一语一默、一饮一食、一进一反,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苟能致谨于斯,浅言之则小学之科条,深言之即收心之要法也”(同上,第71页),蕺山是这样说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设教一以严肃为主,盛暑未尝去冠服,有荡简者则摒诸门墙之外,大约规模视丁末更宏阔云”(同上,第71页),而一反后儒对古人礼教的弃若敝屣,以其对礼教的身体力行,使自己成为其时代的“克己复礼”的真正先驱。
实际上,这种对道德行为的亲自践履、身体力行才是其“工夫之深”最有力的说明。这使蕺山的“迁善改过以作圣”的人生之旨并非仅仅停留在所谓“工夫论”的理论说教层面,而是以一种中国式的“示范伦理”的方式,“即身而道在”地就体现在他自己一生那种“不废兢业”的活生生的生命之中。试看蕺山的“行状”与“年谱”为我们留下有如下记载:
(于其师许敬庵先生的教诲)先生终身守之不敢失。自此励志圣贤之学,谓入道莫如敬,从整齐严肃入,自貌言之细,以至事为之著,念虑之微,随处谨凛,以致存理遏欲之教。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直勘前所繇来为如何,又勘后所决裂更当如何。(同上,第62页)
先生通籍四十五年,立朝仅四年。在家强半教授,敝帷穿榻,瓦窀破缶,不改儒生之旧。士大夫饰其舆服而来者,不觉惭沮。故见先生者,多毁衣以入。甲戌、乙亥之间,先生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从而效之,其价为之顿高。先生饭客不过数器,而士大夫之享先生者亦遂以乾饭寒浆,先生未尝不心知其伪也。(同上,第47页)
三世七丧尚在浅土,先生营立墓,御史徐缙芳资之百金,先生谢曰:“百金之馈,其所取义乎?不义乎?即使君有以处仆,仆则何以自处也?已矣,勿污我先人墓上石。仆所未了者,固仅有先人一事,试将茹荼带索以毕余生,何至烦故人为念”。御史不敢复言。(同上,第46页)
先生德日慎小,心日谨微。官行人时,梦转卫经历,不乐,觉而自责曰:“此梦从何来?终有荣进念头在,乃知平日满腔子都是声色货利,不经发觉,自不察耳”。(同上,第48页)
先生在事,缙绅素惮清刚,莫敢干以私。惟中贵人习难骤革,遇事把持,先生谢之,则闯入,堂皇言状,不应,出语相诟谇,先生为不闻也者,治政事自若。中贵知先生终不可挠,好语慰曰:“公执拗人,吾且去,再求未晚也”。竟亦不至。居数月,中贵屏迹于公庭矣。(同上,第100页)
先生候召在京邸,适上严禁馈遗。士大夫每于揖见时,袖中相授受。有万寿赍表官来候先生,亦以是法行之。先生谢不受,退而负愧曰:“此何为至于我哉?知平生不足取信于人,故有是馈耳。”自反者累日。(同上,第183页)
先生在留都一月,日给不过四分。每日买菜腐一二十文,长安谣曰:“刘豆腐”。出入都门,行李一肩,长安又谣曰:“刘一担”。(同上,第190页)
先生著述多不存稿,即存稿不以示人。汋私抄笔札,先生知必切责之。盖平生无一毫名心。临没,犹戒以勿刻文集,勿倩做葬文。(同上,第193页)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蕺山认为辨得吾道德上的义利则必然破得吾生命上的生死(同上,第102页),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蕺山在明亡这一“天崩地圻”之际,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绝食自尽的“烈烈而死”,以无人可望其项背的壁立千仞的舍生取义之举,使自己当之无愧地赢得所谓“海内第一人”的称誉(同上,第194页),并且也把其所谓的无极而太极的“人极”,也即中国式的“道德形上学”,用自己的生动的生命践履出神入化地谱写到了极致。
在这里,蕺山的“工夫之深”已不是随机显现地体现在禅宗的“担水劈柴”上,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上,而是从一种原始返终的方式,深契生命本身地体现在其自身生死河界的超越上。而这种关乎“第一大事因缘”的极其彻底的工夫之所以成立,实际上是“归显于密”地以意根这一本体的奠基为前提的。此即蕺山所谓的“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黄宗羲全集》八册,第945页)。所谓的“不识本体,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识本体,即须认定本体用工夫”(《刘宗周全集》六册,第103页)。反之亦然,一旦工夫得以躬行,也必然意味着工夫即用显体地使本体得以真正实现。此即蕺山所谓的“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刘宗周全集》三册,第309页),所谓的“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熒”(《刘宗周全集》六册,第103页),也即黄宗羲所谓的“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明儒学案·黄梨洲先生原序》),(在论蕺山慎独工夫时)所谓的“本体只是些子,工夫只是些子,仍不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亦并无这些子可指,合于无声无臭之本然。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消息动静,步步实历而见”(《刘宗周全集》六册,第39页)。或换言之,对蕺山而言,真正的本体,既非阳明良知说的那种“终属想象边事”的“识认”,也非阳明良知说的那种“索吾道于虚无影响之间”的“别有一物”,④而是一如古人以“人之所行”训“道”那样,它就体现在迈向无上的崇高道德目的的人的一步步的行动之中、践履之中。
对牟宗三“三系说”的重新勘定
如上所述,我们把蕺山学说视为一种解行双彰、亦本体亦工夫而不无圆融的“意本体”的学说。那么,在整个宋明新儒学本体论里,就有一种“三系”之说依次推出。其分别是程朱的“理本体”、陆王的“心本体”以及蕺山的“意本体”。而与此几乎如出一辙的是,在牟宗三宋明新儒学的哲学研究里,我们也同样看到一种“三系”之说的分厘,即以程朱为一系,陆王为一系,以及以五峰、蕺山为又一系。然而,同为三系,此三系却非彼三系。牟宗三论三系说时指出:“至伊川、朱子重格物穷理,言‘涵善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学路之端绪稍转向而歧出,转为静涵横摄之系统,而静涵亦为外延型。南宋胡五峰承北宋前三家(濂溪、横渠、明道)首言‘尽心成性,以心著性’之形著义,不走伊川、朱子之路也。象山兴起,本孟子明本心,辨端绪之得失,遂扭转朱子之歧出,而归于正。阳明承之言致良知,使‘明本心’更为确切可行者。至蕺山‘归显于密’,言慎独,明标心宗与性宗,不期然而自然走上胡五峰‘以心著性’之义理间架,而又著《人谱》以明实践之历程,如是,内圣之学、成德之教之全谱至此彻底穷源而完备,而三系之分亦成为显然可见者。”⑤关于牟氏的这种三系说,罗义俊先生的概括解释尤为明确和到位。其谓“(一)五峰蕺山系:此承由濂溪、横渠,而至明道之圆教模型(一本义)而开出。此系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以《论》、《孟》为主。特提出‘以心著性’义以明一之实以及一本圆教所以为圆教之实。于工夫则重‘逆觉体证’。(二)象山阳明系:此系不顺‘由《中庸》、《易传》回归于《论》、《孟》’之路走,而是以《论》、《孟》摄《易》、《庸》而以《论》、《孟》为主者。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现,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润;于工夫,亦是以‘逆觉体证’为主者。(三)伊川朱子系:此系是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于《中庸》、《易传》所讲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炼为一本体论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于孔子之仁亦只视为理,于孟子之本心则转为实然的心气之心,因此,于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涵养须用敬’)以及格物致知之认知的横摄(‘进学则在致知’),总之是‘心静理明’,工夫的落实处全在格物致知,此大体是‘顺取之路’”。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的是,牟氏这里的三系说,看似为三系,实际上从根本上讲,却是形三实二地仅为两系的“三系两型”说。因为在牟氏眼里,无论是陆王系还是胡刘系,其都一反程朱的从“理”出发的理本体,其都不失为一种从“心”出发的心本体,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如果说陆王系所坚持的是一心之独尊的话,那么,胡刘系所坚持的则是“以心著性”的心性之对扬、心性之双彰,并以这种心性之对扬,心性之双彰,为陆王心学填补了客观的性天之尊的缺失这一理论的空场,而最终体现了对该心学的一种乘弊而起的纠弹式的弘扬。故牟宗三先生本人对这种“三系两型”亦直言不讳,他写道:“陆、王系与胡、刘系总可合为一大系,同一圆圈之两来往,亦成为显然可见者”。⑦此处的“同一圆圈”是指二者均为以心体为圆心的同心圆,此处的“两来往”则是指陆、王系较多从主观方面切入讲心体,而胡、刘系则较多从客观方面切入讲心体。故归根结底,之于宋明新儒学的解读,牟宗三先生看似以其三系说的首创为我们另辟出理论蹊径,实际上却不越理学、心学二分之窠臼、之成规,而使自己最终依然是以众所公认的传统的解读为归。
然而,一旦正如我们所做的工作那样,把蕺山学明确定位为一种有别于“心本体”的自成一体的“意本体”,那么,这不仅使王学与蕺山学的分野从根本上得以澄清,也同时意味着一种“三系说”随之真正地被给予厘明。而宗三先生之所以将此二者“可合为一大系”,也恰恰在于其之阳明的“心本”之“心”与蕺山的“意本”之“意”二者之歧异义有未谛。若深而究之,二者之歧异之处如此难以弥合地表现为:
其一,从理路入径上讲,如果说阳明的“心本”之“心”以其“逆觉体证”而循“逆取之路”的话,那么,蕺山的“意本”之“意”则既是“逆取之路”又为“顺取之路”。也就是说,前者的“逆取之路”是指,本心之奠定之发明并非是外展的而是内敛的。按《孟子》的表述,即所谓的“求其放心”,所谓的“反求诸己”,按阳明的表述,即所谓的有别于“格物”的“复良知”,所谓的“在于体当自家心体”。而后者的既是“逆取之路”又为“顺取之路”则是指,主意之奠定之发明既是内敛的、又为外展的。就“意”作为“心之意”而言,为我们指向了内敛,就“意”的“朝向”、“指向”、“心之所之”,以及“意之所在便是物”与“意”的“好好色,恶恶臭”而言,其又为我们指向了外展。故“意”以其亦内亦外而成为连接内与外的中介和桥梁。因此,“意”就是蕺山所谓的“本无内外”的“道体”。关于这种“道体”的“意”,蕺山极富慧悟地指出“道体本无内外,而学者自以所向分内外。所向在内,愈寻求,愈归宿,亦愈发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寻求,愈决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学者幸蚤辨诸”(《刘宗周全集》二册,第309页)。而正如梅洛-庞蒂从(内在的)“不可见的”与(外在的)“可见的”二者的交织、统一中发现了“身”(并且梅氏的“意”乃为“身体意向”的“意”)那样,在蕺山那里,这种“本无内外”的“意”亦为我们指向了“身”。这就导致了阳明心学与蕺山意学之间的第二层不同。
其二,从理论归依上讲,如果说阳明的“心本”之“心”,以一种名副其实的方式使自身最终趣向了“心”的话,那么蕺山“意本”之“意”,则实际上作为“身的意向”而非“心的意向”,以一种异名同谓的方式使自身最终趣向了“身”。在阳明那里,“致良知”致的是“心”,“心即理”即的是“心”,“心外无物”无外的是“心”,无论是“我的灵明”还是“天地鬼神的灵明”都无一例外地点出了“心”。而在蕺山那里,却宣称“诚意章言‘德润身、心广体胖’,蚤已身心齐俱到”(同上,第347页),而“以诚意配诚身”(同上,第445页),“身”成为“意”的别称。故有了其所谓“满腔子生意流行,自有火燃泉达而不容已者,又何患天地万物不归吾一体乎”(同上,第488页)这一意的“古人务本之说”,便有了其所谓“吾儒之学,宜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同上,第579页)这一蕺山的身的本体论。有了其力挺的《大学》的“诚意”之“诚”,便有了其独发的《人极图》、《人极图说》的“修身”的“工夫之深”。故在蕺山的学说里,伴随着大写的“意”的觉醒的,是大写的“身”在哲学视域中的挺立。也正是这种大写的“身”的挺立,才使蕺山不仅发阳明所未发地对“工夫论”给予了极为深切著名的发弘,而且也一改心学的致思倾向,把身体践履的“礼”、身体流体的“气”、身体生生的“几”,以及血缘、男女、五伦、家国、动静、吉凶、生死这些范畴再度提到了宋明新儒学的哲学议事日程。同时,也正是这种大写的“身”的挺立,才使蕺山力纠以龙溪为代表的阳明后学的重心轻身的“唯心主义”,与深揭“血缘之身”的近溪、高抬“功利之身”的李贽一起,以“道德之身”的空前标举,使自己当仁不让地成为宋明新儒学新时期的“身学”转向的理论先驱,而同时又让自己避免了尊身、重身的泰州学派的那种“流于禅”的误迷。
故从一定意义上说,蕺山学既是一种以“意”为本的意本主义,又不失为一种以“身”为本的身本主义。缘乎此,才使蕺山言称“则修身为本,正是诚意为本也”(《刘宗周全集》一册,第617页),言称“《大学》言修身为本,《中庸》亦曰‘本诸身’”(《刘宗周全集》二册,第461页),言称“身在天地万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同上,第394页),言称“论本体,则天地万物是吾身种子;论工夫,则吾身是天地万物种子”(同上,第328页),而哲学的“体用一源”又使其在《大学杂言》中最终断言:“言本体工夫一齐归管处,吃紧得个‘身’字”(《刘宗周全集》一册,第656页)。除此之外,蕺山对《大学》的“止至善”所内蕴的“身本”思想的解读更是别具只眼和极富启迪,其谓“止至善,止诸躬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也。止诸躬者,修身为本也”(同上,第656页)。在这里,他把“止至善”的“止”理解为“行止”的止,又从“行止”引出“躬行”的躬,进而又把“躬行”的躬还原为“修身”的身,由是将“止至善”的《大学》之道与“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的大易之道妙契为一,并从中为我们破揭出中国哲学中深深蕴含且不言而喻的身本主义。
既然身本主义为蕺山的最终归宿,同时既然蕺山学又作为其理论的完成被视为是宋明新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最终和最高成果,以至于一如牟宗三先生所指,蕺山学的音歇响绝恰恰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命脉已绝,那么,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种身本主义亦同样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真正的理论正解。舍此,我们就不能了解何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思想内核,舍此,我们也无从分辨出中西哲学之根本的“理论分野”。就此而言,但凡“从身行出发”的哲学应划入中国哲学之列。故坚持“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的《周易》、坚持“敬身为大”的《周礼》属于中国哲学,主张“践仁知天”、“克己复礼”的《论语》、主张“反身而诚”、“形色之践”的《孟子》属于中国哲学,提出“贵身养生”、反对“以身为殉”的老庄属于中国哲学,既强调“诚意”又强调“修身”的《大学》、《中庸》属于中国哲学,“重返《易》、《庸》”的濂溪、张载的学说属于中国哲学,发明“方信大道只在此身”的近溪的学说属于中国哲学,为我们推出“即身而道在”命题的王夫之的学说更旗帜鲜明地应纳入中国哲学。与之相反,但凡“从知解上入”的哲学则应划入中国哲学之歧出、之“异端”之列。故朱子虽衣被着“身任道统”的光环,其学历南宋、元、明、清七百年之盛而不衰,但由于其说以“格物致知”、“穷尽天理”为宗旨,不仅与中国古代一脉相承的身道传统不类,也理所当然地使牟宗三所谓的“别子为宗”恰恰成其准确的理论定位。
其实,岂止是朱子的“理学”,即使对朱子的“理学”力辟的阳明“心学”,尽管其提出“无身则无心”、“知行合一”等诸如此类的命题,但其坚持“致知焉尽之矣”的“致良知”这一其学说根本的总纲领,却决定了该说依然未脱“从知解上入”这一朱子学的误区,由此才有了蕺山所谓“(阳明)所云良知,亦非究竟义也”(《刘宗周全集》二册,第317页)这一断语。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虽同为“从知解上入”,如果说朱子的知解是循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悟”而进行的话,那么,阳明的知解则是以不无禅学化的“顿悟”为其理路,或借牟宗三先生的表述,是以康德式的“智的直觉”为其理路。进而,如果说朱子的“渐悟”使形下之心与形上的“天理”始终歧而二之的话,那么,阳明的“顿悟”则“心即理”地使二者完全合二为一了,并使“心”即知体即本体地一跃成为天地万物的策源地,从而阳明学的推出,实际上标志着一种中国古代“心本主义”哲学的真正确立。
因此,当牟宗三先生的“三系说”严分朱、王,在道统上将朱子学视为别子为宗而将阳明学视为嫡系之际,他却使我们忽略了二者异中有同的东西,即忽略了二者同为一种“从知解上入”的哲学而对“身”的背离。同理,当牟宗三先生的“三系说”统摄王、刘,在道统上将蕺山学最终纳入阳明心学之际,他却使我们忽略了二者同中有异的东西,即忽略了正是对“身”的肯否使二者实际上大异其趣。故身已成为中国哲学流派的真正的判准,乃至随“身体”而非“心识”在中国哲学上的凸显,随着“身道”而非“思理”成为中国哲学学脉的真正所在和体现,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宋明新儒学本质认识上的一场彻底革命,也使人们之于宋明新儒学理论谱系的划分必须重新书写和完全改观。其结果,将导致一种面目一新的“三系两型”说的出现。这种全新的“三系”是指:朱子为代表的“理本体”系、阳明为代表的“心本体”系以及蕺山为代表的“意本体”系;这里的“两型”并非表现为朱子为代表的“理本体”为一型,而阳明为代表的“心本体”与蕺山为代表的“意本体”则为另一型,而是表现为朱子为代表的“理本体”与阳明为代表的“心本体”为一型,而蕺山为代表的“意本体”则为另一型。同时,一如蕺山所指“斯知诚意之为本而本之,……呜呼!‘诚意’之说晦而千古之学脉荒”(《刘宗周全集》一册,第613页),由于“本而本之”的“意本”即为“身本”,故既不是朱子为代表的“理本体”,又非阳明为代表的“心本体”,而是蕺山为代表的“意本体”才使中国古代哲学正本清源成为可能,才为我们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真正之“正宗”,也即那种“即身而道在”的中国古代之道的真正之“道统”。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牟宗三这位被誉为“最具哲学家气质”的大师之于中国哲学的解读之失。其实,这种失误不仅表现在其宋明新儒学“三系两型”的理论定位上,而且更重要也根本地表现在他对真正的中国哲学的哲学范式的体认上。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移花接木地以康德的“知识”范式解读中国哲学,并非如其所是地以中国固有的“身体”范式解读中国哲学,从而使其对中国哲学的解读看似臻于思辨之至,看似被真正提升到人类的普世性哲学之真理,实质上却与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理论真谛失之交臂。
众所周知,在牟宗三那里,这种康德主义的对中国哲学的解读,集中表现为其对康德所谓的“智的直觉”在中国哲学中别具匠心的创造性运用。也即当康德把“智的直觉”视作是一种之于“物自身”即宇宙本体的把握,并认为这种仅为上帝拥有的直觉之于我们人类认识是不可能之际,牟宗三却宣称恰恰在直承孟子的“良知良能”的阳明的“致良知”的“良知”里,这种“智的直觉”为自己找到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也即对于牟宗三先生而言,一方面,正是这种“良知”使我们人自身的有别于“见闻之知”的“德性之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种可能又天人合一地使具有“好生之仁”的宇宙之德性本体得以奠定。其实,依中国哲学自身的逻辑,从孟子到阳明的“良知”,与其说是一种康德式的“智的直觉”,不如说是一种梅洛-庞蒂式的“用身体知道”的“身的直觉”,或用蕺山的表述,一种“在践履上做工夫”的“体验”。而这种“身的直觉”、这种“体验”之所以可能,并非源于那种“上根之人”所谓的“生而知之”的知性里,而是深深植根于那种但凡人类都具有的与天地万物共始终的和“宜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的“大身子”之中。也正是基于这种极其彻底的天人一体的“大身子”,才使我们可以真正做到“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阳明语),做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禅宗语),做到“举杯辄知饮水”、“捧茶童子即是道”(近溪语);进而,也在此知识论的身知与目的论的身行深契为一之中,使“良知”所深隐的亦存有亦活动的本体得以如如呈现和揭晓。
因此,这一切表明,在牟宗三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解读中,以其不无鲜明的康德的唯识主义倾向,而存在着一种难掩的“身学的空场”。而其宋明新儒学研究中的重“心”轻“意”即其显例。除此之外,这种“身学的空场”还表现为,与康德哲学中那种被推向极致的“主体性”哲学一致,一种在“道德绝对性”、“道德超越性”、“道德形上性”追求名下的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确立的一味的深深痴迷,亦成为牟氏学说自身的一大宏旨和归趣。这种对“主体性”的痴迷不仅导致了牟宗三先生之于中国哲学“下学上达”、“以你释我”诸如此类智慧的背离,不仅使梅洛-庞蒂身体哲学所谓的“交织”、海德格尔生存哲学所谓的“缘在”、于连汉学研究所谓的“之间”等范畴难以进入他的视域,而不得不借助于一种对之取而代之的所谓的“诡谲的即”的二值逻辑,而且也由是使自己对中国哲学的诸如“阴阳”、“交道”、“血缘”、“家族”、“礼”、“气”、“际”、“时”等等概念无心顾及、了无兴趣,而这些概念在我们看来,以其极具中国特色而恰恰为中国哲学打下了其特有而原始的胎记。他不明白,一种对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的发掘固然理所应当和势在必行,但此“主体性”并非彼“主体性”,如果说康德的能动的主体性的确立是以受动的客观性降尊纡贵为前提的话,那么,一种“天人合一”思想却决定了,中国哲学的能动的主体性的确立则是与受动的客体性的确立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它就体现在“阳禀阴受”这一“能受一体”之中,一如在中国哲学中,坚持“人能弘道”的儒家离不开“儒道互补”这一大背景,一如在蕺山那里,其认为“心本”的发明有赖于“本而本之”的“意”的奠定。
正是针对这种“身学的空场”,海外新生代中国思想研究者中的“身学”研究的异军突起,才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不容轻视的一大景象。在这些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杨儒宾先生的“气化身体观”的研究,吴光明先生、黄俊杰先生的“身体思维”研究,杜维明先生的“体知”研究。尽管这些学者曾紧随着牟宗三这位思想巨人的步伐步入中国哲学的殿堂,但一旦真正走近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时却发现,其身上虽衣被着中国“道统”的夺目的光芒,而身后却拖着“食西未化”的长长的魍魉。虽然这些学者的研究以其各立门庭尚未形成为“学术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理论的“范式”,虽然这些学者的研究以其刚刚起步、浅尝辄止尚未能与牟宗三这位“中国哲学中的康德”相颉颃,却春江水暖鸭先知地为我们指向了一种“后宗三时代”的中国哲学的新的愿景和理想。
傅伟勋先生断言,中国哲学的未来关涉着如何超越牟宗三的思想。故中国哲学未来看似遥不可及实际却近在眼前,它就现实而生动地体现在今天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开出的近取诸身的“身学转向”之上。
①《刘宗周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②③⑤⑥⑦《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0、363-364、376-377、397-398、377页。
④“石梁言‘识得本体,不用工夫’,先生曰:‘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熒。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至为无忌惮之归而已’。其徒甚不然之,曰:‘识认即工夫,恶得少之’?先生曰:‘识认终属想象边事,即偶有所得,亦一时恍惚之见,不可据以为了彻也。其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为别有一物可以两相凑泊,无乃索吾道于虚无影响之间乎?’”(同上,第42-43页)
作者简介: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特聘教授。西安,710048
〔责任编辑:吴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身体哲学视域中的中西体育思想的比较研究”(项目号:15BTY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