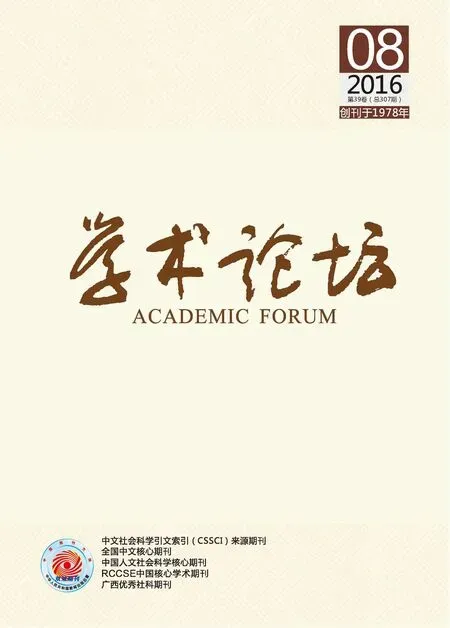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视野下“同一犯罪”之判断与启示
——以美国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
2016-02-26娄超
娄超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视野下“同一犯罪”之判断与启示
——以美国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
娄超
“同一犯罪”的判断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的核心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在1932年树立了“要件包含原则”,却在近年受到了Grady案“同一行为标准”的挑战,后在Dixon案中得以回归。我国可参考上述判断标准,通过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发布制度等路径,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确立并应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同一犯罪;要件包含原则;同一行为标准
如何识别和评判“同一犯罪(same offense)”,直接关系着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和生命力。了解并分析美国典型案例中的不同观点,对我国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之确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背景下,参考美国在适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中的典型案例,应当会有利于开启我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思路,有利于走出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权益可能受到国家公权力多次侵犯而缺乏保护的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The doctrine of Double Jeopardy或The prohibition against double jeopardy)是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发展至今的一项当今世界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刑事诉讼原则。我国于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3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列入立法规划,这两次均是学界认为确立我国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良好契机[1](P60),但2013年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纳入立法内容。
2014年的念斌案件,引发了对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新一轮思考。“我国未来有必要确立禁止双重受罚的原则,树立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性、维护程序的安定性、保障被告人的人权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避免刑事追诉的恣意化。”[2]在复杂犯罪、多重追诉频发的当下,在短时期内《刑事诉讼法》不会再次启动修改、而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刚刚起步的
二、美国“同一犯罪”判断标准的演进与评析
判断“同一犯罪”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的关键问题,不仅美国联邦法院与各州法院所持标准不同,联邦最高法院不同时期的判例也显示了不同观点的胶着和纷争,并代表着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融合。
(一)Blockburger案与要件包含原则
1932年的Blockburger案件中,对于被告同一个销售毒品的行为,陪审团基于毒品法案(The Narcotics Act)中规定的两个不同法条给被告分别定了罪。法院解释道:第一个法条针对的是非原始包装的违禁药品销售,而第二个法条针对的是向有购买许可之外的人销售违禁药品。可见法典创设的是两个显著区别的犯罪,因为每个犯罪要求证明的证据都有一个不同的要素。如果一个行为或交易,构成了对两个显著区别的法律规定的违反,那么就要明确这里是有两个犯罪还是仅有一个,而怎样去明确,就是要看其中一个法律条文的规定中是否要求有某项事实的证据,是另一个条文不要求的。
Blockburger案的判断方法被总结为要件包含原则(Same Element test)。这一原则要求法院对比法律规定的内容,分析其中一个诉是否包含有另一个诉完全没有的要件(事实及其证据),如果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要素是X法条要求且Y法条不要求,而X法条涵盖了Y法条要求的所有要素,那么虽然X与Y不是相同,却符合“同一犯罪”的定义,因为Y是一个被包含的少要件罪(lesser included offence)[3]。该原则成为了检验双重危险的最合适的原则,因为它可以在立法已经给出更重的处罚且包含了轻罪的情况下,阻止法院给被告分别进行两次单独的处罚。有学者指出,Blockburger原则的核心思想是“法官不应施加给被告比立法规定还要重的处罚”[3]。
(二)Grady案与同一行为标准
1990年的Grady案是一起交通肇事行为所引发的多重诉讼案件。在该案中,托马斯·卡宾已被交通法庭判处罚款350美元、执照吊销6个月之后,大陪审团突然指控卡宾过失伤害和过失致人死亡。卡宾提出因违反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而应驳回起诉的抗辩,但未被初审法院采纳。上诉法院认为虽然依照Blockburger原则来检验,不应禁止后诉,但如果前诉判决的行为,对后诉是否成立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事实(establish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second crime),那么后诉也应该禁止。联邦最高法院的布伦南法官采纳了这个观点,认为要件包含原则已不能充分满足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所希望达到的保护被告人的政策目标,应适用“同一行为”(same conduct)标准,也就是说后续的诉讼即使通过Blockburger测试,但如果为了证明其中一个关键事实的成立而会用到已追诉过的案件中被告的同样的行为,那么这个后诉就是被禁止的。
同一行为标准要求,在判断后诉是否违反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应首先适用要件包含原则来判断(但这一判断方法不应是唯一的方法,因为这一原则是产生于同一诉讼程序中多重处罚的时代背景,但现在是多重追诉的背景,所关注的方面应该更多),如果适用要件包含原则认为后诉不需禁止,那么应进一步考察,后诉成立是否必然需要以前诉已决的事实为关键的一个要素,借以弥补要件包含原则的不足。
尽管有四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反对,但这一判决树立的同一行为标准仍然以多数意见得以通过,并宣告法院对卡宾肇事致人伤亡的后果不能再次追诉。
(三)Dixon案与要件包含原则的回归
三年之后的1993年,在Dixon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推翻了Grady案提出的“同一行为”标准,这一案件与Grady案同样,对判决结果有五名法官支持而四名反对。
Dixon案是两个案件的合并审理。被告迪克森因持有并试图销售毒品而违反了“假释期间不得从事任何犯罪行为”的命令,因此被判藐视法庭罪。后检察官对其毒品犯罪行为提起控诉。而被告福斯特因违反了民事人身保护令(保护令的内容是不得对其妻子进行任何人身侵犯或威胁)而被判藐视法庭罪后,再次因其伤害并威胁妻子的行为而被提起了五项控诉。两个被告都提出了因违反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而应驳回诉讼的抗辩。初审法院认为被告迪克森的抗辩成立,而被告福斯特的不成立,上诉法院认为两个被告的抗辩都成立,依照Grady案的同一行为原则,两个后诉都应禁止。
联邦最高法院斯卡利亚法官分析道,法律并没有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保护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而在目前多重处罚与追诉的背景下,对于不能通过Blockburger测试的后诉或处罚应被禁止。Grady案中树立的“同一行为”判断标准必须要摒弃,理由是:同一行为标准没有历史根基,与之前联邦最高法院的先例都不相符,打破了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一致性,与普通法理解的双重危险不相一致,并且在实务操作中引起了混乱。该法官陈述,虽然最高法院并不愿轻易去否定一个先前的案例,但由于Grady案中充满了缺乏准确的分析,所以不得不宣布该案是一个错误,所以其建立起的“同一行为”标准也不再适用,仍然应该将Blockburger测试作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同一犯罪判断问题上的唯一测试。
自此案之后到现在,美国联邦法院在适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判断“同一犯罪”时,又重新回到了适用且仅适用Blockburger原则的时代。
(四)不同判断标准的评析
1.同一性之判断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中的核心问题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作为宪法的重要内容,在不断发展的美国司法实践中,内涵逐渐丰满,作用不断加强,其效力之高、适用之广泛,甚至超越了更早适用该原则的英国,成为在案件开始实质审理之前,被告用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一项重要抗辩。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能够在多大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被告的抗辩能否成立,法律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而是在判例中通过具体案件而进行阐释。这一问题关乎两个要素:一是时间要素,也就是“危险”何时发生;二是范围要素,也就是“危险”是否发自于同一案件。可见,前诉与后诉是否为同一案件,成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中的核心问题。如何判断不同诉讼程序中审理的是否为同一案件,是否触及了双重危险的禁区而应当阻止,在法典规定交叉复杂、多重追诉常态化的背景下,解答这一问题显得愈发困难。“一刀切”式极宽或极窄的方案难以满足实际需要,所以主流的观点仍然集中于中庸的判断标准,这样就会产生同样的行为引起的控诉可能是不同案件、不同的控诉罪名也可能是相同案件的结果[4]。
2.要件包含原则的局限性
Blockburger案树立起的要件包含原则,被认为很好地解决了案件同一性判断的问题,使法官不能处以被告比立法更多或更少的惩罚,在保护被告权利的同时,也与立法目的相呼应。通过法官在判决中对该原则的阐释,可以看出该原则的适用有两个特点:第一,案与案是否相同,重点要看法定的要件,而非证据形式;第二,思考的路径是要去探求立法者是否要创设独立的两个罪,如果立法规定了两个显然不同的罪,而不是一个包含于另一个,那么就有再次追诉的必要,就没有构成对被告的双重的危险,就不受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约束,即使针对的仍然是同一个犯罪行为。但该原则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其适用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泛,因此得到的争议和讨论也最多。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在多重追诉的背景下,Blockburger原则已经无法充分满足保护被告的需要。法典规定的内容日益精细,而很多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行为表现复杂,使得触犯多项罪名的行为交织在一起,难以割离,因此在要件包含原则的调整下,只要额外要求有一个单独的要件,则构成了新的犯罪,可以追诉,似有放任政府多重追诉的嫌疑。
第二,Blockburger原则在某些案件上的适用会显失公正。比如,多要件的罪被判无罪后,少要件的罪也不得追诉。但如果无罪原因恰好是因为少要件之外的要件事实不成立,那么此时再追诉少要件的罪,并不会给被告造成双重危险,反而有助于惩治犯罪。例如Dixon案中的藐视法庭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间,藐视法庭罪最高刑期只有6个月,非法持有毒品却可处30年,而前者较后者却是多要件罪,这样藐视法庭罪成立后,毒品犯罪依要件包含原则为同一案件而不得追诉,显失公正。
第三,Blockburger原则的适用缺乏弹性。案件千差万别,统一适用该原则来确定案件是否同一,可能会因缺乏考虑案件实际和立法本意,而影响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的效果,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最初就是将该原则结合正当程序原则一同适用,因为正当程序原则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且更具弹性。
3.Grady案的进步与不足
Grady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这是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官方承认要件包含原则存在不足,并提出了一个补充测试方法,试图更好地解决同一犯罪的判断问题。要件包含原则关注的是在立法角度特定罪名成立条件之异同,而“同一行为标准”将关注点转向了案件本身的事实内容。这一关注点的增加,使适用禁止双重原则时,可以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入手,来考察前诉与后诉针对的对象是否重叠、在多大程度上重叠以及是否会陷被告人于再次的危险之中。但不足之处在于,事实的判断仁者见仁,缺乏实际操作性,标准难以统一,适用中很可能会引发混乱。有的下级法院指出,适用同一行为标准要比简单的比较两案行为的一致性要复杂得多,并总结出四个繁复的适用步骤①这四个步骤是:分析第二个控诉罪名成立的关键要素分别是什么;确定在第二个诉中经第一步分析的每一个关键要素对应需要证明的行为是什么;检验第二步中确定出的行为,看看行为本身是否构成一个或多个独立的可控诉的罪名;确定在第一个诉讼中,被告是否已经实质上被控诉了第三步中分析出的罪名。。
4.Dixon案引起的反思
Dixon案否定了Grady案的同一行为标准,回归了要件包含原则。虽然该案件保持了要件包含原则适用的连续性,但仍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其废止同一行为标准的理由并不充分。Dixon案否定Grady案件的主要理由表述为,因为同一行为标准缺乏宪法的根基,破坏了要件包含原则长期以来适用的连续性,且引起实务混乱。可以看出,法官在此处并没有对Grady案中提到要件包含原则在连环诉讼的无力作出回应,也没有去阐释“同一行为标准”在适用中,除了缺乏统一标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如果仅仅是适用中较为混乱,则可以通过补充、细化标准、认可必要的例外来完善这一原则,而不必去废止。
第二,其适用要件包含原则存在错误。虽然Dixon案的法官宣称要适用要件包含原则来判断本案,但其实际进行前、后两诉比较时,比较的却是案件的事实而非法定成立要件,这也就是为什么“藐视法庭罪”与“毒品持有罪”“伤害罪”都成为了同一犯罪的原因。如果严格按照Blockburger原则来判断,那么藐视法庭罪应该包含三个要件:一是有一个民事或刑事的命令;二是命令已为被告知晓;三是被告进行了违反命令内容的实体行为。而持有毒品罪或伤害罪的要件显然未包含其中。而法官却依照被告作出的伤害行为或持有毒品行为等违反法庭命令的实体事实作为要件,得出了前诉包含后诉的结论。Dixon案的一名持反对意见的Rehnquist法官在判决中记载了以上的内容,并指出,Scalia法官否定了同一行为原则,而自己在比较时又恰恰比较的是行为而非要件,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5]。
三、对我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启示
美国进行“同一犯罪”的认定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客体理论中讨论的“同一案件”的判断标准虽然在比较的内容和宽严程序上有很大的区别,但值得借鉴的是其精细化去分析和判断“同一犯罪”的思维方法,以及结合“正当程序原则”适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而彰显的程序上的独立价值,进而可以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较主流的“有错必纠原则”加以反思[6]。具体来说借鉴美国法中的相关探讨,可对我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有以下启示:
第一,案件同一性之比较中应关注事实要素的比较。美国法已对其僵化考量罪名之间的立法要件包含关系、忽略案件事实导致的多重追诉之弊端作出了反思。结合我国刑事诉讼赋予法官变更罪名权利之立法安排,应当明确,在被告提出“禁止双重危险”之抗辩时,应着眼于案件事实要素之比较,避免引发多重追诉。
第二,直视并努力克服“公诉事实”概念的模糊。在美国Grady案中树立的“同一行为标准”是为了克服要件包含原则只着眼于法定要件,而应对连环追诉无力的困扰。但“同一行为标准”被废止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会引发实务操作中的混乱。这也正是我国刑事诉讼客体理论中难以突破的一个难点。可以考虑将检察机关控诉的事实,按照行为主体、行为攻击对象、侵犯的法益、未间断的行动组合等要素来分析和认识,以上要素均为连续不可分且具有一致性的,则可判断为同一事实。但要注意,符合刑事实体法中多个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也可能是诉讼法上的同一案件,不能用实体法上的罪名评价来反推诉讼法上案件是否同一,当被告提出一事不再理之抗辩时,应从诉讼法角度去分析公诉事实。
第三,反思竞合类案件的处理方式。美国刑事司法中,一个犯罪行为触犯多个立法罪名的,允许多个立法罪名同时成立,对该犯罪行为可以且应当进行多重评价。而在我国,一个犯罪行为被认为是一个被评价对象,即使因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而符合多个犯罪构成要件,即使侵犯了完全不同的法益,但都不能进行多重实体法评价,甚至牵连犯、连续犯这种多个犯罪行为、侵犯多个法益的特定情况,也只进行单一的处断。美国的处理方式似更尊重刑事实体法的立法本意,反观我国,也应当对竞合案件按一罪论处,并适用重罪吸收轻罪的这种单一的处理方法有所调整。
第四,借鉴最高法院案例的示范效应,实现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上列举的判断“同一犯罪”之标准,均是通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而得以树立,在我国立法未能明确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当下,借鉴案例的示范效应,可以有效推进该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并可起到统一视听的指引作用。目前我国已推行指导性案例制度和典型案例月度发布制度,如果能够在典型案例中,对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内涵、双重危险的界定、不同案件是否同一等问题作出分析,对被告提出的“一事不再理”之抗辩作出回应,就可以对后续案件作出指导,不仅有利于被告人据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也将使该原则的适用标准更为明确。
[1]张毅.刑事诉讼中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2]熊秋红.以念斌案为标本推动审判中心式的诉讼制度改革[J].中国法律评论,2015,(1).
[3]Akhil Reed Amar&Jonathan L.Marcus.Double Jeopardy Law After Rodney King[J].Columbia Law Review,1995,(95).
[4]Anne Bowen Poulin.Double jeopardy protection against successive prosecutions in complex criminal cases:a model[J].Connecticut Law Review,1995,(25).
[5]Kathryn A.Pamenter.United States v.Dixon The Supreme Court Returns to the Traditional Standard for Double Jeopardy Clause Analysis[J].Notre Dame Law Review,2014,(l69).
[6]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J].政法论坛,2002,(5).
[责任编辑:刘烜显]
娄超,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D0124.13
A
1004-4434(2016)08-015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造法性司法解释研究》(2012FX032)及国家“2011”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