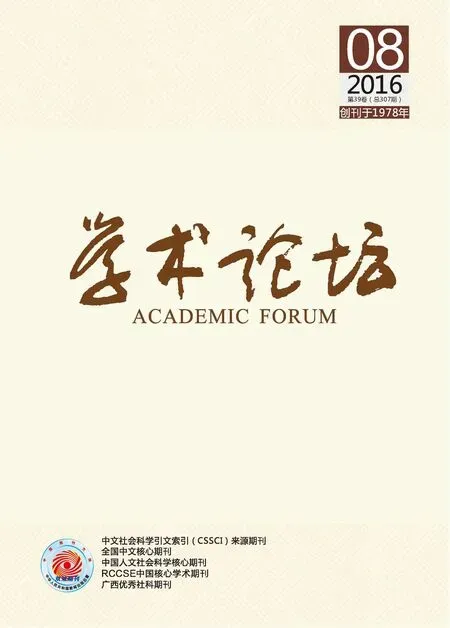论吴伟业的《秣陵春》传奇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
2016-02-26戴健
戴健
论吴伟业的《秣陵春》传奇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
戴健
《秣陵春》传奇因涉及易代之变、亡国之恨,以及鼎革之际文人出处等时政内容,颇能满足贰臣、遗民等特定民众的审美需求,因而社会反响较大。其在清代之传播乃“文本阅读”与“搬演观赏”并行,但后者作用更为突出。经南昌沧浪亭、如皋水绘园等雅集搬演,剧作内容、作者意旨等皆得充分解读与研讨,从而产生更大传播效力。而通过对此剧“读后感”与“观后感”的比较可知,场上传播在接受效果、群体切磋、理解深透等方面皆有优势。
《秣陵春》;吴伟业;宴集;文学接受
《秣陵春》一名《双影记》,乃“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1609-1671)所作唯一传奇,剧作以南唐大臣徐铉之子徐适与黄济之女黄展娘在南唐亡后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前半部分叙写因得后主李煜及保仪娘娘的幽冥庇佑,徐、黄二人终成眷属的婚恋过程;后半部分重点描述徐适在新朝考取状元,却拒不接受、携妻归隐的复杂心态。由于作者显赫的文坛地位,以及故事关涉易代文士的仕隐出处、亡国伤痛等敏感话题,因此《秣陵春》曾在社会中产生深刻影响,实际传播效果与接受程度都远远超出学界的现有认知,具备深入研究之价值。
一、《秣陵春》的文本传播与阅读接受
《秣陵春》传奇之传播,有文本刊刻与场上搬演两种方式。在传播顺序上,先有刊本,后有剧目。有关《秣陵春》的出版时间,学界一般以寓园居士李宜之作《秣陵春序》的顺治十年(1653)为初刻年份。今见刻本又以顺治年间振古斋本为最早也最权威,后有不少重刻本、覆刻本,故《秣陵春》之版本脉络相对简明。
《秣陵春》的文本受众以知识阶层为主,上至帝王,下至文士,皆有阅览记载。如“世祖曾于海淀览其参定《秣陵春》曲”[1],乃顺治皇帝阅读此剧的记述。康熙年间,《秣陵春》刊本在文人中传播兴盛,因此留下一些诗词读后感,如河南新安人吕履恒(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曾作《念奴娇·题〈秣陵春〉传奇》词一阕:
六朝如梦,谁解道、野老江头歌哭。海思云愁还寄托,旧都霓裳法曲。瑶水筵前,翠微宫里,夙世仙缘卜。非空非色,个中人自如玉。争奈身作虚舟,心同明镜,形影相交逐。劫火虽烧莲性在,不怕罡风颠扑。拨尽鹍弦,挝残羯鼓,泪断声难续。曲终人远,数峰江上犹绿。[2]
词中颇多用典:“霓裳法曲”即《霓裳羽衣曲》,唐代大曲中的法曲精品;“翠微宫”为唐代行宫之一;“鹍弦”是指用鹍鸡筋制成的琵琶弦,唐代梨园艺人所创,事见段安节所著《乐府杂录》中;“羯鼓”乐器虽在南北朝时传至中土,但盛行却在唐代开元、天宝间,南卓《羯鼓录》述之甚明。又多诗歌化用,如“野老江头歌哭”与杜甫《哀江头》之“少陵野老吞声哭”“海思云愁”与李白《飞龙引》之“云愁海思令人嗟”“曲终人远,数峰江上犹绿”与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等有化用关系。综上可知,吕履恒在《秣陵春》的解读上,故意将之与唐代文化作勾连。可剧作是以南唐覆亡为背景,与李唐王朝无甚关联,这样的解读又是基于怎样的理由?其实,这既是对前人解读成果的接受(此点将详于下文),同时也是话语背景的潜隐:刚刚覆灭的明朝在政治与文化上皆以唐代为楷模,朱元璋开国不久即诏令天下“衣冠如唐制”[3],如此吕履恒词中之意可以明了,借“唐”怀“明”,真正哀悼的是明亡,体恤的是剧作者吴伟业遭遇易代巨变却仍心念前明的痛苦。这一接受解读的首要特征是表达隐曲,这或与康熙朝文网渐严的时代背景有关;其次是片面,只侧重于此剧所流露的黍离之悲,而未及其在仕隐出处上对新朝的示好之意。
清中叶以后,《秣陵春》传播逐渐式微,不仅表现为其人其事难为人知,如翁方纲(1733-1818)诗中提及此事时已需作注:“《秣陵春》是巢民家所演,梅村填曲也”①翁方纲所作《题冒巢民墨迹并吴梅村手札合卷四首》诗其四为:“碧栏如画草如茵,桃叶飞觞迹又陈。我昨桥边听暮雨,何人记唱《秣陵春》。”详见《复初斋诗集》卷三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454册,第533页。,博学如郭麐(1767-1831)竟不知乡贤吴伟业著有此剧:“曩见《秣陵春传奇》,以为玉茗之后殆无其偶,特未著撰人之名。及见其《金人捧露盘》词,题为《观演秣陵春》……乃知出于梅村之手也”[4];而且体现在接受上,此时的受众已难以体谅作者苦衷,如程晋芳(1718-1784)有:“《秣陵春》事唱都残,谱就繁声字字酸。羯鼓待传天宝录,琵琶刚续玉京弹。荒秤败劫图谋少,逸老元勋位置难。累我书窗烧烛坐,英雄小传夜深看”[5],诗中“残”“酸”“累我”“图谋少”等字句已表明,诗人对剧作的情感倾向是否定的,在回望朝代更替、总结兴亡教训时也表现出了超然与理性的态度。
除完整的剧作刊本,《秣陵春》尚有曲辞雅赏这一文本传播途径,主要通过词选与小说实现。顺治十七年(1660)王士禛与邹祗谟编纂词选《倚声初集》,收录剧中《山花子·闺情》与《菩萨蛮·闺词代拟》两支小令,由此而开《秣陵春》曲辞雅赏之阅读途径:后孙默辑《十五家词》、蒋景祁编《瑶华集》词选时,皆收以上作品。康熙间褚人获《隋唐演义》小说亦引《秣陵春》曲辞:第四十七回《看琼花乐尽隋终殉死节香销烈见》引用剧作第六出《赏音》之【北骂玉郎带上小楼】曲,实际“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秣陵春》传奇在当时文人中的声誉”[6]。当然,从实际传播效果而言,此类“曲辞雅赏”的作用仅是“小助”而已。
二、《秣陵春》搬演概述
《秣陵春》场上演出的最早确切记录乃顺治十六年(1659)的南昌沧浪亭雅集,此由熊文举《良夜集沧浪亭观女剧演新翻〈秣陵春〉同遂初博庵赋得十绝呈太虚宗伯拟寄梅村祭酒》诗而知。这一组诗收录在熊氏《耻庐近集》卷二“己亥诗六十首”中,故“己亥”乃雅集时间。沧浪亭为南昌人李明睿“阆园”中的一景,《西江诗话》载其“归里构亭蓼水,榜曰沧浪。家有女乐一部,皆吴姬极选……公尝于亭上演《牡丹亭》及新翻《抹(秣)陵春》二曲,名流毕集,竞为诗歌以志其胜”。由此可知学界所谓“顺治年间,(《秣陵春》)曾在苏州沧浪亭等处演出”[7]舛误所在:此“沧浪亭”在南昌,而非苏州。
此次雅集的参与者由熊文举之诗可知部分:“遂初”朱徽、“博庵”黎元宽、“太虚宗伯”李明睿等;又据钱谦益《读豫章仙音谱漫题八绝句》诗可知,“梅公”李元鼎、“计百”周令树亦在列。另,朱中楣有《宗伯年嫂相期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漫成十绝》组诗,则当日雅集尚有女眷在场。故此,雅集参与者至少有上述8人。
吴伟业的《金人捧露盘·观演〈秣陵春〉》词作,是此剧雅集搬演的又一记录。据郭英德先生考证,“顺治十七年可为此词作期的下限”[8],则搬演时间在此之前。徐釚曾言:“吴祭酒作《秣陵春》,一名《双影记》。尝寒夜命小鬟歌演,自赋《金人捧露盘》一词”[9](P521),意指搬演乃吴伟业亲自组织,但此说可疑,如王永健先生认为:“创作【金人捧露盘】的那次演出,当是由某家乐或某戏班的全本演出”[10],则吴伟业不是组织者而是观演者;又据词中“逢高会、身在他乡”,则演出应在太仓以外的雅集之上。故此,徐釚所谓吴伟业曾自命“小鬟歌演”的说法难以成立,其所吟咏当为某次雅集中的正式搬演。
康熙间,如皋水绘园是《秣陵春》的搬演中心。许承钦《戊辰仲春偶游雉皋兼再访巢民先生》诗为水绘园搬演的最早记录,由“戊辰”可知,观赏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水绘园主人冒襄极爱此剧,“日日演《秣陵》,歌哭吴司成”[11](P1499),所以搬演频率很高;又因冒襄交游广泛,故此剧的观赏者不在少数。以《同人集》卷十一《己巳清和廿五日冒宪副前辈百岁生忌》诗所述为例,因题下录“吴锵玉川”“三韩董廷荣天锡”“张圮授孺子”“许抡公铨”“石为崧五仲”等5人之作,故参与冒辟疆祭奠亡父事件者至少有此5人;又吴锵诗中有“传家共说今徐庾,故国争伤旧李唐”,并注明“是日演《秣陵春》”,故知此时曾搬演此剧。冒襄又曾以诗相邀佘仪曾观赏《秣陵春》:“梅村祭酒谱《秣陵》,只有临川堪与京……毘陵即至申旧盟”[11](P1491),因二人交往频仍,邀约应得实现。综上,《同人集》所录《秣陵春》观赏者至少有7人:许承钦、佘仪曾、吴锵、许抡、张圮授、石为崧、董廷荣等。
另外,《秣陵春》传奇或曾在昆山南园演出。据吴伟业为徐乾学之父徐开法所作墓文,徐氏晚年“偃息吾吴氏之南园,索余所作传奇,令儿童歌之以为乐”[12](P944),因言明是“传奇”,故所指只能是《秣陵春》。徐开法卒于长子徐乾学及第之前,故而搬演不会早于康熙九年。徐氏乃昆山名门,开法之子中有两探花、一状元,家族有新朝之恩,却无进退之难,为何要搬演反映易代凄楚的剧作?究其原因,除开法本人曾历明清鼎革之外,亦因其妻家乃昆山顾氏,顾炎武为其妻弟,如此的人生经历与家族关系,自是难免兴亡感喟,其对《秣陵春》传奇抱有好感亦在情理之中。
综上可知,从顺治末年至康熙中叶,《秣陵春》皆有搬演记载。前人“《秣陵春》只在吴伟业在世的时候演过”[13]的说法,可以修正矣。因有名流“竞为诗歌以志其胜”,故雅集中的戏剧赏评内容丰富。而沧浪亭雅集与水绘园雅集又分别反映了清初“贰臣”与“遗民”两个文化群体的审美特性,因此更具解析价值,下文将重点考察。
三、沧浪亭雅集中贰臣群体对《秣陵春》的解读
前文已及,顺治年间的沧浪亭雅集参与者至少有8人,除李明睿夫人之外,其他7人生平可知。其中,李明睿(1585-1671)、熊文举、李元鼎、朱徽(生卒年不详,明崇祯四年进士)4人皆曾历仕明、清两代,乃所谓“贰臣”者;黎元宽(生卒年不详,明崇祯元年进士)入清后屡荐不起,是坚定的遗民;周令树(1633-1688)乃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是盛朝新贵;朱中楣为明宗室朱议汶之次女、李元鼎之侧室。综上,沧浪亭雅集参与者的身份多元,遗民、贰臣、新贵相杂,但贰臣人数最多。雅集唱和诗现只存4人之作:熊文举、李元鼎、朱徽、朱中楣,其中又以前两位存诗最多,故由此而探知贰臣群体的观剧之感。
熊文举(1599-1669),字公远,号雪堂,江西新建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知合肥县,擢吏部主事、稽勋司郎中,后曾仕李自成大顺朝,入清官至吏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现有《雪堂集》《耻庐近集》《侣鸥阁近集》《江雁草》等著述传世。此次观剧,熊氏作诗20首:《良夜集沧浪亭观女剧演新翻〈秣陵春〉同遂初博庵赋得十绝呈太虚宗伯拟寄梅村祭酒》10首、《再和李司马远山韵》4首及《又和遂初诗》6首。诗作数量和内容都说明,此剧在诗人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择要而言,熊文举对《秣陵春》的黍离之悲最有体会,试看以下两首诗作:
哀音亡国不堪闻,谁过鸣銮念故君?想见娄江吊双影,伤心如读《战场文》。
量愁底事付东流,吹皱池塘绿未休。漫把山河易真迹,昭陵石马泣高秋。[14]
第一首诗着重于对作者的体恤,诗中的“双影”是指剧作中两样重要道具——宜官宝镜、和田玉杯——的幻影,用以代指《秣陵春》。熊氏说它们寄托了吴梅村的亡国伤感,如同唐人李华《吊古战场文》中描述的那样,凄惨而悲凉,有的只是无尽的苦难与伤痛。第二首诗侧重于对作品的理解,其中“量愁底事付东流”乃正用李煜【虞美人】词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意,而“吹皱池塘绿未休”则反用其另一阕【虞美人】中“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之意,皆述失国悲痛。又接之以“昭陵石马泣高秋”,即通过想象唐太宗墓室中八骏石刻的哭泣,来抒发盛衰难以逆料的悲怆。其次,特别关注《秣陵春》中的这一情节:李煜亡国升仙后仍助徐适、且对其参与新朝科举之事不以为忤:
江南公事榜勾当,一叶寒帆渡李郎。犹为徐卿圆宝镜,数行残墨认宜光。
异代君臣笑李皇,怜才犹自拣徐郎。不知刬袜香何在,昨夜东风诉国亡。[14]
这一捕捉因关涉对《秣陵春》创作意图的解读,故而非常重要。吴伟业《秣陵春》的作意究竟为何?作者虽作《序》,却言“是编也,果有托而然耶?果无托而然耶?即余亦不得而知也”[12](P727),实未明说。当代学者对此曾有揭示:“吴伟业在顺治十年九月出仕清廷之前,就已经借传奇戏曲的写作,既表达对故国眷恋的铭记,也包含着对新朝恩宠的感戴”[8],则其确有为自己即将仕清行为张目之意,而这又实在是无法明白直道的。对照可知,熊文举在作品问世之初已得作者隐曲心理的正解。《秣陵春》中塑造了一位宽宏大量的亡国之君,明显是吴伟业希望减轻负罪之感的心理流露,此为贰臣之共同期盼,因此会得熊文举之敏锐捕捉。而有关吴伟业的一则轶事,也颇能佐证这一心理的萦系之深:
吴梅村于壬子(按:当为辛亥之误,梅村卒于是年)元旦,梦两青衣来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为章帝也,急往。乃见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伤,当日不止汝一人也。[15]“章帝”,顺治也;“烈皇帝”,崇祯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中吴伟业陡见崇祯,正为变节而惭悔痛哭,却得亡国之君的大度宽慰,这样的好事不正是其潜意识的流露?
李元鼎(1595-1670),字吉甫,号梅公,江西吉水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历仕明、大顺、清三朝,入清授光禄少卿,迁兵部侍郎,转左侍郎,著有《石园集》《灌研斋文集》等。雅集中李元鼎有《冬夜同集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次熊少宰韵十首》《再和朱遂初都垣八首》及《又和黎博庵学宪三首》,即咏剧诗21首。同为背负舆论压力的贰臣,李元鼎也对剧作中感旧与恋新的情感矛盾有深切的共鸣之感,既同情失国君主的痛苦:“今古茫茫总未分,可堪异代更逢君。伤心最是离鸿曲,解赠琵琶不忍焚”[16],也悲叹易代文人的尴尬:“话到兴亡事事悲,娄江笔彩绚沦漪。后堂丝竹浑无奈,空忆先朝旧羽仪。”[16]但细究熊、李二人之表达,似又有不同。相较而言,熊文举更为坦诚,颇多代入感,如“见说彭宣四座惊”[14]一句,用彭宣这位东汉名臣不仕王莽新朝的典故,直接揭示自己变节的负疚心理;而李元鼎则超脱些,前述引文之外,再如“钟漏沉沉锦瑟围,镜花杯影共依稀。秣陵春草年年绿,谁向昭阳看燕飞”[16],用时光流转的无情削减朝代更迭的感伤,自我宽慰之意显然。
总体而言,因为经历相似、处境相同、情感相通,以贰臣群体为主的沧浪亭雅集中的戏剧接受主要表现为对《秣陵春》的“正向”解读,即在对作者原意准确理解的基础上展开多向度对话,从而实现了宣泄压抑、求得宽慰的观赏效果。
四、水绘园雅集中遗民群体对《秣陵春》的阐释
如皋冒氏蓄乐始于冒梦龄,但至冒襄(1611-1693)而声名远扬。明清鼎革后,冒辟疆无意用世,隐居于如皋水绘园,寄情声色、园亭,好友李清曾述其声色之娱的行为指向:
梨园之为忠义一大鼓吹也。其事肇于两唐:一安禄山宴凝碧池,盛奏众乐,梨园子弟皆泣;一宋师下金陵,诸将置酒,乐人大恸。呜呼!忠哉。故今者梨园家独冠,故冠以寻源于唐,岂非两唐忠义之余波也。[11](P895)
因为戏剧具有“鼓吹忠义”的独特价值,所以遗民重之乃出于情感寄托,这是冒襄热衷戏剧搬演的文化根源。冒氏家班所演剧目,主要有《燕子笺》《黑白卫》《邯郸梦》《牡丹亭》等,《秣陵春》是其康熙年间的经典剧目。
前文已示,水绘园雅集中观赏过《秣陵春》传奇者至少有7人,但留下剧评的只有许承钦、张圮授2人。许承钦,字钦哉,号漱雪,湖广汉阳人,明崇祯进士,知溧阳县,后迁户部主事。甲申后坚隐不出,有《漱雪集》《粘影词》传世。水绘园雅集许氏著有《戊辰仲春偶游雉皋兼再访巢民先生》组诗。张圮授,明末清初如皋人,字孺子,著有《茗柯集》。水绘园观演《秣陵春》张氏在《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原倡》之十二、十三中抒发了观剧感想。此外,吴锵、佘仪曾亦未仕清,加上雅集主人冒襄,则水绘园雅集中的《秣陵春》赏评是以遗民群体为主。与沧浪亭雅集中各抒己见的赏评氛围不同,水绘园雅集存在意见主导。张圮授曾说:“祭酒谱黄绢,传留绝妙词。故人老巢民,赏音恒在兹。两美互作述,纤悉订无疑。古语成于乐,斯言不我欺”[11](P1503),许承钦亦言:“灵心妙腕忆梅村,更赖巢民细讨论。何用雪儿频记豆?绕梁风雨自惊魂”,都指明一点:因为水绘园主人的细心揭示,《秣陵春》才有了让人“惊魂”[11](P1486)的观赏效果。那么冒襄究竟有何高见?冒辟疆的《步和许漱雪先生观小优演吴梅村祭酒〈秣陵春〉十绝句原韵》组诗中存有答案,试看其中关键的4首:
老气心伤日日增,仙音犹自爱迦陵。西宫旧恨娄东谱,四十余年红泪水。(琵琶所传皆西宫旧恨,非徐学士不能知也)
重谱霓裳乐事多,那知缓急付高歌。曹生早识兴亡兆,薜荔山阿带女萝。(唐《霓裳羽衣》最为大曲,乱失其传。昭惠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天宝遗音复传于世。内史舍人徐铉知音,问之国工曹生曰:“法曲终则缓,此声反急,何也?”曹曰:“旧谱原缓,宫中有人易之,非吉兆也。”后主果亡)
到来旧客妙氤氲,老态犹然痴若云。共听琵琶惊往事,青衫湿透不堪闻。(琵琶是全部龙穴,观者须知其来脉。)
华音敢道发家伶,寂寞凝神始解听。昭惠小周皆绝代,保仪何独擅娉婷?(二周后皆后主飞燕、合德,何以独表不数幸之保仪?作者之意在此不在彼)[11](P1487-1488)
冒襄首先提出“西宫旧恨娄东谱”的剧作主题结论,又由“曹生早识兴亡兆,薜荔山阿带女萝”及自注说明,此“恨”乃亡国之恨,是早有征兆、乱自上作的亡国教训。可又与“西宫”何干?冒襄先在诗中提问:“昭惠小周皆绝代,保仪何独擅娉婷”?后又自答:大小周后皆以色事人、惑主误国的失德之人,《秣陵春》中没有安排她们的戏份,而是让当时并不得宠的黄保仪陪伴后主升仙天国,明显反映出吴梅村对“西宫”的重视,是典型的春秋笔法。这一解读真有道理?据陆游所著《南唐书》,小周后“国亡,从后主北迁,封郑国夫人。太平兴国二年,后主殂,后悲哀不自胜,亦卒”;保仪黄氏“以工书札,使专掌宫中书籍。二周后相继专房燕昵,故保仪虽见赏识,终不得数御幸也……保仪亦从北迁,卒于大梁”[17],则史实中小周后是与黄保仪、后主一起被掳的,对后主也是忠心不二,并非如剧作所述。如此看来,吴伟业确有改窜帝妃关系之意。冒辟疆也是据此认为,《秣陵春》存在近贤远佞的批判之意,“西宫旧恨”的主题之论由此确立。不可忽视的还有琵琶在剧作中的作用。《秣陵春》亦名《双影记》,“双影”即“杯影”与“镜影”,是剧作中最重要的道具。但在冒襄的主题阐释中,琵琶却更重要:“琵琶是全部龙穴,观者须知其来脉”,“共听琵琶惊往事,青衫湿透不堪闻”,原因是它在《秣陵春》传奇中是亡国之恨的象征。剧中南唐“仙音院第一手琵琶”曹善才乐工以琵琶弹唱李煜小令,表达对亡国旧主的祭奠与怀念,即剧作第六出《赏音》之【北骂玉郎带上小楼】【前腔】的内容,实为亡国哀音。将琵琶的作用抬高,是冒襄在《秣陵春》主题揭示中的创造,目的是为主题构建服务。
综上,水绘园雅集对《秣陵春》传奇的搬演,是接受者对作品“发现”的过程:以冒襄为主导的遗民群体,从作品的语言、意象系统中发现了人之所未见,具有鲜明的创新意味。这里尚需交待一个背景:水绘园搬演此剧时吴伟业离世已近20年,距其出仕新朝前的“彷徨失措”更有30多年,尤其是通过《临终诗四首》及《与子暻疏》遗嘱,晚年梅村留给世人的是忏悔者的形象,这是遗民的冒襄极愿看到的——好友终究是眷恋故国与旧主的。这一切不仅淡化了《秣陵春》为失节者辩护的嫌疑,而且加重了亲朋故旧对梅村悲剧人格的认同。因此,冒襄在评剧诗中所言:“今日曲中传怨恨,一齐遥拜杜鹃魂”[11](P1488),是用“杜鹃啼血”之意来祭奠梅村,将亡国失主的痛苦寄情于此,由此而构筑起水绘园雅集审美的逻辑基础,正为其“以戏寄志”行为意义的具体表现。
五、《秣陵春》“读后感”与“观后感”接受比较
由前文所述可明,《秣陵春》传奇在清代兼有刊本阅读与场上观赏两种传播方式,并都留下了一定数量的文字材料,因此,不同传播途径的接受比较研究成为可能。而其中最为显著者乃两种传播方式所导致的接受差异。
首先,“场上”比“文本”更有感染力,从而更具快捷且深刻的接受效果。在沧浪亭雅集与水绘园雅集中担任表演的李明睿家班与冒襄家班,皆当时的一流剧班,声望极隆。裘君弘在《西江诗话》中称李氏家班乃“皆吴姬极选”,实为持正之论,因从尚镕、施闰章、曹溶、毛奇龄、陈弘绪、孙枝蔚、归庄等观赏者称扬的诗文中,可得普遍印证。而冒氏家班亦为极品,班中先后有杨枝、紫云、秦箫、小杨枝、朱音仙等知名优伶,所演剧目皆轰动一时,致有“不遇冒家诸子弟,梨园空自说娉婷”[11](P1487)之说。由这样的剧班搬演《秣陵春》,演出效果可以想见。从两次雅集的“观后感”诗文来看,家班所演皆为全本,其优点是让观众在一个集中的时间长度中,通过对舞台艺术的综合观赏,全面而生动地把握故事的整体,从而达到快捷而深刻的接受效果。许承钦谓水绘园演出:“神观虚凝娇不断,坐停银烛到天明”“唱到断肠心醉处,真疑看杀小婵娟”,熊文举谓沧浪亭演出:“玉人低唱易黄昏”“唱到伤心夜漏稀”“为君此曲堪惆怅”等,皆可见声色俱佳的表演给观众带来的情感刺激之巨,是为个体阅读所难以得到的接受体验。
其次,从文人雅集的群体特性而言,恰当的场合促进了观剧感受的切磋与研讨。“雅集”的重要特性是以诗文创作为主,东晋的“兰亭雅集”、唐代的“滕王阁雅集”等皆如此。而本文所及之沧浪亭与水绘园二雅集,更有参与者关系亲密之特点。他们多为志趣相投、才情相埒的挚友,文学素养方面又旗鼓相当,这为《秣陵春》传奇的接受“对话”奠定了基础。以沧浪亭雅集为例,熊文举吟咏10首七绝之后,李元鼎、朱徽、黎元宽、朱中楣、周令树等皆有唱和,而熊文举又再和李元鼎、朱中楣、朱徽之和诗,切磋兴致甚高。在交流中更可见影响之迹,如熊文举首倡的“观后感”中感伤意味深重:“哀音亡国不堪闻”,“南唐往事犹如此,应为孤臣更怆魂”;李元鼎却说:“秣陵春草年年绿,谁向昭阳看燕飞”,认为人类社会的改朝换代与自然界的时序变化相似,既然无奈所以大可看淡;朱中楣也有类似观点:“为写南唐千古恨,可知不是旧时秋”;故熊文举“再和”时也说:“万古兴亡落照中,玉笙吹彻小楼空”,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观照明清易代,愁苦似得减轻,而这正是对话的结果。
最后,从成果角度而论,“观后感”远胜“读后感”。《秣陵春》传奇的刊本中未见评点本,这是因为它尚未形成如《西厢记》《牡丹亭》那样的文本阅读经验积淀,仅有的二三十首诗词读后感,难与近百首的观剧诗匹敌。除“量”之外,“质”之一面“读后感”也逊色不少。总体而论,《秣陵春》读后感多言简意赅之作,如江苏吴县人韩骐(1694-1754)曾作《舟中书〈秣陵春〉院本》诗:“江上秋风老白蘋,扁舟载得《秣陵春》。消他一掬兴亡泪,泣尽南朝镜里人”[18],仅是点出兴亡主题;又如前文所举吕履恒《念奴娇·题〈秣陵春〉传奇》词,意存偏颇,故在“读后感”中难觅对《秣陵春》全面而准确的解读;相比之下,雅集观赏则尽意而准确得多。
虽然“文本”与“场上”两种传播方式差异较大,但二者亦有交互促进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当观剧经验诉诸于文本时,其思维方式、审美取向等与阅读经验的表达并无不同。《秣陵春》在沧浪亭搬演后,雅集吟咏不仅以文人别集方式传播,而且有《豫章仙音谱》专册,从“江左”传至全国,社会流传度甚高,此由钱谦益《读豫章仙音谱漫题八绝句》诗可知。若以吕履恒《念奴娇·题〈秣陵春〉传奇》词作为比照对象,则“观后感”与“读后感”的内在联系至少有两点:一是化用唐人诗文上的借鉴,以李元鼎《冬夜同集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次熊少宰韵十首》为例,7处化用中至少3处与唐人有关:“谁将江怨入箜篌”与李贺《李凭箜篌引》、“纷纷鼓瑟向齐门”与韩愈《答陈商书》、“殷勤疑唱《比红儿》”与罗虬《比红儿诗》,而至吕履恒之词,经前文揭示可知唐诗化用更为专一;二是使事用典上对“乐工”之典有承继,吕履恒词作中的“拨尽鹍弦”与“挝残羯鼓”两句,实际都指唐代宫廷乐工,回望沧浪亭诸君诗作,朱中楣“只有乐工偏解事,小楼深锁听遗音”、熊文举“江潭数点龟年泪,又到琵琶老乐工”、李元鼎“只恐乐工贪度曲,一时惊散小游魂”等,早已表现出对“乐工”之典的偏好,两种接受渠道之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对《秣陵春》传播与接受事实的廓清,不仅可以揭示这一具体研究对象的历史特性,而且可以重新审视学界的某些说法。如,《秣陵春》是“典型的案头戏”[19]吗?当然不是,众多的搬演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再如,吴伟业的戏剧成就难与汤显祖比肩[20]吗?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答案正好相反。最早提及二者的是熊文举:“紫玉红牙许共论,临川之后有梅村”,意在称许后者,惜未细论;后钱谦益将讨论推进一步:“《牡丹亭》苦唱情多,其奈新声《水调》何?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21],认为《秣陵春》所发虽是黍离之悲,但在抒情言志上仍可见其对《牡丹亭》“多情”传统的继承;至冒襄“(梅村)先生寄托遥深,词场独擅,前有元人四家,后与临川作劲敌”[11](P1488)之述,乃将梅村放置于曲家统序中加以审视,取境扩大,结论明确;而徐釚在《词苑丛谈》中所谓“吴祭酒梅村,撰《秣陵春》《通天台》杂剧,直夺汤临川之座”[9](P274),实为“词评”语境中旁出的“剧评”话语,但却是认定吴伟业戏剧地位可与汤显祖并论的共识性言论。事实上,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曾在沧浪亭与水绘园中搬演过,文人亦有题咏,但观剧诗各是16首与8首,难与《秣陵春》之接受盛况相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易代初期的特点时刻《秣陵春》更能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故此,在戏剧接受的考察中,“史”与“时”并重,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真相。
[1]程其珏等.光绪嘉定县志(卷十九)[M].上海:上海书店,1991.
[2]吕履恒.梦月岩诗余[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洪武元年二月)[M].上海:上海书店,1984.
[4]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二)[A].词话丛编[C].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5]杨钟羲.雪桥诗话全编[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6]朱则杰.读吴伟业诗词曲[J].浙江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2).
[7]齐森华,等.中国曲学大辞典[Z].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8]郭英德.吴伟业《秣陵春》传奇作期新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6).
[9]王百里.词苑丛谈校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0]王永健.大诗人的昆曲情结:论吴伟业的戏曲创作[J].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4).
[11]万久富,丁富生.冒辟疆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12]李学颖.吴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叶君远.吴梅村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4]熊文举.耻庐近集(卷二)[M].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本.
[15]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6]李元鼎.石园全集(卷八)[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7]钱仲联,马亚中.陆游全集校注(第十二册《南唐书校注》卷十六《后妃诸王列传》)[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18]韩骐.补瓢存稿(卷四)[M].四库未收书本.
[19]曾垂超.论吴伟业的戏曲创作:兼评案头戏[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2).
[20]郑良志.吴梅村与汤显祖师承关系的文献考述[J].文献,2009,(2).
[21]钱仲联.牧斋有学集(卷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戴庆瑄]
戴健,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江苏扬州225002
I206.2
A
1004-4434(2016)08-0117-06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510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