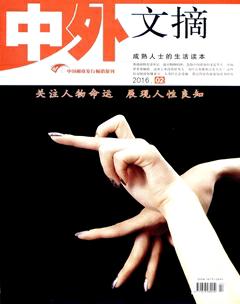“文革”后退隐的党内老人
2016-02-23刘昊孙良滋曾莉蓉
刘昊 孙良滋 曾莉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汪东兴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他在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辞职,获得批准。与他一同淡出政治舞台的,还有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农业的纪登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主管过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的吴德等人。
检讨迟迟通不过
1982年后,汪东兴、吴德和陈锡联进了中顾委,纪登奎进了农研所(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他们面对的,是如何重新融入国家机构的运转,以一种远离权力核心的方式。一件事情可以说明纪登奎的谨慎。纪登奎长子纪坡民回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之间的一年半,邓小平曾让还未辞职的纪登奎管过三件事:制定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与空军分家的民用航空业、发展旅游业挣外汇。前两件都被纪登奎婉拒,他告诉儿子,拒绝是因为这两件事敏感,“犯了错误的干部,不担事儿”。纪登奎接过旅游业后做了两件事:调查外国人一星期来中国能挣多少外汇,翻译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合资饭店合同,借鉴并筹建北京的长城、昆仑、燕京等饭店。
在中顾委担任常委的陈锡联,承担的一项工作就是出席各种纪念活动和开幕仪式。陈锡联在回忆录里写道:“1994年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委托我和其他同志前往山西太原,出席徐向前同志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当时我身体不好,但是中央的委托我不能推托,战争年代徐帅救过我一命,今天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也要去参加。”
对“文革”的反思还在继续。1984年开始,四个老干部成了重点做检查的对象。陈锡联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受邓小平邀请,去他家里谈话。他对邓说:“我这一生中,感到最对不住你的,是在你第二次被打倒时,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说话。”邓小平说:“那个时候谁也没办法,你也无能为力,你在北京不欠账,你的问题主要在东北。”
吴德和陈锡联的检讨迟迟通不过,许多干部对他们“文革”的表现有意见。吴家大女吴铁梅表示,最后是邓小平替自己父亲说了话。陈锡联在回忆录中也写道,邓小平替他跟其他干部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
高层批示定待遇
汪东兴晚年搬离中南海,住在西单六部口新壁街的一座四合院,对面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院落。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后,纪登奎一家也搬到了灯市东口内务部街的一座四合院——狭窄破旧的僻巷中,不起眼的灰色铁门内,藏着一个轩敞的院子。华国锋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时也曾住在这里。吴德晚年继续住在东交民巷17号3号楼,而陈锡联则一直住在新街口航空胡同的四合院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曾撰文指出,“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后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长级范围内的”。例如,纪登奎家里没有中央领导人所配备的保健医生、警卫员等,来九号院时,家中也没有警卫班,出差时也未派出警卫人员。从出差时坐软卧包厢、配一台进口日本车来看,其待遇也属于正部级。纪坡民告诉记者,“我爸在政治局时,家里炊事员是去王府井34号的市场买菜肉粮食油盐酱醋的,我爸不当中央领导人后,就是我妈去买了,炊事员还给我们家做饭,一直维持到我爸去世”。
“高层批示”的确是确定待遇的直接方式。1992年,吴德被诊断出患有血液病,病情加重,吴铁梅向组织申请,给父亲恢复国家领导人的待遇。此后,吴德的医疗费用一直由国家卫生部直接结算。在父亲葬礼时,吴铁梅对于父亲享受的待遇有了更微妙的认识——治丧委员会的人告诉她,葬礼的规模“比国家级领导人低半级,比部级领导人高半级”。这也是之前组织给纪登奎举行葬礼的规格——政治局常委都在葬礼上送花圈,两位政治局委员来参加葬礼。
暮年的归隐生活
住在新壁街的汪东兴,生活得安静低调。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与汪东兴常交流,在阎看来,汪“心很宽,想得开”,他九十大寿时,曾在西单一家饭店请老战友吃饭。汪东兴津津乐道于自己的两次大手术——四分之三的胃部切除和前列腺手术,以及两次小手术。“他身体好时,每天出来散步。”与汪东兴时常走动、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透露。阎长贵回忆,汪东兴暮年时常对他言及毛主席功劳很大,“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杨银禄也忆及,汪东兴常说,“我想毛主席了”,“然后就流下眼泪”。据《南方周末》2011年6月的报道,彼时汪东兴还在通读毛选,“碰到问题会去里面找答案”。
吴德晚年过上了归隐的生活,家里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门可罗雀。吴铁梅告诉记者,父亲在家中看书、写字——用瘦金体抄毛泽东的诗歌,晚上偶尔睡不着,就去院子里看看花,他的车“跑的字儿最少,用的油也最少”。有一次胡耀邦来访,对吴德说:“你可到处看看去,到全国各地啊!”自那以后,吴铁梅陪父亲去了广州,“看看改革开放”,又去了趟西安。之后吴德还去过海南,看到路边浓妆艳抹的拉客女热情地朝他打招呼,他出于礼貌也回以点头,然后困惑地问女儿:“她们为什么这样?”
据吴铁梅回忆,有一次在跟纪坡民的聊天中,“老爷子”听到了“社会上乌七八糟的事情”,挺不高兴,还跑到中纪委去发了言。在《新闻联播》上看到官员贪污的报道,吴德就很生气:“把电视关掉!”陈锡联也会边看电视边骂人。“看贪污腐败的新闻,他会说:该杀头!”陈锡联喜欢四处转悠,把北京周边有鱼的地方都去了一遍,家里有很多钓鱼比赛的奖杯。他晚年的交际圈主要在军队,聊的也都是战争年代的经历。不变的是,陈锡联客厅里的毛泽东像从1973年以来从没换过。
最近十余年,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的日记、口述史或回忆录相继出版。但除汪东兴外,其他人在2000年前就已病逝。这些书中有些回应世人猜测的段落。汪东兴书中公布了林彪事件中自己给毛泽东写的检讨,而陈锡联则回忆,“抓‘四人帮一伙,要动用卫戍区的部队……吴德、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抓捕当晚,是他提醒华国锋,“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枪”。
盖棺定论身后名
汪东兴遗体告别仪式上,《汪东兴同志生平》被印成7页A4纸,装订成薄薄一册。“你一个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给个什么评价呢?就是这个‘生平。”纪坡民说。而官方概括性评价的措辞也历来被家属所看重,他们尤其重视父辈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否得到官方承认。
1995年11月29日,吴德去世后,吴铁梅为了父亲“文革”中的评价措辞,曾一度与治丧委员会争执。当时吴铁梅提出,这份初稿中没有父亲参与的两件大事: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粉碎“四人帮”。治丧委员会认为,吴德“文革”前的事可多写,“文革”后的事可不提。吴铁梅想法刚好相反:“‘文革前的档案里都有,唯独‘文革后要写清楚,我爸不是‘那边的,是‘这边的”。
吴铁梅把父亲1995年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的口述实录《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拿给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回去研究研究”。吴德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夜里11点半,吴铁梅接到电话,父亲“生平”里头多了一句话:“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吴德同志完成了中央部署给他的工作”。
吴德膝下有一对女儿,吴铁梅退休前从事文物局工作,二女儿是医生,家中再无人从政。吴铁梅没有收父亲口述史的稿费,而是换成了成百上千本书,“谁来问我爸爸的事,我就给他看这本书”。汪东兴和陈锡联的儿女大都在军队。陈锡联长子在沈阳军区以大校军衔退休;次子是飞行员,1982年执行飞行任务时遇难;三儿子在2011年晋升中将军衔,小女儿也是一名军医。“军区的人说,这几个子女都比较低调。”纪坡民说。纪登奎有五个子女,两个在国内,三个在国外,纪坡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退休后一直在家中读书撰文。他时常接受采访,替早逝的父亲说清很多事,可有的事连他也说不清。他说,“他们几个人,是大格局中的小事儿。”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