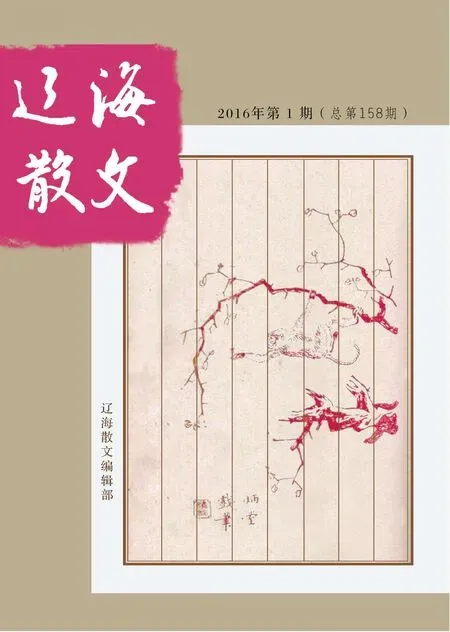大酱情怀
2016-02-23李俊宝
李俊宝
大酱情怀
李俊宝

李俊宝
辽宁省北票市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丹东市曲艺家协会理事。幼时贫寒,小学四年辍学务农。18岁从戎23载,转业至凤城市地方税务局任党委副书记五千余天。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小说、散文、辞赋、曲艺等千字短文百余篇,偶尔获奖。先后出版散文集《岁痕》、长篇小说 《白杨魂》《风雨圣贤堂》和章回体对口快板《喋血辽东》(描写抗日英雄)等作品。
我的生活很简单,对吃、穿、用没有任何讲究,只是习惯于吃母亲做的大酱。若问为什么,我也说不太好,就觉得母亲做的大酱有味道。
小时候,每年春天做大酱时,我总是围在母亲的身前身后转悠,为的是让母亲给我抓一把炒熟的黄豆吃。一来二去,我便掌握了制作大酱的过程。母亲制作大酱的程序可能与其他地区不一样。做大酱前,母亲要把春节前做豆腐时留下的黄豆拿出来,用筛子筛一遍,再用簸箕将其杂质簸出去,然后把黄豆放进锅里炒,一直把黄豆炒爆花才从锅里取出来。炒熟的黄豆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不用吃,闻着都会垂涎三尺。
那时的小孩儿没有零嘴可吃,只有每年炒黄豆时,母亲才给抓一把尝尝,其余的全部装进袋子放进厢房里锁上了。等我背着书包上学后,母亲才从厢房里拿出来,扛到碾房磨成豆面,生怕我把全家一年的嚼裹儿当零食抓没了。等我放学回来时,母亲已把黄豆面攥成了一个个香瓜大小的酱疙瘩,摆放在一个平底柳筐里,放在了一个不冷不热不湿不燥的通风处发酵,等酱疙瘩上长出一层白茸茸的细毛时,才算发酵好了。这时,把酱疙瘩掰开,从里到外全都变成了栗红色,到了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就用它下大酱了。
为什么赶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下大酱,至今还是个谜。我问母亲,她说只有这天下的大酱才好吃,如果早一天或晚一天,大酱就会发酸、发臭、没有大酱味儿。我不知其所以然,探索了好些年也没找到任何关于制作大酱的源头,只是觉得老祖宗太伟大了,不知历经了多少年多少代,才摸索出制作大酱的日子。
庄户人家对大酱是情有独钟的。母亲把大酱下好后装进坛子里或小缸里,放在朝阳的炕头上,每天揉翻一次,连续揉翻几天,缸里就散发出了浓浓的酱香。这时,母亲又用牛皮纸将缸口封严,等什么时候把陈酱吃完,才打开缸口吃新酱。母亲说,大酱不怕年头多,存放的时间愈长酱味愈浓。
在老家,家家户户的炕头上都放着一口小酱缸或酱坛子,这是家庭富裕的象征。如果谁家的儿子大了,媒婆去提亲时见炕头上没有酱缸,就知道这家不会过日子,该成的亲也泡汤了。所以,多数人家宁可春节不做豆腐,也要把黄豆攒下来做大酱。也有个别人家,又想吃豆腐又想吃大酱,只能把生产队分给的有数的黄豆掺上玉米面做大酱。这样的大酱无论色泽、口感、味道都远不如纯黄豆做的好吃。所以,父亲对做大酱的事非常重视,他说:“年节好过,平常日子难熬。宁可春节少做豆腐,也绝不用玉米面做大酱。”所以,母亲做出来的大酱不仅色泽暗红,也非常好吃。每隔几日,用筷子从酱缸里剜一块放进碗里,用水一搅就能调和成稠稠的一大碗,一进院儿就能闻到扑鼻的酱香味儿。
大酱是北方庄稼人餐桌上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在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时,一月一年很少吃到几次炒菜或炖菜,大酱便成了庄稼人一年四季下饭的佐料。白菜帮子、萝卜缨子、婆婆丁、苦苦菜等等,都能蘸着大酱咽进肚里。母亲说,大酱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甭管苦的、辣的、涩的、酸的蔬菜,一经蘸上大酱,就变成可口的美味了。
东北有句民谣:“大葱蘸大酱,越吃人越胖。”其实,我就是吃着野菜蘸大酱活过来的。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山上的野菜都被人掠光了,母亲就从杨树上撸几筐嫩嫩的杨树叶子回来,用开水潦一下放进大缸里泡上三天五日,树叶就发酵了。饿了时,母亲就从缸里捞出一团把水分攥干,让我蘸着大酱充饥。发酵后的杨树叶吃到嘴里苦涩苦酸,可一经蘸上大酱,味道就突然变得可口可乐了。每到青黄不接时,全家人大都以吃杨树叶蘸大酱度日。所以,我对大酱的情怀是发自内心的,对大酱的情感也是由来已久的。
我是大酱的贪婪者。不管是生吃、熟吃,总是百吃不厌。当兵时,部队吃的大酱都是从当地酱菜厂订购的,其味道也不亚于母亲做的。转业到地方后,就买不到那种可口味美的大酱了。有时,朋友送我几罐头瓶家里做的大酱,可我总是吃不习惯。因为,我总觉得这里的大酱跟母亲做的不一样。大酱呈灰黄色,稀稀的酱汤里掺杂着类似婴儿屙出的那种还没消化好的豆瓣儿,吃到嘴里有种咸苦、微臭的味道儿。无论色泽抑或口感都远不如母亲做的好吃。所以,在外几十年,我很少吃外面的大酱。平时除了在市场上买两袋名牌大酱应应急,其余的全是回老家探望母亲时带回来的大酱。有时,妻子为了给我调剂口味,还特意做一碟肉丝酱或鸡蛋酱,可我还是觉得不如原汁原味的生酱好吃。妻子说我好伺候,儿子说我没档次。我以为甜酸苦辣都有营养,风霜雪雨都要生活。
我常想小时候,母亲把高粱面用开水烫一下,再用擀面杖擀成盘子大小、比铜钱还薄的一张张薄饼。吃饭时,把大酱抹在饼上,再卷上一些大葱、香菜之类的青菜,那味道实在是美极了,至今想起来还生津流涎。
现在,我工作在一座非常秀美的山城。每到春季,山上各种野菜发芽吐绿时,我就带着儿子到山上挖野菜了。什么婆婆丁、苦苦菜、曲曲芽等等,我能蘸着大酱美美地吃上一个春天。妻子看我吃得津津有味,对儿子说:“你爸爸还没忘了农民的本色。”更可笑的是,到山上挖野菜时,当地老乡还认真地问我说:“你家还养鸭子呀?”我只好笑笑说:“养,还是挺大的一只鸭子呢!”儿子听了笑得前仰后合。一年之中,我要吃上三个多月的野菜蘸大酱,不仅绿色实惠,还爽胃可口,更重要的是保养了身体。
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经好得无法再好了。但品尝了大江南北的美味佳肴之后,野菜蘸大酱又以其纯朴清新的姿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不管是城里、乡下,还是大酒店小饭馆,野菜蘸大酱又成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有所不同的是,过去吃野菜蘸大酱是为了充饥,为了活命,而现在却是为了调换口味,清理肠胃。虽说野菜蘸大酱的味道有苦有涩,但苦有苦的道理,涩有涩的内涵,除了健康的意义,还能找到回归自然的意境。
对于历史有所记忆的人,在吃野菜蘸大酱的同时,依然能找到一种久违的感觉。而对于80后、90后的青年人,即使知道大酒店里一盘野菜蘸大酱的价格,可能还不理解野菜蘸大酱对于他们父辈生命的意义。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只有吃野菜蘸大酱才能活命的年代,跟他们说这些,还以为在编故事。
责任编辑 江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