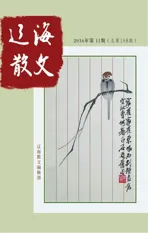蒲公英赞
——我印象中的彭定安先生
2016-02-23张兴德
张兴德
蒲公英赞
——我印象中的彭定安先生
张兴德

张兴德
现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散文学会会员。先后在《红旗》《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辽宁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解放军报》《红楼梦学刊》《红楼梦辑刊》《鸭绿江》等40余家报刊发表五六百篇学术、理论文章和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有红学专著 《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被《红楼梦大词典》收录和被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收藏。新著有 《红学热点话题"透视"》《对社会发展史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等。
回忆是人生思维的一种常态,是多味的:有时是甜蜜的,有时又是苦涩的;有时是感悟,有时又是感谢。我常常回忆起蒲公英,就有这多种感觉。
当年我们家住在北大荒的平原上。我家的门前有一片草地,每到春季,随着绿茵铺上大地,那点缀绿茵的是一片随风摇曳的小小黄花。这就是蒲公英。在草地上用小铲挖蒲公英的茎叶并采摘蒲公英花是我童年的生活和快乐。把蒲公英花采回插在装满水的小瓶里,阴暗的小土屋里格外增加了一份生气;再把挖回的蒲公英茎叶择洗干净,同大酱一起,就是我们农民饭桌上的菜。
后来随父母迁到城市,再后又入伍参军。难得在城市和军营的土地边缘上见到蒲公英。每次,总是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亲切回忆:蒲公英,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有奉献而无索取!
近年,在我居住的小区里的草坪中也常常见到蒲公英。这不仅引起我对童年的回忆,还让我想到一位以“荒原上的一株蒲公英”自喻的老学者——彭定安老人。
去年7月,江洋来大连办事,我们几个老战友借机小聚。他对我讲起前不久去看望彭定安老人,他和彭老无意间提起了我。彭老说:“张兴德这个人我记得,我当年在《辽宁日报》时他经常给我们投稿,诗写得好,现在他在研究《红楼梦》。”江洋转述的这几句,再一次唤起了我对彭老的亲切记忆。前些日子,我整理陈年旧稿,在我留下的一些早年的来往书信中,有一封《辽宁日报》“文艺部”给我的来信引起我的特别注意。这封信的落款是“文艺部”,并盖有公章。但看其字迹似曾相识——这不是彭老的字迹吗?我拿出彭老最近给我来的一封信一比对,果然是彭老的手迹!我好高兴,50多年了!我看后面落款的日期,没有年,只有月、日。我努力地回忆一下,应该是1964年吧?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在过了半个世纪的今天,仍感到十分亲切:“希望你在连队更好地锻炼、更快地进步!”这封信,把我的思绪再一次拉回到50多年前,想起彭老当年在《辽宁日报》文艺部工作时,我们几次亲切的谈话。
我从1963年开始在《辽宁日报》上发表诗歌。一年多的时间,我先后发表了三四次。在发表的那些诗歌中,有的修改很大,有的仅仅改动一两个字。我每次比对原稿发现,不仅改动大的同原稿比水平悬殊,就是改动一两个字的,也使原诗生色不少,这使我明白了诗坛为什么有“一字师”的佳话。我既感谢编辑的认真,更佩服编辑的水平。可是近两年了还不知编辑是谁。我特想认识给我编稿的编辑同志,还因为我给别的报刊投稿的退稿信均是打印的,只有《辽宁日报》给我的退(约)稿信多是手写的,像前面那样来信中的鼓励的话,在其他报刊的退稿信中是根本见不到的。一直到了1964年的下半年,借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我带了几篇新作,去见我从未谋面的编辑。当我带着崇敬、神秘、好奇而又忐忑的心情敲开文艺部的门时,出来的是一个穿着蓝制服的中年人,他一见我就和蔼地问,你找谁?我见他衣着朴素,怎么也同我想象的省报的大编辑联系不起来,也不知为何,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倒像个农民 (后来我知道彭老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才生,我一直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有那么个“第一印象”,今天想来是否和当时他的处境心理有关?),就说:我是驻丹东的部队来的,我想见编诗歌的编辑同志。他看我穿着战士军装,就说:“那你应该是张兴德吧。我就是诗歌编辑。”我一听有点手足无措又很惊讶,习惯性地立马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不等我再往下说,他就把我引进另一个无人的房间。坐下之后对我说,我们通信好久了,只是没见面,我们也没有机会去丹东,你今天能来大概也不容易,带来了什么新作,让我看看……几句话,倒像一个大哥哥对弟弟说的,使我精神放松了不少。他看完了我带去的几首诗歌,留下了两首,其他几首退给我,又问了我一些情况。我来的时候就怀着一个诗歌爱好者的常有心理,想让这些专家们评估一下自己的诗歌究竟有没有“发展”前途,于是就问:“我写的这些诗你都看了,总体上看究竟怎么样,怎样还能提高 ?”这本来是一个难以一下子回答的问题,他听了停了一会说:“写诗没有诀窍。我看你的诗有战士的特点。以后多写,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写诗第一要有思想。另外,有时间多读一些优秀诗歌和诗歌评论、诗歌理论之类的文章,提高鉴赏能力。”当时我听了他的话既受鼓舞又有不满足感,因为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诗有没有“发展前途”这个我十分关切的问题。后来我在实践中慢慢地理解了他这一席话是至理之言。现在回过头看,他给我讲的这“四条”很经典。其中第二条的“读毛著”那是当年特有的要求和语言,应该同“提高思想,写诗第一是要有思想”联系起来理解。这对写诗来说,则是完全的必须。现在一些新诗的思想境界不高,思想性不强,其源即在于此。
以后我又到沈阳去了几次,每次总要看看他。记得1965年夏天,当时正在批判一篇小说。我写了长长的一篇批判文章。他一见是厚厚的稿子,瞄了一下题目,带有几分惊讶地说:“怎么,你不写诗了?”我答:也写诗,我现在也感兴趣写理论文章。“好啊,理论文章可以锻炼思维,提高思想。”他接过稿件,看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看过一遍之后,又翻过来 对看过的有关部分又看了一下。很显然,他的这个动作标志他看得很认真很仔细。完了对我说,理论文章,贵在有说服力。你作为一个战士,应该抓住一个具体的观点,以你们战士的切身体会,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才能有说服力。像你的这篇文章,几个题目都很大,说的道理有些空泛。这样的大文章,应该是专门研究人员,对整部作品做充分的研究之后,才能写好。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你要想写理论或言论文章,可以先从写短文开始。短文也很重要。鲁迅的许多短文,影响不是也很大吗?写好短文,再写长文就有基础了。
这些谈话,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当年第一个接触的 “大编辑”,还因为他同我前不久遇到的另一报社的编辑比,态度是那样和蔼可亲,毫无居高临下之感,谈话又是那样质朴实在,如溪流潺潺,入心入肺。这对于苦于无人指导的初学写作的我来说,无疑是启蒙性的作用。
我以后在部队提干,不久就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农村去了。接着“文革”开始,我的工作也极忙,已无暇写诗,也无缘去沈阳。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我到沈阳去修改我们所属部队121野战医院参加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表彰大会的发言材料,在大会上遇到了《辽宁日报》政法部的记者,问起彭老,他们告诉我,他下放到辽西的什么地方,具体他也不清楚。直到1980年春,我到沈阳开报道会,去看诗人阿红,听他说,彭老回到沈阳后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我转了几次车才找到省社会科学院,找到彭老。我见他脸上虽然已经留下了沧桑岁月的痕迹,脸色黑里透红,但精神还挺好。十多年未见,他一见是我就认出来了,好高兴,并连连说:“你能记得我,还来看我,好、好!这表现出你是一个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这“无产阶级感情”现在有人听起来不大舒服,可当时是流行语言啊!)我对他讲,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怎么能忘呢?你对我的指导,你可能不记得了,但我却是终生难忘的。我对他汇报了我近年在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就是从写短文开始的,还特意告诉他我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短文。他听了挺高兴。那次谈话一个多小时,双方都十分愉快。
这以后,虽然再无机会见面,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退休之后,我“误入红楼”,2007年出版红学专著《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一书。我首先想到彭老。书出版的第一时间就给他寄去一本。不久,就收到他的亲笔回信,对我鼓励一番,其中一句话说,看了其中几篇,这不像是一个业余作者写的。随信将他的两部新著赠给我。今年我的第二部红学著作《红学热点话题透视》出版,他收到我的书不久又亲笔回信,其中说,你对“秦可卿”的分析见解独到,有新意,文章的逻辑性也强,有说服力。
我对彭老真正了解是断断续续通过多种途径,包括从他的几部学术著作中得知的:
他的著述颇丰。在多个学术领域均有创建和贡献。读他的这些论著书稿,如同聆听一位哲人的谈话,或令人感悟或令人深思;又如听一位激情的诗人在述说,或令人同情或令人喜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是他的文章的现实针对性,不是学院式的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注意回答人们的社会关切。这在当前学术界无疑如一缕清风。正如范敬宜送给他的两句诗说的:“落笔行行都带血,剖心寸寸应无埃。”
文如其人。他的人品和学品更令人钦敬。在“文革”中,他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被全家“下放”到辽宁西部的边远地区去。就是在这种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像“一株蒲公英”那样顽强地生存,不改初衷。“在颠簸的敞篷汽车上、风雨道路途中,用心默读、冥想,到驻地时,在农村的昏暗的电灯甚至油灯下”,写出了《鲁迅诗选释》等书、文,这犹似当时的文化荒原的蒲公英,迎接早春的信息。而他自己,就以“荒原上的一株蒲公英”自喻:
“在我的眼前和心里,常常会有一株蒲公英的形象在摇曳,每当它出现时,总有一种心绪萌动,时而轻松、时而宽慰、时而激越、时而凄楚、时而悲怆……
“一望无际的荒原,辽阔而苍凉,风吹过,衰草凄迷;草丛中有一株蒲公英,柔弱却挺拔,开着黄色的花,在扫过原野的风里抖擞。”
这是彭老笔下的蒲公英,看似柔弱,却是坚强的。她从不同狂风斗,是生存之道;凡有泥土的地方就有她的身影,从不向命运屈服!彭老是一株坚强的蒲公英!
我不能忘却童年的蒲公英,更不会忘记“荒原上的一株蒲公英”!他们同样在我的生命的旅途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责任编辑 王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