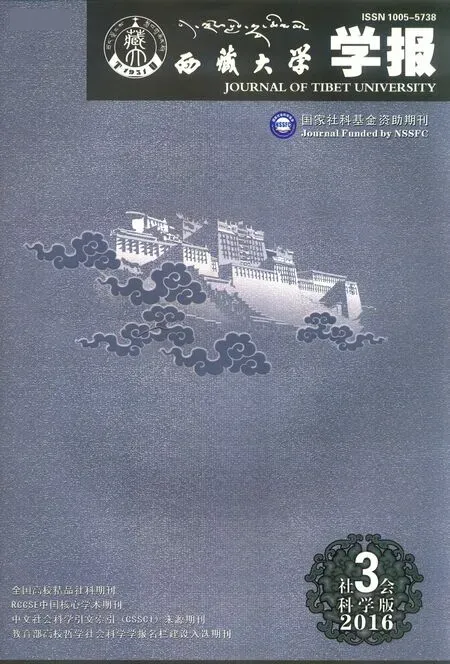大众文化视野下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构建——以涉藏影视艺术作品为例
2016-02-19王传领
王传领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济南 250100)
大众文化视野下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构建——以涉藏影视艺术作品为例
王传领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济南 250100)
在如今大众文化占据主流的文化市场,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小众文化类型,只有和大众文化充分融合,才有可能突破自身的局限,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和传播空间。西藏传统文化亦不例外。事实上,随着政策的倾向和资本的涌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形态已经进入到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并由其独具的世俗性、娱乐性、现代性、商业性、标准化和时效性而广受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而影视艺术作为受众最易接受、传播范围最广的大众文化形式,自然也就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首选载体。将西藏传统文化与影视艺术相结合,充分运用大众文化的传播理念,是如今传播西藏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大众文化;西藏;传统文化;传播路径;影视作品
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已成为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焦点,这既得益于由大众文化在近几十年的迅猛发展所产生的诸多标志性文化景观,还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大众文化对文化传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使得部分民族文化可以在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得以更大范围和更快速度的传播;另一方面,生产大众文化的文化工业也使得没有较好融入其中的民族文化有可能被淘汰,而这也正是大众文化始终无法摆脱毁大于誉的重要原因。“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事实上,它们根本不是企业,而转变成了连它有意制造出来的废品,也被认可的意识形态。”[1]尽管大众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化商品,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始终带着浓重的精英主义式的悲观论调,但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约翰·费斯克的积极观点入手重新审视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认为“大众性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必然焦点和追求。作为一种政治追求,它是反精英的”[2],并尝试将大众文化的理念与本民族文化进行结合,以此来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这种文化传播观念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共存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中华文化向来讲求“和而不同”,在汉民族文化周围,我国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各自创造了具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并与汉文化互相补充,共同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就是这样的典型少数民族文化。尽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文化糟粕,但只要不断地去除这些消极因素并彰显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就能够在现代化国家的文化中拥有一席之地。
西藏素来以其独特的地理属性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无论是游人还是学者,都对这块充满着诸多未知神秘的净土怀有最虔诚的敬意与想象,而这里孕育出的西藏传统文化更是在文化地理学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宗教景观有举世瞩目的寺院、宫殿、佛塔和碑铭石刻;传统文化则有独具特色的语言、医学和文学等。除此之外,西藏的风俗习惯、体育运动和歌舞等也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因此,对于西藏传统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然而,成就了西藏神秘性的交通不便和相对恶劣的自然气候同样也正是西藏传统文化难以为人所了解的重要原因。尽管近年来交通的便利使得这一天然短板有所缓解,但是相较于蒙、回、苗这三大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来说,认识和研究西藏仍然困难重重。因此,对于西藏传统文化传播路径的研究也就更有价值,更能为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典型的借鉴意义。在如今大众文化占据主流的文化市场,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小众文化类型,只有和大众文化充分融合,才有可能突破自身局限,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和传播空间,西藏传统文化亦不例外。事实上,随着政策的倾向和资本的涌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形态已经进入到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并由其独具的世俗性、娱乐性、现代性、商业性、标准化和时效性而广受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而影视艺术作为受众最易接受、传播范围最广的大众文化形式,自然也就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首选载体,这一类型的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等层出不穷,且纷纷赢得了口碑。因此,将西藏传统文化与影视艺术相结合,充分运用大众文化的传播理念,可以说是如今传播西藏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能够将大众文化的传播理念与以藏族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较好结合,则不仅可以促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播和继承,更能增强中华文化整体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本文将以涉藏影视艺术作品为文本,着重分析西藏传统文化的崇高性和隐秘性应如何契合大众文化的传播理念来构建自己独特的传播路径,以期能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藏传统文化的崇高传播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和娱乐性
众所周知,藏传佛教是西藏地区的主流宗教,其悠久的历史使得它不仅在西藏民众心中具有极其深厚的根基,产生了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和萨迦派等五大支派,还由此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化景观,如藏传佛教的寺庙、佛塔和法器等,并演化出了不同的教义理论和管理组织。这些文化形态在西藏的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由于宗教文化与生俱来的崇高性、神圣性以及教育发展的相对迟滞,真正理解藏传佛教的宗教内涵和这些文化景观意义的只有少数宗教领袖和僧人,大部分普通信众连本宗教的核心理念都不一定完全理解,更不要说普通的群众了。与此类似的还有被称为“伟大的英雄史诗,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是古代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知识的宝库”[3]的《格萨尔王传》。这部千百年来由藏族民众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不仅宣扬了正义战胜邪恶的正能量,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围绕它形成了著名的“格萨尔学”。然而,这部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的辉煌巨著“有120部、100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就篇幅来讲,比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古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史诗的总和还要长,堪称世界史诗之冠”[4],这已远远超出普通人所能承受的阅读极限。但是,传统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在西藏这样相对闭塞的地区,如此辉煌的文化成就能够发生并传承下来则更显不易。
2008年,五集纪录片《西藏一年》在英国广播公司首播。江孜县白居寺的次成喇嘛是其中的主角之一,纪录片围绕他接待十一世班禅视察白居寺和组织萨嘎达瓦的活动等事件,将白居寺、坛城沙画和唐卡等宗教文化景观纳入其中,同时也将西藏民众对于宗教的虔诚完全呈现。1987年,《格萨尔王传》首次被拍摄成18集电视连续剧,这部古老的皇皇巨著终于以全新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2009年,“投资5000万人民币的4D巨幕立体动画电影《格萨尔王》开机投拍”[5]。这些相当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无疑都是以西藏传统文化为题材和切入点。由于大众文化“多以日常生活行为和感觉、感触为主要内容,因此特别追求诉诸感官的娱乐效果”[6],所以其作品就可以运用包括娱乐、特技等在内的一系列感官刺激手段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从而达到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除了娱乐性之外,西藏传统文化中的神圣性也开始向大众文化世俗性倾斜。如在《西藏一年》中,镜头将次成喇嘛迎接十一世班禅和组织萨嘎达瓦活动的细节一一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宗教文化只可远观的崇高性,拉近了普通受众与神圣宗教的距离。由此,受众自然也就能够通过这部纪录片对藏传佛教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且不再仅是将宗教作为信仰的符号和图腾,更多了一些难得的亲切感。正如马丁·杰伊所言,“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致力于调和广大观众和现存秩序。”[7]纵然这些文化工业体系下的大众文化产品缺少了本雅明所谓的“灵韵”——“一定距离外的独一无二显现”[8],但是借助于这些大众传播手段,传统的西藏文化的传播范围被急剧扩大,它不再只是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的地区文化,而是逐渐融入大众文化之中,被越来越多的受众所认知和接受。由此可见,西藏传统文化中的崇高传播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和娱乐性并非完全对立,恰当地使用大众文化中的世俗性和娱乐性理念来创造内含西藏传统文化的文化产品,其实是一种较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扩大西藏传统文化自身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二、西藏传统文化的隐秘传播与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和商业性
西藏传统文化之所以充满了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除了西藏地区远离中原文化圈且交通闭塞所造成的遗世独立的地理情状之外,其文化本身所常用的隐秘传播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在西藏上千年的农奴制中,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奴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他们的文化和信息来源主要依靠的是口口相传。以《格萨尔王传》为例,仅仅是这样一部主流的文化瑰宝,其说唱艺人就可以分为神授艺人、掘藏艺人、闻知艺人、圆光艺人、吟诵艺人等五类。其中,神授艺人号称“所谓梦授无师自通”[9],而圆光艺人则指“利用可以反光的物体例如铜镜、一碗水、一张白纸甚至是指甲盖来看到格萨尔王征战的场面,并复述画面的这一类文盲艺人。”[10]这两类艺人在传播《格萨尔王传》时所自带的神奇色彩使得这部文学经典不断被赋予更多的神秘性,加之《格萨尔王传》本身就属神话题材,这种特殊的神秘性也会被再次放大,从而形成了围绕这部作品的隐秘传播。除此之外,西藏地区风俗习惯的独特性也加剧了这种隐秘传播的形成。这些风俗习惯形成于藏族民众所创造的古老文化之中,虽然其中很多很难为现代社会所接受,但却是西藏传统文化特殊性的本色之一。例如在西藏包括江孜等在内的一些地区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一妻多夫制,这种婚姻制度在西藏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既可以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还可以使得家庭财产得以最大化的集聚,充分体现了藏族民众独特的生存智慧。然而在现代文明体制中,一夫一妻制已经在绝大多数国家得以实行,一妻多夫制显然已经超出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接受范畴且不为大众所知。与此类似的西藏传统文化还有天葬这种古老的丧葬习俗。尽管现代文明已经在各个方面影响了藏区民众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但是在相当大的范围之内,这些已经在西藏地区神秘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罕为人知的传统文化仍然被保留下来。
毫无疑问,在西藏特殊地理条件下孕育的这些传统文化都带有隐秘传播的性质,它们或许不符合大众文化的现代文明理念,但却都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现代社会的眼光去评价和批判都是有违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产生于工业社会商业背景下的大众文化在资本的驱使下,其灵敏的嗅觉对于发现这些隐秘文化却极为擅长。实际上,由大众媒介所掌控的大众文化本质上属于消费文化,它是在“生产—消费”的工业社会逻辑之上衍生而来。在这种文化中,“媒体通过制造无穷无尽的、稍纵即逝的影像与时尚,来赋予影像以全新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品位,全面激发大众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消费欲望,并鼓励大众用充满文化意义的影像与时尚来显示自己的个性。”[11]由此,大众文化所要寻找的正是那些能够激发起观众消费欲望的传播材料,而西藏传统文化中的这些隐秘部分,恰恰满足了大众文化的需求,也迎合了大众对于特殊文化的猎奇心理。这就为西藏传统文化进行大众传播营造了绝好的契机:一方面,大众媒介想要寻找不为人所知的文化来创造消费热点;另一方面,西藏也亟需这样的大众媒介来传播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提升自身形象并让观众对西藏有着更加客观的认知。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属性使得“大众生活在由符号和影像主宰的仿真时代,超现实代替了真正的真实而成为真实所在。”[12]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由于大众文化的传播广度,才使得受众可以接受到与以往相比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体量,也使得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有了被广为了解的可能。所以,运用大众文化的传播手段对西藏传统文化中的隐秘传播部分加以适当改造,对于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播无疑将会大有裨益。当然,这种改造的主要目的是要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和文化消费的需求,而并非是要从本质上颠覆西藏传统文化的属性。从这一角度上来说,电视剧《尘埃落定》和纪录片《西藏一年》都是相当成功的案例。
三、西藏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时效性
尽管研究西藏文化的“西藏学”自19世纪上半叶被开创以来一直备受关注,近几十年来其作为一门“显学”更是尤为活跃,但却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并未真正亲临西藏,感受青藏高原的风土人情。即使是中国民众,绝大部分人也惧于旅途的劳顿和高海拔的气候而没有机会来到这片净土,更不用说相隔甚远的外国人士了,“连藏学奠基人、19世纪上半叶法国学者德克勒希、福克斯等人都没有到过西藏,也没来过中国。”[13]所以,更多人对于西藏传统文化的认知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的。从这一点来说,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大众文化产品,如电视剧、电影等,不仅肩负着国内传播的重任,还要作为主要窗口,客观正确地向国外受众传播西藏传统文化。而后者除了文化和商业上的考量之外,其政治上的作用或许更加重要。事实上,国外大众媒介对于西藏形象和文化的扭曲传播早已屡见不鲜。在好莱坞巨作《2012》中,高海拔的西藏成为人类最后唯一的据点。但影片在对西藏进行描写时,其中的藏语、文字、寺庙和生活习惯等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好莱坞成熟的电影工业尚且如此,更无论其他对西藏不甚专业的解读了。“在国际化传播语境中,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突出媒体社会责任,对真实负责,对观众负责,应该是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共同遵守的准则。”[14]因此,对于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播要纳入到大众媒介的标准化之中,同时注重传播的时效性,确保国外受众对于西藏传统文化能够获得正确认知,并由此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西藏新形象。
首先,西藏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应该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标准化之上。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问题的复杂性,西藏历来被反华势力视为极佳的战略平台。这些势力并非单纯的外国敌对分子,还包括了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甚至是西藏前宗教领袖等。所以,在大众媒介日渐发达的今天,对于西藏传统文化和涉藏问题的解读就尤为重要。也正是由于西藏文化对外传播的标准化程度较低,才给了利用西藏来谋求政治利益的敌对势力以较大的解读空间,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淆视听。而西藏传统文化传播的这种标准化需求却正契合了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属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来源于两个方面:在文化工业进行大规模复制和生产时,不可避免地要将大众文化进行标准化处理以降低成本;在大众文化进行消费时,要尽量符合拥有各种需求的大多数受众的需要以使其利润最大化。西藏传统文化所要运用的大众文化的标准化理念与之既一脉相承,又稍有不同。其更多的是对这些文化进行相对标准化的加工与解读时,再叠加一层符合国家利益的标准化的意识形态因素,从而尽量压缩国外势力误导受众的空间,为树立西藏的良好形象奠定基础。而这种相对双层标准化的正确解读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对大众媒介标准化的正确运用。福柯曾经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15]纪录片《西藏一年》在英国广播公司首先播出,然后才由中央电视台向国内观众呈现。这部纪录片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就在于它获得了包括国外观众、中国非藏族观众和作为影片主角的藏族民众三方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恰恰是影片本身通过大众媒介相对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表现方式来获得的。其次,西藏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还应该建立在时效性的基础之上。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速度成为信息传播最大的竞争点,速度快者往往能够占据信息解读的主动权。如在拉萨“3.14”事件中,我国主流媒体速度上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在事件解读上的失语,从而没有在国外势力传播谣言时给予有力的反击。这一政治事件中关于时效性的教训同样适用于西藏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近年来,全面展现西藏风貌的纪录片层出不穷,如《天河》《雪线军魂》和《西藏跨越六十年》等;以西藏为地理背景的电视剧亦是相继推出,如《一路格桑花》《雪域雄鹰》等。这些影视作品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展现了西藏深厚博大的传统文化、美丽诱人的自然风光以及西藏民众的善良淳朴,同时加上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助力,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对于西藏的了解欲望,也让西藏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初现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要运用大众文化的视野和理念来构建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时,我们仍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大众文化的传播理念派生自文化工业体系之下,它的世俗性、娱乐性、现代性、商业性、标准化和时效性等本质属性必然会使它的文化产品呈现出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消极性特征,如过度功利化、娱乐化和同质化现象严重、过度排挤弱势文化等。这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称其为“异化”的原因所在。他们曾经不无忧虑地认为,“大众性不再与艺术作品的具体内容或真实性有什么联系。在民主的国家,最终的决定不再取决于受过教育的人,而取决于消遣工业。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16]尽管如此,大众文化仍然以狂飙突进的速度席卷了整个世界,它对于人类追求娱乐消遣的原始欲望的准确把握使其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有效的抵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众文化与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其实具备相当多的交融点,只要少数民族文化能够运用大众文化的传播理念来进行适当的改造,努力规避大众文本的上述弊端,相信其就能很快融入当今文化市场并取得不错的传播效果。
笔者所说的影视艺术只是众多传播路径中的一条,只要能在保证少数民族文化纯粹性的基础上对其传播做出有益的贡献,其他的路径也都可以为之所用。如王潮歌导演的“印象系列”实景演出,就是一条非常成功的可行之路。她导演的《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雪山篇)和《印象·海南岛》等文化产品分别展现了壮族、纳西族和彝族以及黎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与风情,创造了口碑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些文化产品以山水实景为舞台,同时融入灯光、音响、音乐和舞蹈,既展现了当地少数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因其绚丽多彩的表演而吸引了大批游客亲临观看,甚至成为了当地最成功的文化名片。由此可见,在现代媒介技术的配合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路径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宽,只要创意合理且运用得当,西藏传统文化必将以全面的方式展现在全世界受众面前。
[1](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13.
[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4.
[3][4]其美多吉.“格萨尔王传”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访著名藏族学者降边嘉措先生(之一)[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5][9][10]索南措.《格萨尔王传》传播媒介对藏民族崇拜心理的影响[J].青海社会科学,2012(5).
[6]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7](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242
[8](德)本雅明.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本雅明.经验与贫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65.
[11](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67.
[12]于文秀.第三种大众文化理论——波德里亚大众文化批判理论[M].文艺研究,2010(12).
[13]高有祥.西藏对外传播的艰巨性和有效性[J].现代传播,2011(8).
[14]郑世明.论涉藏纪录片真实性把握的六个平衡[J].现代传播,2010(3).
[15](美)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灌耕,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35.
[16](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艺术和大众文化[M].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75.
Constructing Propagation Paths for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in the View of Mass Culture -Taking Tibet-related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s an example
WANG Chuan-ling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ture Theory&Aesthetic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100)
The dominance of mass culture in the mainstream cultural market has rendered the cultures of minority groups subcultures,which must rely on adequate fusion with mass culture to gain greater room for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despite their limitations.This is also the case for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With the policy orientation and the influx of capital,various forms of mass culture have in fact been increasingly introduced to the minority regions including Tibet,and have,attributing to their secular,recreational,commercial,standardized and updated nature,been well accepted by the minority groups.Among them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have been the preferred media for minority culture as they allow the best acceptance and the widest spread.I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to spread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to incorporate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in video ar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ncepts of ma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mass culture;Tibet;traditional culture;propagation paths;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10.16249/j.cnki.1005-5738.2016.03.014
J952/J905
A
1005-5738(2016)03-095-006
2016-05-18
王传领,男,汉族,山东聊城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艺术传播。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