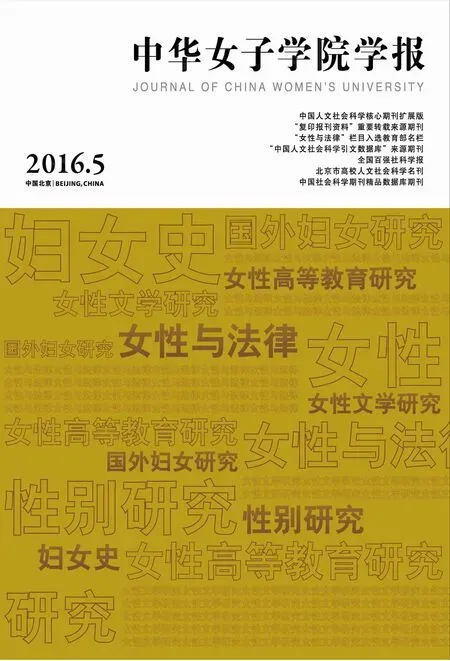从权力结构到行动策略
——国外孕产行为研究述评
2016-02-15邱济芳
邱济芳
从权力结构到行动策略
——国外孕产行为研究述评
邱济芳
国外孕产行为研究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为背景,关注的是社会生物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同时重视分析女性的主体性、行动性。其研究成果可以从权力结构、社会互动和个人能动性三个层面进行述评。研究发现,现有国外孕产行为研究较为成熟,理论经验成果丰富,注重行为内部结构性和复杂性的研究。但是其研究的社会情境和具体内容与我国显然不同,我国尚少有此主题的研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女性孕产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国外孕产行为的研究述评既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思路借鉴,也让我们反思中国社会情境下孕产行为研究的最新范式。
怀孕;生产;权力;行动
一、导言:怀孕生产的生物社会过程
怀孕和生产是人类生殖繁衍的基本活动,既包括妊娠分娩等生物过程,也涵盖了医疗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19世纪下半叶,女性权力意识觉醒,国外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理论对本质主义的反思将女性的生育行为纳入批判范畴当中,生殖繁衍等一系列活动的自然性和绝对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剖腹产以其加速产程和保障母婴生命安全等优势,和现代医院体制一起将女性生育纳入医疗系统当中。为了提前检测婴幼儿质量,降低女性在怀孕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危险,孕妇需要在生产前完成一系列医疗项目检查——产前检查。由此,怀孕和生产已经不再简单是一个从妊娠到分娩的生物过程,其中还包括孕妇本身和医疗体制、家庭、国家的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不仅发生生理上的变化,还受到医疗、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而在当前西方生物医学盛行的时代,伴随着国家制度、医疗科技和市场力量的发展,女性的怀孕和生产等一系列生殖活动也蕴含了多层次的全球化和地方化权力关系,并形成一种金斯伯格和拉普所称的“生殖的政治”(Politics of Reproduction)。[1]
国外的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怀孕到生产的这一生物社会过程,发展了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得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综合国外研究的问题和视角,从梳理已有研究结论出发,介绍国外前沿理论经验成果,从而为国内怀孕和生产等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二、多元权力结构中的怀孕和生产
国外怀孕和生产的研究起步于19世纪晚期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这一时期的诸多研究主要分析女性怀孕和生产行为中权力以及这一过程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学界对孕产行为的关注和讨论已经突破医学的范畴,扩展至社会科学的领域。社会学、人类学等均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分析怀孕和生产过程中所蕴含的权力结构关系。
(一)孕产:从“自然”到“文化”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On Ne nait pas Femme,on le Devient)”。在《第二性》中,波伏娃以女性的整个生物社会过程结合在一起,阐述了女性在何种情境之下被社会“塑造”成女人的过程。[2]早期研究者注重孕产行为的生物性别特征和父权制下的女性压迫。她们大多批判女性的身体机能——生育行为本身观点,认为怀孕和生产过程意味着女性是父权制的生育机器。[3]54
“自然”(Nature)还是“文化”(Culture)在诸多研究领域中都是一个核心讨论问题,在孕产行为的研究中亦是如此。女权主义者争论怀孕和生产行为中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文化建构的?对此,女权主义内部讨论中出现了差异。Beckett和Inhorn对生殖行为的女权主义历史进行梳理后发现: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中认为,剖腹产是一种女性可以选择的、控制自己生育的工具;而随后以母乳协会为代表的回归母乳喂养和自然生产一派认为,女性应该返回自然生产,同时进行母乳喂养;第三波女权主义则认为,回归居家生产并不是给女性赋权,而应该对回归的“自然”状态是什么,女性在其中是否获得权力进行反思。所以她们认为,女性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将产检和剖腹产作为一种赋权的手段。[4][5]
在父权制批判视角下,研究者借鉴了多种不同理论分析女性孕产行为,并运用交叉视角批判女性怀孕和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干预。一方面,她们讨论女性使用何种生产方式和产前检查对怀孕生产具有“控制”权力;另一方面,则关注女性如何“选择”怀孕和生产过程中的医疗技术。对于这种父权制批判下的权力关系,之后的研究加入了情境化和后结构主义的观点,选择和控制的绝对性被弱化。例如,纳美和莱尔莉提出在关于女性受到控制这一点上,女性主体对“控制”的具体含义被忽略,应该首先考虑女性对控制的具体定义,然后再研究是否具有对孕产妇行为进行控制这一问题。[6]
(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子宫=生育机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研究女性怀孕和生产的主要视角之一。马丁将女性的生产行为和工业化生产进行类比,认为女性的孕产行为已经标准化、流程化,并且都是在医院内部的特定规则下完成的。[2]59这一比喻将医疗体制视为一种以效率和速度为“生产”目标的集中权力系统,孕妇在生产效率化和流程化之下则成为一个在医院监督下的“商品生产机器”。[2]这一理论分析视角在当前医学化研究中也有广泛影响。女性使用孕产科技是受到了医疗科技控制,从而给社会再生产提供人口基础。她们一方面进行人口繁衍,另一方面则进行社会劳动力再生产。[7]这一理论视角对女性的生殖行为进行了“生产—商品”视角下的批判。
其他研究者在这一视角下深入阐释,提出女性的孕产行为并不只是政治经济学下的“生产”逻辑,还包括文化背景和其他社会背景因素。当前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文化也对孕产行为造成了特定影响,如泰勒就使用了这一理论视角分析超声波的社会效用。她认为,现在的超声波检查科技实际上将胎儿视为一种商品,一方面赋予其生命,尝试借此降低女性的堕胎率;另一方面也通过与胎儿联系的感情渲染将其商品化,让孕妇消费胎儿四维彩超的照片等。[8]
(三)生命政治视角:国家控制的另一种解读
生产行为关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等国家宏观指标,因此,孕产行为也是国家控制的对象。福柯的生命政治观认为,近代社会以来,国家的管理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国家管理在宏观层面上控制着人口数量,在微观上则控制着女性和男性的身体。[9]这一理论给怀孕和生产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权力分析的视角。以美国财政支出为例,其在住院分娩、产前检查上的医疗支出几乎占到一半以上,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对于国家和个人的重要程度。[10]
在国家治理当中,医院、学校和法律逐渐成为权力扩散的领域。医院机构、国家和社会的健康标准密切相关,它们需要在治理过程中参与控制,“再生产”出符合社会健康标准的世界公民。[11]10-13同时,这一系列的医疗实践还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化为人们的身体实践。医疗监控(MedicalSurveillance)即医生通过医疗手段监督特定行为,同时可以对所有与此行为相关的内容合法化地干涉。[12]215[13]333这使得医生能够从微观上控制女性的孕产行为。女性在孕产行为中接触到一系列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孕产妇所接触的生殖技术产生于医疗体制以及具有社会进步和人类目标认可度的科学文化,而在这种权力关系当中,女性选择顺从还是抵抗,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14]
(四)孕产行为权力机制的揭露:医学化
最早将医学和社会控制联系在一起的是帕森斯。他在其1951年的著作《社会系统》中提出了“病人角色”(Sick Role)的概念,而医学的社会功能则是对这种病人(越轨行为)进行矫正。[15]430医学化(Medicalization)主要是指生活中原本不属于医疗的部分逐渐被医疗知识所解释并成为医学问题,加入到医疗制度安排之下的过程。[16]孕产行为的医学化也是这一社会进程中的一部分,女性怀孕行为从以前的在家生产,变为如今的住院生产;孕妇要经历定期的流程化产前检查来监督胎儿质量,逐渐构成了现代社会医学化的孕产行为。巴克通过分析美国社会中的“产前保健”政策及其变迁,得出美国社会中的生物医疗修辞如何促成了一种产前行为医学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机制。正是这种宏观国家权力的推进,使得医学化拓展到产前检查领域。[17]
与此问题相关,剖腹产在现代医院体制中广泛流行也离不开医学化的作用。然而,研究结果证明,医学化并不是医生一手造成的,而是和其背后所处的医疗体制和相关利益群体,甚至病人本身有关。[16]例如,麦考拉姆通过研究巴西萨尔瓦多的剖宫产居高不下的原因时发现,女性的文化倾向和产科医生的个人利益都会影响到女性剖腹产的选择。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一个单一因素使剖腹产率升高,也不存在特定群体使用剖腹产更多。因此,他提出应该分析影响剖腹产选择的多种因素。[18]
以上几种权力结构关系的讨论互相借鉴影响,同时推进了彼此的发展。这些权力分析给孕产行为研究提供了特定理论视角,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分析女性的权力结构和实际行动。后结构主义者搁置“自然还是文化”的争议,集中关注女性实践。孕产行为中的医疗科技并不一定都是父权制的控制手段。[3]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权力的意义也存在差异。扎尼克通过宗教实践来分析女性使用医疗科技的行为时发现,天主教的女性在宗教信仰下认为疼痛和自然分娩是正常且有意义的,从而以宗教信仰中的解释来抵制医疗科技的使用。[19]由此,各种权力关系的分析交织在怀孕和生产研究当中,衍生出社会互动和个体能动视角下的多样化研究主题。
三、社会互动中的怀孕和生产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胎儿质量和母婴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强。优生学和产前检查的发展使得女性在怀孕过程中需要定期进行母婴健康监测。在面临多种检查的情况下,孕产妇选择过程中的社会互动对其怀孕生产作用明显。研究者主要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讨论女性孕产行为中的社会支持、社会网络等问题,并分析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女性孕产行为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医生、家人成为主要的分析讨论对象,但是对于一系列关系的具体作用方式,学界依然存在争议。
第一,医生和女性孕产行为关系的研究有多元的结论。女权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国家父权制的代言人;医学化视角则认为,医生这一专业群体推进了整个医学化进程。医生对女性的孕产行为影响较大,他们对女性认知和理解产前检查有重要作用。[20]同时,他们还会创造某种女性怀孕的病人角色,以使其在行为规范上服从医院的规定。[21]马肯斯则系统研究了家人、医生对女性产前检查服务选择的影响。她分析了产前检查咨询师的态度,发现他们并不是都支持医疗体制,而是具有多元化的观点和行动方式。[22]洛伦兹通过审视孕妇的医患互动关系发现,女性的孕产经验能够反映医疗权力的作用过程及其抵抗方式。女性是医疗权力关系的参与者,医疗体制中孕产行为的医学化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女性和医疗体制“互构”的过程。女性通过寻求医疗服务,从而为孕产行为的医学化提供条件,同时也达到保证自身健康的目的,因此两者是互相建构的。[23]对此,研究者的结论并未达成一致。玛拉科利达等人通过研究证明,女性在使用医疗保健过程中并没有促成这种医学化的过程。[24]
第二,女性的家人对怀孕生产过程产生影响,尤其是丈夫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丈夫是父权制的代言人还是女性行动的支持者?桑塔拉提认为,女性在产前检查中看似是自行抉择,实际上是流程化下的被动选择,丈夫在其中的角色是多元化的。[25]马肯斯则强调,男性伴侣在女性孕产决策中影响明显,他们通常并不一定是父权制的同谋,而是既希望保证家庭责任,也支持女性控制权力的主体。[26]由此可见,丈夫在孕产行为中的作用需要考虑不同社会中的差异性文化环境。除了丈夫以外,也有学者研究孕妇母亲和朋辈群体的影响。拉普通过分析孕产妇的羊水穿刺决策,得出怀孕和生产不仅是一个医学控制的过程,还是女性不断积累孕产知识,同时在母女、朋友和特定群体之间流传具身性知识(Embodied Knowledge)的过程。[27]204-219
以上社会互动层面的研究,主要以父权制、医学化或者身体政治等理论为背景,在社会互动框架下分析女性的孕产行为。考虑到孕产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金斯伯格和拉普提出,怀孕生产问题既涉及个人的身体,又涉及国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质。[28][29]而在新自由主义转向下[12]11,各领域中的研究者除了关注社会互动对女性孕产行为的影响之外,还开始具体分析孕产行为的体验和选择,产生众多以女性能动范式为起点的怀孕和生产行为研究成果。
四、能动范式中的怀孕和生产
在权力关系分析和互动范式下,女性的能动性似乎没有得到彰显。然而,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对女性怀孕生产过程中的体验和行动能力已经获得诸多关注。以1973年波士顿《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一著作为代表,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中强调女性自身的生育体验与经历,并将其作为和医疗知识相对的女性经验在美国女性中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关注女性主体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的体会和行动能力。
(一)母职建构:怀孕和生产中的心理体验
母职(Motherhood)在国内和国外都得到了丰富的讨论,怀孕生产研究涉及母职的建构问题。里奇认为,女性通常在怀孕生产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母亲身份。这种经历只要由女性自主控制,女性就应该欣然体验生育的过程。[30]2汉森认为,胎儿是母亲身体内的小生命,母亲需要通过维持自己的健康来保证胎儿的茁壮成长。生育文化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女性作为母亲职责的认识。这种社会性建构强调女人在感情上和胎儿的联系,她们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具有所谓的女性特质。[31]9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在一方面得到了发展,但其他方面则在以胎儿为主的价值观下日益受到贬低并且边缘化。[32]99由此,女性的生活以胎儿为中心。为了保证胎儿的顺利降生,女人需要牺牲自己其他方面的要求完成社会的母职期望。否则孕妇本身会产生强烈的自责感,社会也会视其为不负责。
除此以外,生殖技术如产前检查等也对女性的母职建构具有一定的作用。这些医疗科技的陆续出现革新了女性的孕产体验,同时,女性对胎儿的感知和母职建构在科技的作用下加强。[33]哈尔帕使用半结构访谈发现,B超的使用能够缓解孕妇对胎儿健康的焦虑。孕妇看到胎儿图像或者听到医生积极反馈时会降低焦虑感[34],反之会更加紧张。新生殖科技在带来更安全生产的同时,也给女性带来了额外的担忧。[35]在怀孕的不同阶段,女性会被要求进行多种检查,包括超声波和唐氏筛查等。这些检查均为孕妇提供了特定的遗传学信息和对胎儿主体的认知机会,同时将女性置于一种“道德先锋”(Moral Pioneer)的位置,使其成为决定胎儿存活的关键责任主体。[36]对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母亲(如未婚生育母亲等),这种服从医生建议的行为给她们提供了身份认同的途径。她们通过接受医疗建议来强化自己的母职形象。[37]产前检查在控制胎儿质量和保证母婴安全的同时,也让女性在不断参与产检和生产的过程中体验到自己和胎儿的联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母亲身份。
福克斯等人强调,在孕产过程中考察母职的体验不应脱离其生活经验,同时也要分析女性本身对于母亲理想型的具体态度。[38]在当前美国社会中,堕胎的争论极为激烈,母职通常被用来分析女性和胎儿(Fetus/Baby)之间的联系。反对堕胎者对这一联系的强化是为了使更多未婚怀孕的女孩停止堕胎行为,遵从社会的母职规范,保护胎儿的生命。[8]
(二)具身体验:怀孕和生产中的身体体验
在现代医疗科技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女性的主体经验话语通常得不到表达。拉普强调女性话语在产前检查技术中的重要性。[27]具身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就是从女性主体出发,强调女性本身的经验。具身体验是一个动态的权力过程。女性在其中可以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同时将医疗科技或者医学实践作为自己的行为起点,甚至一种抵抗方式。
拉普分析了近年来主要针对高龄产妇或者高危产妇的羊水穿刺,展示了这一医学检查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心理形塑。她的经验研究呈现了孕产妇在选择医疗措施过程中,将该医疗措施社会影响具身化的过程。[39]孕产妇的具身体验还包括她们的产前检查行为、生产方式选择以及饮食健身实践。女性在身体实践中会形塑自己的医学观念以及自己与胎儿的关系。马肯斯通过分析孕妇的饮食实践,认为女性通过饮食实践建构了自己的母亲职责及其与婴幼儿的关系。怀孕中的各种医学建议使得她们将自己主动置于医疗控制之中。[40]纳什通过研究孕妇的饮食实践,发现女性的孕产行为受到医学文化的监督和自我规训,即孕妇在选择自己饮食方面既要考虑孕产过程中的身体和风险,还要考虑自己的需要和经验。[41]
(三)行动策略:怀孕和生产中的实践
已有孕产行为研究除了关注母职体验和身体实践以外,部分学者也致力于分析女性的孕产行为策略及其内在差异。在国家、社会和医学权力控制之下,女性是被动的客体还是抵抗的主体,一度成为学者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在这一权力体系中是完全被动的客体,而非一个有行动和理性思考的主体。马丁则认为,女性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进行抵抗——她们通过采用不同于医生要求的生产姿势或者拖延医院规定的生产时间来进行抵抗。[3]186然而,并非所有女性都会这样做,也并不意味着抵抗医疗权力的女性在这一行为上具有持续性。女性一般根据自己所接受过的知识体系进行医疗选择。如果专业医生的医疗知识体系和她们的日常知识体系发生冲突,她们会根据不同系统的知识和个人经验进行权衡选择。[23]
洛克等人认为,女性身体在受到国家或者医疗权力控制的安排时,依然有自己的主动性和文化规范,女性不会完全服从于医疗权力,也不会进行彻底的抵抗,而是具有一种实用性的特征(Pragmatic Women)。[14]女性在选择医疗措施方面如果明显对自己或者所在家庭有利,那么女性通常会选择医生所提供的医疗措施。例如,在本土的文化和家庭环境影响下,日本的孕妇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影响不大、非入侵性的科技,如超声波检查。因为很多日本女性认为孕期是一段较为危险的时间,应该避免接触那种对孕产行为影响明显的医学技术。[14]229马肯斯则提出,女性孕产行为研究中多关注接受检查者,却忽视了拒绝检查孕产妇的情况。她的研究发现,选择和不选择医疗手段干预对于堕胎、生产等的态度差异并不大。[42]
1987年,切斯基提出在讨论孕产中的生殖技术以前,先要满足所有女性在知识和资源上的获得平等,才可称其是一种知情选择。[34]在之后的研究中,拉扎勒思研究女性孕产行为时按照社会阶层和专业知识将其分为三类群体,分别是具有一定医疗知识的中产阶级、普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研究发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女性对孕产行为的控制和选择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普通中产阶级的态度较为多元化,但大部分都希望能够控制自己的孕产过程;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女性则认为自己需要社会福利的救助,同时希望获得持续性的医疗保健;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中产阶级女性则更关注自己对孕产行为的控制,同时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医疗服务。[43]
拉普根据自己多年在生殖问题上的研究,提出了“层级化的生殖”(Stratified Reproduction)这一概念,即生殖健康、生育体验和养育孩子等问题都会形成某种社会层级式的安排。这一安排既支持鼓励特定女性群体,又将特定的女性排除在法律和政策之外。拉普的研究显示,在医疗知识获得上,中产阶级的女性更为熟练地掌握医学专业用语和医学流程,而平民家庭中的女性则更容易将医疗知识和非专业医疗领域混合,包括她们的地方性知识和过去经验等。[37]312-317拉普的这一分析将生殖的社会分层问题化,并将其纳入社会科学分析领域。这种生殖问题上社会阶层分析的发掘,让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看到现代社会全球化的生存规则。[44]
五、思考与建议
国外怀孕生产行为研究的不同层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宏观权力结构分析离不开社会互动和微观行动,而微观行动体验中则反映出结构权力关系和宏观社会文化含义。综述发现,孕产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物过程,其中不仅涉及女性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国家政策、医疗体制,还关系到女性的家庭社会网络、个体心理和身体体验,以及女性的孕产行为选择。也正因如此,金斯伯格和拉普试图将生殖问题界定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问题。研究者分析孕产行为时,既要关注其技术层面,也要关注其权力层面,同时还不能忽略女性的主体性。此外,孕产行为不只是静态的事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情境行动。[45]综合而言,国外怀孕生产研究领域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国外孕产行为研究从女权主义、身体政治、医学化的宏观理论视角出发,到社会互动、社会分层等分析框架,运用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理论分析路径,得出了丰富的研究结论。孕产行为研究已经囊括了全球化地方化背景以及社会个人多层面的问题,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化。对怀孕和生产过程中各种权力关系、社会层级等问题的争论逐渐变得不再针锋相对,研究者意识到并尽力展现这一过程中的复杂性。怀孕和生产过程既包括一系列的权力关系,也涉及社会互动下的社会关系和个体能动下的行动能力与体验。
其次,国外现有研究着重反思女性行动能力和选择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从应然和本质主义的权力结构讨论转向实然和结构本身的行为内涵分析。研究者解构了不同女性怀孕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特征,同时更加关注女性怀孕生产行为中策略的差异性和内在逻辑。选择和拒绝、使用和不使用不再成为绝对的标准,研究者更多关注这一系列行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从而打破以往二元主义的绝对性分析。
最后,怀孕和生产行为的研究越来越考虑情境、过程以及全球化背景中本地文化的特殊作用。国外怀孕和生产的研究主要以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堕胎权益等问题为背景,他们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不应该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对其他国家而言,研究怀孕和生产的参考借鉴也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文化和社会背景进行历史情境中的分析。从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怀孕和生产等概念本身就需要重新考虑和界定,具体的研究问题也应考虑每个社会文化中的生育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到日常生活领域。生殖医疗技术的普及和国家管理医疗系统的一致性使得各国女性的孕产经验也越来越相似。从常规性的产前检查到后来的住院生产,各国女性的怀孕和生产都被纳入医疗体制的管理当中。1995年,世界妇女运动大会在我国召开,我国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中国女性的生殖健康问题。《母婴保健法》的提出和推行,使得中国女性在孕产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上也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我国所具有的生育政策背景、医疗资源分配问题和生育文化又和国外女权主义运动、医疗资源分配等情况存在很大差异。这一系列相同点和差异性都给我们研究中国女性的怀孕和生产造成了现实的挑战。
因此,在理论层面,从我国女性的实际经验出发,分析她们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权力结构和她们自身的行为策略,必然是有创造性的发现和理论上的突破。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孕产行为研究结论可以充分和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对女性怀孕和生产行为的研究进行补充。在社会现实层面,随着2014年以来新的生育政策实施,孕产妇数量较之以往出现了大幅提升,怀孕和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彰显出来。这就更需要我们引进和讨论国外怀孕生产领域的先进理论,同时调查了解中国孕产妇的实际行为,发现我国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孕产行为特征。
[1]Ginsburg,Faye&Rapp Rayna.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1,(20).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Martin,Emily.The Women in the Body: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M]Boston:Beacon Press,1987.
[4]Beckett,Katherine.Choosing Cesarean: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dbirth in United States[J].Feminist Theory,2005,(6).
[5]Inhorn,Marcia L..Defining Women’s Health:A Dozen Messages from More than 150Ethnographies[J].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2006,(20).
[6]Namey,Emily E.&Lyerly Ann Drapkin.The Meaning of‘Control’for Childbearing Women in the US[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10,(71).
[7]Gimenez M.E..The Mode of Reproduction in Transition:A Marxist-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J].Gender&Society,1991,(5).
[8]Taylor,Janelle S..The Public Life of the Fetal Sonogram:Technology,Consumption,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M].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8.
[9]Foucault,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Volume 1)[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
[10]Conrad,Peter,Mackie T.&Mehrotra A..Estimating the Costs of Medicalization[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10,(70).
[11]Greenhalgh,S..Cultivating Global Citizen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2]Foucault,M..The Birth of Clinic[M].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3.
[13]Foucault,M..Discipline and Punish[M].New York:Random,1977.
[14]Lock,Margaret&Kaufert Patricia A..Pragmatic Women and Body Poli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5]Parsons,Talcott.Social System[M].London:Routledge,1991.
[16]Conrad,Peter.Medicalization and Social Control[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2,(18).
[17]Barker,K.K..A Ship upon a Stormy Sea:The Medicalization of Pregnancy[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1998,(47).
[18]McCallum,Cecilia.Explaining Caesarean Section in Salvador da Bahia,Brazil[J].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2005,(27).
[19]Czarnecki,Danielle.Moral Women,Immoral Technologies:How Devout Women Negotiate Gender,Religion,and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J].Gender and Society,2015,(29).
[20]Press,Nancy&Browner C.H..WhyWomen Say Yes to Prenatal Diagnosis[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1997,(45).
[21]Rosengren,William,R..Social Sources of Pregnancy as Illness and Normality[J].Social Forces,1961,(39).
[22]Markens,Susan.‘It Just Becomes Much More Complicated’:Genetic Counselors’Views on Genetics and Prenatal Testing[J]. New Genetics and Society,2013,(32).
[23]Lorentzen,J.M..“IKnow My Own Body”:Power and Resistance in Women’s Experiences of Medical Interactions[J].Body& Society,2008,(14).
[24]Malacrida,Claudia&Tiffany Boulton.The Best Laid Plans?Women’s Choices,Expectations and Experiences in Childbirth[J]. Health,2013,(18).
[25]Santalahti,Paivi,Hemminki Elina,Latikka Anne-Maria and Ryynanen Markku.Women’s Decision in Prenatal Screening[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1998,(46).
[26]Markens,Susan,Browner C.H.&Preloran H.Marbel.“I’m not the One They are Sticking the Needle into’Latino Couples,Fetal Diagnosis and the Discourse of Reproductive Rights[J].Gender&Society,2003,(17).
[27]Rapp,Rayna.The Power of“Positive”Diagnosis:Medical and Maternal Discourses on Amniocentesis[A].Bassin,D.,Honey,M. &Kaplan,M.M..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hood[C].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28]Ginsburg,Faye&Rapp Rayna.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1,(20).
[29]Ginsburg,Faye&Rapp Rayna.Conceiving the New World Order:The Global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30](美)艾德里安·里奇.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M].毛路,毛喻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31](英)克莱尔·汉森.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与文化(1750—2000)[M].章梅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2](美)苏珊·鲍尔多.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M].綦亮,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3]Petchesky,Rosalind Pollack.Fetal Image:The Power of Visual Culture i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J].Feminist Studies,1987,(13).
[34]Harpel,Tammy S..Fear of the Unknown:Ultrasound and Anxiety about Fetal Health[J].Health,2008,(12).
[35]Gammeltoft Tine M.&Wahlberg Ayo.Selective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14,(43).
[36]Rapp,Rayna.Testing Women,Testing the Fetus:The Social Impact of Amniocentesis in Americ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37]Brubaker,Sarah Jane.Denied,Embracing,and Resisting Medicalization:African American Teen Mothers’Perceptions of Formal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Care[J].Gender and Society,2007,(21).
[38]Fox,Bonnie&Worts Diana.Revisiting the Critique of Medicalized Childbirth: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Birth[J].Gender &Society,1999,(13).
[39]Rapp Rayna.Testing Women,Testing the Fetus:The Social Impact of Amniocentesis in America[M].London: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e-library,2005.
[40]Markens,Susan,Browner C.H.&Nancy Press.Feeding the Fetus:On Interrogating the Notion of Maternal-Fetal Conflict[J]. Feminist Studie,1997,(23).
[41]Nash,Meredith.Indulgence versus Restraint:A Discussion of Embodied Eating Practices of Pregnant Australian Women[J].Journal of Sociology,2015,(51).
[42]Markens,Susan.“Because of Risk”:How US Pregnant Women Account for Refusing Prenatal Screening[J].Social Sciences and Medicine,1999,(49).
[43]Lazarus,Ellen S..What do Women Want?Issues of Choices,Control and Class in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J].Medical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1994,(8).
[44]Rapp,Rayna.Gender,Body,Bio-medicine:How Some Feminist Concerns Dragged Reproduction to the Center of Social Theory[J].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2001,(15).
[45]Almeling,Rene.Reproduc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5,(41).
责任编辑:张艳玲
From Power Structure to Strategy of Agency:A Literary Review of Foreign Studies on Pregnancy and Birth
QIU Jifang
Foreign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power relations around pregnancy and birth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feminist history.Mo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women’s subjectivity and agency.Research found that studies on pregnancy and birth are abundant in theories and practices,focusing more on the inner structure and complexity of agency of pregnancy and birth.However,social backgrounds and contents are different from China.We lack studies on this theme.The launch of“Two Children for All families”bares direct influence on pregnancy and birth among Chinese women.By reviewing foreign studies on this area,we can learn more and reflect on our own paradigm.
pregnancy;giving birth;power;agency
10.13277/j.cnki.jcwu.2016.05.009
2016-05-23
C913.68
A
1007-3698(2016)05-0057-08
邱济芳,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研究、家庭社会学等。210032
本文系江苏省2015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单独二胎政策下高龄女性生育风险及其医疗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YZZ15_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