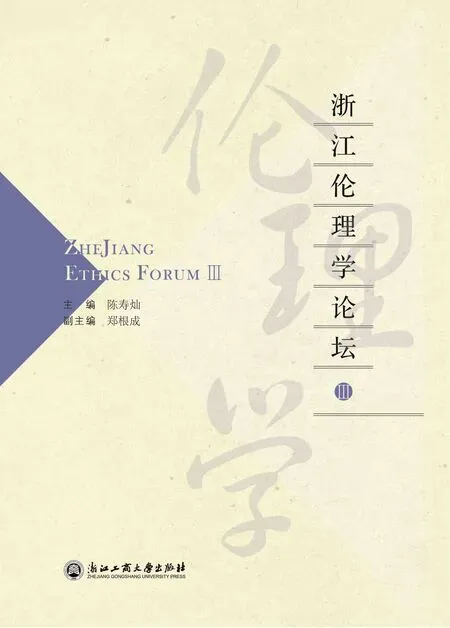道德动机、欲望与实践承诺*1
2016-02-13徐向东
徐向东
◆伦理学前沿与热点
道德动机、欲望与实践承诺
*1
徐向东①
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被认为对我们的实践理性或者理性能动性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乃至不相容的解释:休谟主义被认为不仅得出了一种关于实践理性的怀疑论,而且也对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造成威胁,相比较而论,康德主义则被认为维护了实践理性的“自主”地位和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本文旨在表明,一旦我们澄清了休谟主义的两个构成要素——它对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说明以及它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基础地位的强调——的本质和地位,并给予康德伦理学以一种适度的“自然主义”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义地缓解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被认为存在的张力。本文也试图表明,放弃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的、基础主义的探讨,转而采纳一种以实践承诺为核心的语境主义探讨,或许是值得向往的。
行动的理由;欲望;工具合理性;实践承诺
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往往被认为对我们的实践理性或理性能动性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乃至不相容的解释:休谟主义据说不仅得出了一种关于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对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造成严重威胁,相比较而论,康德主义被认为维护了实践理性的“自主”地位和道德要求的“绝对”地位。①关于这个论点及其争论,例如,参见Philipps Foot:Morality as a System of Hypothetical Imperatives Philosophical Review,1972,81:205-315;John McDowell:Are MoralRequirements Hypothetical Imperatives,reprinted in McDowell:Mind Value and Real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p.77-94;Christine Korsgaard: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reprinted in Kieran Setiya and Hille Paakkunainen:Internal Reasons:Contemporary Readings,The MIT Press,2012,pp.51-72。本文旨在表明,一旦我们澄清了休谟主义的两个构成要素——它对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说明以及它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基础地位的强调——的本质和地位,并给予康德伦理学以一种适度的“自然主义”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义地缓解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据说存在的张力。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将简要地阐明休谟主义者对行动的理由的理解,面对乔纳森•丹西提出的“纯粹认知主义”来澄清对这个概念的一些主要误解。在第二部分,我将把注意力转向克莉斯汀•科斯格尔针对工具理性原则对休谟主义的批评。我将试图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工具原则就像她所论证的那样“不可能独立存在”,这也无须削弱这个原则在我们的理性能动性中的基础地位。在第三部分,通过借助于约翰•麦道尔对知觉信念的论述以及芭芭拉•赫尔曼对欲望和理性之关系的分析,我将简要地表明如何可能在休谟对行动的实践合理性的理解和一种适度地“自然化”的康德式的解释之间实现一种调和。总的来说,本文试图表明,放弃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的、基础主义的探讨,转而采纳一种以实践承诺为核心的语境主义探讨,也许是值得向往的,而不论是对规范伦理学还是对政治哲学,这种探讨都会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重要含义。
一、行动的理由:一个初步描述
在近来关于实践理性的争论中,休谟主义往往被认为倾向于导致关于实践理性的怀疑论,或者说是对道德的理性辩护的一种怀疑——如果休谟主义是真的,那么道德要求就不可能是绝对命令,或者等价地说,道德规范不可能向我们提供服从道德要求的绝对理由。①关于这个论点及其争论,例如,参见Philipps Foot:Morality as a System of Hypothetical Imperatives Philosophical Review,1972,81:205-315;John McDowell:Are MoralRequirements Hypothetical Imperatives,reprinted in McDowell:Mind Value and Real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p.77-94;Christine Korsgaard: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reprinted in Kieran Setiya and Hille Paakkunainen:Internal Reasons:Contemporary Readings,The MIT Press,2012,pp.51-72。一开始就需要指出,如何理解这个主张以及它是否在根本上成立取决于一系列进一步的相关问题,例如如何理解道德要求对我们来说具有一种绝对权威,不服从道德权威是否必定是实践上不合理的,如何区分规范性的理由和激发性的理由,等等。不过,在澄清这些进一步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休谟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遵循一种流行观点,我将把休谟主义理解为一种关于行动的理由的理论,即一种关于一个人有什么理由采取某个行动的理论。一个行动的理由首先必须要说明行动者为何采取某个行动,只有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才能有意义地谈论一个特定的行动是否合理。在唐纳德·戴维森看来,一个行动的理由必须出现在对它的说明中,因此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和在最简单的情形中,行动的理由是由行动者所持有的某个欲望以及一个合适地相关联的目的—手段信念构成的。②Donald Davidson: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reprinted in Davidson: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Clarendon Press,2002,pp.1-20.具体地说,激发一个行动的理由可以被定义如下:
(MR)一个行动者有一个激发性的理由做X,当且仅当存在着某个目的或目标Y,以至于行动者欲求Y,并相信通过做X他就会获得Y。
显然,为了表明对激发性理由的这种理解如何能够说明一个行动的发生,我们就需要对这个定义做出某些必要限定,例如需要假设行动者并不存在相冲突的目的或目标,有能力履行作为实现那个目标之手段的行动,相关的目的—手段信念是正确的,等等。③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能力”的概念是一个复杂概念,它可能不仅包括行动者实现某个行动的物理能力(其中涉及对某些资源的利用),可能也包括某些相关的心理能力,例如并不处于意志软弱或者其他形式的心理沮丧状态。那么,在这些限定条件下,一个欲望和一个合适地相关联的目的—手段信念如何能够说明一个行动的发生呢?设想一个人只是碰巧具有某个欲望,例如想要去看一场电影,他也有正确的目的—手段信念(知道如何实现去看这场电影这个目的),但他并不承诺要去实现这个目的(想去看一场电影只是他的一时冲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许不会采取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因此,我们也必须补充说,为了被激发起来采取行动,作为他的欲望对象的那个目的是他承诺要实现的目的(我们有时候用“行动者强烈地欲望某件事情”来表示这一说法)。给出这些限定条件,不难看出欲望和合适地相关联的目的—手段信念如何能够说明一个行动的发生:如果一个行动者确实承诺要实现某个目的(作为他的欲望的对象),并相信通过做某件事情,他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那么他就会做那件事情。
我相信上述定义对于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之间的进一步争论是中立的;也就是说,它极有可能只是描述了关于我们的道德心理的一个基本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一个欲望和一个正确的目的—手段信念的组合也构成了一个行动的理由?如果一个行动的理由就是能够说明一个行动发生的东西,那么这样一个组合显然构成了一个行动的理由。问题仅仅在于:我们也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谈论一个人有什么理由采取某个行动。比如说,假设我逃课去看电影,你很可能就会问:“你有什么理由采取你实际上所采取的那个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在要求我提出一个理由来辩护我实际上所采取的行动,因为在提出这个问题时,你已经不言而喻地假设我本来应该采取一个不同的行动(例如,按时上课)。我们可以把这种理由称为“辩护性的理由”。辩护性的理由显然不同于激发性的理由:假若确实我逃课去看电影,为了回答你的质疑,我可能会说:“最近压力很大,我需要放松,而那堂课的内容是我已经学过的。”如果你认同和接受我的说法,那么我就对我实际上并未采取、但在某种意义上应该采取的行动提出了一个辩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辩解性理由并不是我用来说明我实际上所采取的行动的理由(尽管二者可能也有关联)。如果我的辩解失败,或者你并不接受我用来进行辩解的理由,那么你是否可以合理地认为我实际上采取的行动总的来说是“不合理的”呢?
这个问题让我们开始触及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之间的核心争论。在上述例子中,当你问我说,“你有什么理由这样做”时,你是在要求我的行动的“正当性”的根据。假设我面临一个选择:是要去看电影还是按照许诺去机场接你。我考虑到这场电影是我期盼已久的,而且认为通过看这场电影我就能够让自己得到放松(比如说,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这种类型的电影历来会让我很放松),而当晚八点的那一场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另一方面,另一个朋友同时也答应去机场接你,并告诉我说他肯定会去;此外,由于某些可理解的缘由,我无法及时向你通告我不去机场接你了。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去看电影的选择。如果我采取我实际上所采取的行动的理由包含了这一切考虑,那么它们就不仅说明了我的行动,而且也辩护了我的行动(当然,如果你认为我的理由足够合理,因此可以接受的话)。然而,康德主义者也许会说,在我所设想的这种情况下,并非欲望本身给予了我采取某个行动的理由,而是决定我采取那个行动的考虑给予了我行动的理由并让我具有了那个相应的欲望。①托马斯•内格尔在“被激发的欲望”和“没有被激发的欲望”之间的区分暗示了这个观点,而在目前所设想的这种情形中,我要去看电影的那个欲望是一个被某些理由激发起来的欲望。参见Thomas Nagel: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29-30。因此,行动的理由无须与就此而论的欲望具有任何本质联系。仅仅具有一个欲望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也有理由采取行动来获得我所欲求的对象。
休谟主义的行动理由概念旨在维护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在主义要求”:行动的理由和行动的动机之间必须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为了说明这个联系,休谟主义者把欲望设想为本质上具有动机效应的状态。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需要预先指出,在休谟主义者这里,欲望是一个专门术语,不仅包括日常意义上的欲望(例如本能欲望或身体冲动),也包括戴维森所说的“赞成态度”,即能够具有动机效应因而不同于纯粹信念的精神状态,例如道德观点、审美原则、经济成见、社会习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②Donald Davidson: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reprinted in Davidson: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Clarendon Press,2002,p.4.威廉斯也对“欲望”提出了类似理解,见Bernard Williams: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in Williams:Moral Lu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1-113,特别是第105页。换句话说,欲望的概念是按照一种精神状态在行动产生中的功能作用来界定的:欲望是一种旨在让世界发生某种变化以便让自身得到满足的精神状态,相比较,信念是一种旨在符合世界的真实状况的精神状态。对“欲望”的这种理解显然符合一个直观认识:我们欲求某个东西,是因为它在某个描述下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值得欲求的或有价值的,而正是对这个特点的认识让我们产生了想要获得它的欲望,并通过采取合适手段来满足这个欲望。因此,我们实际上无须否认,在我们所具有的欲望中,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具有某些认识或考虑的结果。
然而,承认我们的大多数欲望具有这个特点并不是说信念本身就能激发行动,这是休谟主义的一个核心信条。为了看看它在什么意义是可以合理地接受的,不妨考察一下乔纳森•丹西所谓的“纯粹认知主义”③参见Jonathan Dancy:Moral Reasons,Basil Blackwell,1993,特别是第二章;Jonathan Dancy:Practical Re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特别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如前所述,一个人可以因为认识到某个东西在某个方面对他来说是好的、值得欲求的或有价值的而对之产生欲望。然而,在丹西看来,即便这样一个欲望确实存在,也无须认为它在行动的产生中起到了任何作用,因为“欲求就是被激发”——欲求某个东西只不过是处于有动机把它当作目标来追求的状态。但是,显然不是任何一种信念都能把我们置于这种状态。纯粹的事实信念或描述性的信念,若不与某个欲望相结合,显然并不足以产生行动的动机。我合理地相信今晚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但是,如果我并不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我可能不会采取晚上出门时穿保暖衣的行动。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我欲求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具有那个信念的情况下我才采取了那个行动。丹西或许认为每个正常人都有维护身体健康的欲望,因此在这个行动的说明中无须提到这个欲望,但是,对于休谟主义者来说,对这样一个欲望的提及在行动的产生和说明中仍是本质的。这种类型的欲望无须明确地出现在一个人对自己行动的说明中,但必须出现在由具有动机作用的状态所构成的背景条件中。①关于这一点,见Philip Pettit,Michael Smith:Backgrounding Desir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90,99,pp.565-592。
不过,丹西或许反驳说,隐含在背景动机条件中、在完整地说明一个行动时需要被诉求的欲望可能也是被激发的欲望,特别是因为具有了某些信念而具有的欲望。为了回答这个异议,考虑他对纯粹认知主义的正面提议:行动实际上可以由两个信念激发起来:一个信念所说的是“某件事情值得欲求”,另一个信念关系到如何导致那件值得欲求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关于值得欲求的目标与获得其手段的关系的信念,即通常所说的目的—手段信念。因此,在丹西看来,一个评价性信念加上一个恰当地相关联的目的—手段信念不仅提供了一个行动的理由,也足以产生行动的动机。这意味着评价性信念就是本质上具有动机作用的要素,因此欲望在行动的产生中没有任何功能作用。但是,评价性信念如何具有动机效应呢?如果信念只是具有从心灵到世界的适应方向的精神状态,那么对我来说,相信某件事情值得欲求仅仅意味着,在我的认知视野内我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在世界中存在某个事态或性质,它是值得欲求的。即便如此,这样一个信念如何能够对我产生动机影响呢?直观上说,只有当我能够经过慎思把对那个值得欲求的特点的确认(这可以表现为一个信念)能够与我的主观动机集合中的某些要素联系起来时,这种确认才有可能对我产生动机效应。比如说,我或许认为宇宙中的恒星数目是偶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件“好事”,现在,天文学研究表明宇宙中的恒星数目很有可能是偶数;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被认为合理地持有了一个相应的评价性信念。但是,很难看到这个信念本身如何能够激发我采取某个行动,除非在我的动机集合中我已经对所有与偶数有关的东西有了偏好或兴趣。
甚至就道德信念而论,我们也无须接受丹西的提议。为此,让我首先考虑一个与审慎(prudence)有关的信念。假设我相信及时去医院看牙疼对我来说是值得欲求的。表面上看,这个信念似乎可以合理地说明我为何具有去医院看牙疼的欲望。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信念本身是否足以激发我采取去医院看牙疼的行动。对于这个信念的形成,我们可以提出两种可能解释。首先,它可能是一个归纳概括的结果:我观察到,对于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严重牙疼的人,他们都一致认为最好及时去医院治疗,在这个意义上,去医院看牙疼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值得欲求;此时,我有严重牙疼,因此我相信去医院看牙疼对我来说值得欲求。如果我的信念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那大概就可以合理地说明我去医院看牙疼的欲望——不管我是否确实具有这样一个欲望。在这种情形中,这个信念似乎是用一种很像证据支持的方式来说明牙疼的欲望:如果“做X是值得欲求的”这个一般信念能够说明想要做X的欲望,那么,只要我接受了这种说明上的联系,“去医院看牙疼对我来说值得欲求”这一特定信念也能说明我去医院看牙疼的欲望。这就类似于如下情形:只要我相信某个命题p,也相信“p支持q”,那么,当我最终相信q的时候,前两个信念就对我最终具有的那个信念提供了证据支持。但即便如此,我最终具有的那个信念无须是由那两个信念引起的。同样,“做X对我来说值得欲求”这个信念能够说明我对做X的欲望,但无须引起我具有那个欲望。其次,如果“去医院看牙疼对我来说值得欲求”这一信念确实在我实际上采取的行动中发挥了某种作用,那么就需要仔细审视一下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之所以相信去医院看牙疼对我来说值得欲求,很有可能是因为牙疼让我遭受痛苦,而我想要终止这种痛苦;我进一步相信,及时去医院治疗是终止这种痛苦的唯一有效方式。因此,从根本上说,我最终形成的欲望是(因果地)来自我要终止牙疼的欲望。后面这个直接的欲望,加上一个相关的目的—手段信念,不仅说明了我采取相应行动的动机,也说明了我为何相信去医院治疗对我来说值得欲求。看来,若没有某个作为背景条件的欲望,我也不可能具有一个能够对我产生动机影响的评价性信念。即使评价性信念貌似能够产生动机影响,但它实际上是通过背景动机条件来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它被认为具有的动机作用其实是来自两件事情的恰当组合:其一,通过一种纯粹理智的认识,我相信某个东西具有某个值得欲求的特点;其二,通过我的背景动机条件,我对我所认识到的那个特点有了一种实践意义上的承诺。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承诺,一个把评价性命题当作对象的信念才有了它看似具有的动机效应。
我相信类似的分析也适用于道德信念。考虑“无辜伤害他人是道德上错的”这一信念。作为一种认知状态,信念旨在获得真理。因此,若把这个信念解释为“有充分的理由或证据断言‘无辜伤害他人是道德上错的’这个命题是真的”,就很难看到它怎么能够具有动机效应,因为一个道德信念对动机的影响显然并不仅仅在于我有充分的理由把它看作是真的(除非我对“是真的”这件事情本身也有一个实践承诺,例如认为凡是真理都值得追求并承诺要这样做),而是在于作为其对象的那个命题本身的规范内容。换句话说,如果“无辜伤害他人是道德上错的”这一信念确实对我产生了动机影响,那不可能只是因为我对那个命题采取了一种认知态度,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对“道德上错的”这个概念的规范地位有了一种实践意义上的承诺。换言之,在说某件事情是道德上错的时候,我并不仅仅是在陈述一件事情,甚至也不是在认知上有充分的理由确认它具有“道德上错的”这一特点,而是在表达一种能够对我产生动机效应的实践态度。①在笔者看来,这个观点为理解和说明丹西为了论证其观点而不断提及的意志软弱和倦怠(accidie)的情形提供了一个合理起点。在我看来,它们不是为丹西的纯粹认知主义提供了支持,反而构成了对其观点的一个有力反驳,尽管在这里我将不详细论证这一点。意志软弱的人和能够自制的人能够分享对好生活的同一个认识,他们的差别恰好在于:在面对强有力的感性欲望的诱惑时,前者不能坚持他对自己认识的承诺,而后者能够(尽管需要一番努力)通过这样的承诺抵制诱惑。而按照丹西自己对“怠倦”的理解,“遭受倦怠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一时间并不在乎正常情况下他们认为有很好的理由去做的事情……情绪沮丧可能是倦怠的一个原因。情绪沮丧者并没有因为沮丧就丧失了相关的信念;他们只是对这些信念无动于衷”(Dancy 1993 p.5)。如果倦怠的人是因为其意动系统(conative system)而不是认知系统方面的原因而没有被他们原本具有的行动理由激发起来行动,那么倦怠的可能性显然就在于行动者不能坚持自己对行动理由的认识(可以用信念的形式表达出来)和承诺,而且这种失败不一定是实践上不合理的或非理性的。意动系统或动机系统与认知系统(其中包括对善或价值的认识)的脱节是理解这两种情形的一个关键。
二、工具合理性原则与欲望的评价
只要以这种方式澄清了行动的理由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说明和澄清休谟主义的第二个本质要素即工具合理性原则的规范地位。为此,让我首先简要地阐明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可能联系。
以上我已经试图维护一个休谟式的论点:欲望是本质上具有动机效应的状态。我已经遵循戴维森等人的做法,将欲望广泛地理解为一种赞成态度(proattitudes),一种能够具有动机效应因而不同于信念的精神状态。即便如此,一些康德主义者(典型地,例如科斯格尔)已经论证说,欲望本身不可能有任何实践辩护的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欲望若要具有这种作用,就必须是由理性承诺构成的。①Christine Korsgaard:The Normativity of Instrumental Reason,in Garrett Cullity and Berys Gaut:Ethics and Practical Reason,Clarendon Press,1998.在科斯格尔看来,若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拒斥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一种休谟式解释,转而采纳一种康德式解释。科斯格尔对休谟主义者提出的挑战不仅涉及如何理解(就行动而论)激发性理由和辩护性理由的关系,也关涉如何理解工具合理性原则的地位——或者用她的话说,如何理解工具理性的规范地位。科斯格尔对休谟式解释的拒斥从根本上说来自一切康德主义者都会分享的一个忧虑:如果一切行动的理由都取决于欲望,那么不仅没有绝对命令这样的东西,也不可能对道德提出辩护。之所以如此,据说是因为:如果辩护一个特定的道德就在于说明我们有什么理由服从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服从道德规范的理由取决于我们想要通过这样做来获得的目的,那么在没有欲望获得这样一个目的的情况下,似乎也没有理由服从道德规范。即便认为人们应当普遍欲望这样的目的,但如果这个高阶的“应当”也要通过诉诸理由来加以说明,而理由进一步取决于欲望,那么要么就会陷入无穷后退,要么对道德要求的服从就会变得不稳定,因为在一种康德式的道德心理学中,任何欲望被认为都是偶然的。康德主义者把这种怀疑论追溯到休谟主义的两个基本要素:它的行动理由概念及其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解释。为了便于讨论,让我先把这个怀疑论论证介绍如下。②在这里笔者直接引用詹姆斯•德雷尔对这个论证的重构,尽管德雷尔自己并不认为这个论证是有效的。参见James Dreier:Humean Doubts about the Practical Justification of Morality,in Garrett Cullity and Berys Gaut:Ethics and Practical Reason,Clarendon Press,1997,pp.81-100,especially p.91。
(1)只有当道德是由绝对命令组成的时候,道德才能得到辩护。
(2)一个命令是绝对的,当且仅当一个人有理由独立于自己所欲求的东西而遵循这个命令。
(3)一个人有理由做某件事情X取决于存在着某个Y,以至于他欲求做Y,并相信通过做Y他就会取得X。
(4)因此,一个人可能具有的任何理由都取决于他的某个欲望。
(5)因此,不存在绝对命令。
(6)因此,道德得不到辩护。
詹姆斯•德雷尔指出,在该论证的前三个前提中,“理由”的概念并不具有一个单一的含义,因此这个论证实际上是无效的:在论及道德辩护时,我们所说的理由是合理性的规范理由(normative reasons of rationality),因此第二个前提中所说的“理由”不能被理解为激发性理由,但第三个前提中所说的“理由”显然指的是激发性理由。但是,在我看来,仅仅说合理性的规范理由不同于激发性理由并不是消解这个论证的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因为这种做法取决于两个假定:其一,道德是可以按照合理性原则以及相关理由来说明或辩护的;其二,在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之间没有(或者不可能存在)任何可理解的联系。但是,这两个假定都是成问题的,或者至少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
就康德认为道德的理据和动机都只能来自纯粹实践理性而论,第一个假定显然是一个康德式的假定,在此我将不予以追究,尽管我对第二个假定的讨论也会得出一些与评价这个假定有关的含义。我对道德的理解植根于一个我认为是直观上合理的主张:任何合理的道德都需要考虑正常人一般地具有的动机条件①对这个主张的一个深入论述和讨论,见Owen Flanagan:Varieties of Moral Personality:Ethics and Psychological Re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如果一个道德对任何具有适当理性能力的人都无法产生动机影响,那么它理应被拒斥,因为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可以合理地应用于人类及其存在状况的理想。当然,既然在服从道德要求和追求自我利益之间总有可能存在张力,我们并不指望人们总是有自然的欲望服从道德要求,但是适当的道德教育和理性反思应该能够让人们逐渐认识到服从道德要求的理由。反思认同可以成为学会服从道德要求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这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纯粹理论认知的事情,而是就像亚里士多德已经充分论证的那样,唯有通过行动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有美德的人。②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的一个有影响的解说,参见M.F.Burnyeat:Aristotle on Learning to be Good,in A.K.Rorty: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69-92。因此,从道德动机和道德品格发展的观点来看,不应该把人们学会采取道德行动(或者符合道德要求的行动)的理由与理论家们(或者具有理性反思能力并试图追问道德行动的根据的日常行动者)在理论反思层面上尝试用来说明或辩护道德的理由截然分离开来。另一方面,我们也无须先验地排除如下可能性:处于合适的动机状态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所认识到的道德理由行动。
在这里我无法对这些评注提出进一步的说明或论证,但我相信它们是有充分根据的。在上一节中我已经试图表明,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行动的动机是一种休谟式的动机;也就是说,是由欲望和合适地相关联的目的—手段信念构成的。当这样一对信念和欲望成功地激发一个行动时,在能够说明这个行动为何发生的意义上,它们(或者行动者对它们的明确诉求)也构成了如此行动的一个理由,即前面所说的激发性理由。这样一个理由,在满足伯纳德•威廉斯所说的“程序合理性原则”的条件下,也能为行动提供理性辩护。①参见Bernard Williams,Moral Lu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3ff。威廉斯对行动合理性的理解大体上就是休谟的理解:如果一个行动者对其欲望对象持有错误信念,例如错误地相信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对象,或者对如何实现一个目的持有错误信念,那么他的行动就是不合理的。不过,鉴于威廉斯强调一个内在的理由必须是与行动者的主观动机集合具有慎思上的联系的理由,并认为慎思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目的—手段推理,我们也可以认为,对威廉斯来说,在行动者进行慎思的时候,在他自己的最大认知视野内具有一个融贯的主观动机集合,对于行动的合理性来说也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超越威廉斯所说的程序合理性的要求来有意义地谈论行动的实践合理性?或许可以认为不审慎(imprudence,这里指的是以损害或牺牲自己所确立的一项重要的长远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当下的一项相对不太重要的利益)是实践上不合理的,甚至也可以认为意志软弱的行为(采取违背自己的深思熟虑的最佳判断的行动)是实践上不合理的——尽管是否确实如此仍然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类似地认为没能按照道德要求来行动是实践上不合理的呢?即便道德在康德的意义上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必然要求,但是,从日常观点来看,没能按照道德要求来行动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是不合理的或者甚至是非理性的,至少因为如下情形不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并不认为他有理由承诺要接受某个特定的道德要求②在这里,笔者之所以强调“某个特定的道德要求”这一说法,是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合理地设想一个全域的非道德主义者(global amoralist)的可能性。我们对行动的实践合理性的评价总是相对于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行动环境而论的,因此在道德行动的情形中,也是相对于具体的道德规则而论的。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一个全域的非道德主义者,那么我们大概就只能说他不属于人类共同体。,而且我们也无法通过单纯的理论论证向他表明他有理由这样做。③科斯格尔似乎在某个地方也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她认为“真正的不合理性”(true irrationality)的可能性表明:“要通过论证去说服某个人采取理性行为,这总是不可能的”(Christine Korsgaard: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reprinted in Kieran Setiya and Hille Paakkunainen:Internal Reasons:Contemporary Readings,The MIT Press,2012,quoted on p.62,强调是笔者添加的)。参见下文讨论。此外,没能按照某个特定的道德要求来行动的情形可以是很复杂的,比如说,道德要求本身可以发生冲突(道德义务的冲突是其中的一种典型情形),道德主张也可以与一个人对自己的理性的自我利益的主张发生冲突——而在后面这种情形中,假若行动者经过慎思决定放弃道德主张,一般来说,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是实践上不合理的,因为对自己的理性利益的追求同样是实践合理性的一个要求。对行动的实践合理性的评价取决于行动者自己对有关原则或理由的认同和承诺;如果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使他认识到他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承诺,或者对其中一些从第三人的观点来看与他自己已经接受的原则或理由发生冲突的原则或理由做出承诺,那么我们大概就不应该用“实践上不合理”这样的语言来批评或指责他。正如威廉斯所说,我们或许把他说成是残酷的、冷漠的、不人道的,但无须说他是实践上不合理的——合理性的语言不是我们所能具有的唯一的评价语言。
即便如此,一些康德主义者仍然坚持认为,欲望本身不可能具有任何实践辩护的作用,或者,若要具有这种作用,欲望就必须由理性承诺构成。①Christine Korsgaard:The Normativity of Instrumental Reason,in Garrett Cullity and Berys Gaut:Ethics and Practical Reason,Clarendon Press,1998,pp.215-254.若是这样,就必须拒斥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一种休谟式解释。这个动机在根本上说来自康德主义者普遍分享的一个忧虑:对一种休谟式的行动理由概念的接受倾向于导致所谓的“关于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为了便于论证,让我首先指出我同意科斯格尔的一般论点:对理性作为一种动机的范围的怀疑取决于对理性考虑能够影响慎思和选择活动的怀疑。②参见Christine Korsgaard: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reprinted in Kieran Setiya and Hille Paakkunainen:Internal Reasons:Contemporary Readings,The MIT Press,2012,p.52。科斯格尔认为,休谟的动机论证就典型地示范了这种情形:通过假设理性的职能仅仅在于确立观念之间的推理/概念联系和发现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休谟论证说理性本身不可能对我们产生动机影响。③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休谟对理性的职能的界定实际上是当时公认的观点:在康德对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提出论证之前,至少经验论的传统就是这样来理解理性的。因此我们可能需要提防用一种康德式的方式来解读和评价休谟的做法。实际上,笔者相信休谟已经用他所特有的方式对规范考虑的本质和起源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述,虽然他仍然可以坚持他所提出的动机论证。在这里笔者将不论证这一点,一些相关的讨论,见Annette Baier:A Progress of Sentiments:Reflections on Hume's Treati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Elijah Millgram,Was Hume a Humean?reprinted in Elijah Millgram:Ethics Done Ri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18-246。不过,休谟并不否认理性能够在如下意义上引导行动:正确的目的—手段信念以及关于欲望对象的正确信念能够帮助我们成功地实现预定目的。因此,只要我们承诺要实现某个目的,我们就有一个规范的理由关心这两种信念的正确性。这样一个理由是规范的,是因为它来自我们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理性承诺——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承诺,在没有采取我所能采取的必要手段(或者在我的理性慎思下最有效的手段)来获得预定目的的情况下,我才能被说成是实践上不合理的。按照这种理解,休谟并没有犯科斯格尔指责他犯下的那种错误:“要是休谟相信工具理性,他就不得不接受对工具原则的第二个表述——如果你要追求一个目的,你就有一个理由采取获得它的手段”。对于休谟来说,我们的行动的目标确实是由广泛意义上的欲望来设定的,但这无须意味着行动者对这样一个目标的设定没有任何考虑。即便某些欲望可以直接“驱使”我们,但若没有正确的目的—手段信念,我们也无法成功地满足这样一个欲望;而作为生活在社会世界中的存在者,只要我们已经有了最低限度的合理性,我们也会考虑一个必要手段的恰当性。我们如何能够具有这种考虑无须是一件不可阐明的神秘事情。例如,在休谟对正义及其美德的起源论述中,他已经对此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说明。在社会世界中生活的可能性意味着我们能够对他人的正当需求和相互期望保持合适敏感,而在休谟这里,这个要求可以体现在一个“合情合理的个性”的概念中,即便不是体现在他所利用的那种前康德式的“理性”概念中。另一方面,尽管某些考虑只有在与背景动机条件恰当地结合的时候才能导致一个欲望,但只要那些条件在行动者自己的认知视野内是一致的或融贯的,只要他的目的—手段信念是正确的,他所采取的行动也是实践上合理的。
在这里我要表达的要点是:工具合理性原则本身不是不能产生对目的的理性评价①史密斯对此提出了一个详细论述,见Michael Smith:Instrumental Desires,Instrumental Rationality,Supplement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2004,78。——问题仅仅在于这种评价对于评价行动的实践合理性来说是否已经是充分的。大致说来,对手段的慎思,或甚至对一个手段的尝试性采纳,可以导致我们发现我们拟定追求的一个目标要么是不可实现的,要么与我们已经接受的某些其他目的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恰当地修改我们的目标系统,因此修改我们的欲望系统。按照工具合理性原则,只要我确实欲求一个目标,就我有能力获得它而论,在没有冲突欲望的情况下,我也应当欲求获得它的必要手段,否则我就是工具上不合理的。在这里确实有一种动机力量的传递:在适当条件下,对目标的欲求会导致对必要手段的欲求。但这种传递显然不是用一种液压机式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因为其根据就在于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承认和接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理性认识和实践承诺的结果。进一步,如果我承诺要实现一个目标,在上述条件下,我也倾向于采取作为必要手段的行动。我在欲望系统的融贯性方面所经受的压力会导致我修改相关的目的—手段信念;另一方面,对目的—手段关系的反思也会导致我恰当地修改我的欲望系统。因此,只要可以对目的—手段信念进行理性评价,也就可以对相关的目标欲望进行理性评价。休谟固然认为“原初的”欲望或许是不可评价的,不过,只要我们发现所有相关的工具欲望(对满足目标欲望的可能手段的欲望)都遭受连续不断的挫败,我们也有可能放弃目标欲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它只是不符合我们的整个欲望系统的最大融贯性要求。因此,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继续持有那个欲望才是不合理的或无理性的。
而且,休谟允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价欲望,甚至评价非工具性的欲望。①休谟:《人性论》,“论意志的有影响的动机”那一节的第三段。科斯格尔承认这一点,见Christine Korsgaard:The Normativity of Instrumental Reason,in Garrett Cullity and Berys Gaut:Ethics and Practical Reason,Clarendon Press,1998,pp.225-234;也见Christine Korsgaard: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reprinted in Kieran Setiya and Hille Paakkunainen:Internal Reasons:Contemporary Readings,The MIT Press,2012,pp.60-62。休谟认为,趋善避恶是人性的一个本质特点,也是一个能够对意志产生影响的形式原则(在幸福是一个形式原则的同样意义上)。个体总是按照他们对善恶的具体理解来行动,因此,如果他们把审慎认同为一种善,他们就倾向于按照审慎的要求来行动,就需要冷静地计算一个即将采取的行动或打算满足的欲望是否符合审慎的要求。因此我们很容易把向善的一般欲望的运作和理性的运作混淆起来。然而,休谟明确指出二者实际上是不同的:一般的欲望可以对意志产生影响,但理性本身不能直接对意志产生动机影响。按照这种理解,当一个人已知地和自愿地采取违背自己所认同的最佳利益的行动时,就可以把他说成是“不审慎的”,或者在某些情形中是不自制的,但不是“不合理的”或“无理性的”。他的失败是在美德或品格方面的失败,而不是在理性方面的失败,因为他既不缺乏慎思,亦不缺乏采纳有效手段来实现他实际上所采取的行动的能力。对休谟来说,品格上的失败并不是理性的失败,但是,一个人确实可以从自己的品格(或者与此相关的美德或恶习)来决定是否要满足或抵制某个欲望。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需要培养和发展一个强健而稳固的道德品格,并不只是为了纯粹道德认知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和不断重塑能够与道德规范保持一致并相互促进的欲望,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已经强有力地表明的。
科斯格尔争辩说,工具理性原则不可能独立存在,因为我们需要其他合理性原则(特别是道德原则)来评价非工具性欲望。但是,我已经表明工具理性原则本身不是不能产生对欲望的评价。由此看来,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必定涉及这样一个问题:用合理性的语言来评价非工具性的欲望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可理解的做法?在这里我将不一般地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科斯格尔之类的康德主义者往往强调对非工具性欲望的道德评价,但是,其中所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按照道德要求来行动是不是一个实践合理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定论。在这里我只想强调说,即使我们确实可以有意义地用其他形式的合理性原则来评价非工具性欲望,但是,与这些原则相比,工具合理性原则至少在如下意义上占据了一个基础地位:它是我们的理性能动性的本质的构成要素——只要我们试图成功地行动,我们就得满足工具合理性原则的要求,但是,能够成功地行动确实就是我们作为行动者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生活在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我们的行动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够面对他人、面对我们所生活的状况来反思自己的行动,因此在适当条件下不仅能够反思性地认同其他形式的理性要求,也有可能把新的理性生活规范创造出来。这就是我们作为理性动物的最本质的方面。只要我们已经成功地行动,我们就满足了工具合理性原则的要求。我们可能因为持有错误的目的—手段信念,或因为把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当作欲望的对象,而不能成功地实施一个行动。如果这种错误不是我们在自己的最大认知视野内所能发现或纠正的,那么这种情形就说不上是没有满足工具原则的要求。我们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放弃一个预定目标。例如,在经过严肃的尝试后发现自己能力不足,或者对预定目标的追求要求我们放弃一个我们此时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对预定目标的放弃反而是实践合理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动性应当是时间上扩展的。①对时间上扩展的能动性及其与理性慎思关系的强调,见Michael Bratman:Structures of Agen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是因为意志不够坚定之类的缘故而放弃一个预定目标,那么我们的失败更恰当地说是在品格方面的失败,而不是在工具合理性方面的失败。当对目的—手段信念的反思能够用前面所描述的那种方式来修改我们的欲望系统并对特定欲望做出评价时,在严格意义上违背工具理性原则的情形实际上很罕见。这也是这个原则的基础地位的一个体现——它很可能像休谟所说的那样已经植根于我们的人性中。
当然,康德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这种理解,因为他们强调说,我们无法独立于对欲望本身的理性评估来评价行动的实践合理性:如果一个欲望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那么也不可能认为相应的行动是合理的,即使行动者满足了工具理性的要求。比如说,怎么可能认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是实践上合理的呢?即使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他卓越地满足了工具合理性的要求。但是,我们真的准备用实践合理性的语言来评价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吗?为什么不说那种行径是残忍的或不人道的呢?从道德的起源及其在人类生活中所要发挥的功能来看,我们似乎不能认为道德仅仅是一个实践合理性问题。康德主义者试图把理性的权威提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来彰显“理性”对于“欲望”的支配地位。然而,甚至在未能回应理性考虑的一些情形中,在“实践合理性”的某种直观意义上,一个人也无须是实践上不合理的。为了看到这一点,考虑科斯格尔的如下说法:
好像有大量的东西能够干扰一个特定的理性考虑的动机影响。愤怒、激情、沮丧、分心、悲伤、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它们都能引起我们无理性地行动,也就是说,未能在动机上回应我们可得到的理性考虑。
假若我们接受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或斯多亚式的观点,我们就无须认为情感反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理的。①一些学者已经论证说,在无须否认情感具有动机效应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对情感的本质和起源提出一种认知的解释,而且,情感本身就表达了一种价值判断。例如,参见Martha Nussbaum:Upheavals of Thought: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此外,如果一个人因为沮丧或悲伤而不能回应他曾经认识到并加以承认的理性考虑,他也不一定就是实践上不合理的,不仅因为他可能有(回顾式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未能回应特定的理性考虑,因此为他的不能回应提供一个辩护,而且因为某些形式的沮丧或悲伤本身就是对其生活状况的一种合理回应。最终,如果一个人因为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而不能回应某个理性考虑,就这样一种特定的疾病既不是他本人所意愿的,也不是他能够自主控制的而论,我们也无须认为他的不能回应是一种实践无理性的表现。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追问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采纳实践合理性的语言来评价一切行动和品行呢?在这里我将不尝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完整回答。不过,科斯格尔对休谟所说的“冷静的激情”的评论暗示了一个部分的回答。她说:
只要这个冷静的和一般的激情仍然对具体的激情具有支配地位,一个人就会审慎地行动。正是在这个目的的影响下,我们用一个可能的满足来权衡另一个可能的满足,试图决定哪一个有益于我们的较大的善。但是,如果对善的这个一般欲望并不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做将有助于促进较大的善的事情的动机和理由就消失了。
这就是说,如果休谟所说的“冷静的激情”只不过是个欲望,我们就无法指望它能够可靠地击败一个与审慎的合理性不相一致的欲望。休谟用“欲望”来称呼这个激情的做法也许是一个错误,但在其哲学体系中是一个可理解的错误,因为对他来说,唯有广泛意义上的欲望才具有本质上的动机效应,而与审慎相联系的那个“冷静的”激情是能够对意志产生影响的东西。这个激情确有可能在特定场合不能占据支配地位,但是,这对于科斯格尔所说的理性也是真的,因为在澄清对所谓的“内在主义要求”(在这里,内在主义指的是,道德动机是内在于道德判断)的误解时,她明确指出,这个要求“并不要求理性考虑总是成功地激发我们,而仅仅是要求:就我们是理性的而论,理性考虑总是成功地激发我们”。一般来说,这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主张,但它掩盖了一些需要进一步阐明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笼统地说一个理性行动者就是总是按照理性考虑来行动(或者至少总是回应理性考虑)的行动者。然而,为了让这个说法变得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显然就需要对“理性”概念本身给出一个独立界定,因为要不然就无法具体地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理性的,或者要不然就会得出一些有悖于直观的判断。在上述例子中,因为精神沮丧而未能回应特定的理性考虑的人必定是无理性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也许我们可以像科斯格尔曾经尝试的那样,通过与理论理性相类比,用普遍性、充分性、无时间性以及非个人性之类的特点来表征或界定“理性”。①参见Christine Korsgaard: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reprinted in Kieran Setiya and Hille Paakkunainen:Internal Reasons:Contemporary Readings,The MIT Press,2012,p.61。但是,在实践推理上满足这些要求、但仍然未能回应某个理性考虑的人必定是实践上不合理的吗?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回应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考虑,但其实践推理并不满足上述特点,那么他就必定是不合理的或无理性的吗?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给予它们一个明确回答,而是要暗示说对它们的回答至少是有争议的,而且这种争议本身就具有规范含义。如果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行径部分地是立足于其种族主义偏见,而他自己没有威廉斯意义上的内在理由来纠正或消除这种偏见,那么我们倒宁愿用其他的评价语言来评判其行为。我们或许认为,希特勒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不能对我们大多数人当作道德理由的东西做出实践承诺;但是,不能做出这种承诺也许不是实践推理的失败,而是因为他的动机系统缺乏做出这种承诺的根本依据——他看不到按照我们所说的道德理由来行动的要旨。
康德对工具理性原则的表述有助于澄清在这里所碰到的一些困惑。按照这一表述:“不管谁意愿目的,(就理性对其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论)也意愿对其行动来说绝对必要且在其能力之内的手段。”即使我们在这里把康德所说的“意愿”解释为包含了承诺的要素,我们也必须特别注意他所提到的限制性条件的重要性。就手段而论,他所提到的那两个限制性条件是我们可以从对工具合理性原则的“传统”解释中推导出来的,因为从工具合理性的观点来说,欲望目的当然就意味着欲望对于实现目的来说必要的,且行动者能够采纳的手段。如果一个行动者已经承诺要实现某个目的,但并非出于自己的过错而对目的—手段或者对欲望的对象(即那个目的)持有错误信念,那么他在这方面的失败大概算不上实践合理性的失败。另一方面,如果他本来就能对欲望的对象以及目的—手段关系持有正确信念,却在这方面出了错,那么,就他(在回顾中)仍然承认他确实想要实现那个目的而论,他的错误来自他在认知上的缺陷,但这好像也不是实践合理性的失败。进一步,如果我们把这些情形都排除,那么,在我看来,似乎可以合理地设想的“意愿目的,但未能意愿行动者有能力采纳的必要手段”的唯一情形就是广义上的意志薄弱的情形——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有某个其他的欲望诱惑行动者偏离了他原来承诺要实现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不能把自己对“实现目的”的承诺坚持到底。然而,甚至在这种情形中,认为行动者的失败就在于“理性未能对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是一个过于笼统而未能阐明失败的具体原因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一时懈怠或懒散而未能去做他原本打算去做的事情,那么他的失败来自他在品格方面的缺陷,例如缺乏坚韧的美德。在这种情形中,只有当他原本打算去做的事情有助于促进他已经承诺要去追求的某个长远目标时,我们才能说他在品格方面的缺陷也产生了一种实践不合理性。相比较,如果一个人是因为可以理解①在这里,这个说法旨在表明:若有必要,他在事后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辩解他当时为什么未能采纳那个作为必要手段的行动。的精神沮丧而未能采纳他有物理能力采纳的必要手段来实现他所承诺的目的。那么,直观上说,似乎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指责他是实践上不合理的。当一个人出于可理解的缘由而放弃追求他此前承诺要实现的目的时,他其实并未违背工具合理性原则。因此,意愿目的意味着意愿在那两个限制性条件下所说的手段,这是人类能动性的一个最低限度的构成性条件——只要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就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若是这样,康德在其限制性条款“就理性对我们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论”中所说的理性就仍然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这个原则并承诺要按照它去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是实践上合理的——对这个原则的承诺构成了我们的实践合理性的本质方面。而且,这个原则本身也不蕴含实践合理性的其他要求,尽管它可能要求某些认知美德,以确保我们能够对目的以及目的—手段关系具有正确信念。
我已经暗示说,我们的理性本质来自对某些根本原则的认识和承诺,例如工具原则。我这样说是为了强调实践理性的构成性特征:我们不可能先于我们对某些根本原则的认识和承诺而具有我们称为“理性”的那种东西,尽管一旦我们已经承诺和采纳了这样的原则并按照它们去行动,由此被构成的理性也可以进一步发展自己并有可能取得一种相对自主或独立的地位,因此相对于我们心理结构中的其他要素(例如日常意义上的欲望)而具有某种权威。但是,我们首先想要知道我们如何可能认识到某些原则并对它们有所承诺。在工具原则的情形中,这个问题并不难以回答——实际上,休谟自己提供了一个在我看来最可理解的回答。首先,让我们承认我们寻求满足自己欲望的倾向是内在于我们作为人的本质的,甚至是所有动物都分享的一个本质特点。正是由于我们的本性的这个原初特征,我们可以理解对目的的欲望为何可以传递到对实现目的的必要手段的欲望。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对于一切寻求欲望满足的动物来说,这无须是一个哲学上特别深奥的事实。在很多情形中,我们的目的—手段信念是广义上的因果信念,因此我们对具体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和反思会让我们逐渐形成“手段”以及“正确手段”的概念。随着我们的欲望系统变得更加复杂以及工具性欲望的出现,我们对目的—手段关系的推理也会变得更为复杂,例如可以包含威廉斯划归在“准休谟式的模型”这个说法下的那些实践推理。①参见Bernard Williams:Moral Lu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04。当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尝试采取的行动未能满足一个目标欲望时,我们可能就会去反思我们对这一行动所做的慎思或推理。我相信正是这种反思导致我们对工具原则有了明确的表述和承诺:假若我们确实想要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就得接受工具原则并对目的—手段关系以及有关欲望具有正确信念。在这里,我使用“确实想要”这一说法,而不是“承诺要”这样一个更加康德式的说法,是因为寻求满足欲望的倾向无疑是人性中一个原初的、至少在哲学上(如果说不是在生物学上)无须进一步说明或论证的特征。相反,对我们的理性能动性的任何进一步的要求或理解都必须把这个本质特征当作一个说明上的出发点。类似地,与意志软弱的某些有争议的情形相比,我们之所以倾向于认为,已知地和自愿地采取一个与自己的最佳利益(或者对这样一个利益的深思熟虑的判断)相违背的行动是实践上不合理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样一项利益有着实践承诺,而这样一种承诺很有可能是按照上述方式从我们对与此相关的目标(例如个人健康或幸福)的欲望中发展而来的。相比较,一个行动者是否会因为没能按照某个道德规则去行动而受制于“实践不合理性”的指责,取决于他是否认为他有理由以及相应的欲望承诺要服从那个规则。如果我们不是在谈论就此而论的道德,而是在谈论一个社会中的道德规则,那么我们大概无须使用实践合理性的语言来谈论一个人在服从某个特定的道德规则上的失败——这种失败无须像科斯格尔所说的那样意味着一个人因此“不再是人”①参见Christine Korsgaard:The Sources of Nomrativ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特别是第四个演讲。:基本的道德意识可能是我们作为人的实践同一性的一个构成要素,但特定的道德规则无须具有这个特殊地位,因为对某个特定的道德规则(或者对这样一个规则在特定情况下是否适用)的怀疑无须成为实践合理性失败的一个标志,反而有可能是实践合理性的一个体现,因为对特定的道德规则及其可应用性的理性反思恰好是我们理性能力的一个本质方面。
三、欲望、理由和承诺
在试图把合理性的语言提升到一个独一无二的最高地位时,科斯格尔大概想要强调理性对于我们日常所说的欲望或激情的绝对权威。但是,即便她所设想的理性能够具有这种地位,对于个别行动者来说,它是通过在实践上承诺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规范理由和原则而具有这种地位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具有规范权威的理性本身就是由这种承诺构成的。但是,即便作为一种精神才能的理性在我们的心理体制中占据一个独特地位,为了正视我们在慎思和选择活动中所体验到的各种复杂性,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个意义上的理性对规范理由和原则的实践承诺与我们的心理体制中的其他要素不可分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如果具有规范权威的理性就是用我所暗示的那种方式被构成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我构成”),那么把理性的权威固化就不仅是危险的(比如说,在阻挡了理性能力的自我改进的可能性的意义上),而且也没有忠实地反映和公正地对待我们进行慎思、做出选择、具有承诺的经验。当科斯格尔认为只有理性承诺才能构成是辩护的根据时,她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她之所以断然否认欲望本身能够为行动提供辩护,根本上说是因为她把欲望一般地理解为行动者的前理性的、消极地感受到的状态。现在我想简要地表明,一个合理的康德主义不应该像她那样把欲望和理性承诺绝对分裂开来。①下面的分析得益于如下论述:Barbara Herman:Making Room for Character,in Stephen Engstrom and Jennifer Whiting:Aristotle,Kant,and the Stoics:Rethinking Happiness and Du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6-62;Paul Hurley:A Kantian Rationale for Desire-based Justification,Philosophical Imprint,2001,1(2)。值得指出的是,科斯格尔其实意识到了与我下面要发展的思想很相宜的一个观点:“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即合理性是人类行动者能够具有的一种状况,但不是我们已经处于的一种状况),某些以理性的观念为核心的伦理理论最好被认为确立了品格的理想。按照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具有良好品格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来回应自己可得到的理由,他的动机结构是为了理性的接受性而被组织起来的,因此理由就可以按照恰当的力量和必然性来发挥动机作用”(Korsgaard:Skepticism aboutPracticalReason,reprintedinKieranSetiyaandHille Paakkunainen:Internal Reasons:Contemporary Readings,The MIT Press,2012,pp.62-63)。
休谟主义的核心就在于把广义上的欲望设想为行动的本质上具有动机效应的力量。因此,从一个休谟式的观点来看,我们也需要从欲望的“逻辑”或动力学中来寻求把人类生活中规范性的东西产生出来的根据以及我们对规范理由和规范原则进行反思认同的动机。一个不一致或者不融贯的欲望系统会对我们产生压力,要求我们去审视我们究竟在哪里出了错。这是关于人类心理的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欲望本身并不具有接受理性考虑的倾向,我们就无法指望消除在欲望系统内部存在的张力或冲突。当这种张力或冲突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时,我们的欲望系统就会崩溃,因此我们就会冒险丧失我们的能动性的一个本质方面。不过,尽管某些欲望确实是以一种前反思的方式(不是通过有意识的理性慎思活动)到达我们这里,但是,不是所有的欲望都具有这个特点,正如赫尔曼所指出的:
一个成熟的人类行动者的欲望,除了包含一个对象的观念外,往往也包含对象的价值的观念,因为对象的价值是由它与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的适应以及它自身的满足来决定的,因此其自身就与……实践理性的原则保持一致。我们可以说,如此设想的欲望已经被置于理性的范围内,或者本身已经被理性化,或者,就一个行动者的欲望系统已经逐渐用一种回应理性的方式发展出来而论,她至少在这些方面有了一个理性行动者的特征。
通过诉诸约翰•麦道尔对知觉经验和知觉信念的论述①参见John McDowell:Having the World in Vie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说明欲望(甚至前反思的欲望)为什么往往涉及理性承诺的某个方面。麦道尔的论述以威尔弗雷德•塞拉斯的一个思想作为其出发点: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具有概念内容的东西才能为信念提供辩护,那么,就知觉经验能够为知觉信念提供辩护而论,我们必须假设知觉经验至少已经被部分地概念化。②参见Wilfrid Sellars:Empiricism and Philosophy of Mind,reprinted in Sellars:Science, Perception and Reality,Routledge,1963,pp.127-196;Wilfrid Sellars:Science and Metaphysics:Variations on Kantian Themes,Routledge,1968。对于塞拉斯来说,关键的问题显然是要说明知觉经验如何可能已经被概念化。按照麦道尔的分析,尽管在知觉经验中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以一种前概念的、前理性的方式被给予认知主体的,因此其本身不可能担当辩护作用,但对其内容的理性承诺能够产生信念。这种理性承诺的可能性就在于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已经具有概念能力对知觉经验的内容进行理性操作,但是,为此我们就得假设知觉经验本身已经具有易于接受理性操作的倾向。换句话说,对于正常的人类认知主体来说,当我们具有知觉经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是在一个理由空间中来具有知觉经验并因此能够对其内容做出判断。当然,知觉本身可以是可错的,因此我们对一个单一的知觉经验的内容的判断也可能出错,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整个认知活动是在一个理由空间中来运作的,我们可以按照自己已经具有的其他信念来纠正这样一个判断。在实践领域中,欲望的地位就类似于在理论领域中知觉信念的地位:在成熟的人类行动者这里呈现出来的欲望,用赫尔曼的话来说,已经是由塑造他的知觉领域或慎思领域的理性原则来“规范化”的欲望。因此,尽管欲望可以是一种前理性的状态,但是,对于成熟的人类行动者来说,它们能够具有接受理性考虑和理性批评的倾向。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具有一个欲望本质上涉及把它的内容经验为在某个方面是好的或值得欲求的,并因此把其目标看作意向行动的合适对象。
赫尔曼之所以对欲望提出这种理解,其目的是要表明,一个合理的康德主义者无须采纳那种把欲望与理性对立起来的模型。实际上,在她看来,假若我们采纳了这个模型,我们也就无法对道德品格的发展提出一个合理说明:我们的欲望之所以能够回应理性考虑和理性要求,就是因为它们已经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以某种方式“分有理性”。因此,赫尔曼认为,“我们的发展原本就是回应理性的,而不是遵循理性的,这是一个关于具有欲望的理性存在者的本质的主张”。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只要我们接受了对欲望的这种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无须把一种合理的休谟主义和一种合理的康德主义对立起来。①在这里,就伦理学而论,所谓“一种合理的休谟主义”,我主要指的是以休谟自己的思想和威廉斯的内在理由概念为主线发展出来的一种观点,正如我在本文以及《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试图发展的;所谓“一种合理的康德主义”,我主要指的是赫尔曼(以及一些其他的康德学者例如Allen Wood)在本文提到的这篇文章以及其他著作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康德式的伦理学,例如Barbara Herman: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Barbara Herman:Moral Liter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休谟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充分认识到并在理论上尊重欲望及其动力学在人的能动性中的本质地位;不过,至少在休谟本人那里,这仅仅是这种观点的起点,因为休谟实际上试图说明规范的东西(其中包括康德意义上的理性)怎么能够通过对一个社会观点的承认和接受、从我们的原初的、具有欲望和激情的感性本质中发展出来。在休谟这里,工具原则之所以能够在构成我们的理性能动性方面占据基础地位,不仅因为它是我们只要行动就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而且也因为:只要我们需要与他人一道生活,这个原则也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反思的起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休谟这里,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愿望就是规范意义上的理性的一个基础和来源。在对人类为了共同生活而必须接受的根本原则的反思性的认同和修改中,我们也在不断地改进和重塑我们原来具有的欲望,乃至我们的品格。我们对所谓的理性原则进行反思认同的动机就存在于我们本来就具有的欲望系统中,但我们无须认为那个系统具有一个完全抵制外部世界的冲击和理性影响的地位,不仅因为它自身就包含了休谟称为“冷静的激情”的那种东西,一种在合适的条件可以让我们承认和接受休谟所说的“一般观点”的动机和根据,而且也因为,若没有正确的认知信念,欲望就不可能成功地寻求自身的满足。但是,只要一个人已经生活在社会世界中,正确的目的—手段信念就不仅涉及事实问题,也涉及规范理由和考虑。然而,对于休谟主义者来说,与这些理由和考虑相关的要求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无条件的有效性的绝对命令。休谟主义究其本质而论强调人在世界中的包嵌性存在。因此,当它所倡导的那种实践反思具有强烈的语境主义特征时,它也能够提供思想资源来抵抗把任何规范权威抬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做法。②普莱斯最近已经对实践推理提出了一种语境主义论述,见A.W.Price:Contextuality in Practical Reason,Clarendon Press,2008。
参考文献
[1]DANCY J.Practical Real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KORSGAARD C.The Normativity of Instrumental Reason[C]//CULLITY G,GAUT B.Ethics and Practical Reas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3]KORSGAARD C.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C]//SETIYA K,HILLE P. Internal Reasons:Contemporary Reading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2.
[4]KANT I.Groundworkfor Metaphysicsof Moral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5]HERMAN B.Making Room for Character[C]//ENGSTROM S,WHITING J. Aristotle,Kant,and the Stoics:Rethinking Happiness and Du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本文是笔者《休谟主义、欲望与实践承诺》的一个更加完整的版本,那篇文章原来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第37卷第21期。
①徐向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政治哲学、早期现代哲学以及分析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