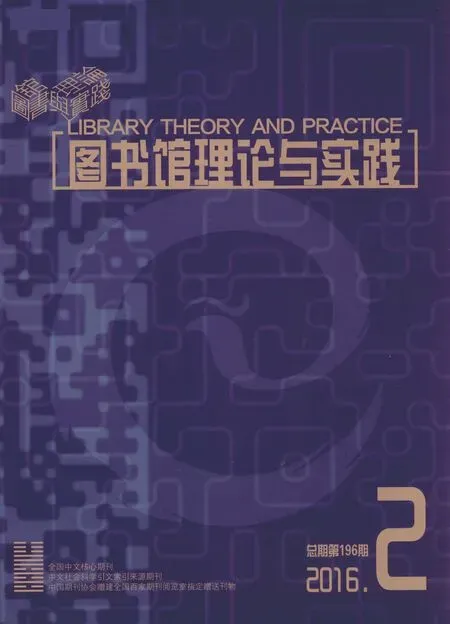试论新出“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借鉴史料批判研究模式的讨论
2016-02-1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杨 博(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试论新出“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借鉴史料批判研究模式的讨论
杨博1,2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新出楚竹书“语”类文献,既为文献史料稀缺的先秦史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又由于其本身主题、人物、事件等重见叠出的现象需要进行考辨的工作。作为一种独特的史书体类,“语”类文献是当时流传的存故实、寓劝诫和助游谈的材料。一方面以作史素材被成文史书如《左传》等所吸收,另一方面以助游谈的材料为诸子书所吸纳。近年来盛行的史料批判研究,可以作为考量“语”类文献史学价值的一个重要准则。通过探求“语”类文献的构造与执笔意图,对于去除附着于其上的“再回忆”与“再创造”等因素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将“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简要归纳为对先秦文献史料“真”“伪”的审慎认知、对春秋战国史学著述的发展具体了解、对先秦学术思想面貌的整体把握及对其记述的先秦史事的批判认识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语”类;史料批判;战国楚简;史学价值
《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中期楚庄王问傅太子之道时,大夫申叔时列出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九种所要“教之”的文献。一般认为,“语”书作为一种文献分类在春秋时期即已广泛存在,传世文献中《国语》《新序》《说苑》等均属此类体裁。以《国语》为例,《汉志》将其与《左传》并列收入“春秋家”,刘知几将其列为“六家”之一,“语”书作为一种重要的史学体裁已极显明。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证明了“语”在春秋时期的客观存在。近年来,以上博楚简为代表的新出文献中也发现有大量“语”类文献,“语”类也由此深为学界所重视。如李零先生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语类或事语类的古书非常流行,数量也很大。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种,这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1]
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种,这与历史学求真求实的本质必然存在矛盾。与之相应,学界历来有史料考辨的传统,如刘知几曾将史料分为“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1984年,王玉哲先生主要以时间为序将中国上古史的史料分为四大类。[2]具体针对新出文献而言,陈伟先生亦曾指出其存在时间上的差异。[3]史料的分类,时间是第一要素,而且这种强调形成时间的分类,存在按史料性质排队,条理清楚且简明扼要的优点,使我们可以很轻易地通过史料的性质、形成年代判断史料的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具有指导价值。但同时需要留意的是,强调形成时间的分类似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上述“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种”的史料考辨问题。这似需要引入或借鉴新的理论模式来帮助我们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史料批判研究又称“史料论式的研究”,是近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界青年研究者中比较盛行的一种研究范式。其定义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4]如孙正军先生所总结,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相比,史料批判研究并不满足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史料是怎样形成的?史家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史料的性质又是什么?[5]笔者以为上述思路似可为我们探讨新出“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提供借鉴和帮助。
一、战国时期“语”类文献的内涵
在讨论“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之前,需要先对战国时期流传的“语”类文献的内涵以及与相关文献的区别等问题作一简单说明。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墓地中出土有中山王鼎(《集成》02840),其铭文在文首言曰:
“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旃,宁溺于渊。昔者……”其后即用三个“昔者”指出了三件过去的史实和教训,分别是中山国王年幼继位事,燕王禅位于子之事以及越克吴事。其中又用“寡人闻之”另引用一句格言:“事少如长,事愚如智。”所谓“语不废哉”的“语”,不仅仅是指铭文所引用的“寡人”所闻的两句格言,而且还应该包括“昔者”所发生的三件事情。整篇铭文,就是节录“语”的内容来进行说理。这样的“语”,既有格言的内容,也有史事的内容,不仅可看出当时“语”类文献的流行,亦可看出“语”类文献所包含的特质。
《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的言论,有“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的说法,韦昭注:“语”为“治国之善语”。《左传》文公六年有“著之话言”,孔颖达疏曰:“著之话言,为作善言遗戒,著于竹帛,故言著之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国语·周语》亦有“庶人传语”的说法。《礼记·曲礼上》还有“史载笔,士载言”的记载。无论是“古之王者著之话言”的“善言遗戒”还是“矇诵”“庶人传语”“士传言”“士载言”,经过上下两个渠道的采择,这些“治国之善语”都可能通过“著于竹帛”而流传下来。一方面保存了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珍贵资料,另一方面成为时人以至后人常用以劝诫的材料。
“语”与“言”“传”“说”等同样表示话语的词汇,先秦时期都有可能视作记述历史故事或传闻的文本,或是格言汇编。但是就细微处,“言”“语”之间也存在着区别,不免有所混淆。特别是战国后期以后,“传”“说”都被用作解“经”的文体,纳入经学体系,其区别就更为显著。
《说文·言部》:“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可见不同于“言”,“语”具有议论的特点。《诗·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直接的诉说是“言”,相互论辩就是“语”,这种理解与《说文》完全相同。孔颖达正义:“‘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指出“言”“语”存在着说话者人数上的不同。《礼记·杂记》有:“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郑玄注:“言,言己事也。为人说为语。”孔颖达正义:“谓大夫、士言而后事行者,故得言已事,不得为人语说也。”居丧之时可以“言”却不能“语”,显示出在表达上“言”“语”存在着主动和被动的差别。《左传》庄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学者即曾指出:“主动说话叫作‘言’,与人相对答才是‘语’。”[6]此外,《国语·鲁语下》记载:“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与之言,弗应。”“与之言”清楚地指明是季康子单方面的主动说话。可见,“语”和“言”的差别是存在的。当然,这种区别也并非绝对。
“传”“说”也可被视作述古讲史的一种文体,如《墨子·非命中》载:“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此处的“于传有之”可见这种叙述传闻故事的文体也可称为“传”。同样的例子还见于《墨子·明鬼下》: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诸侯传而语之曰:“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其憯速也!”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此处“说”明显指这个传闻故事。《史记·五帝本纪》亦有:“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里的“传”、“说”、“语”皆可视作是记述历史故事或传闻的文本,或是格言汇编。但是,可以看出,“传”与“说”更多的是与诸子经传联系在一起的。“传”“说”虽然都是解释“经”的文类,二者也存在区别:“说”“传”处在学术传授的不同层次中,“传”是对“六艺”经义直接作的阐释,而“说”是为解释“传”或诸子理论而产生的“师说”。[7]“说”“传”的区别可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形式上,“说”与“经”是分开的。如《韩非子·外储说》这种标准的“说”,经的部分和“说”的部分是分开的,“说”更像是为阐发义理的“经”而准备的资料库,《说林》之“林”,《说苑》之“苑”的命名,或正有这种含义。而“传”则是与“经”文合在一起的,《史通·补注》:“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传字或作傅,读曰附,谓附著。”如《韩诗外传》即先言故事或阐述义理,而后引出与此段“传”义理相通的《诗》句。
第二,就《汉志》来言,“六艺”均有“传”,而非皆有“说”。此外,以《六艺略》为例,其叙述一经的各种文献顺序是:经→故→传→(记、说、章句)。由此“说”在《汉志》存录等级中的地位要低于“传”,同于“记”与“章句”。在这个序列中,“说”可以敷衍“传”,而“传”却不能解释“说”。对此《汉书·五行志》在解释《尚书·洪范》中亦提到的“五行”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经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说曰:“木,东方也。……是为木不曲直。”
明了“语”与“言”“传”“说”等同样表示话语的词汇的区别以外,还需要讨论“语”与“书”“子”等文献的区别。“语”与“书”可分别以《国语》和《尚书》为例。白寿彝先生曾指出,《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书,所记的言多是贤士大夫的谠言高论,跟《尚书》记言之限于官文书有严格的区别。[8]而从《尚书》与《国语》之间“言”“语”的细微差别来理解:《尚书》之“言”大多是君王对臣下所发布的言论,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些言辞基本是独白,话语的指向也是单向性的,在这个层面上王者的“主动”说话,正与左史记“言”“言为《尚书》”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国语》之“语”更多的是对当政者的一种委婉警告,“语”采用对话的形式,记录了大量辩论性的内容。“语”者借助各种论据,使用多种论证方法,希冀与执政者成功沟通,使之接受自己的意见。《尚书》所记的言语局限在帝王或是重要大臣的范围之内,听众是臣民;《论语》除了孔子的教诲外,只有少数贤弟子的言语,“语”的直接对象多是门下弟子。《国语》记载的言语不能是演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者社会地位降低决定的。[9]
接下来需要讨论“语”“子”的区别。不得不承认,“语”类文献本身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即是由诸子所创造出来的(这也是“语”类文献需要鉴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此而言,“诸子百家语”的说法是有其道理的。但是站在史料考辨的角度,以记述先秦史事为主的“语”和专在表达诸子政治思想的“子”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当然,“语”书同样可以表达政治思想,“诸子”也或被称为“诸子百家语”,但是二者之间在外在表现形式和性质上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子”类文献的表现形式多为师徒问答,或君王诸子问对,而“语”类文献在表现形式上与诸子无关。当然,“语”类文献也会表达某些诸子政治思想,即“语”类文献不是以诸子如孔子等人的事迹展开的。其次,“语”类文献多为叙述性语言,旨在通过讲述一件或数件史事来说明一定道理,而“子”类文献全文多是议论之辞。第三,李零先生曾就子类文献的“述”古指出,“这些诸子书,往往都是‘借古喻今’,具有寓言的形式,利用‘古’作谈话背景。”诸子书的谈资除了借用“世”“书”外,李零先生认为主要来自“语”类作品,儒家喜欢讲唐虞三代故事,墨家喜欢讲夏禹故事,道家喜欢讲黄帝故事,来源就是这类传说。[1]就此意义上讲,“语”类文献相当于一个资料库,所以经常为诸子所取材。这也就是诸子百家之书也可称“语”的主要原因。
因此,对于“语”类文献有很多互见于诸子文章的现象:它们或是同源材料,或是由更古之语类材料被诸子锻炼改造,后又被从诸子著作中抽离出来的。语类文献的这个流传模式为:语类材料→熔铸入诸子文章→从诸子文章中抽离(新的语类材料)。从这个层面讲,诸子书中存留的故事也可为我们所取作为史料以探讨其研究史实的价值。但需要留意,诸子书记录的人与事,可能与事实拉开了一段距离,其故事性要远胜于记录性,是一种再回忆与再创造。在这样的书中,回溯的事实取代了真正的事实。所以也可以说,在“语”类为诸子提供这样一个交流背景的同时,诸子也以自身的创造性不断丰富着“语”的内容。
综上述,“语”是战国时流传的存故实、寓劝诫和助游谈的材料。除谚语外,其最显著之特征即在于“故事”性。这里的“故事”性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每个篇章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故事,基本是由故事背景+故事经过+故事结果组成,如上博竹书《昭王毁室》,开篇“昭王为室”为故事背景,“一君子丧服……”为经过,结果是“因命至(致)俑毁室”。
其二,也有部分篇章会引用过去明君圣王的典型事例,甚至开篇即言明其讲古的性质,如清华竹书《赤鸠之集汤之屋》开篇云“曰故……”或在篇中显示这一点,如上博竹书《容成氏》讲“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正如“书”类文献在先秦文献中曾多次被征引作为论据的情况近似,“语”类是作史、论说的基本素材之一。如清华简《系年》第九章记有晋襄公卒后,灵公时年少,晋人欲立长君公子雍,“襄夫人闻之,乃抱灵公以号于廷,曰:‘死人何罪?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将置此子也?’”。与之相应,《左传》文公七年曰: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其内容不仅与《系年》互为印证,史料取材当也以“语”为主。这些可以较明确断定为“语”类文献在史书中的应用的情况,似也可以作为“语”类文献的衍生加以讨论。
二、史料批判研究的价值
如上所述史料批判研究的模式对于同样史料奇缺、且旧说成熟的先秦史研究领域亦有一定的适用性。如在明确战国时期“语”类文献所包含内容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新出“语”类文献及其衍生所提出的对史料考辨的新要求。上文已述“语”类的特质是同一人物、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种。笔者将其推广为与新出“语”类有关涉的史事记载,存在同一主题、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等重复情况,且这些情况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异。这就需要考虑“语”类史书单篇与整体的撰述背景、意图等方面的因素。下文拟从主题、事件、人物的重复等三方面举例说明其价值。
其一,是同一主题的重复,如上博简《鲁邦大旱》《柬大王泊旱》《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以及《竞公疟》等篇的共同主题,则是由于疾病、旱魃等神罚,或日食等异象的降临,然后藉由国君的反省,“为善政”即可解除或规避灾殃。[10]而且《鲁邦大旱》中“哀公问孔子”的“母题”,由《绎史·孔子类记一·哀公问》可知其材料分布于《论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史记》《孔丛子》《孔子家语》《说苑》《新序》等多种典籍之中。
其二,是同一事件的重复,如上博竹书《竞建内之》追述殷武丁祭祀时,有雉雊于彝前,商王召祖己询问缘由。祖己对以先代贤君面对失政而采取求诸鬼神与修善政的措施,如今若要借祭祀求福,则需要烹煮此雉,祭祀完毕后修先王之法。高宗从之,其结果是“服者七百邦”。此事与《尚书·高宗肜日》篇相似,均是祖己针对商王祭祀时发生的异事进行评论,故有学者认为简文是编纂者在理解《高宗肜日》基础上所作的发挥。[11]就《高宗肜日》所记内容看,其基本反映了殷代的史实,惟此篇文字如“天”“德”等是周初诰命中的习惯用语,可知此篇成书时代当不早于周初,应系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商书”中所记之史实。[12]亦曾有学者推知《竞建内之》与《管子》中《霸形》《戒》两篇内容相似,只是所涉人物与事件背景有很大差别。[13]清华竹书中亦有“语”类《赤鸠之集汤之屋》篇,讲述有鸟“赤鸠”落在商汤的屋顶上,被商汤射获。后来商汤有要事外出,临行前嘱咐小臣伊尹将这只“赤鸠”烹煮作羹的故事。
其三,是同一人物的重复,清华竹书《赤鸠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均涉及汤相伊尹(小臣),加上《尹至》《尹诰》,清华竹书中目前已发表5篇与伊尹相关之文献。此外,上博竹书《容成氏》中对伊尹的事迹也有反映。[14]《汉书·艺文志》“道家”下有“《伊尹》,五十一篇”。班固自注:“伊尹,汤相。”现已佚失不存。学者亦曾注意到战国文献中存在伊尹学派之问题,[15]如李零先生指出战国时期有依托商周故事讲“阴谋”的一派,《汉志》将其列入道家,它以《太公》为代表作,《伊尹》等是同类著作,《鬼谷子》是其余绪。银雀山汉简、八角廊汉简中发现的《六韬》,其实部分应属于《伊尹·九主》。[1]《汤处于汤丘》简文有“以设九事之人,以长奉社稷”之语,或与《伊尹·九主》“事分在职臣”有关。[16]楚竹书中伊尹故事的重复出现,说明了对某一典型人物的重复记述是战国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
按三者的区别,同一主题的重复指的是随着说话者的需要,虽将故事叙述的模式进行了变化(如将旱灾的发生地变为有鲁、有楚),但是其叙述的主题仍是一致的(“为善政”即可解除或规避灾殃)。同一事件的重复则指的是同一故事被处在不同时代与出于不同论说目的的说话者所不断征引(如商人祭祀时有雉雊于彝前)。而同一人物的重复则是古史典型人物在多种历史记述中不断重复的现象。
从这些重复的情况看,一部分记述大致相同,其余很大的一部分则存在歧异。对于存在歧异的内容,仅按照时间要素对其进行史料层面的考辨,似不能很好地分辨出具体的差异。而史料批判研究于此则显现出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其对史传书写模式的讨论,关注史传中那些高度类型化、程式化的文本构筑元素。[5]笔者推而广之,似可将其理解为历史叙述中的套语、典型人物事迹和著名事例的重复等多方面因素。惟需要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对这些或本诸现实、或由史家新造的因素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学者曾经讨论清华简《芮良夫毖》中含有大于55%的套语成分,反映作者创作时多处都是拿固定的语句或结构来套用。[17]后者有关人物事迹、著名事例等方面的认识,对于目前只能认定成文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语”类文献的考辨,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对于这些文献中所反映的史实及其与传世记载的差异问题,学者也作了大量的研究,注意到简文与传世文献叙事的差异,既和体例有关,也和简文的写作意图有关,揭示出“语”类古书意之所在不是记史,而是说理,劝导读者接受篇中讲述的道理,以资鉴戒。语书“有时言辞之首,或书史以交待其背景。言辞之末,或附史事以为之征验,皆无非是增加其说理的效果而已”。[18]尽管至战国时,语书亦杂采事件,但仍保留着语书的特征。虽然如此,语书中的记事仍然是为记言服务的。[19]
所以,对于这些差异恐怕还需要从编纂过程、用途来理解,而不能直接据之以反对传世文献对某些史事的记载。笔者上文引述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时有所谓“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一项,以上博简楚国故事来看,如《郑子家丧》为楚庄王没有在郑子家弑君当年就发兵讨郑寻找理由、《昭王毁室》之赞扬昭王德政、《申公臣灵王》的表彰楚灵王的政治风度等,都会作为彰显“先王之明德”的材料为贵族子弟所学习,正是申叔时所论的题中之义,其反映的史事似未必一定会是真正史实,先君先王的美好形象确是当时年轻子弟学习的典范。
三、“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
上文以“同时代”“类”为标尺,将“语”类文献从新出文献中析分出来,而对于“语”类文献本身,则需要具体借鉴史料批判研究中对史传书写模式的认识进行单篇、几篇甚至整体的具体考辨。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似可对新出“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作一简单的归纳总结。
第一,对先秦文献史料“真”“伪”的审慎认知。大量“语”类文献在主题、人物、事件上的重复现象,自明郎瑛起即对“秦汉书多同”这一现象加以注意,其后章学诚的“言公”、余嘉锡的《古书通例》及裘锡圭先生《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等相关论述,“使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大多数典籍是很难以‘真’‘伪’二字来判断的。”[20]“语”类文献的重复性印证了这一判断。这就为先秦史料的考辨工作提供了审慎的前提。
第二,于春秋战国史学著述的发展。一方面,新出“语”类文献多单篇流行,同时亦有意识整理、蒐集同类文献。如上博简“语”类文献,多数单篇别行以外,也有《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等两篇合抄的现象。特别是郭店简《语丛》(一)至(四)更是体现出时人有意识地整理同类文献的过程。而学者针对简背划线的研究,指出清华简《赤鸠之集汤之屋》当接于《尹至》《尹诰》之前,三篇竹书原编于同卷。[21]其原因当是时人将同属伊尹故事的文献汇集整理在一起。另一方面,上举上博简《竞建内之》追述殷武丁祭祀时,有雉雊于彝前,商王召祖己询问缘由等事。上即可与《尚书·高宗肜日》篇相关联,下则可与《管子·霸形》《戒》相联系,为我们提供了“语”类自“书”类取材继而最为资料库被“子”类涵化运用的实例。此外,上举清华简《系年》第九章、第十四章中与《左传》《国语》在“语”上的相似性,则可看出“语”书作为基本素材为史书所取用的情况。凡此对于我们了解春秋战国史学著述的发展情况提供了极大帮助。
第三,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整体把握。一方面,上揭“秦汉书多同”的情况反映的是在为天下统一构画蓝图的一致政治目标下,诸子虽各抒己见,但由于关涉目标相同,则不可避免会出现言语、思想上的雷同。“语”为“子”中的这些雷同提供了材料支撑。这些雷同的出现,促使人们在思考先秦学术思想诸问题时,不得不从整个思想领域的问题整合考虑。学者已注意到对于先秦思想的研究似需要从一个整体来综合考察。如刘泽华先生早年在针对先秦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曾提出注重“共识”的研究手法,[22]即“注意那些共同的资源、共同的话题,不拘泥、纠缠于学派具体的判定区分,将研究对象本身作更为细化的分析”。以色列学者尤锐(Yuri Pines)在研究战国时期思想动态时,关注的就是战国思想家的共同遗产,强调的是战国思想家共同关注和普遍认识的理念,从而界定出当时诸子等人共同关注的话语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战国时期思想变迁的模式。[23]
第四,对其记述的先秦史事的批判认识。文献的本身即反映出文献流传、整理等情况,文献的应用也会直接呈现当时的学术思想状况,这两点可以通过文献本身“类”的因素来加以析辨。而对于文献中所记述的先秦史事,则需要通过时间——“同时代”和史料批判的方法加以综合考量。特别是成文年代并不能很明显地拉开时间距离的“语”类文献,史料批判倒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通过上述准则,“语”类文献于先秦史事研究的价值,应该说首先体现在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后世文献(也包括部分当时文献)对于典型人物、事迹所进行的加工与再创造。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语”类史料虽不排除有伪托的可能,但是其史事当有所本,应该依托于一定史迹,故其史料的可靠程度和价值也相对较高,不能一概否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故事的叙述主干应该是真实可靠的,所谓的“加工与再创造”,笔者更多的以为其体现在一些具体细节的处理上。再以《容成氏》为例,其所记古史圣王事迹与先秦历史密切相关,禹、桀,汤、纣,文、武的世系清晰可靠。此外,其叙事主干,如汤伐桀,武伐纣也没有大的问题。就一些细节问题来说,则既有事实又有所演绎,如著名的纣为酒池事,普见于《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论衡》《韩诗外传》《史记》等众多的古籍记述,但战国文献多见“酒池”之名,并没有细节方面的记述。《尚书·酒诰》:“在今后嗣王……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02837)铭文有:“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矣。”“酒池”之说应有商末殷人酗酒的史实依据,但明显带有演绎色彩。故子贡评价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综上述,借助有利的抓手,新出“语”类文献于先秦史学的研究价值得以具体展现,特别是通过史料批判研究,将史家新造的因素有效地从典型事例上剥离,从而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四、小结
按《国语·楚语上》记载“语”类在春秋战国时期本身已独自成类,这一点也日益得到了新出文献的证明。作为一种独特的史书体类,“语”书是当时流传的存故实、寓劝诫和助游谈的材料,一方面,作为作史素材为成文史书。如《左传》等所吸收,另一方面,作为寓劝诫、助游谈的材料为诸子书所吸纳。其与“言”“传”“说”等同样表示话语的词汇存在区别以外,与“书”“子”等文献也有较为明显的不同。时间是史料分类的第一要素,所以“同时代”的史料为治先秦史者所重视,而对于成文年代并不能很明显地拉开时间距离的“语”类文献,史料批判研究中对史传书写模式的讨论值得借鉴。通过对“语”类文献所体现的再回忆与再创造的辨析,相当的记述歧异可以得到圆融的解读。通过“类”“同时代”及史传书写模式三把抓手,“语”类史料可以对我们在史料学、史学史、学术思想史及先秦史事等众多研究领域起到补史、证史的重要作用。
通过史料批判模式可以深入挖掘“语”类文献的史学价值,也提醒我们一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对于其他“类”的新出文献的适用性,如叙事学中叙事角度、方式对“史”书记载的影响。如清华简《系年》有关携王史事的记载似属于此种范畴。
[参考文献]
[1]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97,221, 327-328.
[2]王玉哲.漫谈学习中国上古史[J].历史教学,1984(2):2-8.
[3]陈伟.试说简牍文献的年代梯次[C]//李宗焜.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出土材料与新视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493-500.
[4](日)佐川英治,等.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动向[C]//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8.
[5]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C].“首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论文.天津,2014.
[6]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255-259.
[7]徐建委.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计与学术史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1-74.
[8]白寿彝.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国语[C]//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30.
[9]李佳.国语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9:132.
[10]杨博.论史料解读的差异性——由楚竹书灾异文献中的旱灾母题入手[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0-87.
[11]李伟泰.《竞建内之》与《尚书》说之互证[M]//周凤五.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发展与转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1-16.
[1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1032-1033.
[13]刘信芳.竹书《鲍叔牙》与《管子》对比研究的几个问题[J].管子研究,2006(7):32-38.
[14]于凯.上博楚简《容成氏》疏劄九则[M]//朱渊清,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384-386.
[15]夏大兆,黄德宽.关于清华简《尹至》《尹诰》的形成和性质——从伊尹传说在先秦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流变考察[J].文史,2014(3):213-239.
[1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M].上海:中西书局,2013:134.
[17]陈鹏宇.清华简《芮良夫毖》套语成分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2):62-70.
[18]张以仁.从《国语》与《左传》本质上的差异试论后人对《国语》的批评[M]//春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109.
[19]傅刚.略说先秦的语体与语书[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7.
[20]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M]//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32.
[21]肖芸晓.试论清华竹书伊尹三篇的关联[M]//简帛(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71-476.
[22]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
[23]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M].孙英刚译,王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8-10.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Value of New“Yu”Literature
Yang Bo
Abstract:New“Yu”literature, as a new vitality to the scarce study of Pre-qinhistory, needs testification for lots of duplicated theme, characters, events, etc.“Yu”is a special kind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which was a reference for not only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Zuozhuan”but also some other materials.The popularity of criticism research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riteria for historical value of new“Yu”literature and the value could be summarized from 4 aspects: prudent cogni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Pre-qin history, comprehensionofdevelopmentof historicalmaterial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overall understand ofacademic atmosphere and realization of criticism of Pre-qinmaterials.
Keywords:“Yu”Literature; Critic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Chuzhushu; Historical Value
[收稿日期]2015-03-25[责任编辑]李金瓯
[作者简介]杨博(1986-),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先秦史。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5-8214(2016)02-0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