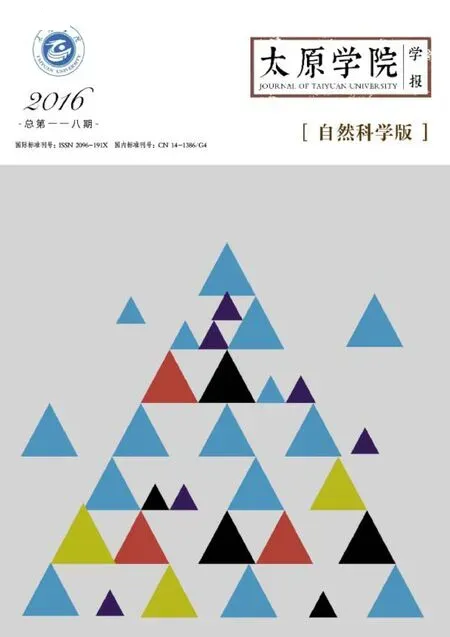创客时代视角下青少年玩商培育的研究
2016-02-12李英华
李英华
(太原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随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号召在神州大地激起创业的热潮,“创客” 一词也渐渐为我们熟知。“创客” 一词意译自英文单词 “Maker”,是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在今日之中国,创客被赋予更加积极的本土含义,专指那些坚守创新、持续实践、乐于分享并且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简而言之,即“玩创新”的一群人。李克强总理在深圳考察时曾对创客作出这样的评价:创客充分展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这种活力将会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不熄引擎。
由兴趣生发创意,将创意变为现实,这是创客的表现,同时也是玩耍的内涵所在。玩耍既需动手又需动脑,是一种放松、惬意、自由的实践状态;玩耍也是一种分享,有趣、有意义的体验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玩耍更是一种境界,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创客” 时,世界将因“玩” 而改变。对于青少年来说,玩耍更具要义。玩耍是青少年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也是他们潜在的学习驱动力,更可激发、催化其创造潜质。在“创” 字当头的今天,提升青少年玩耍能力,培育青少年玩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玩商概念及理论支撑
“玩商” (Leisure Quotient,简称LQ),即玩乐商数,亦称休闲商,用来描述个体是否善于休闲、善于生活,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健康玩乐的素质与能力,其表达形式类同于智商 (IQ)、情商(EQ)、逆商(AQ)。休闲学、人本主义理论、积极心理学都为玩商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1.1 休闲学视角
最早对休闲进行关注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休闲是人类天赋的要求和意愿:“我们曾经屡次申诉,人类天赋具有求取勤劳服务同时又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1]他认为休闲是一种深思的、冥想的状态,是一种忘我的、无需考虑生存问题的状态。休闲和思考密不可分,它耕耘了心灵、精神和个性。随着社会发展,休闲从边缘性活动逐渐演变得主流化。1899年,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指出,闲暇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建制。1967年,法国社会学家杜马哲迪尔提出,休闲是指个人“从工作岗位和社会义务中解脱出来,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从事娱乐消遣或是培养与谋生无关的智能,以及自发参加的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力的活动”,[2]这是思想上的随心所欲,是个体生命的一种崭新的、自由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们体验到身心愉快、精神满足与自我发展,实现了个体与环境呼应式协调发展。
玩耍从属于休闲,是休闲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玩耍活动能将休闲具有的特点,如解脱感、趣味性、自由性、建设性等,融合并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原生态的心力驱动下,个体以自身和谐发展为目的,平和、自由而宁静地进行着玩耍活动,从中能够获得成就感、满足感、自豪感等愉悦的心理体验,有助于塑造健康和谐的心性,进而逐步成就幸福饱满的人生。
1.2 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主张关注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一些复杂的经验——诸如动机、兴趣、需要、自我意识等真正属于人性各种层面的问题。人本主义注重人的独特性和社会性,强调人是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生物,其行为要受自我意识支配;强调人具有发展的潜能和自我成长的需要,会本能地寻求改善环境的方法以利于自身人性的充分发展,追求自我实现。当人们眼前的需要得以满足后,并不会止步不前,而是仍会积极地寻求发展,朝着最后的令人满足的状态不断进取。马斯洛认为,这种积极的状态源于个体“自我实现” 的需要。罗杰斯则将自我获得发展、追求实现的过程定义为“成长过程”。
在玩耍活动中,个体精神放松、心智活跃,易于产生具有积极效应的乐观体验,“这样的乐观体验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自己及自己的经历,体验到存在感、能力感,并有发现了自我的感觉”。[3]这对于个体自我满足感的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乐观体验的逐步积累、发酵,更可提升个体对自我生活的控制力,对个体未来成就及其人生幸福感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1.3 积极心理学范畴
美国心理学家塞里基曼在1997年提出 “积极心理学” 的概念时指出,积极心理学的力量在于帮助人们发现并利用自己的内在资源,进而提升个人的素质和生活的品质。积极心理学主张“要以人固有的、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提倡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对人的行为作出解读,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与优秀品质”,[4]并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来帮助普通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美好的生活。积极的情绪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例如爱、高兴、满足、自豪、幸福感,都属于正向的、建设性的情绪体验。这些积极的情绪体验不仅能够使人们瞬间的知行能力得到拓展,而且能构建和增加个人资源,如体力、智力、社会协调性等,还能够催生积极个性品质的形成,提升幸福感。
“玩耍”一词被赋予自由、快乐的情感色彩,并且演绎为具有主动精神倾向的行为,它非常有利于个体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并由此产生源自内心的、建设性的正能量,这种能量又能促使个体生发乐观情绪,建立主观幸福感,有助于个体表现出更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进而提升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力,轻松地面对压力、逆境和损失,最终收获幸福人生。
2 青少年玩商培育的要义
2.1 玩耍与成长
玩耍伴随着青少年的成长,他们在玩耍中获得技能、体验情感、学会合作、发展自我,从而一步步成长。结伴玩耍、群体玩耍对个体社会性的健康发展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在玩耍过程中,青少年的沟通能力得到锻炼,并渐渐形成礼让、互助的意识,同时逐步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尤其是有效地控制、疏导负面情绪,增强自身心理调节能力。心理调节能力因其内隐性、边缘性易被忽视,然而它对于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在校生自杀事件呈上升态势,震惊慨叹的同时令人深思:当事青少年都是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长大,他们的玩耍活动,不论从空间与时间上来说,还是就内容与质量而言,都是“打了折扣” 的,这些青少年在自杀事件中表现出心理调节能力的严重不足,与其成长背景不无关联。
青少年的生活以学业为主,但玩耍与学习绝非对立。“臧焉息焉,息焉游焉”,玩耍是青少年一种积极的放松方式。正所谓 “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玩耍与学习和谐共融,能够有效促进青少年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协调发展,对青少年成年以后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实现自我价值、提升人生幸福指数都有着重要的心理奠基作用。
2.2 玩耍与创造
玩耍是青少年的天性,是青少年对自然万物、大千世界以及深邃宇宙的探索和追问。对于青少年来说,玩耍是一个灿烂无比的世界。在玩耍的世界里,他们的心性是原生态的,是最自由且最具有创造力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的产生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惊异、闲暇和自由。贪玩的人需要这些,科学更需要这些贪玩的人”,[5]这里的 “贪玩” 是指专注的、投入的、酝酿灵感的玩耍,古往今来,有许多科学发明都是脱胎于这种玩耍时产生的灵感,并于进一步的思考中反复实践、逐步完善进而得以问世的。与“擦燃火柴” 相似,玩耍也可以 “点燃”、“催生” 青少年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 “玩耍” 与 “创造力” 共生互利的良性互动中,青少年创新的意识渐渐萌发直至牢固树立,这对青少年的成长将产生可持续的良性影响。当前,我国正朝着“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前进,“实现中国梦” 已成为时代最强音。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说,“中国梦” 就是创新梦、科技梦、人才梦。因而,时代呼唤更多的 “创客”。在此背景下,科学培育青少年的玩商兼具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
3 不容乐观的玩商现状
3.1 被魔化的玩耍
在传统文化意识中,玩耍可以说是边缘化的负面角色,背负着非主流的原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玩物丧志、吃喝玩乐”,这些词语都似在拷问玩耍的意义。这样的认知基础奠定了玩耍的边缘性角色,而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才价值取向的巨变又恰巧夯实了玩耍的非主流地位。“新时代对人的素养不断提出挑战,这会综合性、渗透性地持续影响这一时代的青少年;同时,社会对学历的看重,对名校的青睐,也加剧了原本已十分激烈的升学竞争,使青少年越来越早地被驱赶到这一竞争的漩涡之中”。[6]“玩耍” 在人们非理性观念的推动下,逐步蜕变成了 “学习” 的对立面,开始被魔化。而在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构建的压力场域中,被魔化的玩耍逐渐显现其 “魔力”,“没写完作业你怎么就去玩?”、“马上就要月考了,别去玩了!” 这样的声音高频次地充斥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在这样的 “魔力” 下,孩子们早早背负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的家族厚望,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了周末“上班族”。2011年,一份 “想得美课程表” 走红网络,它浓缩了一名小学四年级男生的美好愿望。在这份课程表上,玩的内容成了主打。令人忍俊不禁,却更使人深思。这份课程表反映了青少年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玩耍本应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可现如今却成为稀缺资源,只能望 “玩” 兴叹。畸形的教育理念将玩耍一步步“妖魔化”,孩子们 “不敢玩、没时间玩”,自然也“不会玩”。玩耍从 “必需品” 变成了 “奢侈品”,他们拥有的是僵化的、无趣的童年,这已然成为大多数青少年的生活样态。
3.2 被异化的玩耍
3.2.1 宅在家里的“玩耍”
智能电子产品的迅速普及以及各种游戏软件的开发运用,使得很多青少年自小与“电子保姆” 亲密无间,而且,电子产品“照料” 孩子的低成本性与室外活动存在的安全潜在危机,致使家长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让孩子们留在室内玩耍,造就了“原生宅” 的一代。这些“室内儿童” 长期与电子屏幕近距离接触不仅损坏视力,而且,成长期极少的运动量也势必导致其新陈代谢紊乱,更为深重的影响与孩子心智发展有关——他们正逐渐受到“自然缺失症” 的侵扰。正是由于成长期缺乏足够的自然接触造成了现代青少年一系列的问题:近视率逐年增加、肥胖率上升、注意力紊乱、抑郁现象等等。
尽管内容极为丰富且升级非常迅速的各类学习软件、益智游戏软件可以无缝隙地填满青少年玩耍的时间,但玩耍的场所却极为单一,这已然是被异化的玩耍。对于自然模式的欣赏是产生创造力的关键,因此这样的玩耍无形中会限制青少年创新意识的萌发,阻碍其创造能力的发展。
3.2.2 狂欢在外的“玩耍”
玩耍的天性被压抑,但却不会消失。来自外界的约束效力一旦减弱或者消除就会出现行为反弹,于是有的孩子出现利用家长或学校监管的空当疯狂玩耍的行为。对于部分青少年而言,即便约束的效力一直存在,长期被压抑的欲望也终会有强烈释放的时候,但是很多玩耍方式具有明显的年龄限制性(如跳皮筋、逮人游戏),加之当今社会进程与新媒体时代对传统玩耍方式破坏性的、强烈的冲击,以及亲子矛盾、厌学心理、人际关系困惑等问题叠加发酵,致使很多青少年干脆以“出格的玩耍” 来释放自己,如玩网络游戏、去通宵娱乐场所,甚至吸烟、酗酒、吸食毒品等等,尤其是处于感觉寻求水平快速增长时期的、16 到18 岁之间的学生。
沉迷于网络的 “少年玩家” 不在少数。据报告,青少年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要高于网民总体。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将会对青少年影响越来越大,网络依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青少年网民偏重娱乐类应用,使用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和网络文学这四类应用的比例均高于网民总体水平,其中网络游戏高出7.9 个百分点”,[7]娱乐类应用为青少年的课余生活带来愉悦,对学习生活起到适当的调节作用,但有些青少年却过度依赖娱乐类应用,尤其沉迷于网络游戏,玩得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严重影响到生活、学习,以及身心健康。青少年还普遍具有好奇心,喜欢冒险与刺激,同时也需要强烈的群体认同感,这些心理可能会使部分青少年将一些通宵娱乐场所作为情绪释放之地,然而,长期如此,亚健康状态自不待说,更可怕的是,如此“狂欢” 可能招致另一个恶魔——毒品,那将是无法回头的深渊。
网络游戏、通宵娱乐场所、毒品,这些孩子越“玩” 越出格,成为人生路上迷途却执拗的羔羊。这样的玩耍已被异化,彻底背离了玩耍的本质,不仅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而且进一步偏离了玩耍的含义,从本质上异化了玩耍,将玩耍向舆论法庭的拷问更加推进了一层。
4 有关玩商培育的构想
4.1 创客时代的舆论土壤:为玩耍正名
创客时代需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舆论土壤,需要社会对玩耍内涵及意义的真正认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提到“儿童有权享有闲暇,从事与其年龄相宜的娱乐和游戏活动,以及自由地参加文化艺术生活。” 社会舆论有待为青少年的玩耍 “正名”,不能简单地将玩耍与虚度光阴、不务正业相联系。玩耍与学习绝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恰恰相反,二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玩耍也绝不是青少年应当远离的恶魔,要将那种“玩就是不务正业,就是虚度光阴” 的观念永久封存。同时,全社会都要认同这样的观念:玩耍能促进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尊重和释放青少年的玩心更有助于解放、催生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有助于他们在获得 “自我成就” 感的过程中健康成长。这样,“创新意识从小培养” 的全民创新氛围才能得以产生并长久存在。
光为玩耍正名、形成创新的舆论土壤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推进具体措施的出台。首先,要真正地、有意义地发挥少年宫此类机构的作用,不仅在设施上为青少年提供萌生创造力的可能性,也在形式上提供给青少年交流共享、智慧碰撞的合作空间,让创新的萌芽在全社会的呵护下得以茁壮成长。其次,政府还可以鼓励民间力量加入进来,因地制宜,发挥创意,针对青少年的不同年龄段与相似的兴趣爱好,结合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特点,筹办各类主题活动机构,如创意机械师、我的实验室、扎染小组等等,并且持续关注和扶持这类机构的发展与成长。在尊重、鼓励青少年玩耍的全民认知前提与社会舆论背景下,在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投入与持续支持下,在各类民间组织的相互合作、积极参与下,全民创新的舆论土壤就能渐渐得以肥沃,逐步形成立体、和谐、有序的强大而持久的创新教育场域。
4.2 家长思路上的调整:玩物也会励志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告诫父母,“不要剥夺孩子游戏的权利,要让孩子有充分游戏的时间与空间。”陶行知先生也曾为解放孩子的创造力提出“六个解放” 的教育理念,告诉我们要让孩子“学一点自己渴望学习的知识,干一点自己高兴去干的事情”。青少年可以从玩耍中得到许多新的体验,这也是求知的过程。但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弊端的阴影牢固地融入家长的教子意识,形成 “过度教育”、“唯分数论” 的短视教育观念,并外显于强势、高调且“义无反顾” 的行为,基本表现为以爱的名义绑架孩子的时间与空间、以前程的角度限制孩子心性的自由、以成绩的效应挟持孩子的天性。一些家长功利化地使用“玩耍” 的功能,在对待作业效率低的青少年时,将玩耍做为奖励,如“写完作业就让你玩一会儿”,甚至有的家长已经形成牢固的 “畸形玩耍” 观念,如 “今天作业写得挺快,可以玩会儿电脑了”,这种观念不仅完全背离孩子与自然的本真联系,而且意味着玩耍属于机会难得的、高层次的消费,对于玩耍为天性的孩子是多么可怕的、病态的反差。
孩子的玩耍行为起步于家庭。玩物未必丧志,玩物也会励志,家长不能将青少年专注投入的玩耍行为简单粗暴地冠之以“贪玩” 的罪名,让自己处于焦虑状态,并在所谓的教育中再将焦虑传染给孩子,同时将玩耍中可能存在的创新意念无情扼杀。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场所,家长有必要形成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意识,解放孩子的玩心,并创造充分玩耍的条件,让青少年从面对书山题海无奈叹息的状态中走出来,既非 “宅在家里”,也非 “狂欢在外”,使青少年能有充分的时间与空间投入到玩耍中,创新的意识就有可能在长久的、专注的玩耍中诞生。值得一提的是,要着力恢复青少年与自然的内在联系。青少年 “就像需要睡眠和食物一样,需要与大自然的接触”,[8]“别把孩子囚禁”,要让自然滋养孩子的灵性,促进其心智的健康发展。
4.3 学校措施上的孵化效应:奇思妙想我能行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拥有幸福的人生,成为快乐的人,因此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应该是快乐的。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则主张“从做中学”,他提倡学习要从孩子的天性出发,促进其个性发展。教育者要引导青少年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使其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获得知识,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这里的“活动” 即指青少年以玩耍的心态对待感兴趣的学习内容的过程。既然“玩” 是青少年的天性,我们的教育就应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非逆“天” 而动。教育部有关教育体制的系列改革已经在扎实稳步地推进,以遏制学业负担过重的畸形教育现象。教育部拟定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2013年9月4日再次征求意见稿)第四条就明确规定:“减少作业”、“要积极与家长互动,指导好学生的课外活动”。[9]减轻学业负担的同时倡导多样化课外活动的开展,这是培养青少年玩商的重要且有效的途径。作为实施集体教育的场所,学校可充分发挥自身的机构优势培养“未来创客”,将“启发”、“点燃” 等教育理念深度融入各科教学,同时着力营造浓郁的探索氛围、创新氛围,并且结合创新成果的展览与创新思路的交流,呵护青少年的奇思妙想,使青少年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参与分享,体验 “智慧众筹、合作创造”的快乐,让创新与思考、探索与分享逐步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主旋律,进而成为全社会发展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