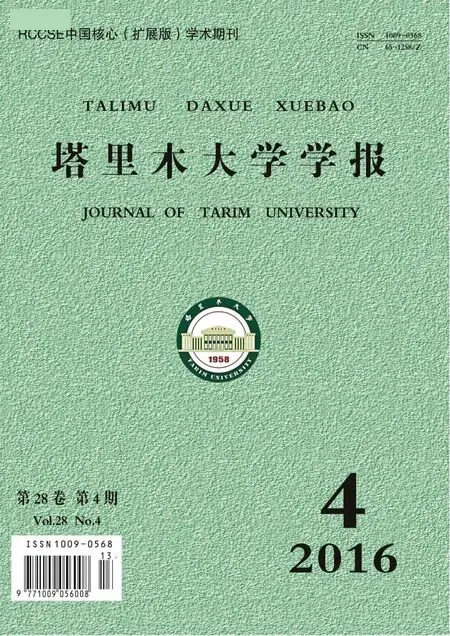塔里木大学维吾尔族大学生汉文化接纳程度的调查报告
2016-02-11谢贵平
张 砾 谢贵平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塔里木大学维吾尔族大学生汉文化接纳程度的调查报告
张 砾 谢贵平*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在多民族聚居的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少数民族先进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与引领者,自新疆双语教育实施以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水平越来越高,和汉文化的接触也日益频繁,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同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和彼此的理解与尊重。通过对塔里木大学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考察,了解他们对汉文化的接纳程度,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推断在其家乡少数民族中小学生汉文化的学习情况,及维吾尔族民众对汉文化的认同现状,据此,在双语教育方面为提高维吾尔族汉文化接纳程度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和对策。
维吾尔族; 汉文化接纳程度; 文化认同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资本,要体现这种社会资本的作用,关键在于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不仅仅包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非本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从群体层面来看,民族文化认同在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增进民族交流、增加民族认同感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地区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睦共处的思想前提。”[1]
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对促进民汉族际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新疆总人口为2 181.33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为1 001. 98万人,占总人口的46. 42%,汉族人口为 841. 69万人,占总人口的39%,[2]汉族和维吾尔族是新疆两大主体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大多数居住在新疆南部的阿克苏、喀什、和田三个地区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合称南疆四地州),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乡村。汉族主要居住在新疆除南疆以外的其他地区,而且多聚集在城镇。新疆大力推行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促进了维吾尔族学习汉语、使用汉语,推动了维汉民族的交流交往和彼此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而维吾尔族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状况是新疆维汉民族关系和谐与否的核心变量,维吾尔族对汉文化的接纳程度也反映出他们对汉民族的认同程度。
1 调查目的和研究意义
1.1 调查目的
认同是接纳的前提和基础,对汉文化的接纳首先需要对汉文化了解并认同。维吾尔族大学生群体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更长,了解的信息更为广泛,受汉文化的影响更大,可以看作是维吾尔族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和引领者。对这个群体进行考察,有利于动态地把握维吾尔族民众关于汉文化认同的现状与趋向。本课题旨在通过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汉文化的认知与接纳情况,推断维吾尔族大学生及其所生活区域内的维吾尔族民众对汉文化的认同状况。
1.2 研究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3]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是不同文化交汇融通的重要途径,双语教育不是仅仅教授语言,更要传递文化。本课题调查的意义正是在于了解维吾尔族大学生在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学习汉语的背景下,是否能正确认知汉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接纳汉文化,同时以此为依据,为推进和深化少数民族学生双语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建设性建议与对策。
2 调查对象的选取和问卷样本设计
2.1 调查对象简介
塔里木大学位于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边缘,现有各类学生13 0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8%,维吾尔族学生占少数民族学生的65%,他们大部分来自南疆四地州,此外,伊犁、塔城、博乐、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库尔勒等地也均有生源。大多数维吾尔族学生来自县城或乡村,父母多以务农、放羊为主。他们毕业时通常会选择返回家乡就业,或尽可能地就近择业,少部分由于报考公务员、特岗教师等原因可能远离家乡,但极少会离开新疆,因此他们生活学习的区域主要在新疆。
2.2 调查问卷样本设计
本次调查以问卷为主,主要涉及到汉民族的语言、节日、禁忌、影视、歌曲、小说、传统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此外,调查者还对部分学生就个别问题进行了访谈,对一些维吾尔族聚居区的中小学进行了社会调查。
问卷调查选取了塔里木大学从预科到大四的160名维吾尔族大学生,包括人文学院、植物科学学院、生物科学学院、机械电气化工程学院的71名男生和89名女生,专业分别涉及到文科、理科和工科。调查者利用预科和大一晚自习时间去教室发放问卷。大二、大三和大四的学生没有晚自习,调查者在宿舍楼随机发放问卷,并当场回收。问卷发放160份,回收了160份,有效问卷150份,比例为93. 75%。有效问卷中,预科生32人,大一33人,大二29人,大三和大四各28人。
被调查的学生年龄主要集中在18至24岁,受教育经历相似,几乎都是从一年级开始学习汉语。其中19名来自城市,57名来自县城,74名来自乡村。民考汉学生11人,双语班学生87人,普通班学生52人。来自县、乡的学生家庭背景大致相似,绝大部分生活在维吾尔族聚居区,其中有14名学生的家长跑运输或者做生意,其余的都是农民。来自城市的学生主要生活在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哈萨克等多民族混居社区,家长至少有一方是在企事业单位上班或者从单位退休的。
3 调查问卷分析
3.1 对调查结果的整理和分析
通过对问卷的统计,从以下七个方面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
3.1.1 对汉语文学作品的接纳程度
从调查结果来看,“从来不看汉语文学作品”的维吾尔族大学生仅占5. 3%,但是“经常阅读”的比例也不高,仅占10. 7%。79. 3%的被调查者表示“知道四大古典名著”,而“读过原著”的仅占7. 3%,16%的被调查者说不全四大名著的名称,还有4. 7%完全不知道四大名著。
根据样本信息,“从来不看汉语文学作品”的8名学生和“完全不知道四大古典名著”的7名学生均来自和田和喀什地区的农民家庭,均是普通班的学生。由此可见自然地理地域人文生态环境对维吾尔族民众汉文化认知与接纳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南疆维吾尔族高度聚居的农村,汉族人口少,人文环境相对封闭,维吾尔族民众之间多以维语交流,汉语言与汉文化教育较为滞后,学生受家庭与社会影响大,课外汉文化阅读条件不能保证。另外,普通班的维吾尔族学生汉语水平有限,阅读汉语文学作品的主动性不太高。
3.1.2 对汉语音乐及影视作品的接纳程度
维吾尔族是热爱音乐的民族。被调查者中“平时从来不听汉语歌曲”的只有一名预科生,没有“从来不看汉语影视节目”的学生。从预科到大四,“有时候、或者经常听汉语歌曲、看汉语影视节目”的学生人数呈上升趋势,说明到大学以后,维吾尔族学生对汉语歌曲和影视节目的接纳程度逐渐提高,也反映出语言环境的重要性。塔里木大学汉族学生比例高,维汉学生的交往较中学阶段有所增加,另外,学校全部使用汉语作为教学语言,这为维吾尔族大学生接触汉语、使用汉语创造了很好的汉语与汉文化环境。
3.1.3 对汉民族节日、禁忌的接纳程度
作为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影响深远。但是调查结果显示,有13. 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了解”汉民族的节日,“非常了解”的仅占9. 3%。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曾随机询问学生,通过哪些渠道来了解汉民族的节日,有一种回答是:“汉族人过节的时候要放假。”得到周围同学们的随声附和。对于“是否会和汉族朋友一起庆祝汉民族节日”,只有10%的被调查者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还有20%的被调查者态度消极。愿意和汉族朋友庆祝节日的学生集中体现在民考汉学生群体,他们汉族朋友多,对汉族节日的熟知程度也高。例如访谈对象中的依力沙提同学,计算机19-1专业,被调查时为人文学院预科生,男,博乐市人,幼儿园到小学阶段都是民考汉类型,和汉族学生在一起上课。他告诉调查者,自己从小到大的汉族朋友多于维吾尔族朋友,春节时他会去汉族朋友家拜年,古尔邦节时汉族朋友也会来他家玩。大家在交往过程中会非常注意尊重彼此的风俗习惯,从来没有因为是不同民族而产生不自在或有差别的感觉。而持排斥态度的学生全部为农村生源,他们表示对维汉民族饮食习惯不同存有顾虑,认为去参加汉民族的节日可能会尴尬。汉语表达能力差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禁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世界上已知的各种文化之中。它是指社会力图避讳的某些行为、事物或关系。”[4]禁忌约束着人们的语言和行为,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敏感问题。不同民族之间如果不了解对方的禁忌,就有可能成为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此项调查发现,维吾尔族大学生整体来说对汉民族禁忌文化都知之甚少,调查者认为,这既和被调查者生长生活区域中民族成分的相对单一性有关,也和他们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汉文化内容教育的缺失有关。
3.1.4 对汉民族服饰的接纳程度
汉民族传统服饰简称“汉服”。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汉民族服饰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并独具特色。虽然大江南北不同地域的汉族服饰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但在款式、工艺、色彩、图案等方面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统一。
问卷中此题为多选题。从调查结果来看,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服饰的接纳程度较高,而对汉民族的传统服饰缺少认知。被调查者中认为“汉民族没有传统服饰”的约占16%,表示“不了解汉民族的传统服饰”的约占68%,认为“现代服饰已经没有了民族的区别”的约占36. 7%。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很多学生就此提出疑问:“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是什么样的?”通过访谈,调查者发现,从小生活在南疆和田、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学生更注重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而生活在南疆以外其他地区的学生则相对淡化服饰的民族因素。对于汉族的传统服饰,维吾尔族大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旗袍、西装和影视剧中的古装当作汉服。访谈对象布祖热汗同学,计算机19-1专业,被调查时为人文学院预科生,女,喀什莎车县人,除了体育课穿运动服以外,一年四季都穿裙子,裙子下面一定要有裤子,从不光腿或只穿长筒丝袜。裙子最短也到膝盖,不穿超短裙。裙子的颜色也较为单一,一般是深色,如果是花裙,基本上都是艾提来斯花纹,鲜见其他样式。她认为一些对个人来说重要的、有意义的民族节日就要穿戴本民族传统服饰,如果汉族人也穿戴具有维吾尔族传统特征的服饰,她会觉得很高兴,对于汉族人的传统服饰是什么,她表示很难确定,她推断汉族“传统”服饰应该是旗袍和西装。日常生活中大家的服饰都差不多,北疆的维吾尔族同学穿着打扮更加流行,看上去和汉族同学的服饰没有什么差别。前文中提到的依力沙提,从小和汉族孩子一起长大,他认为汉族的传统服饰就是古装剧演员穿的那种衣服,现在已经退出生活,除了拍影视剧会用到,再就是照相馆能见着了。他很喜欢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即使和汉族朋友在一起也不会介意穿戴民族服饰。他说现在北疆能看到很多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相结合的民族服饰,如时尚的长版衬衣或连衣裙,用艾提拉斯的花纹装饰衣领、腰身和袖口,面料是可以随意清洗、略带弹性的流行材料,也受到很多女孩子的喜爱。对于来自南疆农村的女同学们浓厚地域特色与传统民族风格服饰的穿着,他表示很难以理解,说以前从来没见过裤子配裙子的穿法。调查者认为,这种认知主要源于课堂、会议或其他某些重要活动的场合中汉族老师和同学们常穿西装、旗袍;以及出于个人的主观认识与想象,把影视剧中古装演员的服装当作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并非在汉语与汉文化学习过程中了解过这些知识。
3.1.5 对汉民族宗教及传统思想的了解情况
众所周知,孔子的思想在汉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被调查者中有27. 3%对“孔子和孔子的思想”相对陌生,35. 3%的同学表示“了解一点”,仅有4%的同学表示“很了解”。关于“汉民族宗教信仰”的问题是多选题。此项调查中,14%的被调查者认为“孔子的思想就是汉民族的宗教信仰”,14%的被调查者认为“汉民族没有宗教信仰”,绝大部分被调查者对汉民族的宗教信仰缺乏准确的理解。
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不够,一方面反映出新疆双语教育中汉文化教育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维吾尔族学生汉文化阅读视野非常有限。如果维吾尔族不能正确认知与了解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文化,就难免在跨文化交际中对汉族的某些行为方式产生误解,影响到对汉民族的认同。
3.1.6 对汉民族语言文字的接纳程度
对一个民族来说,语言和文字是最明显的具有民族标志的内容,但只有25. 3%的被调查者同意“汉字反映了汉文化”的说法,而还有24. 7%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理解‘汉字反映了汉文化’这句话的意思”。通过和大四的六名被访谈者(这六名被访谈者分别是:阿迪力,男,喀什泽普县人;阿迪拉,女,阿克苏温宿县人;木卡代斯,女,喀什麦盖提人;亚森,男,吐鲁番鄯善县人;阿布都热西提,男,喀什莎车人;海日古丽,女,阿克苏库车县人)进行座谈,调查者了解到,在学生看来,文字只是一个符号,是用来书写的工具,和文化没什么关系,也无从谈起对文化的反映。
相比较汉字而言,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关系”的认识比较明确,没有“认为汉语和汉文化完全无关”的。这说明虽然大部分被调查者能认识到学习汉语对了解汉文化有一定关系,却对汉语缺乏综合的认知。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汉字的演变经历,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一些维吾尔族学生学了十几年的汉语,对汉语的认识仍只停留在语言交流层面,不仅对文字这种书面表达形式不够重视,也没有意识到语言在文化传递方面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双语教育中单纯地“就语言而教语言”的弊端已经日益凸显,在汉语言教育中加强汉文化教育势在必行。
3.1.7 对汉族人的接纳程度
在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交往意愿方面,“持积极主动态度”的占78. 7%。虽然没有坚决不和汉族同学来往的,但有6%的被调查者表示“很不愿意”。根据样本信息,这6%的被调查者均是普通班的学生,来自农村。调查者认为,“很不愿意和汉族同学来往”反映出这部分被调查者在心理上对汉族有一定的隔阂与排斥。除了受南疆地区社会与家庭环境的影响,也和他们自身的性格及汉语水平有限、对汉文化认知不足有关。在对“维吾尔族大学生对国家、家乡和本民族的认同度”的调查中可知,被调查者愿意表明自己维吾尔族身份的,占70. 7%;愿意用“新疆人”介绍自己的,占20. 7%;愿意用“中国人”介绍自己的,占8. 7%。这说明,被调查者的本民族认同度最高,地域认同度次之,国家认同度最低。
近几年来,由于新疆暴恐案件的升级和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一些内地人产生了“新疆人都是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人都是坏人、都是暴恐事件的制造者”等错误的认知心理。在新疆本土,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维吾尔族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如安检口对维吾尔族的检查相对更加严格,某些火车站的候车厅有集中安排维吾尔族群众候车的区域,外出住宿必须要出示无犯罪记录的证明等等。对维吾尔族大学生来说,面对这些具有族际差别性、标签性与针对性的变相“社会歧视”与心理压力,他们的内心冲撞也很剧烈,有的会产生更加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甚至对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产生排斥乃至敌视心理;也有的对本民族同胞感到反感,认为维吾尔族落后不开化;还有的想逃避现实,对境外与新疆维吾尔族有一定历史文化渊源的土耳其等国家产生向往。
3.2 对调查结果的总结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塔里木大学维吾尔族大学生在对汉文化接纳程度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1)对汉民族音乐影视作品的接纳程度高于对文学作品的接纳程度,对汉民族音乐影视娱乐节目或娱乐文化的接纳程度更高;(2)对汉语口语的接纳程度高于对书面语即汉字的接纳程度;(3)对汉民族传统服饰、宗教、节日、传统思想和禁忌文化了解得很少,认同程度不高,更谈不上接纳;(4)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高于对汉民族的认同和国家认同,虽然绝大部分维吾尔族大学生并不排斥和汉族的交往,但他们同汉族仍有一定的分界意识。(5)北疆的、城市的、维汉民族混居区的、家庭汉语与汉文化教育环境较好的、上过汉校的维吾尔族学生对汉文化的认同度较高;南疆、农村的、维吾尔族单一民族聚居区的、家庭汉语与汉文化教育环境较差的、只上过民校普通班的维吾尔族学生对汉文化的认同度较低。
4 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汉文化接纳程度不高的原因分析
4.1 学生自身原因
4.1.1 重视汉语言学习而对汉文化缺少关注,重视口语而对书面语缺少关注
大多数维吾尔族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对听说的重视超过对读写的重视。因为听和说是交际的最基本方式,哪怕不会读、不会写,只要能听懂、能说,就可以实现和汉族人的交流。再加上汉字数量多、笔画书写复杂,和维吾尔语这种拼音文字完全不同,学习难度大,都使得维吾尔族学生偏重于汉语的听说训练。所以,他们对汉语口语的接纳程度高于对汉字的接纳程度,对汉民族音乐影视作品的接纳程度高于对汉民族文学作品的接纳程度。
4.1.2 和汉族人的交往及汉语和汉文化的交流非常有限
虽然塔里木大学多方面鼓励民汉同学交往,但是维吾尔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交际并不广泛,许多维吾尔族大学生甚至一个汉族朋友也没有。这虽然和学生个人性格、汉语表达水平有关,但对汉民族文化的不了解也是阻碍维吾尔族大学生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娱乐性的、体育类的集体活动之外,维汉民族大学生即使同在一层宿舍楼里生活、同在一层教学楼里上课,彼此也多是擦肩而过,缺少交往与交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对维汉民族相互之间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会造成消极影响,对维汉和谐族际关系的构建也是非常不利的。
4.1.3 学习语言的短视性和功利性
“决定语言教学是否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学生是否喜欢上这门课。……成功的语言学习可以归结到愿望和需要上。”[5]在新疆双语教育推行过程中,能使家长和社会对双语教育增强信心的,主要是学生成绩的提高。一些学生和家长乃至教师认为推行双语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率和民族大学生的就业率,“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是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更是家庭的期望,这种实用主义思想片面地将双语教育等同于汉语教育,将学汉语等同于找工作,从而阻碍了家长、学生和教师正确地认知双语教育。当学生认为生活中完全不需要使用汉语或者学汉语并不能给生活带来什么变化的时候,学习的动力就会大幅度降低,并进一步削弱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这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据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去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实习支教的学生说,乡里小学四年级的维吾尔族学生都还几乎听不懂汉语。当问及他们为什么学了四年了都还听不懂时,有学生说:“我们乡没有汉族人,学了汉语跟谁交流呢?”还有学生说:“我的梦想是小学一毕业就当农民,所以不用学汉语。”这种现象在南疆乡村小学并非个例。
4.2 教师教学原因
4.2.1 汉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育的缺失
虽然维吾尔族大学生基本上都有十年以上学习汉语的经历,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年级的分布对他们汉文化接纳程度的高低并没有明显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是在长期的双语教育过程中厚此薄彼、重语言轻文化的结果。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预科,汉语课的教学模式大多是学词语、背课文、做练习,教学要求即“汉语考试过关”。课堂上,教师只管教材,不管课外知识的扩展和实际交际方式的学习,也不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汉文化的教学内容匮乏。教师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脱离,是民族学生汉文化接纳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
4.2.2 部分教师责任心不强
一些从事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老师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提高整个民族素质中所担负的神圣职责,没有把汉语教学和培育少数民族人才挂钩,缺乏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从根本上影响了双语教学的质量。在南疆四地州的很多乡村学校,教师的教案完全是为了应付教育局的检查,抄旧教案、互相抄教案、让实习生帮忙写教案、甚至直接把实习生的教案拿来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布置的作业以字词抄写为主,收上来也是光打“勾叉”,只批不改,或者全部作业都让实习生来改。当教育局抽考的时候,为了学生成绩达标,竟然有老师把答案直接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在和田地区墨玉县、阿克苏地区沙雅县、阿瓦提县、拜城县实习支教的学生均经历过这些。在这些实习生眼里,南疆维吾尔族乡村学校的学生之所以学习主动性差,汉语水平低,和当地学校的管理与老师的教学有直接关系。这部分教师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双语教育和汉语教学中去,没有尽职尽责为提高教学效果而努力。
4.2.3 教师自身素质的局限
“大部分双语教师从事双语教学是因为学校指派,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也未必能够胜任双语教学工作……很多教师的汉语水平只能应付听说,还有极个别教师完全不懂汉语。”[6]南疆四地州比较偏远的学校普遍存在师资不足的现状,为了将推行双语教育落到实处,只能“矮子里面拔将军”,一些教学水平不高、专业知识不过硬、或汉语教学能力不过关的教师也被安排在汉语教学的岗位上,虽然可以完成教学任务,却无法保证教学质量。
4.3 学校文化交流环境的局限
就学校而言,民汉合校为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共学、共乐、共同提高”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能真正达到这种效果的非常少。大部分民汉合校针对汉语系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各有一套领导班子,有各自独立的课程设置和教师队伍,民汉学生除了课外活动有可能共同参与以外,平时基本没有交往。事实上,即使在课外活动过程中,民汉学生的交流也是非常有限的,汉族学生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不会主动和少数民族学生交谈;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有限,也缺乏和汉族学生沟通的主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民汉学生看似亲如一家,其实形同陌路,有的甚至有很多误解和隔阂。
调查者曾在阿勒泰市三中进行调研,该校是民汉合校,少数民族学生都是维吾尔族。被调查者中有近一半的汉族学生表示少数民族学生“很没礼貌”、“很野蛮”、“光欺负人”等,表示愿意主动与少数民族学生交往的只是个别。而被调查者中的少数民族学生对汉族学生的认识则是“骄傲”、“爱打扮”、“不团结”等,交往意愿同样很低。不仅是学生,就连维吾尔族老师和汉族老师都没什么交往,甚至连办公室也是分开的。
4.4 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原因
4.4.1 地域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如果家庭的、学校与社会生活中的语音环境都偏重民族语言,那么这种语言文化环境会对其汉语学习产生不利影响。”[7]在南疆四地州维吾尔族聚居区长大的孩子正是缺少良好的语言文化环境,虽然在学校学习汉语,但是离开了课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使用汉语。访谈对象中的古丽努尔·努日麦麦提同学(学前教育19-1专业,被调查时为人文学院预科生,女,和田洛浦县人)在访谈中告诉调查者,学汉语的过程中,除了上课造句、读课文用汉语,其他时候根本不说汉语。而对全班同学来说,能在课堂上用汉语表达的机会也是非常少的。
另外,当家长自己文化素质不高时,即使关心孩子的学习,有时也不知该如何参与,更多的是把教育的责任完全移交给老师。也有家长则毫不关心,孩子放学后常常是帮忙干活儿,甚至连写作业的时间都没有。大部分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处于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接触汉语的机会少,学习汉语的主动性不高,学习效果就不会好。
4.4.2 政策落实不到位
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了实施双语教育的方针,对双语教育提出全面要求,各地党委政府都制定了落实的规划和步骤。但是很多地方双语教育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很难将文件精神真正落实到位。要解决师资、教材、不同阶段教学衔接等问题,需要因地制宜调整规划。如在南疆四地州,双语教师紧缺、教学能力低和汉语水平低的情况非常突出。为了完成自治区的双语教师培训指标,很多学校在师资不够的情况下还要派出培训,汉语课的教学任务几乎全落在实习生的身上;相当一部分年纪大的老师已经不能适应双语教育的要求,但是不愿转岗,还占着编制;本科学历的教师和中专学历的教师享受的是同样待遇,教师工作积极性低,流失严重;只用考试成绩评价汉语教学质量的高低,重点关注双语班,忽略了普通班的学生等等。
5 提高维吾尔族学生汉文化接纳程度的对策
5.1 提高双语教师的综合素质
实施双语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师资问题。“是否有足够数量的、合格的双语教师是决定新疆双语教学能否实施的关键。”[8]而目前“全疆少数民族学校从总的情况来看,南疆地区普遍缺教师,……北疆地区教师总量基本满足,但也存在结构性短缺现象。……长期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队伍客观存在的‘一缺二低’问题(汉语交际能力低、教师业务水平低)”[8],已经成为制约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的瓶颈。
尽管十多年来国家和自治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推动双语教师的培训工作,培训效果却不够理想。调查者在阿克苏拜城县进行调研时,拜城县教育局双语教研室主任说:“每年的双语教师培训任务给各个中小学的教学工作也带来一些影响,首先是在校的教师数量满足不了教学要求,有的学校全靠实习支教的学生填补空缺;其次是培训回来的老师并不能全部实现转岗,即使是培训结业时通过了汉语水平等级考试的要求,能够在返校后顺利担任双语教学的还是少数。”拜城县康其乡中学的一名老师说:“双语教师的培训虽然很好,但是很多老师都是被迫参加的。一是因为老师们年龄层次不一样,受教育经历不一样,在同一个培训班上学习,不能统一进度,学习困难大;二是即便能通过最后的结业考试,回到学校以后还是教书本上那些东西,能理解的理解,不能理解的一样讲不清楚;三是老师们多数都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阶段,家庭生活方面也各有难处,大部分老师并不是自觉自愿地参加培训的,在培训过程中要么总是找机会请假,要么就是人在课堂心在家,学习效率不高。”
南疆地区很多双语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包括职业道德、双语能力、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都比较欠缺,必须要通过完善现有的双语教师培训体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首先,要让教师们先在思想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即双语教育意义何在,双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到底是什么。“实施双语教学,用汉语授课,这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转换、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学习习惯的转换。要实现这种转换,需要多方努力,特别是需要教师本人的愿望、意志和刻苦努力。”[9]其次,在培训中增加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内容,引导教师对中华文化有正确的认知,培养教师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力和包容的心态。再次,负责培训的教师也应该是双语人,应具备很强的教学能力和文化素养,除了能在双语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方面胜任培训任务以外,还应在课堂组织、教学方法和授课技巧方面对参加培训的教师起到示范作用。同时,在培训中增加课堂教学实践的环节,由双语教育专家进行指导。培训结束后,受训学校要关注参加过培训的教师们,在他们教学期间予以更多的支持,也要相应增加考核的内容。
5.2 超越功利性的语言学习目的
“双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中包含有两种语言和文化因素,即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来学习中华民族文化、国家主流文化、现代科技文化,使少数民族学生能够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获得更大发展;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来学习少数民族文化,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10]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双语教育,不应该只是学会说汉语就行了,还要学好自己的母语;不应该只是为了学语言而学语言,还要通过语言,学习现代科技文化。在这方面,教育主管领导和双语教师责任重大,只有他们正确认知双语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意义,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学生与家长加强宣传和引导,才能使学生和家长在观念上形成正确的认识,才会在行动上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超越功利性的语言学习目的。
5.3 创设良好的维汉语言和文化交流环境
相互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无法实现不同民族之间语言文化的广泛交流并增进对彼此的了解。笔者认为,对这些学生来说,要促进他们汉语言文化的学习,首先要促进不同族际学生之间的交往;而促进交往最有效的方式是让他们在一起娱乐、在一起游戏、在一起学习。有条件的维语学校尽量选择民汉合校,不能实现民汉合校的,根据学校所在位置,尽量寻找距离较近的汉族学校结成友谊班级,鼓励并帮助学生结对子。民汉合校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不同年级或不同年龄段组建兴趣小组或课外活动小组,让维汉同学都必须参加进来,同时选派指导老师,每天抽出一定的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训练或活动,引导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交流,互学语言,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维吾尔族聚居区中单纯的维语系学校则要自己想办法创造条件,如充分使用多媒体技术扩展教学内容;通过电影、图画、音乐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有直观的认识;聘请能熟练使用双语的当地的艺术家、运动员、作家或商人等来学校和学生交流互动;实行寄宿制的学校,要求校园公共语言一律使用汉语等。
5.4 加强文化教材的编制、出版及推广
就目前双语教学使用的教材来看,各地双语班主要使用的是人教版的各科教材,部分课程使用汉语统编教材,部分课程使用民文教材。而民文教材全部是从汉文版教材翻译过来的。这些教材的内容缺少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不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再者,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尚未能很好地了解本民族文化,就马上接触和本民族文化有一定差异的国家主流文化,如果教师的讲解不够清晰,便容易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视点是必需的”[11]。因此,在教材改革方面,编制、出版与推广适合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现实需求的文化教材是首要任务。文化教材要让维吾尔族学生既了解中华文化,又学习汉语交际技能,还要考虑到跨文化交际;可以作为教辅资料,也可以单独设置文化课进行使用。教材编写目标应该是既要向学生系统介绍汉民族表层的日常交际文化,又要介绍相关的深层心理习惯、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既要有文化对比的内容,又要有进行口语表达的训练。内容的安排上应该以当代文化为主,客观描写维汉文化差异,避免出现文化误读,切实为现实交际服务。
5.5 因地制宜,调整落实并有效执行双语教育政策
各地党委政府应该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通过踏踏实实的调研,切实了解本地双语教育现状、困难,倾听师生、家长们的心声,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落实双语政策的规划。如,根据本地各所学校具体师资情况和教学需要,有针对性地派出参加培训的教师;做好年纪偏大和不能适应双语教育的教师们的转岗工作,如考虑转到教辅岗或者管理岗等;根据双语教育发展的需求,积极向自治区申请,增加双语教师编制,引进学历高、双语水平高、有责任心的老师,提高双语教师队伍质量;严格学校管理,加强制度建设,根据实际情况实行绩效考核,提高教学奖励额度。激发双语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维护优秀教师的尊严;在汉语教学方面对双语班和普通班的少数民族学生一视同仁,创新教学评价体系。同时积极争取非政府组织与个人对双语教育的投入,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等。
6 结语
在新疆,扩大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交往范围,增进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教育和引导维吾尔族民众正确处理好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和对汉文化认同的关系是一个长期过程。新疆双语教育的深入开展不仅要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技能,更要通过双语教育去学习了解、认同与接纳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文化,才能增进维汉族际之间的交流交往,才能维护民族团结,培养他们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激发他们学习以汉文化为主要信息载体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才会真正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社会快速发展,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新疆的团结与和谐、稳定与发展。
[1] 陆学杰.文化认同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J].广西社会科学,2009(7):84-87.
[2] 新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年鉴2011[M].乌鲁木齐: 新疆年鉴社,2011:1.
[3] 陈世明.新疆民汉双语现象与社会发展之关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381.
[4] 张洁茹.东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差异——禁忌语[J].宁夏社会科学,2009(2):171.
[5] 余理明.韩建侠.双语教育论——加拿大浸入式教育对我国高校双语教育的启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54-155.
[6] 王兆璟,黄非非.维汉双语教学现状及有效策略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10-116.
[7] 陈世明.新疆民汉双语现象与社会发展之关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415.
[8] 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82-83.
[9] 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86.
[10]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双语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解读[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2.
[11] 安然,崔淑慧.文化的对话:汉语文化与跨文化传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68.
A Survey Report on the Han Culture Accepted by Uygur College Students in Tarim University
Zhang Li Xie Gui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Xinjiang is a place where many ethnic groups live, where the minority students are the main successors and developers of advanced ethnic culture .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the Chinese level of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Therefore, their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has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ethnic group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Uygur students in Tarim University, the acceptance of Han cultur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and It is deduced that the study of Han culture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students in their hometown,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Han culture. Accordingly,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counter measures about improving the acceptance of Han culture of Uygur people in term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re put forward.
Uygur people; the acceptance of Han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文章编号:1009-0568(2016)04-0014-09
2015-12-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1XMZ066);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TDSKSS1102)。
张砾(1981-),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双语教育、新疆区域民族关系和跨文化交际。 E-mail:10092566@qq.com
*为通讯作者 E-mail:249603691@qq.com
C956
A
10.3969/j.issn.1009-0568.2016.0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