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辨析
2016-02-05徐卉
徐 卉
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辨析
徐 卉
为了能够从建筑可译论的角度,对北京圣公会救主堂以及它所代表的近代 “中西合璧式”教堂建筑遗产在风格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对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进行细读和分析。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当时向苏联学习的愿望和实践可能直接促使梁思成提出了建筑的 “可译性”。根据他在这一时期的少量建筑设计实践,能够看出建筑可译论不仅局限于对建筑的 “词汇”的翻译,还包括对于施用建筑的 “词汇”的原则和方法—建筑的 “文法”的翻译。而建筑可译论的提出,对于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思想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梁思成;建筑的 “词汇”与“文法”;建筑可译论
本文源自对一类具体而实际的近代建筑遗产—“中西合璧式”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关注。我曾经以其中的代表性建筑之一北京圣公会救主堂(Church of Our Saviour in Peking, 1907)为研究对象(图1),通过对这座教堂的建造者史嘉乐主教(Charles Perry Scott, 1847~1927)及其所在教区英国圣公会华北教区的建筑实践进行研究,寻找形成这座教堂“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元素的历史来源①。然而,仅仅找到这些建筑元素,并不足以解释它们具体是如何在一个建筑物中相结合,从而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换句话说,我找到了“中”和“西”的建筑元素,但是并没有解决他们如何结合成“璧”的问题。
“合璧”的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南朝江淹的《丽色赋》中有“赏以双珠,赐以合璧”之句,这里的“合璧”,是指将两个半璧合成一个圆形,有“完满”的意思;清代李伯元在《文明小史》中说:“管夫人的写竹,有赵松雪的题咏;柳如是的画兰,有钱蒙叟的题咏,多是夫妇合璧,这就很不容易呢!” 可见“合璧”还有汇集两者之精华、两相对比参照的意思。民国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传入,“合璧”经常被用来形容结合中国与西方元素的事物,例如茅盾在1936年发表的《故乡杂记》中曾经写道:“从火车上就看见‘欢迎国联调查团’的白布标语横挂在月台的檐下,这是中英文合璧的标语。”在中国近代基督教教堂建筑中,也存在众多的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西方外来建筑元素的“中西合璧式”教堂,那么它们是如何结合成璧的?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判断这种结合的优劣?又应该如何评价它们?在这些问题上,赖德霖的《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一文②,提供了再次贴近这座对我而言颇为熟悉的教堂建筑的新角度,即梁思成的 “建筑可译论”。赖德霖先生在文中从这个角度对北京圣公会救主堂进行了分析:
……中国近代还有若干“西译中”建筑的原型来自西方的哥特建筑传统。由主教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主持、建于1907年的北京南沟沿的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Beijing Anglican Church,又称安立甘教堂)为已知北京近代建筑中最早采用中国风格的教堂,该教堂的平面以祭坛为中心,其北是长3开间的圣坛,其南为长6开间的中厅,祭坛东西两侧各为长2开间的侧厅(transept),整体构图是哥特教堂常见的拉丁十字(Latin cross)。但该教堂的屋顶结构采用木屋架,高起的中厅和低下的边廊部分分别覆青色筒瓦,使得建筑的外观呈现为中式的重檐形象。此外,屋顶上的钟塔和采光亭也不是哥特式的尖塔,而分别是三重檐和双重檐的两座八角亭阁,它们的平面与哥特教堂八角尖顶(spire)相似。可见整座建筑也经过了从西到中的“翻译”③。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风格是由中西两种建筑风格结合而成:来自西方哥特传统建筑风格的元素,以拉丁十字形平面为代表,以及来自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元素,如木屋架、青色筒瓦、重檐和八角亭阁。但是这座教堂真的像这段论述最后所说的那样,是“整座建筑”从西到中的“翻译”吗?
先来看看听上去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木屋架”结构,不难发现救主堂的屋架确实使用的是木材,但是它的结构却是一种源自西方传统的“立字桁架(king post truss)”结构(图2),并不是中国传统建筑抬梁式或者穿斗式的屋架结构,我们可以先把这种情况归到“假翻译”的范围。与之相似的一个“翻译”是救主堂呈现“重檐”形象的屋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檐屋顶,是在基本屋顶下重叠下檐形成的,作用是扩大屋顶以避风雨,另外可以增加屋顶的高度和层次,调节屋顶和屋身的比例。而救主堂的“重檐”效果则是由中殿和侧廊的高度差直接造成的(图3),从建筑外部的结构上看,与意大利罗马式教堂的典型代表—比萨大教堂几乎完全一致(图4)。如果我们分别从结构和建筑材料来看这个对于屋檐的“翻译”,就会发现屋顶的结构并没有被“翻译”,视觉效果上呈现出的类似“重檐”的形象,似乎是因为对建筑材料的“翻译”而造成的。也就是说,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屋顶并没有被完全的“翻译”,或许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半翻译”的范围中。因此,严格来说,赖德霖先生所说的中国风格的元素中,真正经过“西译中”的只有屋顶采用的青色筒瓦,以及分别作为钟楼和采光亭的双重檐和三重檐八角亭阁(图5、6)。仅仅在北京圣公会救主堂中,从建筑可译论的角度来看,对建筑的“翻译”似乎呈现出“假翻译”、“半翻译”和完全的“翻译”三种情况。

图1:北京圣公会救主堂(1928年摄)

图2: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立字桁架屋架结构

图3: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由于中殿与侧廊之间的高度差形成的“重檐”效果
在语言学中,翻译是表达意义相同的“词汇”之间的直接转换。那么建筑的“翻译”,应该就是不同风格建筑中为了满足同样的需要和解决同样的问题而出现的构件之间的转换。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判断,我们又可以发现北京圣公会救主堂对于哥特式教堂钟楼和采光亭的“中译”并不是一种对应“词汇”的翻译。如果完全按照英国哥特式教堂的要求,钟楼和采光亭应该使用中国的“塔”作为对应的“词汇”才对。而救主堂却用中国传统建筑语言中亭或者阁这两个“词汇”翻译了英国哥特式教堂建筑中的“塔”,这证明在实际的“西译中”过程中,还存在不采用对应“词汇”进行“翻译”的情况。
通过对北京圣公会救主堂中存在的建筑“翻译”现象的分析,我们发现至少有“假翻译”、“半翻译”、完全“翻译”以及一种采用非对应“词汇”进行“翻译”的情况,那么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类型的“翻译”?通过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是否可以更加系统和规律地对建筑的“翻译”现象进行总结呢?如果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弄懂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究竟是么。而仅仅依靠《中国建筑的特征》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论述似乎无法全面地把握这个理论。为了能够从建筑可译论的角度,对北京圣公会救主堂以及它所代表的近代“中西合璧式”教堂建筑遗产在风格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对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进行细读和分析。
目前关于梁思成建筑可译论的研究主要有李华《从布杂的知识结构看“新”而“中”的建筑实践》④、赖德霖《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⑤和《构图与要素—学院派来源与梁思成“文法—词汇”表述及中国现代建筑》等。
李华在《从布杂的知识结构看“新”而“中”的建筑实践》针对梁思成的建筑“可译性”的观点包括:对建筑的“文法”的演绎是梁思成提出不同国家的建筑形式具有“可译性”的前提,但是将语言作为“可译性”的类比是一个含混且容易引起误会的比喻。原因在于这种方式无法描述语言的特点:一方面,不同语言的词汇是基于意义建立对应关系,但是它们的意义是“相互交叉而不是完全重合”的;另一方面,不同的语法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因为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使用标准。换句话说,无论是词汇还是语法都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而梁思成将“翻译”的方法引入建筑时,假设了一个前提,即“建筑中有一种通用的‘规则’,它不仅使不同建筑的直接比对成为可能,而且相对简单”。赖德霖则认为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是19世纪以来关于“中国风格”建筑创作的最清晰的理论,他在文章中谈到“翻译”的方法是基于认为中西古典建筑要素在造型部位和结构功能上具有对应性的观点,而在“翻译”的方法之外还有另一种“中国风格”的建筑设计方法—“点缀”。他认为“翻译”实例通常以西方建筑的经典构图原型为参照对象,并强调对西式原型整体意象的中国化,而“点缀”是按照西方建筑特别是现代建筑的原理设计出的形体构图基础上局部添加中国风格的建筑或装饰要素。
根据对梁思成相关著述的细读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可译论”是以他对建筑的“文法”与“词汇”的表述为前提的,但是“文法”与“词汇”的表述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而梁思成对中国风格的新建筑的探索则开始的更早,那么为什么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才提出建筑的“可译性”问题?虽然梁思成是在1954年发表的《中国建筑的特征》中首次明确提出建筑的“可译性”问题,但是在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已经可以体会到他对建筑的“可译性”的理解了:“凡是别的民族可以用他们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个民族没有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形式建造的”⑥。也是在这次发言中,梁思成提出了要向苏联学习的观点,而建筑可译论从最基本的层面上看,即是一种快速而有效地学习和掌握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设计的方法。

图4:意大利比萨大教堂

图5: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双重檐八角形亭子钟楼

图6:北京圣公会救主堂的三重檐八角楼阁式天窗
一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发表了一系列涉及学习苏联建筑设计思想及其实践的文章,其中包括《〈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译者的体会》⑦、《苏联专家帮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⑧、《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⑨、《我对苏联建筑艺术的一点认识》⑩、《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专题发言摘要》⑪等等。
在《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一文中,梁思成总结了苏联建筑专家在建筑设计思想上对他产生的五点影响,其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筑的民族性”,在同时期关于“文法”与“词汇”的讨论也开始使用“某一民族”的建筑这种表述方法。而在继承优秀的建筑遗产方面,苏联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因为苏维埃建筑“通过新的形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实现了古代的优秀传统。这说明在苏维埃国家内,古代遗产和现代生活之间,批判地应用过去和大胆创造新的之间,是没有矛盾存在的”,这与梁思成一直以来想要继承中国建筑的优秀传统不谋而合。他在文章中写道:
因此,我们建筑也就应该要肯定地是民族的,带有我们的民族特性,表现着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我们反对“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我们的建筑可以吸收外国进步的技术,同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筑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我们要清理我们古代建筑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
……在建筑上,每个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灵活地运用建筑的材料、构件,为了不同的需要,构成极不相同的形体,创造出极不相同的类型,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结论是:凡是别的民族可以用他们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个民族没有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形式建造的。⑫
不难看出,梁思成针对如何创造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的问题提出了要“吸收”两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筑”学习,其次是吸收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民主性的精华”。从这个角度看,梁思成提出的建筑的“可译性”除了使继承中国建筑传统成为可能之外,也使得中国的建筑师能够直接地利用当时苏联的建筑创作实践已经取得的成果。而梁思成在1953年2月至5月访问苏联期间,苏联建筑师将本国各主要民族的建筑传统分别吸收到不同城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创作中的做法,更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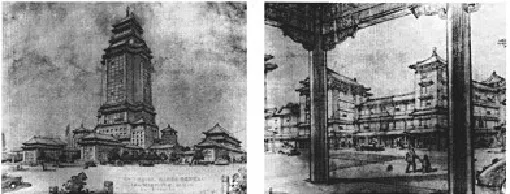
图7:《祖国的建筑》中的“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

图8:北京民族文化宫(1959年建)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一文正是从苏联考察回国后写作的,他在开篇就点明:“我们在苏联学习中最主要的收获是认识了苏联建筑的总方向。基本原则就是研究、设计、建造、发展反映社会主义面貌并具有民族特有风格的建筑”。梁思成在苏联到访莫斯科、基辅、塔什干等多个城市,苏联各民族不同的建筑形式难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文章中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市的原有风格主要是‘俄罗斯古典式’,……乌克兰的民族形式就很明显地和西欧古典不同。……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民族形式……和我们祖国的建筑比较接近或类似的作风”。因此,可以说在“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个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苏联各民族都各自创造出本民族的建筑形式。《我对苏联建筑艺术的一点认识》中也提到苏联对各民族建筑遗产的应用问题:“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院士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但不消灭各民族间的区别,而且要发扬各民族的文化。他认为,建筑师必须以艺术家的身份在他的作品中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建设之伟大,而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的美的问题的时候,就应当应用各民族的建筑遗产。这种应用遗产并不是带批判地吸收,而是经过深入研究,去其糟粕,吸收其精华”。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应用民族遗产中的“精华”,来创作“能表达崭新的内容,适合于新中国的建筑”呢?梁思成1953年10月在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说:
在我们实践的尝试中,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应用遗产中的优良传统。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吸收“外国的、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在吸收外国的或其他民族的“用得着的东西”时,主要的不在其形式,而在其方法与方向。我们要尽量的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的基础。我们要学习罗马人怎样在土斯干尼原始建筑的基础上吸收希腊的东西而创造出辉煌的罗马建筑;我们要学中国南北朝的匠师怎样在汉朝的重楼的基础上吸收印度的东西,创造出中国型的佛塔;我们要学习欧洲的许多民族怎样在中世纪建筑的基础上,吸收希腊罗马的传统,创造出文艺复兴的建筑;我们尤其应该学习苏联的各民族怎样各自在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古典的和新的手法,利用工程技术的所有成就,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俄罗斯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阿尔美尼亚的,乌兹别克的,……苏维埃建筑。……我们要大胆地吸收,大胆地创造。但是吸收不等于生硬地搬用。我们必须反对生硬的搬用,那样就必然会破坏或歪曲我们人民的艺术。我们也坚决反对墨守成规,一成不变。

图9:那布莱斯卡市议会大楼(1922~1932年建)

图10:梁思成建筑设计中窗户的比例

图11:民族文化宫对窗户比例的处理和强调
这篇文章几乎与《中国建筑的特征》同时发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梁思成所说的从吸收“用得着的东西”到创造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的方法,尤其还强调向苏联的各民族学习如何各自从自己的民族传统出发创造各民族自己的“苏维埃建筑”。从上述几篇文章来看,梁思成对于为什么及如何向苏联学习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在这个背景下,建筑“可译性”的提出无疑与学习苏联的建筑创作思想与实践有关。换句话说,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的来源,的确像李华、赖德霖等学者所说的那样,与梁思成接受的巴黎美院派的教育背景有关。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向苏联学习的愿望可能直接促使梁思成提出了建筑的“可译性”。
梁思成在1954年发表的《中国建筑的特征》中首次明确提出建筑的 “可译性”,他说:
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多少民族创造了多少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的窗子“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罗马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造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就如同不同的民族有用他们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⑬
在这段论述之前,梁思成先是对中国建筑的“文法”与“词汇”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接着他提出了在中国的建筑传统中值得学习和吸收的东西—“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认为“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的有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单单从梁思成当时提出建筑的“可译性”的表述来看,这种“可译性”是存在于“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而不是古典建筑与现代建筑之间的。如果我们结合同时期他关于向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与实践学习的观点来看,这种民族间的建筑“可译性”很有可能是从苏联各民族的建筑实践所呈现的各不相同的形式中获得灵感。
需要强调的是,在梁思成看来苏联在二战后的建筑设计是成功的,苏联建筑师在建筑设计中尊重“当地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环境”的做法,以及窝罗宁在《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中提出的建筑师对于历史和后代都负有重大责任的观点,不但符合梁思成通过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来创造新建筑的设计思路,并且与他对于建筑师在专业伦理上的要求十分相似⑭。早在1932年他就提出“(建筑师)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的观点,而建筑不仅是建筑,还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⑮。因此,当他与林徽因通过窝罗宁的著作得知苏联建筑师的创作思路是“考虑到民族传统,把它融汇到新计划之中;把它和新兴的,现代标准所需要于建筑的各方面调和起来”,同时在保护文物建筑和传统时倾向于“特别小心温柔”,在对历史悠久、古建丰富的城市进行规划时“准备按照古代都市计划的制度将城市重建起来—当然加上现代化的改善”时,自然而然地得出要向苏联学习的结论。而当时苏联在战后重建中的各项建筑设计与规划的成功,也坚定了梁思成创造中国新建筑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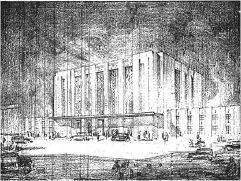
图12:《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火车总站图(19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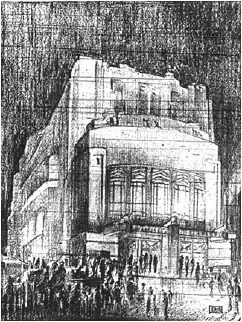
图13:《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民众剧场(1930年)

图14:《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海光寺公园市立图书馆(19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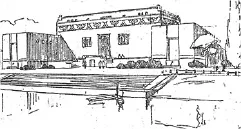
图15:《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特二区河岸林荫大道市立美术馆(1930年)
二
令人困扰的一点是,梁思成在1954年《中国建筑的特征》中提出各民族建筑的“可译性”问题,但是他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再也没有明确地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论述。这或许是因为就在《中国建筑的特征》发表后不久,苏联建筑界的指导方针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1954年11月30日,苏联召开了全苏第二次建筑工作者会议,会上严厉批评建筑设计中的复古主义、浪费和虚假装饰的问题⑯。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中国也开始将探索民族形式的建筑实践视为复古主义和浪费的行为进行批判,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思想被认为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而遭到反对。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梁思成没有进一步讨论在向苏联学习的背景之下提出的建筑的“可译性”问题。
梁思成关于建筑可译论的论述,大多是后来经过他的学生张镈转述的。张镈是梁思成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的学生,毕业后在基泰工程司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又受到杨廷宝的诸多影响。他于1951年离开香港基泰工程司回到大陆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曾经设计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友谊饭店、民族文化宫等建筑。张镈在《怀念恩师梁思成教授》一文中回忆到,在1953年举行的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建筑界专家学者多数都认为“走民族形式的方向是对的,但怎么走法则都说不清”。针对这个问题,梁思成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建筑可译论的长篇发言⑰。这篇发言稿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1954年2月的《新建设》杂志上,即在上文讨论过的《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先是讲到与当时的苏联相比,中国的建筑师对于建筑的艺术性没有给予应得的重视,接着谈到建筑的阶级性和党性,认为苏联建筑选择民族形式是一种“同资产阶级的建筑的斗争”,采用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建筑具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随后,梁思成转而谈到中国的建筑界应该如何进行自己的建筑创作的问题,首先要对新时代的建筑的特点有所认识,即“在生产和生活上满足对于一切实用方面的要求,同时还是高度科学的、经济节约的工程结构和具有崇高思想的艺术性:我们要要求得到这三方面的辩证的统一,而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然后一方面要向苏联学习,另一方面要继承并发扬民族传统,而在整理和研究民族遗产的工作中,还是要向“最好的范本—苏联”学习。最后梁思成强调“一切创造只有理论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得到解答”。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吸收“外国的、我们用的着的东西”,虽然梁思成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建筑可译论,但是他用罗马建筑、中国佛塔、文艺复兴建筑以及苏联建筑作为实例,来说明如何在自己民族的建筑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因素从而创造出新的建筑形式,这一过程与梁思成对建筑的“可译性”问题的阐述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张镈在回忆录中曾经对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有所记述,他先是介绍了梁思成关于建筑的“词汇”的观点,接着说道:
……中英文字语音不同,而功能类似。文字可译,形式艺术风格可依据中西手法不同而迥异。他草画了一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轮廓图,先把中间圆顶(dome)改成祈年殿的三重檐;第二步把四角小圆顶改成方形、重檐、钻尖亭子;第三步把入口山墙(pediment)朝前的西洋传统做法彻底铲除,因为中国传统建筑从来不用硬山、悬山或歇山作为正门,把它改成重檐歇山横摆,使小山花朝向两侧;第四步,把上主门廊的高台上的西式女儿墙的酒瓶子栏杆改成汉白玉石栏板,上有望柱,下有须弥座,甚至把上平台的大石阶也改为两侧走人,中留御路的形式;第五步,把环抱前庭广场的回廊和端亭也按颐和园长廊式改装,端头用重檐方亭加以结束。最后,梁师认为,用中国话说中国式的建筑词汇,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和形象风格加以改头换面,就是在高大到超尺度的圣彼得大教堂上去运用,同样可以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改成适合中华民族的艺术爱好的作品。⑱
在张镈的这段文字中,梁思成将圣彼得大教堂“翻译”成“适合中华民族的艺术爱好的作品”的方法,可以被看作是在1954年《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关于各民族之间建筑的“可译性”问题的一个直接实例,但是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方式看上去似乎过于机械和粗暴,只是“词汇”之间的简单替换,甚至不对建筑中至关重要的比例问题做出调整。这与梁思成在其他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存在矛盾。例如他在《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一文中提醒要“创造性”地学习苏联,并且学习不应该是抄袭和模仿,在创作实践中要“大胆地吸收,大胆地创造。但是吸收不等于生硬地搬用。我们必须反对生硬的搬用,那样就必然会破坏或歪曲我们人民的艺术”。
正如上文所说的,梁思成虽然在《中国建筑的特征》中提出了建筑的“可译性”问题,但是他却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论述,导致我们无法在其著述中对建筑可译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同一时期梁思成所做的能够体现建筑可译论的一个建筑创作实践,即1954年出版的《祖国的建筑》的结尾处给出的“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及相关的一段论述:

图16:吉林大学教学楼和礼堂东楼 (1930年建)

图17:吉林大学教学楼和礼堂东楼立面细部 (1930年建)

图18: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公共图书馆 (1914~1917年建)
最后,让我提出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作为在我们开始学习运用中国古典遗产与民族传统的阶段中所可能采用的一种方式的建议。这两张想象图,一张是一个较小的十字路口小广场,另一张是一座高约三十五层的高楼。在这两张图中,我只企图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
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这两张图都不是任何实际存在的设计,只是形象处理的一种建议。我们在开始的阶段掌握了祖国建筑的规律,将来才有可能创造出更新的东西来。这样做法是否正确,希望同志们给予批评。⑲
从图片上看(图7),梁思成所设计的这两组建筑物群无疑都采用了“翻译”的方法,但是如果配合他的文字介绍来看就会发现,在“翻译”建筑的“词汇”的基础上,梁思成还注意到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问题。梁思成曾经在《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问题》中总结了建筑师在设计新中国建筑中所遇到的难题:“例如以民族的形式创造高层建筑物的困难就很突出。如何在大建筑群的布置中取得民族风格,也许还比较容易解决。而多层楼的窗子的处理,和房屋顶部的结束,以及建筑轮廓线的民族风格问题,就常常是建筑设计时的最大苦恼”。而早在1950年他就针对中南海修建的宿舍的窗户的形式提出过“避免西洋系统的窄长的长方形而采用中国近似方形的比例,强调横着排列的方式”的建议,以此来表现中国建筑的风格⑳。根据赖德霖、朱涛等学者的研究,《祖国的建筑》一文中的这个设计,以及梁思成的学生张镈在1959年所设计的民族文化宫(图8),都是以美国近代著名建筑师古德休(Bertram Grosvenor Goodhue, 1869~1924)在1924年设计的那布莱斯卡市议会大楼(Nebraska State Capitol, 1922~1932年建造)作为“翻译”的对象(图9)㉑。
在此,我们从建筑可译论来的角度试着分析一下梁思成所设计的这座高层建筑。以屋顶和窗户这两个建筑的“词汇”为例,首先,梁思成将那布莱斯卡市议会大楼的半圆穹窿“翻译”成重檐歇山屋顶,如果从翻译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对建筑的“词汇”的“直译”。半圆穹窿和重檐歇山屋顶在形式上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无论在视觉效果还是实际功能上都具有非常相似的意义:西方古典建筑中,穹窿顶一方面给建筑外观带来一种醒目而壮观的效果,使得建筑具有一种特别的轮廓线,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建筑内部的光线来源,特别是对于宗教建筑和公共建筑而言,在营造建筑内部的氛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而传统中国建筑的屋顶在建筑物轮廓线上带来的效果不用赘述,是林徽因、梁思成总结出的中国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翼角翘起”与“飞檐”的处理实际上也使得更多的光线能够进入室内。半圆穹窿和重檐歇山屋顶形式不同而功能相同,这是建筑的“词汇”之间进行直译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们再来看看对于窗户的“翻译”。在对梁思成建筑可译论的相关讨论中,大多数人会马上注意到对屋顶的“翻译”,但是很少有人分析过他对于窗户的“翻译”。不可否认的是,梁思成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窗户在比例上的区别,而这种区别从根本上说是由建筑的结构决定的。中国传统的木构架建筑因为不需要墙体承重,发展出比例更为方正的窗户,而西方传统建筑由于对承重墙的依赖,一般的窗户比例都更加瘦长。梁思成在这张高层建筑的想象图中,显然运用的是中式窗户的近似正方形的比例(图10),如果说这次建筑“翻译”的“原文”是那布莱斯卡市议会大楼,那么这座西方建筑的窗户的瘦长比例明显被“翻译”成中国那种更加方正的比例了。在张镈设计的北京民族文化宫中,窗户也采用了中式窗户的比例,同时还用装饰进一步强调了这种窗户比例所表现出的横向的趋势(图11)。根据梁思成对建筑的“文法”的定义—施用建筑的“词汇”的法式即原则和方法就是建筑的“文法”,这种将西方建筑的窗户所具有的瘦长比例替换成中式窗户的近似正方形的比例,已经进入了“文法”翻译的层面。在此可以通过一个语言翻译的例子来帮助理解这种“文法”的翻译,法语的“我爱你”是Je t'aime,其中Je是“我”,te(t’)是“你”,aime是“爱”,如果我们直接按词汇的顺序进行翻译,得到的结果是“我你爱”,这是因为法语有宾语前置的语法规则。如果我们要将Je t’aime翻译成中文的“我爱你”,那么就需要把这个句子中原来的宾语前置的语法也“翻译”成中文的主谓宾顺序的语法。而梁思成对于窗户比例的“翻译”,正是类似的对于建筑的“语法”的翻译。

图19:巴黎圣日内维耶芙图书馆 (1838~1850年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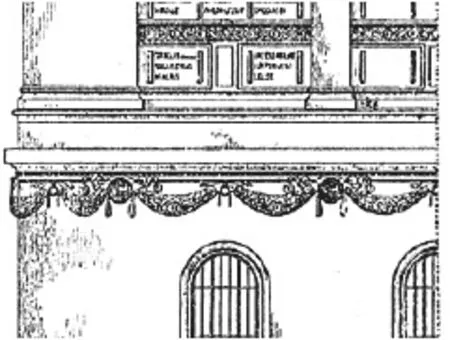
图20:巴黎圣日内维耶芙图书馆的柱顶盘连续花环饰

图21: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公共图书馆的柱顶盘连续花环饰

图22:天龙山北齐石窟中仿木构石刻
出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无法找到更多梁思成自己关于建筑可译论的说明和阐释,只能通过间接的材料进行梳理和推测。梁思成对于建筑的“翻译”真的仅仅局限于“词汇”的层面吗?在各位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节通过分析梁思成在《祖国的建筑》中提出的中国风格的高层建筑设计,发现了“屋顶”和“窗户”的两种不同层面上的“翻译”,这仅仅是一个小的突破口,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总结出更多不同的“翻译”方法,丰富对于建筑可译论的认识和理解。

图23:吉林大学教学楼和礼堂东楼转角处
三
梁思成提出建筑的“文法”与“词汇”的概念,进而发展出建筑可译论,这对他的建筑创作到底有没有产生过影响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针对梁思成早期的建筑实践之一《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的公共建筑设计进行分析,此时对于建筑的“文法”与“词汇”的研究尚未展开,以此为例查看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思想和方法,与前文所讨论的在建筑可译论影响下的建筑设计进行对比。
对《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较早的研究是高亦兰、王蒙徽的《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㉒,作者在引言中表示这篇文章“仅就梁思成在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方面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作一个较系统的介绍,重点在建国初期梁思成所主持的首都规划编制工作”,认为《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是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会规划思想的两个来源之一,并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介绍了《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思想和内容,总结这一时期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特点。而关注到《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公共建筑的形式问题的研究是李军的《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作者以此为例说明梁思成早期的建筑设计使用的是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老师保罗·克列的方法㉓。朱涛在《阅读梁思成之七—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综述:1930~1949》一文中比较具体的讨论了张锐、梁思成合拟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㉔。在讨论到两人的具体分工时,根据1930年9月出版的《城市设计实用手册—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的封二注释“天津规划,由张锐制定、由梁思成绘制”,以及方案的内容来推断,“张锐作为公共管理和市政专家,负责文案中大部分文字,尤其是公共政策提议部分;梁思成作为建筑师,主管其中‘有形’的空间部分:街道网划分、城市设计和公共建筑提案。梁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方案中22张插图和少部分文字阐述”。按照这个思路来推测,《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的第十一部分“公共建筑物”应该就是梁思成编写的。朱涛将梁思成在该部分提出的“公共建筑物形式之选择”分为两类:“新式中国建筑”和“新派实用建筑”(即现代主义建筑),并与1929年南京国都建设委员会编写的《首都计划》中的公共建筑形式进行了对比分析,阐明了《首都计划》对于《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在各个层面上的影响。
梁思成在第十一部分“公共建筑物”的最后明确了重要公共建筑物的类别。这些建筑物如果按照前文的讨论来划分,首先是采用“新式中国建筑”形式的市行政中心区建筑,包括市议会、市行政机关及地方法院。而采用“新派实用建筑”的公共建筑物有火车总站、美术馆、图书馆、民众剧场和公营住宅。根据方案中的附图“火车总站图”、“民众剧场”、“海光寺公园市立图书馆”以及“特二区河岸林荫大道市立美术馆”(图12~图15),我们不难看出“新派实用建筑”实际上存在两种风格,甚至在绘制图片的表现方式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虽然它们都是根据“用心于各部分权衡及结构之适当”这个原则来设计,但在图书馆和美术馆的设计中明显出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标志性元素—斗栱和正脊吻,因此也更多地向着“新式中国建筑”的范畴靠拢。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还无法解释出现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
尽管《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的建筑设计最终都没有实现,但在同一时期稍早梁思成与陈植、童雋、蔡方荫共同设计的原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做法(图16、17)。李军在《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认为梁思成的这一处理方法来自于他的老师保罗·克列的设计方法。克列在他设计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公共图书馆(Indianapolis Public Library, 1914~1917年建,图18)中采用了法国建筑师拉布鲁斯特(Henri Labrouste, 1801~1875)所设计的巴黎圣日内维耶芙图书馆(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 Paris, 1838~1850年建,图19)中所使用的柱顶盘连续花环饰的主题(图20、21)㉕,而梁思成在原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的设计中则代之以一斗三升与人字斗栱的饰带,在《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则采用连续的一斗三升饰带,而这一斗栱形式以及支撑其重量的八角形柱则都源自天龙山北齐石窟中对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模仿(图22)。梁思成把克列的来自西方古典传统的柱顶盘连续花环饰“翻译”为带有中国风格的斗栱饰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建筑材料的改变,斗栱原有的结构功能被削弱了。虽然一斗三升是斗栱中最简单、最原始的一种,但是它在木构架建筑中也承担着传导荷载的作用。
采用石质材料将一斗三升和人字斗栱作为饰带表现出来,使得本身源自木构架承重要求的斗栱形式失去了它在结构方面的精神,而仅仅沦为形式上的模仿。从建筑可译论的角度来看,作为建筑“词汇”的斗栱在“翻译”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本来的结构含义,这与语言翻译中的“音译”有些类似。例如我们根据发音近似的特点,把英文的sofa音译为“沙发”,在这个过程中,“沙”和“发”都失去了自身的原意,只保留了语音和书写形式。而从柱顶盘连续花环饰到斗栱饰带的“翻译”,则是将斗栱视为与柱顶盘连续花环饰性质相同的装饰构件,在“翻译”的过程中使它原本的结构含义消失了,仅仅保留了外观和形式。
这种会导致中国建筑的结构构件丧失功能的“音译”似乎与梁思成、林徽因所提倡的“诚实原则”和“骨干精神”存在矛盾,林徽因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所批评的“美术思想这边,常常背叛他们共同的目标—创造好建筑—脱逾常轨,尽它弄巧的能事,引诱工程方面牺牲结构上诚实原则,来将就外表取巧的地方”㉖,不正是这种“音译”吗?在吉林大学教学楼和礼堂的设计中,“音译”现象对中国建筑的“文法”的破坏还表现在柱网结构方面。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柱按照其所在位置及功能可以分为檐柱、金柱、中柱、山柱、童柱、角柱以及雷公柱等。其中角柱位于建筑物转角处,承托不同角度的梁枋,其上为转角铺作斗栱。而在梁思成将克列的西方古典圆柱和柱顶盘连续花环饰“翻译”成中式八角形柱和斗栱饰带的过程中,如果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的“文法”,在建筑物转角处本应“翻译”出一根角柱和一攒转角铺作,但是在实际的吉林大学教学楼和礼堂中我们发现,在建筑的转角处仅仅存在两个装饰性的壁柱和普通的斗栱,这完全不符合中国建筑的结构(图23)。
总之,以建筑可译论的立场来看,克列对于拉布鲁斯特的柱顶盘连续花环饰的“翻译”是一个建筑“词汇”的“直译”,而梁思成对克列的装饰的“翻译”应当被视为一种“音译”,这种“音译”的后果是,尽管在“词汇”的形式上保持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但是这种保持是以牺牲“词汇”在原有建筑系统中的“文法”层面上的含义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建筑可译论提出之前的部分早期建筑设计实践中,梁思成对于建筑的“翻译”还并未进入“文法”层面,例如在《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海光寺公园市立图书馆的设计中,对窗户的处理仍然采用西方建筑强调垂直的比例,这与后来他在《祖国的建筑》中的构想截然不同。
四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梁思成建筑可译论的一些观点:首先,建筑“可译性”的提出是建立在梁思成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词汇”与“文法”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与他接受的巴黎美院派的教育背景有关,同时,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愿望可能直接促使梁思成提出了建筑的“可译性”。其次,梁思成从建筑的“可译性”到建筑可译论的建筑设计思想,并不仅仅是对建筑“词汇”的简单直译,还包括对于施用建筑的“词汇”的法式即原则和方法—建筑的“文法”的翻译。第三,通过对于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实践与《祖国的建筑》一文中“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的对比,不难看出梁思成在早期建筑设计实践中存在违背他与林徽因所倡导的“诚实原则”和“骨干精神”的现象,将本来具备结构功能的斗栱处理为装饰,而在建筑可译论提出之后,对于窗户的比例问题的讨论和实践,则体现出对于建筑的“文法”的翻译,对于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思想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注释:
①徐卉:《史嘉乐与北京圣公会救主堂建筑研究》,硕士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11年6月。
②赖德霖:《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建筑师》第137期,2009年2月。
③赖德霖:《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建筑师》第137期,2009年2月,第25页。
④李华:《从布杂的知识结构看“新”而“中”的建筑实践》,该文为作者博士论文(2008年)第二章“‘布杂’的知识实践与中国建筑知识体系的构筑”中的第一节;本文参考自朱剑飞主编《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10月。
⑤赖德霖:《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原载《建筑师》,2009年2月;本文参考自赖德霖《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赖德霖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
⑥梁思成:《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本文参见《梁思成全集(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192页。
⑦林徽音、梁思成:《〈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译者的体会》,《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龙门联合书局,1952年5月;本文参考自《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
⑧梁思成:《苏联专家帮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原载《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2日第三版,后转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2期;本文参考自《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
⑨梁思成:《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原载《新观察》,1953年第14期,梁思成访苏之后所著;本文参考自《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
⑩梁思成:《我对苏联建筑艺术的一点认识》,为作者亲笔修改的一份清样,从内容上看是在1953年5月下旬访苏归国后写的,是否发表待查;本文参考自《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
⑪梁思成:《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专题发言摘要》,1953年10月在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专题发言,原载《新建设》,1954年2月号;本文参考自《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
⑫梁思成:《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本文引自《梁思成全集(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189-192页。
⑬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原载《建筑学报》1954年1月;本文引自《梁思成全集(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184页。
⑭林徽音、梁思成:《〈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120页。
⑮梁思成:《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原载《中国建筑》创刊号,1932年11月;本文参考自《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312-313页。
⑯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一代宗师梁思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8月,第235页。
⑰张镈:《怀念恩师梁思成教授》,《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91-92页。
⑱杨永生主编:《张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91页。
⑲梁思成:《祖国的建筑》,本文为梁思成在中央科学讲座上的讲演速记稿,1954年10月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单行本;本文引自《梁思成全集(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3-234页。
⑳梁思成:《致朱德信》,1950年4月4日;本文参见《梁思成全集(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82-83页。
㉑赖德霖:《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本文参见《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赖德霖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77-78页;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55页。
㉒高亦兰、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原载《世界建筑》,1991年3月。
㉓李军:《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原载《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2年4月。
㉔朱涛:《阅读梁思成之七—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综述:1930-1949》,原载《时代建筑》,2013年4月。
㉕李军:《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原载《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2年4月,第395页。
㉖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1、编辑委员会编:《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
2、高亦兰编:《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3、梁思成:《梁思成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4、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一代宗师梁思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
5、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
6、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7、(美)费慰梅(Wilma Fairbank)、成寒译《林徽因与梁思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
8、杨永生主编、《建筑创作》杂志社承编:《张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增订版)》,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9、单踊:《西方学院派建筑教育史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1、Julien Guadet, Éléments et Théorie de L’architecture, Paris: Librairie de la Construction Moderne, 1909.
12、Nathaniel Cortland Curtis,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in, Lincoln Press, 1923.
13、John F. Harbeson, The Stud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Pencil Points Press, 1927.
14、Elizabeth Greenwell Grossman, The Civic Architecture of Paul Cr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Simona Talenti, L’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en France: Emergence d’une Discipline (1863-1914), 2000.
16、Claire Barbillon, La grammaire comme modèle de l’histoire de l’art, de l’histoire de l’art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2008.
徐 卉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讲师 博士
A Discussion of Architectural Translatability Theory of Liang Sicheng
Xu Hui
For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s combine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tectural translatabili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crutinize and analyze Liang Sicheng’s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translation”. By means of reading and organizing Liang’s treatises and articles in 1950s, it could conclude that the idea of architectural translatability could be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and practice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is time Liang’s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translation” included the translation of both “vocabulary” and “grammar” which is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application of the “vocabulary”of Chinese architecuture. Meanwhile, Liang’s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translation” had a fundamental influence to his architectural design.
Liang Sicheng, th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of architecture, the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translation
J59
A
1674-7518(2016)04-01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