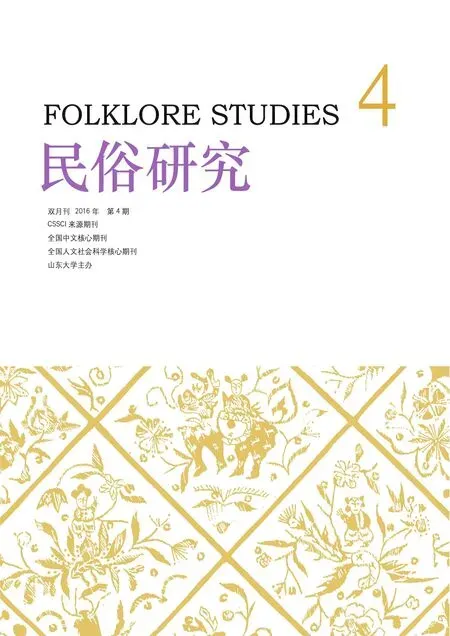“义岩别祭”:个体经验·国家认同·历史认识
2016-02-04赵彦民
赵彦民
“义岩别祭”:个体经验·国家认同·历史认识
赵彦民
摘要:“义岩别祭”是韩国为祭奠在壬辰战争(1592-1598)中殉国牺牲的民族英雄论介而举行的纪念活动。朝鲜时代,论介的个体经验存在于国家内部对其认同与否的层面上。国家在书写历史和教化民众时,对不符合朝鲜时代作为治国理念的儒家道德规范的个体经验进行了选择与排斥。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个体经验中的忠烈精神作为凝聚民族国家和化解社会动荡不安的有效因素,继而被官方吸收和改造。殖民地时期,论介的记忆成为殖民地统治者压抑与忘却的对象。战后,韩国社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论介的记忆进行了重新构建,以此来强化和想起被殖民地统治时期的记忆,促进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与社会共鸣,应对当代东亚社会中对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的差异。
关键词:义岩别祭;论介;记忆;想起;忘却
一、问题的提出
“义岩别祭”是韩国为祭奠在壬辰战争(1592-1598)①1592-1598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朝鲜请求明朝出兵共同抵抗日军而展开的三国间的战争。战争分为1592年4月-1593年7月、1597年2月-1598年12月的两个阶段,关于这次战争的称呼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韩国称“壬辰·丁酉倭乱”、中国称“万历朝鲜战争”,可以看出三国对这一战争的历史认识各有不同,本文从东亚这一区域的视角,称之为“壬辰战争”。中殉国牺牲的民族英雄论介而举行的纪念活动。纪念论介的活动初始于17世纪的晋州民间,在18世纪纳入当地官方祀典,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期间被迫中止。现今,每年在晋州举行的“义岩别祭”活动是1992年恢复的。本文即以“义岩别祭”这一战争纪念仪式活动为考察对象,探讨国家记忆与个体体验的互动关系。
“义岩别祭”作为壬辰战争诸多历史记忆中的一个表象,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其表象的背后隐含着国家的历史记忆对个体的体验有意图地选择、取舍与重构。如果用记忆的概念来审视这种选择、取舍与重构,不难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是想起与忘却相互纠缠与影响的过程。对于这样的现象,日本的政治学者石田雄指出:“如果把记忆作为理解现实世界,其理解主体的行为是构成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契机的话,必须要重新认识成为其媒介的记忆具有通过忘却与想起进行重构这一必不可缺的两面性。”②石田雄:《記憶と忘却の政治学》,明石书店,2000年,第13页。换言之,在记忆的分析框架中,在想起的同时通常伴随着忘却,为了想起某一事物、强化这一事物的记忆时必须要忘却或抑制与其背离或矛盾的部分,所以哪些部分被忘却,哪些部分被凸显,是行为主体对现实世界判断的价值取向,也是记忆与忘却的政治性体现。同样,在“历史与记忆”的讨论中,Yoneyama Lisa对记忆概念的解释与上述讨论有相似之处。Yoneyama Lisa指出,在涉及对过去表象的诸多话语中,仅有“记忆”这一话语能显示出对“被压抑的事物”的姿态;不仅是被明确的事物,被言语及形象所掩盖或者是说相反正因为此处有言语或形象,反而看不到过去的体验或情感,“记忆”就是具有暗示被抹消事物的存在的话语;无论讲述了什么,总是有隐藏在主体内心身处难以倾诉的部分,记忆是让我们想起这样结构的一个概念。*关于Yoneyama Lisa的观点详见岩崎稔、富山一郎、米山リサ(Yoneyama Lisa)的三人对谈记录,富山一郎编:《記憶が語りはじめる》,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28页。在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层面上,有把“历史”与“记忆”置于二元对立结构中的讨论,即把“历史作为权力者的产物”,是自上而下形成的话,那么“记忆”是接近民众的真实历史体验,前者是历史学家们通过客观实证的研究更能真正的反映过去,对此记忆是情绪化并且含有个人的主观色彩的表象。*富山一郎编:《記憶が語りはじめる》,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28页。对此,Yoneyama Lisa指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并非完全是对立与排他的,“记忆”被“历史”压抑并不是“记忆”的消失,并且承认“历史”对“记忆”的压抑也就是说认同“记忆”的存在;历史学作为近代的学问,是建立在单线性的时间上,历史的研究对象过去是与现在、未来完全切割开来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制度化的历史学趋于安定,但是“记忆”的出现,动摇了“历史”这一概念的安定;为了批判性地把握因为这样而产生的动摇,使用了“记忆”这一概念。*富山一郎编:《記憶が語りはじめる》,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28-229页。
关于上述记忆的讨论,前人学者在指出记忆具有想起与忘却的两面性的同时,强调需要关注记忆的忘却作用,想起与忘却是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过程。记忆的这一结构特征,为本文考察“义岩别祭”这一历史记忆的表象提供了分析的视角。“义岩别祭”祭祀的对象主体论介是朝鲜时代晋州的官妓,因为论介的身份,最初的祭祀活动源于民间。壬辰战争结束约一百年后,“义岩别祭”在地方的推动下从民间纳入官方的祭祀体系。如果这里把初始于民间的祭祀活动作为记忆看作“俗”的层面,把官方的祀典作为史看作“礼”的层面的话,是祭祀的行为主体从民间转向了国家的过程,在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梳理和考察在祭祀行为主体转变过程中蕴含的国家历史对个体体验的想起与忘却的互动关系,国家在建构自己历史记忆时对个体的体验是如何选择与取舍的,近代以后这种记忆是如何被抹消与重建的,以及在其背后隐含了哪些政治性。
二、国家记忆与个体经验:“礼”对“俗”选择与排斥
“义岩别祭”这一祭祀活动源于韩国庆上南道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晋州,在壬辰战争爆发后,晋州是连接全罗和庆尚两道陆路交通的要塞,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朝鲜为了阻止日军侵入朝鲜粮食产地全罗道,在晋州与日军展开了两次激烈的攻防战。“义岩别祭”的祭祀主体论介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1593年6月)的晋州城攻防战中。
论介在日本和中国未被更多的认知。但在韩国论介作为民族英雄,她的故事被民众广泛熟知并且不断地传颂。在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中,有论介的事迹和生平及民众对其死后祭典活动的简略介绍。关于论介的生平有如下记载,论介为朝鲜时期晋州牧的官妓,1593(宣祖26)年壬辰倭乱时,晋州城被日军攻陷,论介诱敌同尽南江,是殉国的“义妓”。*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http://encykorea.aks.ac.kr/(2016年1月10日阅览)。从这一记录可以看出论介的身份。在朝鲜时代有等级森严的身份制度。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层,即(1)两班、(2)中人、(3)常民、(4)贱民;两班是指通过科举制选拔出的官僚士大夫,这些人具有儒学的知识和思想,是朝鲜社会的统治阶层;中人是居于两班和常民之间的胥吏和具有专门技术的官员;常人主要是从事农、工、商的生产阶级,绝大多数是农民;贱民位于朝鲜社会的最下层,在贱民群体中典型的身份是奴婢,奴婢又分为官奴与私奴两种,奴婢以外还有妓生、白丁(屠户)、僧侣、巫女等。*张起灌:《朝鮮時代後期の社会変化と民衆意識の成長:近代仮面劇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大手前大学人文科学部论集》,2006年第7号,第63-64页。从当时的朝鲜时代社会的等级身份制度可以看出,论介属于身份低下的贱民阶层。论介的这一身份地位是其主体经验被主流社会压抑,未能成为历史叙述对象的主要原因。
晋州被日军攻陷时,虽然身份卑微的论介诱敌同尽南江而亡的事迹在当地民众之间广为颂扬,但在官方的记录中并未有出现。关于论介故事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朝鲜的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1559-1623)的《於于野谈》中。《於于夜谈》是广泛地记录朝鲜时代民众间流传的传承故事、街头巷尾及社会底层的奇闻逸话。论介的故事具体如下:
论介者,晋州官妓也。当万历癸巳(1593年)之岁,金千镒倡义之师,入据晋州以抗倭,及城陷军人民俱死。论介凝妆服,立于矗石楼下峭岩之巅,其下万丈直入波心。群倭见而悦之,皆莫敢近,独一将挺然直进,论介笑而迎之倭将,诱而引之。论介遂抱持其倭,投于潭俱死。壬辰之乱,官妓之遇倭不见辱而死者,不可胜记,非止一论介,而多失其名。彼官妓淫娼也,不可以贞烈称,而视死如归不污于贼,亦圣化中一物。不忍背国从贼,无他忠而已矣。欹欤哀哉。*柳梦寅:《於于野谈》(汉文本),韩国国家图书馆藏,第28-29页。
上述记录被推测是在晋州城被攻陷的第二年,柳梦寅作为三道巡按使去晋州体察民情,在整理壬辰战争牺牲者人员名册时,收集并记录的。*崔官:《文禄·慶長の役》,講談社,1994年,第202页;柳承宇:《晋州城义妓伦介考》,《韩国史学论丛》,1987年,第907页。柳梦寅被论介身份卑微却能以死守节不屈殉国的故事感动,把论介的事迹收录到《於于夜谈》的《人伦篇》《孝烈条》,并没有把其编入到《娼妓条》。
壬辰战争从开始到结束,持续七年有余。长期的战争,使朝鲜社会遭到很大的打击和破坏。更重要的是,战争也扰乱了儒家治国理念和规范。1617年,为了重建儒家规范教化民众,抚慰长期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朝鲜国王光海君(1575-1641年)决定以朝鲜时期的人物为对象,下令地方收集朝鲜社会的忠、孝、烈事例,编撰了《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被朝鲜官方认同、选择和收录于《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的烈女篇的事例共717件,其中朝鲜时代的事例占691件,在691件中有63%的事例发生于壬辰战争期间。*郑夏美:《絵画としての〈倭軍〉と烈女イデオロギー:十七世紀の〈東国新続三綱行実図〉の分析から》,大口勇次郎编:《女の社会史:17-20世紀-〈家〉とジェンダーを考える》,山川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例如,在《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烈女图卷之六中,有如下事例:
郑氏投渊:
郑氏骊州人士人尹光禄妻也,率二子避倭贼,贼执欲污之,投渊而死,儿子一人同溺死。*《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卷六《烈女》。
朴氏不污:
朴氏永同县人幼学姜景贤妻也,与其夫奉祖母避倭贼,贼至,朴氏及景贤恐害祖母,挺身出走,贼杀景贤,逼朴氏欲污之,不从贼害之。*《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卷六《烈女》。
如上所示,壬辰战争时期,作为烈女被记录于《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的女性身份,都是经过朝鲜官员的审核,符合当时朝鲜时代儒家道德规范的条件。如柳梦寅在上述记录中所述,像论介那样不屈服于入侵者的暴力以死来抗衡的官妓也为数不少,但国家在构建历史的叙述过程中,她们作为官妓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受制于朝鲜保守士大夫官员的“彼官妓淫娼也、不可以贞烈称”这一儒家思想观念的束缚,个体的经历与记忆被边缘化、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这里不难看出,历史在构建过程中,隐含的对记忆的压抑与排斥,即“礼”对“俗”的选择与排斥。
三、“民众记忆”的“官方化”:由排斥到包容
论介的个体经历虽然未被纳入到国家的宏大历史叙述之中,但在民间的记忆中并没有因为她身份的卑微而被忘却与湮没。朝鲜时代,像论介这样的妓生通常被认为是与贞节无缘,不分敌我,视所有男性为夫。而对一般女性而言,儒家思想的“忠”是她们日常行为实践的准则,“忠”的表象是对丈夫坚守节操。所以,如上文《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卷六《烈女》中朴氏事例所示那样,在壬辰战争中,大多的女性是与丈夫同存亡、或坚守贞节以死来抵抗敌人的玷污。与此相比,论介虽然是一个妓生,但她的死超越了上述一般女性的“贞烈”,成为与敌视死如归、殉国“忠烈”的象征。正是论介的这样的身份与超越先见的行为,得到了柳梦寅及一些地方思想开放士大夫及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同,论介的记忆也由此在地方社会被连绵不断地传承。
在当地,地方有识者与民众通过不同形式的彰显和祭典仪式,使论介的个体经验作为记忆被表象和可视化。1629年,朝鲜著名义军将领郑文孚*郑文孚是壬辰战争时期朝鲜的著名义军将领,组织普通百姓抵抗日军侵略,在咸镜北道吉州郡临溟村一举击败加藤清正率领的日本侵略军,史称北关大捷。(1565-1624)的儿子郑大隆(1599-1661)在论介抱敌投江的岩石上刻下“义岩”的文字。*鲁成焕:《日本人が祀った論介という朝鮮女性》,《日本研究》,2014年第49号,第117页。1651年,在吴斗寅(1624-1689)的《义岩记》中记载,每年的春秋两次举行对论介义举的祭祀,所有祭礼活动都是由官妓们来完成。*鲁成焕:《日本人が祀った論介という朝鮮女性》,《日本研究》,2014年第49号,第117-118页。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壬辰战争结束后的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末,民众就开始为论介立碑举行祭典活动了。论介殉国的美谈在当地广为传颂的过程中,为了得到朝廷的认同和表彰,当地民众不断地向地方官上书请愿。庆尚右使崔镇汉(1652-1740)被幼学尹商辅等晋州民众的上书所感动,在1721年,崔镇汉把民众的上书直接提交至备边司,请求当朝褒奖论介。
矗(石)楼之下,南江之上,有天下伤心处,乃义岩也。岩之义号,昔自龙蛇倭变(壬辰倭乱)后始有其名。则岂非千万古不朽之大义哉!何者当失守,城陷之日,师臣及守令(地方官),诸将血战,数三十员与皆抗节死义之后,惟余一妓论介者,生为国歼贼之计,(中略)唐薛仁杲之降旁地仙复叛。有王氏女取地仙所佩刀斩地仙,诏封崇义夫人。则惟此论介为公(国)除害(倭贼)之义烈,安有肯落于王女之后哉。当时战亡诸臣,则祠之额之,今无后憾。而至于论介,则百余年来,犹未能上彻天听,前后识者之。心惜义憾(后略)。*《忠烈实录》卷二《两祠宇修改先报备边司状》,韩国国家图书馆藏,第6-8页。
如以上引文所示,这封给朝廷的上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讲述论介殉国的遭遇;第二部分引用唐朝封王氏夫人为崇义夫人的典故,请求朝廷给予论介褒封;第三部分请求论介也如战亡将帅一样给其建祠题额。最终,在崔镇汉与晋州民众不断地努力向朝廷上书请求下,1722年,朝廷终于赐封了论介“义妓”的称号。论介的事迹得到官方的认可后,1724年,以崔镇汉与郑拭为中心,修建了“义岩事迹碑”;1740年,庆尚右兵使南德夏(1688-1742)修建了祭祀论介的“义妓”祠,并把晋州城沦陷、论介忌辰的6月29日这一天设定为祭日。*鲁成焕:《日本人が祀った論介という朝鮮女性》,《日本研究》,2014年第49号,第118页。此后,晋州地方废除了每年6月29日的祭典活动,把论介和祭典晋州战役中诞生的朝鲜民族英雄金时敏的忠愍祠及晋州“三忠”(金千镒、崔庆会、黄进三)的彰烈祠一同,实施春秋两次祭祀。*崔官:《文禄·慶長の役》,講談社,1994年,第207页。1868年,晋州牧使郑顯奭(1867-1780在任)重建了“义妓祠”,并且在原有的春秋两次祭祀外,恢复了每年6月举行祭祀论介的仪礼和歌舞活动。这样,官民一体祭祀官妓成为朝鲜王朝有史以来的“事件”,这一祭祀活动称为“义岩别祭”。“义岩别祭”的称呼源于当时的晋州牧史郑顯奭编写的《教坊歌谣》一书。郑顯奭非常关心妓生文化,对板索里和音乐也有非常高的造诣。在《教坊歌谣》的“义岩别祭”的条目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每年由300人的妓生连续三天举行的盛大歌舞祭典活动。*《朝鲜新报》,《朝鮮史を駆け抜けた女性たち③侵略に命をかけ抵抗した義妓-論介》2009年4月10日;http://www1.korea-np.co.jp/sinboj/j-2009/06/0906j0410-00003.htm(2014年3月6日阅览)。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论介的个体经历的记忆化是在晋州地方社会的士大夫、有识者及与论介有着相同身份官妓们的推动下,经过百余年后,于1722年被纳入到官方的祭礼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论介的个体记忆超越了出身的贵贱,成为被高度认同与颂扬忠烈、殉国精神的象征;与此同时,朝鲜社会在壬辰战争后再次遭遇外族入侵即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个体经历中的忠烈精神作为化解社会动荡和不安定的有效因素,再次得到了最大化的颂扬。在此社会背景下,颂扬忠烈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个体记忆进而被“官方”统合、吸收和改造,作为官方教化民众与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因素,由排斥转向包容、再到利用。
四、超越国家的个体记忆:“记忆与忘却的政治学”
祭奠论介的活动“义岩别祭”从17世纪开始持续到朝鲜时代末期。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畏惧“义岩别祭”这样的祭礼活动成为鼓舞民族独立精神高涨的契机,由此“义岩别祭”被迫废止。这里,论介的记忆不仅仅是朝鲜时代忠烈形象的代表,近代以后更凸显出的是超越国家成为抵抗殖民地侵略的象征。在朝鲜社会殖民地统治时期,日本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对朝鲜社会中危及其殖民地统治的历史记忆进行了肃清,论介的历史记忆成为殖民地统治者压抑和忘却的对象。
战后,论介的记忆在韩国脱殖民地化后现代国民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中,由殖民地时期的被压抑、被遗忘而转向重构与苏生。1954年,在论介的家乡长水成立了“义岩朱论介事迹保存基成会”,通过当地各界人士的捐助,在南山建立的“义岩祠(论介祠堂)”,祠堂上的牌匾由当时韩国的副总统咸台永题字;同年同地又修建了“论介画像阁”与“义岩朱论介娘生长地事迹不忘碑”;此外长水郡在修建“义岩祠”后,又把论介殉节的7月7日作为纪念日,在每年的7月7日举行祭礼活动;1968年,长水郡又把7月7日定为“长水郡民之日”,论介的祭礼活动是“郡民之日”的主要内容;1986年,长水郡又在论介的出生地长溪面大谷里修建了论介父母之墓,复原了论介的故居,并且定在每年9月9日举行“论介祭典”。*鲁成焕:《日本人が祀った論介という朝鮮女性》,《日本研究》,2014年第49号,第118页。
1973年,韩国导演李亨杓以论介的事迹为素材,启用了当时韩国的著名演员申星一和金芝美,拍摄了电影《艺妓论介》。除电影外,论介的故事还以其他的形式在韩国民众中广为传播。例如,深受民众喜爱的歌手李美子等人创作了歌曲《论介》,她们的歌声一时遍布街头巷尾;2011年,在艺术殿堂举行的韩国歌剧节上,用歌剧的形式表演了论介的故事;2012年,韩国国立舞蹈团在国立剧场公演了以《论介》为题名的舞剧。*鲁成焕:《日本人が祀った論介という朝鮮女性》,《日本研究》,2014年第49号,第117页。如上所述,论介的记忆通过媒体、音乐与舞蹈等形式的传播,不断地在韩国社会中扩散、渗透和流通,在这一过程中,论介的精神存在达成了社会的共鸣,逐渐形成了抵抗外来侵略、殖民地统治的集体记忆。
在论介的义举之地晋州,“义岩别祭”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才得以重建。战后,仅是一些在朝鲜时代末期有过妓生经历的人们定期地来到义祭祠举行简单的祭礼活动,她们的活动并未得到当地社会的广泛关注。90年代后,“义岩别祭”能得以恢复源于传统艺人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在朝鲜王朝末期做过官妓的崔顺伊曾经亲身参与过“义岩别祭”的祭礼活动,她把“义岩别祭”完整的祭祀过程传授给了传统文化表演艺术者成桂玉。从1960年代开始,成桂玉为了恢复“义岩别祭”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她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查找到了郑顯奭的《教坊歌谣》,为了解读这部古籍,她还到高丽大学学习了古汉文。1992年,“义岩别祭”从日本殖民地时期被废止以来,经过了82年终于重见天日。*“义岩别祭”的恢复过程详见《朝鲜新报》,《朝鮮史を駆け抜けた女性たち③侵略に命をかけ抵抗した義妓-論介》2009年4月10日;http://www1.korea-np.co.jp/sinboj/j-2009/06/0906j0410-00003.htm(2014年3月6日阅览)。2002年,晋州市的文化艺术者们,以地方传统艺术为基础,把壬辰战争时期的民、官、军的忠义精神作为地方的主要标志性特征,设立了以“义岩别祭”为中心、全体市民共同参与的“晋州论介祭”。“晋州论介祭”在每年5月的第四周的周五至周日三天举行,参加人数达十万人。
如上所述,论介的记忆在战后韩国的社会化过程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构建了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记忆之场”*“记忆之场”这一概念源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诺拉在解释这一概念时指出,“记忆之场”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物质的场所”“象征的场所”“机能的场所”。详见皮埃尔·诺拉编:《記憶の場-フランス国民意識の文化·社会史》(第1卷、对立),谷川稔监译,岩波书店,2002年。,“义岩祠”、“义妓祠”、纪念碑及相关设施的建造是韩国社会想起外来侵略、殖民地强权统治记忆的“物质的场所”,同时也是颂扬论介精神成为韩国民众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象征的场所”,地方社会、市民共同参与的祭礼活动则是产生社会共鸣、促进相互间的认同,向下一代传承历史记忆的“机能的场所”。这种“记忆之场”形成,对现今东亚中日韩三国对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的差异,即加害侧对于历史记忆的忘却和被害侧对历史记忆的想起的相互关系上,隐含着各自对历史记忆想起与忘却的政治性。
五、小结:个体经验·国家认同·历史认识
本文以“义岩别祭”为考察对象,通过记忆这一概念中包含的想起与忘却的两面性,探讨了国家的历史记忆构建与个体经验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经验在转化成社会化记忆后如何成为强化被殖民地侵略的历史认识的问题。“义岩别祭”的祭祀对象论介的个体经验,在四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由朝鲜时代国家内部的认同到殖民地及后殖民地时期针对外部强化国家历史认识的转变。
朝鲜时代,论介的个体经验存在于国家内部对其认同与否的层面上。国家在书写历史和教化民众时,对不符合朝鲜时代作为治国理念的儒家道德规范的个体经验进行了选择与排斥。论介为国殉身的行为虽然在当地广为传颂,但她身为官妓卑微低下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未能冲破朝鲜保守士大夫们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观念的束缚,论介的个体经验被排斥于主流历史之外。百余年后,论介的记忆在地方社会的推动下,在1722年终于得到国家的认同被纳入到官方的祀典。官方这一态度的改变,与其时代变化密切相关,在壬辰战争后朝鲜社会再次经历外族的入侵,论介虽然身份卑微但能舍身殉国这样的精神成为教化民众的象征,个体经验中的忠烈精神作为凝聚民族国家和化解社会动荡不安的有效因素,继而被官方吸收和改造,由初始的排斥转向包容、再到利用。
殖民地时期,日本对殖民地社会中有碍于其权力统治的因素进行了肃清,祭奠论介的活动“义岩别祭”被认为是燃起韩国民族独立的契机,论介的记忆继而成为殖民地统治者压抑与忘却的对象。韩国脱殖民地化后,论介的记忆在韩国市民社会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如影视媒体的传播、纪念设施及纪念碑的建立、相关文化节的设立来强化和想起被殖民地统治时期的记忆,以此来促进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与社会共鸣,来应对当代东亚社会中对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的差异。
[责任编辑李浩]
作者简介:赵彦民,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青年团队项目(项目编号:IFYTI1202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