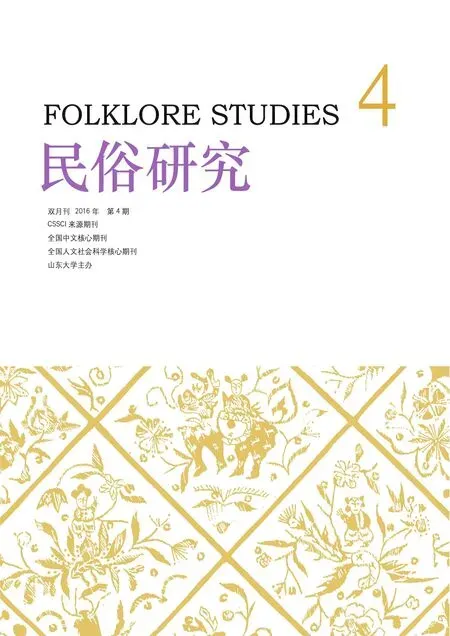什么是民间江湖的爱与自由
2016-02-04户晓辉
户晓辉
什么是民间江湖的爱与自由
户晓辉
摘要:仿照康德的先验排除法,首先区分人的知识水平和道德判断能力,然后在道德判断能力中进一步区分出理性的一般实践应用和纯粹实践应用。民间江湖是江湖中人的道德场域,只涉及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与其知识水平无关,而评价道德判断能力的依据,既不是对行为的经验观察,也不是行为的感性目的和一般的理性目的,而只能是通过对行为准则的先验还原所得的普遍实践法则和纯粹理性目的。因此,民间江湖的爱与自由不是来自经验观察和田野作业,而是来自先验的和超验的理性推论。简言之,民间江湖的爱指的并非侠骨柔情和爱恨情仇,而是理性的实践之爱,即纯粹以履行普遍的实践法则为动机(目的)的爱;民间江湖的自由也不是任逍遥意义上的所谓“自由”,而是理性对人的意志的一种必然设定。
关键词:排除法;还原;江湖;自由
一、在江湖
一向以德国思想史研究见长的“叶隽这些年在跨文化个案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成果迭出,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想从个案上升到理论,大胆提出了‘侨易学的观念’。这种可贵的理论勇气令我钦佩”①户晓辉:《主持人语:侨易学的几个问题》,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67页。。但他此番关注民间江湖并且以此为题来做文,却让我既惊讶、又新鲜。叶隽自己解释说:“我对民间的关注,其实更多出于一种对江湖的亲近。”相比之下,我这个做“民间”学问或者想认识“民间”的人,反倒显得对民间江湖有些生分。不过,亲近也好,生分也好,都只能表明我们与民间江湖或近或远的距离,却没能道出我们身处江湖的实情和况味。
在中国文化中,“江湖”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词。它不是一个实际的场所,而是指一种远离朝廷与公家的民间生存状态。有人把传统的中国社会划分为庙堂和江湖,庙堂属于朝廷(统治者),而江湖则属于民间,所以,“江湖”几乎成了“民间”的代名词;也有学者认为,“江湖”实际上是一种陌生人社会结构,是对熟人社会结构的扩展和补偿,“在缺乏统一、清晰、制度化的基本规则以及维护这套基本规则的体制性力量的情况下,不同层次或/和不同主体的‘利害’矛盾和冲突,很容易走向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对抗,最终只能诉诸最原始的手段——暴力。这样一种非熟人、非透明、乏规则的混沌交互空间,就是‘江湖’。”“更准确地说,传统中国人没有结构清晰、秩序井然的社会,只有茫茫江湖;出了作为熟人世界的有限范围,就置身于陌生人组成的混沌的交互空间——‘江湖’。”②李恭忠:《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内涵》,《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当然,这种由“陌生人组成的混沌的交互空间”并非完全缺乏规则和秩序,至少还在渴望规则和秩序。
在此,我不准备对“江湖”这个词追本溯源,也不打算对江湖文化展开论述,而只想指出,一方面,所谓江湖与庙堂在结构上是同形同构的,江湖常常依附于庙堂而缺少真正的独立性,而且一直没有壮大到足以与庙堂相抗衡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所谓江湖与庙堂又保持着既相互对立和对抗又彼此渗透和影响的张力关系。因此,与其说江湖是中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形态,不如说它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的泛江湖化,使各行各业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江湖气。正因为江湖规矩弥漫于中国社会,所以我才认为,它不仅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写照,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正因如此,江湖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几乎都是江湖中人,而且中国人心中和身边几乎都有一个或若干个江湖。所以,“作为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事实,‘江湖’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同上。无论怎样界定“江湖”,在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江湖险恶和刀光剑影,也可以看到是非纷扰和恩怨情仇。在这方面,我们又可以说,江湖直指人心,江湖不在别处,恰恰就在人心。在这人心的江湖里,正邪殊途、恩怨分明。因此,江湖是江湖中人的道德场域,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作为普适性的江湖规矩主要是复制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仁、义、礼、智、信’,要求江湖人士崇尚武德,爱惜名誉,信守承诺,弃小利而趋大义。江湖规矩是江湖世界里的通行法则,门派戒律则只约束门徒帮众,二者相辅相承[成],共同拱立江湖。”*周志高:《江湖世界:武侠小说中虚构的可能世界》,《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如果说“义”“利”“报”三者相互依存、相辅相生的关系是中国“整个江湖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特色”,那么,这“三者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和交际心理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人之间都称兄道弟、谈交情、讲面子,每个人都竭力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用义气和报做网线,利就是那一个个的网结。”*[韩]李银贞:《中国江湖文化中“义气”、“利己”与“报”探究》,《黄海学术论坛》第2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281页。其次,江湖规矩也是为了使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或松散或密集的亚结构组织成为可能。据说,江湖规矩受墨子兼爱思想影响甚大,奉行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基本准则。尽管现实的江湖永远都有违反江湖规矩的现象存在,但我们仍然不难看到,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在当前的中国现实中,江湖在与庙堂若即若离、时远时近、或对抗或合作的关系中的确表现出了积极行动和自我管理的自组织能力。
那么,政府和学者该如何看待民间江湖以及江湖中人?江湖中人又该如何看待自己?民间江湖是不是一个爱与自由的世界?这些不仅是数千年来一直存在却一直没能得到恰当思考和妥善处理的问题,也是中国民俗学首先遇到的重要问题。我之所以说这些重要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恰当思考和妥善处理,恰恰是因为以往人们仅凭经验观察来评价江湖中人,许多人同样会站在经验立场上认为,民间江湖当然有爱与自由,因为江湖中人常常爱得轰轰烈烈,他们浪迹江湖也往往显得自由自在。但我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经验立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的理由需要仿照康德式的排除法来加以说明。
当然,在对民间江湖进行还原分析之前,我必须指出,与中国古代文人的自我定位相比,现代知识阶层与民间江湖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说法即使不能概括所有古代文人的想法,至少也可以表明他们“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主流心态,即江湖的“穷”只是他们不得志和不得已时的暂时状态,庙堂的“达”才是他们不思量自难忘的真正目标,因此,“无论是‘穷’还是‘达’,他们的心中和背后总是站着仕宦的影子,而仕宦也就是科举入仕的文人。文人与仕宦实际上是一币的两面。”*户晓辉:《从古代文人的人格悲剧说开来》,2013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可以说,直至近代,古代文人多把自己想象为游离于庙堂和江湖之间,这种社会定位即便暂时低于庙堂却随时准备升入庙堂,因而一定高于江湖。直到现代民俗学的发生才引发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自己和江湖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或者更应该反过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现代学者对自己和江湖关系的重新定位才催生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诞生。也就是说,只有当现代学者不再把庙堂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及衡量江湖的尺度时,他们才能重新给自己和江湖定位,才能发现自己也在江湖之中,并且在江湖中重新发现“民”。因此,1918年开始的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基本态度”*[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绪论”第1页。,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现代学者在江湖中的自我定位。“对于多数欧洲学者来说,‘民’是他们要摆脱的对象,是他们的对立面,而对于中国现代学者来说,‘民’是一个被认同和整合的对象。”*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1919年,李大钊就明确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8-649页。
其实,知识精英与民间“江湖”的关系问题,是中外民俗学共同遇到的一个问题。当马里恩·鲍曼(Marion Bowman)指出“民俗是我们周围的一切,无论我们是谁和我们在哪里,而且我们都是民”*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7页。时,无疑道出了民俗学者在自我定位上的一种心声。我对阿兰·邓迪斯的人人都可以是俗民观点的分析(《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以及对民是人(《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和民是自由主体(《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的论证,恰恰可以印证当代民俗学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进程,也是民俗学者自我反思的一种结果。
不过,顾颉刚当年喊出的那句话,“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顾颉刚:《〈民俗〉发刊辞》,原载《民俗周刊》第1期,1928年3月21日,见王文宝编:《中国民俗学论文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5页。可谓说出了中国民俗学者独特的现代性之声。随着时间的推进,在这些年里,作为一个民俗学学者,我越来越感同身受地体会到顾颉刚这句话的切肤之痛。在中国,如果“民”不是自由人,民俗学者岂能独是自由人?如果江湖中人没有尊严和权利,民俗学者又怎能独占或独享人的尊严和权利?在这方面,真是“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页),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书,第50页),如果违背这个前提,就不是共产主义。从自由主义立场来看,这种主张也许并非真的要在社会现实中取消一切阶级差别,而是为阶级差别创建一个无差别的平等身份基础,其实践目的论的原理与自由和权利的目的论原理有相似之处,即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的自由受到了侵犯就潜在地等于所有人的自由都受到了侵犯;一个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就潜在地等于所有人的权利都没有得到保障。正如吕微唱和陈泳超的一首短诗所写:
我知道你没哭
但我知道,你真的想哭
因为,我们都是稻草人
不管你假装看不看我
你我都在倾听着
关于我们的传说
传说中
那个舞弄着自制的三尖两刃刀
又用两支刚签锁了口的人
何尝不是我们自己*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1页。
作为民俗学学者,我们益发地感到,我们不仅脱离不了江湖,而且我们自己就是江湖中人。我们与民间江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方面,又怎一个“亲近”了得?因此,怎样看待和对待江湖,实际上就是我们怎样看待和对待我们自己。
二、江湖中人是否身不由己
人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似乎总是由各色人等混迹其中。江湖的各种规矩甚至潜规则好像的确使江湖中人有时显得万般无奈和“身不由己”。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江湖固然不乏自己的各种规矩和组织形式,但也的确有各种乱象,并由此遭到庙堂的冷眼相看和打压。当然,江湖中人被冷眼相看甚至常常自以为低人一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认为而且自认为愚昧无“知”,事实上,他们中间也的确有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老粗”。这一点从“民”的本义即可看出。汉代许慎解释说:“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又曰:“氓,民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第265页。清代刘树屏释“民”为“众萌也。萌者,盲昧无所知也。引申为众人之称。古者言‘四民’,士、农、工、商是也”;又释“氓”为“自彼来此之民曰氓。从亡,从民。犹言流亡之民也。氓与民通,亦兼盲昧之义。”*(清)刘树屏:《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繁体横排点校本),新星出版社,2014年,卷二,七○可见,“民”与“氓”本可互训互通,无知或缺乏知识是“民”的根本特征,以至于《论语·泰伯篇》所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该如何断句,至今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公案。对“民”的这种认识也影响甚至决定了古代庙堂文化和文人对民间江湖的总体印象和整体评价。但正如叶隽敏锐指出的那样,“民间文学就是人文世界的江湖,这里不仅有下里巴人,更有真金存焉,不仅是简单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还有庙堂高处常见江湖风云,江湖低地不避庙堂波涛。”*叶隽:《民间江湖,那爱与自由的世界——侨易学视角下的民间文学》,《民俗研究》2016年第4期。本文所有叶隽的引文,均出自该文,以下不再一一注明。民间江湖的“真金”若要不被埋没,当然“关键还是在于学者自身能否去慧眼发掘”。前辈学者并非没有做出过这种“慧眼发掘”。如果说“‘民’在先秦汉语中与‘盲’、‘氓’音义相近,意思是说群盲或愚氓之众”,那么,“到了‘五四’,社会上的‘愚民’观念开始有了一次大的转变,用胡适的话说,这是因为‘五四’学者从学术和思想上为那个时代提供了‘几个根本见解’,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民’要成为社会主体的思想”。*吕微:《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但是,这些见解并没有真的使“民”成为主体,也没有实现其良好的愿望和初衷,除了因为不具备客观的社会制度条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没能对“民”的理性能力做出理论使用和实践使用的区分。换言之,要想从根本上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甚至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对民间江湖的认识局限,并且从中发现“更有真金存焉”,我们就需要借鉴民俗学之外的学术资源。这并非取决于我们的个人爱好,而是由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在这方面,学者与老百姓虽然同处于江湖的生活世界,但有分工的不同。正如叶隽别具慧眼地指出的那样: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之所以可爱而让人心生亲近之情,就在于日常生活仍有其不可溟灭的“见道”之义,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或许也更可解释民间文学的价值所在,正是因为能相对更加贴近生活世界的本质,虽然未必就是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但至少可以“由象见道”。
也就是说,“道”在老百姓那里虽然可以“日用而不知”,但我们学者却需要“由象见道”。尽管学者也是老百姓,但既然学者又是专门从事观察、理解和研究的专业人士,那就至少应该对老百姓凭借自己“最普通的知性”(der gemeinste Verstand)做出“一种模糊区分”(eine dunkele Unterscheidung)的事情,给予“更为完备地、更易理解地展现”并且“更方便地展现其应用原则”,“在单独的科学(in abgesonderter Wissenschaft)中来阐明普通的理性认识(gemeinen Vernunfterkenntnis)只是混杂地把握的东西。”*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8-459页,第411-412页,第397页;译文据康德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的德语原文有改动。因此,既然民间江湖是一个实践的道德场域,我们就有必要仿照康德的道德哲学来发现其中“更有真金存焉”。换言之,除非我们不愿对民间江湖以及江湖中人做出根本评价和整体判断,否则,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看待和对待江湖以及江湖中人?民俗学者作为个体可以只研究和描述江湖中各种具体的习俗现象和规矩,但民俗学作为学科却不能回避甚至忘却学科伊始时的实践理性起点和宏愿:即在民间江湖发现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户晓辉:《返回民间文学的实践理性起点》,《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因此,我们有必要仿照康德的排除法对民间江湖做一番还原分析。
经验告诉我们,从古到今,民间江湖上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大恶人也有大善人。于是经常出现这样几种情况:一方面,如果仅仅根据对民间江湖的经验观察来做判断,有人就可能依据其中的善行得出江湖中人是好人的结论,也有人可能依据其中的恶习而认为江湖中人是坏人,认同这两种相反结论的人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从各自的依据来看似乎各有道理。由此就可能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幻象。这不仅涉及对江湖行为的评价标准,而且涉及对江湖中人的根本认识。另一方面,人们通常又从心理经验上来评判江湖中人的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因为“通俗的道德哲学总是与经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即使要立足于行为的动机来考察其道德意义,但实际上却仍然把这种动机看作一种经验的事实。于是,人们永远可以从这种经验事实的后面再假定一种隐藏更深的不道德的动机,因而否定有任何真正的道德行为;或是假定一种虚构的高尚动机,从而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假象而沾沾自喜;而由于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可靠的经验事实来作最后的裁定,人们将陷入有无真正的道德行为的辩证论(二律背反)。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只有坚决把经验的事实排除在道德哲学的考虑之外,不靠举任何例子或榜样来说明道德的原则。”*邓晓芒:《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从经验上说,我们不仅无法猜透别人的心理动机,而且也难以认清自己的心理动机,因为我们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自欺欺人。还有一个方面是,人们常常因为江湖中人的文化程度低而认为他们容易行善或作恶,但这种观点实际上更不得要领。因为按康德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仅仅因为民间江湖中人受教育少和知识水平低而轻视甚至排挤他们,那就犯了把知识水平与道德判断能力混为一谈的错误。即便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当初在重新“发现”民众时仍然没有明确地做出这种区分,由此大大削弱了其洞见的理论力度和适用范围。做出这种区分的理论必要性和实践价值在于,即便民间江湖中人或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的知识水平不高,但这并不影响、更不能决定他们道德判断能力的高低,相反,道德判断能力的高低与知识水平的高低无关。中国的许多启蒙者都没有搞明白,人的道德判断能力实际上“无师自通”,老百姓需要被启蒙的是科学知识,而不是道德判断能力。
因此,仿照康德的排除法,我们至少需要对民间江湖做几个步骤的还原:
(1)首先区分知识水平和道德判断能力。既然民间江湖只涉及道德判断能力而与知识水平无关,那我们在评价江湖中人的道德行为时就应该把知识水平排除出去。也就是说,民间江湖是一个道德判断能力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经验认识的世界,江湖中人不是为了去认识物而是为了与其他人打交道。这样一来,我们对江湖中人行为的判断或评价也就不应该依据其知识水平,而是应该依据其道德判断能力。按康德的理解,理论认识(知识水平)是要认识事物的已然和实然,而实践认识(包括道德判断能力)则是先验地认识通过自由意志应该发生什么。因此,通过某个意志可能或必然被设想的一切东西都是在实践上可能的或必然的。*参见Rudolf Eisler, Kant-Lexikon. Nachschlagewerk zu Kants sämtlichen Schriften/Briefen und handschriftlichem Nachlass, Georg Olms Verlagsbuchhandlung Hildesheim, 1961, S.430。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具有按照法则的表象去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就是人的意志或实践理性。换言之,在康德看来,意志就是只选择理性在实践上认为必然的和善的东西而不选择那些偶然的和恶的东西的能力,也就是一种按照法则的表象规定自身去行动的能力。人的意志完全无假外求,独自就有能力实践出应该发生的事情。显然,民间江湖不是一个客观知识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于应该如此才可能如此甚至必然如此的世界,因为它是由人的行为和意志可能造成或必然造成的世界。
(2)其次是排除江湖中人行为的非道德动机(目的)。也就是说,江湖中人的行为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目的,或者为了争名夺利和飞黄腾达,或者为了光宗耀祖和一己私欲,但这些感性的行为动机尽管也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合理体现,但在康德看来,这些目的借助于本能也可以达到,因而不具有道德价值。只有理性的行为动机才可能具有道德价值。换言之,道德行为一般都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某种只对行为者自身主观有效的准则,而这种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则取决于它的准则能否成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普遍有效的客观法则。
(3)所以,排除法的第三步是从一般的理性行为动机(目的)中还原出纯粹理性动机(目的),从对个别人主观有效的行为准则中还原出对所有人普遍有效的客观法则。为了寻求道德的纯粹源头,康德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还原思路。对个别人主观有效的行为准则能否成为对所有人普遍有效的客观法则,是一个形式化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考察行为动机(目的)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前提,因为只有通过了这种可普遍化的形式标准,各种对个别人有效的行为准则才不至于互相打架或相互矛盾。只有这样的标准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平等相待和一视同仁。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即使是理性的行为动机(目的)也要产生在法则之后而不是之前。*感谢吕微在2015年12月27日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提示说:“真正出于道德的理性目的(质料),不是实践理性直接给出的,而是实践理性通过纯粹形式的道德法则推论地给出的,用康德的话说,是先给出了道德法则的形式,然后把道德法则的质料(人是目的)‘补充’给道德法则的形式(见《实践理性批判》),所以,康德才把道德法则表述为单纯的形式原则。”一方面,江湖中人的许多行为可能合乎义务*康德所谓义务“就是对法则的敬重的一个行为的必然性”([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见《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7页);“因为要使某种东西在道德上成为善的,它仅仅符合道德法则还不够,而且它还必须为了道德法则的缘故而发生。否则,那种符合就只是很偶然的和糟糕的,因为非道德的根据虽然有时会产生符合法则的行动,但多数情况下却将产生违背法则的行动。”同上书,第397页。却不一定出自义务,因而不具有绝对的道德价值。因此,我们不能依据经验观察,而只能依据对这些行为的先验还原和设定来评判其道德价值。*康德指出:“事实上,绝对不可能通过经验以完全的确定性澄清任何一个事例,说其中通常合乎义务的行为仅仅依据道德根据、依据其义务的表象。”[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见《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3页。另一方面,即便江湖中的恶人,也有善恶观念和是非判断。也就是说,在民间江湖中,其实也就是在一般的中国社会中,“任何人,哪怕是最坏的恶棍,只要他在通常情况下习惯于运用理性,当我们向他举出心意正直、坚定地遵守善的准则、同情和普遍仁爱(为此还与利益和适意的巨大牺牲相结合)的榜样时,他都不会不期望自己也会这样思想。”*同上,第462页。因此,“在道德领域里,人类理性甚至在最普通的知性那里(beim gemeinsten Verstande)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被引向超乎寻常的正确性和详尽性。”*同上,第398页,译文据康德的德语原文有改动。康德运用还原法详细描述了每一个普通人如何能够具备比知识能力高得多、也普遍得多的实践判断能力:
因此,我应当做什么,才能使我的意愿在道德上是善的,对此我根本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洞察力。即便对世事的进程没有经验,即便不能把握世事进程的所有自行发生的意外变故,我也只问自己:你能够也愿意你的准则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吗?如果不能,这个准则就是卑鄙的,而且这虽然不是因为由此将给你或者还有他人带来某种不利,而是因为它不能作为原则适用于一种可能的普遍立法;但对于这种立法来说,理性迫使我给予直接的敬重,我虽然现在尚未看出这种敬重的根据何在(哲学家可以去研究这一点),但毕竟至少懂得:这是对远远超出由偏好所宣扬的一切价值的那种价值的一种尊重,而且我出自对实践法则的纯粹敬重的行为的那种必然性,恰恰就是构成义务的东西,而任何别的动因都必须为义务让路,因为义务是一种本身即善的意志的条件,这种意志的价值高于一切。
这样,我们就在普通人类理性的道德认识中一直达到了它的原则;尽管普通的人类理性当然不会这样用一种一般形式来单独思考这一原则,但毕竟随时都现实地记得它,并把它用做判断的圭臬。在此,如果人们不教给普通人类理性丝毫新东西,只是像苏格拉底做的那样,使它注意自己的原则,那就很容易指出,它手拿这个罗盘,在一切出现的事例中都能够清楚地知道如何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合乎义务的、什么是违背义务的;因而不需要任何科学和哲学就能够知道,为了成为诚实的和善的,甚至成为睿智的和有道德的,人们必须做什么。这也就已经能够在事先很好地推断,关于要做什么的认识、因而也是每个人有义务知道的认识,也将是每个人、甚至最普通的人的事情。在这里,人们毕竟能够不无惊赞地看到,在普通的人类知性中,实践的判断能力(das praktische Beurteilungsvermögen)超过理论的判断能力竟是如此之多。*同上,第410-411页,译文据康德的德语原文有改动。
在这里,康德不仅从普通的善举和恶行中同样还原出普遍的实践法则,而且直接表明,普通的人类知性都不难知道和领会这样的道德实践原理,每个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都具备对道德上的应该的实践判断能力。知道了这种应该当然不一定能够时时处处让它变成现实,正因如此,这种应该才表现为对人的一个定言命令: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或者说: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的行动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这种应该不仅不超出人的能力(否则这种命令对人就没有意义),相反,它完全处于人的意志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人的意志不假外求,也不需要附加其他条件,只要愿意就能够独自执行这种应该的定言命令。正因如此,这种应该的命令才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定言命令,也才是一种包含着实现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的义务。即使作恶者想违背这种义务,其想法也会陷入自相矛盾。因此,任何一个出自义务(aus Pflicht)的行为,如果它的道德价值“不在于由此应当实现的意图,而是在于该行为被决定时所遵循的准则(Maxime),因而不依赖行为的对象的现实性,而仅仅依赖该行为不考虑欲求能力的一切对象而发生所遵循的意愿原则(Prinzip des Wollens)”*同上,第406页,译文据康德的德语原文有改动。,那么,“当一个行为出自义务而发生时,它就必须完全被意愿的形式原则所规定,因为它的一切质料性的内容都被抽掉了”*同上,第407页,译文据康德的德语原文有改动。。可见,道德原则不是来自对各种经验现象的归纳和总结,也不取决于各种行为目的的质料,而是来自一种必然的设定:除非我们不承认江湖中人有理性,否则就只能从人的理性这个前提中推论出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存在。按康德的思路,对个人有效的实践准则必须从对每个人都普遍有效的实践法则中派生出来。当然,“感性的人总是免不了从他的自然本性和生存环境中获得自己行为的动机,因而无处不构成对道德自律的外部干扰。不过人性中的根本恶并不在于感性动机本身,而在于摆不正感性动机和理性的道德动机的位置关系,也就是不去使感性动机为道德动机服务,而是反过来使道德动机成为感性动机的借口或工具。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欺和伪善……”*邓晓芒:《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康德当然不是要求人们完全抹杀或彻底取消行为的感性动机,而只是主张应该正确处理感性动机与道德动机的关系,由此才能产生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也即更重要的一步是,即便在理性的实践应用内部,我们也有必要进一步区分理性的一般实践应用和理性的纯粹实践应用。大体来说,理性的一般实践应用主要指按照个人主观有效的实践准则行事,理性的纯粹实践应用则指按照对每个人都普遍有效的客观法则行事。道德法则要求我们防止理性在实践应用中偏离方向,即防止让理性的纯粹实践应用为一般实践应用服务,而应该让理性的一般实践应用服务于纯粹实践应用。因为在实践领域中,理性的最高使命和第一位的使命是建立善良意志,第二位的意图才是实现幸福。
(4)排除法的第四步是,从人的道德判断能力中进一步还原出人的自由。
如果把眼光从道德的普遍法则转向实践这种法则的人,那么,按康德的思路,即便江湖中人缺乏理论的判断能力,但他们完全具有“超过理论的判断能力竟是如此之多”的“实践的判断能力”,而这种“实践的判断能力”实际上就是自由的能力。通俗地说,江湖中人能够知道,他自己的行为准则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对每个人都普遍有效的客观法则就可能与别人的主观准则相互冲突,即使那些有意无意的“犯规者”也可以从反面印证这个道理。因此,无论事实上做得怎么样,江湖中人都能够意识到这种对每个人都普遍有效的实践法则的存在并且有能力按照这种客观法则来为自己立法,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种普遍的实践法则当作行为的目的实现出来,把这种应然变成可然和实然。因此,康德论证道:“我们必须也把自由的理念必然地赋予每一个具有某种意志的理性存在者,他只在这个理念之下去行动。因为在这样一个存在者里面,我们设想一种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它就自己的客体而言具有原因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设想一种理性,它就其判断而言凭借它自己的意识从别处接受某种操控;因为那样的话,这个主体就不会把对判断力的规定归于他的理性,而是会归于一种{外在的}推动力(Antriebe)。这种理性必须把自己视为自己的原则的{内在的、原发的}发起者(Urheberin),不依赖于外来的影响;因此,它作为实践理性,或者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必须被它自己视为自由的。也就是说,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只有在自由的理念下才能是自己的意志,因而必须在实践方面被赋予一切理性的存在者。”*[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见《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6页,译文据康德的德语原文有改动,大括号中的文字是笔者为了有助于理解而增加的内容。只要是理性的、自由的人,就能够独自成为实践的原因并且能够独自带来实践上的原因性(Kausalität),因为能够借助理性的表象或法则的表象来规定意志是自由人或理性人的客观根据而非主观规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论证不需要借助对民间江湖的经验观察,而完全是一种先验论证和逻辑推论。也就是说,假如有人不承认江湖中人有理性,那就等于说江湖中人不是“人”。只要承认江湖中人是“人”,他们就必然具有理性。因此,无论别人是否承认,也无论江湖中人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必然拥有自由的权利。在康德看来,理性存在者必然拥有的这种自由尽管不能被我们认识,却仍然是我们通过理性的排除法而能够知道的一个“某物”(ein Etwas):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某物,当我只是为了限制出自感性领域的动因原则,而把属于感官世界的一切都从我的意志的规定根据中排除掉之后,就剩下这个某物”*同上,第470页,译文据康德的德语原文有改动。。因此,从意志的规定根据上来看,只要我们具有人的意志,这种意志就应该是自由意志。由此看来,我们人是被抛入自由的。我们不得不自由,自由是我们的宿命,因为不自由就不是人。*户晓辉:《返回民间文学的实践理性起点》,《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既然如此,启蒙就是让每一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理性和自由,学会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学会自己走出误用理性的不成熟状态。
三、何谓爱与自由:驳中国某些“后现代”
既然自由对人如此重要而不可或缺,那么,江湖中人岂可没有自由?所以,叶隽一眼就看出,“在晓辉兄的心目中,大约没有比‘自由’更重要的概念,所以他始终将‘自由’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作为一以贯之的追求,至于‘民间’、‘文学’等反而衬作了红花旁的绿叶了。”因此,他的大作开宗明义地宣布,我们有必要“重寻民间,理解博爱与自由”。这无疑切中了我的本意,即重新理解民间江湖的爱与自由。
尽管有些中国学者还生存在象牙塔的幻觉之中,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身在江湖来研究江湖,尤其是民俗学者本来不仅离江湖最近,而且就是江湖中人。社会学学者已经看到,中国现实中原来一些扶弱抗暴的江湖组织正在向做慈善、做维权、做公益的方向发展,原先民间江湖的一些秘密结社正在追求合法化并且逐渐成为公开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学学者已经在研究民间江湖的自组织能力和当代转型中的小政府与大社会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促进所谓庙堂与江湖关系的改建。可是,中国的民俗学者如果仅仅以自己一贯对本学科浪漫主义起源的误解*相关分析和批评,参见户晓辉:《返回民间文学的实践理性起点》,《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德]哈尔姆-佩尔·齐默尔曼(Harm-Peer Zimmermann):《审美的启蒙:以民俗学为目的对浪漫派的修正》(sthetische Aufklärung. Zur Revision der Romantik in volkskundlicher Absicht, Verla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GmbH, Würzburg, 2001)。而陷入单纯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或者仅仅满足于描述民间江湖的各种经验现象或经验事实,那就不仅落后于社会学学者的种种实绩,而且彻底遗忘了中国民俗学在起源时的根本目的。换言之,如果仅仅局限于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那我们就会对民间江湖的爱与自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真正的爱与自由不是来自经验观察和田野作业,而是来自先验的和超验的理性设定。简言之,民间江湖的爱指的并非江湖的侠骨柔情和爱恨情仇,而是理性的实践之爱,即纯粹以履行普遍的实践法则为动机(目的)的爱。只有这种爱的义务(Liebepflicht)或作为义务的爱才能被要求:“毫无疑问,要求爱自己的邻居,甚至爱我们的仇敌的那些经文也应当如此理解。因为作为偏好(Neigung)的爱是不能被要求的,但出自义务本身的行善,即使根本没有偏好来驱使,甚至有自然的和无法抑制的反感来抗拒,却是实践的爱,而不是本能的爱*本能的爱(pathologische Liebe),或译“病理意义上的爱”,在康德那里指受感性支配并且以感性偏好为动机的爱。。这种爱就在意志之中,而不是在感觉的倾向之中,在行动的原理之中,而不是在温存的同情之中;惟有这种爱才是可以要求的。”*[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见《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6页,译文据康德的德语原文有改动。这种爱也就是纯粹以普遍的实践法则为动机(目的)的普遍之爱或纯粹之爱,“那些只顾个人利益或一己之私的所谓爱,名义上是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实际上必然导致各种自爱或偏爱之间的相互矛盾和绝对对立,从而使它们相互冲突和抵消;普遍之爱或纯粹之爱则是出于绝对平等法则的爱,只有这样的爱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和维护个人的自爱的尊严或价值”*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页。。同样,民间江湖的自由也不是任逍遥意义上的所谓“自由”,而是理性对人的意志的一种必然推论。“自由是一个纯粹的理念,它的客观实在性绝不能按照自然法则来阐明,所以也不能在任何一种可能的经验中被阐明。因此,由于它本身绝不能按照任何一种类比来配上一个实例,所以它绝不可能被理解,哪怕仅仅是被看透。它只是被视为理性在一个存在者里面的必然设定……”*[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见《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7页,译文据康德的德语原文有改动。
由此来看,我们以往对民间江湖的认识,最缺的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而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从学理方面说,人对自身的自在生活与自由存在的实践觉醒发端于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只是承接了其学理的余绪,但这并不是说,人对自身的理性存在与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世界的实践觉醒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是本土的内在性问题;恰恰相反,人作为人自身(先验自我)的个体主体性存在(主体本体论)的自在、自由的生活意义,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本土性来说,恰恰是一个更严重的事情或问题。”*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既然每一个学者都在民间江湖,那么,我们是否愿意把民看作自由人并且当作自由人来对待,实际上就是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当作有尊严、有权利的自由人来看待。只有首先想成为并且愿意成为自由人,我们才有可能成为自由人。我作为学者并不在民间江湖之外而恰恰就是江湖中人,因此,我也承受着民间江湖的荣辱和苦痛,“这种承受和苦痛的痕迹,使得民间文学能连接上一种大气象和大关怀”。不仅如此,正如吕微指出的那样,“民俗学——中国民俗学也是一样——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参与了对现代人的‘元身份’的‘身份设计’,即把‘民’作为本学科的核心问题来讨论”*同上,第539页。,但“民俗学能否重新参与对国人元身份的设计实践,端有赖于民俗学能否对人性有更深刻的把握,而不是流于对人的实践行为、活动的现象描述”*同上,第540页。。只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民俗学在拥有一个伟大开端之后逐渐走上了一条与民族救亡和民族国家建设等意识形态逐渐合流甚至“合谋”的发展轨道。只是由于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这种合流甚至“合谋”在中国和欧美产生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别。黑格尔、胡塞尔和马克斯·韦伯等德国思想家都曾认为,只有在欧洲才产生了理性主义或合理主义(Rationalismus)实践目的论以及体现这种目的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对此,黑格尔从他的哲学体系出发并且以他对理性精神的逻辑发展过程的理解有过不少相关的论述,例如,他认为“精神的朝霞升起于东方,[但是]精神只存在于西方”([德]黑格尔:《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I分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利群、沈真、张东辉、姚燕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3页);胡塞尔也认为只有欧洲人才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而成就了“精神的欧洲”([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7页,第374-375页)。另参见[德]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吴乃昌、简惠美、张炎宪、胡昌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3―164页,第166页。尽管可能有不少中国人认为这种观点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我们为什么不能冷静地想一想:这些大思想家的自信来自哪里?难道他们仅凭一种豪情万丈的所谓民族自豪感就可以如此“口出狂言”而且还可以“妖言惑众”吗?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道出了一种客观事实,因为“这种合理主义一方面具有特殊性,即为西方所特有,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它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无论有些人是否愿意承认,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理性主义或合理主义在全球的普及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欢迎。例如,“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公民的民主理想在本世纪得到全球性发展,其速度和深度堪称最为重要的‘全球化’之一。一个世纪以前,公民性理想对世界大多数政治文化来说都是陌生的,而现在只要是与民主公民性的观念有点同属一个相似家族的观点,都会在几乎全球每一个角落找到支持者。这是一种像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现代兴起一样的世界性变化,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对此并没有完全理解。……把公民性理想说成是‘西方的’,首先会忽视这一事实:民主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甚至在今天也不再仅属于西方文化……”*[美]罗伯特·W.赫夫纳:《公民社会:一种现代理想的文化前景》,李朝晖译,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按哈贝马斯的说法,欧洲的这种合理主义现代精神的方案就是18世纪启蒙哲学家表述的基本理念,即追求客观化的知识学(die objektivierenden Wissenschaften)、道德和法律的普遍主义基础、艺术的自主发展和生活关系的理性结构。即便在欧洲,这些也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Jürgen Habermas, Die Moderne-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Die Zeit, 19. September 1980.简言之,这些现代精神或现代价值观都可以归结为追求人格的独立和意志的自由,让理性的太阳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升起,让社会治理从人治走向现代法治。尽管它们并非完美无缺或十全十美,却是迄今对人性最合理、最客观也最有效的认识。除非我们认为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完全不适合中国,除非所谓的中国特色可以特殊到让中国完全隔绝于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全球合理主义整体趋势,并且特殊到否认中国人具有理性和逻辑,否则,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果说现代精神在欧洲都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那么,在中国,它不仅尚未完成和建立,甚至可谓方兴未艾,尽管从近代以来的现代精神启蒙和转型的历程已经为时不短而且历尽坎坷。换言之,在欧美社会,理性的思维方式可谓历史悠久、传统深厚而且是社会的主流取向,以康德哲学为代表的哲学论证不仅使自由、平等、民主等社会价值观在人们的主观上被普遍确立起来并且成为不证自明的社会共识和无需质疑的基本前提,而且已经在客观上被制度化和法治化。因此,那里的后现代思潮反对理性“主义”其实是反对理性的误用(比如,把理性的实践用法与理性的理论用法混为一谈或者让理性的纯粹实践应用服务于一般实践应用),而不是反对理性本身,否则,后现代自身的一切反对不仅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而且本身也会因为否认了理性的前提而变成无谓的徒劳。*胡塞尔的名著《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欧洲人误用理性所造成的“近代物理学主义的理性主义”危机的哲学批判,而且开启了西方后现代批判的先河,他认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一种误入歧途的理性主义。但是不可由此认为,仿佛合理性本身是坏事,或总的来说对于人的生存具有次要意义”,恰恰相反,人只有通过理性才成为人类,“将自己理解为理性存在的人理解到,它只是在想要成为理性时才是理性的;它理解,这意味着根据理性而生活和斗争的无限过程,它理解,理性恰好是人作为人从其内心最深处所要争取的东西;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感到满足,感到‘幸福’;它理解,理性不允许再细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审美的’,以及无论其它什么的;它理解,人的存在是目的论的存在,是应当—存在,这种目的论在自我的所有一切行为与意图中都起支配作用。”[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2页,第324页;反过来说,如果西方没有理性主义的高度发达、极度分化和对理性的误用,胡塞尔的批判不仅可能无的放矢,而且根本就没有必要。相比之下,中国后现代如果单纯地反理性,那才真正是无的放矢,类似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更关键的是,西方后现代看起来解构了主体的人和本质,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和反对一切普世价值的前提。首先,他们是讲道理和讲逻辑的,否则,他们的否定和反对本身(无论内容是什么)就根本无效或不能成立;其次,主张差异和多元的西方后现代一定不会反对这样一种主张和前提: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和意志自由。否则,它的一切多元和众声喧哗行为就会自动失效,而这种主张正是民主、平等和自由这些普世价值的一个基本内容。因此,所谓普世价值之所以是普世的,恰恰因为它们是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推论,而不是个别人的想当然、主观爱好或者特殊的立场。中国某些后现代学者却往往忽视了西方后现代默认的普世价值前提。在中国,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后现代崇尚的真正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众声喧哗不仅不是被鼓励的、被保障的,而且往往是不允许的,尽管中国从西方移植来的后现代在解放思想的社会进程中也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由此来看,西方的后现代在总体上是对那里的理性误用现象打的一剂预防针,或者就是对现代理性启蒙中的理性误用现象的一种纠偏,因而有时难免矫枉过正。同样,欧美民俗学者对本学科浪漫主义起源的狭隘理解所导致的单纯民族主义立场还可能与它们各自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制度形成一种矫正和补充关系。但在中国,由于经验主义认识传统的盛行和理性思维传统的匮乏,不要说自由、平等、民主等社会价值观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即便这些观念在所谓的知识阶层也远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更没有成为普遍的共识。*即便在学者当中,认为中国不适合西方“市民社会”和民主、平等、自由理念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杨美惠指出,“由于中国同西方在文化出发点上相当的不同,中国民间有可能根本不能以个人权利与公民权作为其出现或再出现的肥沃土壤。在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主要是由关系权利的,尤指个人权利的话语推动的;在中国,国家形式外社会领域的形成,最有可能是由相互联系与义务的话语来推动。在中国,文化强调的不是抽象的普遍人格,而是由社会关系和角色定义的人。”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因此,中国某些后现代学者往往把专制与理性混为一谈,以至于在反专制的同时实际上也把理性拒之门外。在缺乏理性共识和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中国的某些后现代学者不仅无法带来像西方后现代那样的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社会效果,反而可能带来一种自娱自乐、逞一己之意而对社会于事无补、反而有害甚至雪上加霜的恶果。因为他们自相矛盾的语言狂欢不仅无助于中国现实的改善,而且有可能与那些不讲理性和逻辑的中国特殊论者和既得利益者达成某种不谋而合。恰恰因为中国缺乏理性的和逻辑的传统,所以那些极端的特殊论者充满自相矛盾的论调才能够通行无阻、招摇过市甚至甚嚣尘上,仿佛世界上真的存在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仿佛世界上真的存在着两种人,一种叫人,另一种叫中国人。问题的关键在于,按照这些人的“中国逻辑”,这两种逻辑和两种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共同之处和相通之处,因此他们的潜台词就等于宣布:中国逻辑不是逻辑,中国人也不是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资产阶级革命使“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这句名言可能既让中国某些后现代学者欢呼雀跃,也让中国那些拒绝承认并接受普世价值的既得利益者暗自欢喜,因为他们恰恰可以利用许多中国人不讲逻辑的思维习惯来混水摸鱼,借以维护并巩固他们在中国现实中既得的利益和权力。同样,中国民俗学者如果仍然固执己见地以自己对本学科浪漫主义起源的误解所带来的单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立场为民俗学唯一可行和当行的路径,那么,即使这些民俗学者主观上想与中国特色论保持距离,但客观上仍然可能造成与它们“共谋”与“合谋”的效果。因为这不是由人的主观随意性而是由事情的客观原理决定的。这种效果即便不一定是学者的主观愿望,却很可能是一种事与愿违的无奈现实。但无论前现代还是后现代,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理有固然、人有本然。人和事情的根本不取决于种种变化多端的表象,而是取决于固然和本然的原理。爱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普世价值恰恰是这样一些能够让我们摆脱偶然命运和弱肉强食的任意摆布而生活在一个相对有把握和有保障的目的王国之中的原理。例如,从原理上说,失去普遍原则制衡的民族主义很难避免自身不陷入极端,也很难不被某种意识形态利用,极端的例子就是纳粹对德国民俗学的利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问一问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或江湖中人,他们是否愿意被当作或者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先验和超验的自由意志,民俗学者们一贯强调的那种不同民族或个人的特殊文化身份和文化权利如何得到有效的论证和保障?
只有站在实践理性的立场,我们才能看到叶隽所谓“文学的伟大传统,并不简单地以庙堂或江湖为标尺,也不应以所谓的雅文学、俗文学而简单二元对峙。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超越功利的文学的伟大传统”。在欧美国家,人的主体性不仅已经被现代性牢固地确立起来而且还需要后现代来对这种主体性的某些异化加以解构,而在中国,确立人的主体性仍然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未竟事业和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因此,中国的民俗学者如果单纯步欧美后现代之后尘,那就很可能直把他乡作故乡。当然,我的意思并非反对后现代的反思,而是赞同吕微所说,“在后现代学术反思的进程中,民间文学、民俗学首当其冲,因为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经典研究对象正是那些被‘现代性’知识系统(包括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知识)异己化、他者化的知识系统的客体对象。如何恢复这些已经被异己化、他者化的客体对象本应享受的主体地位,这既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在今天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这个学科对人文学科整体有可能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吕微:《反思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学术伦理》(代前言),吕微、安德明编:《民间叙事的多样性》,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同样,只有在真正的爱与自由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赞同叶隽的断言:“晓辉兄给我们所描述的民间江湖,不仅是一个属于民俗学的‘爱与自由的世界’,而且更应当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应该为我们‘学者共和国’的成员所共享,对于当下中国仍处于建构过程中的学术共同体来说,其意义则尤显急迫而重大!”当然,叶隽十分委婉地批评我说,他“不太赞同过于强烈的‘学科雄心’”。其实,这一点于我心有戚戚焉。正如他敏锐指出的那样:
……民俗学学科在中国(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和民俗学运动)和德国(赫尔德、格林兄弟)的起源,确实极关重要,因为这批人物所牵连起的绝非仅是一个单纯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问题,他们本身就是主流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核心人物,在胡适、周氏兄弟,乃至赫尔德、格林兄弟的心目中,哪里会仅有一个单纯的“民间”存在呢?
我虽有学科意识,但向来并不主张学科本位,而是认为要先出乎其外,然后再入乎其内。仅仅闭门造车式地看待本学科的问题,不仅可能一叶障目,甚至可能看错方向。正如我的研究一向试图表明的那样,如果仅仅局限于经验观察和现象描述,那就不足以认识人及其文化,也不足以认识民间江湖和江湖中人。康德看起来天马行空、飞檐走壁,但实际上他的学说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近,也最接地气,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说,他的“这种研究能给其余所有人赋予一种恢复人类权利的价值”(diese Betrachtung allen übrigen einen Wert geben könne, die Rechte der Menschheit herzustellen)*Ernst Cassirer, Kants Leben und Lehre, Verlegt bei Bruno Cassirer, Berlin, 1921, S.251;正如邓晓芒所指出,“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为他那表面看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达方式所吓倒,而是认真且耐心地切入他所表达的思想本身,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确是处处在为普通老百姓考虑他们生存的根据,他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立足于普通人的思维水平,但力图把他们的思想往上提一提,以便能够合理地解决他们在人生旅途中所遇到的困惑。”邓晓芒:《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从原文来看,这种价值也可以理解成“为其余所有人确立作为人类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就相当于后来国际社会所谓的人权。简言之,中国的民间江湖已经走过了数千年,我们在民间江湖中也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一个简单的问题却一直被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且由此被耽搁了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当“人”?我们是不是想让别人和政府把我们江湖中人当“人”来看待和对待?这里似乎至少有这么几个层次:即每个人彼此把别人当人看待、学者把民众当人看待、各级政府官员把民众当人看待。当“人”看待的意思是说,当作有理性的人,有自由能力和有尊严的人,有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权利和义务的人。至少在自己的事务上,每一个老百姓是有能力、有权利也有义务自己给自己做主的。所谓“民主”也是“民”自己做主而不是让别人为民做主。这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等了这么多年才明白,尽管远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而要真正在中国实行起来也许更加困难。因为在中国,仅仅在道德上认识并认可这些道理并且达成普遍的共识已属不易,而要用法治化来对人的自由进行制度保障就更加不易。也就是说,民间江湖中人的自由能否被认可尤其是能否不被公权力侵害,仅凭道德论证是不够的,还必须实行真正的法治。只有在一个真正追求平等和公正的法治社会里,道德才可能具有被广泛实践的外部条件。当然,这已经不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方式,也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但康德的道德论证至少已经从道理和原理上表明,只有建立在可普遍化的客观法则基础上的道德才可能避免种种伪善和伪道德,才可能使民间江湖拥有真正的爱与自由。
既然作为学者,我们也在江湖之中,既然无论是否情愿,我们都是江湖中人,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做出可靠的论证,而且需要经常像叶隽那样扪心自问:
现代学术发展到今日,究竟距离当初求取真知的前贤理念有多少,其实每个学科都应该反躬自问。我们是否还在那条向知向道的崎岖小径上执着而行?我们是否还能承担起作为人类象牙塔的明灯之责任?我们究竟是席勒所言的“哲学之士”还是“利禄学者”?
[责任编辑刁统菊]
作者简介:户晓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