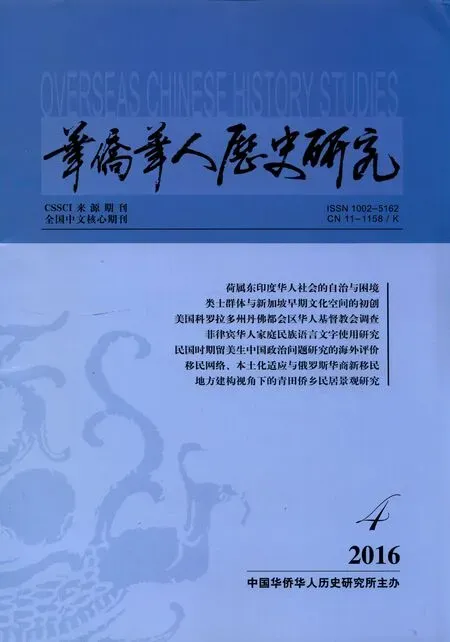地方建构视角下的青田侨乡*
——幸村之民居景观研究
2016-02-02
侨乡研究
地方建构视角下的青田侨乡*
——幸村之民居景观研究
夏翠君
(浙江大学 跨文化与区域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58)
浙江青田;侨乡研究;文化景观;民居景观;田野调查;地方建构理论;幸村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之后,许多华侨不惜代价把大量的精力与金钱投放在家乡的祖屋上,新建的房子或中或西,形成了侨乡的独特文化景观。论文聚焦浙江青田侨乡幸村的民居景观,以历史与地方建构的视角对侨居景观的社会变迁历程及新建侨居社会博弈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索了民居景观与侨乡地方建构的具体社会过程。研究发现,言说与竞争、他者想象、“构想的空间”及“生活的空间”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侨乡的地方建构,把握与利用这些因素对完善侨乡治理与侨乡地方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青田是浙江省著名侨乡,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文化源流影响,其境内逐渐形成了一批地方特色鲜明的著名侨乡,本文所述的幸村就是其一。①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本研究涉及的幸村及村民的姓名均为化名。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之后,许多华侨不惜代价把大量的精力与金钱投放在家乡的祖屋上。他们或修葺,或改建,更多情况是重新建造房子。新建的房子风格或中或西,形成了侨乡的独特文化景观。学界对侨乡民居景观的研究举不胜举。②关于侨乡房屋景观的研究综述可以参阅夏翠君:《房子与华侨村的地方认同》,载《中国侨乡研究》2014年第一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第136~144页。然而,大多数研究缺乏历史与社会建构的视角,更关注民居景观的宏大叙事,却很少聚焦侨乡民居景观形成的社会过程。因此,本研究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入手,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对空间内部丰富片段的还原与观察,对侨居景观的历史变迁历程及新建侨居社会博弈过程进行深入解读。
幸村地处青田南部,四周山峦叠嶂,地势高低不平,这家的门对着那家的屋脊是常有的事。幸村共214户家庭,其中212户都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在海外发展。[1]据青田县侨办2013侨情普查数据,幸村共有华侨1363人,侨眷222人,归侨18人。[2]在幸村,侨汇是大多数家庭最主要且唯一的经济来源,而用于建造房屋的资金绝大多数属于侨资。
在地方形成机制的议题上,无论是人文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承认人的主观性在地方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早在1947年,地理学者怀特(Wright)就提出,地方承载着人类主观性,是一种意义建构方式。[3]以段义孚(Yi-Fu Tuan)、雷尔夫(Relph)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将地方视为一种源于生活世界的主观感受和经验现象。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通过大量生活世界的经验描述来阐释空间转变成地方的过程。他指出,“当我们对空间有所了解,并赋予空间价值的时候,空间就转变成了地方。”[4]雷尔夫强调地方是人的现实经历构成的生活世界。[5]马西(Massey)则认为地方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6]基恩(Gieryn)进一步提出,地方是物理建造或雕刻出来的,但同时地方也是阐释的、叙事的、感知的、体验的、理解的与想象的。[7]
本研究尤其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影响。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对空间生产的内涵及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考察了真实的社会空间是怎样为具体实践所生产,又如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形塑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此外,他开创性地建构了空间的三元辩证理论框架,对索亚、哈维等学者的后现代空间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规划、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8]他认为空间是由相互联系并持续发展的三个部分组成,即“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构想的空间)和“表征的空间”(生活的空间)。地方正是这三者转换过程中某一时刻所形成的特殊空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9]值得注意的是,生活空间并不是空间实践与构想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对他们所假定的完整性进行拆解和重构之后,形成的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选择项。[10]换言之,构想空间有可能通过权力实现空间控制,但是有控制就有反抗,构想空间在生活空间中会遭遇无视甚至反抗。显而易见,上述建构视角的地方形成机制是一种抽象的宏观的概括与归纳。本研究的目的是进入社会构建的微观过程,进而丰富微观层面的本土化研究。
为了进入微观具体的生活世界,2011—2014年,笔者在幸村先后进行了六个月的田野调查,运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辅以查阅幸村及青田档案资料。调查期间,笔者借住在幸村一户人家,一方面能细致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活与日常言说,另一方面也能在串门聊天、倾听村公共空间闲聊中了解幸村的社会互动。
一、幸村侨居的历史变迁
马西强调地方意义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11]地方认同也是一个不断对地方进行想象与再想象的过程。从时间的视角来看,认同的建构从来都不是稳定的,而是动态与流动的。[12]从历史的视角看,幸村作为侨乡的地方意义建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朱竑等认为,“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的形成并非仅局限在地方本身的过程中,外部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情景的变化同样也会对基于本地的地方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13]以下即从外部社会环境的视角梳理幸村侨居的社会变迁历程,展示地方建构意义的动态过程。
“乾成旧居”是幸村第一幢用侨资建造起来的民居,建于1930年。据记载,乾成1905年走出国门,去过比利时和美国,靠贩卖茶叶和青田石发了家,在美国和上海都成立了股份公司。[14]1930年乾成回到幸村,盖起了中西合璧的小四合院,在幸村甚至整个青田县都造成了不小的轰动。造房子所需的钢筋水泥从美国直运回来,门楼顶部塑石质地球仪,壁屏上交叉的美国国旗与青天白日旗惟妙惟肖,两侧门墙开设的冲天铁栅窗也是成品采购于欧洲。这些代表海外文化的建筑元素与中国传统特色的照壁、厢房、中堂、福字喜字木雕共同建构起幸村第一幢侨居。乾成从一个普通村民,摇身一变成了海外发财致富的地方传奇,一时声名鹊起,显赫一方。然而由于外部政治经济大气候的影响,幸村第一幢令人羡慕的侨居并没有立即带来模仿效应,幸村在之后的五六十年里都没出现第二幢侨资建造的新居。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20世纪3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出现了经济危机,青田小贩在欧洲各国的状况令人堪忧。驻欧洲各国大使馆纷纷要求外交部转咨浙江省政府,要求青田县劝阻青田小贩赴欧。青田县档案馆里保存了一宗档案,题为“奉令劝阻小贩被诱赴欧卷”。[15]该档案涵盖了驻比利时、朝鲜、德国、葡萄牙等国大使馆通过民国政府外交部转呈浙江省政府公文,及浙江省政府关于劝阻青邑小贩赴欧所发的政府训令。其中驻德意志共和国大使馆于1936年直接发函浙江省政府呈报,在德国的青田小贩越来越多,引起了很多问题:
此辈小贩商人,言语不通,服饰不整,礼貌不谙,动辄违背警示,遭受拘禁,每为外报指摘,且所贩卖XX①本文引文中出现的“X”,均表示该文字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属粗劣杂货,X不为人欢迎,生计已属困难,比岁一来,经济恐慌,震XX欧,影响所及。青田小贩,敞衣粗实,X卑陋XXX屋,过非人之生活。[16]
文中还提到许多青田商贩均设法借贷而出洋,题系有人引诱他们出洋谋生,而从中谋取私利。这些无知的青邑商贩来到海外之后,“受残酷之待遇,贻国体羞,其愚蠢可怜!”对于那些以出洋致富引诱乡民贸然出国之人,在文中被称为“国家民族之罪人”,“应严以惩戒,以防效尤”。[17]为此,浙江省政府及青田县政府都做出了相应的策略,以停发护照、停办签证等方法劝阻青田小贩赴欧。在这样的环境下,出国谋生被认为是生活所迫,无可奈何之举。村民智会感慨道,“但凡富裕一点的家庭,谁会去走番邦,那都是拿命去搏生活啊。”村民明成告诉笔者,小时候祖父告诉过他,在乾成前后也有村民出洋去谋生,只是后来杳无音讯,都说是死在了路上。之后政府抓得严,出去的人就少了。
第二,国共内战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地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让村民谈侨色变,更不敢建盖侨居。智会每每谈起乾成都会表示遗憾,他说:“乾成在国外辛辛苦苦发了财,回来盖了房子,刚好评地主。”那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在之后的运动中成为“剥削阶级”的铁证。在土地改革中,小洋楼被分给四户人家,乾成家也当上了“地主”。智会说:“其实我祖父也是出过洋的,跟乾成一批的。也赚了不少钱。但是他不喜欢露富,很低调。他说露富要闯祸的。”[18]幸村人看在眼里,谁都自觉把自己与贫穷挂沟,以求安全,更不用说建盖房屋了。村民成启回忆说:“那个年代谁有钱,谁倒霉。”[19]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海外关系”意味着可能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海外关系”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污名”。[20]智会的小祖父一家在俄罗斯,那时候经常来信。智会回忆说:“每当来信了,我家里就紧张。村里的干部就要来询问,信里写了什么。”[21]在那个年代,任何与侨相关的元素都是让人胆战心惊的禁忌话题,幸村人拼命掩盖与侨相关的任何线索与事实,以求自保。
1978年党和政府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向了经济建设。华侨华人在资金、技术及管理方面的经验越来越受重视,他们被视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独特机遇”。[22]华侨华人逐渐成为青田侨乡建设的中坚力量。智会感叹说:“如今真是个好时代,你是华侨你光荣,你有钱,政府还要捧着你。”[23]幸村人从此蜂拥出国,人人争当华侨,家家以侨眷为荣。在华侨及侨乡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背景下,幸村迎来了“以侨为荣”,以侨元素为载体进行侨乡空间再生产的新时代。幸村的侨居也开始进入一个爆发建设的阶段。下面就新时期侨居建造过程中各种博弈的社会过程进行详细分析。
二、攀比与言说:地方认同建构
走进幸村,最惹眼的景观是房子。它体型较大,可见性高,被谈论与凝视的机会自然也多。笔者走进村落去参与观察,正好扮演了一个观众的角色,共同参与侨乡的建构过程。幸村新造的房子很多,到处是工地。有的在建设中,有的则停工许久。2011年笔者刚进幸村就已经开工,到2014年田野调查结束还未完工的房子并不在少数。村民说,因为施工队少,很多工程都被拖下来了。但是能被拖延的关键是幸村人都不着急,他们不等房子住。造好以后,房子多半也是空置的命运。为什么明知是空置,还要花巨资造房子?村里的韶华调侃说:“房子不造出来,谁知道你有钱啊?钱又看不见,房子才看得见啊!”[24]
幸村几乎没人缺房子,但是幸村的房子却越造越多,越盖越“漂亮”。经由口口相传、新闻媒介及各种关于侨乡的知识、想象等话语的推波助澜,幸村也逐渐赢得了“到处都是别墅”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成为“常识”的一部分,一种“自然化”的意识形态。赫兹菲尔德指出,刻板印象倾向于把群体特征描绘成“固定、简单、清晰”,因此“将多重解释的巨大空间掩饰起来”。[25]Thomas[26]、Zhang Li[27]则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刻板印象提供的单一的阐释会受到被压制群体的争辩甚至颠覆。然而,本研究发现这种有利于提升群体身份地位的刻板印象却在社会空间建构中起到了一种模范作用,它促使人们不断努力去附和这种刻板印象。接下来笔者将用丰富的民族志解释来展示言说与攀比在幸村地方建构过程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华侨开始回村建造房屋。每每谈起村里的房子,幸村人都毫不吝啬地展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他们经常会说,这家房子花了几百万,那家房子有电梯,装修得有多豪华。这种在外人面前的地方认同和自豪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同时,幸村人之间又充满了攀比的味道。人们如何谈论和评价自家的房子,成为幸村人最关心的事情,这也成为很多人造房子的动因之一。2012年笔者遇到了刚从意大利回来的村主任建华。说起造房子的初衷,建华说造房子都是为了他母亲。母亲几次都在他面前说,谁谁谁的儿子造房子了,还问他为什么不造。[28]后来房子造好了,建华母亲很满意。但有意思的是,她坚持不肯搬进儿子的新房。她解释说:“我还是喜欢自己的老房子,习惯了。那房子爬上爬下的,太累了。我不喜欢。”[29]建华母亲满意的并不是房子本身,也不打算住进豪华的新房。让她满意的是从此她可以坐在村公共空间,接受大家恭维她儿子房子造得漂亮的话语,进而在村民谈论房子时有自己的话语权。房子能够在村里被谈论,被赋予正面的评价,比建造房子本身更重要。
在幸村,攀比使得景观建造者非常在意别人对房子的谈论,因为这些谈论往往会从房子本身进而评论到房子主人的成功与否、财富多寡与声誉。不过,幸村人这种攀比往往是暗暗较劲,很少发生正面冲突。借由建盖民居景观的象征意义在村里赢得一定地位的人,在此等讨论与闲聊中必定滔滔不绝,或者喜欢参与到此等讨论中去。他们通过把握话语权控制了幸村的社会空间。那些被认为还没有经济资本建盖小洋楼的家庭,则很少会评论别人的房子。他们在“生活空间”中往往失去了话语权,进而被边缘化。但是这些文化景观(房子)对他们而言并非只有排挤和边缘化的意义。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自我身份建构中逐渐明晰了未来的“意向性”——出国打拼,回来建别墅。这也呼应了列斐伏尔把空间当做社会控制的核心要素的观点。
2011年,笔者在青田街头遇到了摆地摊的幸村人连云。连云说自己在清货,马上就要去意大利了。被问起出国前的心情,连云说:“我的心情就是快点赚钱,赚完了回来盖别墅。”[30]连云家的房子是四层楼,造房子的时候他还在读小学。当时在村里也算得上好房子了。用连云自己的话说,他们家的房子现在叫做农民房,与村里那些华侨盖起来的小洋楼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笔者穷追不舍,问农民房与别墅到底有什么差别。连云想了许久也没有明确的答复,他含糊地说:“可能别墅样子要好看点吧,风格是不一样的呢,都是国外的风格,是那些华侨去了国外带回来的。”[31]
虽然是暗自较劲,但是对于那些有经济实力建盖房子的村民,却可以开玩笑,拿房子说事。建华家的房子被认为是全村最漂亮的小洋楼。然而紧挨着的邻居家的房子却是村里排得上号的破旧。房子为三间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大门紧闭,木头门和木窗框已开始腐烂,手轻轻一碰,大片的木屑就往下掉。建华说,别看房子这么破,这户人家很有钱的。房子主人比建华小几岁,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房子主人20岁出头就开始全国各地跑,现在河南那边发展,在同一个县里,开了六家连锁超市。按建华估算,资产至少是几千万。建华与他开玩笑说:“你这破房子,赶紧扒了盖新房了,放在这里,影响我们村容村貌了。”[32]说完这话,两个人都笑了,对方表示的确要回来盖房子,只是生意太忙了,总也抽不开身。建华强调说因为关系好,他才会开如此玩笑。可事实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户人家并不缺钱,已经拥有盖房所需的经济资本,盖房也是迟早的事。当房子本身与主人身份不相符合的时候,谈论房子的破旧并不会拉低主人的社会地位。如Julie Chu所言,房子无论大小,无论什么风格,除去房子本身的现状与各种不同想象,房子主人在时空中的各种轨迹活动也参与房子的意义建构。[33]“影响村容村貌”的玩笑实则是幸村地方认同的一种具体表现。在此,人造景观的象征意义被凸显,景观成为一种象征资本。
三、他者想象与构想空间
村主任建华介绍说,最早的时候,大家比谁造得高,比谁建得阔。你造了三层,我就造四层,他就造五层。村民南平就造了一幢六层半的房子,每每谈起房子,他就来了兴致,必定滔滔不绝。南平自豪地说,他儿媳妇的大学同学来玩,都住那里,他们都说住得舒服,跟城里的宾馆一样。见笔者有兴趣,他还特意从城里回来,带笔者参观了一番。一楼的厨房甚是吸引眼球。一边是设施齐全的橱柜、煤气灶与油烟机,另一边却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土灶台。南平说,逢年过节全家团聚的时候,都是这个土灶台发挥了大作用。而装修气派的煤气灶用上的机会很少,就看看漂亮。二楼以上的每个楼层都用实木地板铺砌。最让南平得意的是顶楼的露台。站在露台上,南平说:“你们城里人不就是稀罕这个露台嘛,坐在上面打打牌,晒晒太阳,现在我们农村条件也好了,都可以做到了。”[34]
然而幸村“比高比阔”的地方建构在青田县领导的一声怒斥后就转向了。当时青田县领导一行到幸村走访。走进村口,看到六层楼高的房子,当时的县长勃然大怒。智会当时还是村干部,一道陪同。他回忆道:
他刚刚走进村里,看到六层楼高的房子,他就怒了。他大骂道,“难道城里还没看够高楼大厦吗?需要在侨乡也造高楼大厦!”他马上责问身边的陪同,问谁给审批建的房。搞得大家都很紧张。后来大家都觉得这房子恐怕要被拆了,或者至少要整改了。但是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35]
在地方身份和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中,经常通过选择“他者”作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36]此时幸村人作为参照物的他者是城市。伴随着当代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城乡二元、城乡差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存在。在中国官方话语中,农民和乡村被看作是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拖后腿的角色。[37]城市意味着“现代化”、“先进”、“文明”,而乡村则是“落后”、“贫穷”。幸村人一旦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就通过对“城市”的想象塑造对城市的“空间意识”,并根据这种“地理想象”[38]来构建自身的地方性。鉴于自身与城市的一定接触和日益丰富的媒介话语,幸村人对城市的地方知识也日益丰富。因此他们建盖跟城里一样的高楼,用木地板铺设地面,打造城里人一样的厨房,修建城里人喜欢的露台,并且随时可以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在露台上晒太阳、打牌。这些都是幸村人对城市及城里人生活习惯的想象。令南平自豪的是,他儿媳妇的大学同学们都对他造的房子赞不绝口。而南平为什么这么看中儿媳妇大学同学的赞扬呢?因为这些大学生不论起初的背景,都是在城市接受的高等教育,都是见过世面的人,而且都在城市扎根落户,都是城里人。能得到城里人的赞同对南平来说意义非凡。有趣的是,当笔者与南平的儿媳妇聊起这事时,她却说那里空气好,不像城里那么拥挤,其他也没什么的。
村口那幢六层楼的房子虽然不了了之,但在那之后,村里建的房子再也不比谁高了。建华说,上面不批,谁也造不了。县长的愤怒来自他对侨乡的地方想象,他认为侨乡就应该具有城市不具备的地方性。而这种地方性的核心是“侨元素”。当华侨成为侨乡建设的中坚力量,华侨就从“农民”或“乡下人”的身份中跳出来,变成了跨国移民。他们定位自身及地方的他者参照物应该是“欧洲”。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东方与西方是不平等的。西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是有优势的,他们是先进的、文明的、科学的。这就是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组合中的“构想的空间”,也称空间的表述。列斐伏尔认为,构想的空间是所谓理论家、规划者以及政府官僚等用空间符号编篡、构想出来的概念化空间。这其中充斥着为了达到空间控制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结合华侨在欧洲的见闻和人们对欧洲地方与欧洲生活的想象,幸村地方建构开始转向。从此,人们谈论房子的视角开始转变,他们用“漂亮”二字来评论,而漂亮的审美视角根源自“欧洲”。罗马柱、拱形窗户、宽敞的阳台、玻璃房等都被视为欧洲建筑风格,都是漂亮的。反之就是“老套”,或者“不稀奇”。幸村人介绍说,这些小洋楼和小别墅,是在欧洲的华侨从欧洲借鉴过来的,与其他地方的房子不一样。由此幸村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性或个性得以建构。而这种特殊性或个性就是地方性。[39]
2014年暑假,几个孩子介绍说,村里公认最漂亮的房子是村主任建华盖的别墅。别墅三层半,在村里并不算高。建华妻子说:“房子不用建那么高,没用,人家外国人的房子都是只有两三层的。”[40]罗马柱、彩色外墙、拱形落地窗、二楼半开放的阳光房、前后院、深红色的大铁门、几个崭新的空调外机。单从外部看,这房子就很耀眼。幸村人都说建华家的别墅是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图纸是建华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幸村人认为意大利人的房子就是建华家这个样子。后来笔者遇到建华,恭维他家房子最漂亮的时候,建华笑了。他很谦虚地说:“没有啦,其实大家都造得很好的呢。”不过后来他又说,他的房子是专门请青田设计院的人设计的,仅设计费就花了四万。他笑着说:“这钱不是白花的。”建华自己的说法与村里广为流传的“意大利设计师”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笔者几次试着更正幸村人的说法,但是似乎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大家还是固执地认为,建华家的房子就是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通过重复、传播和扩散,这些关于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想象与建构自身身份的欲望交织在一起逐渐成为坚不可摧的“事实”。而人们也不会质疑其真实性。在侨乡地方建构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在意空间实践的真伪,也不着急去求证,他们传信传疑,更关注这些人造景观能带给村庄什么样的意义建构。意大利设计的说法似乎把这中国的乡村与欧洲的距离拉得更近了。于此,基于欧洲国家想象的地方建构在动态中得到发展。
段义孚认为:“人造景观阐明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通过人造景观,人们更清楚自己是谁,应该怎么做。”[41]自从“小洋楼”成为评判景观的主流审美视角后,幸村的小洋楼开始越盖越多。而这些越盖越多的小洋楼逐渐形成了幸村的“欧洲风味”,使侨乡光环越发闪耀,幸村人越发自豪。2015年初建华介绍说,村里还有很多人家要造小洋楼,目前在走土地审批手续的就有30多户。幸村结合青田县规划局的意见,打算把30多套房子进行统一设计,把幸村打造成一个“欧洲小村”。建华说:“你过几年再来看,你会发现我们村还会大变样,还要漂亮。”[42]建华的言下之意是指侨乡地方建构将进一步发展,欧洲建筑风格的小洋楼将为幸村营造、建构更加浓郁的侨乡地方性。县规划局与村委会通过对建房审批权力的控制再一次使“构想空间”介入幸村的地方性建构。从县长发怒,从此“上面不批”高层房子建盖,到县规划局联合村委统一对房子进行设计与规划,计划把幸村打造成一个“欧洲小村”,权力的参与作用显露无疑。这里的权力不仅仅指行政上县政府对村级单位的管辖,也包括对他者想象与建构的文化政治。
四、在空间实践中妥协: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角逐
2011年村口有一幢很特别的民居。不同于其他砖结构的房屋,这房子全部用鹅卵石堆砌而成。房子主人远在意大利,因为年久失修,房子的一边已经倒塌。在幸村轰轰烈烈的民居景观建造氛围下,笔者推断这房子的主人必定也在规划着新房的建造。可村民却说这房子不能拆。原来县政府有规定,村里那些年代久远,或者有自身特色的房子都不能随便拆。除了鹅卵石房子,乾成家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及村小店旁边的四合院老宅都在不能拆之列。智会说,县里想留着这些房子,是从旅游开发的设想与视角考虑的。小洋楼中西合璧、四合院老宅保持着清朝年间的结构与风格,可以从遗产角度获得当代存在的意义。而鹅卵石房子符合旅游景观审美价值,也是需要保留的。如果说以遗产与旅游的视角介入幸村的空间规划是构建空间(空间表征)的战略,那么村民就在微观层面上对其进行“抵制”。在德塞都的理论中,所谓“抵制”指的是在宏观上服从强势群体所设立的主流空间秩序,却暗中突破防范,灵活随机地实施小规模的违规。[43]
智会介绍说,很多城里人专门跑到鹅卵石房子跟前拍照,他们都说这个背景好看。然而房主并不认同好看。房主告诉智会,等准备好资金,他就会回来修建新房。对于县里不许拆的禁令,智会与房子主人达成了一致的见解。智会说:“一个县政府要管的事情太多了,他还天天盯着你的房子看啊!到时候拆都拆了,上面也就没办法了。”还有人说,根本不用自己拆,房子失修多年,最多再过两年,它自己就塌了。也有村民担心县政府较真,但是早就有人想好了应对的策略。他们说政府来较真,让他们到意大利去较真。言下之意是政府够不到跟一个意大利华侨较真。
四合院风格的老宅属于一个大家族,东西南北各归四个分支所有。而四个分支对老宅不能拆的规定也存在看法。东边与南边两家都公开表示了不满。他们几次与村委会与县政府交涉,要求政府为他们重新安排地基建盖新房。几年下来,县政府松口了,除了乾成的小洋楼,其余的都可以拆除重新建盖。村主任建华说,这些房子如果不维护,迟早要倒塌。而县财政的保护资金也没有落实到位。另外当事者的抵制与交涉也是县政府调整政策的原因。这体现的是生活空间对构想空间的胜利。笔者2013年重返幸村再次进行田野调查时,鹅卵石的房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三层小别墅。四合院的东边和南边也被崭新的房子取代。明成说,北边的这户人家来年也要拆了重建。
乾成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却没在松口之列。更甚者,通过县政府的努力,小洋楼被评上了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以更加正式的权利机制被保护起来。县政府坚持保护小洋楼的背后动机来自小洋楼的特殊背景与象征意义。小洋楼是乾成在美国赚了钱后回国盖起来的。虽然在政治动荡年代,小洋楼遭到破坏,但是大局完好。而改革开放以来对华侨政策的转变,小洋楼本身已经成为早期“华侨”勇于海外开拓、致富不忘桑梓的历史见证。保护小洋楼,借用早期村民海外开拓的集体记忆,构建幸村拥有华侨的悠久历史,更加凸显幸村作为侨乡的特质和氛围,进而建构侨乡的地方性。
五、结语
本文以历史与地方建构的视角对侨居景观的社会变迁历程及新建侨居社会博弈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索了民居景观与侨乡地方建构的具体社会过程。景观代表着一个地方群体的自我文化与社会认同方式。而在地方身份和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人们经常通过选择“他者”作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随着华侨、侨乡在当地话语中的权力地位变化,幸村经历了从“城市”他者到“欧洲”他者的蜕变,建盖起想象中的与欧洲人一样的小洋楼。而小洋楼的象征意义刺激并引导着更多人的未来建造意向。在景观建构过程中,竞争与言说、他者想象及来自政府与专家层面的“构想的空间”,共同作用于侨乡地方建构的生活空间。构想空间对于地方空间的整体设计,是否能成功介入地方建构,还取决于人们在“生活空间”中的对应举措。构想空间对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及欧洲村的构思通过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取得了地方空间控制的胜利。然而,生活空间中的人们对于强势的构想空间并不是一味地顺从,他们也会展开抵抗,甚至能迫使构想空间调整政策,从而实现生活空间对构想空间的胜利。
本研究的现实及学术意义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以地方构建的理论视角考察侨乡民居景观的动态发展过程,让人们认识到地方建构之复杂社会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列斐伏尔指出,社会空间的建构会巩固政治、经济、社会的形成。[44]当地政府及社区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在地方治理与地方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家庭、社区、言说等来塑造、引导和影响人们的所思所为,让“构想空间”与“生活空间”在一种和谐的环境下相互作用,以改善地方治理,实现较理想的地方建设。
其次,本研究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展示了地方建构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截然不同的意义解读。因此在处理地方建构相关问题时要充分尊重地方历史及历史遗留问题,理解并巧妙做好历史转承。本文并不致力于得出一个最终的研究结论。因为“地方经由人类主观性的重新建构与定义,超越了空间实体单纯的物质性,进而成为了一种充满意义、且处在不断动态变化中的社会与文化实体”。[45]笔者判断,随着时空压缩时代的到来,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局势的不断变化,侨乡的民居景观与地方建构也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并将赋予地方新的意义。因此,面对未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新的局势。
最后,比起广东、福建等传统侨乡,青田新侨乡所受的学界关注与青田华侨在当今侨界的地位并不相称。本研究选择聚焦青田侨乡,不仅丰富了侨乡研究的视角和田野个案,增进了国际国内移民学界对青田侨乡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关注,同时也丰富了空间生产及地方建构理论的微观研究。
[注释]
[1] 2016年11月6日幸村主任建华提供的最新侨情数据。
[2] 数据由青田侨史馆言小海先生提供。
[3] J. K. Wright,“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Terican GeograPhers,Vol. 37,No.1,1947,pp.1-15.
[4] Y.F. Tuan,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p.6.
[5] E.Relph,Place and Placelessness,London: Pion,1976,pp.2-46.
[6] D. Massey,“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lace”,in D. Massey and P. Jess eds.,A Place in the World? Places,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 45-85.
[7] T. F. Gieryn,“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 26,No. 1,2000,pp. 463-496.
[8] H.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 Blackwell,1991,pp.68-168.
[9] K. Hetherington,“In Place of Geometry: The Materiality of Place”,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Vol. 45,S1,1997,pp.183-199.
[10] 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1] D. Massey,SPace,Place and Gender,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12] E. Said,Culture and ITPerialisT,New York: Knopf,1994,pp. 3-18.
[13] 朱竑、钱俊希、陈晓亮:《地方与认同: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人文地理》2010年第6期。
[14] 青田华侨史编纂委员会:《青田华侨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0~311页。
[15] 青田县档案局、浙江大学历史文献与民俗研究中心编:《青田华侨档案汇编》(民国)第一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9~119页。
[16] 《青田华侨档案汇编》(民国)第一辑,第103页。
[17] 《青田华侨档案汇编》(民国)第一辑,第104页。
[18] 2013年8月8日,笔者于村民智会家中访谈智会。
[19] 2013年8月8日,笔者于村民智会家中访谈成启。
[20] 范可:《“海外关系”和闽南侨乡的民间传统复兴》,杨学潾、庄国土编:《改革开放和福建华侨华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6~157页。
[21] 2013年8月12日,笔者于村民智会家中访谈智会。
[22] 庄国土:《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华侨华人态度和政策的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
[23] 2013年8月12日,笔者于村民智会家中访谈智会。
[24] 2012年12月23日,笔者于村小店门口访谈村民韶华。
[25] M. Herzfeld,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Indifference: ExPloring the SyTbolic Roots of Western Bureaucracy,New York: Berg,1992,p.73.
[26] T. Nichola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ATerican Ethnologist,Vol. 19,No. 2,1992,pp. 213-232.
[27] L. Zhang,Strangers in the City,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8] 2012年5月1日,笔者于村小店门口访谈村主任建华。
[29] 2014年12月23日,笔者于建华家中访谈建华母亲。
[30] 2011年10月5日,笔者于青田夜市访谈连云。
[31] 2011年10月5日,笔者于青田夜市访谈连云。
[32] 2013年8月10日,笔者于建华家中访谈建华。
[33] Julie Y. C.,CosTologies of Credit: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estination in China,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p. 41.
[34] 2013年10月6日,笔者于南平家中采访南平。
[35] 2013年8月8日,笔者于村民智会家中访谈智会。
[36] 安宁、朱竤:《他者,权力与地立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人文地理》2013年第1期。
[37] M. L. Cohen,“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Peasant’”,Daedalus,Vol. 122,No. 2,1993,pp. 151-170.
[38] D. Harvey,“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Terican GeograPhers,Vol. 80,No. 3,1990,pp. 418- 434.
[39] 周尚意等:《“地方”概念对人文地理学各分支意义的辨识》,《人文地理》2011年第6期。
[40] 2014年12月23日,笔者于建华家中访谈建华妻子。
[41] Tuan,Y.F.,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p.102.
[42] 2015年2月11日,笔者于建华家中访谈建华。
[43] 练玉春:《论米歇尔·德塞都的抵制理论:避让但不逃离》,《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44] H.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401.
[45] 朱竑、钱俊希、陈晓亮:《地方与认同: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人文地理》2010年第6期。
[责任编辑:胡修雷]
Place Making: A Study on Dwelling Landscape in Qiaoxiang—Xing Cun Village in Qingtian, Zhejiang Province
XIA Cui-jun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and Reg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place making; space production; qiaoxiang; dwelling landscape; fieldwork; Qingtian
Dwelling landscape in qiaoxiang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cademic attention place making remains a topic that is overlooked by many previous studies. Focusing on dwelling landscape in Xing Cun Village, a famous qiaoxiang in Qingtia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adopts Henry Lefebvre’s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and makes use of abundant ethnographic data. Combing theories and data, it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s dwellings and explores the social making process of newly built dwelling landscape. The study finds that many factors (including speech and competitio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s, conceived space, lived space and etc.) contribute to qiaoxiang’s place making. Thus it is beneficial to adopt these perspectives to improve loc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further enriches ethnographic case studies, by promoting people’s understandings of Qingtian, a significant qiaoxiang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is study helps to locate place-making theories at a micro and local level.
D634.2
A
1002-5162(2016)04-0082-09
2016-09-13;
2016-11-14
夏翠君(1981—),女,浙江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侨乡研究与话语文化研究。
*本研究得到广东五邑大学“中国侨乡研究博硕士论文资助”项目资助,特此表示感谢。此外,浙江大学徐立望副教授与青田侨史馆言小海先生为本文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浙江大学阮云星教授、浙江师范大学胡美馨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余华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侯松博士及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