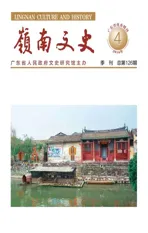明清之际岭南文学世家的伦理处境与家学传承
——以番禺王邦畿家族为考察中心
2016-02-02李婵娟
李婵娟
明清之际岭南文学世家的伦理处境与家学传承
——以番禺王邦畿家族为考察中心
李婵娟
明清之际番禺王氏家族是岭南地区典型的文学世家。清乾隆《番禺县志》载:“今彭孟阳、王邦畿两家子弟俱能以文藻世其家,且抗高节,而王氏尤胜……不独勋业名节自奇,难其人皆有集,不失琅琊家风耳。”[1]王氏家族的盛名始于明遗民王邦畿。王邦畿(1618-1668),字诚籥,明崇祯时副贡生,明隆武元年(1645)举人。明唐王绍武中,以荐官御史。后追随永历帝,桂林倾覆后,永历帝西逃,王邦畿遂回乡避于顺德龙江。晚礼函昰于雷峰寺。著有《耳鸣集》。他文学、气节兼胜,极受乡人景仰,开王氏诗书传家之先河。其子王隼、侄王鸣雷、孙女王瑶湘均能坚守遗民气节,且富有诗文;王隼妻潘孟齐、子王客僧、婿李孝先、族人王者辅、王佳宾等亦博学能诗。在明清易代之际,番禺王氏家族在伦理处境、家庭文化建设及家学传承方面均呈现出独特之处,蕴含鲜明的时代意义,为洞悉遗民诗人的生活世界开启了一扇窗口,也为深化家族文化的传承研究提供了新的样本。
“留得孤魂归侍帝”——别样的政治伦理图景
番禺王氏家族崛起于明亡清兴的易代之际。在“以夷变夏”的特殊政局下,儒家伦理秩序经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忠君”与“养亲”、“为国”与“为民”、“仁”与“忠义”等诸种矛盾迅速激化,儒士们在生死出处之际面临着异常艰难的抉择,对自我的身份探寻与价值认同也成为日常的困惑与焦虑。在这种特殊的政治伦理困境下,王家的文化传承呈现出别样的图景。
易代之悲带来的政治伦理困境,首当其冲地表现为“生”、“死”的抉择。但与中原文人及江南士人相比,岭南文人在生死之际所遭受的精神磨难似乎相对平缓。概因岭南远离明朝帝都,信息有所滞后,加上南明政权迭起,明祚绵延的表象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岭南人因崇祯帝殉国而引起的悲痛。王邦畿的伦理选择就真实反映了当时岭南士人的生存状态。从王邦畿在崇祯帝殉难后义不容辞地服务于诸个南明政权的行迹看,似乎他和诸多投身于抗清前线的岭南志士一样,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生”“死”困扰。但若细品王氏诗作,则可读出另一番况味。其《丙戌腊末》诗云:“草野知今日,飘然愧古人。此心空有泪,对面向谁陈?”[2]清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清将李成栋攻破广州,大肆屠戮。王邦畿虽幸免于难,但自觉有愧于古人“成仁取义”之训,心中有无限悲痛却无人倾诉。另其《西风飒然至》诗云:“西风飒然至,瑟瑟入长林。木落水流处,孤舟明月心。美人敛颜色,游子罢瑶琴。珍重平生意,前溪霜雪深。”该诗托物言情,寄喻遥深。陈永正认为:“国运的衰颓,志士的悲慨,前路的艰难,都一一寓于诗中,非寻常嘲风弄月之作可比。”[3]看来王邦畿依然经受着苟活于世却无所作为的心理煎熬。这是岭南文人并未彻底摆脱生死的伦理难题、在思想困境中苦苦挣扎的隐微心态的真实反映。
两难的伦理处境,更集中地体现在“死君”与“养亲”的矛盾冲突中。王邦畿也一度陷入困境,他最终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遁入空门,“礼僧函昰于雷峰。”[4]本文认为,王邦畿的入禅更多地是带有一种忠君、悼君的仪式感,此与一般的抗拒清廷或政治避难截然不同。从其所作的“虚堂独坐闻寒雨,疑有孤魂泣夜声”(《庚寅冬夜宿诃林》);“莫忆前时事,风寒鼻易酸”(《禅院小除与莫思微》);“暂且忘思虑,焚香礼佛名”(《闲居》)等诗句可看出,永历帝惨死滇南后,王邦畿深知国事无望,遂毅然出家,借青灯古佛为先帝守灵,以示对故国故君之忠诚。看来在“君”“亲”之间,他果断选择了前者。后来其子王隼也在他的影响下遁入缁流,以遗民终老。王鸣雷云:“叔(王邦畿)向时语匡庐,以不及游为恨事,辄泫然。隼弟饱卧数年匡庐云,饱食数年匡庐水。”[5]道明王隼披薙出家、栖隐山林的人生选择乃深受其父之影响。江西易堂诗人魏礼《悼王说作》诗云:“留得孤魂归侍帝,近闻一子竟为僧。”[6]可谓知己之言,准确道出了王氏父子遁迹空门的深层动机。
王氏父子两代为僧的现象在明清之际是极为少见的,他们在政治伦理困境下的人生选择,使得遗民气节作为家学传统得以承传,并博得世人称赞。王邦畿逝世后,梁佩兰作《挽王说作》诗云:“几人泉下路,似汝世间贤?”[7]陈恭尹祭词云:“早宾于王,多士眉目。天工人代,云章玉轴。时移步改,振缨濯足。”[8]赵执信曾将王隼和陈恭尹比拟为“冰与雪”[9],对王隼不改父志的遗民节操赞赏不已。此外,王氏家族的子弟们也很好地继承了忠贞的遗民气节。史称王隼女王瑶湘“怡然矢节,自称逍遥居士。”[10]王邦畿从子王鸣雷与其父王者辅在明亡后均不再出仕。
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王家的遗民气节及不仕清廷的家学传统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陈垣曾感叹:“遗民易为,遗民而高寿则难为。”[11]道出了易代之际欲保全志节者之艰难。遗民尚且如此,而作为遗民子弟,当遗民话语及遗民节操在时间中备受剥蚀、销磨之际,要想继承父志,其艰难更是不言自明。王隼虽能秉承其父遗志,不仕清朝,但晚年仍避免不了与清吏的交游酬唱。王隼所作的《仲冬陪尹澜柱铨部、陈元孝、林叔吾入羚羊峡,怀梁药亭先生》、《送孔樵岚参军六首》等诗即是王隼与清吏交往之明证。更为严酷的是,历史推动遗民社会无可避免地走向消亡,遗民现象的时间性也必然决定了遗民身份的世袭之难。王瑶湘能秉承庭训,坚守气节,对此历代士人多有赞赏。然据清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五记载,王隼子王客僧中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科举人,官云南知州。对于此点却少有人论及。此事颇值得玩味。于此,钱穆曾感叹:“弃身草野,不登宦列,惟先朝遗老之及身而止。其历世不屈者则殊少。既已国亡政夺,光复无机,潜移默运,虽以诸老之抵死支撑,而其亲党子姓,终不免折而屈膝奴颜于异族之前。此亦情势之至可悲而可畏者。”[12]可见,世族家学及遗民节操的传承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政治、时代思潮及伦理处境的影响。
“古风妻似友”,“父子自相知”——易代境况下的家庭文化
作为岭南较有影响的文学世家,番禺王家在夫妇、父子、联姻等家庭关系的处理上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其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践行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较之君国、父子,夫妇一伦是私密的。易代之际,遗民士大夫更要强调君、国为重而家室、妻小为轻,因此他们对夫妻间的私密情感与生活基本上讳莫如深。王氏家族以君、国为重而家为轻的态度是勿庸置疑的,但在夫妇关系的处理上,王氏却并非不近人情。王邦畿《客中寄内》诗云:“客逢风雨衣裳薄,望转乡园道路遥。梦见仪容来昨夜,修将书信寄今朝。”在家国飘零、羁旅奔波中对妻子寄予无限思念与深情,可见王邦畿对妻子的温情体贴。对妻子的辛劳与病痛,王邦畿也充满了感激与怜惜:“闺人呼犬子,掌梦叶熊时。对此劬劳意,亲恩无尽期。”(《生子》)另外,《为圃》一诗则展现了自己学耕种的乐趣:“未农先学圃,编槿复诛茅。乞得瓜壶种,忙乘春夏交……笑共家人语,秋来满素庖。”在士大夫普遍以“不事家人产”而自得、大多将门户经营交由妇人之际,王邦畿能放低读书人的姿态,对家务躬亲操持,足见其对妻子的爱惜。此类表现家庭温馨的内容在遗民士人笔下是不多见的。妻子逝世后,王邦畿毫不掩饰对亡妻的思念:“欲落上弦月,犹存亡妇灯。垂帘就襟枕,竟夕寐无能。”(《夜归》)朴素的语言中自有一种深情在。王邦畿对妻子的态度也影响到王隼。史载王隼妻潘孟齐亦能诗,王隼隐遁山林之后,潘孟齐作《寄怀夫子》诗以表相思之意,有“如何伯鸾妇,翻作仲卿妻”[13]之恨。其后潘孟齐亦事优婆夷。对妻子的偕隐之举,王隼深为感动,作《客中七夕答孟齐内子见寄》诗示之:“喜汝能偕隐,惭余久未还。”[14]其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后来“蒲衣将返初服,报书孟齐。孟齐答曰:‘君既有意,妾亦同心。’遂归室。”(《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粤小记》)从现存的史料中,我们认识到的是王氏父子坚守遗民气节、弃家参禅的刚硬形象,而从王邦畿父子对夫妻间琐屑生活的描述中,人们读到的是夫妻间朴实的温存与真情。由此可见,忠贞遗民之士,其处夫妇也是极为通达乃至深情的。这或许才是遗民精神世界的最真实状态。归庄诗云:“古风妻似友”[15],王氏家族夫妇间的融洽关系正是对此种诗意般家庭生活的极好呈现。
父子人伦是传统家庭伦理的主轴。关于父子关系,赵园曾指出:“古代中国的知识人,严于等差、伦序,却又不无变通,不乏欣赏融和之境的能力——是伦理的,又是审美的。”[16]王氏家族可谓是一门之内“自相师友”,父子关系充分体现了通达融和的一面。王邦畿是一位开明慈爱的父亲,谈及儿子,他用得最多的是“稚(穉)”字。如“穉儿师放读书归”(《己亥小除立春》);“长路随行怜稚子”(《客中呈苏元易并示隼儿》);“穉齿昨朝初及长”(《为隼儿娶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儿子的温情与关爱。王隼笔下的父亲也极其仁慈:“忆余七岁咏凤凰,趋庭问礼大夫旁。改诵子山《枯树赋》,坐客期我似班扬。大人抚摩恒置膝,口授《离骚》《老》与《庄》。”(《述怀杂言与熊燕西野人结交》)同时,王家极为重视家庭教育,父子有时又似严明的师生。王邦畿“常诲隼曰:‘若作衣裳尔时佩,若种涧松尔其岁。慎毋时俗以为雷同,慎毋唯诺以为取容……’隼曰:‘谨受命。’”[17]王邦畿教育王隼不要受时俗束缚,更不能唯诺以求容合。王隼虽生长于清朝,未受明朝之恩,从当时的流俗及公议来看,似可不再受“尽忠”、“守节”之限制,但他依然能克绍箕裘,一生不仕清廷,可见父亲的教诲对其影响深远。不仅如此,王隼也善待子女,对后代子孙的教育亦能谨守其父之遗训。王隼之女瑶湘博学多才,能读《礼经》、《南华》、《离骚》,深得梁佩兰赏识。需特别指出的是,王客僧的出仕也是在父亲王隼去世很久之后,且当时清廷的统治已基本稳定。这说明遗民子弟的家学传承往往要承受比常人更大的道义压力。
王氏家族在联姻问题的处理上也别具特色。从营造家庭氛围及传承家族文化的角度看,联姻往往责任重大。因此在儿女婚姻方面,王氏家族可谓煞费苦心。王邦畿为王隼聘娶好友潘楳元之女潘孟齐为妻。潘楳元,广州番禺人,出生于书香之家,曾被荐举为广州教授。晚筑西山草堂,凿池种竹。后入空门,礼天然和尚。著有《广州乡贤传》。潘氏与王氏在家学渊源上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两家的联姻遂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王邦畿曾作诗云:“最喜新盟联旧好,交情一倍重南金。”(《与潘浣先定男女婚姻》)岭南诗人程可则、梁佩兰、王鸣雷等均有诗祝贺。后来,王隼继承了父亲的联姻理念,将女儿王瑶湘许配给故人李恕之子李仁。王氏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成功构建了和谐统一的家庭文化,使得家庭成为家人精神的归宿和心灵的港湾,这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
“诗是吾家事”——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
王邦畿一生肆力于诗歌创作,“诗书传家”遂成为王氏家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对王氏父子的诗学传承,当时诗人论述较多。屈大均说:“蒲衣赋才奇丽,能出其新意,追琢为乐府、五七言体,陵轹汉魏、三唐,仍其家学。”[18]陈恭尹亦云:“先生(王邦畿)以诗名世者也,清古峭健,而王子以春容富丽承之,得其旨矣。”[19]陈恭尹在评价王隼诗时,更指出了王氏父子在诗学上的共同特点,他说:“丽则典赡,与其尊人若有浓淡之分,而骨清神寒,即无差别。”[20]那么,“骨清神寒”的内涵究竟为何?首先,我们来看看后人对王邦畿诗歌的评价。屈向邦《粤东诗话》云:“说作怀亡国之痛,悲天下事无可为……适遇社题《燕台怀古》,乃尽情泄发之。上半言欲如荆轲之击秦,下半则故宫禾黍,遗臣与周道之悲矣。”[21]檀萃《楚庭稗珠录》评邦畿诗云:“集中近体为多,托喻遥深,缠绵悱恻,憔悴婉笃,善于言情,哀而不伤,甚得风人之旨。”[22]上述评论提及王邦畿诗歌的两个主要特点:其一,多抒发亡国之痛,颇具感伤情调;其二,表达含蓄委婉、寄托遥深,甚得风人之旨。本文认为,此二点正是对“骨清神寒”的最好注解。
在王氏家族的家学传承过程中,王隼是异常关键的人物,其诗歌创作体现出传承父辈诗学的自觉意识。屈士煌曾一语道中王隼诗歌的特点:“禾黍故宫,吊春魂于望帝;风尘歧路,写幽怨于恨人。”(屈士煌《大樗堂初集·题辞》)王隼的《咏怀》、《杜门》、《村居》等诗均委婉地抒发了对世事兴亡的感慨与孤愤哀愁的幽怀,此类诗作与其父诗歌中哀悼故国、自伤身世的内容是一致的。另外,在表现手法上,他学习了父亲《秋怀十首》、《西风飒然至》等诗托兴暗寓的隐曲笔法,“以凄思苦调为哀蝉落叶之词,致自托于佳人君子、剑侠酒徒、闺闱边塞、仙宫道观,以写其呵壁问天、磊落扼塞、怫郁侘傺、突兀不平之气”。(梁佩兰《大樗堂初集叙》)王隼还擅长运用比兴和寄托的手法,使诗含蓄蕴藉、韵味无穷。其《西山杂咏》诗“或以男女相思之辞,或以破寺落日之语,隐寄对故明的缅怀,用心可谓良苦”。[23]黄培芳评其诗“极才士绮丽之词,复不失风人蕴籍之旨”。[24]含蓄委婉的诗风经由王邦畿、王隼父子的努力,遂成为王家鲜明的诗学传统。王瑶湘的《逍遥楼诗》也传承了这种家学特色。其《拟送别》、《独坐》等诗寄情于景,蕴籍婉转,不减乃祖之风。王鸣雷诗亦“纯乎中唐钱、刘、韩、王诸家,真得风人之旨。”[25]
王氏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除了表现在对感伤情调、含蓄委婉诗风的继承之外,还表现为一种明确的诗学理想的建立,即由诗歌创作扩展到诗集编选方面。其中王隼的表现尤其突出。他精心编选了大量诗歌选集,展现出树立雅正的诗歌范式以传承家族诗学理想、宣扬岭南诗学传统的良苦用心。如其编选的《唐诗五律英华》“精取其浑,朴取其完,能使读者见选者之心,与作者当日之心相遇”(梁佩兰《五律英华序》);其编选的《岭南诗纪》是已成书的清代最早的一部广东省的通代诗歌总集;《岭南三大家诗选》的编选则隐然有抗衡江左三大家之意,对确立和提高岭南三大家诗人的地位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另外,王鸣雷在康熙初也曾参修《广东通志》,时称典核。这些均体现了王氏子弟弘扬家族诗学传统的决心及整理乡邦文献的自觉意识,对推动岭南诗歌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王氏族人还通过广泛的交游与频繁的文学雅集来扩大王氏文学世家对岭南诗坛的影响。王邦畿为“岭南七子”之一,也是清初岭南重要的遗民社团西园诗社的核心成员,他与屈大均标举“祖述风骚,流连八代”[26]的宗旨,借诗歌酬唱传承《诗经》及《离骚》以来的诗歌传统,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岭南诗风。在西园诗社的社集活动,王邦畿经常与诗友们进行自觉探讨及自由论争,王鸣雷说:“九叔说作览山水,立论说……俾环坐而听者皆解颐。”[27]可见,王邦畿的诗歌主张在当时诗坛应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另外,王隼、王鸣雷也是西园诗社后期的重要成员。王氏子弟的诗歌活动对推动清初岭南诗坛的繁兴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王邦畿及王氏家族的发展中可以看到,文学世家的一门风雅和家学文化对于窥探社会历史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世家文化既集中体现了地域特色,又是对时代文化的典型概括。特定的政治环境、伦理处境及时代风尚使得家族成员的发展既有个性特点又兼具一家之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家族文化的形成与传承。透过王邦畿及王氏家族“诗书传家”的一门盛景及其对遗民气节的坚守,我们能窥见到明清之际岭南遗民士群整体的生活状态及真实的精神世界,而在特定的政治局势与社会背景的视角下考察家族文化的传承,也为理解传统文化的延绵兴衰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有利于传统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文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批准号:16YJC751012);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培养项目(批准号:Yq2013162)。
注释:
[1]任果:《(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五,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2]本文所引王邦畿诗,均出自《耳鸣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3]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4]陈伯陶:《王邦畿传》,《粤东胜朝遗民录》,卷一,清代传记丛刊本。
[5]王鸣雷:《大樗堂初集叙》,王隼:《大樗堂初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6]魏礼:《魏季子文集》,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刊本。
[7]本文所引梁佩兰文字均出自《六莹堂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8]陈恭尹:《独漉堂文集》,卷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刊本。
[9]赵蔚芝、刘聿鑫:《赵执信诗集笺注》,黄河出版社,2002。
[10]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二十,影印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
[11]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五,中华书局,1962。
[12]钱穆:《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
[13]吴绮:《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4]本文所引王隼诗文,均出自《大樗堂初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5]归庄:《归庄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6]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7]陈伯陶:《王隼传》,《粤东胜朝遗民录》,卷一。
[18]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9]陈恭尹:《独漉堂诗集》,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0]伍元薇:《大樗堂初集》跋,王隼:《大樗堂初集》卷末,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1]钱仲联:《清诗纪事(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22]檀萃:《楚庭稗珠录》,卷四,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23]陈永正:《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4]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嘉庆十五年(1810)岭海楼刻,嘉庆十六年重校本。
[25]陈伯陶:《王鸣雷传》,《粤东胜朝遗民录》,卷一。
[26]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
[27]温汝能:《粤东诗海》,下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