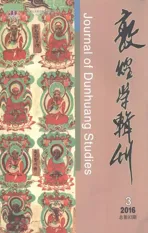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出世论考(下篇)
——兼对古灵宝经出世时间下限的考定
2016-02-02王承文
王承文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五、《灵宝经目序》与敦煌本《灵宝经目》的内在关系
敦煌本《灵宝经目》与现存《灵宝经目序》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将直接决定敦煌本《灵宝经目》究竟是元嘉十四年(437)的《灵宝经目》,还是宋明帝泰始七年(471)陆修静所编《三洞经书目录》中的洞玄部灵宝经的目录。我们认为现存陆修静《灵宝经目序》与敦煌本《灵宝经目》是两个相互关联亦高度倚存的文本。陆修静《灵宝经目序》所说的《灵宝经目》,其实就是指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中一些最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陆修静《灵宝经目序》所称“《旧目》所载”和“篇章所见”涵义辨析
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中,专门记载了他在整理古灵宝经之前古灵宝经的混乱状况,其文称:
顷者以来,经文纷互,似非相乱。或是《旧目》所载,或自篇章所见,新、旧五十五卷。学士宗竟,鲜有甄别。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寻觅,甫悟参差。
究竟什么是陆修静所说的“或是《旧目》所载”,什么是“或自篇章所见”呢?学术界一般认为这里的“或是《旧目》所载”,是指《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即“十部妙经三十六卷”;至于“或自篇章所见”则是专指“新经”。不过,近年来,刘屹博士对此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他认为“或是《旧目》所载”,是指《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而“或自篇章所见”,则是指在“元始旧经”和“新经”之外单独流传而后来却又失传了的一批“断简残章”。其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还有“一些灵宝经,现已没有完整篇章传世,但却在某些现存的古灵宝经中被转引或提及过”[注]刘屹《“元始旧经”与“仙公新经”的先后问题——以“篇章所见”的古灵宝经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1页。。由于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敦煌本《灵宝经目》的结构等十分关键。对此,我们试作简要讨论。
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中前后所说的“《旧目》”以及“十部《旧目》”意义应完全相同。《灵宝经目序》所称“或是《旧目》所载,或自篇章所见,新、旧五十五卷”,如前所述,所谓“《旧目》所载”,其“《旧目》”就是是特指元嘉十四年(437)陆修静着手整理古灵宝经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专门著录“元始旧经”的《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陆修静将其简称为《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因为,无论是古灵宝经本身,还是陆修静,其所说的“《旧目》”都是特指《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而这里的“或是《旧目》所载”,是与“新、旧五十五卷”中的“旧”经即“元始旧经”相对应的;至于“或自篇章所见”,则是与“新、旧五十五卷”中的“新”经相对应的,是专门指“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近年来,小林正美亦指出所谓“或自篇章所见”,是“指代葛仙公所受的‘新经’”[注][日]小林正美著,王皓月译《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134页。。
那么,陆修静为什么要用“或自篇章所见”来专门指代这批“新经”呢?这是因为在陆修静编纂《灵宝经目》之前,“元始旧经”已有《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这样一个专门的目录。然而,这些“新经”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尚处于一种分散无序的状态,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目录将它们编纂在一起,因此陆修静特地将它们称之为“或自篇章所见”。与此相关的表达方式还有很多。例如:(1)《灵宝经目序》称:“虑有未悉,今条《旧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注解意疑者略云尔。”其中“并仙公所授事”即专指“新经”,而且是与“今条《旧目》已出”相并列的;(2)敦煌本《灵宝经目》逐条列举了全部“元始旧经”和“新经”之后,称“十部《旧目》及新名录记如前”。其中“十部《旧目》”,就是指《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著录的“元始旧经”。而“新名”则是指所有“新经”的经名;(3)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称:“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其中“并仙公所禀”即指“新经”,并与“今见出元始旧经”是相并列的;(4)《云笈七签》卷三《灵宝略纪》称:“(葛)孝先(即葛玄)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并语禀请问十卷,合三十三卷。”其“并语禀请问十卷”就是指“新经”,而且是与“(葛)孝先(即葛玄)凡所受经二十三卷”即“元始旧经”相并列。可见,陆修静所称“或自篇章所见”,本身是与“或是《旧目》所载”相并列的。否则,大批“新经”的存在将会无所指归。也正因为如此,陆修静所称“或自篇章所见”,并不是指在“元始旧经”和“新经”之外还有单独流传的“断简残章”。
其次,刘屹博士所提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古灵宝经“新经”(他将其称之为“仙公新经”)是在“元始旧经”之前出世这样一个结论为前提的。他认为“‘新经’不仅没有称引任何一部‘旧经’经名和内容,而且表现出与‘旧经’建构的经教体系有所不同”。对此,我们经过重新研究,证明古灵宝经“元始旧经”一般都比“新经”更早出世,“新经”不但大量征引了“元始旧经”的经名及其内容,而且从整体上来看,古灵宝经“新经”也主要是对“元始旧经”的诠释和进一步发展。[注]王承文《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兼对刘屹博士系列质疑的答复》,《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最后,陆修静所称“顷者以来,经文纷互,似非相乱。或是《旧目》所载,或自篇章所见,新、旧五十五卷”,是指原《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再加上《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之外的“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即“新经”,总共为55卷。然而,陆修静认为这55卷的“旧经”和“新经”中,各自都存在十分严重的真伪不分、鱼龙混杂的情况,所以陆修静通过仔细甄别,去伪存真,最终才形成了这部《灵宝经目》。而原来的“新、旧五十五卷”,变成了敦煌本《灵宝经目》所说的:
(“新经”)右十一卷,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都合前元始[旧经],新旧经见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为三十五卷,或为三十六卷。
因此,陆修静编成的这份《灵宝经目》,既包括了经过他确认的由《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也包括了经过他确认的真正可信的“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
(二)陆修静《灵宝经目序》所称“十部《旧目》”,究竟是“出者三分”,还是“出者六分”?
1.从《灵宝经目序》看“元始旧经”之“出者六分”的可能性
陆修静《灵宝经目序》记述了古灵宝经“元始旧经”的出世数量,其文称:
但经始兴,未尽显行,十部《旧目》,出者三分。虽玄蕴未倾,然法轮已遍于八方,自非时交运会,孰能若斯之盛哉!
所谓“十部《旧目》”,如前所述,是专门指陆修静《灵宝经目》中“《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即“十部妙经三十六卷”。而陆修静所称“但经始兴,未尽显行,十部《旧目》,出者三分”,是说“元始旧经”并没有全部出世。而其中一个最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里究竟是“十部《旧目》,出者三分”,还是“十部《旧目》,出者六分”呢?近三十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是严重困扰国际学术界的难题,亦是导致各种争议纷纭最主要的根源。因为,如果是在“十部妙经三十六卷”中“出者三分”的话,那么,当时就只有大约11卷“元始旧经”出世。然而,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却称:
……右《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今分成二十三卷,十五卷未出。
其称“元始旧经”中“二十一卷已出”,显然与《灵宝经目序》中“十部旧目,出者三分”,即11卷不相符合。也正因为如此,小林正美、刘屹等研究者判定敦煌本《灵宝经目》是泰始七年(471)陆修静所编《三洞经书目录》中洞玄灵宝经的经目。如果小林正美等学者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在公元437年陆修静写定《灵宝经目序》之时,必然还有大量“元始旧经”尚未出世。也就是说,作为“元始旧经”系列主体为数众多的古灵宝经,其实都是在公元437年到471年之间才被创作出来的。[注][日]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41-142页;王皓月《再论〈灵宝经〉之中‘元始旧经’的含义》,《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第85-90页。
1997年,大渊忍尔和柏夷(Stephen R.Bokenkamp)在其各自的著作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出敦煌本《灵宝经目》就是元嘉十四年的经目,并且都认为《灵宝经目序》中的“出者三分”,是《云笈七签》在流传过程中因为抄写等原因所导致的错误,其原文本应是“出者六分”。[注][日]大渊忍尔《道教とその经典》,东京:创文社,1997年,第88页;Stephen R. Bokenkamp,“The Wondrous Scriptures of the Upper Chapters on Limitless Salvation”,in Bokenkamp,Early Daoist Scriptur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p.396-397.Bokenkamp,Stages of Transcendence: The Bhūn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s,” in Robert E.Buswell,Jr.ed.,Chinese Buddhist Apocraph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140.如果是“出者六分”的话,那么,“元始旧经”之“十部妙经三十六卷”中“已出”的数额,则应为21.6卷。这与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中“元始旧经”的数量21卷基本符合。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对此稍作引申。因为如果是“出者五分”,则应为18卷;如果是“出者七分”,则应为25卷。所以“出者六分”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数目。也就是说,在刘宋元嘉十四年(437)之后,不再有新的古灵宝经典问世。
从小林正美等学者所列举的相关证据来看,陆修静《灵宝经目序》中的“十部《旧目》,出者三分”,应是其整个立论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证据。[注]小林正美所列举的另外两条主要证据包括:第一,鸠摩罗什所译大乘佛教经典在江南的影响,开始于公元420年左右。因此,古灵宝经中的大乘佛教影响,必定在此之后。而柏夷所发表的多篇论文,证明了古灵宝经中的大乘佛教思想,主要源于孙吴时期支谦所译佛经的影响(见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 Strickmann ed,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A.Stein,Vol.2.Brussel.,1983, pp.434-486,1983);第二,小林正美从《道教义枢》卷2《三洞义第五》所引古灵宝经“新经”《真一自然经》中,出现了刘宋后期南岳道士徐灵期的名字,从而认为古灵宝经的创作应延续到了刘宋中后期。不过,敦煌文书P.2452“新经”《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上卷》即《真一自然经》有关古灵宝经的传授,却只有东晋建元二年(344)葛洪在罗浮山传经的记载。并没有其后包括刘宋后期徐灵期等人的记载。而大渊忍尔和柏夷的结论,则主要建立在他们对古灵宝经的整体把握上,并不局限于某一孤立性的证据,因而也具有较大的合理性。然而,这两位学者所称“出者六分”的说服力则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我们试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包括道教经书在流传过程中,“二”、“三”、“六”、“七”、“八”等这些数字发生误写的现象确实比较常见。[注]例如,“二”与“七”字就容易相混淆。唐代闾丘方远《太上洞玄灵宝大纲钞》称葛玄卒年曰:“仙公以吴赤乌二年八月十五日,于天台山白日升天。”(《道藏》第6册,第376页)然而,陶弘景撰《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却称“仙公赤乌七年太岁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长往不返”(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2页);元代谭嗣先《太极葛仙公传》记载其于“赤乌七年八月十五日”升仙。又称“于甲子岁八月十五日午时上升,径赴阙庭”,“仙公上升时年八十一”(《道藏》第6册,第847页);元代赵道一《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卷23《葛玄传》称“于甲子岁八月十五日午时飞升,径赴阙庭”(《道藏》第5册,第229页)。而“甲子岁”即为吴大帝赤乌七年(244)。因此,《太上洞玄灵宝大纲钞》中的“吴赤乌二年”必定是“吴赤乌七年”的错误。我们试图通过一些相关例证来进一步说明。敦煌文书P.2452号《灵宝威仪经诀上》,即古灵宝经“新经”《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的残卷,该经记载从太极真人徐来勒以来灵宝经的传授过程,其文称:
……抱朴子君建元六年三月三日,于罗浮山付[葛]世,世传好之子弟。
以上敦煌文书的字体属于行书。其“建元六年”应是“建元二年”的错误。因为东晋康帝司马岳在位并以“建元”纪年,总共就是两年(343-344),因此,以上敦煌文书中的“建元六年”,必定是抄写者错误抄写所致。[注]王承文《葛洪晚年南隐罗浮山事迹释证——以东晋袁宏〈罗浮记〉为中心》,载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11月),第253页。刊载于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1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58-184页。另外,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道藏通考》中也指出了这一点,见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The Taoist Canon :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236.而与此类似的讹误实际上也同样出现在收录有陆修静《灵宝经目序》的《云笈七签》中。我们试举有关灵宝经传承的资料来说明。
唐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二《三洞义第五》所引《太玄都四极盟科》称:
……(葛)洪号抱朴子,以晋建元二年三月三日,于罗浮山付弟子海安君望、世等。至从孙巢甫以晋隆安之末,传道士任延庆、徐灵期之徒,相传于世,于今不绝。[注][唐]孟安排《道教义枢》卷2《三洞义第五》引《道藏》第24册,第813页。对这一资料的来源,我们将另有专门讨论。
《云笈七签》卷六《三洞经教部·三洞并序》引《四极盟科》称:
……(葛)洪又于晋建元二年三月三日,于罗浮山付弟子安海君望世等。后从孙巢甫,晋隆安元年,传道士任延庆、徐灵期,遂行于世。[注][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6《三洞经教部·三洞并序》,第90页。
而《云笈七签》卷六《三洞经教部·三洞品格》所引《太玄都四极盟科》却又为:
……抱朴[子]以建元六年三月三日,于罗浮山[付弟子安海君望、世等。至从孙巢甫,以晋]隆安之末,传道士任延庆、徐灵期之徒,相传于世,于今不绝。[注][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6《三洞品格》,《道藏》第22册,第34页。按:《正统道藏》本此段残阙较多,据[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校补。
如前所述,东晋康帝“建元”年号,前后总共只有两年。因而“建元六年”亦必然是“建元二年”书写的讹误。至于前引《云笈七签》引《四极盟科》所称“隆安元年”,亦仅属于一个非常孤立的个案,与其它所有记载都不合,因而也完全可能是“隆安末年”的讹误。因为“元”与“末”字的书写亦确实很容易造成混淆。
近年来,刘屹博士判定敦煌本《灵宝经目》属于泰始七年(471)经目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云笈七签》本《灵宝经目序》是经过北宋官方组织编纂的传世文献,其文字的整齐规范程度要大大超过敦煌写本”;并进而认为“除非能找到别本证据来参校,否则无法让人相信‘出者六分’或‘未出者三分’才是正本”。[注]刘屹《敦煌本〈灵宝经目〉研究》,《文史》2009年第2辑,第66页。应该说,刘屹博士对这一问题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值得肯定和赞赏。然而,现存《云笈七签》在其第六卷中对《太玄都四极盟科》一书的前后两次征引,竟然存在“建元二年”和“建元六年”两种完全不同的写法。而且“建元六年”又必然属于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的讹误。因此,不能因为《云笈七签》在宋代以来道门内部流传广泛亦很权威,就排除形成这种讹误的可能性。但是,以上这种明显的讹误却又可以肯定并不是北宋官方编纂《云笈七签》时所出现的,而是该书在其后来流传过程中因为抄写所出现的错误。这种错误出现的时间,应该在明代《正统道藏》编纂之前。因此,结合其它证据来看,我们认为《云笈七签》所收陆修静《灵宝经目序》原文中的“出者六分”,在后来流传过程中被误为“出者三分”,应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
2.从《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看“元始旧经”之“出者六分”的必然性
陆修静的《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明确说明此前经过整理后的古灵宝经数目是“三十五卷”,从而也证明了敦煌本《灵宝经目》就是公元437年编成的经目。由于有关古灵宝经出世的记载本身极其匮乏,因而这一条材料也是最能说明古灵宝经出世的极少数关键证据之一。《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称:
臣修静依栖至道,翘竚灵文……自从叨窃以来一十七年,竭诚尽思,遵奉修研,玩习神文,耽味玄趣,心存目想,期以必通,秉操励情,夙夜匪懈。考览所受,粗得周遍,自觉神开意解,渐悟理归,宛义妙致,本自仰绝,其粗迹近旨,谓可彷佛。伏寻灵宝大法,下世度人,玄科《旧目》三十六卷……但正教始兴,天书宝重,大有之蕴,不尽显行。然即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根末表里,足相辅成;大乘之体,备用不少。[注]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道藏》第9册,第839页。
陆修静所称“自从叨窃以来一十七年”,大渊忍尔考证是指陆修静入道之后17年,为元嘉二十一年(444),也就是其编纂《灵宝经目》并撰写《灵宝经目序》之后的第七年。[注][日]大渊忍尔《道教とその经典》,第74页。按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所称“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与敦煌本《灵宝经目》对“元始旧经”和“新经”的记载符合。学术界只是对《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的成书年代存有争议。小林正美先是提出《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成书于“元嘉之末”即公元453年(见[日]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第136、170页)。然而,小林正美在其新著《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的《前言》中,则提出《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成书于“元嘉十八年(441年)”(见[日]小林正美著,王皓月译《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8页)。不过,小林正美的新观点实际上对其自己最初的核心观点作了极为重要的修改。因为小林正美一直坚持元嘉十四年的《灵宝经目序》中“十部《旧目》,出者三分”是正确的。如果其新提出的《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作于“元嘉十八年”的观点能够成立,则意味着大量新的“元始旧经”都写成在“元嘉十四年”到“元嘉十八年”仅三至四年间。而不是原来的从“元嘉十四年”到“泰始七年”(471)的长达三十四年之间。同时也就意味他否定了自己在《六朝道教史研究》中所列举的古灵宝经创作延续到刘宋中后期的证据。近年来,刘屹博士则提出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与《灵宝经目序》一样,均为公元437年所作(见其《古灵宝经出世论——以葛巢甫和陆修静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5页)。刘屹博士一方面并未说明其将该书确定在公元437年的理由,另一方面则会使其前后观点相抵牾。因为如果刘屹博士此说能够成立的话,则应该明白无误地确证了敦煌本《灵宝经目》必然是属于元嘉十四年的《灵宝经目》。因为《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已非常清楚地说明“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与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和“新经”的数量,即“今为三十五卷”正好相符合。不过,刘屹博士在此前所撰《敦煌本〈灵宝经目〉研究》(《文史》2009年第2辑)等一系列论文中,亦将敦煌本《灵宝经目》看成是陆修静于刘宋泰始七年(471)所编《三洞经书目录》中灵宝经的目录。认为陆修静《灵宝经目序》中的“出者三分”不可能是“出者六分”的抄写错误。进而认为有大量“元始旧经”都是在元嘉十四年(437)《灵宝经目》编成之后直至公元471年之间才出世的。刘屹博士最近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其前后观点存在抵牾和矛盾之处。一方面他虽然仍然坚持敦煌本《灵宝经目》是泰始七年所成经目,大量“元始旧经”是在元嘉十四年之后作成,但是,另一方面则对《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所称“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称“是后人根据陆氏471年的目录所做的改写,因为那时的灵宝经卷数在很长时期内已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最终卷数”(见其《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第141页)。即“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是后人甚至可能是明代人改写而成的。不过,从现存资料来看,这种观点目前恐怕还很难加以证实。以上“伏寻灵宝大法,下世度人,玄科《旧目》,三十六卷”,所谓“玄科《旧目》,三十六卷”,就是指“《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三十六卷“元始旧经”。而陆氏所谓“正教”与敦煌本《灵宝经目》中宋文明所作注释中的“正文”一词具有相同的涵义,都是特指“元始旧经”。而所谓“并仙公所禀”之“并”字,当为“合在一起”的意思。所谓“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是说经过他甄辨并确认可信的古灵宝经是“三十五卷”,应指“二十三卷”的“元始旧经”,加上“十二卷”的“新经”,总共三十五卷。有关其具体计算方法见后面的讨论。
在《灵宝经目序》中,陆修静一方面强调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出世的不完整性,其称:“期运既至,大法方隆。但经始兴,未尽显行。”而其《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亦称:“但正教始兴,天书宝重,大有之蕴,不尽显行。”二者都是说“元始旧经”没有完全披露出来。然而,另一方面,陆修静却又非常强调现有已出“元始旧经”所具有的度人救世的重大意义。其《灵宝经目序》称:“十部旧目,出者三(六)分。虽玄蕴未倾,然法轮已遍于八方,自非时交运会,孰能若斯之盛哉!”而《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亦称:“然即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根末表里,足相辅成;大乘之体,备用不少。”而敦煌本《灵宝经目》陆修静即明确称:
……都合前元始[旧经],新、旧经见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为三十五卷。或为三十六卷。
因此,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实际上已经证明了敦煌本《灵宝经目》就是元嘉十四年的经目。而这一条材料也非常确切地证明了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应属于陆修静撰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之前的经目,而不是泰始七年(471)陆修静奉宋明帝敕编成的《三洞经书目录》中灵宝经的目录。
3.从陆修静著作的整体论述看“元始旧经”之“出者六分”的必然性
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将敦煌本《灵宝经目》确定为公元437年的经目,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者三分”,并不真正符合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中上下文的表述。因为陆修静在该《序》中,一方面对于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伪造古灵宝经的行为,都给予了极其严厉的谴责,并严厉禁止道教中人继续创作任何新的古灵宝经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公元437年之后,无论是“元始旧经”抑或“新经”,还在继续增加扩充。也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陆修静本人以及“他身边的天师道道士们”直接参与了古灵宝经的创作。而坚持敦煌本《灵宝经目》作成于公元471年的研究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似乎都有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灵宝经目序》这一特定文本中,看看陆修静整理之前的古灵宝经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尤其是要理解陆修静甄别和整理古灵宝经究竟包括了哪些具体内容。其《灵宝经目序》称:
顷者以来,经文纷互,似非相乱,或是《旧目》所载,或自篇章所见,新、旧五十五卷,学士宗竟,鲜有甄别。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寻觅,甫悟参差,或删破上清,或采搏余经,或造立序说,或回换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图,或以充旧典,或別置盟戒。文字僻左,音韵不属,辞趣烦猥,义味浅鄙,颠倒舛错,事无次序。考其精伪,当由为狷狂之徒,质非挺玄,本无寻真之志,而因修窥阅,假服道名,贪冒受取,不顾殃考,兴造多端,招人宗崇。敢以鱼目,厕于隋侯之肆;辄将散砾,托于和氏之门。衒诳愚蒙,诬誷太玄。既晚学推信,弗加澄研,遂令精粗糅杂,真伪混行。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上则损辱于灵囿,下则耻累于学者。进退如此,无一可宜。徒倾产疲力,将以何施?夫轻慢之咎既深,毁谤之罪靡赦。
所谓“顷者以来,经文纷互,似非相乱,或是《旧目》所载,或自篇章所见,新、旧五十五卷,学士宗竟,鲜有甄别”,均是指古灵宝经存在大量鱼目混珠的情况,“元始旧经”和“新经”的总数已达到55卷之多。而陆修静所称“既加寻觅,甫悟参差。或删破上清,或采搏余经,或造立序说,或回换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图,或以充旧典,或别置盟戒”,则是说当陆修静对这些经书加以整理研究之后,他也才明白了这些经书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有些经书是从上清经典剽窃而来的;(2)有的是依据对其他各种经书的摘录而形成的;(3)有的是伪造了经书的序言;(4)有的是替换了原来的篇目;(5)有的增加了章句;(6)有的经书制作了新的符图;(7)特别是所谓“或以充旧典,或别置盟戒”,是说有人用虚假的经文去充当“元始旧经”。而有的则在经书中添置了其它的盟誓文字和戒律;(8)这些伪滥的经书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文字僻左,音韵不属,辞趣烦猥,义味浅鄙,颠倒舛错,事无次序”。
陆修静对于出现这样严重伪滥情况的原因也作了专门分析。他认为,一方面是“狂狷之徒”,不惧怕因果报应而胆大妄为地加以粗制滥造。他说:“考其精伪,当由为狷狂之徒,质非挺玄,本无寻真之志,而因修窥阅,假服道名,贪冒受取,不顾殃考,兴造多端,招人宗崇。敢以鱼目,厕于隋侯之肆;辄将散砾,托于和氏之门。衒诳愚蒙,诬誷太玄。”然而,另一方面,则也是因为后来的修道者真伪不分,盲目崇信所造成的。他说:“既晚学推信,弗加澄研,遂令精粗糅杂,真伪混行。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而灵宝经书真伪不分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则是“上则损辱于灵囿,下则耻累于学者。进退如此,无一可宜。徒倾产疲力,将以何施?夫轻慢之咎既深,毁谤之罪靡赦”。所谓“上则损辱于灵囿”,“灵囿”在中国古代指供帝王狩猎和游乐的园林。《诗经·大雅·灵台》记述了最早的周文王灵囿,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此代指帝王的大业。可见,陆修静认为伪滥的经书不但损害污辱了帝王的大业,也严重败坏了道教的声誉。
正因为如此,陆修静既表现了对有意造伪者行为的极端深恶痛绝,又对众多信奉者被蒙蔽感到极为痛心疾首。同时也表明陆修静自己是坚决反对伪造灵宝经的。其称:“余少躭玄味,志爱经书,积累锱铢,冀其万一。若信有可崇,何苟明言,坐取风刀乎!”意即自己从年少之时就开始崇信道教,敬奉灵宝经书,而且尽力做经书的搜集和积累。如果道教信仰本身是值得尊崇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随随便便地公开来说,以招致死后下地狱的恶报呢?所谓“坐取风刀”,在古灵宝经中常见,代表地狱恶报。显然,陆修静在此是以极其虔诚的道教信仰,来向天神誓言其自己的所作所为均符合灵宝经本身的实际情况。
历史资料证明,陆修静本人与江南“葛氏道派”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而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中批判道门内部伪造古灵宝经的同时,也强调“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寻觅,甫悟参差”,“余少躭玄味,志爱经书,积累锱铢,冀其万一”。这些都显示陆修静所整理的古灵宝经经书,主要源于他自己长期以来对古灵宝经的搜集和信仰。[注]王承文《陆修静道教信仰从天师道向灵宝经转变论考——以陆修静所撰〈道门科略〉为起点的考察》(上篇、下篇),《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3期。所谓“甫悟参差”,“甫”是指方才,刚刚,意即虽然他对古灵宝经的搜集研究的过程很长,但是真正领悟并能分清其中真伪混杂情况,却是在其撰写《灵宝经目序》之前不久。而其撰写《灵宝经目序》之时,距离东晋安帝隆安(397-401)末年葛巢甫“造构灵宝,风教大行”[注][梁]陶弘景《真诰》卷19《翼真检第一》,《道藏》第20册,第604页。,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而此时有大量“元始旧经”和“新经”已经流传于世。《灵宝经目序》称:
元嘉十四年某月日,三洞弟子陆修静敬示诸道流。相与同法,弘修文业,赞扬妙化,兴世隆福。每欣一切,遭遇慈泽,离彼恶道,入此善场,逍遥长乐,何庆如之!
以上都是陆修静对当时道门中人共同修奉灵宝经盛况的描述。而且陆修静又进一步强调,此时古灵宝经“虽玄蕴未倾,然法轮已遍于八方,自非时交运会,孰能若斯之盛哉!”也证明此时道门内已经有大量道士正在修习灵宝经。也就是说,在公元437年之前,古灵宝经早已成为道门内部普遍修奉的经典。陆修静作为道门领袖,他对前人和同时代的人大量伪造古灵宝经的行为作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和谴责,并把他认定为伪造的大量假古灵宝经排除在其《灵宝经目》之外,而且又以其道教信仰来誓言他自己甄别古灵宝经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似乎很难想象,此后他自己却又明目张胆地鼓动“葛氏道派”中人或者“他身边的天师道道士们”继续创作新的古灵宝经,甚或自己还亲自动手来创作古灵宝经。并且直到公元471年编纂《三洞经书目录》时,他却又将这些经典名目堂而皇之地都编在一起。
《正统道藏》和敦煌遗书共保留有陆修静著作八种,即《陆先生道门科略》、《灵宝经目序》、敦煌本《灵宝经目》、《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太上洞玄灵宝法烛经》、《太上洞玄灵宝众简仪》、《洞玄灵宝五感文》等。根据我们的研究,陆修静对古灵宝经严谨而忠实的态度,也贯穿在其一系列现存著作中。除了《道门科略》专门阐述天师道的宗教传统、制度和教义思想之外,陆修静的其它所有著作,则都是通过大量直接征引古灵宝经并且按照古灵宝经教义思想编撰而成的。在这些著作中,陆修静把对古灵宝经原文的征引与他自己的发挥和论述都作了相当清晰的区别。也证明了他自己不可能参与古灵宝经的创作,同时也决不可能容忍其同时代的其他人创作新的经典以冒充古灵宝经,然后他自己还特地加以征引。例如,其《太上洞玄灵宝众简仪》称:
《明真》、《玉诀》并有其详,而晚学暗惰,志性浅略,遇见一科,不加精寻,率意施用,遂致矫错,亡首失尾,永不悟非。若斯之徒,常为痛心,视其沦溺,惧伤慈教,谨依旧典,撰投简文次第,复为甲乙,注解法度,以启昧者之怀,自为门人成轨,岂苟施悠悠者哉。[注]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道藏》第6册,第563页。
我们将陆修静的《太上洞玄灵宝众简仪》,与相关古灵宝经的原文逐字逐句地核对,可以发现陆修静这一著作95%的内容,其实都能在古灵宝经中找到原始出处,而陆修静本身也将其出处作了尽可能明确的说明。至于陆修静自己的注解,则以小字加以区别。[注]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7-534页。而这就恰恰证明了陆修静对待古灵宝经极其严肃和恭敬的态度。其《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亦称:
自灵宝导世以来,相传授者,或总度三洞,同坛共盟,精粗糅杂,小大混行。时有单受洞玄,而施用上法,告召错滥,不相主伍。或采博下道,黄赤之官,降就卑猥,引屈非所,颠倒乱妄,不得体式,乖违冥典,迷误后徒。臣每晨宵叹惋,内疚泣血。既真师渺邈,不可希期钻求,世学永无其文。事要急用,实宜充备。[注]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道藏》第9册,第840页。
以上一方面对灵宝经真伪混乱的情形给以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则表明要加以纠正。按照陆修静自己的说法,其在编撰该书的过程中,“执笔战栗,形魂交丧,惧以谬越致罪,又虑造作招考,进退屏营,如蹈刃毒。缮治虽竟,不敢擅用,谨洁身清斋于三宝御前,诵读一过。恩惟太上众尊、玄中大法师,垂神照鉴,矜察所启。若万有一毫之补,合请施行。如其不允,辄当毁除。可否之宜,要以灵瑞为证,愿特赐告效,伏须感应”。以上足见其态度极其虔诚真挚。同时陆修静亦是要人们相信其编撰此书,是完全忠实于古灵宝经经典本义的。
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中,陆修静也说明了自己编撰该书所依据的主要经典及其对待灵宝经典的态度。其文称:
臣敢以嚣瞑,窃按《金》、《黄》二箓、《明真》、《玉诀》、《真一自然经诀》,准则众圣真人授度之轨,敷《三部八景神官》,撰集登坛盟誓,为立成仪注。执笔战栗,形魂交丧,惧以谬越致罪,又虑造作招考,进退屏营,如蹈刃毒。缮治虽竟,不敢擅用,谨洁身清斋于三宝御前,诵读一过。恩惟太上众尊、玄中大法师,垂神照鉴,矜察所启。若万有一毫之补,合请施行。如其不允,辄当毁除。可否之宜,要以灵瑞为证,愿特赐告效,伏须感应。谨启:臣修静诚惶诚恐,稽首再礼以闻。臣陆修静谨进。
陆修静称其“撰集登坛盟誓,为立成仪注”,明确提到所依据的最主要材料,包括这样一些古灵宝经:(1)“《金》、《黄》二箓”,是指“元始旧经”《太上洞玄灵宝经金箓简文三元威仪自然真一经》;(2)“《明真》”是指“元始旧经”《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3)“《玉诀》”是指“元始旧经”《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4)“《真一自然经诀》”则是指“新经”《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上卷》;(5)所谓“敷《三部八景神官》”,是指敦煌本《灵宝经目》著录的“元始旧经”《太上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三部八景自然神真箓仪》,《道藏》本称为《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经》。
根据我们的研究,该书90%以上的内容均源自其对13部古灵宝经的征引。其中“元始旧经”包括:《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太上洞玄灵宝经金箓简文三元威仪自然真一经》、《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洞玄灵宝三部八景二十四生图经》等。而其所征引的“新经”包括:《太上玉经太极隐注宝诀》、《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上卷》、《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等。在这部著作中,陆修静亦尽可能地将其所征引的古灵宝经经文的出处加以说明,并使之与自己的论述区分开来。
陆修静在刘宋元嘉三十年(453)撰写的《洞玄灵宝五感文》,是其以灵宝经法思想为基础对汉晋以来道教斋法的第一次总结。其文称:
至道清虚,法典简素,恬寂无为,此其本也。而世物浮伪,鲜能体行,竞高流淫,信用妖妄,倚附邪魅,假托真正,君子小人,相与逐往,昏迷长寝,曾莫甄悟。致上危神器,下倾百姓,灭身破国,犹不以戒。至乃浊乱正炁,点染清真,毁辱大道,可为痛酷。[注]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道藏》第32册,第618页。
以上也反映了陆修静将道教斋戒仪式是否真正符合“法典”即道经原典,看成是极其庄严神圣的大事。并认为伪滥的经书以及斋法,将会“上危神器,下倾百姓,灭身破国”,“浊乱正炁,点染清真,毁辱大道”。从该书所记载的灵宝斋法即金箓斋、黄箓斋、明真斋、三元斋、八节斋、自然斋六种斋法来看,陆修静对以上六种斋法概括性的论述,都能在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包括《无上秘要》斋法对相关古灵宝经的征引)中找到原始出处和相关对应。
需要指出的是,小林正美先生其实也认为陆修静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古灵宝经的创作。[注][日]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第130页。然而,从现存陆修静著作与古灵宝经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很难想象陆修静一边对前人伪造古灵宝经的行为加以严厉谴责和批判,一边却又允许甚或鼓励身边的道士们继续大量创作古灵宝经。学术界近年有研究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陆修静虽然表面上严厉谴责道教中人伪造灵宝经,而他自己却一方面续写完成了人间实际存在的元始系《灵宝经》,另一方面又大量亲自创作了原本未出的“元始旧经”。[注]王皓月《再论〈灵宝经〉之中‘元始旧经’的含义》,第85-90页;王皓月《灵宝经の研究—陆修静と灵宝经の关系を中心に》,早稻田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从现存的各种资料来看,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还需要重新斟酌。
总之,从陆修静《灵宝经目序》整个文本的结构和前后语境来看,很显然,他的目的决不是为“葛氏道派”的道士们抑或“他身边的天师道道士们”继续创作古灵宝经张目,也决不是为他自己对古灵宝经进行大规模修改、续写甚至亲自来重新创作而张目。其真正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批判和谴责业已存在的古灵宝经真伪混杂的情况,并要努力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另一方面也是要坚决遏止禁绝道教内部继续伪造古灵宝经的行为。
(三)《灵宝经目序》末尾所称“今条《旧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与敦煌本《灵宝经目》的对应关系
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的末尾,实际上已经指明了其《灵宝经目序》与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的对应关系。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一个重要证据。其文称:
虑有未悉,今条《旧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注解意疑者略云尔。
所谓“虑有未悉”,是指陆修静一方面忧虑道教中人不能知晓和分辨古灵宝经鱼目混杂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在经过他甄别整理之后,这种情况又重新出现,所以他特地要加以逐条说明。以上的“条”字是一个动词,古代有“条陈”、“条写”、“条具”、“条述”、“条列”、“条白”等表达方式,还有“条分件系”的表达。而这里的“条”就是指逐条梳理校核之义。所谓“今条《旧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就是指陆修静在《灵宝经目》中,既逐条陈述了“《旧目》”即《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各经“已出”或“未出”的情况,也逐条叙述了各“新经”已出世的情况。而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对《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元始旧经”之“已出”或“未出”,以及“新经”的出世情况都有非常明确的说明,证明《灵宝经目序》所述与敦煌本《灵宝经目》的实际状况是完全符合的。
小林正美先生在其新著中,一方面根据《灵宝经目序》所称“今条《旧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认为其中“并仙公所授事”是指“仙公新经”,并强调这一种表达能够证明“仙公系《灵宝经》在元嘉十四年都已经被编纂了”。[注][日]小林正美著,王皓月译《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第134页。然而,另一方面他似乎又过于执着于“出者三分”这样一种非常孤立的表达,坚持认为大量“元始旧经”都是在元嘉十四年以后才被创作出来。不过,这一点却与他新提出的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成书于“元嘉十八年(441)”的观点又是相矛盾的。[注]见本文前面对《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年代的讨论。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陆修静所称“今条《旧目》所出”,实际上也能证明真正出世的“元始旧经”都已经通过《灵宝经目》列举齐备了。不存在用新创作的古灵宝经来继续补充这份经目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灵宝经目序》所称“十部《旧目》,出者三分”,完全有可能就是“出者六分”。至于陆修静所称“注解意疑者略云尔”,是指陆修静除了在《灵宝经目》中逐条陈述“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出世情况之外,还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各自出世和分卷总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说明,对灵宝经“十二部”的名称及其含义也作了简约的注解。而这一点也是与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的情况相符合的。
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中既然明确说正是因为“虑有未悉”,所以他才“今条《旧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一方面表明他已经将古灵宝经“已出”和“未出”的情况在当时道门内部广而告之;另一方面,他自己对道门内部伪造灵宝经的现象作了如此严厉的批判,也就表明了他要禁止道门内部继续伪造或重新创作古灵宝经的事情再次发生。因此,可以确定,在《灵宝经目序》最末的这一句话之后,紧接着的应该就是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至于《三洞经书目录》中洞玄部灵宝经部分,应该仍然是按照公元437年编定《灵宝经目》时的原貌来编纂的。反之,如果他在公元437年甄别整理古灵宝经之后,却又将新增加的古灵宝经重新编入《三洞经书目录》的话,一方面他必须要重新修改他在437年《灵宝经目》中对相关“元始旧经”所作出的“已出”或“未出”的具体说明;而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他完全背信弃义,公然也公开地违反了他自己此前的誓言和承诺。
至南朝中期,宋文明所作《灵宝经义疏》除了辑录陆修静《灵宝经目》之外,又注称:“后有三十五卷伪目,仍在陆《源流》卷末,不录入此也。”以上是指在陆修静编成《灵宝经目》之后,曾经另有一部关于伪古灵宝经的“三十五卷伪目”。因为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中称“顷者以来,经文纷互,似非相乱。或是《旧目》所载,或自篇章所见,新、旧五十五卷”,而陆修静认为这“新、旧五十五卷”中恰恰都是真伪混淆的。因此,在被陆氏确定为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之外的经书,原则上都属于“伪经”,其数额大致是23卷,再加上在元嘉十四年之后至宋文明重新整理古灵宝经之前新出的12卷伪古灵宝经,它们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三十五卷伪目”。而这也证明了自陆修静于元嘉十四年确立《灵宝经目》后,任何未被陆修静《灵宝经目》著录的古灵宝经,都被视为“伪经”。因此,宋文明所称“三十五伪目”的存在,恰恰证明了陆修静作为道门领袖,其在公元437年所进行的“今条《旧目》已出并仙公所授事”等做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并且在道门内部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宋文明本人也坚持了陆修静所确立的原则。他在注解《灵宝经目》时称:“正文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二卷见行于世,余十四卷犹隐天宫。”所谓“正文有三十六卷”,就是指《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所著录的“十部妙经三十六卷”即“元始旧经”。而“其二十二卷见行于世,余十四卷犹隐天宫”,与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对“元始旧经”的著录情况相符合。[注][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6《三洞经教部·三洞品格》称:“元始天王告西王母曰:‘《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有十部妙经,合三十六卷。’是灵宝君所出,高上大圣所撰,具如《灵宝疏释》,有二十一卷已现于世,十五卷未出。”(第93页)按以上《灵宝疏释》就是宋文明《灵宝经义疏》。
至北周武帝天和五年(570),甄鸾上《笑道论》三卷,该书“道经未出言出者”条称:
案玄都道士所上经目,取宋人陆修静所撰者《目》云:上清经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于世。检今《经目》,并云见在。乃至洞玄经一十五卷犹隐天宫,今检其《目》,并注见在。臣笑曰:修静宋明[帝]时人,太始七年因勅而上《经目》,既云隐在天宫,尔来一百余年,不闻天人下降,不见道士上升,不知此经从何至此?[注][北周]甄鸾《笑道论》卷下,载道宣《广弘明集》卷9,《大正藏》第52册,第151页。
可见,从宋文明到南北朝末期的甄鸾写成《笑道论》之间,原《灵宝经目》中注明“未出”的一批“元始旧经”亦已经出世。所谓“洞玄经一十五卷犹隐天宫”,与宋文明称“余十四卷犹隐天宫”含义相同。至于其“一十五卷”和“十四卷”的区别,仅仅是对相关经典卷数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四)《灵宝经目序》与敦煌本《灵宝经目》所称古灵宝经数目的计算方式
中外学术界有关古灵宝经出世的分歧和争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对这些经典数量计算方式的不同而引发。因此,我们不妨将《灵宝经目》中几种计算方式详列如下。
(1)敦煌本《灵宝经目》陆修静原文称:“都合前元始[旧经],新旧经见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为三十五卷,或为三十六卷。”以上所谓“三十二卷真正之文”,应是指“《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即“二十一卷已出”的“元始旧经”,再加上“十一卷”已出的“新经”,共32卷。
(2)敦煌本《灵宝经目》陆修静所谓“今为三十五卷”,应是指“今分成二十三卷”的“元始旧经”,再加上分成十二卷的“新经”。因为在这种计算中,《太上洞玄灵宝天文五符序经》已不是原来的一卷本,而是“仙公在世时所得本,是分为二卷”,共为35卷。
(3)敦煌本《灵宝经目》陆修静所称“或为三十六卷”,指“元始旧经”和“新经”总数为36卷。在这种计算方式中,“元始旧经”已经变成了“今分成二十三卷”,加上十三卷“新经”。因为《太上洞玄灵宝天文五符序经》为“今人或作三卷”。因此,共36卷。
(4)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表》称:“然即今见出元始旧经,并仙公所禀,臣据信者,合三十五卷。”所谓“并仙公所禀”,这里的“并”是指再加上“仙公所禀”的“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即“新经”。陆修静认为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经典中真正可信的,加在一起为35卷。根据我们前面的考证,“新经”和“旧经”共35卷,是指“今分成二十三卷”的“元始旧经”,再加上分成十二卷的“新经”。此与敦煌本《灵宝经目》所称“都合前元始[旧经],新旧经见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为三十五卷”相符合。
六、结论
有关古灵宝经的出世年代,一直是近三十多年来国际道教学界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灵宝经研究者群体的扩大,相关争议和分歧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在越来越扩大。在相关讨论中,敦煌本《灵宝经目》本身的结构及其成立年代具有最为关键的意义。在目前和未来不可能有更多新材料发现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更加重视对现有文本资料的深入解读和内在理解。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早在公元437年陆修静编撰《灵宝经目序》和《灵宝经目》之前,古灵宝经的创作者实际上就已经编制了最早的经目——《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这个经目与《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等一批最早的“元始旧经”的创作基本上是同时完成的,并且是按照“十部妙经三十六卷”的结构来设计的。在古灵宝经的创作者看来,“元始旧经”在名义上均为元始天尊所说,而且均由《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直接演化而来,因而具有“新经”所远不能比拟的神圣性和崇高地位。而《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的存在,也证明“元始旧经”在本质上是一批具有统一性经教体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经典。而相关“篇目”则代表它们在阐述灵宝经教体系中承担不同的使命,因而每一部经书的内容和侧重点虽然有较大的不同,但是在一些最根本性的教义思想等方面却又是相同和相通的。《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既是陆修静《灵宝经目》中《元始旧经紫微金格目》的直接来源,也是陆修静在公元437年完成甄别和整理“元始旧经”最主要的依据。陆修静对“元始旧经”的甄别和整理,一方面是依据这个经目对真伪混杂的“元始旧经”进行去伪存真,另一方面则明确标明各部“元始旧经”之“已出”和“未出”的状况。至于古灵宝经“新经”在本质上应是对所有“元始旧经”的诠释、补充和进一步发展。除了《太上灵宝五符序》之外,“新经”的出世一般都是在“元始旧经”之后。
我们的讨论也证明,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中所说的《灵宝经目》,其实就是指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这两个文本之间具有内在的不能分割的关系。而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最核心的教义思想具有高度的连贯性。与陆修静《灵宝经目序》一样,敦煌本《灵宝经目》亦作成于刘宋元嘉十四年(437)。而《灵宝经目》所著录的所有“元始旧经”和“新经”,其最晚成书也应在元嘉十四年之前的刘宋前期。而且,现存敦煌本、《道藏》本由陆修静本人所撰写的多部经书,其内容大都是在大量而直接地征引古灵宝经的基础上形成的。陆修静本人及其身边的道士们都属于古灵宝经的信奉者,并未直接参与过古灵宝经的创作。同时,我们还认为“元始旧经”和“新经”均为“葛氏道派”所创作。该经目中“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划分,保存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本来面目。陆修静并未“变更”相关古灵宝经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