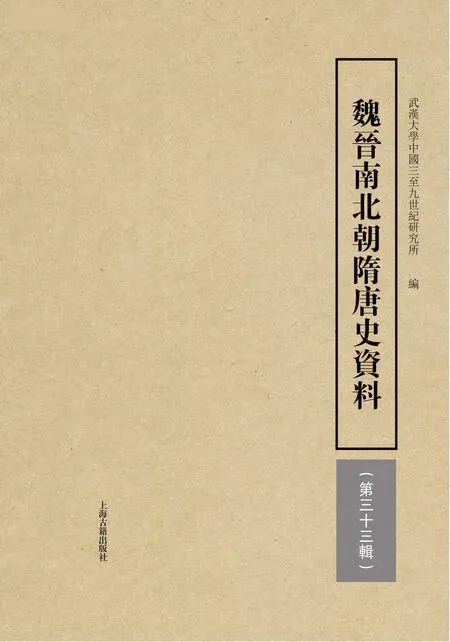“西人”與“東人”
——讀南朝史劄記
2016-02-02胡寶國
胡寶國
“西人”與“東人”
——讀南朝史劄記
胡寶國
侯景之亂後,梁元帝在荆州江陵即位。當時關於建都江陵還是還都建康,在“西人”與“東人”之間曾有一場爭論。這場爭論反映出南方内部的地域問題。
一、 “西人”與江陵
《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
時朝議遷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遷,唯弘正與僕射王襃言於元帝曰:“若束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鄴,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荆、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還都。
“西人”即荆州本地人,“東人”是指王襃、周弘正等從東部建康過來的人。西人希望建都於江陵,而東人則主張還都建康。《周書》卷四一《王襃傳》也記載了這場爭論,可與上條互相補充:
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荆郢。嘗召群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襃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襃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襃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閒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
除刘瑴外,胡僧祐、宗懍、黄羅漢都是“楚人”,也就是前引《周弘正傳》所説的“西人”。蕭繹普通七年(526)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大同五年(539),離開荆州,入爲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547),徙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承聖元年(552)即皇帝位於江陵。他長期在荆州,所以“故府臣寮皆楚人”,他本人“意好荆、楚”也不難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西人”中的重要人物多不是江陵本地人,而是從南陽遷來的。胡僧祐是南陽冠軍人。深得梁元帝信任的宗懍也是南陽人,“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梁書》卷四一《宗懍傳》。推薦宗懍給梁元帝的劉之遴也是南陽人。*《周書》宗懍本傳載,“及梁元帝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劉之遴父劉虯,“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徙居江陵。”*《南史》卷五○《劉虯傳》。劉喬曾參與八王之亂,任豫州刺史,卒于西晉末年。*見《晉書》卷六一《劉喬傳》。又,樂藹,“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梁書》卷一九《樂藹傳》。《梁書》卷一九《宗夬傳》:“西土位望,惟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信。”宗氏、劉氏、樂氏是荆州最著名的家族。他們都是從南陽遷到了江陵。三姓彼此關係密切,牟發松發現,“遷居江陵的南陽舊族間互爲婚姻”。*牟發松: 《漢唐間的荆州宗氏》,載《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社會與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0頁。
關於永嘉之亂後南陽人遷居江陵,陳寅恪早有關注。他説:“南陽及新野之上層士族,其政治社會地位稍遜於洛陽勝流如王導等者,則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業,而遷至當日長江上游都會江陵南郡近旁一帶。至江左政權之後期,漸次著稱。及梁元帝遷都江陵,爲此集團最盛時代。”*陳寅恪: 《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氏著: 《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3— 65頁。因文章主旨不在於此,故陳氏對此未深究。
關於南陽,我曾撰文指出東漢的南陽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南方的荆州,但在文化上卻屬於中州。南陽士人與汝潁名士爲代表的中州士人關係非常密切,毋寧説,南陽士也是中州士。*胡寶國: 《南陽士與中州士》,載《北大史學》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南陽與汝南、潁川屬於當時最重要的地區。
東漢都城在洛陽。就距離洛陽遠近而言,荆州與揚州相比並不差,荆州最北端的南陽更不必説。但是從孫吴在建業立國後,局面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孫氏父子出自吴郡,他所依靠的勢力主要來自揚州的吴、會地區,特别是吴郡。陸凱説,“先帝外仗顧、陸、朱、張。”*《三國志》卷六一《陸凱傳》。《世説新語·賞譽》注引《吴録·士林》:“吴郡有顧、陸、朱、張,三國之間,四姓盛焉。”與之相比,荆州在政治上處在了邊緣地位。建安二十四年孫權平定荆州,“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陸)遜上疏曰:‘……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三國志》卷五八《陸遜傳》。從以後的情況看,陸遜的建議並没有什麽實際效果。
西晉平吴後,南人仕途受阻。華譚建議:“吴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晉書》卷五二《華譚傳》。以後被吸納到洛陽的“南士”如陸機、陸雲、顧榮、賀循、孔愉、張翰等重要人物均來自揚州。著作郎陸機上疏推薦賀循説:“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晉書》卷六八《賀循傳》。荆州竟“無一人爲京城職者”,可見在政治上不受重視。如上所述,揚州的吴人是孫吴朝廷所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所以西晉朝廷考慮政治上籠絡江南舊政權人物也自然是以吴人爲主,而無須顧及荆州士人。東晉建都於建康,朝廷在政治上關注的重點依然是揚州的吴人。《晉書》卷六五《王導傳》載,北人初到江南,吴人不附,王導稱:“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吴會風靡,百姓歸心焉。”《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荆、揚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閫外。”《宋書》卷五一《劉義慶傳》:“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强,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荆州的價值主要在軍事上,“地”雖重要,但“人”並不被重視。
永嘉之亂後遷居江陵的南陽士因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建康,在政治上已經邊緣化了,遠不能與東漢時期相比。東漢的南陽士雖然籍貫屬荆州,但實際上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而到了江陵的這批南陽士隨着時間的推移,終於變成了真正的荆州土著。
江陵距離建康相當遥遠,“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宋書》卷三七《州郡志》。從江陵至建康需要多少時間,史無明文。據何德章考證,從建康溯流而上至江陵,平均日行60—90里,全程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何德章: 《中國經濟通史》第三卷第三章《城市與交通》,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5頁。因爲距離太遠,在江陵的人們不可能像三吴人士那樣輕易地往來於本鄉與建康之間。這是宗懍等西人不願意還都建康的主要原因。*“西人”中也有個别人建議還都建康。《隋書》卷七八《庾季才傳》:“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他建議梁元帝不要久留荆州:“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
按前引陳寅恪文,遷居江陵的南陽人“至江左政權之後期,漸次著稱”。這與齊梁時期一批在江陵的南陽士去了建康有關。宗夬,齊代“舉郢州秀才,歷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梁初宗夬官至“五兵尚書,參掌大選”。*《梁書》卷一九《宗夬傳》。樂藹,天監初官至御史中丞。*《梁書》卷一九《樂藹傳》。他們都長期生活在建康。劉之遴父劉虯,齊國子博士,之遴也是自幼生活在建康。*《梁書》卷四○《劉之遴傳》。討論南陽士,不能不提到庾信。庾信家族也是出自南陽。庾信八世祖庾滔隨晉元帝渡江。自此以後庾氏就定居在江陵,但是到庾信父輩,終於離開了江陵。庾信父庾肩吾、伯父庾黔婁、庾於陵都長期在建康任職。侯景之亂前庾信任東宫學士,領建康令。
從以上宗氏、劉氏、庾氏家族的情況看,到政治文化中心的建康去發展十分重要。相反的例證是宗懍。《周書》卷四二《宗懍傳》:
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宫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荆州,……令兼記室。……及移鎮江州,以懍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梁元帝重牧荆州,以懍爲别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爲尚書侍郎。
宗懍長期在荆州本地任職,如果不是梁元帝建都於江陵,他的影響可能很有限。此外,須要强調的是,這些進入建康的南陽人多是在學術文化上有突出表現,政治上遠没有進入權力核心。因此陳氏所説“漸次著稱”,只能在文化的意義上來理解。
侯景之亂後,在建康的南陽人有的選擇了還鄉之路。劉之遴,“避難還鄉,未至,卒于夏口”。*《梁書》卷四○《劉之遴傳》。庾肩吾,“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梁書》卷四九《庾肩吾傳》。庾信,“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台城陷後,信奔於江陵”。*《周書》卷四一《庾信傳》。對於他們來説,還鄉與歸朝是一致的。
二、 “東人”與建康
如同“西人”中的重要人物不是江陵本地人一樣,到江陵的“東人”多數也不是東部揚州地區的土著吴人。力主還都建康的王襃、周弘正都是北來僑人的後代。《周書》卷四一《王襃傳》: 王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梁末,王襃“遷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襃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内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襃以不次之位。襃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襃乃將家西上。”《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 周弘正,汝南安城人,“晉光禄大夫顗之九世孫也。祖顒,齊中書侍郎,領著作。父寶始,梁司徒祭酒。”梁元帝在江陵遣使迎之,“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授黄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與王襃、周弘正類似,當時去江陵的如顔之推、王固、王通、王勱、殷不害、柳裘等也都是北來僑人的後代。這是有歷史原因的。永嘉之亂後追隨司馬氏南來的北方高層人物大多世世代代生活在建康,死後也大都葬在建康或附近地區,雖然不放棄舊籍郡望,但事實上建康已經成了他們唯一的居住地。《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 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梁末他已經預感到即將天下大亂,但“不知何所逃之”。他的困惑反映了建康僑人在地方上没有鄉里可以回歸的處境。因此之故,當梁元帝新朝出現後,他們自然要去江陵。但是比較而言,他們更願意回到世代居住的建康。所以當梁元帝徵求意見時,這些“東人”明确要求還都建康。
西去江陵的“東人”中也有揚州三吴地區的土著士人,如沈重、姚僧垣。《周書》卷四五《沈重傳》:“沈重字德厚,吴興武康人也。……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周書》卷四七《姚僧垣傳》:“吴興武康人,……及宫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吴興。……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
與沈重、姚僧垣不同,多數在建康的三吴士人並没有西去江陵,而是逃回了家鄉。吉川忠夫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他分析説,“大概是因爲他們在鄉里擁有某些生活的基礎。”*吉川忠夫: 《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0頁。我同意這個意見,即使後來去了江陵的姚僧垣也是先回到了家鄉。此外,我曾注意到,六朝時期南方土著不論死於何地,最終往往還是要歸葬家鄉。*胡寶國: 《從南京出土墓誌推論東晉南朝僑舊之别》,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5頁。結合兩個方面,可以認爲儘管有些吴人任職建康,但與本鄉本土仍然有着密切的聯繫。與“西人”不願意離開荆州一樣,他們也不願意離開家鄉太遠。這是在江陵朝廷中很少見到吴人的主要原因。吴人不願意西遷是一向如此的。《三國志》卷六一《陸凱傳》:“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引謡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武昌尚嫌遠,更遠的江陵自然不必説了。
關於本節討論的“東人”,胡三省在《通鑑》注中解釋説:“周顗、王導自南渡以來世居建康,故謂爲東人。”*《資治通鑑》卷一六五元帝承聖二年。他的解釋固然不錯,但是他没有意識到“東人”這個相對於“西人”而來的稱謂本來也應該包括東部地區的土著居民的,從而失去了進一步思考的動力。
六朝建都建康對東部地區的土著有極大的方便,以三吴爲例,吴郡“去京都水六百七十”,吴興“去京都水九百五十”。會稽雖然稍遠,“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但這也比江陵距離建康近多了。*《宋書》卷三五《州郡志》。《宋書》卷九四《恩倖傳》載: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吏傳署,入爲尚書倉部令史。”《南齊書》卷五六《倖臣傳》吕文度:“會稽人。宋世爲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類似戴法興、吕文度這樣的來自三吴地區的小手工業者、小商販在建康很多。這使得他們有機會接近上層權貴。周一良先生曾發現,南朝寒人多是本地土著。他解釋説:“帝王欲引進寒人爲親信自難求之於畿甸以外,揚州僑人本不多(1.5%),南徐州幾占其半(53.63%),數不爲少,然僑人中高門甲族本多於凡庶,建康附近之僑民尤爾。……於是土著寒門得進之機緣自較僑姓寒人爲多,如《宋書·恩倖傳》《南齊書·倖臣傳》所載十六人中,除宋於天寶先世胡人外,十五人皆出於丹楊、會稽、吴興諸郡,其明證也。”*周一良: 《南朝境内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 中華書局,1963年,第66頁。作者着眼點在僑、舊兩個方面的差别。但是若從荆、揚二州相比較的角度看,又可發現這些寒人幾乎没有來自荆州的人。這當是因爲路途遥遠,荆州的寒人很難像揚州的寒人那樣大批湧入建康。
三、 陳 代 僑 人
劉師培論及陳代文學稱:“然斯時文士,首推徐陵、沈炯,次則顧野王、江總、傅縡、姚察、陸瓊、陸琰、陸瑜,並以文著。”*劉師培: 《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五課“宋齊梁陳文學概略,丙陳代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3頁。在這個名單中,除了徐陵、江總、傅縡之外,其他人都是土著吴人。這個局面是侯景之亂造成的。《太平寰宇記》卷九○《江南東道二·升州》引《金陵記》:“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餘户。西至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東西南北各四十里。自侯景反,元帝都於江陵,冠蓋人物多南徙。洎陳高祖復王於此,中外人物不迨宋齊之半。”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去江陵的“冠蓋人物”基本是建康的僑人。除個别人物如周弘正得以突圍逃脱外,*《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及江陵陷,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大多數人都隨着江陵政權的崩潰而被强行遷至北方關中地區。
徐陵、江總、傅縡都是因特殊原因而留在了南方。徐陵,太清二年出使北方。《陳書》徐陵本傳稱:“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陳書》卷二六《徐陵傳》。徐陵未能南歸,但其家人還是去了江陵。徐陵本傳附子徐儉傳稱:“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幼避於江陵。”*《陳書》卷二六《徐陵傳附徐儉傳》。江總的情況也比較特殊。他是濟陽考城人。建康陷落後,他没有去江陵,而是“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這大概是因爲他的先輩在東晉時曾在會稽置業。但是祖上的産業早在劉宋元嘉時已改建爲龍華寺,他只能暫停於此,不久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後,“征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内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給總行裝。會江陵陷,遂不行”。*《陳書》卷二七《江總傳》。可見江總雖然最初没有去江陵,但最終的政治歸宿還是在江陵。傅縡是北地靈州人,“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毁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陳書》卷三○《傅縡傳》。他也是因爲不在江陵而免遭北遷的命運。
在劉師培開列的陳代著名文士名單中,南方土著士人顯得很突出,這固然體現了土著吴人在學術文化上的進步,但這也與僑人的去留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徐陵、江總、傅縡這些人不是因特殊原因而僥幸留在了南方,土著吴人會更突出。相反,如果庾信、王襃、顔之推等人没有去北方,那麽土著吴人肯定不會顯得這樣突出。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
2016年7月,16— 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