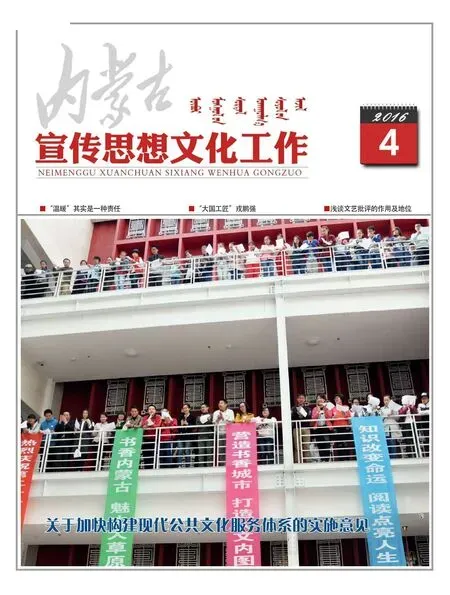浅谈文艺批评的作用及地位
2016-02-02尚贵荣
■文/尚贵荣
浅谈文艺批评的作用及地位
■文/尚贵荣
关于文艺批评的重要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是这样表述的: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总书记的表述简明扼要,但说明了文艺批评的份量。尤其是“引领”二字明确地为文艺评论定位。既为引领,就要走在前头,站在高处。在中国悠久的文学、艺术创作进程中,优秀的先进的文论主张、文艺批评一直参与其间,没有缺过位,而且总是站在制高点上指导引领文艺创作,并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中国最早的文论主张出现在《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涉及诗歌与音乐创作。历代批评家对这一主张多有解释和发挥。这一理论对古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它鼓励作家在作品中真实反映生活,写出真情实感,直言无讳,抨击时弊,对于阻抑浮靡庸俗的创作倾向和形式主义文风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一主张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不过它发表的时间距今至少有三千年了。仅仅是对古代诗歌和音乐创作现象的客观表述,还未进入自觉的批评状态。
中国古代真正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出自孔子。在《论语》中,孔子的文艺批评论述很多。比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等,孔子的文学批评主要体现在《诗经》中,因为那时文学创作远没有他的后代和我们今天这么丰富。
在孔子的众多文学、音乐和绘画的批评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指的是文学的创作方法,具体为引譬连类,抒发情志;观,指的是通过读“诗”,可以提高人的观察识别能力,观风俗,考得失,辨真伪;群,指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教化凝聚人心,群居切磋,使人心向上向善;怨,指的是诗人通过诗歌作品发表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以诗为器,讽怨时政风俗。兴观群怨,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批评主张,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命题。它的重要性在于连续不断地影响了中国二千五百年的文学创作实践,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另一个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是“文以载道”。这个思想的雏形始于先秦,经过一千余年文学家批评家的阐释、发挥、提炼,最终定形于宋代。欧阳修说文与道俱。周敦颐则明确地说文所以载道也。从周敦颐的角度来看,他所说的“道”就是儒道,他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坚定捍卫着儒家道统。但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则不必拘泥于此,它可以是宇宙运行、自然运行的天道,也可以是社会发展或治国理政之道。“文以载道”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实践影响之重不亚于兴观群怨。
以上两说,是先举其大者。从孔子到近代的漫长的文学批评过程中,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论述连绵不绝,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都曾起到过积极的指导作用。比如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以意逆志”说,宋玉“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说,《文心雕龙》的“神思”“夸饰”“通变”“六义”“体性”等主张,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意象”说,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说,陆游的“功夫在诗外”,苏东坡的“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不可不止”,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说,清代沈德潜的“格调”说,等等。另外,还有大量的文论学说散集在具体的文学作品、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门类的创作理论以及卷帙浩繁的诗话、文人笔记中。比如宋代三大文人笔记《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和《困学纪闻》,内容宏富,见识独到,文字优美,其中包含着许多非常有见地的文学艺术主张,为同代及后世文人学者所称道。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阅读《容斋笔记》,并做了大量批注。
孔子以降至清代,除“文以载道”做了较详细的解读外,其余只是罗列例举。但近代的大批评家王国维不能不说,他的《人间词话》是一座文学批评的高峰,一个里程碑,一个划时代之作,无法越过。《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唐宋至清代的词的批评与鉴赏的专门著作,王国维的文学主张与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这本书里。他的批评与鉴赏,见识深邃,表述精确,文字有力,境界高远。在我国漫长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叫“意境”,它指的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是情和景意与境的交融,是客观和主观的融汇统一,能够形成鲜明的艺术形象并由此获得艺术感染力。它涉及到文艺创作中的虚与实,有限与无限,个别与一般的统一问题。这个主张由来已久,从先秦一直到宋元明清,经过无数代文艺家文艺批评家的提炼总结,到了王国维,在前人提炼总结并实际使用的基础上,归纳提升为“境界”说。《人间词话》的第一句即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接着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用“境界”学说观照总结唐宋词的同时,王国维最后将他的学说这样概括:“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至此,他的“境界说”仿佛蝉蜕龙变一般,由小变大,由单一至复杂,从专门的词学美学范畴中升华而起,成为可以评价概括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一个标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王氏说“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也就是说,他在总结概括的时候,所注意的是那些久经历史检验的“大词人”之作。这些“大词人”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不断流传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总是能够从普通人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和客观事物中抽取出有价值的人生经验来。这些“经验”也许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但一般人往往视而不见,或者即使见到了,又无法用文字来作出表述,无法道也。而大词人做到了。这就是文学或文字的力量所在。真正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这种力量。王国维更了不起,他站在这些大词人的肩膀上,为后人奉上了“三境界说”。
以上仅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引领文艺创作的一些概要性的例证,在世界范围内,文艺批评引领文艺创作亦不乏其例。比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理论对苏联戏剧、中国戏剧甚至世界戏剧表演及创作的影响。比如别林斯基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批评,涉及到那个时代俄罗斯一批重要作家,如果戈理、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确立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的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莱辛的诗学美学名著《拉奥孔》和戏剧理论名著《汉堡剧评》对于德国以及世界十八世纪以后的诗歌、美学以及戏剧创作的影响,十分深远。当时的歌德毫不讳言《拉奥孔》对包括他在内的德国一代年轻作家的影响力:这部作品把我们从一种可怜的静观境界中拉出来,引进爽朗自由的思想境界;这个美好的思想连同他一切的推论像闪电一样照亮了我们。海涅称“莱辛是德国文坛的阿米尼乌斯,他把我们的戏剧从异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歌德、席勒“思想中一切健康的东西都是莱辛提示给他们的。”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代相传接,无有竟时。这已经足以证明文艺批评及文艺理论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和它的地位,足以支撑文艺评论家们理直气壮地站立在文艺实践的潮头和前沿,当仁不让,指点臧否,论说品评,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文艺批评的地位问题,本来是早已经在漫长的文艺创作实践中确立下来的,不容置疑。现在之所以旧话重提,不厌其烦地去解释论证,是因为现在的文艺批评出了问题。问题有三:
第一,批评精神的缺失。关于这个问题,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称,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这段话中列举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批评领域。境界低下,衰弱无力,敢怒而不敢言,患得患失,无原则的吹捧,是笔者对这种现象的补充。
第二,文艺批评家自身修养的不足导致批评乏力。文艺批评家应该是兼容并包,学识广博的通才。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应该在自身关注的领域通贯并旁及与该领域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古今大批评家无不如此,孔子自不必说,刘勰、钟嵘 、苏东坡、欧阳修、白居易、韩愈、王应麟、洪迈、王国维、鲁迅、钱钟书等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国学皆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后才能有鉴赏鉴别能力,才能有区而别之的眼光,才能在丰富广阔的文学艺术之海中寻找到规律,也才能站在高处,高屋建瓴,引领文艺。一星半点,东鳞西爪,吉光片羽,难免生搬硬套,难免力不从心。我所说的修养,其实不仅指学识,仅仅学识渊博还不够。还应该包括鉴赏能力、境界、品格、胆识、责任心、使命感等诸多元素。只有这样,才能见出一个批评家的修养来,有了这个修养,才能秉持批评精神。
第三,“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说对于文艺批评的影响。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对于文艺批评和文艺的关系,有这样一个表述: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坦率而言,这个表述看似形象,但这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述,它降低了文艺批评的品格和地位,与今天大力倡导的重振文艺批评精神的现实要求不适应。文艺批评应该是旗帜,是号角。文艺批评走在文艺前面引导鼓舞文艺前行,是其使命之所在。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