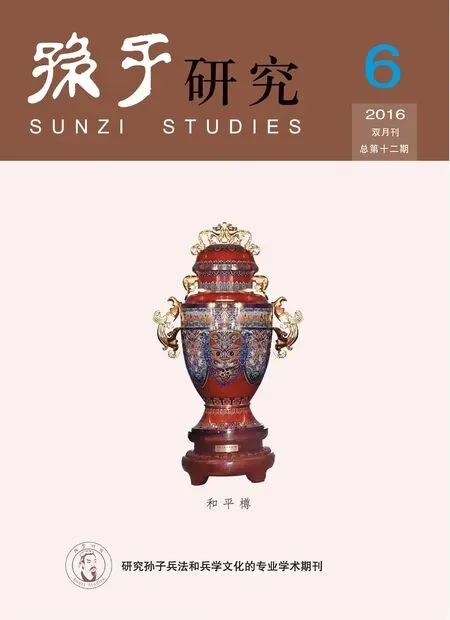从《孙子兵法》视角解读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2016-02-02阎盛国YanShengguo
阎盛国/ Yan Shengguo
从《孙子兵法》视角解读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阎盛国/ Yan Shengguo
汉武帝是一位知识复合型政治家,他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既受儒学的浸润,也受神仙道术的熏陶,还受《孙子兵法》的影响。汉武帝的知识结构属于“金字塔”模式,而独特的兵学素养,使他在内外斗争中如虎添翼。对内,汉武帝在与赵王刘彭祖较量当中巧妙应用《孙子兵法》制胜对手;对外,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以《孙子兵法》智者行事的标准考虑重大问题,取得受降匈奴浑邪王的重大胜利。汉武帝灵活应用《孙子兵法》“造势”思想,对匈奴造成强大心理攻势,震慑了对手。由此而言,《孙子兵法》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提供了智慧源泉,为缔造汉武帝的伟大功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汉武帝 雄才大略 《孙子兵法》 影响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人所共知,但汉武帝巧妙应用《孙子兵法》战胜许多对手的事迹,却鲜为人知。综观学界对汉武帝的研究,应该说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只是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视角进行的,很少有人关注汉武帝的知识结构。①即使专门研究汉武帝军事思想的学者,也未从中发掘汉武帝知识结构中的《孙子兵法》这一特殊兵学素养。本文正是立足于此,并以此作为研究汉武帝的一个重要视角,重新审视汉武帝对内政治斗争与对外军事斗争中究竟如何巧妙地应用《孙子兵法》,从中分析《孙子兵法》是如何为其伟大功业不断增添砝码的。
一、汉武帝知识结构中的《孙子兵法》
知识结构,是指一个人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与组合方式。②从知识结构的整体性考察,汉武帝的知识结构具有多元性的特点:
一是受儒家文化的浸润。
这主要是受他的老师卫绾的影响:“上(汉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召(卫)绾拜为太子太傅。”③卫绾表面上奉行黄老之术,但实际上却推崇儒术。这是从其行为做出的判断:卫绾在建元元年(前140年)上奏汉武帝:“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④武帝随即采纳其建议。汉武帝在卫绾的引导和辅佐之下,身上显现了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汉武帝的理政表现也是如此。他即位之初,“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⑤。此外,他还“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⑥。“贾生”指贾谊。贾谊是汉初有名的儒生,可惜英年早逝,汉武帝对其充满景仰之情,故而授贾谊之孙以高官厚禄。从“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到任用“文学之士”公孙弘为丞相,再到采纳大儒董仲舒的主张,以儒术作为治国思想,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反映出汉武帝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
二是受神仙道术文化的熏陶。
这主要来自其祖母窦太后潜移默化的影响。窦太后喜欢黄老道家之术。早年的汉武帝生活在祖母身边,无形中受到窦太后的影响,故而他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对神仙道术文化异常迷恋。史载,“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⑦。又载,方术士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⑧。汉武帝还相信齐人公孙卿“黄帝且战且学仙”⑨的话,并任命公孙卿为朝廷中的郎官。这些记载都表明,汉武帝对神仙道术文化有着执着的向往与追求。
三是受《孙子兵法》的影响。
武帝对《孙子兵法》的喜爱与韩嫣有很大关系。韩嫣字王孙,是弓高侯穨当的孙子。当年,汉武帝身为胶东王时,韩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聪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⑩。从这一史料可以看出:汉武帝与韩嫣是同窗同学,两人亲近友爱。而韩嫣擅长骑射,精通军事,深受武帝的尊崇。汉武帝研习《孙子兵法》,很可能是韩嫣引导的结果,因为《汉书》明确提到韩嫣“先习兵”。其时,韩嫣为了迎合汉武帝的志向和兴趣,提前研习了《孙子兵法》。汉武帝步其后尘,也学习掌握了《孙子兵法》。
不论是韩嫣引导的结果,还是汉武帝自学的结果,汉武帝研习过《孙子兵法》这一论断,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因为,史书中有两个重要的证据可以证明汉武帝研习过《孙子兵法》:
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汉武帝曾向爱将霍去病推荐《孙子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这则史料提及汉武帝推荐的“孙吴兵法”,分别是指《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学界以往对这则史料的解读,多是站在霍去病的角度,强调不学古兵书也可打胜仗。本文立足于汉武帝的视角解读这则史料,它却是揭开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一个“教”字的信息表明,汉武帝研习过《孙子兵法》,并深刻认识到《孙子兵法》的宝贵价值,因而才会将其推荐给自己的爱将霍去病。
另一个证据是,汉武帝曾引用过《孙子兵法·作战》中的“因粮于敌”。具体情况是,元狩四年(前119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五万骑兵,虽然装备与大将军卫青的军队相等,而没有裨将,只以李敢等人作为大校,权当裨将,出击代郡、右北平之地一千多里,但斩获俘虏敌人的功劳,却远超过大将军卫青。军队凯旋后,汉武帝嘉奖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从汉武帝对霍去病此次军事行动的精彩点评来看,他显然认为霍去病采用了《孙子兵法·作战》“因粮于敌”的作战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以“取食于敌”代替“因粮于敌”,当是师其意而用之,是一种间接引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霍去病曾说“不至学古兵法”,但这并不是真实情况,并不能说明霍去病根本就不肯学“古兵法”。理由是,霍去病的个性是“为人少言不泄”,懂得保守秘密。明人梁见孟就认为,霍去病所说的“不至学古兵法”,是“英雄欺人,非通论也”。术兴”。所以,甚至号称“滑稽之雄”的东方朔,也曾研习过《孙子兵法》,并对战争之道颇为熟悉。因为他在上书中就曾说过,自己“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真实的情况是霍去病不愿把研习《孙子兵法》的情况透露给外界与敌人。
汉武帝为何热衷于推介《孙子兵法》?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受那个时代氛围的影响,战国至汉初,儒家文化远远没有兵家文化受世人重视。正如《汉书》所言,“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
不同的知识结构决定吸收知识的快慢、深度和广度以及创造能力的强弱。知识结构的基本模式主要有六种:“金字塔”模式、“网络型”模式、“树状”模式、“T”字型模式、“干”字型模式、“飞机型”模式。从知识结构的基本模式分类来考察,汉武帝的知识结构属于“金字塔”模式。具体而言,宽阔的塔基是“儒家文化”,较大的塔身是“道家文化”,尖细的塔顶是“孙子兵学文化”。《孙子兵法》作为当时军事文化的前沿,居于汉武帝整个知识结构的最高端,在其知识结构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相关研究认为,具有“金字塔”模式知识结构的人士,头脑灵敏,思路开阔,基础宽厚,有很强的创造性,甚至会做出重大的理论突破。所以,独特的多元性知识结构,使汉武帝不仅在思想领域独树一帜,而且在国内政治斗争和对外军事活动中受益匪浅。
二、汉武帝在政治斗争中应用《孙子兵法》
汉代有位特殊的历史人物赵王刘彭祖(前166~前92年),他在诸侯王位上的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几乎历经整个景帝、武帝主政时期。他所在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汉代中央政府着手解决同姓诸侯王国问题的时间节点上。身为赵王的刘彭祖,自然不能置身“局”外,曾为赵国政治管治权与中央政府展开过激烈较量。
赵王作为汉武帝的“同父异母”之兄,具有独特的多重性格:一是奸诈机巧;二是谄媚逢迎;三是内心严酷;四是喜好法律;五是善于诡辩伤人。他的这种个性,使其曾在众多场合击败对手。赵王“奸诈机巧”的个性容易欺骗对手;“谄媚逢迎”的个性容易让对手获得好感,使之放松警惕;“善于诡辩”的个性却使之在是非面前能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喜好法律”的个性使之只讲法,不讲情,以法绳人;“内心严酷”使之总是置对手于死地。赵王个性极其邪恶,具体表现就是:凡被中央派到赵国监督其政务的国相和二千石官员都受到了他的陷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甚至,路过赵国的朝廷使者也都提心吊胆,不敢停留:“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郸。”因此,赵王彭祖治下的赵国,俨然成为中央政府的法外之地,不受朝廷任何约束。
汉武帝在与赵王的斗争中,又是如何巧妙应用《孙子兵法》来制胜对手呢?在汉武帝看来,赵王彭祖之所以能以全力抗衡中央,并拥有独立自主的政治管治权,关键在于以赵王彭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彭祖利用自己的财富,随心所欲地收买人心,培植个人势力,并且早已把触角伸向中央。赵王的野心终于引起了汉武帝的警觉,他决定铲除这一游离于中央之外并对中央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于是,汉武帝采用《孙子兵法·九地篇》“先夺其所爱”的战术,“避实击虚”,开始行动。
《孙子兵法》中的“所爱”,其含义是指具有重要影响的战略因素,包含四个属性层面:一是重要的战略区域;二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三是重要的依靠力量;四是重要的精神象征。在汉武帝看来,“太子丹”就是赵王彭祖之“所爱”,是他重要的依靠力量,因而他借江充告发之机,果断行动:“遣使者发吏卒捕丹,下魏郡诏狱,治罪至死。”太子丹“下魏郡诏狱”时,赵王彭祖“上书冤讼丹”,表示“愿从国中勇敢击匈奴,赎丹罪”。后来,他又入朝“因帝姊平阳隆虑公主,求复立丹为太子”。由此不难看出,汉武帝的判断是准确的。
经过这一回合的较量,赵王彭祖心理遭受沉重打击,他再也不敢与中央政府对抗了。这样,赵国政治管治权终于被汉武帝成功地收归中央政府。
三、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应用《孙子兵法》
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应用《孙子兵法》成效显著,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战争中,汉武帝能以《孙子兵法》智者行事的标准来考虑重大问题。
《孙子兵法·九变篇》云:“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即智者行事时,要把“利”与“害”统一起来考虑。因为,考虑“利”可坚定信心和信念,考虑“害”可采取预防措施来消除祸患。曹操注云:“在利思害,在害思利。”这无疑抓住了孙子思想的精髓。汉武帝能够成功地接受匈奴浑邪王的投降,就在于他是以《孙子兵法》智者行事的标准来考虑问题的。
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单于因为浑邪王、休屠王所守之地被汉军杀虏数万人,故要将二人加以诛杀。浑邪王与休屠王感到忧惧,便谋求投降汉朝,并派使者在边境遮拦汉人,通报了汉朝。史载,“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可见,汉武帝在获知浑邪王、休屠王想要投降时,面对突如其来的“利”,并没有忘乎所以,相反却担心匈奴利用诈降袭击汉朝边境。
为保证受降的安全,汉朝做了充分精神准备和军事准备:第一,汉武帝选择最具实战经验和指挥能力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作为此次受降活动的全权负责人;第二,汉武帝让霍去病全副武装率军前去进行受降活动。从史实记载看,受降活动开始时,浑邪王手下许多裨将内心感到恐惧,发生动摇,有些人甚至要逃跑:“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面对受降活动发生的突然变故,霍去病异常镇静,随即与投降的浑邪王取得联系,“骠骑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果断采取措施,“斩其欲亡者八千人”, 并对浑邪王与匈奴降军采取“ 分而治之”的办法,从而控制住了随时有可能发生重大变故的局面。
此次受降虽一波三折,但最终取得圆满成功,关键在于汉武帝以孙子智者行事的标准去考虑受降问题。汉朝政府成功受降,带来巨大的胜利成果:“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汉匈边境赢得了少有的安定局面:“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二是汉武帝把孙子的“造势”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最能展示汉武帝善于“造势”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接。史实中提到的“二万乘”这一数字,耐人寻味,值得关注!“对敌宣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造传递暗示给敌人的方式和手段。”汉武帝不失时机而又巧妙地利用浑邪王投降作为“宣传素材”,制造出“规模浩大”的汉朝礼遇声势。
汉武帝所造“声势”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妨大略估算一下。黄志禄在《资阳日报》发表的《中国汉代第一车——资阳铜车马完成修复》一文,为我们提供了汉代一个车辆的标准长度:2005年12月21日,在雁江区雁江镇资溪村出土的资阳汉代青铜车马,被誉为“中国汉代第一车”。而整个铜车马修复后,铜马残高114厘米(马头暂缺),宽51厘米,长117厘米,重41.5公斤。铜车长133厘米,宽104厘米,宽87厘米,重47公斤。铜车马组装后长184厘米。值得注意一点是,资阳地区出土的“铜车马组装后长184厘米”,这大致是汉代车马的标准长度规格,便于参照,为计算汉武帝用车“二万乘”的总长度,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数据:184×20000=3680000厘米=36.8公里。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计算车与车之间的距离,汉武帝竟然是以36.8公里的车队前去欢迎匈奴人投降。如果每辆车间隔100厘米,那么这个车队的总长度则变为3680000+100×19999=5679900厘 米 =56.799公里=103.598里。这意味着汉武帝是以“百里”长的车队迎接浑邪王投降。
汉武帝的这一“出奇”行为,不仅符合贾谊主张向匈奴人“谕陛下之爱”。同时,借迎接浑邪王降汉车队隆重场面不仅表达了自己欢迎匈奴人归附,而且巧妙表达了愿意招降匈奴军民的潜在用意。汉武帝“少而聪明有智术”,确实不枉其名。“善于将自己的观点和倾向性隐含在精心选择的新闻事实里,这样的人被认为是高明的宣传家。”从这一点来看,汉武帝的确是非常善于“造势”的高明“宣传家”。
第二件是汉武帝亲自“勒兵十八万”巡边,扬言要与匈奴寻求决战。孙子“造势”思想强调,要善于运用已有的力量,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宏大态势。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诏告匈奴:“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汉武帝随后亲自巡边,作出要与匈奴单于决一雌雄的姿态,整个行程很长:“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汉武帝所造的声势是如此的浩大:“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十八万骑”与“千余里”,点明这种声势前前所未有,大大超过先前迎接匈奴浑邪王降汉时“造势”的规模,是其“十倍”。由于匈奴多次遭受过汉军沉重打击,故而汉武帝这一行动,很好地达到了震慑匈奴的效果。史书明确记载,汉武帝此行是“威震匈奴”。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派使者郭吉正告匈奴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尽管郭吉劝说匈奴臣服汉朝的行动最终没有成功,但汉武帝通过汉军强大的军事声势威慑了匈奴。汉武帝这种“造势”行为带来了积极效果:“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汉武帝这两次“造势”活动,做得有声有色,在取得绝佳效果的同时,也体现出“造势”的四大原则,即:一是要以实力为依托;二是要有“奇异”性;三是要有可操作性;四是要选择好事件、时机与策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对汉武帝影响非同寻常,为他缔造伟大功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而这与汉武帝多元性的知识结构有着密切关系。
在汉武帝的身上,体现了“外儒道,内为兵”的个性特质。他借助儒家文化和道家神仙文化作掩护,暗地里却在应用《孙子兵法》,从而让他的对手无法正确判断他的决策与行动。至于霍去病不屑学习《孙子兵法》,则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让更多的人远离《孙子兵法》。这样就人为地降低了《孙子兵法》的影响力,再加上汉朝一度禁止《孙子兵法》在民间的传播,从而使“《孙子兵法》在社会上的公开地位受到压抑” 。如此一来,就为汉武帝应用《孙子兵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使《孙子兵法》成为他制胜众多对手的一个重要法宝,而对手却始终没有机会去掌握这一法宝。汉武帝的对手由于缺乏当时这种极为高端的兵学素养,自然在个人知识结构上不占优势,从而为他们决策水平趋低定下了基调。
总的来看,汉武帝不仅是汉朝历史上第一个对《孙子兵法》深入学习并用于实践的帝王,而且也是应用《孙子兵法》最卓有成就的一位帝王。他之所以具有雄才大略并能够建立不朽业绩,显然与《孙子兵法》为之提供了重要的智慧源泉有关。
注释
①陈梧桐:《西汉军事史》,《中国军事通史》(第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王咏红:《青年干部修养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5页。
③《汉书·卫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01页。
④《汉书·武帝纪》,第156页。
⑤《史记·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52页。
⑥《史记·贾生列传》,第2503页。
⑦《史记·孝武本纪》,第451页。
⑧《史记·孝武本纪》,第453页。
⑨《史记·孝武本纪》,第468页。
⑩《汉书·佞幸传·韩嫣》,第3724页。
(责任编辑:李兴斌)
Interpreting the Great Talent and Bold Vision of Emperor Hanwu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rt of War
Emperor Hanwu was a politician with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He was influenced by many kinds of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The Art of War . Emperor Hanwu’s knowledge structure is like a pyramid mode. His unique military science cultivation made him powerful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ggles. Internally, when combating with Liu Pengzu—King Zhao, Emperor Hanwu flexibly utilized The Art of War to defeat his adversary. Externally, in the war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Hun, with the standards of The Art of War , Emperor Hanwu considered the important events and eventually won a victory, which made the King Hun Xie of Hun surrender. By flexibly utilizing the thinking of making “energy”, Emperor Hanwu formed a powerful psychological attack on Hun, which frightened the adversary. Therefore, The Art of War provided the source of wisdom for Emperor Hanwu’s great talent and bold vision and rendered energetic contributions to him to build up a great cause.
Emperor Hanwu; Great Talent and Bold Vision; Influence of The Art of War
2016-8-7
阎盛国,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