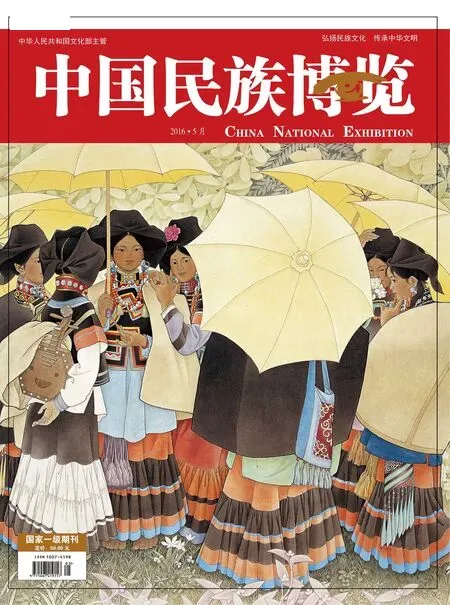《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是谁的错?
2016-02-01王玥
王 玥
(江苏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0)
《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是谁的错?
王玥
(江苏扬州大学,江苏扬州225000)
【摘要】心理学出身的米德后来跟随博厄斯学习文化人类学,米德在博厄斯的帮助下选择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作为范例,向遗传派发起挑战。后来引起了学术界种种争论,其真实性问题也遭到质疑。本文通过对田野、自身、导师这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造成人们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质疑原因,引发在人类学中性别差异的思考。
【关键词】米德;《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博厄斯;田野
一、作者及《萨摩亚人的青春期》
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是为数不多的美国女性文化人类学家之一,也是心理分析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博厄斯门下学习,长期从事以野蛮社会为对象的野外调查,主要研究区城为南太平洋地区,由于米德是心理学出身,所以她习惯将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联系起来,侧重研究人的生理生长阶段、性格、气质等问题。主要著作《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928)、《男性与女性》(1949)、《三个野蛮社会的性与气质》(1935)等。萨摩亚位于中太平洋南部,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一部分,热带雨林气候。萨摩亚群岛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居住,先被荷兰航海家罗捷文发现,随后法、英、德、美相继侵人。
米德选择萨摩亚作为研究对象,并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受到了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米德的本科学习是从德保大学转入巴纳德学院,当时博厄斯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巴纳德附属机构的人类学学院院长,本尼迪克特为其助手。米德因为选修了博厄斯一门人类学的课程,同时真正结识了对她今后研究影响重大的两个人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据米德的记录,正是由于本尼迪克特对人类学浓厚的兴趣再加上博厄斯清楚且引人入胜的课堂讲解,才使她产生了对人类学浓厚的好奇心和兴趣。米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完心理学硕士毕业后,1923年攻读了博厄斯的人类学硕士,就走上了人类学的研究道路,并与博厄斯一起学习工作。博厄斯一直是反对遗传派的领袖,他想通过调查一个与欧美不同文化的国家的青春期来挑战遗传派。而米德是他这个研究计划的不二人选。同时米德也意识到只有拥有自己研究的对象,自己研究的田野才能成为一名有分量的人类学家。博厄斯想让米德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但米德意志坚决的要去南太平洋群岛,为了安全起见,博厄斯安排米德去了南太平洋群岛的美属萨摩亚。1925年下旬,米德开启了她的萨摩亚之路。
1928年《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出版反响很大,读者不仅有同行还有普通大众,同时得到了其导师博厄斯的大力推崇,萨摩亚地区也因此书而出名。在米德去世的第五年,也就是1983年,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写了《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批驳了米德早期的实地研究。他认为米德关于萨摩亚人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萨摩亚不是米德所描述的人类乐园而是一个充满忧郁和矛盾冲突的社会。弗里曼在书中从人类学的“后天与先天”矛盾讲起,随后分别在社会制度、竞争合作、侵犯行为、宗教、惩罚、孩子的抚养、萨摩亚人的性格、性道德与行为、青春期、萨摩亚民族的文化精神这几个方面,提出了与米德截然不同的结论和观点。弗里曼书中所描述的这些方面,涵盖了米德书中的所有方面,弗里曼也遭到了许多批评与指责。两个人都偏向了相对的两个极端,“弗里曼与米德”之争,更是将“先天与后天”之争推向一个高潮。
女人类学家的田野真实性问题:
关于“弗里曼与米德”孰对孰错的问题,就像“先天与后天”的争论至今仍无法解决一样,是无法明确判断的,也不是一个还未出茅庐的学生能评价的,所以笔者在此抛开这个问题。有句很俗的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若米德的研究没有问题,弗里曼也就无话可说,或者至少不会全盘否定米德的研究结果。米德不仅仅是代表她自己,她还代表了人类学界的女性声音,那么她所研究的漏洞若分析其原因(是谁的错?是什么造成了米德研究的结果?),对进行田野工作的女性还是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米德《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中影响其真实性的原因:
(一)田野调查的对象、当地人
1.地点的原始性
米德称萨摩亚人为原始人,但这个原始人早就不原始了,她到萨摩亚的时候,美国已经在萨摩亚殖民了20多年,萨摩亚还有传教士建立的学校。萨摩亚人早在无形中被白人影响了,所以她所选择的这个原始地区的原始是不成立的。而且她在去之前就已经知道萨摩亚地区是美属萨摩亚,她还是选择这里作为田野调查地点,更是想在这里试图证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与美国人的青春期不同,对于一个被美国影响几十年的地方,她选择这里也算是冒险了。
2.白人与原著人的隔阂
米德在研究期间住在霍尔特家,霍尔特是海军诊所首席药剂师,在米德初来乍到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又请她去旗舰赴宴。这些在萨摩亚人看来都是高不可攀的;另外美国在1899年就开始了对萨摩亚的殖民统治,萨摩亚人对于美国白人自然没有太多的好感或存在抵触心理。米德在萨摩亚的调查期处于该地区政局动荡时期,无形中拉远了米德与萨摩亚人之间的距离。
3.当地人说谎的习性
在弗里曼对萨摩亚人的走访中,问到关于米德所问的问题,萨摩亚人竟然说那些女孩子是在戏弄米德,而这种戏弄被他们叫做“塔乌法赛”(说谎、欺骗)。这是一种萨摩人最容易表现的行为,“这是萨摩亚人很爱用来消遣的一种方式,……他们明显表示出不愿意和外来人或当权者讨论性行为问题,在这方面女青少年表现得尤为含蓄、羞于启齿”。面对敏感的问题,萨摩亚女孩很可能就是用说谎来回应米德的。
4.自然灾害
米德在萨摩亚田野调查期间,该地发生了一场强烈的热带风暴,灾难过后,之前调查过的少女也都失去了联系,这对米德调查的连续性影响很大。之前做的调查也无法再从原受采访者中再度确认或证明。
(二)自身
1.住处
因为对原著人住宿环境的厌恶,不利于她搞研究。所以米德选择住在塔乌岛唯一的白人之家——霍尔特的家中,偶尔会去传教士创办的女子住宿学校。在住宿问题上她失去了与原著人朝夕相处拉近距离的机会。
2.知识有限
米德是心理学出身,是在做人类学研究生时候才展开田野工作的,接触人类学的知识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资历尚浅的学生,选择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并将之与美国人的青春期相比较,急于求成地验证了文化决定论的观念。当时她的知识储备还不足以胜任这项研究。在她之前的19世纪,就已经有学者对萨摩亚地区做过研究,包括他们的社会、制度等,她显然没有做足这方面的功课,不然不会与之前学者的调查出入如此之大。米德在决定去萨摩亚与他到萨摩亚开始研究的时间间隔短仅有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她既要准备田野中必要的物资,又要恶补萨摩亚地区的信息,还要学习萨摩亚的语言,所以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
复杂问题简单化:博厄斯布置给米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生物与文化复杂关系的问题,米德由于缺乏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她也坚定地相信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方向的正确性,对文化人类学方向的深信不疑,所以她认为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推翻之前所有的生物决定论者。
3.抽样问题
在米德整个研究中,选择了五六十个女孩子,分别分布在各个年龄阶段,这种分层抽样的方法是科学的,但是这对于生物与文化方面的复杂问题,抽样的数量显然不够详尽。弗里曼在反驳她的书中,单单一个小方面就选了100个左右的人对位调查对象,那么抽样的效度比较也就不言而喻了。
另外对抽样中的个别情况(犯罪),米德认为是偶然现象,25个青少年少女中有4个偶然现象,由于与她想证明的方面相反,所以她选择忽略不计。如果25中有4个,那么50就是8个,250个就是40个……这样的比例,认为是偶然现象是不科学的。又由于她来萨摩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证明博厄斯、本尼迪克特那些观点的正确性,所以可能存在对真相忽略甚至视而不见的情况。
4.女人的身份
这是对米德田野调查影响最大问题,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因为萨摩亚中的有些政治性仪式或会议是不允许女人参加的,所以萨摩亚中关于社会制度的一些问题,她只能从他人口中得知,这就造成了她过分依赖信息提供者,也对信息真伪的验证带来了困难。因为是女人,考虑到安全问题,选择的田野地点不能太原始;因为是女人,对环境的要求相对男人要高,所以没有跟萨摩亚人住在一起。
5.研究时间短
“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调查的时间是1925年8月31日至1926年6月初,3个月在图图伊拉,大约6个月在马努阿。”在萨摩亚地区总共呆了9个月的时间。现代社会人类学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历时约4年才完成了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调查。弗里曼对萨摩亚地区的调查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4年多。相比之下,米德的田野调查时间尚短。但是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类学学生来说,这9个月确实也实属不易。
(三)导师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博厄斯派范例基本定型,其核心“社会刺激比生物机制远为强烈”的假设还没有经过论证。文化与遗传的斗争还在继续,所以博厄斯急需一个证明假设成立的事实。在米德带着丰硕的成果回来时,博厄斯在没有验证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就行了大力推行,没有对米德的调查进行任何科学性的检验。
博厄斯在此阶段的人类学思想因为过分强调文化,所以存在一种极端倾向的可能。这种观念对博厄斯无比崇拜的米德来说,不会对导师有任何的疑虑。“博厄斯给米德提出的人类学上的任务是要去击败有关‘人性遗传是全人类的共性’
的观点。”米德也把这次调查当作是一场与遗传的斗争,能支持导师观点的都会吸取来,有偏差的观点就会当作偶然性而忽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极端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米德关于萨摩亚调查的真实性问题,是多方面造成的。田野、自身甚至是导师都是造成后人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质疑原因。这些方面也是作为学习音乐人类学的我们值得共勉的。
1985年著名的女性研究者Joan Neff Gurney提出:“尽管有很多研究证据显示男性与女性研究者的田野研究经验不同,但是质性研究方法的数据依旧持续忽视田野研究的性别差异。”
在田野工作中,女性研究者有优于男性研究者的特点,比如女性较为温和,能更容易地进入田野,并且可以借助女性优势获得田野资料。但当谈论到田野资料的真实性时,这种优势就不再明显了,女性往往被认为是弱势群体,那么在实际的田野中,被调查者可能觉得女性没有男性的那种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所以也就敷衍几句。这也是我此次进入田野时感受到的,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男性被调查者,他们觉得我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丫头,他们比较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家庭情况等,当聊到关于田野的事项,他们并不会说得太详细,甚至用对或不对来回答。女性研究者会经常帮忙打扫房间、端茶倒水等,他们会夸她们贤惠、懂事之类。但不会对她们田野工作做出评价。还有一些男性会主动与她们搭讪,都是关于有没有男朋友之类的问题,或者要不要去哪里哪里玩。这些都是我在田野工作中真实遇到的。
田野工作中的性别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不是用一视同仁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针对性的计划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彭克宏主编.社会科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2]郝时远,朱伦主编.世界民族第8卷美洲大洋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德里克·弗里曼著,李传家,蔡光曙译.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4]蔡玲.女性在田野调查中的性别处境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
【中图分类号】I106.5
【文献标识码】A